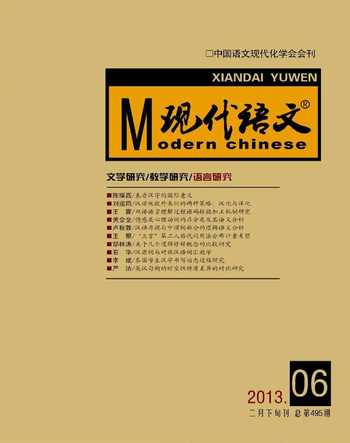浅谈“六书”中假借与形声的次序问题
摘 要:“六书”是中国古代文字学的核心概念,东汉时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对于六书的次序问题,后人认为许慎为六书所定的次序不能反映汉字发展的实际情况。一般认为,“六书”的名称当依许慎,而次序应从班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关于“六书”的次序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论。本文将着重讨论“六书”中假借与形声的次序问题,笔者认为,假借的次序应位于形声之前,而不应位于其后。
关键词:假借 形声 六书 次序
“六书”作为汉语义文字学的核心概念,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指出了“六书”之名:“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继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了“六书”的性质:“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稍后,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中首次给“六书”分别下了明确的定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至此,“六书”开始成为我国古代文字学的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
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时,多依朱宗莱的主张,从许慎“六书”的名称而遵班固“六书”的次序,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文字起源于图画,“画成其物”的象形字最先出现,这毋庸置疑。指事字是在象形字上加指示符号构成,必然出现在象形字之后。会合几个象形符号,综合表意的会意字,也必然出现在象形字之后。“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种构字模式,属于典型的以形表意阶段,对于它们的次序问题,无需过多讨论。然而形声与假借的次序问题,至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首先,从发展历程来说,假借字大量出现于形声字之前。“象形、指事、会意”三书创造的文字,都是纯表意字。运用这三种方法创造的文字在人类还处于比较蒙昧的时代是够用的。但随着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进步,语言日益丰富精密,词汇量不断增加,需要有更多的文字来如实地记录、传达,“象形、指事、会意”三种造字方法已不能满足语言发展的需要。用这三种造字法创造的文字数量有限,并且有些字难以创造出来,这些字不但包括那些只有语法意义的虚词,也包括某些实词,而且这三种方法创造出来的字都是没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字,也不能如实地记录和传达有声语言。于是,人们发明了假借法。假借是在表意的方法造不出所需的汉字时,选取同音字来记音。假借字的大量使用,虽然临时解决了造字难与用字多的矛盾,并使汉字在记录有声语言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后来假借字使用泛滥,“一字借表多词”“一词借用多字”成为常见现象,这就造成了汉字这一符号体系的混乱。常常是一个字不仅要用它的本义,还要表众多的引申义,这种现象不符合记录语言的要求。原有表意功能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日益符号化,它们的形体许多已经不能反映它们的本义,加上假借字的大量使用,汉字体系的表意性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种情况下,汉字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人们在一些假借字的基础上加注形旁,便创造出了分化职务的形声字。由此看来,形声的造字方法是在假借的方法引起汉字体系的混乱、不能满足人们使用需要的情况下才开始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的,其出现的顺序晚于假借。因此,对于六书的次序,应稍作调整,将假借移到形声之前较为合适。
其次,大量例字表明,假借早于形声。如“师”字,“师”的本义是古代军队编制的一级,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当“狮”这个事物出现时,只有“shi”这个音,却没有汉字来记录它,便假借了与其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师”字来记录这个事物。但在使用过程中,“师”字承载的意义太多,容易发生混淆,后来便在“师”字的基础上加注形旁“犭(犬)”来分化词义,造出形声字“狮”字来专门表示“狮”这个事物。此时,分化字“狮”就记录了“师”字的假借义,“师”字的职务便减少了。在“师”字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先有假借,后有形声。这类例字还有“直(值)”“工(贡)”“正(征)”等。又如“其”字,甲骨文字形象簸箕形,为“箕”之本字,后来在表示“他、他们、那”等意思时,因为代词“其”本无,遂将“其”假借为代词,此时“其”字功能太多,为了避免发生混乱,便将“其”固定表示代词,另造形声字“箕”来表示其本义。此时,分化字“箕”字就记录了“其”字的本义,“其”字的职务也就减少了。这类例字还有“它(蛇)”“易(蜴)”“西(棲、栖)”等。这些例字表明,很多形声字的出现,不论代表本义还是假借义,都是为了分担汉字的功能,减轻假借造成的混乱局面,从而也证实了假借早于形声出现。
再次,许多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假借位于形声之前。如1956年,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其《殷墟朴茨综述》一书的“文字”一章中,提出了“三书说”,包括“象形、假借、形声”三类。1957年,文字学家和训诂学家刘又辛在其《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的改革》一文中,把汉字的演变史分为“表形、假借、形声”三个阶段。先不论其概念与内涵,单就次序来说,这两位文字学家都将假借置于了形声之前。其实早在汉代,郑众就置“假借”于“谐声”之前(说见《周礼·地官·保氏》注),在他看来,假借先于形声而发生。随着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相关的甲骨文、金文材料的证据也完全验证了郑众的这个次序。
总的来说,假借是形声的先驱,形声是对假借的优化。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假借是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没有假借也就不可能有形声手段的成熟。因此,在“六书”中,将“假借”的次序置于“形声”之前,更符合汉字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阳明强.对“六书”中几个问题的看法[J].语文学刊(基础教育
版),2010,(9).
[3]王卫峰.假借形声略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张文君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