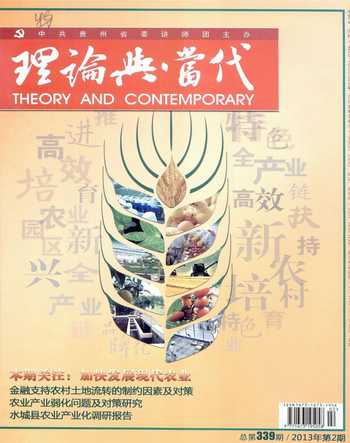碑刻与黔西南乡村治理
李晓兰
碑刻是前人记载时人时事的手段之一,是前代保存下来的具有较大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物,是研究近现代历史发展状况、社会风俗演变的宝贵资料。黔西南地区现存的近代碑刻由乡规民约碑、禁革碑和晓谕碑、界碑、修路建桥碑、少数民族文字碑、记事碑等六类组成,广泛分布在兴仁、兴义、安龙、册亨、贞丰、普安、晴隆各县。碑刻记事的年代从道光四年(1824年)至民国年间,超过一个世纪,主要以道光、成丰、同治、光绪四朝为主。从立碑者看,有寨老或头人独立、寨民合立、众寨合立、地方知县所立等。碑刻记载了近代以来黔西南地区乡民在世风日下的背景下,“齐心众议,挽此颓风,禁此不良”,进行乡村治理、开展乡村自救的状况。
现存的大多数碑刻,均记载了黔西南人民遭受盗贼、窝赃严重侵扰的情景。位于兴义县兴化乡的水淹凼四楞碑(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立)记载了盗贼猖獗的情形,轻者或“被贼挖墙入室”,或“被贼盗窃牛马”,甚至“禾苗成熟之时,三五成群结交,偷割田谷”的现象屡有发生。重者更是“勾内入党,成群入户,劫掠财帛牛马等件”,使得乡民屡被“恶匪掳掠”,敢怒而不敢言。如恰逢“年岁荒歉”,再经历偷盗、劫掠,乡民们“田谷无几”,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系。长此下去,良善之民将无安身立命之所。
清朝明文规定禁赌,从《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条目众多、惩罚严厉的禁赌例文即可窥知。普通民人如“将自己银钱开场诱引赌博、经旬累月聚集无赖放头、抽头者,初犯,杖一百、徙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禁令严厉反衬着清朝的赌风之盛。地处僻远的黔西南地区也深受影响,世风日下。从现有的碑刻记载来看,黔西南地区近代以来的许多贼盗现象均起于赌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所立册亨县马黑“永垂千古”碑记载:“士农工商,是君王之正民,奸诈淫恶,及乡里之匪类,所口奸情贼盗,起于赌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立安龙县阿能寨公议碑描述了嗜赌之徒的日常生活,“日则摇钱赌博,夜则偷盗口生”,“从不务农”。赌博使人们事业荒废,精神沉沦,礼仪丧失,道德沦丧,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由赌博引发的偷盗等行为破坏了当地传统的民约乡俗,造成社会风俗败坏,社会秩序混乱。
针对偷盗、窝赃、赌博、乱砍滥伐、不讲公共卫生等现象,淳朴的乡民为保卫家园,采取了多样化的整治手段,安良缉盗,保护生存环境。以寨老、头人为首的乡寨领袖肩负起维持村寨安全、寨民生活有序的重任。他们以宗族宗法制度、重义轻利、倡导和谐的传统儒家思想为主导,进行乡村治理。治理的方式包括精神动员、严厉处罚和议定处罚条款立碑公示等。乡内众寨老屡次集体商议,提出了改变盗匪、窝赃、赌博、乱砍滥伐、不讲公共卫生等现状的相应对策,不仅把上述处罚方式详列在案,而且把公议的约定俗成的处罚内容和条款镌刻下来,采取立碑的方式,告示乡民,自觉遵守。治理过程中,寨老、头人等扮演着议定治理条款内容、审讯仲裁人等重要角色,同时重视乡民的参与,在由寨老、头人等对违反乡规民约的乡民直接进行审讯制裁的过程中,无论是处以行刑或诛戮,均需“聚众”或“约众”。通过乡民的广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治理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同时也可威慑乡民,起到规谏、劝诫作用。
除乡民自己采取措施挽救颓风外,当时的地方政府为维持地方的正常秩序,亦以官方名义立碑,刻下所议条款和约法,威慑地方。如位于兴仁县大桥河乡海河寨的“奉示勒石齐心捕盗”碑,即由安义镇府右营副府刘德达、兴义县知县杨光辉、普安县知县李培基、兴义府知府陈熙、安南县知县袁汝相、新城县丞赵履增等六位地方官联名所立,“守望相助,声气相通”。偷盗、窝赃之人,如果改过自新,“聊开一面之网”,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则“擒送官究治,活少,死多”。以官府的名义来威慑四方,安民缉盗,一方面说明黔西南地区的确存在较为严重的匪患,一方面也说明地方官员同样希望社会安定,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以地方官员名义竖立的石碑,较之乡民所立者更有号召力与威慑力。
近代以来,黔西南地区面临世风日下、违法犯罪日渐猖獗局面。当政的清政府自身正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对地处偏远的黔西南地区给予较为有效的政府行为控制。地方政府希望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在政府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他们一方面制定政策措施加强官方控制,一方面寄希望于寨老、头人等乡寨威望较高的宗族领袖,希望他们能够以宗法制度为本,以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维护乡寨正常的秩序,以延伸和扩展政府对边远地带的控制。此种治理方式把官治与民治结合起来,是维持边远地带乡村安全和乡民生活有序的必然举措和必要行为,是近代以来黔西南人民试图营造和谐乡村的朴素体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愿望。碑刻记载的大量保护山林、禁止开挖、禁止乱砍滥伐、禁止纵火烧山的措施,就是他们对于人与自然和谐意识的朴素体现,有利于乡民们逐渐形成良好的环境意识。当然,乡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一定的封建迷信思想,有的碑刻称栽蓄树木是为了“培风水,光前代兴裕后人”,但以立碑公示的方式约束民众不“妄砍树木”,却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偏僻落后、民众文化素质低、缺乏环保意识的黔西南地区,此种方式可以广泛号召民众自觉参与保护森林、不乱砍滥伐,可以为后人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功德无量。
其二,体现了人与社会和谐的要求。以地方官或寨老、头人等有威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的名义,联合寨民以及周边村寨合立告示碑的方式,通过公认的乡规民约、严厉的惩罚措施,约束和警示民众遵规守法。正是这些大家公认的乡规民约一定程度上约束着民众的行为,即使世风日下,大多数乡民仍能保持淳朴的民风,自觉抵制偷盗、窝赃、赌博等非法行为,有力地遏制了犯罪的蔓延,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乡民们与其所生活的乡村社会以及乡民之间的正常秩序,恢复乡寨旧有的宁静生活,回复乡民旧有的良善品行。
其三,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愿望。协调乡民之间的关系、和谐乡邻、淳朴民风是碑刻记载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调戏人家妻女”,“估淫人妻”,乡寨中富贵之人“恃尊凌卑,凶行磕索”,甚至仅因“口角细故”而对簿公堂的现象,碑文明确规定“不许调戏人家妻女”,“不准估淫人妻”,不准乡寨中富贵之人“恃尊凌卑,凶行磕索”。乡邻之间“禁有口角细故”,如出现纠纷,应“经头人”秉公处理,“不可枉控”。邻里之间如有何矛盾,要先在本寨头人处进行协调,不可意气用事而随意告官,以免伤了和气。为避免因信仰、习俗上的差异导致的民教冲突再发生,册亨州正堂特立晓谕碑,规定“所有迎神赛会,不准攀教民,倘有等情,致干查究不贷”。在西方宗教已经深入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普通乡民必须面对的现实时,此种处理方式开始正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现实,客观上有利于协调民教冲突,化解矛盾。
其四。体现了人自身和谐的要求。为改变不卫生的用水方式,碑文明确规定,公共用水的井渠边,“将鸡、猪崽、口水,在此井边合息禁止:凡不洗菜、布、衣,污秽水井”。实行居民饮水和畜养家禽、日常洗刷用水分开,保持饮水的清洁。如有违者,“猪、鸡、酒加培(倍)赔完”。这些条款,说明了黔西南乡民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开始认识到不卫生的饮水方式导致病从口入,身体各部分有机协调功能下降,从而又导致身体素质下降,疾病缠身。只有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日常卫生,才能强身健体,使身体各部分处于良性循环。
黔西南地区现存碑刻记载了乡民们应对巨变、开展乡村治理、以期恢复和谐乡村的具体举措。不可否认,他们仍然以儒家思想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导思想,以公认的乡规民约作为治理的基准,他们想要维护和实现的仍然是男耕女织、世外桃源般的小农生活。他们一心向善、纯洁无瑕的心灵,是铸造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有利于人民树立正确的善恶观,培育和保持朴实、善良的民风。通过对普通民众生活处世观念的向善诱导,引导民众自觉树立良好的品德,从而有利于民众的长期安居乐业,国家的长治久安。
责任编辑:郭渐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