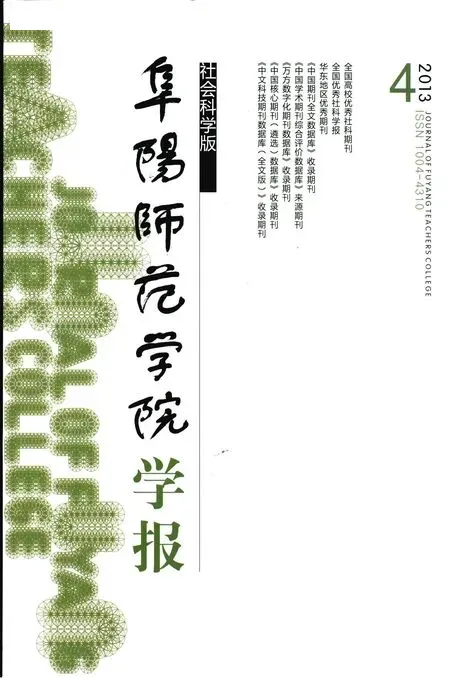论恶的辩证法
常 娟
(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在《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大词典》、《辞海》等一系列辞书中,对恶(evil)的解释都大同小异。恶主要包括三类含义:一、令人讨厌的、使人不舒服的;二、坏的、堕落的,由坏品行造成的;三、有害的,不幸的。这三类含义从个人的“使人厌恶的”生理感受开始,进一步解释了恶在主体和客体上的表现。而在《大英百科全书》中,恶的词条的释义是将恶分成两组含义来理解:一是在道德意义上,恶与善相对,恶是对秩序的破坏,并导致痛苦、精神的困顿和灾祸;二是在延伸的意义上,恶常常被作为哲学和神学的问题来讨论[1]。
一、必要的恶:既恶且善
根据元伦理学的说法,恶是以对需要、欲望、目的的满足与否的有效性为评判尺度的,也就是说,一切不能满足主体需要、不能符合主体欲望、不能达成主体利益的客体属性即是恶的。反之,则是善的。斯宾诺莎说:“所谓善是指我们确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言。反之,所谓恶是指我们确知那阻碍我们占有任何善的东西而言。”[2]157如果说斯宾诺莎是从效果和功能角度来思考善恶的话,那么霍布斯则是从心理的情感反映上来区分善恶:“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说来,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称为恶;……。”[3]111中国古代孟子也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也是从人的愿望是否满足上来说明善恶的含义。两千多年后,罗素表达了与孟子看法十分接近的观点:“‘善’的定义必须出自愿望。我认为,当一个事物满足了愿望时,它就是善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把‘善’定义为‘愿望的满足’。”[4]67以上诸人都是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上来判断善恶的,他们不约而同地以愿望、需要、目的实现的有效性作为判断善恶与否的标杆。
如果按照以上对善恶的界定,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们视欲望的不满足是恶的,那么如偷盗、吸毒、杀戮这样的欲望满足,难道它们应当被认为是善的吗?罗素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只要我们独立地考察,不考虑它们的伴随物和后果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把一些满足看作是恶的。”[4]69
罗素的意思是说,对愿望的满足者来说,它是善的。但是当我们将判断的参照物转移为他人、社会的需要和愿望时,这些行为就被称为恶了,因为这些愿望的满足损害了其他人的愿望,因而是恶的。实际上,在伦理学中,善恶的区分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讨论,在元伦理学层面上的善恶和道德学意义上的善恶,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意义上的恶(非道德的恶),后者我们称道德恶。
总体上说,世界上只要是与主体发生关系的事物都可以言善恶:吃饱穿暖、朝花夕阳、民主自由,对于主体而言是有用的,它们是善;饥饿冻瘐、山洪地震、专制愚昧,对于主体而言是有害的,它们是恶。但是,并不是这些事物都可以称作道德的善恶。弗兰克纳(William K.Frankena)就认为可以言说道德善恶的东西应当是人、人群,以及人的品质、性情、情感、动机、意图。总之,是人、人群和人格诸要素[5]17-18。显然,道德的善恶是针对人的行为和品德而言的,它的论域相比一般意义上的善恶而言要狭窄的多,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和品德是道德善或道德恶呢?
我们假设,当一个人脱离了社会,就像鲁滨逊在一个孤岛上生活,那么他的行为无所谓对他人是善是恶,他只需考虑是否对自己有益即可。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只有一般意义上的善恶之分,而不存在道德的善恶之分。当我们探究某个人的行为是道德善或道德恶时,是以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性为标准的。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善恶价值判断只是和单一主体相关,而道德的善恶标准则涉及到多个主体的利益关系。
道德是行为规范,它是个人的行为与社会规约之间具有的利害关系。道德恶即是对一定社会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的侵犯和违反,比如偷盗、强奸、抢劫以及对老弱幼小的遗弃、欺凌等等。规范伦理学辨认道德现象有两个形式要件:“一、它一般是关涉到他人,关涉到社会的;其次,它还须是以一种外在的、实际可见的、会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行为方式关涉到他人和社会的。”[6]25这就表明只有当一个人的实际行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了影响时,我们才能从道德的角度对这一行为做适当的价值判断。
由此,一般意义上的善恶和道德的善恶的联系与区别,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道德善恶从种属关系上是隶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善恶的,是种和属、个别和一般的关系。这正如伦理学家石里克所言“道德上的善只是更一般的善的特殊情形”[7]22。反之,则是恶和道德恶。两者的区别不论从客体属性还是主体特征上都可见出:首先,从一般善恶和道德善恶的客体和对象上来看,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善恶言说对象,只要客体与主体相关就可言善恶,而道德善恶的客体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是以他人和社会为参照系的。其次,两者的主体也有区别,只要是产生需要、欲望、目的的任何人都是一般善恶的主体,与此相异,道德善恶的主体则是社会,客体的属性需要满足的是社会的需要、目的和欲望,是社会创造道德的目的、需要和欲望[8]。这样看来,一个人自我牺牲就其自身来说,是恶,对社会和他人来说则是道德的善;双赢或多赢既是一般的善也是道德的善;以损害别人来满足私欲是一般的善,却是道德的恶;既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既是一般的恶也是道德意义上的恶。
亚里士多德曾将善区分为目的善(内在善)和手段善(外在善):“善显然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事物自身就是善,其二是事物作为达到自身善的手段而是善。”[9]8如锻炼身体和健康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善,后者则是手段借以达到的目标,即是目的善。当然,手段善与目的善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有时目的善也可以成为手段善。反之亦是如此,如身体健康又可以是实现人生抱负这一目的善的手段善,锻炼身体-身体健康-实现人生抱负环环相扣,前者是后者的手段善,直到达到最高的目的善,也就是绝对的内在善——至善。至善就是最终的目的。元伦理学家艾温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统,他在《善的定义》一书中,对善恶作了更加精细的划分和解析。他认为善包括着手段善、内在善、至善和道德善等[10]112-117。按照善恶相对的原则,他认为恶区分为内在恶、至恶、道德恶等等。
如果说最高的善是幸福,那么至恶就是不幸。至于与内在善(目的善)相对的是内在恶,它既可能阻碍愿望的满足,从其自身到它的结果都是恶的,如不治之疾,但也可能其自身为恶,结果却产生了善,如身体的疼痛感,这种痛感就其自身来说是对欲望、需要的压抑和阻碍,是一种恶,但这种恶却遏制了更大的恶的产生,因为痛感这种机能,使我们能够对身体的疾患产生机敏的反应,避免更严重的疾病甚至死亡。这种恶我们称之为必要的恶。必要的恶既恶又善,它实质上是手段的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善的范畴。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法律、警察、监狱等等,无疑是恶的,因为从主观意愿上来说,受到它们的制裁不会是任何人想要满足的愿望,但国家机器的暴力行为的根本立场却是为了符合社会整体的愿望和利益,它的存在是以恶治恶,达到向善的目标,所以是必要的恶。道德也是如此。就道德范式对个人的约束而言,无疑它是对个人的欲望、需要的阻碍和压制,因此从其自身来说,对个人而言,它不是善的,而是恶的,但是显然这是必要的恶,因为就其向外投射的结果和目的而言,是能够防止更大的恶和产生更大的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是恶的且是善的。
在上文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善恶和道德善恶时,我们已经涉及到善恶的辩证关系:因为手段和目的的区分,当我们在善恶的界定时,就会看到必要的恶的存在和合理性,其中就涉及到善恶的转化和辩证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在西方宗教观念中的善恶观所表现出的辩证特征。
二、西方宗教观的恶:由恶向善
从道德塑造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在认识善恶问题时,毫无疑问的是趋善避恶。无论是在伦理规范的领域,还是在法律刑罚的范畴,人类都在不遗余力地力图塑造出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人——从人的行为、习惯直至思想、观念。人们被要求以善为本,勿存恶念。显然,这样意义上的善与恶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被认知的,善与恶是相互冲突的两种力量,它们是截然相反的存在物,彼此对立、互不相容,恶就是恶,善就是善。虽然善恶彼此对立,互不相容,但当我们将问题推进一步考察时,我们会发现,善恶虽然代表互不相容的立场,但它们并不是只存在相互冲突的状况,从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姿态退后一步,我们会发现善恶不仅不是绝对界限分明、凝固封闭的,甚至可能是相互依存纠葛在一起的。这样的观点在西方宗教传统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在基督教神学中,恶包括道德上的恶(moral evil)和自然的恶(natural evil),前者是指在道德上与善相对的行为和品质,它代表着人与上帝之间的一种疏离和违抗状态;后者是指使人类遭受痛苦的来自自然状态的凶险,如地震、飓风、洪涝、瘟疫等等。
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世界起源于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恶在这个世界中并无存身之处,因此善相对于恶有着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在基督教的哲学中,善与恶并不是二元论的,这两者在本源上不是同时出现、并驾齐驱的,也就是说在上帝创世纪之时没有恶的存在,恶不被理解为恶魔作怪的结果,也不被理解为创世纪之前的原初的混沌状态和黑暗力量。它是发生在上帝创世之后的美满世界中,它产生于人类的起源,从亚当、夏娃不能抵抗外在的诱惑而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造成人类的原罪开始,世界才开始有了恶。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他们的后代带着原罪出生,恶成了人类无法左右的先天存在,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现世的从善去反抗恶,于是,恶成为善产生的基础和理由。从西方的宗教观看,恶实际上是善的缺失,是由于人的堕落造成的。莱布尼茨就说:“世界上之有恶并非作为现实,而是作为缺失、缺陷而存在于创造物……”[11]17
在上帝造人之后,人类是如何由上帝创造的清白之身而堕落为罪恶之体的,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一书中通过对远古史诗中的神话进行研究,说明神话是以故事的形式将人类的体验演化出来,并通过故事的叙述表明人类是如何从原本清白状态的存在转变为邪恶的现实物的。“神话试图去了解人的存在之谜,也就是在作为实质的、生物的、清白状态的基本实在和作为被玷污的、邪恶的、有罪之人的现实形式之间的不一致,神话用故事解释这种转变。”①[12]165
在亚当神话中,亚当和夏娃遵照上帝的旨意在伊甸园中生活,但撒旦诱惑了夏娃,继而诱惑了亚当——从人类学的意义上,夏娃和亚当都是一个符号,即人类始祖的符号——偷吃了上帝特意叮嘱禁止他们食用的智慧树上的禁果,人类由此滑入“堕落的瞬间”[12]249,这个时刻是一个标志,它划开了堕落的时刻与清白的过去的界线。亚当违抗了上帝的命令,做出这一裁判的前提是上帝制定的律令,所以在上帝的立场上,他是犯了罪的,是恶,是堕落。如果说上帝是善的代表,亚当则是恶的化身。人类的这一原罪开篇,使得上帝的创造物从一开始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要以忏悔的姿态来面对上帝。所以,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而非创世纪的前提下来看,恶先于善而存在,人类为了救赎人的罪恶只有在现世向善,正如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的比喻:“恶往往是为了使人对善有更高的鉴别力,它甚至有时帮助那种有耐性的人达到更高的自我完善,好像人们播下的种子,先经过某种霉败,然后发芽。”[11]122莱布尼茨实际上是在神义论的基础上生动地说明了恶与善之间的辩证关系:恶不仅仅只是人类必须鄙弃和挣脱的与生俱来的有限性和否定性,它还在这种消极因素中生长出积极的和肯定性的价值,它使人在检视、反省自身后达到了更高的自我完善。换句话说,恶是善生成的基础,没有针对恶的抗争,善就不能显现自身的价值。正如西方有学者所说:“恶对于我们的世界而言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正是它的存在,才产生了勇气、坚忍、仁慈和同情等等品质。”[13]484
关于这种善恶的辩证法,西方的文学家们的认识也同样深刻。如弥尔顿就曾说过:“假如能驱走罪恶,那么我们驱走了多少罪恶,同时也就驱走了多少美德。”[14]4歌德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的另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时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要有一片温和的地带,就必须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15]282
西方的宗教学基础上形成的善恶观,使得西方社会普遍将善恶这对范畴视作是彼此依存的,没有善就无所谓恶,没有恶也就谈不上善,善恶是相互依存的,人类社会只有通过恶才能意识到善的必要性及其真正价值。恶被认为不但具有否定的、消极的意义和价值,它还会引发肯定的、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恶会激发善的要求和向往,在一定的意义上恶成为了通向善的路径。
有趣的是,当我们摆脱宗教原罪与救赎的立场来看亚当和夏娃的违规行为时,善与恶的辩证法的另一重含义显现出来了。因为如果说人类最初的罪“是作为先前存在方式的失落、作为清白的失落而出现的”[12]251,是对上帝的违抗,那么这其中何尝不又是善的最初契机:恰恰是因为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人类才不再是无忧无思,才开始有了耻感,这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可贵萌芽,人类籍由此才孕育了文明和历史的可能性,从这一角度看,人类对于上帝的违抗不是恶,反倒是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恶开创了自由的契机。这就是里克尔指出的善恶的悖论,也是西方宗教在恶的辩证法上出人意料的另一重内涵。从亚当夏娃的神话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善与恶也是始终相互依靠着的,恶造就了善,但这里的恶所造就的善与基督教要求救赎的道德自然不同,它表达的是恶中蕴藏着对权威的反叛,“在原罪的故事中,我们成了‘不’和否定精神诞生的见证人”[16]10。没有违抗的“恶”,就不会有人类由恶向善的努力以及由此激发出的无限创造力。黑格尔在解释原罪的故事时,就没有将它看做堕落,而是视其为成功的历史的开端。别尔嘉耶夫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善恶辩证法中恶的自由的重要价值。“……恶具有肯定的意义,因为它唤起了克服它的善的崇高的创造力量。恶的自由是善,没有恶的自由就没有善的自由,也即没有善。恶的可能性是善的条件。强制性的禁止恶与强制性的消灭恶本身成了最大的恶。”[17]可见,恶作为否定性的力量,在面对现存势力时有着革命性的颠覆作用,并启发了人的自由之旅。
总之,西方宗教观在充分认识到恶具有的否定性价值的基础上,正视恶,认可恶存在的必然性,认为恶会生成积极的否定性价值而成为善。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待恶时应当有一定的辩证法的眼光和方法:恶一方面是作为人的、社会的阴暗面的存在而受到否定和批判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作为善的支撑物而存在的,会导致善的发生,会激发出善的向往和要求。
西方宗教思想中的善恶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善恶观相比是判然有别的。如果说,前者是在一元论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善恶的辩证关系,那么,后者则一开始就把善恶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来看待。中国传统上对善恶的讨论一开始就是在人性的范畴内展开,虽然这与西方的善恶观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西方论恶也是从人性恶的本源开始的,但它有原罪的宗教背景,因此对于恶的追问是在道德的和神学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这是中国传统所没有的,中国古代论善恶是在世俗背景中讨论人性的善恶的,具有代表性的人性论思想,一是孟子的“性善论”,一是荀子的“性恶论”。实际上,如果我们细加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虽然两者的人性观各执一端,但在根源上却并无实质的冲突。
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之体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孟子并没有无视人与动物都有的本能,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本能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质,所以不能称之为人性,人性应是人的本质属性中区别于动物的一面,即符合人类社会道德要求和规范的善。更进一步,君子之所以能成为君子就在于他能够保存并扩充人人都有的善端。荀子则在他的《性恶篇》开篇就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认为口好味、耳好声、目好色等等,是人生而俱来的本能,人的本性虽然是恶的,但是只要学习和遵从法度、礼义,就能去恶为善,这依靠的是后天的教育来改造人的本性,“化性起伪”即是此意。
如果说孟子看重的是人应当区别于动物的一面来规定人性,因而将人性落实到善端上,那么荀子则抓住人与动物共有的本能来理解人性,将人性的重心放到恶端上。实际上,二者都承认人具有和动物相似的性质,只不过前者侧重的是人的社会属性,后者侧重的是人的自然属性,虽各执一端,但却并无实质性的冲突。其次,二者不约而同的都要求以礼制教化为手段来塑造人性,在这一看法之下隐藏的是对人的道德完善的可能性的肯定。两者人性论的缺陷在于都没有意识到人性应当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性质的统一,只是执其一端来思考人性善恶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单一和绝对化的人性论,缺少辩证的立场。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性善、性恶论从存在论的角度看,都承认人性中存在着性恶的因素和成分,但从价值论的立场上,两种观点都对恶抱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恶是不可取的,不应该的。这样的观点和看法导致了中国古代关于恶的理论的尴尬性和割裂感:一方面学者们主张肯定人性恶存在的真实性、必然性,另一方面却否定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18]。这同样是缺少辩证思维方式的表现。
综观中国古代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的儒家人性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性善论或是性恶论,其最终的伦理旨归都是一致的,两者都是要求加强后天的道德修炼,以成就道德理想化的人。这样的观念不但将善恶问题的讨论局限在人性道德论的范围中,而且将恶视作善的性质上的对立物和地位上的附属物,容易导致对人的道德要求的理想主义绝对化的倾向。与西方的善恶观相比,中国传统的善恶论还是相对缺少辩证法的,这种将善恶单一化、绝对化和极端化的看法,无疑是不利于我们对恶的深入认识和理解的。
注释:
①里克尔归纳出四种神话类型,包括创世神话,如苏美尔神统神话、荷马和赫西俄德神统神话; 古希腊悲剧神话;亚当神话和灵魂放逐的神话,即俄狄浦斯神话。他在论述苏美尔神话时阐明了恶的起源和终结问题。世界万物的起源的开始是无序的,是混沌的,“秩序是最后来到而不是开始就有的(第178 页)”。要想确立秩序,就必须依靠暴力,于是恶成为了建立秩序的基础。在巴比伦史诗中众神的阴谋、诡计、暴力行为“被铭刻在万物的起源中(第184 页)”。恶显然并不只是显现在这一种史诗中,它普遍存在于各类史诗中。
[1]The New Encyclop? dia Britannica (15thedition)By Encyclop? dia Britannica,Inc.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荷]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英]霍布斯.利维坦[A].黎思复,黎适弼,译.龚群.善恶二十讲[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4][英]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肖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社,1992.
[5][美]弗兰克纳.伦理学[M].关键,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6]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奥]石里克.伦理学问题[M].张国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王海明.善与恶的解析[J].思想战线,2001,(6).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0]Ewing.A.C.The Definition of Good.New York:Hyperion Press ,Inc Westport ,1979.
[11][德]莱布尼茨.神义论[M].朱雁冰,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7.
[12][法]保罗·里克尔.恶的象征[M].公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3]Edward H.Madden.The Many Faces of Evil.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24 No.4 1964.
[14][奥]雷立柏.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C].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6][德]萨弗朗斯基.恶:或者自由的戏剧[M].卫茂平,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7][俄]别尔嘉耶夫.堕落、善与恶的产生[J].石衡潭译.哲学译丛,2000,(3).
[18]张登巧.中国古代“恶”之存在论与价值论探讨[J].伦理学研究,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