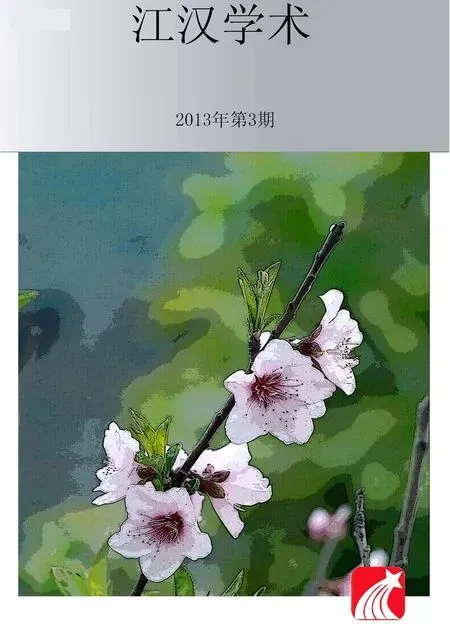论荣格对深层审美心理学的开拓
张玉能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9)
把深层心理学和深层审美心理学进一步推向前进和发展的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是他继承而又超越了他的老师弗洛伊德,开创了分析心理学和分析心理学美学,把深层审美心理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的名著《无意识心理学》便是标志。荣格对于深层心理学的最大贡献,或者说他与弗洛伊德的根本分歧在于,他提出了“集体无意识”这个划时代的概念,重新划分了人的心理结构(人格结构)。荣格把弗洛伊德关于“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的以个体经验压抑和泛性主义为特点的心灵结构(人格结构),改造为“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心灵结构(人格结构)模式,以强调人类原始种族的集体经验的积淀和原初的生命力对于人们心理活动、行为、人格的决定性影响。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荣格研究了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特别是研究了梦、神话、原始宗教等具体形态,提出了“原型”和“原始意象”的概念,并细致地研究了一些重要的原始意象和原型。荣格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绪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了那些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经由遗传具有的性质……发现了一些先天的固有的直觉形式,也即知觉与领悟的原型。它们是一切心理过程的必不可少的先天要素。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他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原型也迫使知觉与领悟进入某些特定的人类范型。”[1]5因此,原型是一切心理反应的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先验形式,即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而原始意象这一概念,荣格经常把它与原型概念相混用。其实,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尽管联系密不可分。初步地可以这样说,原始意象介于原型与意象等感性材料之间,起一种规范意象的桥梁和中介作用;而原型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荣格指出:“原始意象……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1]9因此,荣格把“原型”称为相当于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纯形式”,“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而把“原始意象”比喻为“心理中的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可以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1]7,9他根据这种基本原理,从梦、神话和原始宗教习俗的大量材料中归纳抽绎出几种主要原型:母亲原型、儿童原型、阴影、人格面具、阿妮妈(anima,男人身上的女性倾向)、阿妮姆斯(animus,女人身上的男性倾向)。此外,荣格还根据人类无意识的生命力(里比多)的趋向把人格分为外倾型和内倾型两大类,然后再配上感觉、直觉、情感、思想等四种心理能力,进而把人格分为八类:外倾思维型、外倾情感型、外倾直觉型、外倾感觉型、内倾思维型、内倾情感型、内倾直觉型、内倾感觉型。荣格的这些主要学说极大地丰富了深层心理学的内容,促进了其深入发展。
一、强调原始经验对于审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
荣格在上述这些主要学说的基础上,对文学艺术与心理学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从而同样也丰富和推动了深层审美心理学。他在这方面的伟大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荣格把文学艺术和审美现象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强调了历史积淀的原始经验对于审美活动(特别是文学艺术活动)的决定性作用。荣格反对像弗洛伊德那样把文艺和审美看作是个人无意识,即性欲或恋母情结的升华或替代性表现,而反复强调文艺和审美是集体无意识(原型或原始意象)的象征性或符号化活动。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中,他指出,“原始部落的传说与原型有关”。“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表达原型的方式是神话和童话。”[1]53-54在《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中,他指出弗洛伊德对于达·芬奇的那幅圣·安妮和圣母玛丽亚与儿童基督的画的解释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那幅画“与明显的个人心理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非个人的母题。……这就是‘双重母亲’的母题,它是神话和比较宗教中以各种变体出现的一个原型,它构成了无数‘集体表现’的基础”[1]97。他还列举了大量的神话和宗教传说的实例说明,达·芬奇表现的不是个人无意识的心理现象,而是表现了人类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需要——集体无意识中的“两次诞生”的原型。他多次强调艺术是某种超个人的东西,因此,在《心理学与文学》一文中有了他的一句名言:“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1]143在他看来,《浮士德》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象征,它早就活在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不过一般德国人尚未把它认识清楚,而歌德则促成了它的诞生。荣格的这些论述和断言,虽然有些神秘玄虚,也难免偏执和片面于“集体无意识”而忽视了文艺和审美的个性特征,但是,其中所表示的沉重的历史积淀,却给人们洞开了一扇揭开文艺和审美的奥秘的窗口。因此,在荣格思想的启发下,一种原型——神话批评模式在20世纪的美学和文艺学界产生了并且具有了很广泛的影响,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批评的视角。
二、揭示艺术的社会意义
荣格具体阐述了集体无意识通过原始意象和幻想而显现为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并由此揭示出艺术的社会意义。荣格在《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原始意象或者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形象是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1]120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心理学看来,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是通过创造性幻想显现为各种形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形象和艺术形象)。因此,“创作过程,在我们所能追踪的范围内,就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通过这种造型,艺术家把它翻译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并因而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道路以返回生命的最深泉源。艺术的社会意义正在于此:它不停地致力于陶冶时代的灵魂,凭借魔力召唤出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1]122由此可见,荣格赋予艺术的社会意义在于,通过原始意象在创造性幻想中的显现,引导人们返回到生命的最深泉源,从而补偿现代人由于文明而变得匮乏和片面的精神世界。
三、揭示艺术创作中的两种模式及两种审美心态
荣格在心理类型学的构想指导下,揭示了艺术创作中两种模式以及两种审美心态。荣格在他的名著《心理类型学》中,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心理类型问题,发现有两种最基本的性格类型:内倾型与外倾型。他分析了各种文化现象发现,内倾与外倾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倾向,在人类全部历史文化领域乃至日常生活中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比如,哲学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艺术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社会生活中政治家与理论家的对立,实干家与空想家的对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无不是内倾型与外倾型的对立。他还具体分析了许多著名思想家和艺术家,比如,柏拉图是内倾型,亚里士多德是外倾型,席勒是内倾思维型,歌德是外倾直觉型,立普斯是内倾型,詹姆士是外倾型,等等。荣格把这种心理类型学的观点运用到艺术创作和审美现象的分析之中,从而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两种模式(心理学创作模式和幻觉式创作模式)以及两种审美心态(移情和抽象)。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认为:“《浮士德》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的深刻区别,标示出艺术创作的心理模式和幻觉模式之间的区别。”[1]128心理的模式加工的素材来自人的意识领域,例如人生的教训、情感的震惊、激情的体验,以及人类普遍命运的危机,这一切便构成了人的意识生活,尤其是他的情感生活。而幻觉模式所处理的素材则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它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又仿佛来自光明与黑暗对照的超人世界。由此可见,心理的模式是倾向于显在的意识,而幻觉的模式则倾向于深层内在的意识,因此,它们便分别与外倾型和内倾型相对应。因为在荣格看来:“外倾意指力比多的外向转移。……外倾是一种从主体到客体的兴趣向外的转移。”[2]520“内倾意味着力比多的向内发展,它表现了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否定性联系。主体的兴趣不是向客体方面运动,而是退回到主体。每一个持内倾态度的人都按照下面的方式思考、感觉和行动,这种方式就是:清楚地展示出主体是动机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客体则至多不过获得了次要的价值。”[2]543-544在《心理类型学》中,荣格还分析了他的内倾和外倾的人格类型与席勒的感伤的诗人和素朴的诗人的分类以及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分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诗人就是自然:自然在他身上创造产品。他听任自然绝对地支配他。他把最高权力给予了客体。在这种程度上,素朴诗人是外倾的。”[2]146“感伤诗人具有对客体持反思和抽象态度的特点。……对他来说,客体的外在印象并非某种不受限制的东西,而是依据他自己的观念所把握的材料。因此,他超越于客体之上,而又仍与它保持联系,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易受印象影响的联系,而是他自己把价值与本质赋予客体的自由选择。因此,感伤诗人具有一种内倾的态度。”[2]147-148那么很自然的,与此相应,席勒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心理对立,也就是外倾型与内倾型的对立。同样,他还把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描述为外倾情感型:“这是一个情感的外倾问题,这些情感同感觉的因素紧紧依附,不可分割”,而日神精神则被描述为内倾思维型:“它是一种内省的状态,一种对永恒理念的梦的世界的内在沉思:因而它是一种内倾状态。”[2]160-161由此再进一步,荣格分析了美学中的类型问题。他借用了美学家沃林格所用的移情和抽象这样两个概念来阐明他的外倾和内倾的心理类型。他说:“移情是一个知觉过程,它通过情感的媒介而转化成一种基本的进入客体的心理内容;因此,客体就被内向投射了。这种内容由于它与主体的密切关系而使客体同化于主体,这样,主体感觉到他自己与客体联系起来了,就好比说主体进入了客体之中。不过,主体不仅感觉到自己注入了客体,而且,客体也完全感觉到自己被注入了生命,从而表达了与它自己的要求一致的东西。……因此,移情是一种外倾。”[2]348“抽象的移情则意味着客体方面的某种生命力和活动力;因此,它企图摆脱客体的影响。所以,抽象的心态是向心的,即内倾的。……抽象的心态对客体怀有一种心境,认为客体具有令人恐惧的性质,即一种有害的或危险的影响,这种客体用以防卫自身的可怕影响是必须反对的。毫无疑问,客体的这种明显的先验本质也是一种投射或移情,只不过是一种否定方式的移情。所以,我们必须设定无意识的投射活动是抽象活动的先导,在这里,否定性的强调的内容转换而进入了客体。”[2]350-351简而言之,荣格认为,移情和抽象都要以无意识的投射活动为先导,不过,移情是一种肯定性的无意识投射,能形成主观性的美,而抽象是一种否定性的无意识投射,能形成客观性的美。荣格的这些分析及其结论,当然从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显得神秘莫测,但是,也给我们研究艺术创作和审美心态以及审美形态开辟了新路,挖掘到了人类心灵深处,拓展了人们的思路。
四、揭示无意识的象征或符号化在艺术中的根本意义
荣格为了揭示象征的含义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表现和意义,在晚年组织写了一本专著《人类及其象征》。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人类与象征共存,尽管人类没有意识到,但象征的意义却使人类生活生机盎然。”[3]62在荣格那里,象征之所以如此重要并广泛存在,就是因为他赋予了象征这个范畴非常宽泛的涵义:“当一个字或一个意象所隐含的东西超过明显的和直接的意义时,就具有了象征性。象征有着广泛的‘潜意识’方面。”“我们不断运用象征的名词来表示我们无法下定义,或者不能完全理解的概念,乃是因为有无数事情人类还难以认识。这也是所有宗教运用象征语言或意象的原因之一。这种有意识地使用象征,只是极为重要的心理事实中的一个方面:人类仍在潜意识地、本能地以梦的形式创造象征。”[3]2这样,荣格就把凡是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的语言或形象的表达都算作是象征,不过,他特别把象征看作是人类无意识(尤其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同时,他也特别强调象征与符号的区别:“符号的含义总是比它代表的概念更少,而象征总是代表超出其自身明显和直接含义的东西。不仅如此,象征又是自然的产物。……梦是所有有关象征知识的源泉。”[3]32具体来说,荣格认为,象征是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表现:“本能是生理上的冲动,并且被感官所感知。但同时,它也在幻想中表现自己,时常是仅仅通过象征意象表现它们的存在。这些表现便是我所说的原型。”[3]50而“原型却创造出能够影响整个民族和时代,并赋予其特征的神话、宗教和哲学。”[3]60综上所述,荣格把象征当作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含蓄的、间接的、模糊的、多义的、形象的显现,或者换句话说,人类的艺术、宗教、哲学与梦一样,都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象征或象征性表达。尽管荣格的这种说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弗洛伊德的本能升华说和白日梦说的艺术本质论的窠臼,但是,荣格却揭示了人类的艺术(与宗教、哲学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的历史积淀性、集体(社会)性,并通过象征最一般地标明了艺术的含蓄性、间接性、形象性、模糊性、多义性,并且通过象征与原型的关系表明了艺术与集体无意识的密切关系,从而高度强调了艺术的超个体性。正因为如此,荣格的私人秘书和传记作者阿·扎菲夫人才得以在《人类及其象征》一书的第四章中用荣格的理论分析了“视觉艺术中的象征主义”。她在那里这样写道:“人类及其制造象征的嗜好,潜意识地把客观对象或形式改变为象征(从而赋予它们以伟大的心理价值),并以宗教和视觉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追溯史前时期,组合在一起的宗教与艺术历史,是我们祖先留下的象征记录。这些象征对他们来说,既有意义,又有变化性。甚至到现在,正如现代绘画和雕刻表明,宗教和艺术的相互影响仍然充满生机。”[3]210像这样把宗教、艺术、哲学都当作象征形式并植根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的思路和实证,是否从另一个侧面参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根于经济基础及各种意识形态的相关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呢?难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人竟会想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包括荣格的理论)结合起来,其中的奥秘并非一个荒唐的词语可以了结的。
五、揭示20世纪现代派文学代表作品蕴含的无意识内涵
荣格具体分析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一些代表作品,揭示了其中深蕴的无意识内涵,加深了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的理解。荣格不仅一般地论述了他自己关于文学艺术的美学理论,而且还具体评论过现代派文学艺术作品,以充实他自己的深层心理学和深层审美心理学或无意识美学。他在《〈尤利西斯〉:一段独白》之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之一,詹姆斯·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进行了具体入微的分析,得出了非同一般、入木三分的阐释,也具体地阐发了分析心理学的美学观念。荣格一针见血地从纷繁杂乱的文字表达中揭示出,“这彻底无望的虚无,便是统领全书的主调。”[1]146然后又从《尤利西斯》嘲弄读者的态度,文字语句的似断又续(像被斫成两段又能再生)的特殊构成,作家顽强的自我表现以及反传统的艺术表现,指出了它的实质:“在《尤利西斯》那些篇章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精确的观察能力,一种感官知觉的照像似准确的记忆,一种既对内心现象也对外部世界的感官好奇心,一种显著而突出的过去的题材和忿恨,一种主观心理现实同客观物质现实谵妄似的混乱,以及一种毫不考虑读者、一味滥用生造词、零碎摘引、声音与语词联想、突兀的转折和思维中断的表现方法。我们还于其中发现了情感的衰退达到了玩世不恭的顶点与荒谬绝伦的程度。即使外行人也不难寻出《尤利西斯》与精神分裂的心理状态之间的相似之处。”[1]152接着,荣格分析了这种精神分裂的表现与现代人人格分裂集体无意识的关系,进而肯定了《尤利西斯》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他如是写道:“在艺术家中,这种以陌生眼光看待现实的倾向就不再是任何个人疾病的产物,而是我们时代的集体的表现。艺术家并不顺应个人的冲动,他顺应集体生活之流。这集体生活之流不是直接起自意识,而是起自现代精神的集体无意识。正因为它是一种集体的现象,所以它才能够在绘画、文学、雕塑、建筑等各个彼此不同的领域内都结出完全相同的果实。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主义运动精神上的父亲之一——凡·高——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精神异常者之中,通过荒谬古怪的物质现实或者同样荒谬古怪的非现实来歪曲美和意义,这种行为是人格毁灭的结果。但在艺术家中,这种行为有一个创造的目的。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远不是其人格毁灭的结果,相反,他在毁灭中找到了他的艺术人格的统一性。靡菲斯特式的美丑倒置与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相互颠倒带有非常夸张的色彩,这种方法使无意义几乎被赋予了意义,使丑具有了一种刺激血性的美。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成就,它在人类文化史上从未像今天一样被推到这样极端的地步。”“《尤利西斯》在对统领至今的那些美和意义的标准的摧毁中,完成了奇迹的创造。它侮辱了我们所有的传统情感,它野蛮地让我们对意义和内容的期待归于失望,它对一切合题都嗤之以鼻。”[1]154-155以后,荣格还从《尤利西斯》的象征意义出发,分析了现代人的特征:情感的萎缩,四处流浪和无家可归,并且充分肯定了《尤利西斯》的真实、绝对客观和诚实,从而指出:“乔伊斯作品的一切否定,一切冷血,一切怪诞与可怕,一切陈腐与荒唐,都是值得称颂的积极价值。”[1]166读荣格的这一篇评论文章,真令人惊叹他的高屋建瓴的理论把握,入木三分的洞察能力,敏锐的审美穿透力以及行云流水、妙笔生花的表达功夫,真正堪称文学批评的楷模。荣格不仅评析了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而且探究了现代主义造型艺术的典型人物——毕加索,写了一篇名为《毕加索》的专论。该文于1932年在报刊上发表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强烈反应,因为它对毕加索及其作品作了深层审美心理学的独树一帜的研究。荣格认为,毕加索的艺术是一种非客观艺术,主要取材于“内”,即一个潜藏着无意识心理的世界,“如果把他的作品按编年排列,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有一种逐渐脱离经验物体的倾向,可以看出一些不符于外部经验的、来自于‘内’的因素的逐渐增长。”[1]172由此进一步,他还认为,毕加索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这种病人的画揭示着它们对情感的疏远与离异。“这类画都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断裂;它们以布满整个画面的所谓‘断裂的线条’,即一系列的心理‘断层’(就这个词地质学上的意义而言),来表达自己。这种画使人感到心寒,它们以其荒谬无情和对观众的古怪的冷漠搅扰人们的内心。毕加索正属于这一类型。”[1]173荣格还分析了毕加索的画的象征性内容:在现代人心底涌起的这样一些反基督的、魔鬼的力量,从这些力量中产生出了一种弥漫着一切的毁灭感,它以地狱的毒雾笼罩白日的光明世界,传染着、腐蚀着这个世界,最后像地震一样地将它震塌成一片荒原残碟、碎石断瓦。“毕加索与他的画展,连同那二万八千名前来看画的观众,便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印证。”[1]174-175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毕加索这种神经分裂症病人的象征着现代人集体无意识的断裂和零碎的绘画作品呢?荣格的答案是:因为现代人向往原始完整的人。他分析道:“人类精神史的历程,便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这个‘完整的人’由于当代人在他们的单面性中迷失了自身而被遗忘,但却正是这个完整的人在所有动荡、激变的时代曾经并将继续在上部的世界中引起震动。这个人与现在的人是不同的,因为他一如既往,亘古不变;而现在的人则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在我的病人中,接着内外的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人性中的两重性及其对立面相互冲突的必要性的承认。在经历了那些崩溃、分裂时期的疯狂的象征以后,随着便会出现一些表明明与暗、上与下、黑与白、男与女等对立因素互相靠拢与融汇的图象。在毕加索最近的绘画中,对立面直接的并列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融合的主题。”[1]176荣格就是这样从集体无意识的历史积淀的角度,揭示了现代主义艺术所显示出来的病态象征含义。这无疑是深层审美心理学的推进和拓展,也是深层审美心理学的实际应用。荣格的这些基本观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在他主编的《人类及其象征》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该书第四章“视觉艺术中的象征主义”的作者阿·扎菲夫人,正是依据着荣格的深层无意识心理学和深层审美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对现代主义的各个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艺术创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具体的分析。这些无疑都大大地促进了深层审美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荣格是深层审美心理学的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1]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
[2]荣格.心理类型学[M].西安:华岳出版社,1989.
[3]卡尔·荣格,等.人类及其象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