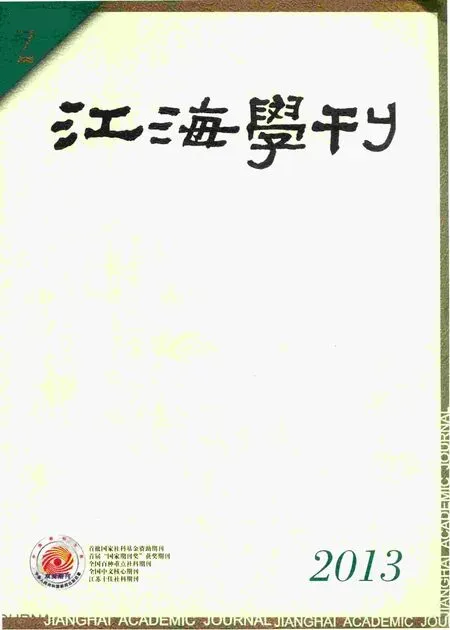语言与图像的符际冲突
[爱沙尼亚]玛瑞娜·格瑞莎柯娃 李玉平 译
元表征
西蒙尼德(Simonide)将画视为“沉默的诗”,把诗看作“言说的画”,自然揭示出语言与视觉媒介的互补性: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由此观之,语言与视觉媒介至少是部分地共存的。达·芬奇在《画论》中也宣称,“画是哑巴的诗,诗是盲人的画”,诗、画之间的差异决定了综合这两种艺术的困难之大。在此种情况下,每种艺术的“缺憾”便成为其寻求突破的建构原则。语言艺术追求视觉性和感觉的呈现,“可视的写作”成为传统的主题,哪怕这仅是一种渴求和无法企及的目标。反之,视觉艺术诉诸意义生成的指示(indexical)与规约(symbolic)形式,追求语言式的分节(articulated)。无论是语言艺术还是视觉艺术都很难达到上述理想状态,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意义的罅隙。
过去40年间,涌现出众多的视觉理论,它们都把语言与图像之间的意义生成罅隙作为其研究的起点。这些理论凸显不同媒介的固有特性——在同一“像似文本”(iconotext)中视觉媒介对语言媒介的抵牾或者像似(连续)与规约(离散)因素的相互混合。视觉媒介与语言媒介相互冲突同时又相互补充的特性成为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约瑟夫·古尔特斯(Joseph Courtés)主张,视觉符号与其假定的意义之间不存在静止的对等,将视觉符号化约为对等的系统(譬如语言)是错误的。①依尤瑞·洛特曼(Jury Lotman)之见,在离散语言和连续语言之间不能相互翻译。离散语义实体(规约符号,譬如语言)与连续语义实体(诸如绘画、电影、梦境、舞蹈、仪式活动等)之间只能建立大致的对等。从视觉到语言的翻译会导致意义的大幅度错位和感觉生成的转移。
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张力在“元图像”(metapicture,米歇尔语)或图像悖论中尤为明显。在这里,图像表征与感知都成为问题。“元图像”的不稳定性及其蕴含的“混乱”和抵制阐明了“严格意义上元语言的不可能性”和“视觉与语言经验的交叠”②。元图像在现代艺术与先锋艺术中相当普遍。魏福德·诺斯(Winfried Nöth)区分了“元图像”(关于图像的图像,包括引用或其他形式的互文性指涉)与“自我指涉图像”(指向自身的图像)。诺斯宣称,“元图像”与“自我指涉图像”只是部分重合,米歇尔却忽视了两者的区别,它的定义既包含“元图像”也囊括了“自我指涉图像”。诺斯通过与“元语言”(第二度的语言,抽象和描述性的更高层次的语言)和“自我指涉语言”(指向自我的第一度语言)进行类比,厘清了“元图像”与“自我指涉图像”的区别。
米歇尔的“元图像”作为一种人工制品和元反射形式是“元小说”(metafiction)的视觉对应物。在这里,第一度与第二度的语言共存,而非对等于元语言。一方面,“元图像”揭示了严格意义上元语言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它自身也转换成为一种元反射的描述。
与“元语言”和“自我指涉语言”不同,元小说和自我反射小说的概念可以作为同义词互换,两者皆指暴露小说表征惯例的自我反射现象,它们告诉我们通常意义上关于小说性的一些东西。同理,元图像告诉我们图像生成的一些事情,它们反射图像自身及其他图像。元小说和元图像整合了元指涉性和元描述性。米歇尔的“元图像”适用于关于图像的元表征和自我表征,而笔者创立的“元视觉”(metavisual)与“元语言”(metaverbal)这两个概念则是跨媒介的元表征(intermedial metarepresentation)。很明显,存在与米歇尔“元图像”类似的语言对应物——自我反射的语言元文本。在这里,语言表征的过程暴露无遗或者遭受质疑。如同元视觉文本对语言表征的呼唤,元语言文本激起视觉表征,以此补偿语言信息本身的缺憾与不足。元视觉与元语言文本都是元表征的重要类型。
“元表征”在认知语言学与心理学中,指某种(精神的、内隐的或者公共的、外显的、物质化的)表征之表征,“在其中包含着低层次表征的更高层次之表征”③。在这一用法中,元表征已然涉及媒介间的转换,譬如:精神表征呈现为声音或图像实体,反之亦然。在媒介间(图像—语言)转换与翻译的情况下,像似与规约符号、语言与视觉表征之间建立起约略的、松散的对等系统。跨媒介的元表征凸显了以上诸要素间的张力,同时也证明了单媒介无法表达感知的多模态特性。语言与视觉文本都是潜在的图像文本或像似文本。不论是像似符号占主导还是规约符号占主导,这两种符号都处于或多或少的相互张力之中。玛格丽特著名的题铭“这不是一只烟斗”与烟斗的图像表征,彰显了图文不同表征对象之间的相互抵牾。元语言文本(譬如述画书写【ekphrastic】、电影小说、图像诗)通过探求语言表征的局限,诉诸视觉形式(图解要素、真实或虚拟的电影镜头、艺术品、梦境、幻觉、心像等)反映出语言媒介的不完整性。元视觉文本借助图像与语言信息的并置,凸显二者的差异,从而揭示出视觉表征的不完整性。
视觉艺术(尤其是绘画)中规约与像似要素之间的张力业已得到充分的研究。相比之下,心像由于其稍纵即逝、难以言表的特性,尚未得以深入探究。小说文本中语言与视觉张力的第一可能来源是虚构行为的双重性质——叙述表征中模仿与叙述(diegetic)层面、呈现与讲述之间的差异,用格雷马斯的术语来讲,就是叙述的行为与认知层面之间的差异。任一小说作品都既是一个文本又是一个虚构的世界。阅读行为涉及语言表达与感知的视觉模式(譬如读者从故事世界中衍生出来的心像)之间的相互协调。相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读者处于有利位置,因为他(她)的视觉“盈余”囊括了多元的视角,激发对虚构世界的心像。文本提供的图式化指涉框架与读者意识对虚构世界的综合心像之间存在意义的罅隙。我所说的“虚构世界的心像”大致相当于罗曼·茵加登(Roman Ingarden)的文本“具体化”层次。依茵加登之见,艺术作品是一个包含着很多不确定点的“图式化构成”,在阅读过程中被读者部分地充实(具体化)。
语言与视觉张力的第二个来源是叙述功能讲述与观察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在第一人称的参与故事叙述者(人物叙述)身上最为明显。第一人称的参与故事叙述者(见证—参与者)在保留自身部分“不可见”的同时,拥有在虚构世界中观看他人的特权。他只有从外部被他者作为模仿对象或者从内部作为“内体验的语言”(巴赫金语)时,方可被观察。作者的全知全觉观念和将“看”等同于“知”,有时会导致对作者视像隐喻的现实主义式理解。一些受福柯影响的批评家甚至对现实主义作者求全责备,认为他们通过“全景视角”对人物实行警察式的监控。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无法苟同。作者并不拥有完全的知识,他们只是在叙述的过程中,通过叙述中介(narrative agency)扩展自己的理解与知识。叙述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而非由作者向读者传递的现成的信息包。作者的功能分配于他所调停的叙述中介,譬如:将物理视像(亦即虚构世界中视像)的功能分派给参与故事的叙述者或某一人物。显而易见,作者—叙述者并不能(物理地)“看见”故事世界。任何“语像”(verbal icon)都只是形象创造的蓝图,而非形象本身。第一人称的参与故事叙述者处于沟通作者与人物的跨媒介位置,体现了语言与图像、表征中模仿与叙述层面之间的张力。叙述者对“全景视像”的“特殊欲望”由于“知”的阈限受到阻滞。
元视觉文本
肖像画是元视觉文本的一大类。尽管肖像画遵循各自时代的美学与文化惯例,但是模特与其表征的相似性是肖像画不变的原则。相似性规定就包括姿态(posing)。尽管姿态受艺术家(肖像画的作者)的操控,但它归属于所画的模特:姿态意味着确证画中人物的身份。这样一来,肖像画就转变为第一人称叙述。肖像画包含着像似要素与规约—指示要素(叙述)之间的张力。而后者(姿态,手持之物——书本、地图、工具,衣饰,背景等)发挥了身份确证的功能:它们意味着特定现实的投射与解读。
希区柯克(Hitchock)的电影《后窗》(Rear Window,1954)体现了角色—观察者对视觉意义的追寻以及与叙述操控的争斗。正如影评家所言,希区柯克电影中的“窗户”正是一面镜子。后窗对面房间里发生的所有的事件,林林总总的生活故事,或多或少皆可看做主人公与他的未婚妻丽萨“潜藏”的故事——在潜意识驱动层面渐次展开。因此,通过后窗所看到的故事揭示了潜藏和压抑在角色间或传统或模糊的对话之下的一切。观察,或曰见证或曰“眼睛”的角色,由于主人公的职业而自然主题化:杰夫是一位摄影记者,他并非情愿做一位观察者,而是因为腿有残疾,不便四处活动。作为行动不便的补偿,他沉浸在孜孜不倦、持续不断的偷窥之中。无论从电影制作还是电影观赏的角度而言,《后窗》都是一部自我反射的电影。整部电影充斥着照片—相机的运用。杰夫可以看做是其他人物潜在生活故事的叙述者,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通过他的眼睛展开。在凶杀故事的叙述中,摄像机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杰夫熟睡,不再偷窥,电影镜头径直扫过后窗、院落),杰夫的“后窗”仍然充当着主要的参考点——即使动用“客观照相机”时,希区柯克依然通过杰夫“后窗”的视点给观众以附加的信息。影评家对杰夫古怪行径(痴迷于偷窥、抵制婚姻)的原因缺乏深入的探究。他们总是将其归结为杰夫的个人中心、同性恋压抑、阳痿、忧郁、神经衰弱。尽管影片中充斥着众多与性相关的隐喻和双关,杰夫潜在的同性恋与阳痿还是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影片中的两位女性斯特拉与丽萨以常人之心揣度杰夫。起先,她们认定杰夫行为变态,从而设置重重障碍以阻止他,为将杰夫的注意力从近乎偏执的后窗偷窥转移开来,她们与杰夫不停交谈,并不时打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们最后也都加入了偷窥的游戏。电影的图像与角色之间的交谈有着明显的冲突。如果说希区柯克电影中的音响是对视觉形象的补充,那么人物对白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在《后窗》中,人物对白凸显了语言与视觉之间的内部冲突——它们之间是紧张的、敌意的、悖反的,刺耳、焦虑的语调遍布整个影片。人物的语调与音响、音乐相冲突,而后者是为衬托、呼应视觉形象而服务的。在希区柯克这一视觉元文本中,存在着一个无言的语言对应物。这一对应物经由尖叫、刺耳的语调、叹息、杰夫房间神秘的声音显现出来。
视觉与语言的冲突成为电影《后窗》的主轴,其他二元对立(女性—男性、传统—前卫)皆从属于这一主轴。希区柯克从早期的默片尤其是德国表现主义电影获益良多。《后窗》仿效了默片的电影结构,影片中的视觉信息与语言表征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另外,影片通过摄影记者杰夫促成了电影与照片的连接,使有声电影的观众意识到电影文本中语言与图像固有的张力。
在视觉媒介中,经由语言媒介而来的元小说和元叙述的手法发挥了新的功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小说中,作者与人物的转喻性接触(metaleptic contacts)通常会产生人物的“超现实”效果——人物被提升到与真实作者平起平坐的本体地位,而作者的活动能力介于神、人之间。纳博科夫的小说《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里,小说人物听到了“书页爆裂的神奇声音”,而这一页乃是小说中人物得以创造的一页。随着这一页抛入作者的废纸篓,此人物在小说世界中的生命便宣告结束,但他却在处于外叙述层面的现实世界中活了下来。在《洛丽塔》中,“真实的”洛丽塔在母亲分娩时本已殒命,但她却作为作者想象力的产物焕发出不朽的艺术生命力。还有马克·佛斯特(Mark Forster)的电影《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2006),影片中的作家Karen Eiffel通过元虚构进入了她所创造的人物的生活,作家与人物的相遇使作家褪去了文本外操控创作的神性(Karen Eiffel以擅长通过各种残忍手法使小说主人公毙命而著称),降为食人间烟火的真实角色。与小说人物遭遇的过程中,Karen Eiffel逐步放弃了原先设计好的迫使主人公死亡的构思计划,改变了小说的结尾。原因很简单,主人公不再是书页上的“纸人”,她不能杀死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
元语言文本
相对于元视觉表征中不完整或虚拟的语言对应物,元语言文本过量的语言化则意味着对视觉表征缺乏(叙述者和人物都竭力去“看”,但往往最后无功而返,或只能在想象中实现)的补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螺丝在拧紧》(Turn of the Screw)堪称范例——这是一个能够很好地激发视觉想象的文本。圣诞夜的朋友聚会上,道格拉斯道出了一个深埋多年的恐怖故事:年轻的女教师接受了一份照看两个小孩的工作,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前仆人昆特的幽灵频频造访,妄图控制两个小孩。女教师为保护孩子同幽灵周旋,竟被当做精神失常。女教师给雇主写信,企图挽回整个局面。正如克瑞斯汀·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所言,詹姆斯的小说“邀请批评家在无意识中跳出家庭女教师的两难的困局”④,批评家通过添加缺失的细节开始重写整个故事。与此类同,女教师将故事语言化是对视觉缺乏的补充。幽灵与“信件”(亦即女教师亲自写的关于故事的信)之间互相参照,阐明了故事作为叙述与观察相悖反的元小说意义。
詹姆斯小说中的视像与镜子结构特别引人注目。女教师总是在寻求“镜像接触”:通过视线的交接,她将“自我”认作他者,重获对他者的视觉操控。对女教师而言,视觉是最可靠的信息之源:“看”便意味着“知”,从而实现语言化(“我要求他知道,确保他知晓的唯一途径就是使他看到”⑤)。然而,女教师的有限视角限制了她对叙述的操控,视觉“盈余”超出了女教师本人的阈限,并顽强抗拒着语言化。在我看来,解释詹姆斯小说中视觉与语言之间张力的路径,除了精神分析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考察其叙述功能的分布。
若干事件的回环往复组成了故事的框架,它们以颠覆或变形的形式在主要叙述中重复出现。小说制造了一系列完美的镜像接触:妈妈看孩子在看什么;第一人称叙述者通过道格拉斯的一瞥“阅读”他的思想;女教师看道格拉斯在看何处以及道格拉斯看女教师在看他等等。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女教师的故事却蜕变为一系列犹豫不决的反射与不完美的视觉接触:孩子们也是一面镜子,但他们不反射任何物像,管家格鲁斯太太似乎是一面不完美的镜子,幽灵总是避免与女教师直接接触。因此,留给读者的只是一系列不确定,从来都不知道镜子的背面是谁。
小说的三重叙述媒介(女教师、道格拉斯和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已经引入了语言与视觉的众多差异和冲突。叙述在小说开始时就被延宕,基本信息少得可怜,道格拉斯也暗示出故事未来的发展也不会改变这种局面。女教师(以及读者)对故事的“视觉化”怀有强烈的欲望,企图操纵叙述的进程。于是乎,女教师终于跳出了故事,接管了作者的角色,代替其他人物进行虚拟的言说。
女教师语言化的机会遭受重重限制:家庭主人对她的警告——“不准打小报告”;管家不识字,无法阅读校长的来信,加上她浓重的拉哥尼亚口音总是叫人似懂非懂;孩子们对她的抵制与排斥。在女教师的手稿中,将第一次幽灵显现与信件联系起来,破天荒地“看”不意味着“知”,语言化遭遇阻滞。管家认定迈尔斯在学校里偷了信,因此被校长开除。这就建立起信件与秘密败露之间的隐喻联系。对女教师而言,第一次幽灵显现是视觉操控的反转:她反被陌生人观察。女教师被监视的感觉在湖边风波中达到高潮。
女教师在孩子们与幽灵之间充当着幕帐的角色(“我看到的越多,孩子们便看到的越少”⑥)。吊诡的是,孩子们逃出了女教师的视线,背着她与幽灵交往。女教师需要尽快目击幽灵,以便保持视觉接触,达到“完全视域”。为了弥补与幽灵接触的不足,她要求孩子们彻底招供(语言化):“你们为什么不向我坦白?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互相理解,活在真实的世界里。”⑦
小说《螺丝在拧紧》中视觉和语言的张力与叙述权威的争夺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布斯(W.Booth)所言,詹姆斯经常把“纯粹的反射者”转化为“充分的行动者”。他的很多小说都采取两种叙述者不完全融合的双重聚焦形式。⑧《螺丝在拧紧》的情况更为复杂,远不止观察与叙述之间的矛盾、冲突。詹姆斯特意采用视觉与戏剧的隐喻来解释他的写作方法。对詹姆斯而言,小说写作是“在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协商”⑨。《螺丝在拧紧》激发“视觉”阅读,女教师作为故事讲述者保持着对故事的控制。一方面,叙述者追求对语言化的控制以及“观看”人物内心的权力。另一方面,女教师在其他人物身上寻求她的镜像反射的同时,把自己降格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女教师在竭力操控语言化、接近其他人物的内心的过程中,却由于自身视域的不充分与扭曲,永远退缩到了无助的旁观者地位。
结 语
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考察,语言与图像的张力是对知识权的争夺,是两种对立的认识论之间的斗争。“文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语言与图像符号之间持续不断争夺主权的故事。两者都宣布自己对‘自然’拥有专门的权力。”⑩在对知识的有限接近以及对“可视物”语言化的有限可能性之不确定语境中,元表征叙述阐发了这一假定的生成过程。人类的认知是多模态的:不同来源(语言、视觉、听觉、嗅觉等)的多重线索共同形成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知识。这些线索的意义并非一时半会即可明了,并且不同的读者或观众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挪用这些线索。正如鲍德维尔(Bordwell)所言:“观众能够以导演无法预见的方式超越电影给定的信息。”(11)鲍德维尔的话适用于任何艺术作品,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它们都向新的视角开放,向比作品瞬间交流宽广得多的内容开放,时刻做好了迎接新的意义的准备。跨媒介元表征(不管它是视觉表征的语言再表征,还是心像翻译为语言或者语言触发为心像)有效地沟通了感觉与知识之间的断裂,充当着人类遨游世界的导航仪。
① Joseph Courtés,Du lisible au visible,Bruxelles:De Boeck Université,1995,p.243.
②W.J.T.Mitchell,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Chicago&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83.
③Deirdre Wilson,“Metarepresentation i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in Dan Sperber(ed.),Metarepresentations: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11.
④Christine Brooke-Rose,A Rhetoric of the Unreal Studies in Narrative and Structure,Especially of the Fantast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28.
⑤⑥⑦Henry James,Complete Stories 1892-1898,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96,p.652,p.668,p.685.
⑧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83,p.346.
⑨Doroth Hale,“Henry James and the Invention of Novel Theory”,in Jonathan Freedma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199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86.
⑩W.J.T.Mitchell,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Chicago&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43.
(11)David Bordwell,Poetics of Cinema,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2008,p.149.
〔责任编辑:刘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