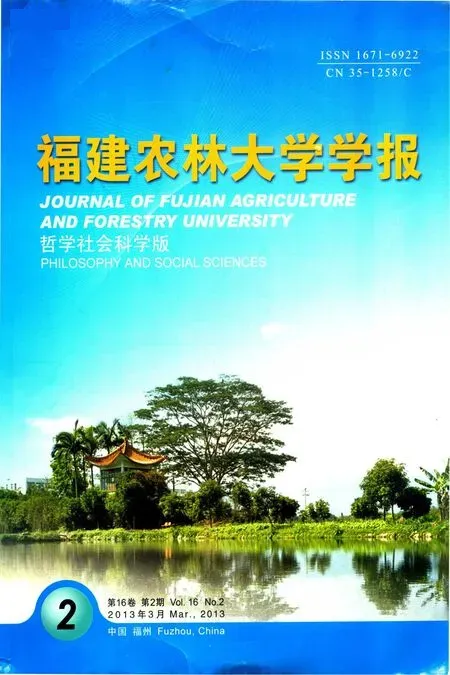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心理动机分析: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黄明妆
(福建农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和策略,不仅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其他诸如应用翻译也可觅到它的踪影。目前译界很多翻译理论都只是从某一个层面解释译者的某种翻译行为,真正涉及隐藏在译者“创造性叛逆”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和思维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翻译的过程及原文作者、译者与译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结合陈来元翻译《大唐狄公案》的具体实践,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对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心理动机进行分析。
一、“创造性叛逆”研究回顾与思考
“创造性叛逆”现象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并不鲜见。它最早由法国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完全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因此,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1]。此后,我国著名学者谢天振在《译介学导论》中指出:如果说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身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2]。谢天振还从具体表现形式层面把“创造性叛逆”分为无意识型和有意识型2类共4种:第一种为个性化翻译,第二种为误译与漏译,第三种为节译与编译,第四种为转译与改编[2]。
埃斯卡皮从作品参照体系的改变和作品生命的延长与传播2个不同层面对“创造性叛逆”行为进行界定,因此,所有的翻译行为都是“创造性叛逆”。谢天振则注重从“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对它进行阐述,并把“创造性叛逆”同一般的翻译行为区别开来。不管译界如何界定和剖析“创造性叛逆”,可以认为:“创造性叛逆”不仅仅是一个外显的语言转换过程,它背后还隐藏着译者复杂的主观努力和思维运作过程。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为了达到翻译目的而造成的对源本的背离,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则是译者在进行有意识的翻译活动时做出的无意识行为。无论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还是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都是译者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翻译行为的具体表现。本文以下论述只针对“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展开。
二、社会心理学理论与“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
翻译不仅涉及语言、文化等各门学科,还涉及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本读者等人际关系。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行为,它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主体间的交际行为,交际方通过语言文本进行交流。可以说翻译是跨文化对话空间的一种延伸和扩展。译者主体进行翻译活动时,基于源语语境和目的语语境的变更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处理,容易受到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Festinger的认知不和谐理论认为认知不和谐是产生压力的原因。当人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不可逆转或不可改变时,减少压力的主要途径是改变自己的态度,以达到认知和谐状态。Heider的认知一致性理论认为,人们常常接受适合他们总体认知结构的态度,往往在他们的态度之间,或者态度与行为之间寻求认知上的一致。尽力保持或恢复认知上的一致性是人们在交际中的一个主要心理倾向。Kelly的动机理论认为,人们在交际中总是采取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态度,并坚持站在对自己利益最大的一面[3]。
李占喜在众多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并把“认知和谐”界定为译文读者在认知处理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过程中,译文话语在译文读者心理上产生的认知上的一致性[3]。译者的翻译态度以确保读者的认知和谐为前提,译者的翻译行为,即译者作出的语言选择和采用的语用翻译策略,应确保这种和谐状态的实现。本文进一步引申,把它细分为原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认知和谐、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认知和谐以及译文读者与原文作者之间的认知和谐。达到三者间的认知和谐是交际方交际的主要目标。
三、翻译过程与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
广义的翻译过程不仅包含狭义的语言转换活动,还包括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生成和文本生命的历程等过程[4]。结合翻译过程涉及的语言转换、译者的动态思维理解和译本生命意义的衍生等层面,本文把翻译过程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译者作为读者,对原文进行解读判断和阐释阶段;第二阶段,是译者作为译文作者,进入语言转换的译文创作阶段;第三阶段,是译文读者与原文作者、译者的对话阶段。一般来说,译者是以读者进行潜在阅读并接受译文为前提进行文本选择和译文创作的,换言之,读者的阅读期待构成译者翻译行为的原因和目的。因此,第三阶段发生在译文读者阅读译文的具体行为中,也隐含在译者对原文进行解读和创作的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解读是这个阶段的开始,而译文创作是这个阶段的延续。
作为前2个阶段的行为主体,译者的参与构成这2个阶段的核心内容,译者的心理活动也尤为突出。在第三阶段,由于读者的实际介入,译者翻译行为的目的性更为凸显,翻译活动涉及的人际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与读者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等边三角形关系。“认知和谐”是维系三者平衡关系的基础和关键点。译者的最终目的是让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形成最佳认知和谐。任何双方的认知不和谐,都会破坏这个平衡状态,达不到成功交际的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同时兼有的3种身份:读者、语言转换者和作者,译者变成了一个矛盾综合体。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的声音和立场,但这些最终都以“译文”的文本形式呈现出来。基于译者多层面的心理活动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创造性叛逆”也成为必然。
(一)源本解读的“创造性叛逆”与“认知和谐”
翻译的第一阶段对译者来说是一个理解阐释与认知判断的交际过程。与作者达成最佳认知和谐是这个阶段的目标。为了达到目标,译者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相关认知,以自己的审美和价值判断,仔细认真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与交际目的,做到不歪曲、不偏离,以完成对源本的最初认知判断。相对于源本来说,译者是读者,他要尽力向原文靠拢,此时原文作者的声音变得强大。这与传统的“忠实”翻译观是相符的。但不同的文化语境、历史渊源、语言体系、法律规范等带来的文化差异,势必造成译者的认知审美或个性与作者意图发生冲突。这时,译者要么“忠实”完整地接受源本的交际意图,要么对源本进行篡改和重组,使之符合自己的认知审美。两者相比,显然前者的压力大于后者。因为“忠实”完整地传达作者的认知意图,意味着译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与自己意愿相违背的思想理念。这种压力,对任何一个有个性,或有明显价值审美取向的译者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根据Kelly的动机理论,译者为了减少心理内在压力,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会对源本的交际意图进行篡改和重构,即出现理解阐释的“创造性叛逆”。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态度极为积极主动,作者是被动地与译者产生认知和谐的。如译《大唐狄公案》的陈来元,在译丁秀才写给他的情人——他父亲的小妾王月花的一首情诗时,觉得“如果直译此诗,有的地方显然不堪入目”[5]。陈来元当时身处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译者本身还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许多观念是难以全盘接受的。基于内心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倾向,他颇费一番内心的挣扎,最终决定不直译此诗。
“翻译总是在差异性基础上谋求一种合理交往,是一种语际和文化际的对话,交往和对话都必须建立在一切确切意义或公式的基础上,否则,对话和交往就不能进行下去”[6]。译者对源本的解读作为交际的第一步,首先需要与作者达成认知和谐,否则后面的交际就无法继续。翻译家傅雷是个倡导“忠实”标准的译者,但他在翻译时,“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翻译”[7]。这个“化为我有”,既有对原作的认同,也有“创造性的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正是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寻求与交际方的共性和认知和谐。
(二)译文创作的“创造性叛逆”与“认知和谐”
译文的创作阶段其实就是语言的选择阶段。对于译本来说,译者是作者。从读者到作者,身份发生转换。作为作者,译者可以在译本释放自己的声音,表现自我的存在。源本通过译者的语言转换,处在一个可能与源语文化语境完全不同的参照体系中,地理位置、时代背景、历史文化、读者的认知和价值判断等,都是构成这一参照体系的要素。据Festinger的认知不和谐理论,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参照体系差异越大,译者所承受的压力也越大,思想冲突也愈激烈。如上述的陈来元认为翻译《大唐狄公案》的难点不在于能不能读懂外文上,而是在读懂的“再加工”,或“再翻译”上[5]。
译者在转换文本的过程中,还要考虑潜在读者的存在。翻译的根本在于影响受众,翻译目的的实现有赖于受众,所以受众理应成为翻译行为关注的焦点[8]。作为译文的作者,译者在语言转换和选择翻译策略时,是以与译本的潜在读者达成认知和谐为前提和目的的,否则译本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译本要顺应读者的阅读期待,读者的声音在译本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译者的译文创作过程也就是读者阅读审判过程。读者在阅读译本时,自然会寻求与原文作者,甚至是译者的认知和谐。译者此时身负双重使命:在与读者达成认知和谐的同时,也要让读者与原文作者达成认知和谐。由于有了读者的潜在介入,译者与作者、读者的抗衡更加激烈,压力也陡然增大。此时,“译者的翻译态度应该是尽可能充分地传达作者的意图,或者对其信息意图进行操作性重构,必须以确保译文读者认知和谐为前提”[3]。
翻译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9]。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和谐以及潜在读者的阅读期待,无疑使译者处于被动地位,翻译的不可逆转性,更使译者内心压力升级。据Heider的认知一致性理论,作为突破口,译者有意对源本信息意图进行操纵或重组,如删减、改译,甚至完全违背源本交际意图进行再创作,以使译本与读者产生共鸣并被接受,达成认知一致性。此时“创造性叛逆”已不可避免,但必须满足2个前提,即对源本的审美判断和选取,以及对译入语语境参照体系和读者阅读期待的认知。只有二者结合,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才得以顺利进行,译者与读者,读者与作者才能达成认知和谐。如上文提到丁秀才写的那首情诗,陈来元如果“忠实”地直译,无疑会给当时的中国读者造成强大的思想意识冲击。因此,陈来元将它译成这样一首不俗的藏头诗:绣衾香罗帐,温柔富贵乡。情痴无章典,心醉忘纲常。月圆成鸾凤,花好配鸳鸯。心曲诉深闺,肝胆照愁肠[5]。译者一方面按自己的审美意识去改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顺应当时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观念,把露骨的描写变得含蓄,与当时国人“含蓄、内敛”的审美标准达成认知和谐。说到底,这是对原文进行语言、语篇甚至思想意念上的“创造性叛逆”。《大唐狄公案》在国内出版后,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和追捧。这也说明译者为了与读者达成认知和谐而进行深思熟虑的“创造性叛逆”,并没有改变原文和译文的交际功能与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交际的成功。
四、“创造性叛逆”的实质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一方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解读源本与创作译文,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文化、语言规范、读者认知审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原文的交际意图与制约因素的差异越小,越能达到交际方的认知和谐。反之,二者差异越大,他们的认知越难重合。为实现翻译目的,译者会寻求摆脱源本的束缚与操纵,通过直接的篡改,或迂回的变通,重构作者的信息意图。
(一)动态的思维过程
理解一个文本是一个不断地超越既有认识并向前发展的运动过程[10]。由此,翻译的实质不是对原作品意义的追索或还原,而是译者能动的理解诠释过程,是译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同时也是译者在理解他人的基础上对自我本性的一次深化理解[11]。从译者对原文内容的批判性接受,到为达到双方认知和谐而进行的思想斗争,再到译本生成的“创造性叛逆”,无不体现译者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痕迹。“创造性叛逆”正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自我和他人的重新认识、审视和再判断,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彰显。
翻译是“在特定译语社会环境中,跨越语言文化边界,通过有效运用语言象征手段影响特定译语受众而创作语篇的过程”[8]。为了让译本读者接受译文并付诸于行动,最终实现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谐,达到交际目的,译者运筹帷幄,不断做出语言选择和利弊权衡,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是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过程,也是动态的思维抉择过程。
(二)“忠实”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要“神”、“形”兼备。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似乎违背了传统理念,走向另一个极端。作为2种不同文化的中介者,译者把忠实传达原文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天职。但文化差异势必造成“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译者好像是本着“忠实”的心做了“叛逆”的事。介于“忠实”与“叛逆”之间,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创造性叛逆”的本质。
Nord认为忠诚包括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为实现译文预期功能所进行的必要调整,包括改变原文的内容和语体特征(如“施加影响类”语篇)[8]。为了促成原文和译文的交际功能,译者对原文内容或语体特征进行篡改的“创造性叛逆”,正是译者“忠实”于翻译职责的表现。
再叛逆的译文中也有十分忠实的成分,再忠实的译作里也有十分叛逆的一面[12]。鉴于此,绝对“忠实”的翻译是不存在的,至少译者在译本创作时,通过语言转换就已改变源本的语言体系和参照体系。译者在“忠实”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叛逆”,又在“创造性叛逆”过程中体现“忠实”,“叛逆”与“忠实”在译者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和谐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正体现翻译的本质。
五、结语
翻译过程就是一个人际交往的过程,“创造性叛逆”以灵活的翻译策略传达作者的交际意图,谋求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和谐,达成交际目的。它是有效的语用翻译策略,也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认真严谨的翻译态度的彰显。它还是一个动态的思维过程,与“忠实”的翻译构成翻译的本质。但是,基于译入语语境以及交际方关系的复杂性,“创造性叛逆”不应是译者的主观臆造,它要符合译文的内在逻辑和语言规范,并被交际方接受。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心理动机和思维过程,可以更深层次探索译者行为背后的内在制约因素,进一步认识翻译的过程。
[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37.
[2]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2-84.
[3]李占喜.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J].外语教学,2012(1):101-104.
[4]许钧.简论翻译过程的实际体验与理论探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4):33-39.
[5]陈来元.我译《大唐狄公案》的酸甜苦辣[J].中国翻译,2012(2):82-85.
[6]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24.
[7]金圣华.傅雷与他的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1998:272.
[8]陈小慰.对德国翻译功能目的论的修辞反思[J].外语研究,2012(1):91-95.
[9]CHRISTIANE N.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6:31 -32.
[10]张道振.意义阐释和文学翻译的伦理[J].中国翻译,2009(3):18-22.
[11]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12]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