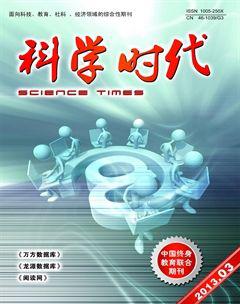魏晋名士儒道互融思想流变探析
梅柳
【摘 要】魏晋玄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阶段,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阶段,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阶段。他们围绕玄学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主张。
【关键词】魏晋玄学;名教;自然
魏晋玄学是儒道两家思想融合的产物。玄学从契合当时政治经济背景出发,将儒家孔孟人伦之底蕴与道家老庄自然之哲理较为完美地融为一体,这种融合是基于魏晋玄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来展开的。纵观魏晋玄学家们由此进行的一系列思考与探讨,可以看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正始玄学阶段、竹林玄学阶段以及元康玄学阶段。正始玄学阶段,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强调“名教出于自然”,儒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道本儒末,崇道抑儒”;竹林玄学阶段,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然”,儒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越儒任道”;元康玄学阶段,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强调“名教即自然”,儒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内道外儒,儒道兼综”。
一、正始玄学阶段:道本儒末——“名教出于自然”
三国两晋时代,自然与名教产生了严重的分离。如何调整或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使双方获得协和与统一,成为玄学的中心课题。何晏和王弼是正始玄学的主要创立者。他们注意到儒家经典中关于本体论的缺失,祖述老、庄,提倡“以无为本”,是玄学“贵无论”的代表。何晏从《周易》、《老子》这两部经典中提炼了“以无为本”的命题,奠定了“贵无论”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儒道两家很难调和,何晏没有找到援道入儒的契机,所以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提出系统“贵无论”思想的是王弼。他先是创造性发挥老子思想,提炼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哲学,进而将之推向社会实践,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论证为“无”与“有”、“本”与“末”的关系,他认为圣人梳理百行,统率殊类,乃是“因其分数”不得不“制官长”,“立名分以定尊卑”。因此,名教的制定乃是顺势而为,无为而为,并无执为之意。圣人体用如一,必顺自然而制名教,即名教本身是自然之道的表现,所以名教的产生完全是自然的,并非人为。这样王弼通过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解释为本末体用,确立了名教生成的合理性。王弼还指出名教需依自然而成。即名教功能的发挥也要顺应自然。圣人“因物之性”,顺任自然,不专执于刑名政教之治,使其自然发挥功能,则万物各得其所,各种社会关系自然协调。不识自然无为为母、为本,反而着眼于刑名礼教本身,“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1]这种背离自然之道,陷于有为之域的做法导致了“过此以往,将争刀锥之末”[2]的后果,离开自然之本,而执于名教之用,会导致名教的异化,即名教在现实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其本来的目的背道而驰。期望百姓朴实、敦厚,却虚伪、狡诈滋生;力图社会和谐稳定,却争端、祸乱四起。执作为末用的仁义礼教为本,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丧失其应有的价值。“自然”是根本的,“名教”是产生于“自然”的末,因此就不能舍本逐末。正是由于人们执着于有为,舍本逐末,弃母用子才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所以,要扭转这一状况,就必须向作为本体的自然之道回归。用王弼自己的说法来讲就是“崇本息末”。 在上者顺应自然,紧握道体不失,以体无之心治理天下,顺任自然而不执于名教,则名教转活,成为治国利器。反而能全名教之序,成名教之功,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仁义礼教的功能,从而实现社会的理想和谐,这是王弼关于名教自然问题的理论归宿。
王弼面对魏晋时期名教流于虚伪的现实,从先秦道家那里得到灵感,将其自然观念嫁接到名教上,将二者理解为本末、体用关系,肯定了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提出了通过“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末”的方式,来消除现实名教所存在的种种弊端,重新确立名教社会的和谐秩序。这样,王弼通过其高超的哲学智慧,对其面临的时代课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二、竹林玄学阶段:越儒任道——“越名教而任自然”
正当正始玄学家们积极从事于“道本儒末”理论建构,努力消除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对抗之时,司马氏父子发动了高平陵政变,一次又一次地举起屠刀,杀名士、杀大臣、杀皇帝,致使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对抗空前激化,名教的虚伪、荒谬、残酷的表现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紧接正始玄学之后,以嵇康、阮籍等人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家们高举起批判的旗帜,否定君权,抨击名教,在其理论建构中抛弃了儒家学说的代表作品《论语》,而于《周易》、《老子》之外又从传统道家典籍中找出一本反对社会异化、注重生命个体的《庄子》,予以承袭、发展,从此,魏晋玄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竹林玄学”阶段。
竹林玄学阶段的最强音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越名教”,主张抛弃社会礼法的束缚;二是“任自然”,主张顺应人的自然之性,因此也可说成“越名任心”论。
嵇康之所以主张“越名教”,依据有二。一是根源于他的人性自然论。他认为,“人之真性,无为至当”,宛如“鸟不聚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3]一样,人性不受任何外力的羁绊。所谓“人之真性”就是“自然”,是指人的自然情欲,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需求和欲望,与世界万物的自然本性一样,是先天固有的,人的本性是“感物而动,应事而作,”这是人先天就具备的能力,这是不能违背的“必然之理”。他认为自然本能的人性特征是“从欲为欢”,其具体内容是“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4]对人来说,不遵循本性,迫于外在要求的行为并不是所希望的。而被称为“六经”的“名教”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困而后学”和“好而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人自觉意识的产物,它以约束人为主旨,是违背“从欲为欢”的本性特征的。所以,依据“六经”来保持本性自然状态的平衡是不可能的。由此,嵇康主张以从欲为欢,即可尽人之真性,并把名教看作束缚人性的枷锁,也为“越名教”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二是嵇康不仅认为“名教”是不自然的,而且认为“名教”是社会上一切伪善、欺诈等现象的根源。他通过古今社会的对比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名教对自然本性的摧残、对社会自然和谐秩序的破坏。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更是一团糟,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招牌,把名教作为其争夺权力的工具,并以此来打击和压迫士人,弄得人人自危,这样的名教在他看来便是 “以名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5]嵇康最后得出结论:“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 [6]从而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虚伪名教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现实中的合理性。
与之相对立,嵇康主张“任自然”。主要途径有三。一是实行“简易之教”,“无为之治”。他说:“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7]“简易之教”和“无为之治”是古代帝王治理万物的重要手段,他们“承天理物”,因循自然之道来推行教化,采用的具体方法是“君静于上,臣顺于下”,也就是无为而治,自然而然。这样,在客观效果上,民众则“不觉其所以然”,一切自然而然地进行,从而实现“天人交泰”和“群生安逸”的理想境界。二是养生。嵇康养生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要求人们恬淡自足,要求人们怡行养神,始终保持本性自然,高扬个体自我的意志自由。嵇康又阐释:“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必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通顺,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8]很明显,在嵇康的思想中,人贵在超越了是非得失,进入“泊然无感”、“守之以一,养之以和”的境地。三是“不存有措”的至人人格。至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不存有措”,嵇康认为“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9] “不存有措”是顺性而行,可谓“任心”的一种方法。能“不存有措”的话,就能实现心理的谐和,其次,“以万物为心”,也就是把自己看作万物的一部分,和万物协调共作,既能对民众宽大为怀,又能对民众尽责任,即“在宥群生”,自己则始终不离“道”,能实现自得。虽居君位,能如民众一样俭朴行事,“以无事为业”,“以天下为公”,其实际的客观效果是,君臣忘记了相互之间职位上的差别,民众则丰衣足食,这是至人无为、“归之自然”的结果。
在对儒道的态度上,嵇康崇尚道家自然无为,强烈抨击儒家名教伦理纲常,“越儒任道”。与王弼 “道本儒末”的理论模式相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完全抛弃了社会功能方面的考虑,彻底转入到了对精神意境的开拓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将个体生命和精神超越的思考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这构成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之辩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逻辑的必然环节。
三、元康玄学阶段:儒道兼综—— “名教即自然”
这一阶段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强调“名教即自然”,儒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内道外儒,儒道兼综”。
向秀将“自然”解释为自然的法则,人的心智情欲以及社会的伦理道德都属于“自然”的范畴。人的情欲只要“节之以礼”,出于人伦,就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这些理论,不仅将儒道完全融合,也充分肯定了儒家名教。
郭象反对当时较为流行的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本体论,他认为无不能生有,在郭象看来,万物存在的依据在自身,外在于自身的依据是不存在的。所谓“无”就是没有或空无,这样的“无”当然不能生成万物,也不能成为其根据。“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是说 “有”的存在尚需别的东西为依据,所以它也不能作为产生别的东西的原因或本体。万物产生于“块然而自生”,和“突然而得此生”,即“自己而然”,也叫“天然”,总之是一种“自然”。接着他提出其“物各自造”的“独化论”。在他看来,世上每一个事物的存在都是自然而然的,每个存在者自己就是自己的存在根据,在它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充当它存在的依据或原因,它的所然就是其所以然,所在就是其所以在,它的自然就是其必然,所是就是其所以是,生是自然而然的生,死是自然而然地死,一切皆自然如此,不假外求,这就叫天然,这就是自生,就是所谓的“独化”。天地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其终极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不是“无”的作用,而是事物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因此,名教亦不例外,仁义等名教道德规范植根于人性之中,既非功名利禄的诱惑所促使,亦非养生安命的需要所导致,而是天然如此。他还举例说,尧为天下所效仿,不在于尧占有天下人心,而是本于自然,所以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是统一的。万事万物成为现实是 “自生”的,没有任何缘由,所以在社会中君臣上下的区分和礼仪法度也是自然的本性使然,是自然而然确定的,并无人为的成分。因此,名教的产生和发展无须任何的本原和根据。伦理纲常、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有关的等级秩序都是“自然”或不可变更的。这样,郭象就把名教本身说成是自然天成、固定不变的东西,从而为门阀士族的统治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反应到对待名教的态度上,他认为应按照名教的自然之理去认识和遵从,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名教,甚至抛弃名教。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援道入儒,融合儒道,使传统学术的两大主流内在地沟通起来,促使儒家的思路坚实有力地伸向了思辨的领域。他们从抽象思辨的高度考察和论证纲常礼教,这为后来宋明理学家把纲常、义理、伦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l中华书局,1980,82页。
[3][4][5][6][7][8][9]邵先锋.从“名教出于自然”到“名教即自然”[D].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6.
注:
项目基金:2011年湘潭职业技术学院科学研究课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互融研究》(ZXSK2011-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