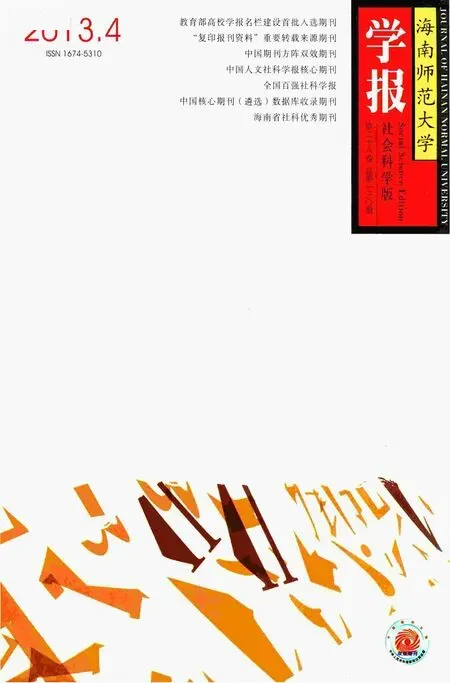论严歌苓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的家庭伦理书写
刘 云
(安徽大学 学报编辑部,安徽 合肥230039)
《第九个寡妇》在2006年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又不断再版,好评如潮。小说主要描述了一个叫王葡萄的女子,在土改中把被打成地主恶霸的公公孙怀清藏匿在自家红薯窖内前后二十几年的故事。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写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在这部小说中,王葡萄在7 岁那年因为家乡闹灾荒父母双亡,在乞讨路上被孙怀清买下做了孙家的童养媳,14 岁和孙家第三个儿子铁脑成了亲,结婚不久丈夫即亡故,在此之前婆婆已经去世,孙家其他两个儿子都在外闹革命,家中只剩下她和公公,共同经营一家小店铺,还种着几十亩地。因为孙家在当地算是家底比较殷实的,在土改时孙怀清被划为地主恶霸要枪毙,在同一批被枪毙的地主恶霸里只有孙怀清侥幸存活,被王葡萄背回家中仔细调养并藏匿了二十多年直至寿终而亡。这部小说有着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色彩,尤其是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表现,更是显示出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家庭(族) 、血缘关系为中心而后推衍至全社会的文化,对于家庭伦理的建构成为其社会伦理的基石。家庭伦理关系在儒家文化中地位非常重要,“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中就有两“纲”涉及家庭伦理,而君臣、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家庭关系在社会中的一种延伸。自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观念之后,经孟子的“五伦”之说再至董仲舒确立所谓的“三纲五常”,建立起一套完整严密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第九个寡妇》在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注重营造传统家庭伦理的氛围,比如王葡萄对家庭、对亲人都极为重视与维护,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美德,但是在此之外我们又能够感受到一些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很不相同的现代思想因子,使这部小说显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文化底色。因此,本文试从家庭伦理中父子、夫妻这两种最基本的关系出发来考察这部小说中的家庭伦理书写,以期对严歌苓的创作特色进行深入把握。
一 父子
在这里出现的父子实际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相当于一个家庭中的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不只局限于父子关系,也包含父女关系。父子关系是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儒家理想的父子关系形态是所谓“父慈子孝”,这其中又格外强调孝,把孝视作一切德性的根本。为了履行孝道,孔子甚至主张“子为父隐”(《论语·子路》) ,孟子则不惜“窃负而逃”(《孟子·尽心上》) ,①关于这一点,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具体可参见郭齐勇《儒家伦理争鸣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郭齐勇《〈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可见孝在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中的重要性。
在《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藏匿孙怀清的根本出发点即是孝。在当时极为严峻的政治背景下,王葡萄的行为属于藏匿死刑犯,且是地主恶霸死刑犯,若被发现也是要被处以死刑的,但是她一点都不畏惧,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个人虽然不是他亲生的爹,但是若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自己;这个人不坏,不该被判死刑,若是这个人死了,她便再也没有爹了。因此在后来的二十几年里,无论中国社会发生怎样的动荡、经历怎样的政治风波,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她都一如既往地用自己柔弱的肩扛起孙怀清的生命。她把这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当她发现孙家二儿子也即她的情人少勇为了个人前途竟然主动向上级请求枪决自己的父亲时,她便决定离开这个“不孝子”,甚至为此隐瞒了她已怀孕的事实。为了养活孙怀清,她狠狠心把刚满月的孩子送了人,因为这个孩子会占用本已少得可怜的口粮。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留给孙怀清吃,宁愿自己忍饥挨饿,这与二十四孝中汉朝郭巨为母埋儿的故事何其相似。
但是我们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孙怀清与王葡萄这对父女关系,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儒家父子关系的传统模式。
这首先在于孙怀清与王葡萄的关系是对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中重男轻女模式的反拨。儒家传统家庭关系中强调父子关系,因为女儿总是要嫁入别家跟人家的姓,只有儿子可以子承父业,因此,二十四孝的故事中出现的都是孝“子”,而无孝“女”。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却颠覆了儒家家庭伦理中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可以媲美二十四孝子的孝女形象。尤其是孙怀清与王葡萄之间的关系既非真正的父女,他们无血缘关系,也已没有法律上的必然联系,公媳关系随着铁脑的死亡自然解体,但是当孙怀清被划为地主恶霸的情况下,连他自己的儿子都要与他撇清关系,这时王葡萄对于孙怀清的“孝”就显示出不同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色彩。王葡萄的孝行在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圣经·旧约》中出现的路德的形象。路德是拿俄米两个儿媳中的一个,在拿俄米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相继去世之后,年老的拿俄米希望回到自己的故乡伯利恒,她觉得没有理由要求两个儿媳与自己同行,大儿媳俄珥巴也更愿意留在娘家,而小儿媳路德却决定跟随老人,她认为自己既然嫁给了丈夫,就应该照顾好他的家人,这是自己的责任,况且拿俄米是那么慈善的老人,所以路德陪伴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但是这时他们已身无分文,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路德就到田地里去捡麦穗。田地的主人波阿斯知道了路德的事情,就请路德吃饭,路德只吃一点点,把剩下的都拿给了拿俄米。拿俄米希望路德能够幸福,就积极撮合了她与波阿斯的婚姻,路德与波阿斯仍然继续奉养拿俄米直至去世。王葡萄与路德都是以儿媳的身份孝敬丈夫的父亲,且始终以父亲为第一位,奉养到去世,不离不弃。王葡萄与孙怀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对于孝的履行上,王葡萄却比与孙怀清有血缘关系的孙少勇更为纯粹,这不能不说是对儒家传统男性话语的有力反拨。
其次,孙怀清与王葡萄之间不是儒家传统中强调的尊卑有序的家庭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和谐的家庭模式。自王葡萄来到孙家,孙怀清对葡萄就非常关心、爱护,但这种关心又是非常有节制的,非常注意保护葡萄的自尊心,他们二人一直以一种平等的、像朋友一样的关系相处。在这个家里葡萄是最能干的,也最能帮上孙怀清的忙,她收账、打理店铺,做各种活计,都是一把好手,他们又是合作者。孙怀清对待葡萄的方式也是形成葡萄自信、乐观性格的主要因素。这有别于儒家父子关系中以父为纲,长辈与儿女之间命令与被命令、管教与被管教的上下关系。这一点在孙怀清对于葡萄情感问题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到。在铁脑死后,王葡萄又经历了几段情感,孙怀清从没有横加干涉,甚至还为她的终身大事考虑、谋划,王葡萄也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情欲而对孙怀清有任何羞怯之意。王葡萄在情感问题上的独立自主与任性而为都与儒家以夫为纲的伦理道德有悖,但孙怀清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一直很开明,他希望葡萄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这一点他很像拿俄米,显示出对于葡萄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人格的尊重与关爱。这正是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中严重缺失的。儒家的“孝”是与“敬”、“顺”并置的,“敬”、“顺”都会导致对于个人主体性的漠视,乃至最终丧失独立思想与反抗精神。对于“顺”的过分强调使儒家传统文化缺少现代文化中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观念,缺少对于个体人格的尊重,最终演变为鲁迅笔下的“吃人”的封建礼教。但是在孙怀清与王葡萄的关系中,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对他们之间那种平等和谐的相处模式印象深刻,这种模式显然不是儒家传统家庭伦理所能涵盖的,而是现代西方民主、平等、自由思想对儒家传统伦理规范的补充与修复。
再次,小说通过孙少勇的行为对儒家传统孝悌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与王葡萄不顾生命危险全心全意照顾孙怀清的行为相比,孙少勇放弃老父、只为自己前途着想的行为则显示出儒家所谓“孝”的局限性——儒家强调的孝悌之道往往成为社会伦理关系的缩影。《论语·学而》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也就是说,一个孝敬长辈的人,很少会冒犯上司,一个不会也不敢冒犯上司的人,则基本就不会作乱了。经过有子的这番论述,孝悌这一家庭伦理观念的社会政治意义便一览无余了。《孝经》中更是把孝敬父母与忠君直接联系起来:“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在这里,“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一种政治工具,部分丧失了其本应发自于内心的人性之美。另外,儒家传统的孝悌思想其实隐含着一个潜在的矛盾难以解决,那就是当孝与忠,也就是亲情与国法发生矛盾、忠孝难以两全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这一矛盾在实际生活中发展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孝”的心理与行为容易受环境影响发生变化。尤其是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忠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孝退避三舍。如孙少勇对父亲孙怀清的感情,随着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其实质往往沦为不同情况下对自身利益的权衡。另外一个倾向则是为一己之私情无视他人权益或国家利益与法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以及“窃负而逃”都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儒家的孝悌思想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变化,逐渐僵化,至宋明理学走向极端,终于成为严重束缚中国人思想文化发展的沉重镣铐,也就是新文化的干将们极力要打倒的“吃人”的封建礼教。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孝弟的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滑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1]他之所以会这样说,也就是看到了儒家孝悌思想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王葡萄之于孙怀清,实际上就是孟子所谓“窃负而逃”这种思想的现实翻版。在王葡萄心中没有关于政治、法律等等其他复杂的想法,她本着最基本的人伦思想对待孙怀清,把他藏匿于地窖,供养侍奉,外界种种国家、政治话语均与她无干。在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当时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王葡萄的行为并没有妨碍国家利益与他人利益,反而以坚守个人道德战胜国家政治强权的行为使人性之美得以彰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私情的关照往往会超越道德、法律的界限,成为建立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严重羁绊。
二 夫妻/男女
儒家对夫妇/男女之关系向来都很重视,孟子言“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孟子·万章上》) ,可见这种伦理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在夫与妻这二者之间,儒家文化又讲究男女的尊卑秩序。《周易》中以乾坤阴阳之说来为男女定位,《诗经》中的弄璋、弄瓦之说,都带有明显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卑弱、顺从、依附于男性是儒家文化对女性人格的要求。所谓“夫为妻纲”、“三从四德”更是强化了社会对于女性的这一要求,使女性完全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播,女性解放也成为时代潮流,许多女性勇敢冲出封建大家庭的牢笼,寻求个人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男女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得到法律确认,可说是女性解放的重大胜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男性乃至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理想人格的期待仍没有多大改变,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仍然是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份定位与角色期待,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女性的自我要求。“温柔贤惠”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要求呢?首先是性格和顺,其次是在工作与家庭二者之间要以家庭为重点、为中心,三是要吃苦耐劳,也就是要能够成为男人的贤内助。这实际上仍然是儒家文化对当代女性的潜在影响。
阅读《第九个寡妇》,我们可以发现王葡萄是个极为贤惠的女人,她有能力、能吃苦,最重要的是她还非常有女人味,是那种能把男人的生活照料得非常舒服的女人。因此,小说中的男人只要是和葡萄亲近过,就都会深深地爱上她。在王葡萄身上,严歌苓表达了她对于传统女性美的理解与向往。在她看来,女人美与不美,不在于外貌,而在于能不能以自己的女性魅力留住男人的心。小说中王葡萄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女子,但她却总是会用她充满女性气息的关爱使她身边的男子不自觉地感受到成为她的男人是怎样一种幸福。她勤快麻利又体贴,做家务是一把好手,她总是能给男人营造出温暖的舒适感,让男人可以身心都得到放松与休憩。这是对中国传统理想女性形象的继承。但是严歌苓笔下的王葡萄又不是一个依附于男性、没有独立人格的所谓“第二性”,这首先表现在王葡萄在守寡后并没有恪守所谓妇德,而是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先是爱上了戏班的琴师朱梅,并与之私定终身,但是身体孱弱的朱梅还是在动荡的生活中早逝了,这段感情无疾而终。之后她又与自己原来丈夫的哥哥孙少勇产生爱情,但因为孙少勇的不孝行为,王葡萄忍痛离开了他。后来她爱上了有妇之夫冬喜,两个人爱得热烈缠绵,没有因为寡妇或者有妇之夫的身份而受丝毫影响,就在冬喜决定要离婚娶她之后,一次灾难使冬喜骤然离世。再后来,她又爱上了朴同志,一个来村里参加四清运动的干部,这次爱情像溪流潺潺,虽然后来二人没有走到一起,朴同志也娶妻生子,但是感情已然在两人心里扎根。最后,王葡萄仍然和孙少勇走到了一起。用王葡萄自己的话说,就是她的心可以分成好几瓣,这些男人在她心里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中对女性从一而终的要求背道而驰。不仅如此,对于葡萄来说,重要的是生命的实质,连婚姻之名也不那么重要了。
其次,在王葡萄对于性的主动迎合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她的独立自主与反传统特性。儒家传统家庭伦理对女性举止行为有明确要求,即要“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专心正色”(班昭《女诫》) 等等,总而言之,是要求女性压抑自己正常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排斥外界一切声色的诱惑与干扰,以合乎“妇德”。但是王葡萄显然与儒家伦理所强调的妇德格格不入,她的身体丰腴充盈,处处都散发着雌性的诱惑,她对于性并不感到羞耻,也不拒斥身体的欢愉,而是陶醉其中。这在她与春喜的关系中表现得格外明显。春喜是冬喜的弟弟,他与冬喜有点相像,王葡萄爱的是冬喜,不是春喜,这一点她自己非常清醒,但是她并不拒绝与春喜交欢。在她看来,她的身体是身体、心是心,她的身体和心是可以分开的。她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身体,也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心。这样一种对待男女情事的态度已然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中以男性为中心、女人总是被动顺从男性的状态完全不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对于生命过程与生命本质的主动取舍,所表现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现代女性观念。
再次,王葡萄对待孙少勇的态度也明显表现出她的自主性。王葡萄与孙少勇相爱后不久,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少勇的父亲孙怀清被划为地主恶霸,少勇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请求上级枪决自己的父亲,王葡萄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少勇,甚至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她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意跟着那个“不孝子”过所谓好日子。这就是葡萄,果敢、坚强又不失女性的温柔贤惠,她从不惧怕生活的艰难、环境的险恶,以朴实的信念坚守着自己内心深处的道义,以自己的大智若愚颠覆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男性智、女性顺的伦理规范,守护与滋养着身边的男性。王葡萄的形象与严歌苓之前塑造的小渔、扶桑等女性形象一脉相承,都是一种“包容的、豁达的、以柔克刚的性格”。严歌苓反对把女人作为第二性,而是强调女性精神与身体的主动性,并且认为女性的性感不单单在于外貌,女性的贤惠本身也是一种性感,[2]对男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也是她笔下的小渔、王葡萄等等女性共同具有的特征。这样,严歌苓既使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女性有相契合的一面,又赋予其新的特质,实现了新旧两种文化的水乳交融。
综上所述,小说围绕王葡萄这个形象衍生的故事情节,承载着严歌苓对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深刻思考,这其中既有对传统伦理的维护与继承,比如对于孝行的倡导与赞颂,对于女性无私、贤惠特质的张扬等等,都渗透了浓厚的传统色彩,使这部小说洋溢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但是,在传统的表象中我们又能够发现作者对于儒家传统家庭伦理的反思与超越,使这部小说对于家庭伦理的书写显得斑驳复杂。应该说,经历了晚清民国思想的动荡,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已渐入人心,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家庭伦理观念造成很大冲击,时至今日,中国的家庭伦理基本参照西方社会的标准来执行,比如一夫一妻制,比如对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提倡等等。《第九个寡妇》的时空背景是上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那个时候的中国虽然已经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是在广大农村社会,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成为严歌苓小说中家庭伦理书写的背景,也是她在塑造人物时不能脱离的思想主线。但是多年的异域生活经验使严歌苓得以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考。她曾经说过,到美国生活之后,她的思想观念有一个“颠覆”的过程,她对于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开始质疑,不是“直接接受一些世俗的观念再转换成文字”,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用含蓄的语言把道德仲裁权留给读者”[2]。严歌苓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态度与现代新儒家们有异曲同工之处。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以儒家文化为本,融合西方文化以改造儒家文化,使之更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第九个寡妇》中对于儒家家庭伦理的继承、反思与超越,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现代新儒家们对中西文化互补、融通的思考,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出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儒家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并使之在文学中落实到世俗生活中去,为现代儒家文化如何融入现实生活描绘了一幅可以想见的图景,开拓出艺术创造的新生面。
[1]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J].新青年,1920,7(5) .
[2]方乐莺.严歌苓:对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开始质疑[N].中华合作时报,2004 -11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