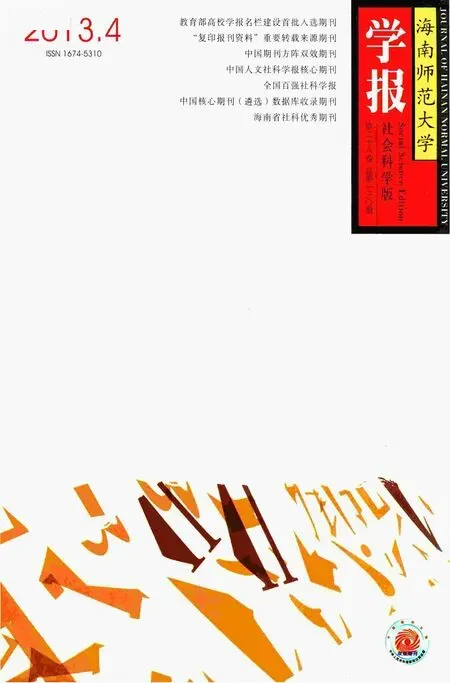得失与启示:重读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
颜红菲
(1.南京工程学院 外语系,江苏 南京211167;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政治抒情诗”,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政治抒情诗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只要有国家、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就会有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广义的政治抒情诗指的是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以文学形式表达政治感情。在内容上往往有很强的时事性和政治性,在艺术风格上多表现为凝重、雄浑、激越、热烈,从而表现出一种崇高和壮美的美学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鼓动性与艺术感染力。狭义的“政治抒情诗”,是指“‘十七年’时期出现的一种‘诗人’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1]的创作倾向,具有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等鲜明特征的诗歌。20 世纪50年代出现的政治抒情诗,到了60年代初以后逐渐形成当时最主要的一种诗歌形式。它以时代重大政治问题为题材,立场鲜明地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情感充沛,语言恣意而汪洋。在“十七年”期间,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从事过政治抒情诗的写作,但其中成就最高、最引人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郭小川和贺敬之。本文拟以郭小川政治抒情诗为个案,将这一诗歌形态置于历史语境中,通过梳理其生成、发展、繁荣及式微的历程,探讨其美学意义和思想价值,揭示其得失与成败,看一看他的诗对当下中国政治抒情诗创作有何借鉴与启示。
一
从价值层面上考察一种诗歌形态,不仅要联系其意义的当下语境,也要考虑其存在的历史语境;既要讨论它的艺术范式,也要估量它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宏观的和局部的、审美规范与个人表达的考量,才能辩证全面地评估这一诗歌形态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十七年”最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郭小川诗歌在思想倾向和艺术造诣上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有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作为诗人,郭小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对他所亲历的现实生活以及特定的时代精神的独特把握,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还在于他具有更大的超越性。在那个思想和艺术都推行标准化的特殊时代,郭小川保持了诗人最可贵的独立精神。”[1]谢冕此话可以帮助我们从两个方面理解郭小川的意义:首先是作为“革命战士”的郭小川,其诗歌在内容上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出一种社会形态之美,同时又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完美地表现了诗歌主题。其次是作为诗人的郭小川,其诗歌实践体现了独立而独特的表现形式。
伊格尔顿认为:“如果离开了处理作品时特定的社会和体制的形式,就没有‘真正’伟大的或‘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可言。”[2]特定的社会和体制产生特定的时代风尚和时代精神,由此而生发出与此相适应的诗歌形式和诗歌内容。能真实地把握时代脉搏并加以艺术化的表现,就有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或“真正”有价值的文学。郭小川的诗歌可以说是把握住了时代风尚,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之美。李泽厚先生在《美学论集》中对社会美有这样的观点:“亿万人民改造世界的雄伟实践,为先进事业奋勇献身的英雄人物的高尚的思想、顽强的意志、丰富的情感、健壮的体魄,成为社会美的主要表现。”[3]这种许多时代所缺失的“社会美”,正是“十七年”文学艺术的审美要求和审美特性。郭小川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首先表现为自觉地将个人的事业、情感与时代精神相融合,使自己投入“火热的斗争”,用诗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完成对时代精神的书写。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方向就是为人民大众报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突出强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在此基础上规定了文艺写作和艺术审美的规范。《讲话》精神要求抒情诗歌不再是诗人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作为阶级利益的表现者,具体说来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表现这一阶级的精神风貌。只有真心拥护那个时代,真正热爱那个时代,忘我地投入到时代中去,才能使自我的思想境界和情感体验与时代精神同步合拍,才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唱出时代的声音,表现出“社会美”来。郭小川不断地呼吁“我要下去啦”:“我的习性还没有多少变移,/沸腾的生活对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我爱在那繁杂的事务中冲撞,/为公共利益的争吵也使我着迷,/我爱在那激动的会议里发言,/就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生产诗。/而那机器轰隆着的工地和扬着尘土的田野呀,/我的心没有一天不向你们飞驰……”(《山中》) 郭小川的诗不是在书斋象牙塔里精雕细刻出来的,而是深入到工农大众的实际生活中去,去感受他们的感受情感和生活,这是其诗歌为什么能如此准确集中地反映时代精神、把握住时代脉搏的根本原因。在郭小川的绝大部分诗作里,个人价值取向自然地与时代政治的目标统一起来了,个人命运自然地与人民群众的命运联系起来了。其诗歌作品歌颂伟大的时代,歌颂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充满了激情和真诚,那是发自肺腑、从诗人生命里生长出来的情感。诗人尽情地抒发这一情感,情感抒发的炽热真实和思想表达的形象质朴,使他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个人的审美创造在社会大时代中取得了高度的共鸣。
郭小川的自身经历也促使他在政治抒情诗写作上取得超越常人的成绩。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诗人,十几岁就去延安参加了革命。在革命风潮里,延安的政治环境与他的诗歌写作是同调同步的。在他那里,没有老诗人们跨越不同时代复杂的个人生活经历,也没有受到西方各种现代诗潮的影响。从延安到北京,他和革命集体一起走向了胜利,所经历的苦难是集体的,同时也是他个人的,所享有的胜利是集体的,同时也是他个人的。正是因此,他才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革命集体之中:“我也是这些兵士中的一个呀,/我的心总是和他们的心息息相通。/行军时,我们走着同一的步伐,/宿营了,我们做着相似的好梦,/一个伙伴在身边倒下了,/我们的喉咙里响起了复仇的歌声,/一个新兵入伍了,/我们很快就把他引进战斗的人生。”(《山中》) 在这种相互的融合中,时代精神和革命的“大我”成了郭小川生命自我的一部分,使作为对象性存在的自我在融合中得到了确证,使其个人生活和诗歌创作都有一种“单向性”。这种单向性也恰恰与时代精神特征相吻合,正是这种单向性使其诗歌超越了同代人,显得纯粹而真诚,浓烈而酣畅,充满了火一般的力量和激情,具有一种强烈的穿透力。
郭小川个人对诗歌形式的天才把握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郭小川的个人性情与政治抒情诗张扬“大”的情感是适宜的。郭小川“喜爱大、喜爱动,喜爱鲜艳的东西,喜爱惊天动地的声音,喜爱没有遮拦的谈话,喜爱宽阔平坦的道路,喜爱一望无际的灵魂”。[4]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真诚的诗人。诗人饱满充沛的激情与艺术形式表达完美地结合,使思想表达更加强烈,更加激动人心。在诗体形态上,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结合得很好。其政治抒情诗追求大气势和大境界,情感激越豪迈,富于力量的健与美,语言表达明快、直接和彻底,从而达到它在社会生活和群众中的战斗性和鼓动宣传作用;同时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述某一政治理念或方针政策,从具体的个人微观角度入手,以小见大,直赋其事,以速写素描式的方法,表现人物的坚定信仰和火热的建设生活;或从宏观入手采用俯视鸟瞰的视角,以充满激情的歌喉去热情歌唱,但所有情感内容和生活现象都被限定在为阐发某一理念或政策的轨道中。比如《投入火热的斗争》:“不驯的长江/将因你们的奋斗/而绝对地服从/国务院的命令,/浑浊的黄河/将因你们的双手/变得澄清,/北京的春天/将因你们的号令/停止了/黄沙的飞腾……”其政治抒情诗一般都是长诗,诗人往往采用赋体手法,抒情、议论、叙述三者紧密结合,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感进行渲染、铺陈,经常使用音步铿锵、节奏明朗、声调高昂的“楼梯式”。《向困难进军》从对个人经历的叙述出发,与时代抒情相结合,用三个“你们再不要……而是怎样”排比句式来渲染铺成,读起来气势昂扬,铿锵嘹亮。从民歌中获取形式和语言的“民歌体”,也是郭小诗作中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诗歌表现形式日益成熟,形成了特有的“郭小川体”:格局比较严整、章节大致对称、音韵铿锵。正如冯牧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标志着郭小川的独特风格的艺术形式,常常是把中国古典诗词的严谨、丰富的结构,中国民歌的健康、朴素、粗犷的表现手法和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生动、简洁的群众语言熔铸在一起,这种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在我们的新诗作中是别开生面的。”[5]
二
“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在为社会主义建设高唱战歌的同时,也消弭了此类诗歌的多重功能,特别是其批判功能,许多诗人只能为现行的政治纲领、路线、政策、观念唱赞歌。他们用政治和阶级斗争表现一切矛盾,包揽所有的情感,使政治成为文学批评的惟一标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诗人们失去了自己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导致在集体话语和政治话语下的个体失语。郭小川以真诚、不甘平庸的个性以及对艺术执着的探索精神,艰难地对人性进行深刻思考,对诗歌内容也进行深层挖掘。这种尝试和努力,使他的部分作品在审美维度上表现出对个体实现本质化过程中的裂痕、矛盾和冲突的关注,在情感维度上表现出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对人的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和情感内涵的复杂性的关注。在《月下集》的“权当序言”中,他说:“核心问题是思想。而这所谓思想,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而应当是作者的创见。”所谓“作者的创见”自然是包含着作家个人主体的审美思想、审美方式和审美情感的综合。“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6]所谓“新颖而独特的东西”自然是题材的创新,“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是多棱的,它从无数个镜面反射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绝不是单一向度所能概括的。题材的创新实质上是指对单一单质内容题材表现的摈弃,是避免理论图示的抽象和生硬的有效途径,这时作家主体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郭小川再三强调作者自己创见的介入。表现内容上的深层思考,使他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向人性的禁区介入。他的两首抒情诗《致大海》(1956)和《望星空》(1959)就是诗人力图冲破当时流行政治语言的禁锢,表达自己“创见”的探索之作。《致大海》叙说“我”两次面临大海的不同感受和体验,表现了个性人格与革命相冲突的迷惑与苦闷的困境以及思想感情的艰难转变过程。“大海”是革命队伍的自然外化,“我”则是一个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历史的庄严性通过“我”这一生命个体的漫长审视与探究后,才得以显现,进而被认同与接受下来。《致大海》中的抒情主体“我”,在思想和情感上还保持着一致性,而在《望星空》中,抒情主体的言说却并不统一,前后分裂成两种话语形式:“个体话语”与“革命话语”,政治上的敏感使作者最后不自然地将“个人话语”消解于“革命话语”之中,两种话语之间的嫁接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缝隙,显得生硬、突兀。在郭小川最重要的三首叙事诗中,“革命话语”和“个人话语”也一直是诗歌中并行的两条线路,两种声音,一个显一个隐,一个高亢一个微弱,最后的结局都是“个人话语”被“革命话语”所规训和消解。由于特定时代的关系,郭小川诗歌突围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郭小川的失败同时也宣告了政治抒情诗在他的时代的失败。
郭小川抓住了政治抒情诗的本质之一,而这正是从1949 到70年代末整个30年的政治抒情诗的缺失:作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丧失了其创作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在思想上表现为空洞的说教,丧失了文学性,堕落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具体到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来说,文学是人学,是关于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的艺术,不是抽象的阶级和本质,文学应当立足人、思考人并且表现具体生活中的人,那么表现政治生活中的人或者说表现人的政治生活则是政治抒情诗不可避免的内容。郭小川在“革命话语”中纳入“个人话语”,在“政治维度”中织入“人性维度”,通过表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个体自我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的彷徨、思考,尤其是情感体验,从真实的个人政治情感中反映出时代精神和政治风貌,这种表现更真实、更丰富、更深刻、更富于审美性。然而,郭小川突围的最终失败,也使其政治抒情诗所追求的对时代的超越,只是一种努力而未能成为一种现实。一首好的政治抒情诗首先要有历史使命感,必须能深刻地把握时代思想和精神面貌,反映当下的政治情感或揭露时代的政治黑暗;同时它必须是文学性和政治性的完美结合,能通过艺术化和个性化的审美传达表现政治情感,成为既有深刻的价值意蕴又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有机整体。其中,诗人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主体性精神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
当今是消费主义时代,经济领域的不断扩张导致其对于公共政治领域的侵占,并使其发生蜕变,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正在大面积“非政治化”。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为核心的经济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公共政治关切,社会重大转型体现在大众消费热情空前高涨的同时,政治冷漠到处蔓延。同时,政治体制的内在弊端所导致的腐败和分配上的不公正正日益蔓延,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也日益严重,穷人富人的概念在消费时代变得日渐明晰,穷人日益处于社会底层的屈辱地位,大多数人处于“失语”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被文学性所清洗的“政治”、“阶级”、“利益”、“对抗”、“意识形态”这类语词,又一次成为本质现实,成为时代的真实和主题。政治再一次强烈地要求诗人们从个人情感呻吟的象牙塔里走出来,进入公共领域,以郭小川所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投入社会生活,把握时代脉搏,自觉地成为底层阶级的代言人,成为社会黑暗的掘墓者,成为心灵家园的守护神,成为理想信念的火炬手。当代的诗人们只有从物欲横流的文化市场中,从中产阶级的精英立场中,从浅唱低吟的小资情调里,夺取曾经失去的阵地,为人民服务,为真理歌颂,才有前途。同时,当今的文坛,也只有遵循“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7]这一道路,坚持诗歌的文学性和政治性,坚持诗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才能避免重蹈郭小川的覆辙,才能追随郭小川让自己的诗歌实现个人与时代的高度统一与高度融合,成为能够代表一个伟大时代的真正的杰出诗人。郭小川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然而他也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立场与个人独立人格的诗人,在他的诗中大量地保存着他对于时代的惊喜与困境,他自我的心灵与精神都可以从其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诗中得以洞见,《秋天》是如此,《团泊洼的秋天》是如此,《深深的山谷》与《白雪的赞歌》等长诗也是如此。请问在今天,我们有哪一位诗人可以与郭小川相比呢?有哪一位诗人的作品产生过像郭小川当年那样的社会影响呢?今天的诗歌境况并不完全是由于时代变迁所造成的,与诗人们的政治与艺术选择也存在直接的关系。需要反思的不是郭小川们,而恰好是我们自己。
[1]谢冕.郭小川的意义[J].中国图书评论,2000(4) .
[2]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37.
[3]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64.
[4]王富仁.充满真实的青春激情[M]//大海晨歌——郭小川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3.
[5]冯牧.不断革命的战歌和颂歌[J].诗刊,1977(10) .
[6]郭晓惠,等.检讨书: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144.
[7]胡少卿.当下诗歌中的“人民性”及其启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