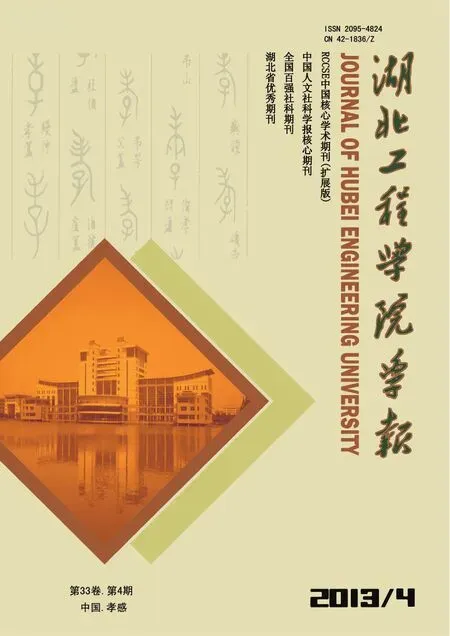诗人与时代
——读管用和的早期田园山川诗作
余行玉
(孝感市作家协会,湖北 孝感 432000)
诗人与时代
——读管用和的早期田园山川诗作
余行玉
(孝感市作家协会,湖北 孝感 432000)
诗歌是时代的产物,生活在某一特定时代的诗人,其作品或多或少地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无论那个时代是进取的,还是颓废的,都必然会反映到他作品的思想主旨和表现形式中去。脱离时代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但是,一味为时代所禁锢的诗人,其艺术创造力也会被扼杀。读管用和早期田园山川诗作,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时代对于诗人,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并且从中窥视到那一时代人们的思想状态、精神风貌和政治环境的一斑。
管用和;诗人;田园山川诗;时代
生活在一个思想极度禁锢、言论极不自由的时代,无疑是诗人的不幸。然而,天才的诗人,能够在夹缝中求生存,从而从压抑的气氛中脱颖而出,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大幸。我们所景仰的著名诗人管用和,他的早期诗作,就可以说是夹缝中求生存的产物。他在诗歌创作领域能够取得后来那样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以为,除了艺术天分外,主要是他能够正确把握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从而在那个时代特定的环境中,在坚守住自己艺术良知的前提下,寻找到一条既能为时代所接受(或者说是容忍),又能在题材选取与表现形式上,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艺术创造空间的结果。
管用和是我青年时代喜爱的诗人之一,记得那个时候,他最让我喜爱的,是《水乡渔家》、《赶路号子》、《麦箫曲》那样一些明显带有新民歌特色的诗章。
管用和早期田园山川诗歌,最赏心悦目的,是其独具视点的叙事风格。《田园诗卷》开篇《深夜“沙沙”声》,首起“夜深,人静/多少人进入了甜蜜的梦境/‘沙沙沙沙……’/是哪里来的声音”,简短的叙述,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意境,让人禁不住有了读下去的欲望。《山川诗卷》开篇《汉江纤夫曲》同样如此,“夕阳如火烫红汉江/斜晖映着岸畔的垂杨/号子震得晚霞飘闪/哎嗨!杭唷/足跨着大江的臂膀”[1]79,寥寥数行,便起到了引人入胜的作用。可以说,叙事风格,最能体现他非凡的艺术天分。我曾试图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诗人写于1959年春的一首《赶鹅》还原成简短的镜头画面:清清的池塘,水面倒影出洗衣姑娘俏丽的身影;旁边树林里,爱恋着她的小伙子正纵情地为她歌唱;姑娘气恼,怨他不像别人那样进取,懒得理他;她捡起一块小瓦砾,赶起水里一只鹅;透着几分爱意的骂声,传达出了姑娘的真实内心:“哦嚎!鹅,你一天到晚唱,就没有唱句正经歌!”[2]小小的一个场景,诗歌比兴手法的运用,炉火纯青。在诗人全部作品中,这样的经典之笔随处可见。不论诗的长短,十几行或数十节,所展现的一幅画面,一个情节,或者一句人物间的逗趣言语,都能让人会心快意,玩味不已。有一首题为《小窗夜话》的诗,写一对久别重逢的年轻夫妻,枕边夜话没有卿卿我我的爱意无限,而是相互夸赞对方离别期间的工作成就。从常理上说,这样的情景应该不多见。很明显地,诗人所要表现的,是那个时代所倡导的进取精神。即便如此,他所渲染出的那个情景,某种程度上,仍能打动人。
浓郁的乡土气息,是管用和田园诗最显著的特色。譬如《头顶红日战山坡》:“太阳好似一团火/晒得雀鸟无处躲/社员尽是钢铁汉/头顶红日战山坡//头顶红日战山坡/犁得荒地笑呵呵/荒地荒坡笑什么/此处要变米粮窝”。[3]朴实、明快,富有画意,充分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新民歌铿锵奋进的鲜明特色,读来脍炙人口。这样的诗章,在管用和的早期田园诗中,俯拾皆是。相对《田园诗卷》中乡村生活图景的温馨与浪漫,《山川诗卷》中许多的诗章,则有一种奔放的豪迈之气。这是诗人早期诗作显著特色的另一个方面,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放筏》、《过峡江》。“老林一夜暴风雨/万山飞泉悬空挂/浪从云中来/水自天河发”(《放筏》)[4];“过峡江,望江峡/漩涡张着嘴/礁石露着牙/巨雷惊吼浪出谷/像千条鲛龙飞鳞甲/山山水水都在说/自古谁不怕”(《过峡江》)[5],那是怎样的一种气势?!
管用和早期诗作,艺术手法上,不乏上乘之作。但不可否认,由于思想方面的禁锢和言论方面的限制,抑或还有认知方面的盲区,存在着那个时代诗人、作家所共有的压抑、困惑,甚至是对肤浅和低俗的迁就。那个时代,虚假成为了我们社会的疾症,它让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几乎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有人说,那是一个诗人与诗歌普遍沉沦与堕落的年代。我们生当其时的诗人,当然也不可幸免地要受到它的播弄与羁绊。
管用和的早期诗作,留下了浓重的时代印痕。那些始于1959年,止于拨乱反正之前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只能属于那个时代。即便是像《头顶红日战山坡》、《赶鹅》、《小窗夜话》那样一些写出了真情实感,读来脍炙人口的诗章,对于现今的读者,也是很难理解的;而对于我们这些深刻了解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心头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因为那些作品与那一时期政治氛围的联系实在太过紧密了,以至于它不能跨越时代。试以《田园诗卷》中创作于1959和1960两年间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作为例:无论是写人们的劳动场面还是写精神面貌,无不充满了热烈、欢乐与激情。其实,它与那个年代人们心灵深处的实际感受,应该说是大相径庭。不可否认,那样一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那样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被一些虚妄的口号所激励,曾经有过。但到了诗人表现它的年代,早已为饥饿、为惶恐所代替。即便是有,也只是一种虚假表象,是被迫,而并非内心激情的迸发。假如,这些诗作的创作年代,提前到较早的那个所谓“大跃进”时期,完全可以看作是现实状况的真实描摹,或者可以认为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向往。而它的创作年代却恰恰是在那个饥饿与死亡相伴的非常时期,广大的人民公社社员挣扎在死亡线上,朝不保夕,怎么会有那样的欢乐与激情呢?我理解,诗人对现实并非视而不见,刻意而为,是迫不得已,是时势使然。否则,就只能三缄其口。在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下,难道还有人胆敢写出真实的状况么?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应该理解诗人的苦衷。有一点让我对诗人由衷地敬佩,那就是,虽然并非由衷之言,却能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诗人将那个时期的作品,大多收入自己的诗集《欢乐的农村》。撇开现实不论,单就作品本身所渲染出的氛围而言,“欢乐”二字的确是实至名归,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正是这一点,充分说明了诗人的艺术天分。
那一时期管用和诗作的高产,绝不亚于当下网络发表作品便捷情况下诸多的高产诗人。能够以如此热情,写出如此数量惊人的作品,除了对艺术的热衷与非凡的创造力,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受到时代精神的感召(即便那个时代精神有着太多的虚假成分),内心里真有那样一种“奋进”精神。
诗歌是时代的产物,生活在某一特定时代的诗人,其作品或多或少地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且不说那些自觉为时代而歌者(这部分人在每个时代都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时期诗人群体的主力军),就是那些思想极端不同流俗的叛逆者,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譬如众所周知的文革地下诗人郭路生(食指),他的诗歌创作对于时代的反思之深刻,开创了其后拨乱反正时期诗歌创作的先河,但遍观他的诗作,时代的胎记也比比皆是。我猜想,当诗人不得不违心地去高唱那些并非发自内心的颂歌时,心灵深处,一定是经历了极端痛苦的挣扎。当然,这也许只是我个人想当然的片面臆想。也许,那原本就是发自诗人的内心,在心灵深处存在着那么一种自觉,就是要紧跟形势,为时代呐喊。但即便是这样,也足以说明时代对诗人的创作有着怎样深刻的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发自内心的主动性迎合,还是被动性妥协。与《赶鹅》、《头顶红日战山坡》等作品艺术手法的炉火纯青相比,诗人写于同一时期的某些作品,则稍显直白。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只能理解,它们并非发自肺腑,有“为诗而诗”之嫌。
诗人当然不能脱离自己的时代,无论那个时代是进取的,还是颓废的,都必然会反映到他作品的思想主旨和表现形式中去。脱离时代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但是,一味为时代所禁锢的诗人,则毫无疑问地,艺术创造力被扼杀。当然,这里有一个对时代精神本真的界定问题。我认为,真正属于某个时代的本真精神,并不是那些人云亦云的所谓主流思想,而应该是潜藏于冠冕堂皇外衣里面的,最能体现人们内心真实的社会精神向度。杰出的诗人,应该洞悉时代的病灶,挖掘出真正的时代精神向度,并加以表现。一味地迎合于“主流思想”的大合唱,就注定不能成为杰出的诗人。诗人对时代的穿透力,主要体现在不同流俗的独立思想,体现在对时代精神向度的深入发掘。唯其如此,他才会具备过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从而才能达到艺术创造的巅峰。
在“诗人郭小川90周年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诗歌与个人命运密切到一首诗即可在瞬间关系一个人祸福的时代,在自己的感受和时代之间,在压抑不住的声音和事实上对他构成压抑的时代精神之间,寻找到平衡,就是一种才能。管用和早期诗歌创作,正赶上极力倡导诗歌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创作环境。应该说,他与同时代许多杰出的诗人一样,寻找到了这种平衡。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思想的桎梏,使得自己的诗歌艺术才华得以尽情地发挥。《田园诗卷》中,那些写爱情、写情趣、写情感的早期诗作,即便是以当下的艺术眼光去衡量,也算得上是上乘之作。虽然那些诗作仍受到那个时代语境的羁绊,但笔之所至,性灵的抒写淋漓尽致,令人心醉。譬如《赶集》一首,开篇四句:“茫茫云雾锁住山/一路担子出云间/绿裤白褂蓝兜兜/张张脸上红霞闪”[6],将一幅美不胜收的绚丽图画兀自呈现在读者眼前。茫茫云雾的山路上,闪现出一队英姿绰约的年轻姑娘,荷担如飞,笑语一路。何事欢欣如此?通过人物间“还把什么嫁妆添”的问话,引出了答案:“步子急,一溜烟/咳嗬咳嗬唱得甜/莫问姑娘急什么/生怕等坏了小青年”[6]。读罢,让人不由得要为姑娘们的甜蜜爱情会心开怀。再如《桂花树下》,通过一位老伯与一个姑娘的对话,将年轻人的爱情写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传神,令人为之折服:“‘小伙名字登了报/怎么你却倒害怕/平日搞试验像一人/得表扬还分你和他’//姑娘脸如胡椒辣/心里却像喝糖茶/‘鬼记者嗄,写他就写他/我帮点儿小忙算个啥……’。”[1]71一个羞答答却又向往幸福爱情的女青年形象,跃然纸上。
时代印记对于诗人诗作本身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也许并不是正面的,但由此,我们可以窥视到那一时代人们的思想状态、精神风貌,甚至是政治环境的一斑。从这一层意义上说,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价值。读管用和的早期田园山川诗作,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在此。
[1] 管用和.山寨水乡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3.
[2] 管用和.欢乐的农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43.
[3] 管用和.头顶红日战山坡[N].长江日报,1960-08-07.
[4] 管用和.放筏[J].长江文艺,1963(4).
[5] 管用和.过峡江[J].萌芽,1964(5).
[6] 管用和.赶集[N].武汉晚报,1962-11-12.
(责任编辑:余志平)
I206.7
A
2095-4824(2013)04-0058-03
2013-04-29
余行玉(1954— ),男,湖北孝感人,孝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