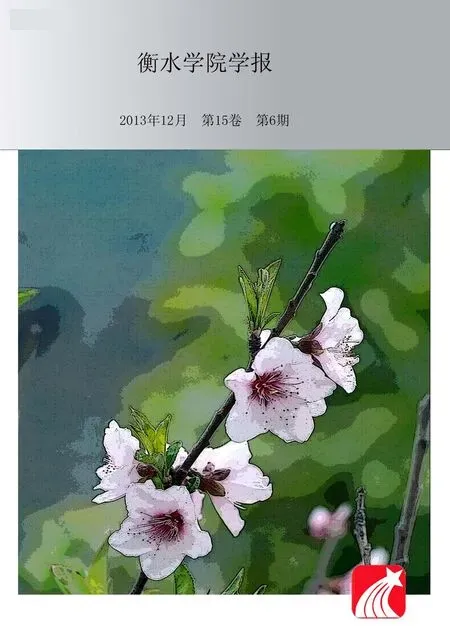古希腊反民主传统之根源研究
李 辉,张艳丽
古希腊反民主传统之根源研究
李 辉,张艳丽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民主的摇篮是靠反民主传统之手推动的。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古希腊,它的反民主传统是古希腊人馈赠给人类的又一份丰厚的礼物。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实践、古希腊人的贵族情结和哲学家们寻求社会稳定的心态等3个方面,全面分析反民主传统中蕴含的深刻的现实根源、文化根源和社会心理根源。
古希腊;雅典;反民主;民主政治;贵族情结
古代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人民对于民主政治的最初实践,为人类政治事务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新的救赎之道。近代以来,人类在政治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民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认可,至少没有一个国家或政府宣称它是反民主的。但是随着民主实践的发展和对民主理论研究的深入,民主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天生万物,相生相克。在民主传统的发源地,反民主传统也在此生根。那些批判民主的人依然可以从民主的诞生地——古希腊寻找到最初的温暖。对此著名学者麦克里兰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如果说有那么一件事物被称为政治思想的西方传统的话,那几乎可以说,对政治的理论化被‘发明出来’,以解释民主政治——人类由他们自己统治——必然被转化为暴民的统治……”麦克里兰总结道:“它以这种深刻的反民主的偏见开其端绪。”究竟有哪些因素导致古希腊反民主传统的产生呢?本文尝试着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一、贫富之争与现实根源
古希腊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尤其发达,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是贫富的两极分化。从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哲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古代希腊社会中的明显的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矛盾,即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及两者之间的矛盾。社会不断地被这两个阶级的斗争撕裂着。富人残酷地剥削着穷人,使很多人沦为债务奴隶;穷人则不堪其辱,意在与富人一争高下,维护作为自由人的权利。这种矛盾是古代希腊政治发展和政体演变中的一条红线。战争使得穷人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相应的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富人与贵族并不甘心权力的丧失,他们反民主的政治实践和对民主政治的攻击为古希腊反民主传统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古典时代的大多数希腊人看来,民主制的对立物并不是个人统治的君主制或僭主制,而是富人和贵族占主导地位的寡头制。寡头势力才是民主政治的心腹大患,是反民主传统的大本营。民主政治与反民主政治的斗争其实质是贫富之争,穷人和富人在政治权力上的争夺。雅典,作为古希腊民主政治的代表,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就充斥着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德拉古改革虽然使得有公民权资格的普通雅典人有权参加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但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机构明显地偏向于富人阶层和传统贵族。德拉古改革使得富人和贵族共同垄断政治权力,形成新旧势力联合执政的极端寡头制,无公民权者和欠债者则遭受着富人和贵族的联合压迫。原先的政治格局是穷人和新富阶层同样没有政治权力,现在则惟有穷人没有政治权力。反民主的力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穷人的相对剥夺感更加强烈。因此德拉古改革非但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斗争。
号称雅典民主改革开端的梭伦改革,虽然“禁止所有以人身为抵押的借贷,还另外颁布法律,取消所有公私债务。这一措施通常被称为‘解负令’”,使得社会矛盾有所缓解,穷人的公民权得到保障并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梭伦依然“按照财产的多寡,把人口划分为四个等级,即:五百斗者、骑士、双牛者和雇工”。政府的高级官职依然有财产富足的前三个等级的人员垄断,第四等级的公民“只能出席公民大会和担任民众法庭成员,而没有被分配其他官职”。另外,梭伦还成立一个四百人大会作为立法机关。由此可见,梭伦改革后的雅典虽然决策人数有所扩大但依然是一个富人占主导地位的寡头制政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兹认为“说梭伦是民主派就如同说柏拉图是一个基督徒——也就是说梭伦根本不是民主派”。
贵族出身的克里斯提尼进行的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的最终确立,他废除了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四大古老部落,代之以地缘为基础的10个部落并在此基础上成立500人议事会。还创立一套“陶片放逐法”遏制寡头和精英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了政治的基础。这样克里斯提尼改革极大地打击了传统贵族的势力,“先前的血缘关系受到了极大冲击,那种按氏族、胞族和部落进行选举的格局被打破,传统的氏族关系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氏族贵族的势力遭到了尤其沉重的打击,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主要依靠血缘关系来操纵选举了”。但是克里斯提尼仍然沿袭了梭伦时期的两项重要的法规,即“只有最富裕的两个阶级才有资格出任高级行政职务;所有的祭司职位必须由贵族担任”。而且,克里斯提尼改革对既得利益者的触动远没有梭伦激烈,只是赋予了公民以政治权力,贵族和富人的经济利益并没有实质上的损失。贵族和富人通过放松政治权力而换取经济利益。因此在克里斯提尼时期,贵族阶级的势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由于客蒙(Cimon,约前512—前449年)和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约前524年—前459年)之类的贵族或半贵族将军在希波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贵族的势力有了明显的上升。另外,历史上残存下来的贵族议事会(Areopagus,即战神山议事会——笔者注)的权力此时也得到了加强”。
雅典的民主到伯里克利执政时期达到鼎盛。伯里克利使得城邦所有公职向全体公民开放。并且为了吸引贫穷的公民参与政治,伯里克利开始发放津贴。平民占主导的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至此,雅典民主的正能量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水满则溢,月盈则亏。雅典民主在其巅峰时刻,也蕴含着倾覆的危机。雅典民主绝非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演说中吹嘘的那样,尽善尽美。即使在伯里克利时代,我们也仍然能够看到贵族的影子,比如十将军大多出身贵族并且握有较大的行政权,伯里克利本人就出身于身世显赫的大家族。客蒙这位雅典贵族派的领袖和雅典海上帝国的主要缔造者就是伯里克利主要的政坛对手,客蒙倡导亲寡头制的斯巴达的外交政策。伯里克利之后,雅典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党争,就说明贵族的势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失去了伯里克利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的调和之后,雅典政治天平上的两端——平民和富人——的利益难以达到有效平衡,平民和富人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雅典的衰落至此而始。
雅典在寡头制与民主制之间的徘徊,实际上是整个古希腊关于这种争论的缩影。古希腊人在寡头制与民主制哪个好的问题上,陷入了争论,最终酿成以斯巴达为首的寡头制阵营与以雅典为首的民主阵营两大阵营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民主的黄昏开始飞起。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和战后雅典政坛的混乱局面,为政治哲学家们反思民主制的弊端,形成反民主理论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这是古希腊反民主传统形成的现实根源。
二、贵族情结与文化根源
古希腊文化中流露出来的浓厚的贵族情结,是反民主传统的文化根源。无论是《荷马史诗》中的君主制倾向,还是赫西俄德的叙事诗中对多王酋长制的赞同,都是渲染了强烈的贵族氛围。在《理想国》《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也明显体现出对于贵族统治的偏爱,对贫民的不信任。在《雅典政制》中更是直言不讳,“将民主政治看做贫穷的、不应得之人对富有的、应得之人的压迫。他解释说,无论在何处,贵族(beltistoi)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最小限度的放肆、不公和最大限度的敏于为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高度的无知、混乱以及可耻;由于贫穷,也因为缺乏教育,他们的道德越来越败坏,在有些时候,由于缺乏金钱,造成了一些人无知。’”政治哲学家批判民主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贫民缺乏教养,理性不足,难以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决策。该理由即滥觞于此。
事实上,“经历了所有的转型和民主化,直至公元前4世纪被马其顿征服,贵族gene创造出来的生存样式(style),始终都是主导的希腊政治文化样式。贵族的政治权力可以打破,但是它的文化却深入人心;希腊的民主化意味着贵族文化扩展到人民身上——尽管在渗透的过程中,质地有所稀释。”雅典高度繁荣的文化离不开富人的贡献。在雅典民主的演进中,有很多改革措施保留了富人和贵族的权力,使其参与公职。雅典很多的引以为自豪的公共设施就是来自于富人的公益捐献。
古希腊的政治统治权始终把持在贵族或富人出身的人手中,即使在以民主著称的雅典也不例外。“权力和威望是来自少数几个富有家族之人所具有的特权,这一观念在任何人记忆所及的时间里,都是希腊人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贵族势力始终活跃在雅典政坛之中。雅典几个著名的政治领袖几乎都是出身高贵,品德高尚之人。从最早的梭伦,到庇西特拉图;从克里斯提尼到克桑提普斯与米提阿德,再到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从埃菲阿尔特到米提阿德之子客蒙;从伯里克利到修昔底德斯。古希腊人坚信贵族在从政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一点是贵族之外的人无法通过后天的补偿所能弥补的了得。诗人麦加拉的特奥格尼斯(Theognis of Megara)坚信“政治权力应当集中到由几个世家大族成员组成的精英手中,他们具有他人永远无法拥有的特殊品质。在这些世家大族之外的人,即使接受苏格拉底那样的比作助产士的机敏教师的辅导,也无法找到处于萌芽状态的、这样的品质。而那些贵族圈中之人所具有的特权地位,会因与圈外的贱民搅和在一起而丧失,但是相反的过程却是不可能的。”
雅典历史的发展,也确实如特奥格尼斯和修昔底德所说的那样。失去了伯里克利这个强悍的政治领袖,使得雅典政坛一时难以适应,无人能与其相媲美。政治决策在伯里克利时代逐渐由民众法庭而不是原来的战神山议事会来决策,但是一旦失去伯里克利,民众法庭显然难堪大任。实际上这是因为雅典的民主制度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主要依靠伯里克利的个人的领袖魅力铸就其辉煌。这样失去雄才大略的伯里克利支持的雅典民主也就失去了精神支柱。修昔底德的一番话道破了雅典民主的玄机,伯里克利卓越的政治才华使得他能够“领导大众而非被他们领导……无论何时,他看到人民无理由的自信和傲慢的时候,他会用言词恫吓他们,使他们有所畏惧;另一方面,当他看到大众毫无理由的恐惧,他就会使他们重新找回希望。这就是雅典所发生的事情,尽管名义上是民主制,实际上变成了第一公民的统治。”可见,雅典民主即使是在巅峰时刻的风采也离不开贵族的文化的支撑与制约。而一旦缺少了贵族因素的限制,肆无忌惮的民主势力也将给城邦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伯里克利时代,贵族与民众之间形成了某种政治均衡,伯里克利与民众的关系正如“风借火势,火助风威”,伯里克利借民众增加政治权力,民众也从伯里克利处获得实惠。但是那些没有伯里克利才能的人,却成了只是讨好民众的蛊惑家(demagogos,这个词字面含义是人民领袖),这些人不惜以牺牲整个城邦的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最终玩火自焚。古希腊的历史表明,民主的繁荣依赖于各方政治势力的平衡,尤其是民主因素与反民主因素的平衡。古希腊人骨子里透露出来的贵族情结对平民的政治参与形成了有效的文化制约,这是反民主传统的文化因素。也因此对于很多政治哲学家来说的理想政体是基于财富或者基于出身,或者二者并重的贵族政体。
三、追求稳定与社会心理根源
社会稳定是个体生存的前提。追求稳定与秩序是在古希腊人的心里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经历了社会动荡、党派纷争的政治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们的理论中更是处于支配地位。哲学家们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检视了民主的对于社会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破坏。这种心理深深地埋藏在哲学家们的心底,是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反民主传统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古希腊人对“自然”的追求,对于“理念论”,对于“逻各斯”的追求和古代希腊悲剧的盛行,所体现的不仅是古希腊人“对自然和社会背后那种主宰一切的力量进行执着的探求”,而且是对于一种能够“安身立命”的状态的渴望。而民主制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威胁城邦稳定的迹象,是许多哲学家们仰慕极具政权稳定性的斯巴达制度、反对民主制度的根源。
苏格拉底对于民主制度下的人们为了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而挣得头破血流的混乱局面痛心疾首。他把自己比作“牛虻”并提出了“知识即是美德”的口号,希望以此蛰刺城邦,教化民众,唤起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和对城邦的忠诚,实现城邦的稳定和谐。然而对于人心已然分裂了的城邦,这种简单的说教未免有点对牛弹琴。“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古代希腊政治现实对其路线的回应。苏格拉底至死没有离开雅典,原因并非是萨拜因所说的对于民主制度的肯定而是对于城邦的忠诚,对于城邦稳定和谐的理想的忠诚。
苏格拉底的死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阴影。柏拉图对于民主制度的种种批判矛头最终指向的仍然是民主制度下的混乱不堪的局面。柏拉图或许是古希腊第一个对民主制度作出系统批判的人。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知识即是美德”这一信念的坚持“本身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柏拉图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一个贵族政治论者,因为只有学识渊博的人才能达到的成就决不能委之于多数人或群众的意见”。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的观念,就源自其“认为无知是民主制特有的祸根。在这里,不是专家而是业余者占主导地位。尤其在雅典,民主制似乎仅仅意味着无知者有神圣的权利来进行错误的统治。任何人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演说并影响它的决定;任何人,不管他的能力如何,都可以由于抽签的运气而被委以行政职务”。此外,柏拉图把城邦公民划分为3个等级,然后通过复杂的设计使得3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从而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运行秩序。他对理想国的设计是对雅典民主制下的极端平等极端自由的强烈反对。柏拉图对于极端的民主制下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认为“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极端可怕的奴役我认为从极端的自由产生”。虽然按照柏拉图对城邦的设计理念,在他的制度统治下的人民与民主制下相比可能并没有多少幸福可言,但是最起码能够使城邦拥有一个整体的稳定的秩序。
与老师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方面的造诣虽没有那么博大精深,亦可为庞大深邃。柏拉图更关注于哲学思辨更关注理想制度的建构,这或许与其本人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明显地要更加关注现实,他“无意探求某种超越现实的、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他真正感兴趣的,主要是如何使现实中既存的制度变得更为稳定、更为完善、并且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收”。他在名著《政治学》一书中探讨分析民主制下动乱的根源使,对人们的心态进行过堪称经典的阐述:“有些人认为其他与自己平等的人多占了便宜,而自己所得甚少,便会起而发难,名曰追求平等;另有一些人自觉与人不平等,其所得却并未多于他人,而是与他人相等甚至更少,同样会起来兴师问罪,以求至不平等与优越。这些欲求之中有的是公正的,有的则是不公正的。自身不如人者为求与人平等遂而诉诸内乱,已经与人平等的人再图变更则是为了高人一等。”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对民主制下能够随意更改法律的行为极其反感;并认为民主制下平民领袖的放肆是导致平民政体变更的主要原因。对此修昔底德深有同感,在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在雅典战争的领导者中,伯里克利是唯一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利用这些易变性的(指人民的情绪化,非理性——笔者注),他的继任者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它”。
总之,古希腊民主制下的那种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混乱局面以及所产生的诸恶,时时撩拨着哲学家们建构理论时的心弦。因此他们的理论中处处透露出对于稳定的政治秩序的渴望,这也是他们反民主传统的心理根源。
四、总结
对于古希腊政治理论中的反民主传统,我们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而应当将这一传统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语境、文化甚至是这一传统的创造者们的心理状态中。唯有如此,才能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在民主的诞生地却也是反民主传统发源地。须知民主的摇篮是靠反民主传统之手推动的。在民主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更应当深刻地意识民主的弊端。笔者认为依据人类现有的理性水平和道德觉悟,民主确实是一种最切实可行的制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民主的批判。孙子兵法有云:“故不知用兵之害者,则不知用兵之利也。”我们对于民主的批判,对于反民主传统的研究同样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1] 珍妮弗·托尔伯特·罗伯兹.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M].晏绍祥,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冯金朋,译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
[3] 阮炜.不自由的希腊民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4] 埃里克·沃格林.秩序与历史·卷二·城邦的世界[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81.
[5]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1-62.
[7] 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M].卢华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10.
[8]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42.
[9]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64-165.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Origin of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Ancient Greece
LI Hui, ZHANG Yan-li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053000, China)
The democratic cradle is pushed by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Ancient Greece, as the birthplace of democracy, its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s another bounty to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all analysis on the rich sources of reality, culture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 its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ancient Greece, the aristocrat complex of ancient Greeks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philosophers in their pursuit of social stability.
Athens; anti-democracy; democratic politics; aristocrat complex
10.3969/j.issn.1673-2065.2013.06.027
K125
A
1673-2065(2013)06-0101-04
2013-05-23
李 辉(1987-),男,河北衡水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张艳丽(1990-),女,山西忻州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