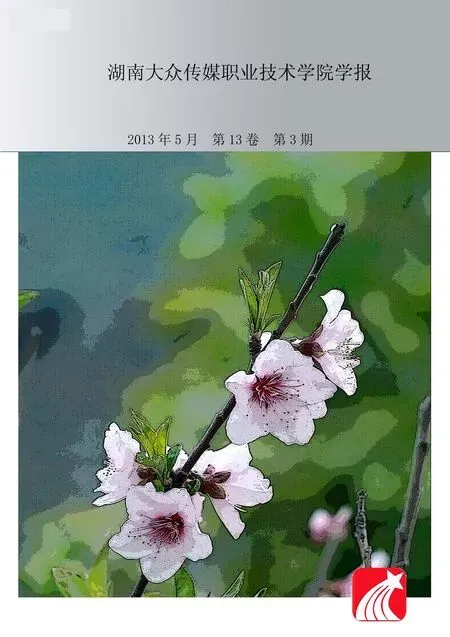把眼睛放在世界中间
万轶群 张 燕
(中国传媒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24)
一、关于纪录片的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这一概念由李普曼提出,认为在大众传播影响下,人们通常会对某一事物或群体产生一个较为固定的印象,这个印象通常并非根据亲身体验而得来,因此往往是简单粗暴甚至是错误的。
在对纪录片的认识上,很多人同样存在这样的刻板印象——认为纪录片就是完全真实的,不能有创作者任何主观意识的存在,拍摄者只要架起机器,将被摄者的真实状态拍摄下来就可以,绝对不能加入任何个人想法。
我们在回顾纪录片创作的历史时不难发现,被誉为“世界纪录电影之父”的弗拉哈迪,在其代表作《北方的纳努克》、《亚兰岛人》等纪录片中,都使用了搬演的方式再现过去的现实。这一做法也引发不少质疑和批判。可以说,从纪录片创作伊始,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就是捉摸不定的。此后各种风格流派也都围绕这个命题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主张。
上世纪20年代,格里尔逊首次提出“纪录片”概念,将“具有文献价值”和“对生活的创造性处理”作为纪录片的两个先决条件。[1]2也就是说,无论各家学派的争论多么激烈,从“纪录片”这一概念产生之初起,就没有完全排斥“虚构”的概念——纪录片从产生之初开始,就不是仅有纪实当道的。
诚然,“真实”确实是纪录片区别于故事性影片的最本质特征,也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在纪录片创作中,绝对不是只有非虚构的部分,“虚构”在纪录片创作中,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纪录片中的“虚构”并不是编造和作假,而是在与绝对真实比较之下的相对真实,包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再现与表达,以及创作者的主观认知和架构。这些再现和架构,不同于故事性影片当中的情节设计,而是在现实真实的基础上,对现有材料进行编辑,以更好地传达讯息,或试图跨越时空局限,以再现被错过的真实。
在纪录片的创作历史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虚构”,尽管各流派对于真实与虚构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几乎都存在着再现与架构的痕迹。我们同样也能发现,无论从实际操作角度,还是从对影片质量的追求来看,纯粹的、完全的纪实都是不可能达到的。
二、纯粹纪实的不可能性
(一)错过的时机
纪录片的拍摄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它不同于故事性影片,只要提前创作好脚本,再调用各种资源,集中时间拍摄即可。对纪录片来说,由于没有规划好每句台词和每个动作的剧本,在拍摄之前很难预料到拍摄对象和内容会有怎样的表现,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记录真实”的拍摄所不能避免的。因此,为了捕捉到创作者需要的镜头和内容,他们通常需要与被摄者保持长久接触,等待时机或让拍摄对象卸下心防。
但是,我们在表现一个人物或事件时,如果只是表现当下现状和未来可能性,很有可能会将拍摄对象变成“一条被切断水源的河”。过于强调现在情况,而忽视追踪行为与情感的源头与历史,这样的表现方式将眼前的真实置于被割裂的状态中,也就失去了内在的真实性。由于这些源头和起因,往往属于被错过的时机,在记录者举起摄像机之前就已消散,甚至有些内容无法只用具象的影像画面表达,因此,许多纪录片会使用采访或旁白的方式,来说明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向观众交代清楚背景和历史。尤其是涉及到历史的事实表达,更要如此。历史的错过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特别对于一个时代的纪录片来说,人们不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同步记录所发生的事件,而这种时机的错过再也无法挽回。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记录完全真实的可能性。
除了使用采访片段和旁白这类语言方式,有些纪录片也会使用影像的方式来再现真实。例如BBC纪录片《我的父亲是纳粹》中,以当年纳粹首领Amon Goeth的女儿和他的“奴隶”的相见为线索,追溯了那段黑暗的历史。在讲述Goeth当年的暴行时,使用了著名影片《辛德勒名单》中的片段——这部影片里恰好有一个军官是以Goeth为原型设计的。而在另一部同样是描述纳粹暴行的纪录片《浩劫》里,克罗德·朗兹曼则让当年历史的亲历者重新回到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几十年之后再次重现当年的行为,以此来呈现那一段痛苦的历史。
使用电影片段和同人再次搬演这两种方式,都不是正统意义上记录真实的手法,但在面对“往日不可追”的历史现实时,这种具有虚构成分的表达,反而更加有力地让观众体会到那段沉重历史的真实性。
由于时间线性而错过的时机不同,还有一些时机则是由于现实的局限而难以把握的。例如,《Lens》杂志2012年10月刊,在“向性别暴力说不”这一专题的开篇文章中,题名为《你几乎不可能拍到一个男人正在打自己的妻子》,文中说到对家庭暴力进行纪实摄影的现实困难,“对女性施暴这个主题,就摄影来说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也可能是我遇到过的最具挑战、最扰乱内心的项目。暴力是如此常见、如此危险,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天,却又难以寻觅踪迹——你几乎不可能拍到一个男人正在打自己的妻子。我只知道有一个人拍到了,她花费了整整九年。”[2]当然,和性别暴力一样,难以把握的时机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可能,只是在现实操作和伦理道德上会受到更大的挑战,对于创作者来说,在现实条件并不那么宽裕的情况下,只能进行适当的再现。
(二)流散的现实
除了捕捉不到的时机之外,现实的过于流散化也是纯粹纪实不可能达到的原因。纪录片是从电影中发展起来的影片类型,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形式与剧情片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通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将创作者搜集制作出来的影像展映给观众,借以传达一定的讯息。因此,在需要表明一定主题的前提之下,影片内容不可能如现实生活一般细水长流。历史和自然题材的纪录片自不用说,即使是对现实人物的记录,通常也要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展现主人公一段时间的生活状态,至于“一段时间”的长短,则由几天到几年不等。
出于影片创作的现实考虑,拍摄者不可能将所有真实素材都放进最后的成片之中。因此,拍摄者必须对已有素材进行架构,通过一定的结构,将这些真实素材有挑选性地展现出来,向观众呈现拍摄对象的状态。正如维尔托夫所说,在银幕上只映出一些真实的片段和真实的分隔镜头是不够的,这些画面要在一个主题下贯穿起来,使其整体上也成为真实的。[3]375而这种“真实”是经过创作者选择、架构的产物,已经不再是最纯粹的真实了。毕竟,任何创作者在进行后期加工剪辑过程中,都会不自觉地融入自己的视角,这与纯粹的客观真实已经有了不同。但在影片创作中,却又是无法避免的。
三、把眼睛放在世界中间
(一)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
在关于纪录片真实与虚构关系的各家学说中,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影响深远。维尔托夫深受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影响。未来主义强调科技对人们生活和思维的影响,偏爱力量和技术,认为艺术家在创作时应表现心境的并发;构成主义则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重于事物本身,主张通过元素之间不同的结构来构建新的现实。在这两种现代思潮影响下,维尔托夫提出“我们的出发点是把电影摄影机当成比肉眼更完美的电影眼睛来使用……我是观众按照最适合于我展示的这种或那种视觉现象的方式去观看”。[4]510这一“电影眼睛”理论,主张在前期拍摄中,不干扰被摄者来攫取素材,而在后期剪辑中又要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统辖素材为我的情感和观点服务——即“我看”,将“我”这一主体使用“电影眼睛看到的生活本来面目”展现出来。[1]68-69
简单概括“电影眼睛”理论,就是在客观拍摄记录真实的基础上,对掌握的素材进行主观的剪辑和加工,从而向观众传达自己所认识到的真实。这一主张在后来深深地影响了直接电影和真理电影这两大流派。尽管这一理论确实存在过分迷恋形式等局限性。但对于客观与主观两大要素的结合,强调在纪录片创作中两者同样不可缺少,在纪录片的创作史上有着深远影响。
(二)把眼睛放在世界中间
维尔托夫对后期剪辑中主观性的提出,实际认可了纪录片创作中的建构。创作者通过对素材的挑选、拼接以及一定方式的架构,将自己看到的世界展现出来。在这样的过程中,又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眼睛是在什么地方看待这个世界的?主观剪辑的素材应是被客观拍摄下来的,那么,摄影机的眼睛从一开始是否就是客观的呢?
在纪录片创作中,有关拍摄者的介入问题,与“现实与虚构”的争论一样贯穿始终。我们不可否认拍摄者在创作中的介入,无论是前期的拍摄还是后期的剪辑,假装不在场只是一种幼稚的伪装罢了——已经没有人仍会以为摄影机是自己摆在现场的。但是,拍摄者介入的程度和方式,仍然是纪录片创作过程中需要引起创作者注意的问题。
美国有一档电视节目,曾经找演员在餐馆里上演“服务员歧视同性恋者”的情景,同时使用隐蔽摄像机拍摄旁观者们的态度。在这一节目中,有一名男子出面阻止了服务员的语言攻击,他对“服务员”说:你信仰基督吗?不要评判他人。“不要评判他人”,既是作为一个人应当尽力做到的准则,同时在纪录片创作中,也应是创作者们时刻提醒自己的原则:纪录,不是评判。
作为一个记录者,无论是采用旁观式的观察还是参与式的交流,都应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尽管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自己的视角,但也要尽可能地保证这一视角的公正客观,我们只需提供真实情况,也可适当表达自己的态度,但绝不是从一开始就带上成见。“电影眼睛”应在世界的中间,而不是放在偏左或偏右的任何一边。只有这样,才能拍摄下真实;只有这样,才能将后续的剪辑加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成为被偏见动摇的空中花园。
正如弗拉哈迪在他的《一个电影制作者的探索》中所说:在面对一无所知的对象时,如果要捕捉它本来的形象,绝不能先入为主。抱有成见地接近事物,很容易从一开始就走错方向。最好的办法是把眼前的杂念洗掉,排除任何情绪的干扰……等待真实出现。[1]65
(责任编辑 之 义)
[参考文献]
[1] 王庆福,黎小锋. 电视纪录片创作[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2] 琳达·福塞尔. 你几乎不可能拍到一个男人正在打自己的妻子[J]. Lens, 2012(10): 80-81.
[3] 单万里. 纪录电影文献[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375.
[4] 维尔托夫. 电影眼睛人:一场革命//单万里主编. 纪录电影文献[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