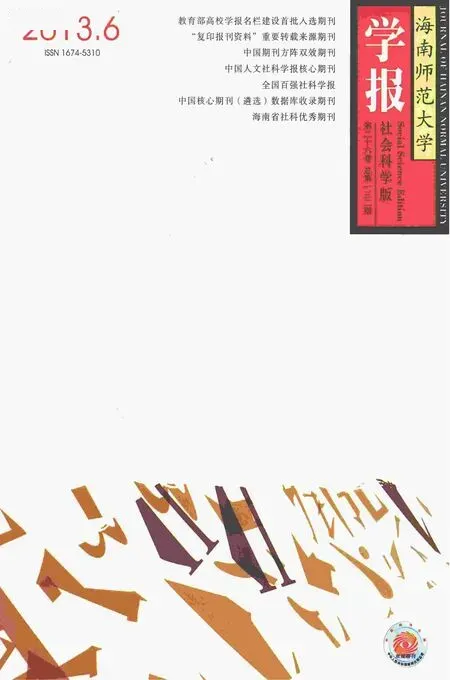莫言的苦难叙事
颜水生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莫言的小说展示了20世纪中国人所能遭受的苦难。为了充分表现苦难,莫言在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的选择上独辟蹊径,他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又吸收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技巧,在艺术效果上追求对社会历史的讽喻与否定。
一 声音与映衬
莫言对叙事策略的选择可谓独具匠心,以声音作为叙述角度,展现了莫言非凡的感觉能力。他是一个天真的孩童,灵敏地感受到了声音的变化;他又是一个深邃的老人,精细地洞察到了声音的内涵。映衬也是莫言惯用的叙述策略,无论是对于声音的表现,还是对于苦难的叙述,映衬手法的运用都恰切地表现了苦难。
莫言擅长从声音角度来表现人所遭受的痛苦,尤其是在叙述战乱、刑罚和生育等苦难时最为明显。莫言的感觉相当发达,声音、色彩都是他可选择的叙述角度,甚至可以说,声音在莫言小说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可以成为一个自在自为的叙事层面,蕴含着丰富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声音是“真理”的“显像”,也就是说莫言小说中的声音是“痛苦”的表现形式。首先,声音包含着表现功能,描写声音可以被认为是在直接表现个体自我意识到的痛苦,正如现象学观点所说,“声音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的存在”,[1]101如《檀香刑》讲述刑罚之苦时,充分运用了声音的力量,比如“孙丙突然地发出了一声尖厉的嗥叫”、“一声高似一声的嗥叫声”、“孙丙的嗥叫再也止不住了,他的嗥叫声把一切的声音都淹没了”、“他的身体里也发出了闹心的响声”,[2]这些声音充分表现了孙丙意识到的痛苦。其次,声音包含着情感功能,声音可以对人产生影响,引起情感反应,正如现象学观点所提出的,“声音被听见,……主体并不要越到自我之外就直接地被表达的活动所影响”,[1]96如《红高粱家族》和《檀香刑》分别写到了罗汉大爷和孙丙的痛骂声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人群里的女人们全都跪到地上,哭声震野。”[3]34最后,莫言以一种声音为中心,并衬以其它多种声音,组合成声音的交响世界,以实现“苦难的混响”效果。如莫言在讲述“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时,[3]11写到了多种声音,有日本鬼子的吼叫、孙五的嚎啕大哭、罗汉大爷的痛骂、女人的震野哭声等;在讲述6个日本鬼子玷污二奶奶的情节时,莫言也写到了多种声音,如“女人的嘶叫,孩子的嚎哭,鸡飞墙上树的咯咯,毛驴挣脱缰绳前的长鸣,夹杂在一起”,[3]318莫言还写到了二奶奶声音的变化,二奶奶的声音在嘶叫、嗥叫、嚎叫、狂叫、吼叫之间变换,夹杂着日本鬼子的怪叫、狂笑与嗥叫,以及小姑姑的惨叫,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集中体现了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以及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痛苦。莫言在描写生育之苦时也是从多种声音来展示女人的痛苦,如写上官鲁氏难产,“她不可遏止地发出了连串的嚎叫”,[4]8上官鲁氏的嚎叫声、念叨声、呻吟声,夹杂着上官吕氏的责骂声、上官家女儿们的哭喊声,混合着日本鬼子的枪炮声,将上官鲁氏的生育之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声音对于痛苦不仅具有直接表现作用,也具有间接衬托的效果,如《红高粱家族》着重讲述的是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毁庄稼牡畜无数,还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使我们村几乎人种灭绝”,[3]11但莫言对声音的叙述使苦难更加恐怖,更加令人绝望。可以肯定地说,罗汉大爷受刑时的痛骂声,二奶奶临死前惨绝人寰的嚎叫声,是《红高粱家族》中最凄厉、最残酷,也是最为震撼人心的声音。总之,声音是莫言叙述苦难的独特角度,莫言能把人间苦难表现得如此深切,与他选择的叙述角度密不可分。
正如对声音的表现,映衬也是莫言苦难叙事的重要特征。莫言经常把物质苦难与精神苦难进行映衬叙述。首先,在物质苦难中,莫言表现最多的是饥饿。他在《粮食》、《丰乳肥臀》、《蛙》等小说中多次讲述了饥饿之苦,饥饿在莫言创作中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他说:“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5]其次,孤独、压抑、变态等精神痛苦也是莫言小说的重要内容。莫言早期小说主要表现了特定年代的人的精神孤独与苦闷,如短篇小说《枯河》展示了小虎孤独、苦闷、压抑的精神状态;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讲述黑孩拔光地里的萝卜以发泄内心的苦闷和冤屈。莫言80年代创作的小说对性的描写表现出性狂欢的特征,而90年代以后的小说更多地表现性压抑引起的心理变态,如《丰乳肥臀》讲述龙场长由于性压抑而心理变态;《生死疲劳》讲述洪泰岳由于性压抑而产生的心理变态,这些精神痛苦体现了莫言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探索与思考所达到的高度。最重要的是,莫言在叙述苦难时,物质苦难与精神苦难是相互映衬的。如在《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娃不得不忍受饥饿与孤独的双重煎熬。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不仅要忍受胎儿难产的肉体痛苦,而且要忍受胎儿性别带来的精神恐怖。《丰乳肥臀》在讲述乔其莎被奸污的场景时,映衬色彩最为明显,“她像偷食的狗一样,即便屁股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也要强忍着痛苦把食物吞下去,并尽量地多吞几口”,[4]400乔其莎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莫言通过映衬手法表现了饥饿带来的肉体痛苦,远超过女人所遭受的精神污辱。
总之,莫言在苦难叙事中,以声音作为独特的叙述媒介,以映衬作为独特的叙述手法,充分展示了苦难的深度与广度;莫言对于叙事策略的选择,展示了他独特的感觉能力和艺术思维。
二 后现代与时空体
自《红高粱家族》开始,为了表现苦难,莫言运用了多种叙述技巧,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技巧,又吸收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述技巧。莫言对小说“叙述者”的灵活运用以及对叙述视角的灵活转换,都体现了他在叙述技巧方面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借鉴吸收;同时,莫言在对时间与空间的表现方面,展示了时间与空间的特殊关系,创造了独特的时空体小说,在完整的时空体中恰切地展示了苦难的深度和广度。
第一,“叙述者”的灵活运用。首先,在莫言小说中,最常见的“叙述者”形式是“元叙述”,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元故事叙事”。[6]157-163《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小说都运用了这种方法。这些小说中的叙述者既是故事行为的讲述者,又是故事行为的参与者。这种叙述形式通过“叙述者”“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引导读者认同叙述的可靠性和权威性”。[7]更为重要的是,莫言发挥了叙述者的思想职能,他经常使叙述者介入故事讨论,如《红高粱家族》在讲述二奶奶的受难情景时,叙述者直接介入了故事讨论,严厉地批评日本鬼子的兽行,小说写到:“我现在想,如果那天面对着二奶奶辉煌的肉体的是一个日本兵,二奶奶是否会免遭蹂躏呢?”叙述者提出这个问题,然后陷入一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中,“会不会啊?会?不会?会不会?”[3]325叙述者的心理独白其实就是介入故事讨论,也就体现了热奈特所说的“叙述者的思想职能”,[6]181-182这种思想职能的发挥加深了对日本鬼子罪行的批判。其次,莫言突破了传统小说只有一个叙述者的写法,他不仅在《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小说中使用了多个叙述者,并且形成了“元小说”叙述形式。《檀香刑》有5个叙述者,《生死疲劳》主要有两个叙述者:蓝解放与蓝千岁,另外还设置了一个名为“莫言”的作家,这三个人物在小说中都充当了“叙述者”的作用,他们三人各自讲述故事,并且相互评论、相互攻击,攻击对方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如:“莫言那小子在他的小说《养猪记》后记中曾提到过此事,并说他参与了编剧,我断定此事多半是他瞎忽悠。”[8]305小说中甚至还有“我要与那种所谓的‘白痴叙述’对抗”。[8]366这种叙述者“使叙述行为直接成为叙述内容”[9]、“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10]其实就是“元小说”叙述方法。
第二,叙述视角的越界与转换。虽然《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的叙述者都是内视角“我”,但两部小说的叙述者“我”完全突破了传统内视角的限制,叙述者“我”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知视角,无论是讲述罗汉大爷的受刑,还是讲述上官鲁氏在战乱中的逃亡,莫言都是以这种内视角讲述故事,这种内视角使叙述者以“亲历者”身份讲述故事,不仅增加了讲述行为的真实性,也能更直观、更真实地展示苦难场景。莫言在苦难叙事中不仅突破了传统内视角的限制,而且还进行了视角的转换,比如《红高粱家族》在讲述二奶奶受难时,有这样语句:“她听到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小姑姑发出一声惨叫。”“二奶奶拼尽全力嚎叫了一声,她想奋身跃起,但身体已经死了”,[3]326显然这些语句的叙述视角已经完全转换成“上帝”视角。《檀香刑》的叙述视角也经历了限知视角到全知视角的转换,小说的凤头部和豹尾部分别以赵甲、眉娘、小甲、钱丁、孙丙、知县等人作为叙述者讲述故事,猪肚部分则又是以全知视角讲述故事。
第三,叙事时空整体化。巴赫金在评价歌德时说,“善于在世界的空间整体中看到时间、读出时间,另一方面又能不把充实的空间视作静止的背景和一劳永逸的定型的实体,而是看作成长着的整体,看作事件。”[11]234这种评价也契合莫言。在莫言小说中,空间和时间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成长着的整体,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活动的、联系的故事整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莫言实践了一种独特的“时空体”小说。巴赫金对“时空体”有过界定,“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11]274-275从这个概念可知,整体性是时空体小说最重要的特征。时空整体化是莫言苦难叙事最重要的叙述技巧,莫言不会片面地、孤立地叙述苦难,他往往会把若干个苦难事件放置在整体的时空背景中,增加苦难故事的内容,形成苦难的“大合唱”,从而更好地展示苦难的深度和广度。如《丰乳肥臀》讲述上官鲁氏的生育痛苦时,整整用了9个章节合计46个印刷页的篇幅,叙述时间的推移从主观上表明上官鲁氏遭受痛苦之久,叙述空间的转换从客观上表明上官鲁氏遭受痛苦之深。时间与空间又是一个活动着的整体,若干个苦难事件在这个时空体中同时发生发展,如第九章的开头鲜明地体现了莫言的“时空体”意识,“一九三九年古历五月初五上午,在高密东北乡最大的村庄大栏镇上,上官吕氏领着她的仇敌孙大姑,全然不顾空中啾啾鸣叫的枪子儿和远处炮弹爆炸的震耳声响,走进了自家大门,为难产的儿媳上官鲁氏接生,她们迈进大门一刻,日本人的马队正在桥头附近的空地上践踏着游击队员的尸体。”[4]43“古历五月初五”既是一个现实时间点(苦难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更是一个历史时间点(爱国英雄屈原投江之日/中国传统的端午佳节)。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官鲁氏难产、日本人践踏游击队员两个事件相互联系成整体。现象般的单纯的随意的时间选择,是与莫言格格不入的,苦难叙事的时间点是刻意安排的,如《红高粱家族》“我爷爷”打伏击、我奶奶牺牲的时间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3]2时间在莫言小说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用时间去充实这种空间的毗邻关系,贯穿在其中。”[11]239“古历五月初五”、“八月十五,中秋节”把历史与现实融合成整体,无声地控诉日本鬼子让中国人适逢佳节却不能过,本应合家欢乐的日子却一个个地深陷苦难之中。现象般的单纯的空间毗邻也与莫言格格不入,“他把空间并列的东西分别归属于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的成长时代。”[11]239莫言具有从空间中看出时间的非凡能力,他把上官鲁氏难产和日本鬼子践踏游击队员两个事件并列,是为了隐含和预示故事的结局,孙大姑的惨死从她的出场就已经预告了。萧红在《生死场》中叙述金枝的生育痛苦时,她也拿动物生产与金枝生产相互映衬,她的叙述目的也是表现女人生育痛苦,表现妇女在男权社会中所遭受的灾难般命运,但是相比较而言,萧红的叙述时空远没有莫言的深广,莫言不仅详细地讲述了上官鲁氏难产时自然存在的肉体痛苦,而且详细地讲述婆婆对她施加的肉体和精神的双层压迫,上官家的驴子难产、上官鲁氏7个女儿的慌乱、游击队的战斗、日本人的屠杀,这些苦难事件都是以上官鲁氏的难产为中心,莫言就是在这样整体的、深广的时空范围内把苦难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在时空整体中展现苦难,增加了苦难叙事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是莫言苦难叙事的精华之所在。
总之,莫言的苦难叙事充分展示了他的叙述天才,在内容方面涉及了20世纪的中国人所能遭受的所有苦难,在形式方面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叙述技巧,大大提升了苦难叙事的深度和广度。
三 讽喻与否定
讽喻是小说的重要功能。无论是中国传统小说,还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都体现了讽喻的价值,诸如吴敬梓《儒林外史》和卡夫卡《变形记》之类的经典小说,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抽象讽喻,其深刻性和普遍性不仅体现了小说文体的艺术高度,而且展现了人类的思维深度。莫言在苦难叙事中充分展示了讽喻的艺术魅力,他的讽喻艺术在世界小说史上也占有一定的位置。
在西方悲剧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悲剧天生蕴含着嘲弄。小说理应也是如此,莫言展示了悲剧艺术的魅力,但无论是他小说中的社会悲剧(如《蛙》),还是性格悲剧(如孙丙),它们都对历史、社会、个体具有强烈的讽喻意义。巴赫金有一句名言:“讽拟滑稽化形式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起着决定作用的方面,为小说作了准备。”[11]481巴赫金把讽刺模拟体视作是小说的重要类型,而莫言小说也表现了讽刺模拟体的诸多特征,体现了讽喻艺术的内涵与魅力。莫言在苦难叙事中主要运用了滑稽、隐喻、对比、戏仿、变形等讽喻方法。第一,莫言塑造了一些滑稽、荒唐的人物形象,增加了小说的讽刺性。《生死疲劳》中的许宝和洪泰岳是莫言特意刻画的滑稽人物,许宝形似小丑、行为怪异,他背着褡裢、手摇铜铃、以劁驴阉马为业,两只眼睛贼溜溜地专往生畜的后腿间瞅,喜欢拿驴卵牛蛋下酒,许宝也就成了人们逗笑取闹的对象,尤其是顽童对许宝的编排嘲笑集中表现了滑稽形象:“许宝许宝,见蛋就咬!咬不着蛋,满头大汗。许宝许宝,是根驴屌。吊儿郎当,不走正道……”[8]60洪泰岳刚出场时也是西门屯聚众取笑的对象,他敲着牛胯骨炫技,以公鸭嗓子卖唱,解放后又始终保留着战时武工队员的装扮,不仅在语言上始终保持着革命时代的话语,而且在行为上做出了许多荒唐的事情。莫言小说中的滑稽荒唐形象可以归之于巴赫金所说的“怪诞形象”系列,“怪诞永远都是一种讽刺”。[11]355莫言通过这些怪诞形象讽刺的是历史的荒唐和人性的异化。第二,隐喻在莫言的讽刺艺术中也占有重要位置。短篇小说《拇指铐》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一部隐喻体小说。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环境都具有隐喻意义。阿义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穷困,母亲病重在床,生命垂危,小说开头就把人生苦难具体化。阿义在买药的路途中所看到的自然环境令人毛骨悚然,他所遇到的人也充分说明了人情冷漠和世态炎凉。小说的情节也隐喻了人生命运的难以预测、难以把握。阿义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铐住了,失去了自由,无论他怎么挣扎反抗都无济于事,最终灵魂出窍。小说的题目“拇指铐”更是意味深长,拇指铐把人固定住,让人失去自由,人越挣扎越疼痛。“拇指铐”是人生苦难的隐喻,它牢牢地固定住人类,没有人可以逃脱。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提出的“种的退化”命题,也是历史的隐喻,莫言追求的“纯种红高粱”隐喻着民族图腾和传统精神。第三,对比也是莫言常用的讽刺技巧。《丰乳肥臀》第九章结尾写日本报纸刊登了日本记者拍的照片,照片内容是日本军医救治中国产妇和婴儿;然而小说的前部分讲述了日本鬼子在上官鲁氏家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种对比充分表现了日本鬼子虚伪、狡诈、凶残的本质。上官家的女人与男人的形象对比,显示了阴盛阳衰的状况,这既是对女性的歌颂,其实也可以说是对男人的讽刺,这与莫言的“种的退化”主题是一致的。此外,上官家的祖先与上官福禄父子的对比,以及《红高粱家族》中的祖先与后代子孙的对比,都是具有现实讽刺意味的。第四,戏仿也是莫言常用的讽刺技巧。《生死疲劳》第三十一章讲述常天红模仿样板戏排演高密猫腔《养猪记》,其中的唱词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代,比如“一头猪就是一枚射向帝修反的炮弹我小白身为公猪重任在肩一定要养精蓄锐听从召唤把天下的母猪全配完”,[8]307这样的语言在特定时代是合乎逻辑的,但现在看来却又是荒唐可笑的,这是一种具有极强讽刺意味的戏仿,莫言对样板戏的戏仿可以说是对特定历史时代的讽刺和批判。第五,莫言在《食草家族》和《生死疲劳》等小说中集中使用了变形的讽刺手法。《食草家族》把祖先描写成手脚生蹼,但正是这些手脚生蹼的祖先有着轰轰烈烈的辉煌历史,而他们的后代相形见绌。食草家族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莫言运用变形手法改变祖先的形象,使后代成为“阉割”的结果,这是对现代人进行辛辣的讽刺。《生死疲劳》中的变形手法,使莫言对人类和历史的讽刺更加入木三分,正所谓人不如驴、牛、猪、狗、猴更具有人性和人情。
如果说悲剧性是对世界与历史的正面否定,那么讽喻性则是对世界与历史的反面否定。悲剧性与讽喻性就像硬币的两面,体现了莫言对世界与历史的整体看法,苦难就在这样的艺术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法〕德里达.声音与现象[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莫言.檀香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373-374.
[3] 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4] 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5] 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C]//莫言讲演新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36.
[6]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 王丽亚.“元小说”与“元叙述”之差异及其对阐释的影响[J].外国文学评论,2008(2).
[8] 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9] 林秀琴.元小说[C]//南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56.
[10] 〔英〕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俊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230.
[11]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小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