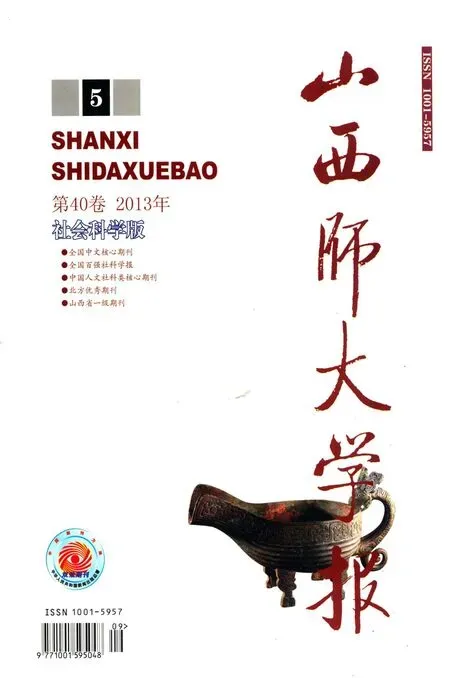从“何为年画”到“年画为何”
——年画研究的路径探析①
王 媖 娴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1620)
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事项,年画在我国源远流长,不少文献典籍均载有年画的相关资料。不过,尽管对于年画的记载发端甚早,自觉的学术性研究却大约迟至19世纪末才逐渐出现。其中,国内外学者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研究旨趣与学科背景,在年画研究的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国内学者多来自美术学、民俗学界,从“年画是什么”的角度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与记录,大多就年画论年画;国外学者则主要以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从“年画为何如此”的角度来就年画论社会。厘清国内外学者不同的研究路径,有益于开阔我国年画研究的视野,开辟年画研究的新路径,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年画的立体化认识,扩展年画研究的学术意义。
一、围绕“是什么”的国内年画研究
就国内情况来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年画这一古老的民俗事项在诸多古代典籍中都留下了它的身影。不过,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成系统的年画研究是从建国后开始的。在迄今为止的几十年中,将年画视为一种“民间美术”或“民间工艺”、主要由民俗学、民艺学、美术学等相关学科展开研究已在学界达成普遍共识。即便在这种概念体系内,也蕴含着不尽相同的两条研究路径——美术学之本体研究与民艺学(民俗学)之功能研究。“前者可以纳入一般艺术分类学的框架,与一般美术相比较,并直接与美学相呼应;后者显示出其自身的特点,使‘民艺学’相对独立,可直接与民俗学相呼应。”[1]6
(一)美术学的路径——对年画之视觉表现的关注。这种研究视角多将年画视为一种美术现象,尝试运用美术学的若干理论与思路进行剖析。就具体的研究内容及目的来看,此种研究更注重我国年画在艺术本体、艺术价值方面的内容,如画面风格、造型特点、色彩搭配,且往往结合与文人绘画的对比,阐述年画作为“民间美术”的特点。
就研究成果来看,美术学视角下的成果可大略分为三类:“描述”、“史”和“概论”。“描述”型作品从微观层面展开,关注年画的视觉特点或制作工艺,对整个过程尤其是最后的图像做详尽描述;“史”类成果则重点考察年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风格流变或工艺变革,注重结合时代背景讨论年画的演变;“概论”类从宏观层面旁征博引,几欲囊括对全国各地年画的研究,对各地年画进行横向比较,但有浮光掠影之嫌。
在研究初期,年画史的撰写蔚然成风。相关代表著作如:阿英编著的《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王伯敏的《中国版画史》(1961),郭味蕖编著的《中国版画史略》(1962),薄松年的《中国年画史》(1986),以及郑振铎的《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2006再版),等等。这类成果详细地介绍了年画在不同时代的艺术特色、制作手法,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年画背后的社会、经济、时代背景,以年画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著名年画研究者王树村的研究便主要立足于此。王树村的研究主要围绕家乡杨柳青的年画,其对于杨柳青年画的研究之细、之广目前无人企及。其代表作如:《中国美术全集·民间年画》(1985)、《中国民间年画》(1989)、《戏出年画》(1990)、《中国民俗版画》(1992)、《中国民间画诀》(2003)、《中国年画发展史》(2005)及其与弟子王海霞合著的《年画》(2005)等。其中,《中国年画发展史》详细介绍了中国年画的发展源流和题材内容、各地年画的特点,尤其对年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流变和制作工艺做了精细的梳理;而《年画》一书则对年画的艺术与文化价值、民间画诀、发展史、搜集与收藏、研究与保护做了探讨。另外,谢昌一的《山东民间年画》(1979)从发展、表现方法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等方面对山东民间年画做了详细论述。
这些学者对于年画的研究功不可没,且由此奠定了我国年画研究的主流范式。在此之后,沿此路径,诸多后起之秀针对国内各年画产地尤其是颇负盛名的年画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记录、整理、描述工作,为我国的年画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限于篇幅,在此不赘言。
(二)民俗学的路径——对年画民俗内涵及文化价值的探讨。实际上,就我国各类古典文献典籍对“年画”的记录来看,彼时便已内含有对“年画”的两种认识倾向。上文提及的工艺美术倾向为其一,而将年画视为春节必备品之民俗考察的倾向亦不鲜见,而这一路径的探讨在建国后的学界尤其是民俗学界亦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总的说来,这一路径按侧重点又可分为两类:
一种是强调年画与民俗生活或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将年画纳入民俗的视野,对年画“民俗”特性的强调胜于对其“艺术”性的强调,如李明的《桃花坞年画与吴地民俗文化》(1993),马福贞的《消失的媒介:农耕时代民间年画的功能和作用》(2007);亦有学者将年画的视觉意象作符号式的分解,对其中的各种视觉符号——如莲、鱼、蝙蝠等,进行有关民俗心理的结构主义式的解读。
另一种是将年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来研究,如冯敏《论中国木版年画濒危的原因与保护对策》(2005),漆凌云的《滩头年画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王海霞的《对传统年画保护问题的思索》(2007),王巨山的《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及博物馆化保护研究》(2007),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成果——《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系列的陆续问世,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书面资料和影像资料。
截至目前年画研究虽然看上去硕果累累,但繁荣之下亦有危机。就像张紫晨先生指出的:“民间美术尽管属于美术范畴,但它与一般的美术有许多的不同,它的实用性和物化性程度相当大,且与其生存、发展的空间环境密不可分。它既是美术,又是一种特殊的美术,因此除了其美术功能之外,必须把它放在生产、生活环境中,发掘和宣扬其在文化史和文化学上的意义,突现其在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史中的独特价值和贡献。”[2]不过,就国内近十几年来对于年画的研究来看,“就事论事”的平面化倾向甚为明显——对年画的研究往往仅仅关注年画的某个方面,如视觉形式或是制作工艺、民俗功能;对年画史的研究则往往止于呈现封建社会中的年画是怎样的,而极少全面、深入地考虑为什么是这样的。两者均未将年画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没有从小年画中折射出大社会、大历史;“做什么”、“怎么做”阐述有余,而“是谁在做”、“为什么这么做”探讨不足。然而,就像彼得·伯克告诫我们的:“如果我们忽视了图像、艺术家、图像的用途和人们看待图像的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千差万别,就将会面临风险。”[3]12也就是说,“解读这类画像也必须将叙事放在具体的背景下。换言之,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历史学家必须问,是谁用这种方式给谁讲故事,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3]208可惜,这类问题在目前的国内年画研究中似乎都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
并且,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由于局限于对已有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内容多有重复之处;络绎不绝的研究者中走马观花者为多,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亦往往囿于年画史(尤其是清代)的叙述及年画民俗功能的介绍,跨学科的问题意识、理论思考在目前诸多的国内年画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体现,这种情况使得年画研究只能局限在相关几个学科内部自说自话,而难以实现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交流。
二、国外的年画研究路径
海外学者对于年画的研究则另辟蹊径,体现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并对其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意义挖掘上有所推进。事实上,本土学者的年画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最早将年画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并进行收藏和研究的是西方学者。他们从异文化的视角,看到了年画所具有的强烈的中国特色;而且,海外学者往往将年画放置在物与人、物与时代、物与国家这样的视野下进行讨论,避免了见年画不见人或是将年画研究静态化、平面化的缺陷。
早在1896年、1897年,俄国科学院院长科马罗夫就曾在我国东北收集了一批年画,并于1898年在圣彼得堡举行展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中国木版年画展。紧随其后,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V. M. Alekseev)在我国北方一些产地也广泛收集年画并进行研究,并逐渐成为一位中国年画的专家。20世纪上半期,Clarence Day以1914年出版的亨利·道尔(Henri Dore)所著《中国迷信研究》一书的材料为基础,从神像年画入手来分析中国的民间信仰,但对年画本身并没有展开论述。
在近三十年中,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年画海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史学界,可大致分为两个主题:
(一)国家、精英、大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相互关系。海外学者们的史学出身使其格外关注年画这一艺术形式在不同的时代的生存、发展状貌,并注重对年画与国家、精英、大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理性思维特征,其角度颇为新颖,论述亦较为深刻。
在这些成果中,较为突出的是霍大卫、洪长泰和安雅兰的研究。霍大卫《革命时期的中国艺术与意识形态》(1979)一书以及洪长泰的论文《社会主义的两种形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木刻画》(1997)均涉及到了延安时期的木刻年画运动,讨论了民间年画与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相互关系。安雅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画家与政治》则涉及了1949—1979年30年间国家的艺术方针以及国家与艺术工作者(包括新年画运动中)的相互关系。
不过,这些研究基本聚焦在年画发展史上某个特殊的时间段——尤其是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这种特殊的年画存在状态并不足以反映中国年画的普遍特点或发展态势,或者说在“年画为何如此”的问题上没能在纵向维度上给予更全面的呈现与剖析,从而难以接近对年画变迁内在动力的探析。正如洪长泰反思的:“要想搞清楚农民对新年画的态度有些困难,因为他们大多几乎不识字,所以很难找到关于其反应的文字记载。……不过,各省的文化部门以及改革工作队发表的文章或许能够为我们了解农民们那不易察觉的心灵世界提供蛛丝马迹。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就是某些杂志、期刊上不时发表的有关年画改革的调查报告,里面会有一些农民的评论。不可否认,打着农民旗号的这些评论很可能迎合精英们的需要而做过改动,但是他们朴实的陈述却让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正是他们真实的反应。我也试图结合这些精英们的报告尤其是年画改革者的文章来讨论这一问题。或许,我也会犯我正在竭力避免的错误。”[4]也就是说,这些年画“断代史”的研究主要基于各种精英撰写的文献资料,作者本人基本上并未亲赴当地展开调查,而只能从间接的渠道——来自上层的“传声筒”窥探民众在年画特定发展阶段中的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研究在说服力上打了折扣。
(二)年画的生产与接受。意识到这一问题,同样出身历史学界的傅凌智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华北地区的年画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其中尤以山东杨家埠、河南朱仙、河北武强三家颇负盛名的年画产地为重点考察对象,最后形成了《对幸福的膜拜——中国北方农村的年画、艺术与历史》一书。作者试图从年画的本质及其功能入手,从年画的生产与接受两方面来探讨人们如何借助年画这一印刷形式来表现和传播其对于过去和现在、对于社会和文化的理解,从而进入对于乡土中国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探讨。
三、年画研究路径新探
如前所述,年画在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术学、民艺学、民俗学学科内部,这些学科的学者多将年画视为一种民间艺术而对其独特的民间风格及制作工艺予以细致描述,从而其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意义;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年画的研究则几乎集中于历史学界,他们以年画为透镜,来透视中国在某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其研究更多地体现了对年画这一文化现象所体现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之关系的探讨。正是国内外学者学科背景、研究兴趣与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双方在针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时的路径殊异。
不过,“社会现象通常并不是单一因果关系的或始终如一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框架能够提供一套全面的解释”[5]27,年画的研究亦是如此。国内近十几年来的年画研究过多地囿于早期诸位大家所形成的研究路径而未能将其推上新的高潮或另辟新的天地,反倒是海外历史学学者的他山之石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学术视界。但就像上文所指出的国外年画研究存在的局限,我们亦不能一味地仿效而失去自我创新的能力。只有立足中国年画的独特历史与现实,立足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广泛借用多学科的视角及理论,我们的年画研究才能跳出现有学科的有限范畴,突破窠臼,开辟自己的崭新路径,从而与国际接轨、与其他学科互动对话。
基于以上思考,结合笔者的田野调查经验,特提出以下两条研究路径供同仁参考。
(一)通俗文化的路径。就年画来说,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民间艺术品有失偏狭,它掩盖了年画最初及最根本的特性——一种用于消费的人工制品,一种传统社会中的大众传媒手段,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也就是说,就其发展历程来看,年画更趋近于强调生产与消费环节的“通俗文化”,“它是由大批生产的工业技术生产出来的,是为了获利而向大批消费公众销售的。它是商业文化,是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它的成长意味着:任何不能赚钱、不能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文化,都很少有地位……”[6]16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化的年画,“所体现的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其所追求的最终是……交换价值,与商品的运作方式是同构同质的”[7]1。这一视角提示我们:作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民间艺术”,年画的制作与传播——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消费品,它的生产与消费的具体运作及内在逻辑——都应纳入我们的视野,我们需采取通俗文化的广阔视野给予考察与反思。
(二)“物的社会生命”的路径。1986年,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在其编著的《物的社会生命》一书中对物的社会建构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关注被交换的物,而不仅仅是交换的形式或者功能,将使我们有可能发现连接交换与价值的东西是广义上的政治……商品,一如人,都有社会生命。”[8]12具体说来,“物的社会生命”指的就是:“商品和其他物品包括礼品一样,在社会不同等级的流通过程中,乃至在跨文化的流通过程中经常得到重新规定。一种物质的生命并不只在它变成商品,走出生产线、走向市场和消费者时就完结了,市场生活只是它生命中的一个段落。……在走出市场后,商品走入的是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走入的是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在这些接下来的阶段中,这一物质开始了它的文化和社会生命,……它可以在文化和社会的流动中被重新界定”[9]12—13。这一视角提示我们,对于年画这一“物”的研究必须跳出“画”的实物层面,而将目光扩展至围绕年画所展开的人与物、人与人等各种关系上,尤其是不同利益主体对物的塑造、认识和利用上,剖析年画“为何”呈现出如此的发展历程——为何产生、为何发展、为何兴盛、为何萧条,甚至为何消亡。由此一来,便打破了将年画置身“世”外、仅做静态描述的研究俗套,而将其研究立体化、动态化。这种研究路径的目标不止于对“年画为何物”的详尽介绍,而在于借助年画这一“工具”来反观中国特有的文化、社会、历史乃至政治,从而使研究视野不再拘泥于“画”中,而体现了对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或时代背景)、空(具体地域的社会与文化)、人(年画的生产者、消费者及其他利益主体)的三维考察,也就赋予了年画以更为深刻的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从而打开年画研究的新局面。
[1] 张道一.民间美术的二分法[A].冯骥才主编.鉴别草根——中国民间美术分类研究[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2] 张紫晨.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J].装饰,1988,(4).
[3]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 Chang- Tai Hung. Repainting China: New Year Prints (Nianhua) and Peasant Resistanc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42,No.4.
[5] (美)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M].张天虹,张洪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6]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A].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美)阿尔君·阿帕杜莱.商品与价值的政治[A].夏莹译.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 孟悦.什么是“物”及其文化?——关于物质文化的断想[A].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