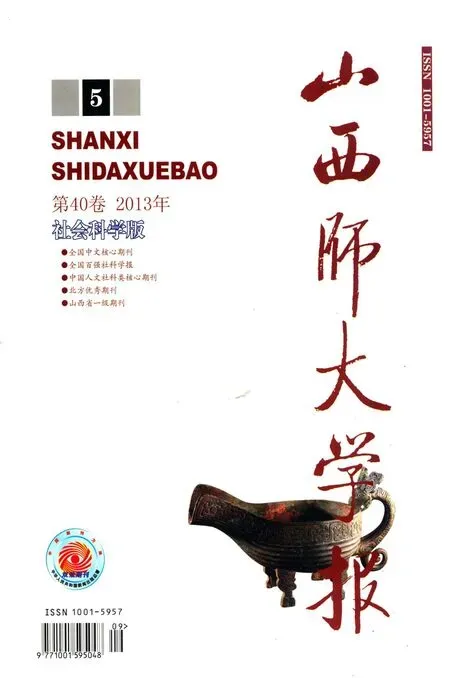从文人创作心态看田园与农村的对立统一
彭 曙 蓉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9)
田园诗是中国诗歌的重要题材,田园作为中国文人的精神归宿,被赋予浪漫色彩。然而,田园的实体是农村,二者不可分离。但田园诗中的“田园”,却与我们理性认知中的农村始终保持着距离。那些反映农村苦难生存的诗,总让人触目惊心。它们通常也被称为“田园诗”,其与乌托邦式的田园诗,二者差异之大,不禁令人对田园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产生深深的困惑。简言之,有关农村题材的诗歌,文学史上出现了“农事诗”、“田园诗”、“农村诗”、“农村词”等几种称谓。但对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间关系却从没有明确的解释和界定。本文旨在通过文人创作心态这个窗口,阐释“田园”与“农村”在诗歌世界中的内涵,探讨田园与农村作为不同写作取材范畴的关系,及文人创作心态在其中所起作用,以期获得对中国古典诗词中这两种称谓的再认识,探寻田园与农村在诗歌中的对立与统一的原因。
一、田园诗与农事诗同源而分流
《诗经》时代,已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农事诗[1]54,其中,《七月》被认为是“《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1]54,甚至被认为是“我国文学史上农事诗的滥觞”[2]19。《七月》中农奴们一年到头紧张忙碌、衣食住行皆困顿忧伤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了文学的画廊中。但那就是“田园”的本初世界吗?事实上,农村,从没有以“田园”的面貌飘离过这充满着压迫的人世间。就此而言,文学史上,对于田园诗与农事诗这两种不同面貌的诗歌,还是隐约有所区分的。然而,这两类诗中真正的“主角”——田园与农村,其实半点不可分离。它们如同一面镜子,光亮的那面是田园,黯淡的那面是农村。关键是,文人意欲将它的哪一面呈现给世人。
首先来看农事诗。在郭预衡先生主编熊宪光执笔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中,对《诗经》的题材进行分类时,专门分出一类“农事诗”,但没有对该概念进行界定。大致意思即农事诗就是描述农事活动和劳动生活、反映农业生产的诗歌,并认为“反映农业生产和劳动生活的农事诗在《诗经》中为数不少”[3]109。当代学者之所以较一致地称《诗经》中描写农村题材的诗为“农事诗”而不是“田园诗”,这与他们对“田园”之内涵的认识颇有关系。“田园”一词主要因陶渊明及其诗歌而进入读者视野,其内涵明显具有文人所赋予农村的人格化、理想化甚至艺术化的色彩,带有鲜明的文人主体意识。因此,用这种带有鲜明的文人自我意识的概念去概括先秦的诗歌,显然是不当的。故在论及田园诗的源起时,学者们基本都步调一致地从陶渊明的诗歌谈起。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1]63“田园诗是他(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1]63
至于“农村诗”的称谓,可参看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执笔者赵仁珪先生认为:“陆游的农村诗既不失中国田园诗的传统本色,又有很强的时代感。……陆游的农村诗既保有田园诗淳朴古雅的传统,又避免了因过分追求闲适隐逸而带来的冷漠绝尘的倾向,最终形成既幽美纯静、又富有生活气息;既清新自然,又不失热烈活泼的一家之风。”[4]196这段评论中,农村诗与田园诗被作为两种诗歌题材而截然分开,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言下之意,田园诗产生在前,风貌上更古雅淳朴,多表现闲适隐逸的情调;而农村诗产生在后,既有传统古朴平淡的风貌,又有关心农事的时代特点和表现家园特色的情趣。
自有农事诗和田园诗以后,诗人们伴随着自己或多或少隐居农村的经历,对农村耕作与风土人情的关注日益增加。当词作为一种新的体裁出现后,诗人们随即又将此题材引入其中,即现代学者在探讨词作题材时通常都会提到的农村词。如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论苏轼词时认为,苏词众多题材中以抒情词、咏物词、农村词三类成就为最高。[4]116—119谈到辛弃疾时,则说“辛弃疾直接或间接描写农村的词约有三、四十首,这是对苏轼农村词的继承和发展。虽和苏轼一样,对农民的痛苦生活缺乏描写,但对农村的劳动生活、自然景色有更为广泛的表现”[4]215。
由上述可知,把最早出现的有关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的诗称为农事诗,与把陶渊明有关农村生活的诗称为田园诗,各位学者的意见基本一致。分歧主要是从宋代范成大、陆游等有关农村的诗与苏轼、辛弃疾有关农村的词开始的。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对田园诗与农村诗二者的内涵进行辨析,首先应辨析田园与农村各自作为一种写作取材范畴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内涵。总之,田园诗与农事诗同源而分流,其主体虽然都离不开农村及其人事活动,但前者带有更多诗人的主体印记,后者的写作态度则更客观冷静。农事诗发展到后来就成为既有诗人自我追寻又充满民生关怀的农村诗。
二、田园与乡村作为写作取材范畴之内涵再界定
田园,在文学领域是一个带有梦幻和理想色彩的词,其核心内容除了描写农事活动与农村风情,更多地含有文人的精神家园的意思。然而,如给它换个名称为“农村”或“乡村”,其内涵即刻让人想起剥削、贫穷与苦难。诗世界中的“田园”与“乡村”是不对等的,它们是一个真实世界的两面,视作者需要而出现在不同场合,成为其“形象代言人”。
“田园”侧重于创作主体的心灵与审美感受,自陶渊明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文人的精神归宿与借以建构自由人格的家园。而“农村”或“乡村”则侧重于创作主体对自身劳动或对农民命运的观察和思考,诗人笔下真实的农村无不是饱浸着血泪的悲惨世界的代表。当“田园”出现在文学的视域中,作者往往在审美中观赏其所处世界,所重视的是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相处,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当“农村”展现在文学的画廊,作者大多数仍是旁观者,而以劳动为生存方式并饱受剥削压迫的农民,才是其中主体,这里既有有声的控诉,也有无声的揭露,主体与外界的相处是对立的,劳动者的劳动既不能获得生存物资也不能获得快乐和自由,当农民“血指流丹鬼质枯”(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之十一)[5]375时,更无从奢谈尊严与人格。
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认为:田园是文人虚构的家园,或否定其存在,或者说田园是对苦难农村的美化和粉饰。因为,田园的美好是文人对农村种种单纯生活的提炼,这是一杯源自现实而又超于现实的“纯净水”。农村的确存在着“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的恬静画面,与“桃杏满村春似锦”(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其三)[5]372蝶燕纷飞的优美风光;也的确存在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其七)[5]373男耕女织的和谐格局与“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的淳朴人性,有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归园田居》其三)的诗意劳动。但诗人笔下,形同地狱的悲惨画面也比比皆是。且看清道光年间鲁一同的一组哀叹民不聊生的画卷,组诗共五首,小序云:“饥沴洊叠,疮痏日甚,闻见之际,愍焉伤怀。爰次其事,命为《荒年谣》。事皆征实,言通里俗,敢云言之无罪,然所陈者十之二三而已。”[6]392诗云:
卖耕牛,耕牛鸣何哀!……牛不能言但呜咽,屠人磨刀向牛说:有田可耕汝当活,农夫死尽汝命绝。旁观老子方幅巾,戒人食牛人怒嗔:不见前村人食人!(其一《卖耕牛》)
拾遗骸,遗骸满路旁。犬饕乌啄皮肉碎,血染草赤天雨霜。北风吹走僵尸僵,欲行不行丑且尪。今日残魂身上布,明日谁家衣上絮?行人见惯去不顾,髑髅生齿横当路。(其二《拾遗骸》)
缚孤儿,孤儿缚急啼声悲!主人出门呵阿母,阿母垂涕洟:已经三日不得食,安用以子殉母为?不如弃儿去,或有人怜取。主人闻言泪如雨:家中亦有三龄女,前日弃去无处所。(其三《缚孤儿》)
上选三诗,写到了封建社会凶年农村可能发生的几乎所有最典型的事情。为了活命,农民连最宝贵的耕牛都卖掉和屠杀,而更可怕的是,人吃人的事情一直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中!此外,那许多因饿死而尸横遍野,因饥饿而卖儿弃女,因无柴而拆屋当柴(见其四《撤屋作薪》),因无以为家而被迫背井离乡的农民们,我们真的也忍不住要为他们掩面悲泣了!这种灾荒饥年,历朝历代都无法断迹:“南走五日道路断,县官驱人如驱蝇。同去十人九人死,黄河东流卷哭声。”[6]395逃难的农民如同苍蝇一样被官吏厌恶和驱赶,可造成这些悲剧的正是贪婪无耻残酷压榨百姓的封建官府本身!诗人虽没有正面指责统治者和剥削阶级,但饱含血泪的画面中已经填满了义愤和悲悯之情,不仅让后人切实了解到农民生存的苦难真相,也对造成这种种悲剧的根源——罪恶的剥削制度产生深刻的认识。
在了解了农村的悲惨真相后,再把它与美好的“田园”相联系,就显得很牵强。然而,“田园”的诗意确也存在,特别是,它往往关系到一些隐居或被迫退隐田园的诗人的生存态度。因此,笔者认为,在诗歌的世界里,田园与乡村是两种不同的写作取材范畴,它们各自反射出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文人心态。以往的文学史及相关论文,对这两种不同的选材范畴常混为一谈并缺乏深入的研究,其实,是对它们的内涵没有进行明显区分和深入思考。
三、农村与田园的对立:文人心态的矛盾表现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农村与田园所描绘的画面常呈现出鲜明的对立,它们仿佛是一悲一乐的二极世界。即使同一诗人笔下,也常常呈现出二者的对立,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文人心态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一方面身处农村贫穷世界,饥寒交迫,叹老悲贫;一方面儒道释作为早已存在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又能从各方位给予诗人思想上的解脱,使他们把自己安贫乐道、超然物外的心态赋予农村,使农村田园化、诗意化、人格化,显得和谐淡泊又充满生机。这种文人心态的矛盾表现,从陶渊明起就代有传人,如陆游、范成大等著名诗人。
陶渊明的诗,其实就已存在着农村与田园相对立的情况。最令人心酸的莫过于《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7]102写诗人为了生存,不得已去一位善解人意并喜欢诗文的富友家讨要食物。那种饥饿犹疑、尴尬嗫嚅的情形,与他“采菊东篱下”之高人隐士的风范,无疑有着天壤之别。
晚年的陶渊明,常常无衣无食,度日如年,这一切都被写进了所谓“田园诗”。然而它们真正呈现的却是当时农民的生存状况与农村的凋敝面貌。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云:“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7]108袁行霈先生认为此诗作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作者69岁时。[7]110该诗讲述了诗人一家虽常年辛勤劳动,却连年遭受水旱风虫等各种自然灾害,以至于日子饥寒交迫,难以为继。然而对于导致诗人苦难遭遇的根源,仅仅归咎于“天”(自然灾害)显然不够,实际上农事凋敝的情况,与当时战乱不休的现实紧密相关。
如果把作者晚年这首诗与其中年所作诗相比,就会产生画面内容与效果相对立的印象。如作于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的《和郭主簿》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7]144诗人生动地描绘了家园环境与田居活动,一千多年后,那林木清阴、园圃菜蔬,与可爱的小孩,及诗人对于农村那颗始终真诚和葆有诗意的心灵,仍一一如在目前。人总是在矛盾中生存的,《饮酒》十六也是一首颇能表明陶渊明矛盾心态的诗歌:“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7]271真实的农村如此衰败贫困,诗人晚年的心灵经历了与所有普通农民一样的痛苦。一方面他写出了乡居生活的贫寒艰辛,一方面他也坚持着固穷守节的儒家操守,至死不移。
之后,许多诗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都曾在农村居住过,有的因年老致仕,更多人则是因为与当道不合而被迫退隐农村。如陆游与辛弃疾。其中,陆游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就表现了较突出的矛盾心态。晚年长期的乡居生涯,有时带给陆游的是一种宁静、喜悦、平和的心情,如嘉泰元年夏作于山阴的《过村舍》[8]2828。表现出农村风貌那种亘古不变的朴素与平淡。有时,农村则以其特有的勃勃生机感染和振奋着诗人,如嘉泰元年秋作于山阴的《鱼池将涸车水注之》[8]2837。诗写陆游和农夫们齐心协力注水于即将干涸的鱼池,画面充满活力和热情,不仅表现出作者受到陶渊明影响“吾爱吾庐”的精神,更传达了作者宽广仁爱、与民同乐的胸怀。然而,事实却是,同年的夏秋,陆游一家经常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正如其诗所云:“巷僻断非容驷路,肠枯那有蹴蔬羊。”(《闭户》)[8]2816—2817“水云深处小茅茨,雷动空肠惯忍饥。”(《朝饥示子聿》)[8]2804嘉泰年间(1201—1204年),陆游所作诗歌仅与悲叹生活贫穷直接相关的题目就有:《苦贫》、《穷居》、《苦贫戏作》、《穷老》、《贫甚戏作长句示邻曲》、《感贫》、《贫中自戏》,[8]这还不计陆游所写与农村相关的全部诗歌中自述其贫寒状况与悲悯农民贫困生活的诗歌数目。
四、农村与田园的统一:文人创作心态的调和
农村与田园作为两种有区别的创作范畴,虽然经常呈现出几乎对立的生存环境,然而二者经由文人创作心态的调和,也时常表现出一种统一的情意和画面,显示出在贫困艰难的农村生活中文人对自我思想的调整与开解。这种情况也始自陶渊明。请看其《有会而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7]306袁行霈先生赞同王瑶、逯钦立等的观点,认同此诗作于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是年天下大旱且蝗”[7]307。既知此诗的创作背景,便可想象诗人一家当时所遭遇的艰辛悲酸,也即诗中所道“老至更长饥”,一家大小暑天仍穿着寒衣,甚至经常期望有“善人”发善举。然而,陶渊明最终以儒家君子固穷的思想战胜了肉体上的痛苦,并以前代贤人兼贫者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使该诗所表达的农村生活中现实之苦难与精神之富足达到了统一。
其后,陆游在其描写农村困苦与田园牧歌的众多诗篇中也时常表现出这种“精神胜利法”。如乾道三年(1167年)作于山阴的《霜风》:“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岂惟饥邻索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身老啸歌悲永夜,家贫撑住过凶年。丈夫经此宁非福,破涕灯前一粲然。”[8]113家贫更逢灾荒年,诗人最终却“破涕一笑”自我安慰,认为“祸兮福所倚”,相信困难终将化为财富,使诗歌传达出强烈的乐观精神。《穷居》也鲜明地表现了诗人创作心态的调和:“阨穷心自乐,寂寞道常尊。老病频辞客,嬉游不出村。淖糜均列鼎,徒步当华轩。不但终吾世,犹堪遗子孙。”[8]2820诗人既穷又老病却不悲伤,反而“阨穷自乐”,甚至想让子孙们继续这种寂寞宁静的生活,因为心中有“道”可尊。其实,此“道”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资源,在陆游晚年贫苦的现实人生与富足的精神世界中发挥了作用。
儒家思想方面,诗人通过《读易》表达了对其中深奥思想的深入领悟:“乾坤要自吾身看,卧听鸡鸣起索衣。”[8]3011认为如王弼、何晏并未领悟到《易经》中的精微哲思,所谓“乾坤”首先就要以自身为观照对象,每个人自身就是一个运转不息的小宇宙,一切皆可通过勤劳获得。再如嘉泰四年夏写于山阴的《农事稍间有作》:“黄云压檐风日美,绿针插水雾雨蒙。年丰远近笑语乐,浦涨纵横舟楫通。东家筑室窗户绿,西舍迎妇花扇红。……客归我起何所作,孝经论语教儿童。教儿童,莫匆匆,愿汝日夜勤磨砻,乌巾白纻待至公!”[8]3324不仅描绘出丰年田园之乐,也表达了自己以儒家思想教育儿童,期望他们能勤奋读书最终获取功名。
晚年的陆游还受到道家与道教思想的较深影响。他不仅以此为对象写了一些诗,还专门建立了“道室”供自己炼丹修养,如《道室杂题》其一:“早访丹砂上岣嵝,晚提河派泝昆仑。阴符后出君无忽,三百奇文要细论。”[8]2842其三云:“山中有草名长生,丹砂可死金可成。服之刀圭齿发换,要看东封告太平。”[8]2843描写了诗人相信道教之长生不老的思想,并采药炼丹作为实践。在修炼方法上,陆游还效仿过道教的辟谷,竟说道:“不饮颜常丹,不食腹果然,金丹亦弃置,我是地行仙。”(《闲适》其二)[8]2859他甚至认为自己的长寿也与修习道术有关:“耄年犹健非无自,一卷旦经受郑君。”(《龟堂晨起》)[8]2841该诗嘉泰元年秋作于山阴,“郑君”指葛洪的老师郑隐,葛洪曾随其学习炼丹密术。
禅宗思想无疑也对晚年的陆游有一定影响。如“偶扶藜杖过傍村,却倚禅床坐小轩。”(《晚兴》)[8]2808“数点青灯经野市,一炉软火宿僧房。”(《法云僧房》)[8]3281《游山》四首提到村庄附近的僧寺与僧友;[8]3175《法云寺》、《冬初至法云》把山寺写得富于田园氛围[8]3223,3229,温馨而充满生机。嘉泰三年冬作于山阴的《庵中杂书》四首,更清楚地表明了禅宗思想对陆游农村生活的支持。[8]3232诗歌融庵寺环境与周围田园风物于一体,既简单回顾了诗人一生的经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期盼和抗金复国的理想,也坚定地表达了他把田园作为人生最终归宿的决心(“走遍世间无著处,闭门锄菜伴园丁”),表现出自己顺应自然躬耕自给的心态。当他为贫困烦恼不堪时,甚至想过从佛教思想中探寻根源:“此穷正坐清狂尔,莫向瞿昙问宿因。”(《苦贫》)[8]2814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杰出诗人,陆游的村居生活确实不同于普通的农父田夫,从他至死不忘抗金大事来看,其晚年的修炼道术和问道禅宗,应与其寻求精神解脱有关,这种心态看似消极实则比较复杂,应放到当时主和派当道抗战志士报国无门的特定背景下加以理解。
五、田园与农村成为“二极世界”的原因
(一)诗意的疏离与漠视——文人寻求精神归属的必然结果。“田园”与“农村”,作为不同的写作取材范畴,承载着文人不同的创作意图,于是似乎常呈现出对立的情形。虽然,这种情况通常为读者和学者所忽视,但确实有必要去探究二者成为“二极世界”的原因。农村与田园“本是同根生”,但由于诗人对理想与现实的不同选择,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分离的趋向。其首要的原因就是文人置身农村时,往往已成为颠簸仕途上的失败者,他们不仅需要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更期望把这个地方作为精神家园,这就是早已被陶渊明及其后来的阐释者理想化了的农村,也即田园。先入为主的对精神归属的寻求,使得文人们内心对于农村的苦难现实,必然会产生诗意的疏离与漠视,尽管他们有时也忍不住跳出来为农民喊一喊冤!
陆游和辛弃疾被迫赋闲农村时,精神上就把农村看成是与黑暗现实相对立的美好家园。如辛弃疾,不仅继陶渊明后在词中屡唱“归去来兮”,也像他一样由衷地喜爱着农村。如其《鹧鸪天·博山寺作》云:“不向长安路上行,却叫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10]144词人把田园作为“长安”也即风波仕途的对立存在,表达了自己即使无法实现复国志意,也要“宁作我”,至死坚持抗金主张。因此,在词人寻求人间温情与理解的心灵中,松竹花鸟便都成为他的兄弟朋友。实际上,这是词人在对昏庸朝廷深深失望后,继之对农村现实世界的有意地疏离与漠视。
(二)痛心的审视与反思——文人的美刺心态与人文关怀。“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古风》其一)[11]2历代文人虽然都有意把农村作为诗意的精神家园,但也有不少诗人清醒而痛心地审视与反思着真实的农村,从而在刻画和揭露农村悲惨真相的无数诗篇中,表现出文人历久弥新的自觉的美刺心态与人文关怀。如采菱,一般文人诗词中的风雅之事,却被范成大描绘成一个悲惨地狱的画面:“采菱辛苦似天刑,刺手朱殷鬼质青。”(《采菱户》)[5]290“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采菱,原来是这样一种如遭天刑的痛苦劳动,采菱户们个个双手血指斑斑,如同青面瘦鬼一样吓人。陆游晚年虽老病穷愁,却始终希望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其《老叹》云:“多病从来惯,虚名不足论。自怜余一念,犹欲济元元。”[8]2860诗人已习惯“多病”,也不奢求“虚名”,惟余一念就是救济百姓,真可谓赤子之心!因此有学者对陆游的农村诗大加赞赏,认为其农村诗中“流露出他一贯的爱国情绪和郁勃之气”,“大量的诗篇又向人们揭示了作者同情人民、热爱生活、崇尚淳朴的另一层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4]第三册189
(三)吃人的剥削制度。有的文人始终吟唱田园牧歌,有的文人却不失血性在描写农村的诗篇中直斥吃人的剥削制度。如范成大的一系列所谓田园诗:《催租行》刻画了一个厚颜无耻的乡官形象[5]30—31,《秋日田园杂兴》之九写农民的粮食被官府巧取豪夺后只能给孩子吃“糠核”[5]375,《冬日田园杂兴》之十讲述了一个与《催租行》相似的故事[5]376,《冬舂行》写农民们一年到头辛苦耕作,最后却不得不把全部粮食作为租税缴纳给官府,而家人只能靠吃糠填腹。他们甚至天真地叹息道“贫人一饱不可赊”,希望可以提前吃饱以后的饭。[5]409—410这些诗都反映了在罪恶的剥削制度下,农民被官府残酷压榨、苟延残喘的悲惨境遇。总之,封建时代的农村“官租私债纷如麻”(《冬舂行》),农民在重重压迫下始终在生死线上挣扎,基本还谈不上对农村环境的热爱和对农村风光的欣赏。关于范成大的这些“田园诗”,有学者这样评价:“他能对传统的‘田园诗’加以发展和改造。他的田园诗既不同于‘聊为垅亩民’的陶渊明,也不同于‘即此羡闲适’的王维,只写些自得其乐的归隐生活和优美宁静的农村风光。他能把中唐以来表现农民悲惨生活的新乐府诗的精神移植到田园诗中,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农家的景物、岁时、风俗、劳作、苦难、煎迫、奋斗等各种内容,尤其能写出上上下下各层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因而相对提高了田园诗的价值。”[4]第三册176显然,所谓对传统田园诗加以发展、改造,实际上即认为范成大这类诗歌已不能简单地归之为“田园诗”。笔者持相同意见。
(四)文人的不同心态与视角决定了诗词中田园与乡村的特定内涵。以上探讨了许多描写农村真实本相的所谓“田园诗”,同时,也不能否认农村确实有属于它自己的美好特质。但这种特质更多地表现于农村的自然景物与风土人情,而不是生存意义上的农村天地。在古典诗歌中,农村与田园之所以在审美、政治、伦理与教化诸意义上产生极大的差异,其实与文人在创作时的不同心态与不同视角也有着很大关系。
农村,是一个自古以来就见仁见智引起文人不断关注的天地,即便同一诗人面对农村,由于选材与构思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所作诗歌面貌和感受的不同。那些描写田园之美的诗章,大多产生于丰收之年与诗人物质无忧时期(至少也有最低保障),诗人自觉疏远政治斗争,心态比较平和淡泊,视野比较明朗分散,在取材上也就易于被一些美好特定的风物与民俗人情所吸引。如陆游的八首《秋日杂咏》[8]2873,就是一组描绘秋日绍兴田园水乡的绝美画卷。与此相反,诗人们置身农村时也写下大量血泪斑斑发人深省的诗歌。这些诗歌大都产生于政治腐败的黑暗时期,加上各种自然灾害或战争,农村几乎成为人间地狱!这时,诗人往往主动关心时事政治,心态比较激愤不平,视野比较阴郁集中,选材易于倾向那些关系生死存亡的事情,如农民们因极度饥饿而造成的食人、杀耕牛、卖儿鬻女等人间惨剧,最后仍免不了流亡四方和饿尸遍野。对此,更多诗人把矛头对准官府,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的血腥罪恶,而企图唤醒统治者的良知。笔者认为,对于这样写农村的诗歌,再用早已有美化之嫌的“田园”一词来冠名就不太合适了。比如“吃人”的历史,诗歌中也有许多明确的记载,如白居易《轻肥》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再如元代无名氏[正宫]《醉太平》:“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12]447这些都是“吃人”的历史在诗歌中活生生的表达。至于饿殍无人收尸、农家卖儿鬻女,更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人,在其生命历程和诗歌之旅中大都关注过农村,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出自农村。应该说,在诗歌世界中看似对立的田园与农村,实际上一直不可分割。只是由于文人的不同创作心态,使它们分别成为中国文人永远的归宿与关怀。自古至今,农村真正的主人是农民。文人们大都是这里的匆匆过客,或是在城市政治生涯中受到伤害或者厌倦了仕途的隐士。如果说带有桃源意味的田园是失意文人们永远的精神归宿,那么,现实中的农村就成为文人永远的关怀所在。虽然,劳动是高尚的,但在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下,农民从没有通过它获得财富、自由和人格独立。对此,文人毋庸置疑很清楚,无论他们出身于农家,还是地主阶层和官僚阶层。这也是大多数文人宁愿在宦海挣扎也无法真正退隐农村的原因。于是,“田园将芜胡不归”成为文人们对自我灵魂永远的追问和拷问!与此同时,文人们也就更深切地关怀着这个养育着整座国家的大家园,把农村这个最朴实最艰辛最贫穷的世界永远地烙记在文学(诗歌)的时空中。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郭兴良,等.中国古代文学(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 钱仲联,钱学增选注.清诗精华录[M].济南:齐鲁书社,1987.
[7]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8] (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全八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 王达津选注.王维孟浩然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 (宋)辛弃疾著,徐汉明编.新校编辛弃疾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11] (唐)李绅著,卢燕平校注.李绅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 赵义山选注.元曲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