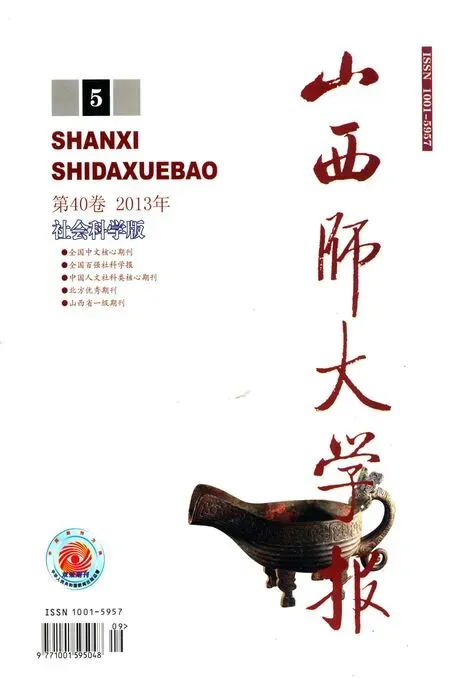“历史内化”视野中的诸子学新探
高 宏 洲
(山西大学 文学院, 太原 030006)
诸子学研究汗牛充栋,且时有质疑之声。刘士林在《先验批判》中说:“对于先秦诸子来说,他们写作和游说的目的,根本就是与当代人所谓的审美需要无关,因此古代各种文本主要是一种政治文本。他们在汪洋恣肆和才华横溢的表象背后,充满的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功利性追求。我曾指出,先秦显学中的儒、道、墨三家,之所以激烈地相互进行思想斗争,主要是他们分别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理想。”[1]45—46同时,他认为当代庄子研究中的两种主流倾向玄学化和美学化是站不住脚的。刘氏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即原始儒、墨、道的经典文本究竟是政治文本还是美学或文学文本?笔者希望通过提出“历史内化”概念为诸子学研究提供一个新视野,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澄清。
笔者认为诸子学是“历史内化”的产物主要出于以下考虑:诸子学是如何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以往历史经验扮演了什么角色?诸子学具有什么精神品格?这些精神品格产生了哪些影响?其影响与诸子学固有精神品格是否一致?笔者认为,历史在诸子学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的角色,但诸子学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再现,而是诸子根据现实需求对历史进行了丰富的想象和逻辑的推演。诸子学具有相关但不相同的两种品格,即历史品格和理想品格。历史品格主要指历史在诸子学形成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诸子思考问题凭借的思想资源主要是记载古代历史的“六经”,诸子理想中的圣王都有历史的原型。理想品格主要指诸子学虽然以历史记载为思想资源,但诸子是带着无序社会对有序社会的缅怀和追认进行思考的,其思想中的历史具有诗化特征,理想中的圣王不等于历史上的君王,渗透了诸子的价值认同。
一、“历史内化”的现实可能性
《庄子·天下》叙述诸子兴起的历史语境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2]983—984《汉书·艺文志》也有类似论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3]166—167虽然庄子和班固对诸子的态度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春秋诸侯力争是诸子兴起的历史语境。需要注意的是,庄子和班固的判断都有一个理论预设即王道未衰之前道术是完整的。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给出详尽解释。钱穆《国学概论》引用章学诚和龚自珍的话,说明原因在于王道未衰之前“治教未分,官师合一”[4]29。就是说春秋以前,治官和教师是统一的。道是圣王(圣即王,王即圣)治理天下的垄断工具,师儒学士都是根据圣王的言行履行自己的职能。韩非对上古时期圣王之所以能够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做过解释,他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5]442韩非虽是针对儒道宣扬的禅让制不合时宜而言的,却无意中道出了古代圣人所以王、所以让的理由。他注意到在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以及圣人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文中提到的有巢氏、燧人氏、鲧、禹、汤、武等都为人类的发展繁衍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就是说在当时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有历史选择的必然性,“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也”。
但春秋诸侯的力争破坏了这一传统,变成了“政教相离,官师相分”,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天子式微,诸侯凭借政治实力获得了现实统治权,但他们不悦学,不拥有使统治合法化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士人虽获得了话语权,但缺乏落实话语权的政治基础。而对于一个合法的政权来说两者就像一辆马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中庸》“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就表达了这个意思。最终开启了诸侯的“有位无德”和士人的“有德无位”的长期博弈。
二、“历史内化”的途径
特定的政治环境为诸子提供了“历史内化” 的广阔空间,那么诸子是如何进行“历史内化”的呢?概言之,主要通过“述而不作”和“学而思”两种方式。
首先谈述而不作。如前所述,政教未分时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只有“有德有位”的圣人才能制礼作乐。但春秋诸侯的力争导致“有德无位”和“有位无德”新的社会格局的出现。二者间的区别以周公和孔子最为典型,章学诚对此有过精辟论述,他说:“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于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6]119—123章氏认为周公集古代“治统”之大成,孔子集教化之大成,造成他们之间差异的原因是“时会使然”。但章氏认为这并不影响孔子的伟大,孔子的伟大在于他“学周公而已矣”。周公的成就在于实践制礼作乐,孔子的成就在于绍述周公制礼作乐的精神。孔子为什么不制礼作乐呢,是孔子谦虚吗?不是,因为孔子“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6]131。其实,孔子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认识。《孟子·公孙丑》记载:“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7]63由此可见,孔子是中国思想的转捩点。孔子之前只有现实的王才能制礼作乐,孔子之后,王不一定圣,圣不一定王。王攫取了现实政权,圣主要阐释先王的精神,变为汉人所谓的“素王”。孔子虽然“述而不作”,但并不意味孔子没有思想创新,他主要是在精神上继承圣人思想的。《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儒、墨、道三家虽然对圣王之道的认识差异很大,但都秉承了“述而不作”的言说策略,在“述”中表达自己的思想。
其次谈学而思。学习与思考并重是诸子“历史内化”的另一途径。诸子是非常善于学习和思考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十室之邑必有忠恕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等。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庄子说“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等。
诸子如此重视学习和思考,那么他们学习和思考什么呢?简言之,诸子主要学习寄存先王之道的“六经”,思考如何用其中的智慧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庄子·天下》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2]983—984庄子没有把“六经”视为儒家的专利,视为天下共同的思想资源。章学诚对诸子与六经之间的关系有过深刻见解,他说“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理由是“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6]60。但是章氏对诸子学并未完全肯定。他说:“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于制度。彼时从事于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而“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其失而为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则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敝,则极思而未习于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6]150—151。可见,章氏是从古人官师未分容易学习,其学信而有征来批评诸子之学“未习于事”、“思之过”的。章氏的这一批评不够公允,他是带着对晚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成见得出这一结论的。如果从诸子学兴起的历史语境来看,诸子“徒于思而不学”正是诸子重“思”的精神所在。其实,诸子也非不重视“学”,只是诸子之学与之前的王官之学存在明显不同。王官之学主要学习各种具体的技能,诸子之学注重学习圣王治理天下的智慧。这一转变是春秋特殊的历史境遇促成的,王纲解纽使原有的官学、乡校等王权教育失去了从“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的功能[8]146,导致知识的下移和士人阶层的出现。而诸侯力争的现实也逼迫士人思考导致社会混乱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由此可见,诸子主要学习记载古人政教典章的“六经”,学习的目的不是熟悉具体的职事,而是思考先王是如何治理治世的。由于诸子对现实的感受不同,所以他们归因社会动乱的原因也不同,他们开出治理社会的药方也迥异。儒家认为天下无道的原因是仁、义、礼、智、信等圣人品格的沦丧,所以呼唤仁、义、礼、智、信等圣贤品格;道家认为是统治者欲望的过度膨胀造成的,因此要“去欲”、“无为”;墨家认为是统治者不能尚贤、节葬、兼爱造成的,因此要尚贤、节葬、兼爱、非乐。
三、“历史内化”的结果:以道为资周游列国
诸子通过“述而不作”、“学而思”完成了“历史内化”,将历史上圣王的政治智慧转化成他们对道的认识,对道的认识成为他们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诸子对圣王智慧的“历史内化”集中体现在他们对理想中的先王、圣人、真人、至人的言说上。他们言说中的先王、圣人、真人、至人都有现实的隐喻性,或者说他们言说的潜在对象就是现实的君王或诸侯,学界对这一点重视得还不够。诸子虽然认为他们掌握了先王治理社会的智慧,但“有德无位”的现实处境不能实现圣王的价值。怎么办呢?他们根据对现实社会的不同认识采取不同的“介入”策略。儒家采取“待价而沽”,“学而优则仕”,“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策略;墨家采取的策略是树立以身作则的“自苦”榜样,如夏禹、商汤等;道家采取“无为”、“无欲”、“自然”的内在超越策略。
尽管诸子对“道”的认识不同,但他们都想用自己的道“格君心之非”。“格君心之非”虽然是孟子之言,但用它来概括其他诸子也未尝不确。诸子认为实现“道”的最好方式是作帝王的老师,于是他们就周游列国寻找可栖之良木,在遭遇坎坷后退而求其次选择授徒讲学和著书立说。在现实中要“格君子之非”非常不易,结果造成“道”与“势”的长期博弈。史书上引以为美谈的稷下学宫等养士之风与此不无关系。当时士气之高扬从《孔丛子》记载曾子与子思的对话中可见一斑:“曾子谓子思曰:‘昔者吾从夫子巡守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世异,人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凶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各时也。’”[4]43正是特定的历史语境造成诸子自由翱翔的精神气质和磅礴宏大的思想规模。
由于现实中“势”高于“道”,诸子学经常沦为统治之术。“势”对“道”的异化遮蔽了诸子学的理想品格。当然,这只是就儒、墨、道的理想境界而言的,以儒、墨、道之学行自我之私利者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此外,诸子多“穷”少“达”的遭遇开出了意外奇葩,如儒家的“孔颜乐处”和道家的“逍遥自适”,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四、如何评价“历史内化”的诸子学
《庄子·天下》批评诸子“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与庄子不同,笔者认为正是“一察之见”成就了诸子。诸子通过“一察”透视社会弊端,使其在某一方面把握了道的真谛。他们对道的理解虽有片面性,但片面的深刻使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握,相互争鸣,游走于诸侯列国之间。他们的“一察之见”虽都有过往历史的经验,但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而是进行了历史的推演和思想的放大。韩非对此早有认识,《五蠹》云:“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5]442韩非虽不能理解诸子“美先王”的良苦用心,但他发现诸子“美先王”的事实却不为无见。
诸子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尽管经常发生变异,但诸子对先王智慧的“历史内化”使士人阶层获得了可以和王权相抗衡的话语权,拥有了制衡君主的思想武器。诸子欣羡的“三代之治”成为许多君主为政的榜样,如汉武帝、唐太宗、宋神宗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其次,复古思维模式的确立。中国政治上、文学上的复古之声绵延不断,而源头却是诸子。复古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通过对“古”的理想化来批判现实。最后,诸子学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诸子之前由于政教合一文治典教都出自君王,未尝有专门著述之事。诸子却经常用故事或寓言表达他们对道的认识和体悟,开了后世专门著述的先河。士人要游说诸侯必须文饰其辞,诸子在文辞之夸饰和思辨之精湛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影响文学深且巨。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6]60—63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历史内化”审视诸子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第一,虽前人对诸子学的历史品格和理想品格多有论及,但大多是站在今人的立场阐释古人,和古人有一定的“隔”。比如有学者将孔子思想概括为民本主义,因孔子明确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从“历史内化”的角度来看,孔子其实是基于礼崩乐坏的现实感受来建构理想社会的。其立论逻辑是如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就能和谐大治,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受知识资源的限制诸子学难免有局限,这是不必为贤者讳的。诸子只是根据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明白了这点就能将诸子学历史语境化,而不是像传统儒生那样“宗经”稽古,自神其道。李贽《童心说》云:“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9]229—231李贽的批判可谓切中肯綮。
第二,对历史品格和理想品格的区分有利于合理评价诸子思想和传统政治的复杂关系。由于未作区分,过去的许多学者将两者视为同一个东西,贬之为吃人的礼教、专制的帮凶。其实两者并不相同。历史品格决定了诸子学有为统治者服务的价值取向,统治者也经常利用诸子学为其统治张目。但理想品格告诉人们诸子学不是统治,统治是异化的结果。如汉武帝表面独尊儒术,实是王霸并用;程朱理学本是心性之学,最终变成吃人的礼教。笔者认为,造成异化的根源在于君主专制制度,而非诸子学的精神所愿。如此区分以后在对待古代遗产方面就能采取较理性的态度。古代的政治制度大多围绕“家天下”的君主专制统治创立的,对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不仅不会有帮助,还会受到它的纠缠。但是对待古代思想就不能如此简单,古代思想积淀了几千年来古人思考如何安顿社会、个体心灵的智慧,抛却其中的糟粕仍可以沾溉今人。这取决于今人如何对其进行“历史内化”,它们作为“历史流传物”应该受到尊重。而且诸子通过“历史内化”生产知识、焕发智慧的方式至今仍有启迪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实现古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第三,“历史内化”有助于解释诸子学究竟是政治文本还是文学文本。毫无疑问,诸子学最初都是为完善现实政治而创作的,在当时都是政治文本。但由于它们具有浓厚的理想品格,如《庄子》为了说明“道”的特性经常采用文学性很强的寓言、重言、卮言,有人把它当文学文本阅读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明白了这一点,在如何对待诸子文本上可以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即看研究者是在什么角度讲《庄子》和《论语》。如果研究者讲历史上的《庄子》和《论语》,必须重视其政治品格;讲阅读者视野中的《庄子》和《论语》就要重视其丰富性。两者是不同的,必须区别对待。其实,古人早有将“经”当文学文本阅读的先例[10]。
第四,“历史内化”有利于解释何以中国历史有诗化的特征,中国的叙事诗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以诗证史”的传统根深蒂固等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这不是古人学科意识淡漠所致,而是古人的用心根本不在于纯粹知识的获得,而是借历史之兴衰成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看法。这一点或许与古代士人的身份有关,他们往往一身兼政治家、文学家、学者等多种身份。
[1] 刘士林.先验批判[M].上海:三联书店,2001.
[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 顾炎武.日知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4.
[9] 蔡景康.明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0] 龚鹏程.六经皆文:经学史/文学史[M].台北:学生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