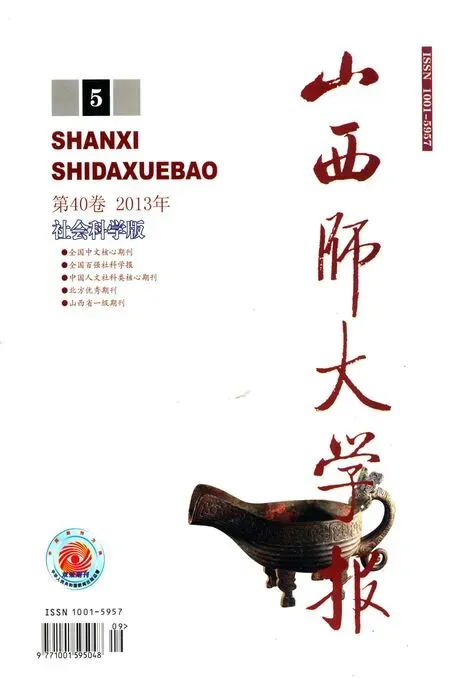托马斯·莫尔的医学伦理思想
刘 月 树
(天津中医药大学 人文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3)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是16世纪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其所著《乌托邦》一书首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先河。[1]88莫尔在书中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岛国,全面描述了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图景。其中,还阐述了他的医学伦理思想,主要涉及健康观念、医学观念、疾病预防和婚姻健康伦理、死亡哲学和安乐死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一、健康观念
莫尔认为构成人类的全部或主要幸福的是快乐。但是,他反对每一种快乐都可以构成幸福,只有正当高尚的快乐才是幸福的基础。对于快乐的内涵,莫尔认为是人们自然而然喜爱的身或心的活动以及状态。据此,莫尔进一步区分了精神的快乐和身体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是指“属于精神的,他们认为有理智以及从默察真理所获得的喜悦。此外,还有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惬意回忆以及对未来幸福的期望”。[2]78而身体的快乐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人能充分感觉到的鲜明的愉快,如饮食、性,以及音乐带来的感官愉悦等;第二类是指身体的安静与和谐。
对于身体快乐的第二种类型,莫尔明确指出是身体的健康:“这其实是指每人享有免于疾病侵扰的健康。苦痛不入的健康本身即是快乐之源,虽然并无从外部所引起的快乐。比起饥渴者强烈口腹之欲,这种快乐诚然不那么明显地被感觉到,可是许多人承认健康才是最大的快乐。几乎全部乌托邦人把健康看成最大的快乐,看成所有快乐的基础和根本。只要有健康,生活就安静舒适。相反,失去健康,绝对谈不上有快乐的余地。在没有健康的情况下而不觉得痛苦,乌托邦人认为这是麻木不仁而不是快乐。”[2]79莫尔将一个人健康时的身体安逸视作最大的快乐,尽管这种状态不能使人感受到鲜明的愉快,但确实是“所有快乐的基础和根本”。
当然,托马斯·莫尔不是一个感性快乐主义者,他认为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应同时具有精神的和身体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是第一位的,而在身体的快乐中,健康又是最重要的。“总而言之,乌托邦人特别不肯放过精神的快乐,以其为一切快乐中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他们认为主要的精神之快乐来自德行的实践以及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至于身体的快乐,他们首推健康。饮食可口,以及诸如此类的享受,他们喜欢,然而只是为了促进健康。这种享受本身没有令人向往之处,而仅是由于其能抵抗疾病的侵袭。”[2]80由此可见,莫尔所认为的快乐除了精神的快乐之外,身体的快乐应首推健康,其他可以带来感官快感的事物都要为健康服务。
为了维护身体的健康,应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在莫尔看来,美观、矫健、轻捷等身体特征是大自然的恩赐,需要加以珍视。那种为了博得虚幻的名声或为了增强自己的忍受能力而故意苛待自己的行为是没有价值的。“鄙视美观,损害矫健的体力,变轻捷为迟钝,因节食而伤生,糟蹋自己的健康,以及摒绝大自然的其他一切恩典”[2]81的行为是疯狂的,是对自己的残忍和对自然的忘恩负义。托马斯5莫尔反对一切毁坏健康的行为,但排除了为了公众的利益而牺牲健康的状况:“除非一个人忽视自己的这一切利益以便更热心地为别人或公众谋取快乐,期望由于这样的牺牲,上帝会给他更大的快乐。”[2]81莫尔的健康观念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想特征,一反基督教伦理轻视身体的倾向,将人的身体健康赋予崇高的价值加以肯定,这是西方医学伦理思想发展历程中“健康观念”在近代的一个重要转变。
二、医学观念
在文艺复兴时期,医学技术的治疗效果有限,医疗市场混乱,开业医生很少或没有专门性地组织,任何人都可以行医。[3]531这直接导致了医疗市场的无序和医生的道德水平低下。因此,当时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对医学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如彼特拉克、伊拉斯谟、拉伯雷等都有相关的文献存世。但是在《乌托邦》中,托马斯·莫尔却大力赞美了医学:“虽然在世界各国中,乌托邦对医药的需要最少,但乌托邦人最尊重医药,因为他们认为医学是最高深和最切于实用的学问的一种。”[2]85
另外,莫尔在医学研究问题上也持积极的态度,他将医学探索视为是对上帝赋予人类求知天性的积极运用,“当他们借助于这门学问对自然的秘密进行探索时,他们觉得不仅工作使他们十分愉快,而且自然的创造者和制造者还给他们以极大的称许。他们设想,这个创造者和制造者如其他所有的工匠一样,陈出宇宙的可见的结构,供人类观察,单独赋予人类以鉴赏这个神妙事物的本领。由于此,这个创造者和制造者所特别喜爱的,是留心认真观察并赞赏他的成品的那种人,而不是另一种人,像畜生般冥顽不灵,在这样伟大庄严的景象前显示出愚昧和迟钝。”[2]85在这段论述中,莫尔赞美了医学研究者的工作,肯定了人类在探索自然过程中的勇气和力量。
在《乌托邦》中,莫尔还谈到了他对于医院医学的设想。医院作为专门的医疗机构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初具雏形,当时主要是作为军事医疗或贫病者的救济机构存在的。中世纪时期医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直到16世纪还不具备现代医院的模式和功能,主要还是作为救济机构的性质存在的,而且条件普遍比较恶劣。[4]直到18、19世纪,近代医院才开始逐步形成。
在《乌托邦》中,托马斯·莫尔已经将医院设想成一个重要的公立的社会职能机构,并且有着良好的建筑环境和合理化的管理。“在公医院治疗的病人首先得到特殊照顾。在每一个城的范围内,邻近城郊,有四所公医院,都是十分宽大,宛如四个小镇。其目的有二:第一,不管病人有好多,不至于挤在一起而造成不舒适;其次,患传染病的人可以尽量隔离。这些医院设备完善,凡足以促进健康的用具无不应有尽有。而且,治疗认真而体贴入微,高明医生亲自不断护理,所以病人被送进医院虽不带强迫性,全城居民一染上病无不乐于离家住院护理。”[2]62—63在这段论述中,莫尔首先规定了医院的公共性质。医院的公共性质是与其政治思想相联系的,他反对私有制度,而医院的公有性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健康利益。他还谈到医院应当合理布局,设立在城郊结合部,并且有足够的空间,其目的是为了病人的舒适和疾病的防疫隔离,这些设想显示出莫尔的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和公共卫生意识。在医院管理方面,莫尔要求除了在物的方面完备之外,医生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要做到认真、体贴的治疗和护理。除此以外,文中还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医学伦理观点,即病人被送进医院是基于患者的意愿,不带有强迫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医学中的患者权利思想。
三、疾病预防和婚姻健康伦理
在《乌托邦》中,莫尔还提出了预防的医学观念,认为避免生病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专注于寻求治疗。“一个明智的人力求避免生病,而不是病后求医;总是使痛苦不生,而不是寻求减轻痛苦的药。同样,与其享乐于前,后果难堪,何如不要这种享乐。”[2]80这种疾病预防观念是他的快乐主义伦理思想的具体体现,生病之前维护健康是减少痛苦的最好方法,也就是说用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快乐。而一旦享乐有损于健康,那么宁可不要这种享乐,也要维护健康的快乐。
与之相关,莫尔还提出了婚姻的健康伦理问题。他设想在相亲的过程中男女要裸体相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看清对方是否有不能接受的隐疾,因为这事关婚姻的幸福。如果对于女方的评价只在脸庞的范围内,而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被衣服包裹,到了婚后再对其身体有不满意的地方,将很难融洽相处。莫尔认为,婚姻与身体和性有着重要的关系,外在的身体之美会促进婚姻的和谐,反之就会引发婚姻的不幸,“即使明智的男人,在婚姻问题上,也会认为美貌大大地增加了美德。毫无疑问,衣服可能遮盖住丑恶的残疾,以致丈夫对妻子产生心理上的反感。而这时躯体上分居在法律上又不许可了,如果这种残疾是婚后偶然引起的,一个男人只有自认晦气。然而法律于婚前应该防止他被骗上当。”[2]88—89莫尔这样说是由于他设想在“乌托邦”中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男子在婚后的选择余地受到了很大限制。另外,如果妻子单纯只是罹患疾病而没有其他不正确的行为,丈夫将其遗弃是残酷不仁的,不可接受的。这段话虽然带有明显的男权主义色彩,但他对婚姻与快乐的关注是值得肯定的。
莫尔的婚姻健康观念在那个时期是很独特的,并且对今天的婚前体检制度依然具有借鉴价值。此外,莫尔的这一思想还激发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有关思想。培根在《新大西岛》一书中一样强调要在婚前进行身体的检查,但与莫尔的区别在于规定并非二人裸体相见,而是要在专门的洗浴池中由相亲者的朋友来相互验证,认为这样更加文明。[5]26
四、死亡哲学与安乐死
在死亡问题上,莫尔反对贪图生命的想法和做法,认为安然地接受死亡才是一种正确的观念。他在书中描述了乌托邦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几乎全部乌托邦人十分肯定并深信,人可以达到无穷的天堂之乐。他们对病者表示悲痛,但对死者无所惋惜,除非是极端贪生而不愿离开这个尘世的死者。一个人临死而有如此的表现,他们认为不祥,预示他的灵魂无望,抱有内疚,对即将到临的处罚怀有默默的预感,因而害怕死去。他们又觉得一个人在受到上帝召唤时不是欣然迅速从命而是勉强不得不去,上帝是不会乐意他的到来的。他们如看到一个人这样死去,不禁为之毛骨悚然,因而在忧郁的沉默中将死者送到墓地上,祈求上帝怜悯死者而且宽恕其罪愆,然后把尸体埋掉。”[2]107与上述相反,一个高兴接受死亡的人在乌托邦中被认为是值得赞美的,人们对于安然于死亡的人并不表示哀悼,而是在歌唱声中为其举行葬礼,怀着崇敬的心理为死者举火焚尸,立碑纪念他们的优秀品质,同时还不断回忆并赞美这些人临死时怡然自得的态度。
莫尔在《乌托邦》中所阐述的死亡哲学思想,其核心是主张乐观地对待死亡,认为天堂之乐和对于上帝召唤的回应是一个人安然赴死的力量所在。这显示出莫尔在这一问题上浓厚的基督教思想色彩。
与上述死亡哲学相关,莫尔还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安乐死思想。在“关于奴隶”等的一章中,莫尔这样写道:“我上面说过,乌托邦人对病人热心照料,不令他们缺乏任何能恢复健康的东西,医药饮食,无不供应周到。对患不治之症的病者,他们给以安慰,促膝交谈,力图减轻其痛苦。如果某一病症不但无从治好,而且痛苦缠绵,那么,教士和官长都来劝告病人,他现在既已不能履行人生的任何义务,拖累自己,烦扰别人,是早就应该死去而活过了期限的,所以他应决心不让这种瘟病拖下去,不要在死亡前犹豫,生命对他只是折磨,而应该怀着热切的希望,从苦难的今生求得解脱,如同逃出监禁和拷刑一般。或者他可以自愿地容许别人解脱他。在这样的道路上他有所行动将是明智的,因为他的死不是断送了享受,而是结束掉痛苦。并且他这样行动将是服从教士的忠告,而教士是上帝意志的解释者,所以那是虔诚圣洁的行动。”[2]87
这段论述首先谈到了医学的道德责任问题,即要做到对病人的热心照料,即使是不治之症者也要给予细致的关怀,减轻其痛苦。但是,莫尔认为这种道德责任不是绝对的,当疾病无法治愈导致病人只能“拖累自己,烦扰别人”的时候,就要考虑病人的生命价值问题。在莫尔之前,关于安乐死的生命观问题主要有两大思想流派:一是柏拉图的生命价值学说,一是基督教的生命神圣理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可以为了城邦的利益而牺牲严重残疾和患重病者的生命。[6]117,120而基督教思想对于安乐死却持反对的态度,因为“不可杀人”道德诫命是普遍的和绝对的。莫尔显然更倾向于柏拉图的观点,将生命的价值与社会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履行人生的任何义务,拖累自己,烦扰别人”是判断是否应实施安乐死的重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莫尔认为实施安乐死不能只考虑病人的社会价值,主张首先要考虑病人的自我价值问题,也即当病人在“痛苦缠绵”,“生命对他只是折磨”的情况下,实施安乐死才是正当的。而安乐死实施的主体,莫尔认为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人,即“他可以自愿地容许别人解脱他”。
莫尔还谈到了安乐死的实施方法、自愿性和程序问题。“听了上述的道理而接受劝告的人或是绝食而死,或是在睡眠中解脱而无死亡的感觉。但乌托邦人决不在这种病人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夺去他的生命,也绝不因此对他的护理有丝毫的松懈。他们相信,经过这样劝告的死是表示荣誉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未得教士及议事会同意而戕贼自己,就得不到火葬或土埋,而是不体面地曝尸沼泽中。”[2]87—88莫尔在这里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两种最佳的方法,即绝食而死或在睡眠中而死,也许莫尔认为这两种方式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最少。另外,莫尔还主张实施安乐死应当是自愿的,“决不在这种病人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夺去他的生命”,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于患者自主性的尊重。最后,实施安乐死要经过一个宗教的程序,也就是要得到“教士和议事会的同意”。
由上述可见,莫尔的安乐死思想是非常全面的,涉及安乐死问题的医学目的、生命观、实施的主体和方式、自愿原则、程序问题等各个方面,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大体不超出这一范围。这是近代安乐死思想的起源。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即莫尔的安乐死思想与他在现实中的信仰和做法是矛盾的。莫尔在现实中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严守宗教诫命,并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被处死前坚决拒绝自杀的刑罚。[7]22—23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乌托邦》中的论述就是他关于安乐死问题的全部观点。这种情况显示出莫尔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复杂性。
五、结语
托马斯·莫尔作为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其政治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学术界持久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是,《乌托邦》一书中的医学伦理思想却长时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是托马斯·莫尔研究的一个理论空白。不可否认,他的医学伦理思想不是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出现的,也不够系统和全面,只是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附属品,是他所设想的理想之国中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纵观《乌托邦》一书对于现实的反讽特质,可以看出莫尔对于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理想的医学伦理精神的向往。
在他的医学伦理思想中,无论是他的健康观念、医学观念、疾病预防与婚姻健康伦理,还是死亡哲学与安乐死思想,都洋溢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显示出对于人的理性精神和现实生活的肯定。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是托马斯·莫尔医学伦理思想的基石,贯彻在他的医学伦理思想的各个方面,这一观念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高建.西方政治思想史:第3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 (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下册)[M].周昌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王斌全,赵晓云.国外医院的产生与发展[J].护理研究,2007,(2).
[5] (英)弗·培根.新大西岛[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 Ian Dowbiggin.Concise History of Euthanasia: Life, Death, God, and Medicin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