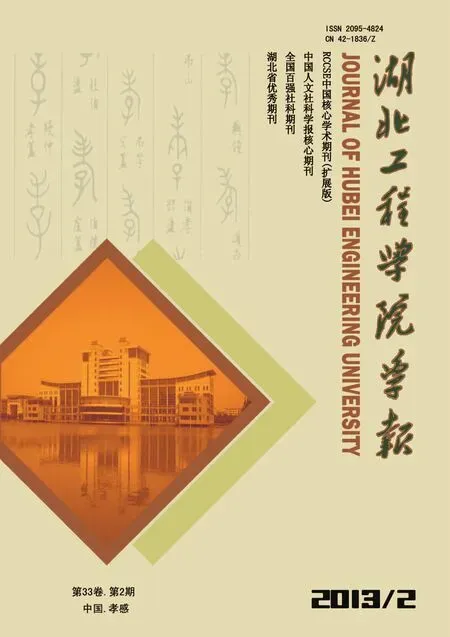关于处置、被动同形标记“给”和“把”的相关问题①
万 群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
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中出现了“给”兼表处置、被动的现象:
你给录音机搁的屋里头,这一家子都回来了,他不知道有录音机。/可能国际友人来,给他偷着照的。(北大电子语料库1982年北京话调查)
以江淮官话、湘语、赣语为主的南方方言中出现了“把”兼表处置、被动现象:
老鼠把米吃了(处置)/米把(到)老鼠吃了
面对这个现象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给”和“把”兼表处置、被动的来源和历史演变过程是什么?“把”兼表被动、处置的原因是一样的吗?“把”在一个语言系统中兼表被动、处置是不是同质现象?“把”和“给”兼用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二、“给”兼表处置、被动的原因与历史演变
1.“给”表处置、被动的历史表现。文献中[注]调查文献《全唐诗》、《游仙窟》、《霍小玉传》、《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朱子语类》、欧阳修作品、柳永词作、元代杂剧、散曲、元明话本、《西游记》、《金瓶梅》、《醒世恒言》、《老乞大谚解》、《儿女英雄传》等,得出大致历史顺序。表现的历史演变的大致顺序是:
(1)“给”表处置。元代以前动词“给”(见母缉韵(jǐ))“供给(使丰足)”义―元明动词“给”“给予”义,出现“给+N+V”,“把/被+N+给+VC”,介词“给”引进受益者―清代处置(到)―现代处置(给)―狭义处置式―致使义处置式。
(2)“给”表被动。元代以前动词“给”(见母缉韵(jǐ))“供给(使丰足)”义―元明动词“给”“给予”义,出现“给+N+V”,“把/被+N+给+VC”―清代至现代介词“给”引进施事表使役―表被动。
(3)最早出现“给”兼表处置、被动的文献。
《儿女英雄传》中最早出现两种可以两解的句子:
一是使役/被动:
[1]“还有十一二岁就给人家童养去的。”
一是受益/处置:
[2]“这准是三儿干的,咱们给他带到厨房里去。”
蒋绍愚[1]指出《儿女英雄传》中出现只能视为被动的句子:
[3]“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
我们看到其中还出现了表原因的“给”字被动句:
[4]“给他落了一韵,连个复试也没巴结上。”
对比“被”字句的演变历史,“给”字句表原因的来源,蒋绍愚、曹广顺[2]分析了开始于宋代的“被”字句表原因来源与发展,原来的句义是“主语被施事通过VP处置了一番”,因为隐含的主语和被动标记后的名词性成分所指完全相同,隐含主语遭受处置的含义消失,原因义被凸现出来。
《儿女英雄传》中也出现只能视为处置的句子:
[5]“张金凤便要去倒那盆子,十三妹道:‘那还倒他作甚么呀?给他放在盆架儿上罢。’”(儿女英雄传)
联系上下文,这一例只能是处置式。表达的是“处置到”,是广义处置式的一种。杨荣祥、郭浩瑜[3]指出:处置(到)比处置(给)的“控制度”低,从语义上看是N2经过N1的某种处置行为而位移到某个位置,N1本身不一定发生位移,并且认为处置(到)的出现是真正的处置式产生的契机。
“把/给+ N1+V(到)+ NL”, N1通过V这个动作,位移到NL这个地方,杨荣祥,郭浩瑜[3]指出这里的“把”的原义“握持”已经退化,控制义减弱。这是由连动式演变为处置式的途径。而“给”字式并没有经历这样的演变过程。
黎锦熙[4]指出,“‘将’和‘把’当初却都是‘手持而送进’之意的动词,渐渐地‘把’意义变虚了。”黎先生举例:
[6]“将是瓜车,来到还家。”(汉乐府·孤儿行)
[7]“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同上)
或者我们可以想,假如“将、把”含有“送进”义,处置(到)基于这样的语义发生重新分析,“送进”N1到NL,动作V是具体动作方式,那么动词“给”处在“送进”这个位置上正好一样语法化为处置(到)标记。我以为,“将”和“把”本义只有“握持”义,所谓“送进”之意,是语境赋予的。所以,“给”和“把”表处置经历不同的语法化过程。
(4)“给”表处置在现代北京话中的情况。
1)广义处置式:
[8]“你给录音机搁的屋里头,这一家子都回来了,他不知道有录音机。”(1982年北京话调查,来自北大电子语料库)
2)狭义处置式:
[9]“结果人家就给我们家就都封了,胡同儿也封上了。”(同上)
3)致使义处置式:
[10]“给我气的,我说:‘你不是不让我赔吗?’”(同上)
我们在早期文献中没有看到“给”字处置式有处置(给)的形式,现代北京话中也没有见到这种形式,老舍小说有:
[11]“玛力给果碟子递给大家”(二马)
但是没有出现“给+N1+给+N2”的形式。这是王健[5]否认这种形式是“给”表处置发生重新分析的句法环境的主要原因。而河南洛阳、开封方言中有这样的形式。所以林素娥[6]等认为这是“给”重新分析为处置标记的来源之一。
其实要解释现代北京话中没有“给+N1+给+N2”也不难,因为北京话中“把”字处置式是强势结构,表达“将物品N1转移给接受者N2”的时候很自然可以选择处置(给):“把那本书给我”,或者N1是无定的时候用双宾语:“给我一本书”。而根据张恒[7]的观点,开封话“给”表处置是强势结构,其具体来源问题还要在方言语法调查做得更深入的情况下再判断,我们暂且不论。
从清代开始“给”兼表处置、被动。 但是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共同语中,这两种用法都是弱势用法,朱景松[8]指出,北京话中“给”表处置已经较普遍,但是我们看到“把”字处置式和“被”字被动式仍是优先选择的强势形式。在有些北方方言中的表现和北京话不一样,“给”作处置或被动是优先选择的,例如张恒[7]指出的开封话,还有辽宁本溪话 。[注]我调查辽宁本溪“给”的用法,发现口语中“给”表处置、被动选用优先于“把”、“被”字句。这个现象处于文白竞争中,将来会发生怎样的状况不可知。
2.“给”兼表处置、被动的原因。
(1)从句法结构和语义角色关系角度分析。使役和被动之间的转化,蒋绍愚[1]已经论证得很充分,我们赞成他的观点,认为“给”基于相同的句法语义环境经由使役标记演变为被动标记。
朱德熙[9]最早从语法功能和功能的演变角度分析“给”的句法作用。朱先生认为我们通常可以变换为“把”字句处置式的“给”字句,例如:“我给电视机修好了”,来源于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名词在语义上是受事,而在形式上是与事。也就是说,“给”成为狭义处置式标记来源于受益标记“给”的重新分析。这个观点得到很多支持。张敏[10]通过制作汉语方言语义地图,也证实非持拿义动词虚化为处置标记一定经过作受益标记这一过程。
但是受益和处置之间的转变是基于什么样的语义基础呢?朱先生的解释只是从语义句法关系上说,处于介词后面的宾语位置本来是与事成分,但是却让受事成分占据了,所以这种实质上的受事在这个句法位置上的出现导致这个句子重新分析为处置式,“给”也就变成了处置标记。王健[5]认为当宾语位置上的论元关系无所谓受益受损,“给”就语法化为处置标记。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本来主要由有生名词充当的与事成分的位置会引进由无生名词充当的受事成分?蒋绍愚[1]所举“给气运使唤着”(儿女英雄传),“气运”是无生名词,这是从使役到被动的一个分界,不再有歧义。无生名词之所以能进入这个句法位置,可以是因为被赋予了人格特征。但是我们看上述的例[2],宾语“他”若是“三儿”则是受益者,宾语是“铜旋子”则是受事,但是受益/损者在认知上说一般应该是有生对象,《儿女英雄传》引进受益者的有130例,全是有生名词,如:“你就给我拴在这窗根儿底下。”在这个语境下赋予无生对象人格特征确实很牵强。
(2)从动词“给”的语义特征和认知的角度分析。
1)徐丹[11]、石毓智[12]从“给”的语义特征出发认为,“给”类动词实际上是“予/夺”动词或“给/取”动词,它们具有朝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兼用的语义基础。
2)石毓智[12]从认知角度出发认为,基于“给”有“取/与”两种语义特征,或者处于宾语位置上的成分施受语义角色的变化,人们出于不同的认知角度,选择不同的参照点,导致“给”语法化方向的不同。
3)江蓝生[13]从历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根据论元语义特征和汉语施受同辞的词法特征,认为“给予”义动词自古以来就能兼表使役、被动、处置,是“万能”成分,能兼用的原因是句中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施受关系的变化,施受关系可以变化是因为“非形态语言的汉语在词法上施受同辞这一本质特点”。
持以上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给”表处置、被动是直接从“给予”义动词演变而来,江蓝生[13]明确指出使役、受益等句式和被动、处置句之间没有发生学关系,只有历时上的先后不同。
从语义特征和认知角度的解释仍然不能排除动词“给”演变为使役标记再演变为被动标记,和“给予”义动词演变为受益标记再变为处置标记的可能性,这个角度的研究只能提供向两个方向演变的语义基础和认知基础,不能肯定演变途径的唯一性。
(3)尚待解决的问题。杨荣祥、郭浩瑜[3]认为广义、狭义、致使义处置式有不同的来源,产生的历时时期也不同:先秦广义处置式―唐代狭义处置式―唐代致使义处置式。林素娥[6]认为“给”字处置式也各有不同来源,“广义”(“给那本书给我”) 来源于“给予”义动词;“狭义”(“给电视机修好了”) 源于引进与事的介词;“致使义”(“当时给我气坏了”)源于“给”表致使的功能。
但是,在北京话和清代文献里我们都没有找到“给+N1+给+N2”形式,不能排除“给”表受益演变为表处置之后,依照“把”字处置式而产生的类推。河南方言里的“给”的问题也没有上溯到“把”和“给”历史关系上考察,也不能断定是不同来源的演变。
所以,我们遇到两个问题:一是与事所处的位置怎么能被受事成分占据,从而导致受益标记演变为处置标记?二是不同意义的“给”字处置式是各有来源还是发生过类推?这是目前我们还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把”兼表处置、被动的原因和历史演变
1.“把”兼表处置、被动现象。“把”作“给予”义动词,并兼作处置、被动标记,主要出现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淮官话区、湘语区、赣语区。这个语言现象,陈有恒[14]、左林霞[15]、黄晓雪[16]等都已经做过比较细致的描写。
我们以江淮官话区的湖北黄冈话为例,来看看“把”的用法。在黄冈话中“把老鼠吃了”的“把”有3种理解:动词“给予”义、处置标记、被动标记。
我们须探究清楚这种同形异义结构的历史层次,从而寻找兼用的原因。
2.动词“把”和处置标记“把”。动词“给予”义的“把”最早见于明代文献。先秦到元代常见的“给予”义动词是“与”,元代出现“给予”义的“给”。在使用“给予”义的“把”的文献里也兼用“给、与”。
“把”表处置从唐代已经开始普遍使用,这在文献中的表现是连贯的,我们调查的语料中,“持拿”义和处置标记,一直都可以并存:
[12]“不若娘子把伞自去。”(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13]“把这先生吊他一年。”(同上)
从文献中的表现来看,“把”虽然语法化为处置标记,但是它作为“持拿”义动词一直是普遍使用的。
3.“把”兼表处置、被动的历史演变。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把”表处置和表被动有不同的历史层次、历史来源。下面我们具体讨论“把”的“给予”义和被动用法的产生过程。
(1)“把”的“给予”义的来源。元明文献中“把”除了作处置标记,还有三种重要的语义句法表现,且与“把”表“给予”义有关:
1)动词“持拿”义:
[14]“你且把出来看。”(元话本·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15]“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来把与娘看,娘道:‘休把出去罢!原先你父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休了。’”(元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2)“把”+V:
[16]“这二十两碎银,把做赏人杂用。”(明话本·玉堂春落难逢夫)
[17]“见武松把将酒食来。”(金瓶梅)
[18]“却舀一碗白汤,把到楼上。”(同上)
[19]“再用十两好绵,都把来与老身。”(同上)
[20]“只把做亲嫂嫂相待。”(同上)
3)“把”+工具+VP:
[21]“想是你见丈夫丑陋,不趁你意,故此把毒药药死是实。”(明话本·玉堂春落难逢夫)
由以上三种用法来看,“持拿”义动词“把”属于当时常用词,且有活跃的组合功能,能够直接和其他动词组合使用,如“把做、把将、把到、把来”等。
往上溯,可以发现“把”直接加动词普遍见于唐宋文献,例如:
[22]“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诗)
[23]“百里音书何太迟,暮秋把得暮春诗。”(白居易诗)
[24]“一枝为授殷勤意,把向风前旋旋开。”(薛涛诗)
[25]“后来有一好砚,亦把与人。”(朱子语类)
“把+工具”的格式中“把”表示“拿”的意义,意义也较实。所以这个意义的“把”也可以直接和动词组合,例如“把做”。
“把与”是动词“把”和其他动词组合的一种。从其组合结构来看,“把”表示具体动作,其后的动词包含了动作方向、目的。“把与”组合中“与”规定了动作的方向、目的。而在具体语境中,动作的对象、方向是明确的,“把”则吸收了“与”的意义,作“把与”义单独使用,如:
[26]“我有两贯钱,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金瓶梅)
[27]“我每人把个帖子,随他来不来!”(同上)
总之,“把+V+N”的普遍使用是“把+与+N”产生的句法语义基础。动词“把”的活跃和“把与”组合的使用是“给予”义的“把”产生的来源。
可见,“把”在近代汉语中意义和功能比较复杂,“把”兼表处置、被动的同形异义结构有不同的历史层次。
(2)“把”表被动的来源。我们赞成蒋绍愚[1]关于“给”演变为被动标记的分析。和“给”字被动式一样,“把”表被动的来源是,由“给予”义的“把”演变为使役标记,然后由使役标记演变为被动标记。
[28]“你把(“给予”义)他吃一点啊。”
[29]“东西都把他带走了。”(东西都让他带走了。)
[30]“脚把石头打了。”(脚被石头打了。)
在例[30]中施事是无生名词,是典型的被动句。
(3)结论。“把”表处置和共同语中“把”表处置是同源的,而表被动来源于宋元开始,发展到明代成形的“给予”义的“把”,“把”作为“给予”动词在方言中普遍使用之后,先演变为使役标记,然后发展为被动标记。
总结“把”演变历程:
1)“把”表处置:动词“把握”义―先秦广义处置式―唐代狭义处置式―唐代致使义处置式―元代遭受义处置式
2)“把”表“给予”义:动词“把握”义―唐代“把+V+N”格式―宋元“把+与+N与(+V)”―明代“把(“给予”义)+N受”
3)“把”表被动:“把”表被动在文献中没有找到例句。对比“给”的被动标记的来源,“把”在方言中的发展过程应该是:
动词“给予”义―“把(“给予”义)+ N与+V”―使役标记―被动标记
四、处置、被动标记“把”和“给”的差别
最后,我们来谈谈处置、被动标记“把”和“给”的差别。表面上看,黄冈话的“把”和北京话的“给”兼表处置、被动似乎是同类现象。黄冈话中“把”作处置标记和共同语没有差别。但是动词“把”及其部分句法表现和北京话“给”很不一样。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差别。
1.“把”和“给”差别
(1)“把”作动词表示“给予”,接受者成分前可以加虚词“到(得)/在“:
把到(得)你/把东西到(得)你
“给”的接受者成分前面不能加前附加性的虚词。
(2)“给+N”可以用在VP后面,而“把”不能:
送给你/*送把你
送东西给你/*送东西把你
(3)“给”可以直接加VP,而“把”不能:
给锁给弄坏了/*把锁把弄坏了[注]黄冈话中不能说“把锁把弄坏了”,赵元任[17]举出北京口语可以说“他偏把弄坏了”。
鸡给杀了/*鸡把杀了
(4)“给”可以引进受益成分,而“把”不能:
给小孩讲故事/*把小孩讲故事
(5)“把”表被动后面可以加上虚词“到(得)”:
东西把到(得)老鼠拖走了
“给”作被动标记后面没有虚词。
2.“给予”义的“把”和“给”句法表现不同的原因。
(1)历史层次和分工。黄冈话表示“给予”义时,老派话优先选择“把”,新派话(所谓“学生腔”)会选择“给”,这是一个新的文白层。但是,我们要再思考历史上的“文白层”分化。
如上文所述,“给予”义的“把”最早见于明代文献,且和先秦至元代常见的“给予”义动词“与”,元代出现的“给予”义动词“给”兼用。但“把”不能引进受益成分,“与”可以:
“官人先与我一两银子。”(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先夫留下银子,我好意把你。”(同上)
“邻舍又与许宣接风。”(同上)/*邻舍又把许宣接风。
“与”后来被“给”替代。可见,黄冈话“把”不能引进受益者是由于词汇语法的历史层级和词汇竞争的结果。表受益只能用“给”。
它们的历史层次应该是这样:
在明代“把”作为新兴的“给予”义动词,和“与”、“给”并用。其后在江淮官话、湘语、赣语中“给予”义动词中“把”处于强势。而在北方话中“给”处于强势,不用“把”。在现代普通话推广的强势入侵之下,南方话中“给予”义用动词“把”的,也开始被“给”冲击。与此同时,“把”字处置式一直存在。
黄冈话“把”不能引进受益成分,无法像“给”一样从受益标记发展为处置标记,但是“把”却是处置标记,在此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复杂的历史变换层次和方言表情达意的方式,可能也是众多南方方言由“给予”义动词演变来的表处置、被动标记不能直接加VP的原因[注]例如陈瑶指出安徽祁门话中兼表处置、被动的“给予”义动词“分”也同长江流域的“把”一样,不能直接加VP。(参见《“给予”义动词兼表“施受”的动因研究——以徽语祁门话的“分”为例》一文,载于福建辞书学会《福建省辞书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九届年会论文集》,2009年),因为存在的历史上词汇语法的更替与竞争,还有可能是表达方式的选择,黄冈话中虽然不用“把+VP”,但也不常用“被+VP”,更不用“给+VP”。
(2)介词“到”的使用。我们注意到黄冈话中的与事成分前一般会加一个介词“到[tau35]”,有时候会语流音变为[t0]。所以有的著作中写作“得”。但是我们认为这里的虚词本字是“到”。
赵元任[17]指出,北京话“他搬得哪儿去了”中“得”是“到”和“在”的混合物。吴福祥[18]指出,唐五代趋向补语中“到”已经由单纯表位移的处所,发展成兼表动作涉及的对象。举例“酒巡到下官。”(游仙窟)从空间上的物体位移的终点,隐喻到动作行为的归属点,是很常见的认知过程。而不同语言系统选择不同的角度进行表述同一事件也是普遍现象。
北京话选择动词“给”加接受者表示事物位移的归属点,而黄冈话选择用介词“到”加接受者表示事物位移的归属点,所以有“V+N+到+N”和“V+到+N”的形式。而“把+到+N+V”是常见的表给予的句式,这个被重新分析为被动句时,容易让人误以为读轻声的“到”是黏附在“把”后面的一个助词。
这种形式的被动不会和“把”字处置式产生歧义,所以,一些学者如左林霞[15]、石毓智[19]认为,“把”加“到”表示被动是因为“把”兼表处置、被动产生歧义,附加上一个“到”则可以消歧。我认为这是从共时层面上观察得到的结论,诚然,“把+ 到+N+VC“是无歧义的被动句,但是,“到”不是为了消歧附加到“把”后面的。
黄冈话中表示“给予”义也常用“把+到+N”:把到我啊/把到我吃。
“到”后面一定要加上接受者,因为“到”是一个引介位移终点/归属点的介词。“把+ 到+N+VP”当 VP是光杆动词时没有两解,“把”只能理解为动词。句子层次是:((把)到我)看。当VP是VC动补结构的时候,“把”有两解,一是动词,一是被动标记:把到猪吃了/把到他扯断;需要在语境中分辨到底是哪种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把+到+N+VC”形式的被动式,来源于连动式的重新分析,“到”一直是一个介词,只是连动式重新分析为被动式的时候,由于句式意义的变化使得“把+到”也发生重新分析,发生了词汇化,被认为是一个词。
[参 考 文 献]
[1] 蒋绍愚.“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M]∥《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26),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9-177,
[2] 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郭浩瑜,杨荣祥.“控制度”与近代汉语处置式的多义性[:J].古汉语研究,2012(4):50-55
[4]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 王健.“给”字句表处置的来源[J].语文研究,2004(4):9-13..
[6] 林素娥.北京话“给”表处置的来源之我见[J].汉语学报,2007(4):84-90.
[7] 张恒.开封话的“给”与“给”字句[D].开封:河南大学文学院,2007.
[8] 朱景松.介词“给”可以引进受事成分[J].中国语文,1995 (1):48.
[9]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 张敏.“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M]∥《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42),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60.
[11] 徐丹.北京话中的语法标记词“给”[J].方言,1992(1):54-60.
[12] 石毓智.兼表被动和处置的“给”的语法化[J].世界汉语教学,2004(3):15-26..
[13] 江蓝生.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M]∥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21-236.
[14] 陈有恒.鄂南方言里的“把”“到”“在”[J].武汉师院咸宁分院学报,1982(2):106-109.
[15] 左林霞.孝感话的“把”字句[J].孝感学院学报,2001(5):77-80.
[16] 黄晓雪.方言中“把”表处置和表被动的历史层次[J].孝感学院学报,2006(4):50-53.
[17]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8] 吴福祥.南方方言里虚词“到(倒)”的用法及其来源[M]∥余瑾.语法论丛.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195-223.
[19] 石毓智.汉语方言中被动式和处置式的复合标记[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2):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