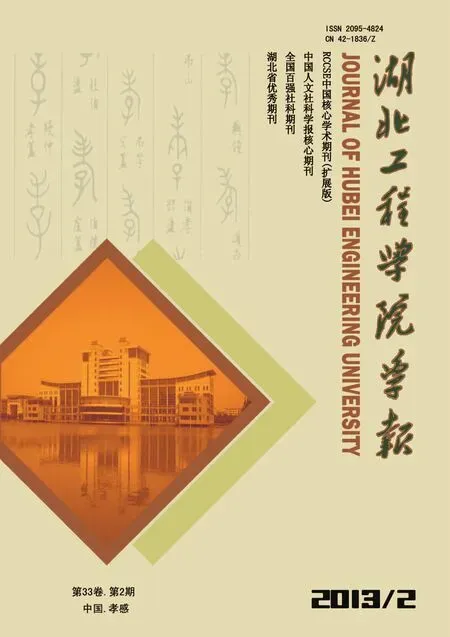论顾一樵的话剧《白娘娘》
李 斌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戏剧资源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13)
表现主义是20世纪西方重要的艺术潮流,这一艺术潮流也对现代中国文坛产生巨大影响。五四时期,中国很多学者、作家对表现主义给予高度评价,进行热情的介绍,或在创作中积极借鉴。高长虹、向培良、顾一樵不约而同地受到表现主义的影响,把目光投向了白蛇传这一古老传说,创作出了颇具表现主义倾向的话剧。相对于传统戏曲白蛇传,顾一樵的改写有何新颖之处?表现主义如何融入这一古老的传说?这些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和问题,对于深入探索五四文学所受外来影响、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等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一 创作的时代背景
顾毓琇(1902-2002)字一樵,著名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是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
《白娘娘》是五幕话剧。顾毓琇在写于1931年的《编剧后记》中说:“曩于冰雪中渡大西洋,狂风怒涛,夜不成寐,因就白蛇故事,草拟剧旨及结构,归国后,卜居西子湖畔,雷峰塔已不复见,姑成此稿,以慰湖山之岑寂,日来漫游镇江,登金山寺,访法海洞,因就旅次录旧作以了因缘。”[1]由此可以看出,此剧是分几次写就的,“曩于冰雪中渡大西洋”是指1929年1月作者从美国到欧洲的途中。万国雄在《顾毓琇传》中对当时的情形进行了“还原”:“顾毓琇学成后,于1929年1月辗转回国,从纽约到欧洲的船行中,有一夜,船摇动得很厉害,彻夜难眠,思绪万端,回味在纽约观看奥尼尔的名剧《奇遇》,联想到中国传说中白娘娘与许仙的神话故事,不是更加‘奇遇’吗?经过一夜的思索,便打下了剧本《白娘娘》的腹稿。”[2]顾毓琇构思《白娘娘》时,是否想到了奥尼尔的《奇遇》,根据现有资料不易做出判断。然而,顾毓琇观看过话剧《奇遇》,《白娘娘》受表现主义的影响则是确定的。1930年夏,顾毓琇在杭州教书时,写成了剧本。
20年代前期,奥尼尔的剧作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很大,1929年奥尼尔访问中国后,国内评介其剧作的文章逐渐增多。奥尼尔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顾毓琇观看过他的剧作,受到其影响,顾毓琇回国时中国文坛对奥尼尔的关注度渐增,这使得顾毓琇的剧作染上表现主义的色彩。
1990年初冬,《白娘娘》在上海首演,王建平以《毓琇先生会欣慰的》为题,发表评论:“国内的许多剧种,都演过《白蛇传》,而在话剧舞台上塑造白娘娘的形象,尚属首次。”[3]“首次”的说法有误,早在1929年10月,狂飙演剧队就在天津演出了高长虹的话剧《白蛇》,许仙和白蛇分别由甄梦笔和郭森玉扮演。1945年,在重庆“抗建堂”演出了话剧《雷峰塔》,周彦导演、卫聚贤编剧。
二、做人的痛苦主题
人的发现与觉醒是五四时期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新文学的作家们在创作中高举启蒙主义的大旗,积极响应“人”的主题。剧本《白娘娘》借虚幻的神话故事,真实地写出五四时期青年们要求做人的强烈愿望以及梦醒后的生命苦痛。
剧本浓烈地渲染了白娘娘与许仙之间的爱:
白 我是一个不懂世情的女子,但是我觉得爱是一件又有趣又冒险的事呢。
许 惟其是冒险,所以有趣,所以值得!姑娘,我愿牺牲一切来爱你!
白 (真是不懂世故地问)牺牲一切,难道连生命也肯牺牲吗?
许 岂止是生命。前面的小河,是我们时常游息的所在,那里我可以死,但是死了以后,我的灵魂还会随着我的爱人。姑娘,真不信么?
白 (听见严重过意不去)好朋友,我早知你的忠诚。我起初还只是糊里糊涂的,但是逐渐地,我感觉到你的温存,你的深情和厚意。
许 姑娘,请你爱我!为着爱——
白 让我们的生命做保障!
许 让我们的生命来牺牲![4]27-28
作品还表现了母子之爱。许仙死后,白蛇无限疼爱小孩子,如法海所说,“宝贝得像夜明珠一样”。为了从法海手中要回孩子,白蛇以首撞门,不惜拼命。
此外,剧本还写出了做人的痛苦,尤其是女性的痛苦。白蛇想做女人,法海劝阻说:“做人不是容易,做人有做人的苦处”,“女人最难做,女人的难处最多”。[4]6-8白蛇坚持要做女人,法海叹息说:“你既然一定要做人,就预备着尝试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你就去做女人吧。世界上一切的情绪一切的欢乐一切的痛苦,只有女人最尝得透!但是最后我叮嘱你一语:做人不是容易,学做人更不容易。你应当预备牺牲,你应当接受痛苦。但是不要怨恨,勇往地做人去吧。”[4]8法海还要白蛇好好做人,争个光荣:“你可知道世界上的人每说人面蛇心,把你当作狠毒的东西?……你须记得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你变成了人也是人面蛇身,你可不要跟人面蛇心的人们学坏了,你还须为天下的蛇类争个光荣,免除一向的丑恶和侮辱。”[4]67
白蛇要求做人的想法以及在做人时所承受的苦痛,具有深刻的时代隐喻。人的觉醒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功绩,要求做人是时代的呼声。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现。”[5]陈漱渝指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而五四文学革命的基本精神则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6]此种情形酷似数百年前欧洲的文艺复兴,其时莎士比亚在其剧作中写下这样令“人”激动的语言:“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7]当欧洲人文主义的阳光照耀在黑暗发霉的中国大地上时,顾毓琇给予了响应,白蛇要求做人同样是他最为强烈的想法。
白蛇经历了做人的痛苦。白蛇爱许仙,然而爱得很痛苦,她明白自己是蛇,对于嫁不嫁许仙感到矛盾,“惟其他是恩人我才不好爱他嫁他”。[4]31她刚刚来到人间就被少帅欺辱,她与许仙只有短暂的爱情与幸福,许仙死后少帅不肯罢休,要把她抢去。尽管她生下孩子,可是她不能将其抚养成人,饱受母子离散之苦。她因要抢回孩子和法海大战,被镇压在雷峰塔下。做人,对于白蛇来说,是个十足的悲剧,正如法海所叹息:“唉,这矗立的雷峰塔,代表着慈母亲子之爱和牺牲。他日山纵崩,塔纵倒,这做人的悲剧将永远流落在人间!”[4]67白蛇在许仙坟前的哭诉:“世上一切原是梦,我们的恩爱本是痴。但是谁又想到这两情相爱的结晶品,这天真烂漫的小宝贝,要你的生命做代价?儿啊,我愿你不要来到世上来受苦吧,世界是怎样的无情!儿啊,我要你,我又没福要你,还是你自己命苦,还是我命苦,害得你的前途也孤苦伶仃?……”[4]55这里既有真挚的夫妻之爱、母子之爱,又有对人世苦痛的控诉。
青海所作的《序诗》也强烈表达了剧本爱与痛的主题:
1.你不见暮山的雷峰,塔上一团团云移,白娘娘在睡着叹息,表现那数说不清的爱?
“我是爱的精灵——我还是爱的精灵!固然,爱是无上的祸根,没有爱?咳,没有爱,世界?顽石一块,乱石一堆!”爱,爱,千年塔下也不孤零。湖边的伴侣,成双的侣影,膜拜着谁?送子观音,砖上留的是热吻;塔边流不住的清泪。
2.如今你不见了雷峰塔影,休将永远不见那雷峰塔影。不是——不是风雨的摧残,也不是白娘娘在翻身。初霜的深夜,一瓣黄叶紧紧的,靠着一瓣黄叶,轻轻的坠落,微微的暗泣,是情在作怪障,爱在造孽。是湖心的白衣女郎,纤腰倚定湖波摇曳,把昨夜和今宵,做一滴泪一声叹息。从此你不见了雷峰塔影,你便永远不见那雷峰塔影。[4]1-4
弥漫于《白娘娘》中的痛苦情绪,大概正是作者内心痛苦的反映。“五四”退潮后,青年们普遍彷徨、苦闷,体验着“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顾毓琇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写作。清华文学社成立,他是小说组织员兼戏剧组主席,后又担任清华戏剧社社长及《清华周刊》文艺栏及新闻栏集稿员。他说:“总结清华求学,以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最有意义。”[8]在国外求学期间,顾毓琇还积极参加话剧表演。可是当时的中国依然处在黑暗之中,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得作者感到精神上的痛苦。
三、别开生面的情节
有论者批评顾毓琇的话剧缺乏独创性:“他的历史剧和神话剧,往往局限于历史记载或前人作品的格局,缺少艺术上的独创性。”[9]然而也有论者指出:“顾毓琇的历史剧是别有新意、别开生面的。”[10]翟毅夫也评价说,顾毓琇在文学创作上不模仿他人,具有独创性:“一樵尝试小说的时间很短,但是从来不屑模仿他人的作品。因为有了这种充满的个性,所以他的创作的天才才能够渐渐显露出来。”[11]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如果结合顾毓琇的作品来分析,后一种观点是中肯的。话剧《白娘娘》在剧情和人物塑造上不拘囿于前人之作,多有创新之处,在艺术手法上具有明显的表现主义特征。
在《白娘娘》中,白蛇和青蛇是经过法海的帮助而化为人的,白蛇和许仙的婚姻也是法海有意撮合而成。而在此前的“白蛇传”中,白蛇是通过自己的修炼化为人身的,为“报恩”而与许仙在西湖相会、结亲,法海是白蛇的对头,要拆散人与妖之间的爱情、婚姻。顾毓琇的改写显然别出心裁,摒弃了报恩说,将法海塑造成白蛇的恩人。
再如“盗草”,在此前的“白蛇传”中,端午节白蛇现形吓死许仙,白蛇冒着生命危险去盗仙草,与看守仙草的鹤童展开战斗;而在《白娘娘》中,盗草的情节省去,仅是简略地交代白蛇出去采药。
在此前的“白蛇传”中,白蛇和许仙是“一夫一妻”制,青蛇是忠实的奴仆——弹词《义妖传》和《前后白蛇传》中有“婢争”情节,青蛇是在白蛇出塔后才成为许仙的小妾的,“婢争”的原因是白蛇早在要小青做媒时许下的诺言。在《白娘娘》中,青蛇是听信了白蛇和许仙的命冲之说,以及许仙占卜说她和白蛇有同样好的丈夫的戏言,才嫁给了许仙的。
在此前“白蛇传”中,许始终存在,白蛇大战金山寺是因为法海要拆散夫妻,许身在金山寺。而在《白娘娘》中,青蛇嫁给许仙后不久,许仙就病逝了——大概是纵欲的结果。白蛇在许仙病逝前就产下孩子,白蛇与青蛇大战金山寺,是因为法海骗走了孩子。在此前的“白蛇传”中,白蛇在金山寺败阵后逃走,与许仙断桥重逢、生子,最后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白蛇后来出塔,或是因为青蛇毁塔,或是因为儿子中状元祭塔;而在《白娘娘》中,白蛇在金山寺战败后就被押在塔下,青蛇逃走,剧情结束。
《白娘娘》不同于传统白蛇传之处,重要的因素就是顾一樵在作品中借鉴了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戏剧注重情感的表达而轻故事叙述,因此剧情常常缺少内在的逻辑关联,《白娘娘》也有这样的特点。例如,白蛇知道许仙是救命恩人后,对自己与许仙的婚姻犹豫不决,担心害了许仙;可是,当青蛇提出嫁给许仙时,她竟毫不犹豫地答应。她为什么不道出“隐情”?白蛇见到明珠后,就告诉青蛇她俩与众不同,有特别的来历,却没有了下文,青蛇也不追问。对于青蛇抚摸许仙,白蛇只是“瞪了小青一眼”。青蛇提出嫁给许仙,白蛇“恶狠狠看了青一眼,亦笑了”,连内心的排斥、苦痛、挣扎都没有,不符合一个常人的心理。
又如,少帅对白蛇垂涎三尺,多次要强抢她;可是许仙死后,少帅却不来抢了。甲乙流氓抱走小孩子引白蛇去帅府,可是这个办法不奏效时,少帅为什么不派人来抢白娘娘?少帅把小孩子给金山寺后,却不再写少帅下一步的行动,没有了下文。再如,关于白蛇的法力问题。白蛇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蛇,可是在流氓要抢她去帅府时,她只是害怕哭泣,毫无反抗之举。流氓抢走了她的孩子,她也只是大哭,没有以法力来反抗,没有去帅府把孩子抢来,可是,后来却在金山寺和法海斗法。
最奇怪的是法海的行为,他先是促成许仙和白蛇的婚事,继而又点拨许仙和白蛇分开。法海是个得道高僧,出于好心,担心白蛇无法把孩子养大而设计夺得白蛇之子,可另一方面,他粗暴又霸道,任凭白蛇和青蛇苦苦哀求,就是不归还孩子,其理由是“克命”:“据我推算,这孩子的命中克爹娘,克了爹又要克娘,克不了娘克自身。”[4]58以至于白蛇气愤得以首撞门,骂他是“助纣为虐的和尚”。后来在白蛇战败之后,他才说白蛇的本来面目是蛇,无法把孩子养大。法海为什么不早讲道理来点拨白蛇呢?再者,白蛇早就知道自己是蛇变来的,难道经过法海的“一语道破”就“羞缩无言”?
此外,清明时节白蛇、青蛇来上坟,白蛇哭诉去年清明才是他们定情的日子,法海对甲乙流氓说许仙的小孩子“五个月”大了,“五个月”显然不合常理,说一两个月不是更合适一些吗?
奥尼尔是表现主义剧作家。1929年1月,顾毓琇在纽约观看过奥尼尔《奇遇》(Strange Interlude)。《白娘娘》是典型的表现主义剧作,或许就受到了奥尼尔的影响。剧本自觉地运用灯光、色彩、音响、布景等舞台艺术手段,如在“幻化”情节中,深山的茅屋,游动的蛇,雷电、乌云、风雨、山林,电闪雷鸣的黑暗世界,雨过天晴。第五幕金山水战和收伏白蛇,也是运用了类似的舞台艺术手段,光线、色彩、声响前后对比反差极大。这些都是表现主义戏剧的重要特征。
《白娘娘》具有“怪诞”色彩。白蛇和青蛇由蛇变成人的“化幻”,深山的茅屋,游动的蛇,电闪雷鸣的黑暗世界,白蛇以极简单的表情和动作来向法海表达意愿,都显得很怪诞,而怪诞正是表现主义的特点之一。
和向培良的《白蛇与许仙》、高长虹的《白蛇》一样,《白娘娘》也有梦幻的描写:许仙对白蛇讲述了明珠的来历后,白蛇昏去不省人事,做了个梦,梦游深山,老僧指点她的本来面目。
[参 考 文 献]
[1] 顾一樵.编剧后记[M]//白娘娘.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68.
[2] 万国雄.顾毓琇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77.
[3] 王建平.毓琇先生会欣慰的[N].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02-01.
[4] 顾一樵.白娘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5]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M].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5.
[6] 陈漱渝.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2).
[7]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M].卞之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63.
[8] 顾毓琇.百龄自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21.
[9] 陈白尘,董健主.中国现代戏剧史稿[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174.
[10] 高恕新,顾一群:国际著名学者顾毓琇[M]//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0:66.
[11] 翟毅夫.芝兰与茉莉·序[M]//顾毓琇.顾毓琇全集:第1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