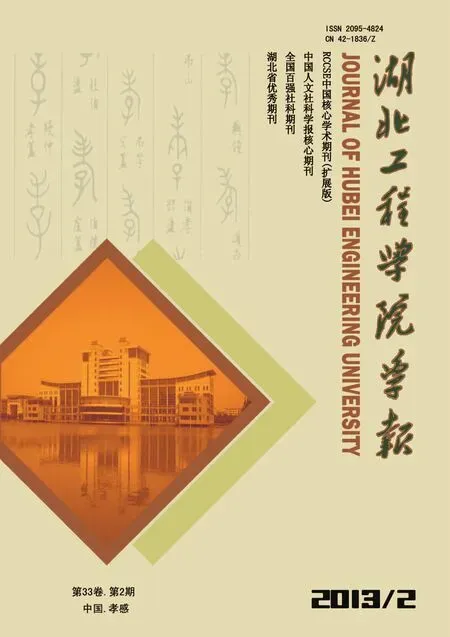论英国宪章派诗歌中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变化
肖四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宪章派诗歌内容上突出的特点,在于描写了工人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而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工人阶级挖掘自身主体性、自我确证的过程。工人阶级从自身处境出发,认识到了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客体地位,形成了群体的自我意识,并通过经济斗争、政治改革、社会革命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主体所潜在地具有并且能够发挥出来的属性”[1]。这一属性,需要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中显现出来。它既包括对外在世界不适应的感觉,也包括通过维持与对象的关系,确立其主体地位的倾向,还包括自觉地改造对象,使对象主体化的倾向。从工人阶级主体性觉醒这一角度,可以将宪章派诗歌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1842年之前的诗歌属于早期创作,1843-1847年间的诗歌属于中期创作,而1848年之后的诗歌属于晚期创作。三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明显体现出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变化。
早期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萌芽。工人阶级从自身的生存处境出发,认识到贫穷的根源,具有了阶级对立观念,并反抗自身的处境与阶级压迫,以罢工的形式进行争取以普选权为中心的斗争,初步具有了阶级意识。这其实是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觉醒。工人阶级认识到了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客体地位,与压迫阶级形成了对立关系,并希望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只是宪章派文学中的主体,不是以个体而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社会历史中的另外的群体,于是主体性以阶级意识的形式呈现出来。
早期诗歌多描写工人的生存处境。在200多首“宪章派诗歌”中[注]诗歌主要来源于皮特·谢克纳编选的《宪章派诗歌选》,其中收录了 220多首诗歌。见Peter Scheckner(ed.).An Anthology of Chartist Poetry:Poetry of the the British Working,1830s-1850s.Lon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 UP,1989.,早期诗歌约占三分之一,而直接反映工人生存状况的就有30首左右。如西姆的《劳工歌》(1940年),描写了工人们整天苦役般的劳作但最后一无所获的现实。他们“从一线曙光干到天暗”,织造出的“最贵重的金色礼服,最华丽的丝绸”,却被那些合法的强盗小偷掠走,自己却“衣服破烂,面包不足”,居住在矮小的茅屋中,冬天冻得“瑟瑟发抖”。
表面上看,它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描写工人生活的民主主义诗歌没有多大区别,表达的是对工人悲惨遭遇的同情。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有本质的不同。比如布莱克《扫烟囱的孩子》(1789年)、雪莱的《给英国人民之歌》(1819年)等,都是描写工人悲惨遭遇的诗歌。但这些诗歌仅仅只是对工人个体生活处境的经验性描述,没有体现出工人阶级整体的生存状况。诗歌中的工人形象,也仅仅只是让人同情与怜悯的弱者,并没有形成超越具体经济结构的自觉意识。更不可能具有阶级意识,因为工人阶级尽管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出现,但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同的等级与阶层,社会结构也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他们还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自己作为社会的存在。
即使与同时代民主主义诗人们描写工人生存状况的作品相比,宪章派诗歌也存在很大不同。比如胡德的《衬衫之歌》(1844年),描写了织工繁重单调的劳动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她们整天“干呀!干呀!干呀!直干到头昏脑痛;干呀!干呀!干呀!直干到两眼朦胧”,但“老天爷啊,粮食如此昂贵,我们的血肉这样低廉”。诗歌也描写了女工对美好生活——阳光、绿草、鲜花的渴望,但这并不是希望把握自己命运的主体性的觉醒,而只是希望这吟唱贫穷、饥饿、肮脏、疾病的歌声,能“传到富人的耳中”,求他们发发慈悲之心。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首“使资产阶级女郎们流了不少怜悯的但毫无用处的眼泪”[2]的诗歌。
相比之下,宪章派诗歌不是从工人个体,而是从整体上把握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存在的。宪章派诗歌中的工人,几乎都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早期的70多首诗歌中,直接以工人阶级整体为叙述主体的占一半以上。其他有些诗歌,尽管表面上描写的是个体的生存遭遇与情感,而实际上所表达的仍然是工人阶级整体的遭遇与情感。整体的自我意识,是阶级意识形成的端倪,也促使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宪章派诗歌也描写工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并不是单纯展示苦难,乞求怜悯与同情,而重在挖掘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早期诗歌在展示苦难的同时,总是要寻找苦难的根源。比如《劳工歌》就指出,工人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被“那些合法的强盗小偷掠走了”。在地西的《压迫》(1842年)中,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冷酷的权贵豪绅的侮弄”和“不义横行”。
对贫穷根源的认识,使工人阶级有了阶级对立观点。在林顿的组诗《无选举权之歌》(1839年)中,工人形象与资产者、地主、贵族的形象,总是以利益对立的“我们”与“你们”的形式出现。在山基的《歌》(1840年)中,“国王、贵族、豪富”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在瓦特金斯的《谷物税和移民》(1842年)中,我们看到,工人阶级认识到“老爷们”的享受——“大厦和高楼,珠宝,舞会,酒肴”,是靠劳动者“光屁股、饿肚皮”来实现的。
阶级对立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文化教育、法律、选举等各种权利上。比如女工斯泰利布里奇在一首诗中,就比较了两个阶级的不同命运。工厂主的妻子与女儿不仅可以穿绫罗绸缎,还可以接受教育;而女工们则既没有金钱,也没有时间去接受教育[3]。
阶级对立导致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意识中具有了反抗性。早期诗歌几乎都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性。在艾夫的《万众一心》(1842年)中,工人阶级决心万众一心,奋勇向前,去“粉碎那万恶暴君的奴役”,去“争取做人的权利”。吉尔在《歌》(1842年)中引用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展示了工人阶级“奋力把暴君从宝座推下,好让自由升上来代替它”的自觉意识与反抗意识。在《劳工歌》的结尾,西姆写到:
唱吧,兄弟们,我但愿听到
你们的歌曲嘹亮豪放,
因为唯有渴望自由的心灵
才能这样豪放地歌唱!
你们快快唱起压迫者的挽歌,
快快大声地敲起丧钟,
葬送公开的掠夺和朝旨王命,
这曲调才配你们歌咏。
在另一首名为《压迫》的诗中,作者地·西连用五个反问,确立起被压迫者“做人的尊严在心中闪光”的自觉意识,并进一步产生“必须解放,一定解放”的反抗意识:
难道我们永远得忍受
冷酷的权贵豪绅的侮弄?
难道我们永远做脏品,
供那些贪婪荒淫者享用?
眼看着不义横行,白劳动,
心里忧伤而态度从容?
……
别让我们这样,
做人的尊严在心中闪光,
正义在要求,自由在呐喊:
必须解放!必须解放!
表面上看,这些诗歌所体现的是诗人主体性的觉醒,不能算是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觉醒。但因为宪章派诗歌的作者无一例外的是工人和宪章运动者,所以这些作者基本可以代表工人阶级。
但早期诗歌中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还十分有限。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与对象的对立关系,但对象的概念还比较模糊。在他们笔下,对象不仅包括资产阶级,还包括地主、贪官甚至恶霸、无赖。多数人还不明白阶级对立的根源,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压迫和剥削。尽管他们已经有了反抗意识,但主要还囿于经济层面,反抗也多停留在抽象的抗议上。即对社会现存制度还存有幻想,希望通过“人民宪章”的实现,改变自己恶劣的生存环境。比如无名氏的《歌》(1840年)中,一再呼吁“宪章万岁”;本斯在《致投我于狱中的官吏们》(1840年)、《宪章主义者母亲的歌》(1840年)、《赐给我们每日的口粮》(1840年)等诗歌中,认为“宪章是我心爱的东西”,为了宪章的实现,不怕坐牢甚至杀头;米德在《宪章派之歌》(1841年)中认为“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就靠这光荣的宪章”,呼吁人们紧紧团结在宪章的周围,去“要求自由人的权利”;艾夫在《致威尔斯宪章派》(1842年)、《万众一心》等诗歌中,呼吁人们“展开宪章主义的大旗”。可以说,早期诗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将改变工人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宪章”的实现上。
中期诗歌大约70首左右,产生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请愿失败之后。两次斗争的失败,使工人阶级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具有了政治独立性。中期诗歌中,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这主要体现在,工人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概念更清晰了,明确把对象界定为资产阶级。并且通过对资产阶级本质的揭露,弄清楚了自身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并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在社会劳动过程中的物化地位,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斗争,保障自己的权利。如果说早期诗歌中的工人阶级作为主体,更多关注主体自身的生存状况的话,那么中期诗歌中工人阶级,更多关注的是对象——资产阶级的属性,以及自己与对象的关系。他们认识到自己只是对象谋取利润的手段,但他们希望通过与对象在互为目的的关系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
这一时期的诗歌,很大一部分是描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工人阶级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财富是靠剥削工人得来的,比如在《蒸汽王》(1843年)中,米德将蒸汽机比做工厂主的巨臂,它在主人的指使下,“把千百万工人治死……拿小孩当食品充饥……把工人的血液变成黄金”。而骄横的工厂主,垄断一切天生的权利,无视工人的瘦骨嶙峋,“大口吞咽人血和黄金”,骄横无道,寻欢作乐。在《宪章派之歌》(1846年)中,琼斯指出,那些所谓的棉纱大王、小麦大王,正是“仗着纺织机和田地谋生”。
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而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是他们通过卑鄙手段得来的。林顿在《工人和利润》(1847年)中,就揭露了窃取别人发明成果而暴富的阿克拉特、皮尔、柯布登等人的丑恶嘴脸。他们的“光景过得真美好……在财富中打滚,钱多得花费不了”,而真正的发明者哈格里夫、皮尔、柯布登等则“孤零零的死掉”,甚至“白白饿死掉”。工业革命的成果被他们无耻地占有,用来作为剥削工人的工具。他们又通过剥削得来的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宰。在《黄金大王歌》(1845年)中,艾伯纳叟模仿“黄金大王”的口吻,描绘了资本统治一切的社会现实:
我们的奴隶数不清,
我们的权力无止境,
别人的死活我们定,
我们出租,创造,杀人。
……
什么地方有生命,
黄金大王是主宰。
资产阶级不仅享用“千万人呻吟着做工”的成果,而且还通过资本占有,获得话语权,将物化现象转化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一种表现形式,特别是生成有利于资本统治的国家形式和法律制度,将剥削制度合法化,名正言顺地统治他人。1846年工厂主操纵议会废除“谷物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顿在《工人和利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工厂主以合法的手段“再压低工资”,其结果是“商业的利润猛涨又飞升,自由贸易真繁荣”,而“每日里饿死劳工”。
工人阶级也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在社会劳动过程中的物化地位,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工厂城》(1847年)中,琼斯描写了工人在大生产流水线上紧张劳动的场面,飞转的车轮就是“当今的刑台”,“血肉和钢铁进行殊死战”,工人的“生命之线飞快地断掉”了。而在工厂主眼中,工人只是能产生利润的机器。辛勤劳作的工人,最后一无所获,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物化的阶级:
机器飞旋,老板发财,
钢铁发出保卫的光芒;
工人双手所创的财富,
却被自己的敌人花光。
工人阶级认识到,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改变与对象的关系。第二次请愿失败之后,诗人托马斯·柯伯就号召工人“把罢工变成政治斗争”。中期诗歌中,普遍体现出工人阶级希望通过政治改革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倾向。
克力图在《自由颂》(1843年)中,表达了工人阶级不惜为自由而献身的壮烈情怀:“万千大世界,一钱也不值,假使自由尽丧失;为了争自由,失去全世界,代价轻微不足惜。”柯尔在《暴君的力量》(1846年)中呼吁人们“粉碎手铐和脚镣”,去“把暴君灭掉”,争取自由。米德在《蒸汽王》中,呼吁工人们“用子弹、烙铁,还有木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去“打倒那君王,莫洛克王,和他手下的恶官暴吏”,只有这样,“公理得伸张,自由得胜利,暴力终于屈服于正义”。以哈尼、琼斯为代表的暴力派甚至主张采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统治,哈尼就说:“我们的任务是立即行动,全心全意地为推翻这个制度而努力。”[4]琼斯在《宪章派之歌》中指出,“我们的生命不是你的麦子,权利不是你的物品”,呼吁工人阶级大胆的站起来,粉碎统治者的“十字架、宝剑和王冠”,把自己劳动的果实夺取。在《工厂城》中,琼斯鼓励工人们“别垂头丧气”,要获得彻底解放,要敢于舍弃自身。义无反顾地“织自己的尸衣,掘自己的坟墓”。
这种自觉意识甚至超越民族与国界,形成了全球工人阶级一家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只有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解放。琼斯就曾说(1854年):“我不只是一个英国人——我是人,我-我们都有一个比狭窄的岛屿更广大的国家,它包括法国和德国——它也包括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我的祖国是世界,我属于最广大的被压迫阶级。我本质上只承认两个民族,暴君和奴隶,富人和穷人。就后者而言,我是一个战士……”[5]215这方面的内容在宪章派诗歌中占相当的分量,而且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比如琼斯的《自由进行曲》(1848年),山基的《致世界各国工人》(1840年),阿诺托的《给兄弟民主党人之歌》(1846年),林顿的《列国哀歌》(1848年)、《保卫罗马》(1849年)等,都是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诗歌。
尽管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发展为比较成熟的阶级意识,但大多数工人,甚至包括宪章派主要领导人,还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政治改革,通过“人民宪章”的实现,在现存制度下确立自己的地位。所以1848年之前的诗歌中,都仍然将“人民宪章”的实现作为斗争的最终目的。比如艾夫在《致威尔斯的宪章派》(1843年)中再次呼吁人们“展开宪章主义的大旗”,吉尔在《歌》(1843年)中热烈地欢呼宪章,米德在《蒸汽王》中呼吁工人们争取宪章的实现。甚至1848年之前的琼斯,都还对“人民宪章”抱有幻想,在1846年发表的《宪章派之歌》中,仍然将实现宪章视为最终目的,坚信“宪章一定属于我们”。在1847年发表的《工厂城》中还认为,“要保卫自己的土地,最好的办法——把宪章实现”。
但是,工人阶级试图与资产阶级在互为目的的关系中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努力,只是幻想和一厢情愿。因为互为目的的关系是以功利为基础的,即工人阶级所希望的是,与资产阶级形成主体-物(客体)-主体的关系,我为你创造利润,你给予我应有的报酬和权利,通过物的中介形成平等关系。而资产阶级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必然通过占有资本而拥有的统治地位,将工人阶级客体化、物化和对象化,变成他们牟取利润的手段和工具。
晚期宪章派诗歌中的工人阶级,再也不满足于政治改革,发出了社会改革的呼声,希望通过埋葬不合理世界求得自身的解放,成为了“自为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发展到了使对象主体化,朝着适合于自身方向发展,自觉改造对象的高度。
1847年还在为“人民宪章”的实现而呐喊的琼斯,在1848年发表的《人民之歌》中,已经抛弃了对统治者的幻想,呼吁诗人们“为人民歌唱——为工人歌唱”,呼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彻底打倒贪婪的权贵人物和黄金大王,不让其统治“再延续片刻”。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因为第三次请愿活动的失败,使以琼斯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认识到,仅以“人民宪章”作为纲领是不够的,必须“从单纯政治改革的思想走向社会革命”[5]38,消灭成为一切剥削根源的社会制度。
尽管在此之前,宪章派已经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利益上的不可调和。但由于工人阶级还缺乏自觉改造对象的主体性,所以斗争一直停留在政治改革阶段。但统治阶级通过残酷手段镇压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使宪章运动处于低潮。这是工人阶级幻想在互为目的的关系中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必然结果,因为互为目的的关系必然转化为互为手段的关系,而必然导致两个阶级更大的对立、对抗和冲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同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以哈尼、琼斯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具有了使对象主体化的倾向。琼斯就说:“我再也不向政府呼吁!我要着重指出,我们不能通过游行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让每个人拿起枪来准备战斗,那时我就能向你们保证,宪章很快就会被宣布为国家法律。”[6]在1851年宪章派国民大会颁布的新纲领中,已经将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
这一时期的诗歌大约80首左右。因为群众性的宪章运动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陷入低潮,大多数诗人隐退了,继续创作的仅限于琼斯、林顿、马西、尼古尔斯、查德威克、柯尔、艾尔弗雷德、罗布森等七八个诗人。尽管如此,但这一时期的创作仍体现出工人阶级对自身主体性的挖掘。而且因为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工人投机分子的退出,使工人阶级队伍更纯洁,阶级意识更强,主体性更自觉,不仅反对资本,而且要改造世界。
晚期诗歌在内容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为社会革命提供依据的诗歌。工人阶级之所以要进行社会革命,是因为他们已经从政治改革的迷魂汤中觉醒,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凶残。比如尼古尔斯的《国会》(1851年),讽刺那些国会议员只关心地主的权利、工厂主的利润,而对工人阶级的利益避而不提,对工人的死活置之不理。在《和平世纪》(1848年)中,琼斯通过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嘲讽英国政治改革的欺骗性。在长诗《新世界》(1850年)中,琼斯虚构了一个叫印度斯坦的地方。在那里,资产阶级利用人民取得胜利后独吞胜利果实,并用改革的谎言欺骗人民。当人民认清了他们的本质起来反抗时,他们原形毕露,进行残酷镇压。很显然,诗歌是在影射英国资产阶级的虚伪与凶残。他还通过印度斯坦人民的觉醒,说明人民的主体意识是怎样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同时说明,如果不进行社会改革,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在《自由神》(1851年)中,琼斯通过对为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们的追思,控诉“压迫者的滔天大罪”。林顿的组诗《现代碑铭数题》(1851年),甚至用墓志铭的方式,为资产阶级及其帮凶唱挽歌。统治阶级对人民欺骗与镇压,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
二是表达进行社会革命决心的诗歌。琼斯被捕后,敌人将他关在单人牢房中度过了孤寂的两年,但他没有屈服,相反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在《沉寂的牢房》(1851年)中,他写到:
从来不打算卑鄙地后退,
或者做个不肖种;
只要我心中脉息在跳动,
勇敢自豪向前冲。
监禁一解除,他们会发现
我坚强而没有改变,
我不是恨哪一个,而是
为他们全体感到可怜。
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他再次表白:“当我被捕入狱时,我是一个宪章派,但当我出狱时,我成为了一个共和主义者……我曾经因为说要让绿色的旗帜飘扬在唐宁街的上空而被捕,但被捕后我改变了我的颜色,我现在变成红色的了。”[5]113在《贱民之歌》(1852年)中,琼斯坚信只要“军号一旦吹鸣”,工人阶级就会伸出手,“击碎那狂妄君主的心”。在《未来之歌》(1852年)中,他鼓励同伴踏过统治者的宫殿,让他们“像玻璃一样破碎,灭亡”,把“新世界”的美好未来变成“今朝”。
在《人民的集结》(1851年)中,林顿将社会革命比做暴风雨的来临,那时候一个个工人如同“雪花”,“全都集齐、结成整体”,变成一场“雪崩”,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滚向统治者,摧毁统治者。在《出路》(1851年)中,林顿鼓励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不要畏缩”。哪怕是流血牺牲,也是为新世界的建设付出的应有的代价。
另外如查德威克《暴风雨即将来临》,(1850年)、马西的《他们死了》(1850年)等,都是激励工人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诗歌。前者将工人阶级的革命比做暴风雨,它是自由的闪电,是愤怒的咆哮,它将使奴役的大地苏醒。觉醒的工人阶级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将骄傲的挺立,去审判统治者的罪行,而专制魔王将在他们的面前瑟瑟发抖。后者通过歌颂1848年革命中牺牲的烈士,鼓励工人阶级在烈士们敲响的战鼓声中,在红色曙光照耀下前进,去迎接专制魔王的末日。
三是设想与建构未来社会的诗歌。社会革命不仅包括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还要建构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诗人们进行了憧憬与展望。罗布森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到来》中,为工人阶级憧憬了一个没有失业,没有饥饿,没有剥削的“伟大的时代”。艾尔弗雷德在《红色的旗帜》中,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公平正义的共和国蓝图。琼斯向人民描绘的“新世界”,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在那里人们悠闲地生活,传统得到延续,科学技术用来为人类造福,没有了纷争,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幸福。美好的未来世界在向人们召唤,从而激发起工人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信心与勇气。
晚期诗歌中的工人阶级,主体性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自觉地改造世界,成为了“自为的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离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还有很大距离。无产阶级是代表全人类的,也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但宪章派诗歌中的工人阶级,所争取的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权利。由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被资产阶级窃取,用来剥削工人阶级,而且从自由贸易中获取利益的也是资产阶级,所以工人阶级对大工业生产以及自由贸易都抱有抵制态度。这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所应该有的态度,也就是说,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盘否定,没有将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历史过程的总体来认识。既然这样,它就不可能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同时它对于社会革命的内容和方法都缺乏明确的概念,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也是抽象的,还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
尽管如此,但宪章派诗歌作为工业革命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合的产物,通过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挖掘,参与了新的世界体系的生成。
[参 考 文 献]
[1] 魏小萍.主体性涵义辨析[J].哲学研究,1998(2):22.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61.
[3] Mikes Sanders.The Poetry of Chartism:Aestheics,Politics,History[M].London.Cambridge UP,2009:1.
[4] 沈汉.英国宪章运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178.
[5] John Saville.Ernest Jones:Chartist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rnest Jones[M].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52.
[6] 库捷尔.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M].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7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