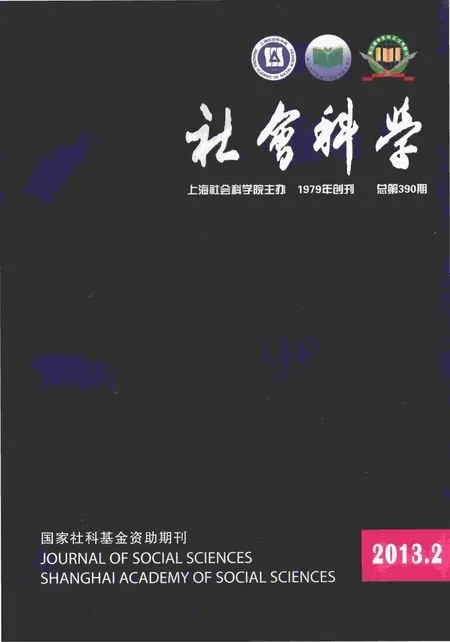“心存即为乡”:清代朝鲜使者对“高丽铺”历史的构建
[韩]黄普基
明清时期朝鲜使者入山海关后,经永平府、丰润县、玉田县等地,最后到达北京。明清两朝对朝鲜使者使行路线有严格的规定,所以朝鲜使者年年记载着同样的地名,沿途看到的也是旧样风景①明时期的朝鲜贡道:自鸭绿江起,历辽阳、广宁,入山海关,达京师。与明代相比,清代朝鲜贡道在辽宁地区有所变化,但整体来看其变化不大,尤其是在河北地区,基本上一仍其旧。。在朝鲜使者的文献里,时常出现丰润县西的一个村落——高丽铺 (有时写作高丽堡、高丽村)。朝鲜使者之所以常常提到它,是因为“高丽”这样的地名自然而然地会引发朝鲜人对祖国的怀想。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使者们已不满足于借助“高丽铺”来寄托自己的怀乡之情,而是开始构建高丽铺的历史,并有意把构建出的历史记录下来,使之流传。
朝鲜使者为何要构建一个中国村落的历史?朝鲜使者刻意构建高丽铺历史的背后,又寄托了怎样的情感?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朝鲜“燕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阅读大量“燕行”文献后,发现不同时期朝鲜人对高丽铺历史的认知并不一致,而在一代代朝鲜使者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关于高丽铺历史的叙述日渐清晰。追寻高丽铺历史的构建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窥知几百年前奔波于朝贡路上之朝鲜使者的内心世界②如葛兆光《明烛无端为谁烧?——清代朝鲜贡使眼中的蓟州安、杨庙》(《书城》2006年第2期),从被朝鲜人的思想与想象所塑造出的蓟州安、杨庙的故事中发现朝鲜人对中国历史有另类的解释;《想象异域悲情》(《中国文化》第22期,2006年)探讨朝鲜人对于季文兰的想象被历史化的过程和原因;《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指出,在异国使者的想象中,茶园演出竟然成为在满清王朝中保存汉族历史记忆和衣冠文明的重要途径。此外,韩国方面:李春姬的《燕行诗与燕行心理变化考察》(《韩国语文学研究》第50辑,2008年)主要考察燕行过程中朝鲜使臣所关注的对象的变化过程。金敏镐《他者视线中的江南意象》(《中国语文论丛》第43集,2009年)分析了《燕行录》中所记载的朝鲜使者所见闻的江南意象,并将其与中国人的江南意象做了比较。《洪锡谟<皇城杂咏>小考:19世纪朝鲜使臣眼中的燕京形象》(《语文论集》58,2008年)探讨当时朝鲜人亲见的燕京的风光意象如何影响了他对清朝的认同。。
一、“兹铺种落本吾鲜”:朝鲜移民建村说法的构建
高丽铺,清代地处北直隶遵化州玉田县、丰润县之间,今天隶属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由于规模太小,中国文献很少提及高丽铺,在清代编修的《丰润县志》里,仅仅记载了高丽铺的名字和方位,再无更多的着墨①《丰润县志》卷一仓储,清光绪十七年修,成文出版社1921年铅字重印本,第163页。。高丽铺虽然是个小村庄,却是明清驿传系统的一部分②“高丽铺”中的“铺”即急递铺。明清时代的急递铺负责传递中央各部院与各省,以及各省府州县之间的日常公文。它们密布于各省的府州县之间,铺的间距一般为15里。,也是朝鲜朝贡使团的必经之地。万历二十三年 (1597),奉命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郑昆寿便对高丽铺有所记录:
初三日……夕到玉田止宿。初四日,发行到高丽铺中火,夕到丰润止宿。③郑昆寿:《栢谷集》卷3《赴京日录》十一月初三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4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50页。
由于高丽铺地处丰润、玉田两县之间的驿路上,往往是使团驻休之所,因而在朝鲜“燕行”文献中留下许多有关它的记载。万历二十二年 (1596)春天,一个叫李好闵的朝鲜使者,途经高丽铺,赋诗一首:
客渡还乡河,来入高丽铺。青春喜还乡,既喜翻自虞。驻马问童子,此是吾乡无?童子笑不应,谓我真狂奴。客是朝鲜人,是处近燕都。四海虽一家,谓乡宁非愚。我闻亦不信,怒目张虬须。高丽我国名,还乡指吾徒。若说非我乡,此名胡为乎?春是故园色,柳亦吾家株。况人生世间,身外无他图。方神游太廓,身亦空皮躯。此身亦非私,顾此闲堂区。有室我入处,有衣我曳娄。心存即为乡,此名知不诬……④李好闵:《五峰集》卷6《燕行录》诗五言古诗渡还乡河过高丽铺,载《韩国文集丛刊》第5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08页。
李好闵见到高丽铺,引发了对故乡的怀思。高丽铺中的“高丽”是什么意思,暂时还不清楚,不过李好闵显然把“高丽”与自己的家乡联系起来,还半开玩笑地问当地童子“此是吾乡无”?结果被嘲笑为“狂奴”。童子解释道:“客是朝鲜人,是处近燕都,四海虽一家,谓乡宁非愚。”在童子看来,李好闵把高丽铺认作家乡纯属一厢情愿。对此李好闵只有坚持说:“高丽我国名,还乡指吾徒,若说非我乡,此名胡为乎?”面对如此固执的朝鲜人,童子也无可奈何,只能“三揖耳趍隅”。
到了顺治二年 (1645),即满清入关的第二年,明清易代的混乱尚未结束,而朝鲜使团的朝贡仍在继续。这时朝鲜人见到的是“丰润、玉田是残邑”、“炮楼之火,达夜不止”的局面,当晚他们只能“宿城西村树下”⑤成以性:《溪西逸稿》卷1《燕行日记》乙酉五月十八日,载《韩国文集丛刊 (续)》第26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版,第91页。。但朝鲜使者成以性仍然记录下高丽铺的情况:
山海关之内,得见田野中荷锄成群者,而皆是黍稷菽麦。沿道数千里之行,水田始见于此。流传此间有高丽村,水田乃丽人之所耕作,因遂不废,未知此言果信然乎。⑥成以性:《溪西逸稿》卷1《燕行日记》乙酉五月十八日,载《韩国文集丛刊 (续)》第26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版,第91页。
这里提到高丽铺一带的水田,“沿道数千里之行,水田始见于此”。中国北方以旱作为主,很少见到水田,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水田,令朝鲜使者感到非常惊奇。成以性记录下当地人的一种说法,“水田乃丽人之所耕作,因遂不废”。朝鲜半岛流行稻作,因而有了朝鲜人经营水田的说法,但成以性对此持怀疑态度—— “未知此言果信然乎”?
顺治十三年 (1656),河北地区的局势已趋于稳定。当年的朝鲜使团中,有一位引人注意的人物——朝鲜王子麟坪大君。他生前多次参加使行,几次经过高丽铺,因而能敏锐地察觉到该村的变化:
经高丽堡,地是村非,城南野有千顷水田。⑦麟坪大君:《燕途纪行》九月十八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31页。规模“千顷”可能有夸张成分,但可以想见其规模不小。与成以性一样,高丽铺一带的水田也给麟坪大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麟坪大君从1650年开始赴京,前后八次经过该村,唯有这次特地提到高丽铺广阔的水田,似乎可以推测,顺治年间高丽铺一带的水田规模比过去有所增大。
朝鲜朝贡使行依旧继续,而到过高丽铺的朝鲜使者不断地强调当地经营水田的信息。到了康熙二十二年 (1683),途经此地的金锡胄除了像他的前任一样,提到高丽铺“下湿且沃饶,宜于秔稻”之外,还提到了村名的由来:“居民皆以东国水耕之法为农,庄之得名以此。”①金锡胄:《息庵遗稿》卷6《梼椒录》上次副使韵,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207页。
之前的使者虽然提到高丽铺的水田,但还没有说水田与朝鲜有什么关系。只有成以性记录了当地“水田乃丽人之所耕作”的说法,但他对此还持怀疑态度。可是在金锡胄这里,高丽铺水田营作源自朝鲜一说则俨然成了事实,而这一说法也成为高丽铺得名的依据。这时的水田已经成为联系朝鲜和高丽铺的重要一环,水田与村落的得名开始成为一套解释系统,并在朝鲜使者的心目中得到强化。这意味着,使者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从“高丽”这一地名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而是要建立高丽铺与故乡之间的联系。此后,高丽铺因朝鲜而得名的说法演变成“历史事实”,在燕行使者中代代相传。这是“高丽铺”在朝鲜使者历史记忆构建过程中相当关键的一步。
朝鲜使者到高丽铺之前,一路上经过“清汉杂处混淆难别”的胡化地区,当地的景象常令他们感到“伤心虏俗移人甚”(有朝鲜使者曾记载,由于朝鲜人“坚守”中华文化,身着明代衣冠,致使该地百姓“怪我衣冠眼见生”②金锡胄:《息庵遗稿》卷6《梼椒录》上次副使韵,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4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207页。,即是一例)。一路上,朝鲜使者碰到的都是“蛮夷之人”,而只有走到高丽铺才得到些许慰藉。因为这里不仅有“高丽”的村号,更有他们熟悉的水田。面对如此亲切的场景,朝鲜使者都不愿相信高丽铺与朝鲜毫无关联,而是想方设法地寻找它与朝鲜之间的联系。通过水田建立高丽铺与朝鲜的关联,正是朝鲜使者上述心态的具体表现。
水田被朝鲜使者认为是高丽铺与朝鲜存在渊源关系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冀东地区,水田并不是高丽铺特有的景观。清朝建立以后,朝廷一直在冀东沿海沼泽地区推广营田水利事业。到了雍正年间,冀东的水利营田取得了显著成绩。如雍正四年,高丽铺、卢各庄营治稻田十六余顷③《(雍正)畿辅通志》卷46,水利营田,第5页。。而雍正五年八月,允祥疏报京东滦州、蓟州、丰润、平谷、宝坻、玉田等6州县,营成稻田335顷④《清世宗实录》卷60,转引自严兰绅主编《河北通史》清朝上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99页。。可见在冀东的很多地区都存在水田,只不过在朝鲜使团的使行路线上,只有高丽铺这一处水田而已。对此,朝鲜使者毫不知情。
朝鲜使者坚信,高丽铺的水田源自朝鲜。但这样的农业营作方式又是如何从朝鲜传到河北的呢?这是朝鲜使者在构建高丽铺历史的过程中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康熙三十六年 (1697),途经高丽铺的朝鲜使者崔锡鼎赋诗曰:
兹铺种落本吾鲜,抚迹伤时一戚然。关内旧为华夏土,周余今带犬戎膻。家家折柳樊蔬圃,岸岸疏渠灌稻田。重是店名存故俗,东槎此日意还牵。⑤崔锡鼎:《明谷集》卷3诗椒余录过高丽堡,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5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473页。
崔锡鼎给出了答案:高丽铺的村民都是朝鲜人的后代,是朝鲜移民把家乡的水田营作方式带到了这里。这样的解释,使得高丽铺的得名和当地水田的由来都变得顺理成章,朝鲜人对高丽铺历史的构建趋于合理,之前由朝鲜人构建的历史记忆被进一步固化为“历史事实”。
朝鲜使者把高丽铺的村民解释成朝鲜人的后代,除了能够圆满回答高丽铺的得名和水田的由来,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明清之际,由于满洲人的大量内徙,朝鲜使者使行路线上的辽东、冀东成为“胡化”严重的地区,这往往引发朝鲜人对中华文化沦丧的担忧,崔锡鼎“关内旧为华夏土,周余今带犬戎膻”的诗句便反映了这一心理。值得庆幸的是,高丽铺这个小村庄还保留着华夏故俗,成为在胡化严重的中华大地唯一未染“膻腥”的地方。而高丽铺的华夏故俗是因为朝鲜移民的缘故才得到保留。这时朝鲜使者对高丽铺乡土情结的认同,则进一步上升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
“高丽铺由朝鲜移民建立”的说法乃是源自朝鲜使者的刻意建构,但奇怪的是,这种说法似乎也能得到当地人的佐证。康熙五十一年 (1712),朝鲜使团又一次来到高丽铺,这时的高丽铺已非常繁荣,“村落颇富丽,村中有戏子阁,扁曰太平玉烛”①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二月十九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140页。。而使团成员崔德中记录下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有高丽铺的居民“自称高丽子孙矣”②崔德中:《燕行录》十二月二十三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85页。。这无疑是让朝鲜人非常兴奋的消息:连当地村民都自称是朝鲜后代,可见有关“高丽铺由朝鲜移民建立”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所以崔德中要把这件事特地记录下来,作为凭证。
那么,原本与朝鲜无关的高丽铺村民为何会自称“高丽子孙”呢?五十多年后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朝鲜使者洪大容的一段记述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这一现象的绝佳注脚:
高丽堡在丰润县西二十里。村前有水田,虽甚粗芜,犹是东国制作,关内外所未有也。有小米糕,杂以枣肉,亦如东国蒸饼。数十年以前,堡人见我使,极其欢迎,享以酒食,自称高丽子孙。近因驿卒辈强讨酒肉、奸骗器物,不堪其苦,遂漠然不相接。或问其有高丽子孙者?则皆怒曰,有高丽祖公、无高丽子孙。③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8《湛轩燕记》沿路记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77页。
洪大容显然受到前任朝鲜使者记述的影响,看到水田便称是“东国制作”,看到小米糕便认作“东国蒸饼”。进入村落,洪大容迫不及待地询问有关“高丽子孙”的下落,得到的回答却令他非常意外,“有高丽祖公、无高丽子孙”。从洪大容的描述不难获知,数十年前的高丽铺村民看到规模庞大的朝鲜使团到来,一定认为这是“牟利”的绝佳机会,故主动接近朝鲜使者。而“自称高丽子孙”无疑会拉近当地村民与朝鲜使者的关系。但随着接触的增多,朝鲜使团不但没能给村民带来实惠,反而扰乱了他们的生活。既然借助“高丽子孙”迎合朝鲜使者已无必要,于是出现了“有高丽祖公、无高丽子孙”的说辞。
虽然高丽铺村民“无高丽子孙”的回应,给洪大容这样坚信传统历史叙述的朝鲜人以极大打击,但朝鲜使者们似乎更愿意相信高丽铺村民就是朝鲜移民的后代,只是因为历史久远和风俗变迁,他们自己淡忘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一代代朝鲜使者来到高丽铺,都会刻意寻找高丽铺与朝鲜的共同点,并将之放大,作为朝鲜风俗遗留当地的佐证。如“第锄制如我国北道锄制”、“种谷耕田除草之法,一如我北道矣”④崔德中:《燕行录》十二月二十三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第86页。;“垣屋制度,颇似我国平安道”⑤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6《入燕记》上五月初十一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15页。;“独此地水种,其饼饴之物……多本国风”⑥朴趾源:《燕岩集》卷12《热河日记》秋七月二十八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首尔)景仁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在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下,朝鲜使者关于高丽铺历史的构建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他们的思想世界里得到强化。也许,当地村民是否承认自己是朝鲜人后代已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高丽铺寄托了远道而来的朝鲜使者的思乡情怀和文化认同。高丽铺与朝鲜使者已结下不解之缘,在朝鲜人的心目中,高丽铺成为“中原中的朝鲜”、“异域中的故乡”。
二、“东民俘虏成乡聚”:对朝鲜移民来源的构建
清代康熙年间,高丽铺乃由朝鲜移民建立的说法已得到朝鲜使者们的普遍认同。但这样的历史叙述仍不完整,接下来亟待解释的问题是,创建高丽铺的朝鲜移民是在何时,又是因何种原因迁入当地的?康熙四十三年 (1704),李颐命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他在诗作中称:
乐浪辽疆汉代移,隋唐师旅济丽时。东民俘虏成乡聚,燕土风尘化羯夷。水耨犹存箕壤俗,世居那识青丘悲。人情久客真堪笑,里号闻来喜曷为。①李颐命:《疎斋集》卷1《燕行诗》高丽堡次副使韵,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7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8年版,第65页。
李颐命除了像他的前任一样认定高丽铺的习俗保留了朝鲜遗风之外,还首次提到了高丽铺朝鲜移民的来源—— “东民俘虏成乡聚”,并感叹当地村民忘记了这段历史,“人情久客真堪笑,里号闻来喜曷为”。那么村民们忘却的又是怎样的历史呢?乾隆四十三年 (1778),朝鲜使者李德懋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高丽堡距城十余里,村家不满数十,萧条零星。垣屋制度颇似我国平安道。有水田,澄明堪映,二千里来初见,可以醒眼。此盖丙丁之乱,被掳留此,因成风俗。自此至于玉田,野多青林,连绵不绝,人烟相望。②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6《入燕记》上五月初十一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215页。
李德懋提到,建立高丽铺的朝鲜移民是在“丙丁之乱”中被掳掠至此的。所谓“丙丁之乱”是指后金皇太极于1627年(“丁卯胡乱”)和1637年(“丙子胡乱”)对朝鲜的两次入侵。需要注意的是,李德懋对这种战乱掳民建立高丽铺的说法还只是推测,所以他用了“盖”字来开始叙述。
不过仅仅两年之后,当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来到高丽铺时,有关丙子掳人建立高丽铺的说法已经成了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他对高丽铺建村的描述是“丁丑被掳人,自成一村”③朴趾源:《燕岩集》卷12《热河日记》秋七月二十八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第195页。。这里,朴趾源明确记载高丽铺始建于丁丑年,即“丙子胡乱”的第二年。为了证明自己记载的真实性,朴趾源还补充了一些细节,“妇女亦不回避,语到古国,多有流涕者”④朴趾源:《燕岩集》卷12《热河日记》秋七月二十八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第195页。。这样的场面,足够刺激朝鲜读者的情感。其实,朴趾源的说法并不可信,通过前文引述李好闵的记述可知,至迟万历二十二年就已经存在高丽铺了,而这时距“丙子胡乱”的发生还有四十余年。朝鲜使者对高丽铺建村年代的构建过程,再一次验证了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历史细节往往愈后愈明,这正是后人集体加工的结果。
高丽铺的历史叙述模式到这个时候已基本建构完成,以后每一位路过高丽铺的朝鲜使者都要对高丽铺的历史抒发一番悯怀之情。如乾隆四十九年 (1784)金熤在路经高丽铺时写道 (并附诗一首):
高丽村在丰润县界。丙丁之乱,东民被俘者聚居于此,名其居曰高丽村云。
蓟北三千客路迟,数家篱落柳垂垂。荒村不改高丽号,遗恨应传故国思。地阅海桑千古感,人同淮橘百年悲。可怜东俗今犹在,白水耕田墓有碑。
自栅外至燕城无水田、无坟墓之制;独高丽村有水田种禾,且或有竖石之墓。⑤金熤:《竹下集》卷4诗高丽村,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4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93页。
除了村名还叫“高丽”,当地已很难寻见朝鲜风貌,这让诗人发出“淮橘”的感慨。不过与前任使者相比,金熤发现高丽铺的墓制与朝鲜类似,在他看来这是高丽铺村民源出朝鲜的又一力证。
乾隆五十八年 (1793),金正中经过高丽铺,看到数十村民“持黄粱饼,环拥马前,齐声买饼”⑥金正中:《燕行录》十二月十九日,载《燕行录选集》第6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164页。,他想到这些村民本来是朝鲜人,现在却变成了“胡人”⑦金正中:《燕行录》十二月十九日,载《燕行录选集》第6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164页。,只知道向朝鲜同胞卖“饼”。这让金正中非常伤感,不禁感慨:
使汝祖无流俘之患,则冠带物未犹是我辈中人。一自被拘之后,后裔皆鸟言兽面,可哀也。⑧金正中:《燕行录》十二月十九日,载《燕行录选集》第6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164页。
次年,洪良浩以冬至兼谢恩正使的身份出使北京,在经过高丽铺时题诗一首:
到高丽堡,招问父老,无人识古事者。怅然而题:
车盖曾经十载前,藩篱阡陌尚依然。篝灯女织扶桑茧,野水牛耕乐浪田。秦汉衣冠今几代,朱陈嫁娶不知年。村人莫恨山河隔,红日箕躔共一天。①洪良浩:《耳溪集》卷7诗燕云续咏到高丽堡,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41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127页。
洪良浩本想找高丽铺的朝鲜后裔叙旧,结果竟“无人识古事者”,不禁气愤地责怪当地村民只知道过浑浑噩噩的生活,忘记了本民族的历史。
半个世纪后的道光二十六年 (1846),进贺兼谢恩使正使朴永元赴燕京途中经过高丽铺,吟诗并记:
圻封千里足耕桑,一色平畴大麦黄。数亩稻田高丽店,果然山水似吾乡。
高丽堡,在丰润地方。丁丑我国被虏人,自沈阳徙居,此自成一村,故名。而高丽人已徙山西,今无余者云。②朴永元:《梧墅集》册4燕槎录诗高丽店,载《韩国文集丛刊》第30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第284页。
这时的高丽铺只有山水与朝鲜类似,而当地村民看不出与朝鲜人有任何关系,对此朴永元只能推测“高丽人已徙山西,今无余者”。
经过一代代朝鲜使者的反复吟咏,高丽铺因“丙丁之乱”而创建的说法变成了“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成为所有朝鲜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写到这里,想必大家还心存疑问:为何朝鲜使者总是执着地相信高丽铺村民就是“丁丑朝鲜掳人”的后代呢?笔者认为,这与明清之际朝鲜两次被后金攻陷亡国的历史有关。在“丁卯胡乱”、“丙子胡乱”中,大量朝鲜人被掳掠到中国,过着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这成为整个朝鲜民族的苦难记忆。这段历史在“燕行”文献中同样有所反映。顺治二年,成以性在辽东见到:
二十六日戊寅晴留,凤林大君行中赎得被掳数十人。自松站以后,家家皆有我国人,见吾等之行,奔走来见,问其故土消息。路上相逢者,亦不知其数。虽素昧平生,必喜色相看。自道其乡里亲戚,眷恋彷徨而不能去。其被虏多少怀土情事,从可想矣。归途永隔,无望生还;一闻赎还之奇,人皆云集仰望。而衙门勒定价本,只赎若干,余皆饮泣而散。③成以性:《溪西逸稿》卷1《燕行日记》乙酉四月二十六日,载《韩国文集丛刊 (续)》第26册,第86-87页。
此时“丙子胡乱”刚刚结束,辽东几乎所有的清人家庭都有朝鲜家丁、奴隶,他们都是在“丙子胡乱”中被掳掠到辽东的。再来看另一个场面:
有一老妪,乃朝鲜人也。其父母丙子来此,而居生壮洞。能解合酱,卖为生理;能行东语。可叹。④崔德中:《燕行录》十二月十五日,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第81页。
康熙五十一年,崔德中在使行过程中遇到一位朝鲜同胞,她的父母是在“丙子胡乱”时被掠到中国的,这些人正是战乱的受害者。
“丙子胡乱”过后,在中国辽东到处都能看到掠自朝鲜的流民。这里以辽阳附近的“高丽丛”为例。高丽丛是“丙子胡乱”后朝鲜人在辽东定居的村子。“高丽村儿童幼作高丽语;及长,衣裳冠服,多用高丽云。”⑤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出疆录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载《燕行录选集》第10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36页。清初,在辽东还能见到许多类似的朝鲜流人聚居村落,但随着文化的融合和人口的流动,这样的村落逐渐消失。而“丙子胡乱”留给朝鲜民族的苦难记忆还在朝鲜使者中世代流传,他们需要一个载体来寄托自己对那段苦难历史的哀思,于是被认为是朝鲜移民创建的高丽铺便成为朝鲜使者抒发这种哀思情怀的最佳对象。
朝鲜使者其实是在自身情感的驱使下去构建高丽铺的历史,而他们所构建出的历史因为能够承载朝鲜人的思乡之情、亡国之痛而在使者中迅速流行。这时历史的真实已逐渐褪去,而民族情绪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却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朝鲜使者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构建出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并在一代代朝鲜使者中不断强化。甚至他们开始埋怨高丽铺的村民淡忘了自己的历史,而他们却在帮助当地村民传承着这个村落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高丽铺村民与“历史”渐行渐远,而朝鲜使者却与“历史”渐行渐近。
三、“河且还乡我独不”:还乡河的变迁与高丽铺的兴衰
以上笔者通过分析指出,朝鲜使者以高丽铺地名中的“高丽”为基础,逐渐演绎出“丙子胡乱”被掳朝鲜人创建高丽铺的历史叙述。这样的历史其实源于朝鲜人的构建,而非事实。既然以往有关高丽铺历史的叙述并不可信,那高丽铺的真实历史又是如何呢?
笔者认为,高丽铺的出现、发展和衰落,与它周边的一条河流——还乡河密不可分。还乡河发源于燕山山脉东段,主要流经今唐山市、天津市,注入渤海。今天,还乡河是一条几近干涸的河流,但在历史上它的规模曾非常可观。万历二年 (1574),朝鲜使团还需要“舟渡还乡河”①赵宪:《重峰集》卷10《朝天日记》七月二十七日,载《韩国文集丛刊》第54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367页。。康熙五十一年 (1712)农历十二月,朝鲜人金昌业记述还乡河“水颇大,几如浑河,流迅不冰”②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十二月二十三日,载《燕行录选集》第4辑,第60页。。农历十二月,河北的河流几乎都会封冻,而还乡河却“流迅不冰”,足见其流量之大、流速之快。金昌业还把还乡河与浑河类比。浑河是辽东境内规模较大的河流,“几如浑河”的描述可以反映还乡河规模之大。
河北地区年降水量在500-600毫米,而在还乡河流域却高达800毫米,而且都集中在夏天。可以想见,集中的降水极易造成还乡河的泛滥和迁徙。这在中国文献中有所记录,如《清经世文编》提到:“还乡河源非甚巨,但近自北山而下,夏秋雨集,诸山水潦一时迸注,而鸦鸿桥以下,河窄流纡不能骤,则溢出为田畴害,东决则淹丰润,西决则淹玉田。”③《清经世文编》卷107《工政》,载《清代经世文全编》第11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又《丰润县志》记载:“(还乡河)每于伏秋之际,积雨未歇,怒流已至,激矢建瓴,悉归并于二大渠,有不啮岸崩堤冲突田庐者哉。”④《丰润县志》卷一,光绪十七年刻本,第14页。由于还乡河泛滥无常,其河道也经常改变。当地志书中常有官府整治还乡河河道的记载。而“燕行”文献里的里程记录,也保留了还乡河河道变迁的印迹。由于朝鲜使团每年经过同样的路线,因此他们有关还乡河里程的纪录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还乡河变迁的重要依据。根据康熙五十一年崔德中的记载,还乡河距丰润县四里⑤崔德中:《燕行录》路程记自汉阳至燕京,载《燕行录选集》第3辑,第68页。;而到了嘉庆八年 (1803),还乡河则“在丰润县西十余里”⑥《蓟山纪程》卷5复路附录山川,载《燕行录选集》第8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127页。。在这九十年里,还乡河的河道向西移动了约十里,这显然与河流泛滥改道有关。而还乡河的泛滥和改道,都会对附近的高丽铺产生影响。
检索“燕行”文献,能够找到关于高丽铺的最早记载是在明嘉靖十八年 (1539),当时一个叫权橃的朝鲜使者留下了非常关键的记录:
十四日,晴。早发涉还乡河,过高丽铺;夕至玉田县阳樊驿。高丽铺,问之未详。⑦权橃:《冲斋集》卷7《朝天录》十月,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44页。
根据上述记载,当时的高丽铺显然是一个刚刚出现的新地名,所以权橃感到非常新奇,还特地去询问有关高丽铺的情况,但结果是“问之未详”。
之所以说高丽铺是当时出现的新地名,是因为在两年前的朝鲜使团使行记录中,还见不到关于高丽铺的记载。嘉靖十六年,丁焕详细记录了玉田县、丰润县之间驿道上的地名:
十六日壬戌……出 (玉田)县之东城。又过汉种玉、雍伯杨公神道碑、双桥儿河、沙流河铺、古永济驿、还乡河,至义丰驿。①丁焕:《桧山集》卷2《朝天录》十月,载《韩国文集丛刊 (续)》第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年版,第225-226页。
这里提到的义丰驿设置于丰润县城。在当时的玉田县、丰润县之间有“双桥儿河、沙流河铺、古永济驿、还乡河”,甚至连“汉种玉、雍伯杨公神道碑”这样的小地名也被记录在案,而唯独不见高丽铺,可见当时高丽铺还不存在。
总之,检索中朝文献,有关“高丽铺”的最早记录是在嘉靖十八年。该年十月,朝鲜使者途经“高丽铺”,留下了记录,然后第一次询问其来历。而在两年前的十月,朝鲜使团途经该地,还没有提到“高丽铺”。“高丽铺”的建村,应当就在嘉靖十六年 (1537)十月到嘉靖十八年 (1539)的十月之间。
嘉靖年间,高丽铺又是因何而建村的呢?笔者认为这与嘉靖十六年还乡河全流域性的大洪水有关。嘉靖十六年夏,冀东地区遭受特大暴雨,暴雨持续数日,直接导致还乡河流域严重的洪涝灾害,此事在中国方志中有零星反映②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7-1008页。。而“燕行”文献对这次大暴雨所导致的灾害后果有详细的记录。该年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丁焕记载,朝鲜使团在前往北京的途中抵达丰润县的义丰驿,得知“丰润以西,水潦犹涨,车路不通云”,因此“令李龟往见知县,讨舡只聚舣于还乡河”③丁焕:《桧山集》卷2《朝天录》八月,载《韩国文集丛刊 (续)》第2册,第212、212-213页。。朝鲜使团不得不改变使行路线,沿还乡河南下七十里,到达还乡河与泃河的汇合处,由此乘船西行。这时的还乡河流域已经变成“四极无际涯”的大湖。朝鲜使团“舡行所历,尽是村居,畎畴覆没之患,什倍三叉河矣”④丁焕:《桧山集》卷2《朝天录》八月,载《韩国文集丛刊 (续)》第2册,第212、212-213页。。他们向西舟行五十余里,再往西北沿着泃河舟行八十余里,最终到达三河县。从三河县开始“讨骑而出”,行走陆地。由于洪水泛滥连使行路线也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在整个明清时期极为罕见,当年洪水之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从朝鲜使者的记述可以看到,嘉靖十六年的大洪水对还乡河流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丰润、三河两县之间数十里范围内的村庄均被毁坏。结合两年后,高丽铺地名的突然出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嘉靖十六年还乡河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害中,还乡河流域原有的村镇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而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村庄被兴建起来,高丽铺应当就是这批新建村落中的一个。因此我们可以明确高丽铺的建立与还乡河流域嘉靖十七年、十八年的灾后重建有关,这才是高丽铺建村历史的开端。
高丽铺乃因还乡河而建,而高丽铺的发展兴衰同样与还乡河紧密相关。从朝鲜使者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明末清初的高丽铺非常繁荣,不仅水田面积广阔,而且村落也颇为壮观。康熙五十一年 (1712),金昌业记述高丽铺“村落颇富丽,村中有戏子阁”。在燕行录中,“戏子阁”只见于规模较大的村落。由此也可推想高丽铺之规模。不过,乾隆年间以后高丽铺开始呈现出衰败的景象。如乾隆四十三年 (1778),李德懋笔下的高丽铺已是“村家不满数十,萧条零星”,这与60年前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到了道光二十六年 (1846),朴永元见到的高丽铺则是“一色平畴大麦黄,数亩稻田高丽店”,连朝鲜人视作朝鲜文化象征的水田营作几乎也消失殆尽。这些变化其实都与还乡河有关。根据中国当地志书,高丽铺约在丰润县西十五里。而朝鲜“燕行文献”里程记录记载雍正年间以前还乡河约在丰润县西四里,则高丽铺距还乡河十余里。到了嘉庆年间,还乡河距丰润县十余里,显然这时的高丽铺就在还乡河沿岸。还乡河河道的变迁势必影响到高丽铺的农田水利环境,乾隆年间以后高丽铺村落的衰败和水田营作面积的减少应当与此有关。以往朝鲜使者曾颇为自责地认为,朝鲜使团成员对当地百姓的袭扰造成了高丽铺的人口流失和村落衰败,现在看来还乡河河道流徙所造成的环境变化才是导致高丽铺衰落的真正原因。
在梳理燕行文献时,笔者还注意到还乡河也时常成为朝鲜使者寄托思乡情怀的对象。如明代赴中国朝贡的金克成曾赋诗曰:“去国三千里,迢迢去更遥。江山非昨日,风雪认来朝。地有还乡水,杨垂赠别条。萍深漂不定,客意倍无聊。”①金克成:《忧亭集》卷2五言四律渡还乡河,载《韩国文集丛刊》第1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388页。还乡河的“还乡”一名,显然更容易引发身在异国的朝鲜使者的思乡之情。明朝末年,冀东地区还流传有宋徽宗因被俘途经还乡河的传说。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徐昌祚《燕山丛录》:
浭水源出崖儿口,经丰润、玉田,由运河入海。凡水皆自西而东,此水独西,故俗谓之还乡河。宋徽宗过河桥,驻马四顾,凄然曰:“过此渐近大漠,吾安得似此水还乡乎。”②徐昌祚:《燕山丛录》卷十四,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8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441页。
这段故事后因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采入《日下旧闻考》而广为流传。很快朝鲜使者便获知此事,并将其记录下来③无名:《蓟山纪程》卷1湾渡十二月二十二日,载《燕行录选集》第8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51页。。于是后来的朝鲜使者在途经还乡河时,除了照例抒发思乡之情外,还要对宋徽宗的悲惨遭遇感慨一番。在朝鲜使者心目中,宋徽宗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而宋徽宗被金人掳掠北行与朝鲜使者被迫向满清朝贡的遭遇又何其相似。“中华”与“悲情”是所有赴清朝贡的朝鲜使者共有的心态,宋徽宗的故事显然更能引起朝鲜士大夫的心理共鸣。一条还乡河,牵系起两批人,这边是不愿东去的宋徽宗,那边是不愿西去的朝鲜使者。“思乡”、“对中华的眷恋”、“对民族苦难的悲思”是这两批人的共同心理。嘉庆年间 (约1803年),一位朝鲜使者所作的诗歌便反映了朝鲜士大夫的这种心理:
万水朝宗失旧流,一源通入海西头。关山匹马临寒渡,河且还乡我独不?④无名:《蓟山纪程》卷1湾渡十二月二十二日,载《燕行录选集》第8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5年版,第51页。
清代朝鲜使者始终赋予“还乡河”特殊的感情。“高丽铺”成为朝鲜使者抒发悲情的主角时,“还乡河”便扮演着配角。“高丽铺”的悲情越浓,“还乡河”也会分担其更多的痛苦。多情的朝鲜人在“高丽铺”不停地寻找“同”,而无情的“高丽铺”却渐渐走向“异”。其实,在这个村子里根本不存在朝鲜人渴望的“同”,这不过是他们集体塑造出来的“历史记忆”。
即便“高丽铺”这个村子没有“同”,朝鲜人的使行还得继续下去。现在,一个朝鲜使者吟咏着“河且还乡我独不”的感慨,匆匆离开了高丽铺,而高丽铺却在那里一如既往地等待着明年要来的朝鲜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