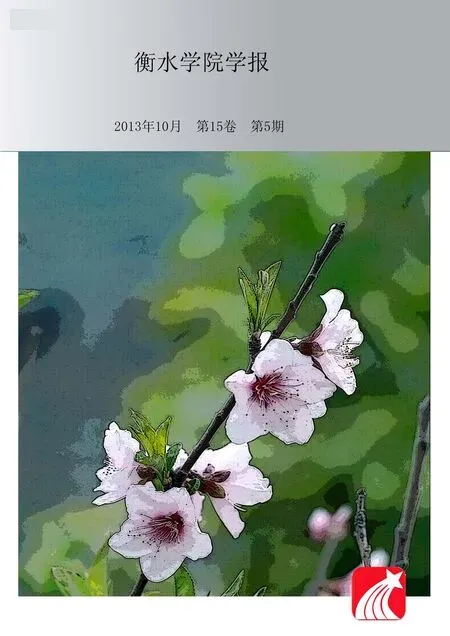董仲舒与秦汉初期体系化思想的建构
李祥俊
董仲舒与秦汉初期体系化思想的建构
李祥俊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体系化的思想。秦王朝统一中国前夕编撰的《吕氏春秋》,以“法天地”为原则,综合道家、阴阳家等建构起了一个天道论体系。秦汉初期,儒家学派虽然遭到“焚书坑儒”的打击而退居民间,但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经典注解之作,崇奉孔子“作新王”为万世立法,建构起了一个以儒为本兼融各家的王道论体系。董仲舒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将天道论、王道论体系合而为一,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体系化思想;《吕氏春秋》;《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天道论;王道论;大一统
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古代的宗法制贵族统治宣告结束,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以宗法等级社会为基础,政治上实行君主集权制度的大一统帝国巍然崛起。秦汉时期从总体上呈现出政治统一、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统一的时代需要统一的学术思想,而对体系化思想的建构成为时代思潮。秦王朝即将统一中国的前夜,权相吕不韦组织编写了《吕氏春秋》一书,接续先秦道家、阴阳家传统,整合诸子思想因素,初步建构起了一个服务新时代的天道论思想体系。儒家学派则从先秦诸子学向经学转型,依托《五经》传记的形式来建构自己的王道论思想体系。秦汉初期,上述两种分别以先秦道、儒两家为主导的体系化思想影响最大,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经过董仲舒的继承、改造、发展,终于形成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影响深远的“大一统”的思想体系。
一、法天地: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天道论体系
公元前241年,在秦相国吕不韦的主持下,由他的众多门客集体编撰了一部《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朝统一中国的前夕,按时间划分,它属于先秦学术,但它所代表的消解学派冲突、建立新官学的学术思潮,却显示了秦汉学术发展的真正开端。
《吕氏春秋》对于思想体系的建构是十分自觉的,它在肯定先秦诸子思想各有特色的基础上,十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反对诸子的自以为是,明确提出要建立服务于统一大帝国的一套思想体系。“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法天地”是《吕氏春秋》思想体系建构的根本理念,在作为全书序言的《序意》篇中,主编人吕不韦直接出面论述了效法天道的“法天地”原则:“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琐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在这段话里,吕不韦假托上古圣王,认为天地之道是最高的“规矩”,是人间是非善恶的评判依据,作为人间统治者的帝王,要把天地之道作为自己行政的依据。天地之道的实质内容就是自然、公平,所以,统治者应遵循自然的数和理,亦即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而不能凭一己之私去妄行,否则的话就会招致目盲、耳聋、心狂,“福日衰,灾日隆”。
《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法天地”,而“天地”的根本就是自然之道。在先秦时期,对天地自然之道论述最多最深的当属老子道家。道论是《吕氏春秋》一书的核心,它以道为化生万物的宇宙本原,成为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点:“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极,化于阴阳……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为创造万物之本原,所以宇宙万物从根本上说是一体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节律,与道同行则昌,逆道而行则亡。《吕氏春秋·十二纪》就以先秦道家学派的道本原论为基础,又融合阴阳家的天人感应、古今变化学说,以及儒、墨、名、法的政治伦理思想,建构了一个大一统的宇宙系统论,集中描述了一幅天人同道的和谐宇宙观。如果人类社会的统治者能够遵循天地万物的运化规律,调节个体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整个宇宙大系统就会呈现出和谐圆融,宇宙中的人和万物都能各适其性地生存、发展。反之,如果统治者违反自然之道,则会招致灾害,这就实现了从天道自然到王道政治的理论推衍。
《吕氏春秋》以源自老子道家的“道”作为理论体系的基点,而在道生万物的过程中,自然宇宙的时、空结构成为其理论体系组织结构的框架依据。《吕氏春秋》全书由3部分构成,即《八览》《六论》《十二纪》,现在的通行本一般是《十二纪》打头,而在司马迁《史记》的《自序》中有“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的话,另外,作为全书序言的《序意》篇附在《十二纪》之末,而古人书序是放在全书之末的,所以,原书的次序应该是八览、六论、十二纪。《览》分为八,显然是顺应空间的八方广延。《论》分为六,是顺应所谓上、下、左、右、前、后的六极,广泛讨论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问题。《纪》分为十二,则是顺应一年12个月的时间流转,而且在每《纪》的文章编排上都遵循季节的变化,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为主题。
在秦国即将统一中国的前夕,《吕氏春秋》建构了一个以“法天地”为主旨的天道自然论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以宇宙本源之道为理论基点,以自然时、空的演进作为理论体系的组织结构,从天道过渡到人道,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帝国提供“一代兴王之典礼也”。虽然由于吕不韦本人在政治上的失败,连带着《吕氏春秋》一书在秦、汉时期被埋没,但它所开创的“法天地”的天道论体系却影响深远,西汉文、景时期盛行的“黄老之学”,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聚集宾客数千人编撰的《淮南子》,以及“独尊儒术”前夜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在这一天道论体系的传统之中。但这种以自然无为的道家天道论来容纳仁义礼法等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体系,其内部的冲突是明显的,而它以自然时、空演进作为理论体系的组织结构也显得机械、呆板,内容和形式上的双重弊端使其难以成为秦汉思想的主流。
二、作新王: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王道论体系
在秦汉初期的思想领域,除了秦始皇与秦二世信奉法家学说之外,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吕氏春秋》《淮南子》和黄老之学,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老子道家思想为根本,建构起了以自然时、空演进为框架的天道论体系。与之同时,儒家学派也在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建构自身的思想体系。当时在朝的一些儒家学者,如陆贾、贾谊等,他们的思想来自于现实社会政治本身,推崇儒学的伦理政治主张,但在建构思想体系的时候,往往都要借用道家思想,自觉不自觉地以自然之道作为思想体系的建构基点。而真正担当起以儒学为根本来建构体系化思想任务的,则要归功于那些在野的儒家学者群体,他们以先秦儒家所传承的古代经书为依托,阐述其王道政治理想,最终成为汉武帝时期儒学独尊的真正的源头活水。
孔子儒学是先秦时期的显学,与其他诸子相比较,儒学的最大特色在对上古、三代元典文化的继承弘扬,史载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经典研究遂成为儒学的特色,成为儒家学派传播文化知识及其自身学派价值理想的媒介,在孔子以及孟子、荀子等大儒身后有一个庞大的经典研究群体存在。在儒学传承的经典中,《春秋》一经尤为特殊,它为孔子所“修”,即为孔子所“作”,而与其他四经以“述”为主大不相同。对于孔子“作”《春秋》的深意,孟子就有揭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发挥孟子的观点,提出孔子“素王”说、“王鲁”说等,认为在王室衰微、诸侯乱政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作新王”,以著作《春秋》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王道理想,为万世立法。
在战国末至秦汉初期,关于《春秋》经的研究在儒学中蔚为大观,而在西汉初期真正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和思想影响的首推《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传说源自孔子弟子子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春秋公羊传》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经典研究的传统,在秦汉初期儒学受到抑制的历史境遇中,薪火相传,为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政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建构思想体系上是十分自觉的,它以经典解说的形式,容纳先秦儒学的思想精髓,建构起了一个系统的王道论体系。王道是儒家学派在人伦政治上的一贯主张,司马迁转述董仲舒的话概括孔子作《春秋》之意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春秋》记录史实极为简略,但后人认为,孔子在整理、删定的过程中对史实的记载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根据《春秋》公羊学派的说法,孔子是承天命作《春秋》为汉代立法的,其中藏有“微言大义”,这个“微言大义”的实质就是孔子以《春秋》当一王之法。
《春秋公羊传》王道论体系的理论基点就是人伦政治的主宰者“王”,要用王来一统天下。《春秋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提出“大一统”,而“大一统”在这里是“大”“一统”的意思,即推崇以王为基点的天下一统。王不仅是人道的基点,同时也是天道的基点,所谓“王正月”。但《春秋公羊传》提出“王”指的是“文王”,即它并非完全以现实王者为基点,而是以理想中的圣王“文王”为王道政治的基点,从中也可以看出,《春秋公羊传》所推崇的王道是孔子儒家变化了的王道政治,是一种理想的政治,而非《春秋经》所记载的春秋时期维持现实人伦政治秩序的旧礼制,当然更不会是当时的种种“非礼”之制。
《春秋公羊传》阐述以王为基点的王道论体系,其基本内涵则是儒家学派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司马迁转述董仲舒的话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政治规范,既是孔子儒家对上古三代王道政治的继承,也是孔子借修《春秋》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它对维护传统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的稳定、有序是最有效的,而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托的《春秋》公羊学之所以在汉代盛行一时,原因即在此。
《春秋公羊传》王道论体系的实质内涵是尊王、大一统、君臣等级制度等,但在理论体系的组织结构上,它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作为框架依据的。它通过评价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事件来阐述自己的理论,以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王道政治为理论体系的归宿,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后代的《春秋》公羊学者总结出《春秋公羊传》中所阐发的体例、义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汉何休的“三科九旨”说,“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这种体例、义法就是《春秋公羊传》历史解释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王道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它所遵循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而不同于秦汉初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吕氏春秋》《淮南子》、黄老之学等所遵循的天道自然的时、空变化。
《春秋公羊传》开创的这种以儒为本,通过经典诠释所阐发的王道论体系在秦汉时期影响深远,是“独尊儒术”前夜儒学的最主要的思想创作,为董仲舒的儒家经学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这种思想体系强调“法古、法圣”,从历史中总结王道政治的根本,但关于王道政治的论述缺乏天道的依据,易限于历史相对主义,所以司马迁在记述伯夷、叔齐之事后感慨:“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另外,这种思想体系受制于儒家经典诠释的限制,往往湮没了其思想的体系性。
三、大一统:董仲舒对秦汉初期体系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董仲舒的主要活动年代在汉武帝时期,此时距西汉建国已经过了60余年的时间,距秦王朝开创大一统帝国则有了80余年的时间。而在学术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黄老之学逐渐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如何会通百家,尤其是汲取《吕氏春秋》《淮南子》、黄老之学的天道论体系,同时继承弘扬秦汉初期儒家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的王道论体系,建构起一个能够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帝国的学术思想体系,成为摆在董仲舒等儒家学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体系是在《春秋公羊传》和之前的《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下提出的,但就董仲舒思想体系而言,其内涵非《春秋公羊传》所能笼络。董仲舒的著述,主要有《春秋繁露》一书和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典籍之一,徐复观先生曾对《春秋繁露》一书的内容作了分类,认为由“《春秋》学”“天的哲学”以及其他一些关于礼制建设的内容等3部分组成。徐先生对《春秋繁露》一书内部结构所作的划分基本可信,但可再作斟酌,即第3部分杂论祭祀等礼制的内容实可归属于其“天的哲学”部分。所以,笔者的观点是,从《春秋繁露》来看,董仲舒的学术主要有两部分内容,即“《春秋》学”与“天的哲学”,前者来自于对之前《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儒家王道论体系的继承发展,后者则更多地汲取了《吕氏春秋》《淮南子》、黄老之学的天道论体系,两者融为一体,正显示出董仲舒对秦汉初期两大体系化思想潮流的综合创新。
董仲舒对于建构统一的思想体系是十分自觉的,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他答对汉武帝的策问,明确提出“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认为,思想统一了,才能有统一的法度,人民才能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样才能巩固和维持君主集权制度。在答对汉武帝的策问中,董仲舒还进一步阐述了大一统政治的实施措施和效果,他说:“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这里的一元论也就是大一统论,董仲舒提出元作为万物和人类的最高本原,元也就是天,以天统率王、以王统率天下,在宇宙上是统一于天、元,在政治上则是统一于王。所谓大一统,就是要使自王侯至于庶人的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的山川、万物统统置于天子的治理之下,大一统不仅是政治统一,也是社会秩序的统一、宇宙秩序的统一,这是大一统的最高境界。
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来自于他对《春秋经》《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发挥,但从其所处时代的思想背景来看,则显然也和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天道论体系的道本源论相关,也和当时流行的“太一”崇拜相关。“大一统”主要有两种意思,即“大”一统和“大一”统,前者是主张政治上以王为中心的统一,后者则是主张宇宙论上以太一为本源的统一。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道、一、元、气等概念都是对本源的指称,天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天既是宇宙的本源,又是王道的本源,天、王合一,尊天、法古合一,这从表面上看是向上古三代天命论和先秦儒家天道论的回归,而实质上则是对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天道论和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王道论的综合。董仲舒把儒家王道政治理论与秦汉杂家、新道家的天道自然论融合起来,所以班固才会评价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董仲舒从理论上论证了天道天意——圣人之意——儒家经典的内在统一性,他说:“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董仲舒把圣人所发天意而制的名号看作是真理的化身,是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所以,集中了圣人名号的《春秋》《诗》《书》《易》《礼》等古代传下来的书籍自然就成为人们必须学习、遵守的经典了。
以天道、王道大一统为基础,董仲舒以从天道到王道的推类作为其理论体系组织结构的框架依据。董仲舒将天道自然流行的时、空架构引入儒家王道论中,两者结合,一方面从历史事实的评价中见王道,另一方面则以阴阳五行为中介讲天人感应。董仲舒所谓的天人感应,主要是指人类的政治活动与具有神学意味的主宰之天的关系,他提出“天人同类”,认为天和人是同一类的,人是天生的,所以人像天,人副天数。人体有小骨节366,跟一年的日数相副。人体有大骨节12块,跟一年的月数相副。人的四肢与四季相副,人的五脏与五行相副。不仅在形质上天人同类,而且在性情上天人也同类,如天有阴阳、人有喜怒等。
以天人同类、天人感应为继承,董仲舒就天道自然与王道政治之间的联系作了进一步阐述。从天道、人道之间的静态联系上,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用天道的阴阳变化为王道政治作依据,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而从天道、王道之间的动态联系上,董仲舒提出“三统”论,把天道自然的流行与王道政治的演进合而为一。所谓三统指的是黑统、白统、赤统,指历代王朝在制度方面循环着采用黑、白、赤3种时尚。董仲舒的三统论是以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史实为基础的,他指出夏代以寅月为正月,以黑色为服色,代表正黑统;商代以丑月为正月,以白色为服色,代表正白统;周代以子月为正月,以赤色为服色,代表正赤统。董仲舒认为,在过去的历史中,夏、商、周三代递相更迭,其制度是这样循环变化的,以后王朝的制度变化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则,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按这三统的顺序展开的。董仲舒的“三统”论与战国末期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显然有一定的承续关系,但它不同于“五德终始说”的自然天道论,而是在其中融入了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体系,将秦汉初期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天道论体系与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王道论体系合而为一,真正达到了司马迁理想中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秦汉以降统一的大帝国构画了较为完备的世界图景,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董仲舒在阐述他的“大一统”理论体系时,更多地倾向于依托儒家经学的著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思想的体系化建构形成了遮蔽。而董仲舒在对秦汉初期体系化思想的综合创新中也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盲点,虽然他也有对人性的论述,但比较简单化,对以《大学》《中庸》为代表的心性论体系缺乏深入体会,表现出秦汉思想更多地面向外在世界的特色。可以说,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完成了“一天人”的理论体系建构,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儒家则更多地致力于“合内外”的理论体系建构。
四、余论:中国哲学内在体系的探索
哲学的体系对于哲学思想本身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哲学家在思考宇宙、人生、社会的终极问题时持有什么样的体系架构,往往会决定其讨论问题的基本思路,同样,哲学史家持有什么样的体系架构,往往也会决定其对研究对象的真切体会。但是,在近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受到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以及过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方法而非固定体系等观点的影响,很少关注哲学的体系建构问题。但哲学思想的展开是离不开哲学体系的,自觉地抛弃一种体系,实际上却总是不自觉地在使用另外一种体系而已。在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往往不自觉地使用西方哲学的体系架构,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或者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或者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来组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材料,这种用外在的体系架构来理解中国哲学是有问题的。
中国哲学有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但作为一门现代的学科,它却是在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在中、西哲学比较融通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意识到中国哲学有自身的话语模式、问题意识,但在对中国哲学自身体系架构的认识上还不明确,对于中、西哲学在体系架构上的异同少有论列。实际上,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学派一般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有一些体系化思想的专门性著作,如先秦时期道家的《庄子·杂篇·天下》和儒家《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东晋僧肇的《肇论》,唐代玄奘、窥基的《成唯识论》,南宋大儒朱熹的《近思录》等。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仅讨论的问题、使用的话语在变化,而且对于宇宙、人生、社会总体性理解的体系架构也在变,今天我们应该自觉地梳理出其体系架构的基本内涵及其演进历程、变化规律,真正站在中国哲学内在体系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
注释:
① 所谓体系化思想,指的是自觉地以一种核心理念为主导而形成的整体性思想学说,它往往以主导概念为思想基点,有稳定的且相互联系的内部组成结构,能够系统地回答宇宙、人生、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种体系化思想的创立者来说,有些是自觉的追求,而有些则是实际地体现在他们的著述之中。
②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序》徐彦疏引,戴宏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0页。
③《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新刊四书五经·春秋三传》,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3页。
④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5页。
[1] 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等.吕氏春秋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陈澔.礼记集说[M].北京:中国书店,1994:148.
[3] 杨伯峻.孟子译注[M].上海:中华书局,1960:155.
[4]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中华书局,1959.
[5]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1-192.
[6] 班固.汉书. [M].上海:中华书局,1962.
[7] 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Dong Zhong-sh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ic Though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LI Xiang-jun
(Research Center for Value and Culture,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Systemic thought often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hilosophy history in China. Lüshi Chunqiu, which was compiled before Qin Dynasty unified China, respected the principles of heaven and earth, merged Taoist school and Naturalist school and constructed a systematic principles of heaven. At the beginning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although Confucianism suffered from attack of “burning of books and burying of scholars”, the classic annotation represented byin which Confucius was worshiped as the new king for eternal legislation, based on Confucianism, merged other factions and constructed a systematic principles of king. Absorbing pervious thoughts, Dong Zhong-shu merged the principles of heaven and the principles of king together and constructed a unified systemic thought of oneness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It had profound influence at that time and later.
systemic thought;iu;;Dong Zhong-shu; principles of heaven; principles of king; unification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10.3969/j.issn.1673-2065.2013.05.002
B234.5
A
1673-2065(2013)05-0003-06
2012-10-10
李祥俊(1966-),男,安徽合肥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衡水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