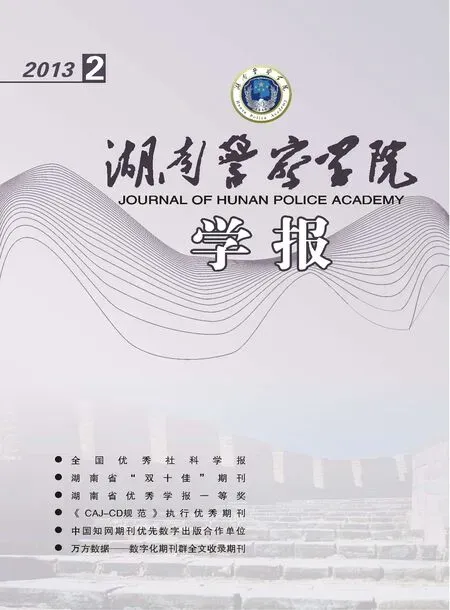论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之建构
刘玉龙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论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之建构
刘玉龙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行政诉讼判决是人民法院判断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制约行政权不当扩张和解决行政争议的最终结果,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原告的诉求能否实现。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判决是一种事后救济机制,与域外法治国家行政诉讼中的全方位的权利救济机制相比,我国的权利救济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禁止判决的缺失往往使得对相对人的救济处于“缓不济急”的状态,对那些通过事后救济难以获得弥补的被损害权利的保护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立足国情并参照国外成功制度的基础上,在我国引入行政诉讼禁止判决非常必要。
行政诉讼;禁令;禁止之诉;禁止判决
一、问题的缘起——我国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缺失
事件一:启东事件
2012年7月28日在江苏省启东市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群体事件—当地百姓占领市政府大楼。这起事件是因市政府批准日本王子制纸集团排海工程项目而触发的。因为担心在当地修建排污设施会对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数万名启东市民在市政府附近的道路集结示威,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并冲进市政府大楼,扒光了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的上衣,强行为市长徐峰套上抵制该项目的宣传衣。要求政府取消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直到当天中午官方宣布“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后,该群体性事件才得已平息。据媒体估计,有超过30,000人参加,游行示威人群加上集会人群将近10万人。
事件二: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
2009年10月中旬,海口市工商局开始对海口市内超市、商场等流通领域的饮料进行专项抽查,并委托海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测技术中心对抽检产品进行检测。11月23日的检验报告结果显示:农夫山泉有限公司生产的混合果蔬、水溶C100西柚汁饮料总砷(砒霜)含量超标。海口市工商局遂向消费者发布消费警示,并要求销售商对问题产品进行下架,等候处理。农夫山泉公司认为检测有误并请河源市质量计量检测所进行检测,该所出具的检验报告却显示上述产品合格。为了查清真相,海口市工商局将抽检产品备份送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复检。复检结果证明上述的饮料全部合格。后经海南省工商局调查表明,海口市工商局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程序错误,初检结果有误,从而使农夫山泉蒙冤。农夫山泉称该事件对企业的影响极大,目前仍有近60%的消费者不愿购买上述饮料,预计损失近10亿元。
上述两个事件均反映出我国现阶段的行政诉讼制度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合理行使职权,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漏洞。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救济是人们在合法权益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最有力的保障。对于不合法的行政行为,通过行政程序无法获得救济时,通过行政诉讼程序加以救济,解决行政纠纷,是对现代法治国家的起码要求。遗憾的是,我国行政诉讼伦理界和实务界大多认为行政诉讼只有在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已然受到实际侵害时才具备提起的合法性。这也决定了我国当前的行政诉讼所提供的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救济渠道。法院只能在损害已经发生之后才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种救济模式往往因为缓不济急而难以达到行政相对人所期待的救济效果,仅仅能起到事后纠偏的作用,对于正在造成或者即将造成的侵害无法起到事前预防性的的救济作用。综上,笔者认为,应借此次修改行政诉讼法的东风,增加一种能够对可预料到的必将发生的或者正在发生的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加以制止,事前预防性地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判决——禁止判决。
二、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理论概述
(一)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界定
学术界对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论述很少,对其尚缺乏明确的界定,本文在结合国外相关的概念的基础上,把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界定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行政机关即将作出的或正在作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嫌疑,将造成重大损失而禁止其自始不得作出该行政行为,或者法院认为已作出的某一行政行为违法,在否定其效力后,禁止作出该行为的被告将来再次作出相同的行政行为的判决方式。包括预防性禁止判决和禁止重作判决两种。
(二)行政诉讼禁止判决之理论基础
1.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
现代法治行政原则不仅要求所有的行政活动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而且更要求对公民的权利保护置于对行政秩序的保护之上。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要求法院向权利人提供全面、具有实效性的救济。该原则在域外的很多法治国家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在德国,德国行政法院为公民提供了三种紧密衔接的权利救济途径,即预防性权利救济、暂时性权利救济和事后的权利救济[1]6。事后救济是法院通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等途径纠正已经发生的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救济遭受该行为侵害的权益。暂时性权利救济是为了避免正在实施的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或损失,法院在审理该案前所作的中间的、暂时的、紧急的规制,如起诉停止执行制度。预防性权利救济,是指法院对行政机关即将作出的会给原告的合法权益带来不可弥补的的损害的行为予以确认或禁止,如禁止判决制度。上述三种权利救济类型相互补充,组成一个全面且有实效的权利保护体系[2]。而我国行政诉讼提供的是以事后救济为主,临时救济为辅的保护模式。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七种判决都只能审查“成熟”的行政行为。“起诉停止执行”也只是作为例外而应用。缺乏预防性的权利救济途径。显然,远未达到有权利必有救济原则所要求的“全面且有实效救济”的理想目标,无法满足权利主体的权利救济需求,例如对上述事件中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审批、不适当的信息披露而造成的损害,现有的行政诉讼救济显得软弱无力。就暂时性权利保护来说,虽然能暂缓执行部分的违法行政行为,但对于及时性完结的行政行为却无法及时提供有效的救济。
为此,应完善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增设行政诉讼禁止判决,填补事前救济行为缺失的漏洞,形成无漏洞的权利救济体系。以期达到在公民权利将要遭受侵害以前,尽量能通过禁止判决预防性地避免遭受不法行政行为的侵害;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及时有效的保护,弥补了事中或者说是事后行政诉讼的不足,顺应法治发展和公民权利保护的需求。
2.当代司法能动主义理论
司法能动主义起源于美国,是对审判行为的一种见解。《布莱克法律词典》把它界定为:“在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僵化地遵循先例和不局限于成文法的字面意思而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法治理念和在该理念指导下的行动。司法机构往往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求及社会发展趋势而发挥其司法能动性,对法律作出更贴切的解释,以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
从上面关于司法能动主义的界定中可以得出,司法能动主义要求法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不能只是在消极地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机械地根据法条作出判决,而要积极地对社会现实加以回应,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前提下,能动地解释和引用法律,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运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手段,快速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新型的纠纷也不断涌现,法律滞后、空白、冲突等情况时有发生,因而能动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对法官和法院来说就十分重要。因为法院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审理已经发生的案件。那么,在法律存在滞后或者不完善的情况下,法官如何积极地发挥司法能动性,高效低廉地解决纠纷,填补法律空白,使法律秩序在稳健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就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3]。相应地,司法能动主义开始勃兴。我国也体现出了这一趋势,最高人民法院的王胜俊院长曾指出:“我国的司法应当是主动型、服务型和高效型司法。人民法院应当使用政策考量、利益权衡、能动司法等方式,合理地行使司法权,注重大局,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研究,提高问题意识,善于从工作中发现社会前进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完善司法政策。”[4]由此可以看出,能动主义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主旋律。
现阶段我国应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主义的推动作用,完善行政诉讼救济制度。对现代行政权扩张背景之下的社会权利保障的需求作出回应。随着服务行政的推行,行政权力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行政分工也趋于精细化和专业化,行政活动过程也愈加强大,严格遵循对行政权力行使的事后监督已不能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而应对行政行为进行纵向监督,司法审查应对行政活动的过程多加关注,而不能仅局限于对其结果的审查。因而,在必要时,应允许公民寻求预防性的权利保护途径,以防止某行为的作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行政诉讼中引入禁止判决这种事前救济措施,无疑是完善我国公民权利救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域外借鉴
正如日本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教授所言:“现代的比较法已不再满足于单纯以认识为目的的对本国法的注释和对各种外国法的罗列,而开始追求以法的改革为行动目标”。[5]因此,在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过程中,应自觉地考察西方行政法治发达国家相对应的成功的制度,总结与提炼他们在建构制度时所积累的共性的经验和特点,取长补短,将其作为完善我国行政法治的参照物,为我国行政诉讼法改革提供借鉴。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禁令制度
1.英国的禁令制度
英国司法审查中的禁令制度,分为禁止令和阻止令两种。前者是高等法院向行政机关和低级法院发出的一种特权命令,禁止其越权行为。禁止令是一种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主要用于禁止行政机关超越和滥用职权。尤其在规制违法发放许可证方面[6]。例如,对于地方行政当局在没有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就决定增加公交车线路的决定,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禁止判决,阻止地方当局的许可行为。
阻止令是法院要求一方诉讼当事人不为一定的行为、或为一定的行为的私法上的命令。前者为消极性质的禁令,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继续存在;后者为积极性质的禁令,阻止消极违法继续存在。行政诉讼中使用的阻止令多是法院为阻止当事人作出一定行为而发布的命令。其最初为衡平法所规定,是禁止私人的违法行为的一种命令。后来随着普通法与衡平法的融合,扩大适用于公法领域,用于阻止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例如在地方行政当局没有听取房屋所有者的陈述就决定强制拆除他的房屋时,法院应房屋所有权人的请求,发出禁止地方政府强制拆除的命令[7]。此外,阻止令也可以用于阻止私人的违法行为的发生。
2.美国的禁令制度
美国的法律制度承袭于英国,两国的禁令制度也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国的禁令制度可以分为民事诉讼法上的禁令制度和行政法上的禁令制度。
(1)民事诉讼法上的禁令是法院要求被告为一定行为或禁为一定行为的命令。它既可以针对私人的违法行为而发出,例如,针对私人违反环境法规的污染环境行为;也可以针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而发出,例如,针对政府的一项侵犯其言论自由的规定,出版商可以向法院寻求禁令加以救济[8]。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衡平法救济方式,禁令在日益增多的家庭暴力、环境保护、商业秘密等案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行政法上的禁令包括禁止状和制止状两种。禁止状是法院应当事人的请求而发布的命令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下级法院停止执行或不执行不合法决定的一种特权状。它适用于作出前及执行中的决定[9]574。制止状是法院命令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停止执行特定的不合法行为,或者命令其执行特定的行为。前者是一种禁止性质的令状,制止违法行为的实施;后者称为命令性质的制止状,命令执行必须执行的义务。它是衡平法上的救济途径[9]571。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救济措施,美国对行政法上的禁令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和审查标准,主要体现为必要性和补充性。即禁令应在行政公权力行为很可能会给申请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且在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及时加以救济时才予适用。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禁止之诉制度
1.德国的禁止之诉制度
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国家,德国有着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先进的法学理论。在公法领域,为了防止公权力的越权行使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德国《基本法》确立了权利有效且无漏洞的保护标准。这一标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反映,比如理论界的预防性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禁止之诉制度。正如弗里德赫尔穆·胡芬所说“如果不能苛求原告必须等到某一负担实际出现才采取行动,就应当考虑采用预防性法律保护。”[10]
德国的禁止之诉包括停止作为之诉和预防性确认之诉。停止作为之诉在德国系一般给付诉讼的一个亚类,指人民依公法上不作为之诉的法律救济方式,诉请行政机关不为特定之行政行为,以防止其因而面临之干预[11]122。这类诉讼主要有:防止事实行为侵权的停止作为之诉、防止内部行政行为侵权的停止作为之诉、防止行政规范和行政行为侵权的预防性禁止之诉。
预防性确认诉讼是在原告具有特定的确认利益时,申请法院对将要发生的法律关系或者将来不得为特定行政行为进行确认的诉讼[1]36。一般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只有在特定行政决定作出后才能提起诉讼。只有在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明显的受损威胁,且无法能通过事后救济获得弥补时,才有采取预防性救济措施的必要,否则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司法越权之嫌。因此,预防性确认之诉应为停止作为之诉的补充。但预防性救济制度的宗旨就是为了防止某种法律或事实状态发生不利于原告的改变。在行政决定还未作出时,预防性确认诉讼往往更适合原告的诉求,也更易被法院采用。在司法实践中,停止作为之诉与预防性确认之诉的适用并没有明显的先后之别,而且在制止违法行为和阻止消极影响方面,预防性确认之诉往往更具优势。
2.日本禁止之诉制度
日本的禁止之诉制度是从法定外诉讼种类演变而来的。在2004年以前,《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以撤销诉讼为中心,未明文规定其他诉讼类型,彼时的禁止之诉是作为法定外抗告诉讼存在于一些学说和判例当中。修订之后的《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作出了很大的变革,不再以撤销诉讼为中心,在法条中明确规定了禁止之诉制度,丰富了行政诉讼的类型。该法中把禁止之诉制度界定为:相对人在行政机关不应该作出一定处分却将要作出处分或裁决的时,诉请法院命令行政机关禁止作出该处分或裁决的一种诉讼。
该法的第37条规定了禁止之诉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了适用范围、原告资格、审理过程、判决形式等。该条中规定禁止之诉只能适用于将要作出的处分裁决很可能会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害时才能提起,而且,禁止之诉还是作为一种补充型的救济机制,只有在没有其他合适的救济途径是才能运用。而在原告资格方面,该条规定了只有与行政机关将要作出的处分或裁决有法律上的利益的人才能提起禁止之诉。对于如何认定法律上的利益以及不可补救的损害该条都做了规定,方便法院认定。例如在判断是否会产生不可修复的损害时,可以结合行政处分和裁决的性质和具体内容、损害的程度、性质、恢复的成本等。法院在经过审查后认为符合禁止之诉适用条件的就应判令行政机关禁止作出特定的处分或裁决[12]。
此外,为提供更加及时的救济,防止在等待作出禁止判决期间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或裁决产生的难以补偿的损害,该法还规定了临时禁止制度。相对人在有紧急处置必要时,可以向法院提出临时禁止申请,请求法院临时禁止行政机关作出特定的该处分或裁决。
四、我国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制度构建
在对英美两国的禁令制度和德日两国的禁止之诉制度作比较考察之后,结合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20余年来的情况,提出以下建构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构想。
(一)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起诉资格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了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行政相对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又将具体行政行为扩展为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并在该解释的十二中对合法权益的认定做了界定,即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可。从上述规定中可以得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就是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是对于禁止判决来说,因其针对的是还未形成的行为的事先审查,这时是否有利害关系相对于事后救济型判决来说应作更加严格的审查。笔者认为,应对禁止诉讼的原告资格须满足以下要求。
1.原告处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中。这里讲的特定的法律关系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由于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被侵害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例如前面案例中提到的农夫山泉公司的名誉权因遭到海口市工商局的不合法的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又如长治水污染事件中,公民的健康权因未得到及时的通知而可能遭受侵害。第二类是通过行政规章、行政允诺、行政合同或其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建立产生的法律关系。例如行政机关即将作出的行政许可与之前行政机关签订的行政合同存在冲突,合同相对方可以基于合同关系而提起诉讼。第三类是因行政行为的前期效力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例如因塑化剂事件引发行政机关即将对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作出的处罚,可能在未作出处罚前已经对其造成了不利影响。
2.事前救济的必要性。即只有在原告不能够通过临时性权利救济或者是撤销之诉、确认之诉等事后救济途径获得权利救济时才能寻求禁止判决加以救济。
(二)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适用范围
上述的两大法系国家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对其事前救济的范围作了不同的规定。但是它们针对的诉讼标的都是即将发生,或正在持续的公权力行为。因而,对那些做出即告完成行政行为和已生效的行政行为,例如强制检查、现场处罚,是不适用禁止判决的,除非这些行为存在重复作出的可能。结合上述国家的做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禁止判决适用情形如下:
1.可能造成既成事实的事实行为。包括:(1)信息披露行为,例如工商、卫生、质量技术监督等管理机关通过媒体发布不合格商品名单,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某类商品的行为。(2)因公权力行为或者公共设施而生的环境污染行为。例如行政机关因通讯需要而架设的无线电设备所产生的电磁污染。(3)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的行为。例如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以殴打等暴力方式造成商贩身体伤害或死亡的行为。
2.需要紧急救济的行政行为。即那些有现实威胁的行政行为,如果等其做成之后通过撤销诉讼等事后救济方式寻求救济的话,将难以对相对人权益进行救济的案件。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1)基于已经确定的行政行为而必将发生的行政行为,例如基于行政规划而即将实施拆迁许可、建设许可。(2)即时强制中的即时完结行为,例如应急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征收、征用。(3)将导致不可恢复、不可弥补的损害危险的行为,如国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中确认不具有报名资格的行为。(4)具有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制裁威胁的行为,例如行政机关针对某区域的交通管制命令[11]135。
3.部分内部和抽象行政行为。尽管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内部和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外,但理论界将它们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呼声很高,而且前面介绍的法治国家也都将上述两类案件引入了行政诉讼当中,例如德国就存在针对抽象行政行为而提起的防止颁发特定规范文件的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所以,为了对相对人提供全面且有效的权利救济,未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将对公职人员的开除、辞退、档案行为、行政规范的制定等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同时在符合禁止判决的适用条件时,应允许其向法院请求救济,由法院判决行政机关禁止作出这些行为。
(三)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适用条件
由于禁止判决是对行政机关尚未最终形成的行为的司法审查,不仅有僭越行政权的嫌疑,同时也是对更具效率的行政复议程序的规避。因此,应对其适用条件加以严格限制。笔者认为禁止判决的适用应满足如下条件:
1.行为发生的高度盖然性。即只有在行政机关将要作出特定行为的意向十分明显,并且内部决定已经形成或者已经开始前期工作的准备,但还没有转化为成熟的外部行动时,法院才能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作出禁止判决。也就是说,只有在可以预见行政机关将会作出一定行为,且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时,才能作出禁止判决。
2.损害的重大性。即只有在行政机关即将作出特定行为会对行政相对人之合法权益造成不可修复的重大损害或者事后补救成本过大时才能适用禁止判决。衡量是否有重大损害时,应当考虑损害的性质、程度、恢复的困难程度以及行为的内容、性质。例如,上述启东事件中,基于南通市政府的行政审批,如果批准了对日本王子制纸集团排海工程的项目的排污许可,该工程对南通市民的生命健康的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3.行为的明显违法性。即除非行政机关即将或正在作出的行为明显违法,否则法院不能运用禁止判决对其加以干预。但对于判决禁止重做的的行为可以参照一般违法判断标准。
4.相对人容忍义务趋零性。即法院在运用禁止判决时,要进行利益衡量,对原告、被告、第三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因禁止判决的作出可能受到的影响加以全面考虑,考量原告是否基于法律、合同、先行行为等存容忍义务。只有在适用禁止判决对被告、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小于不适用给原告带来的损害时,原告的容忍义务趋于零时,禁止判决的适用才具有正当性。
(四)行政诉讼禁止判决的形式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如果认为原告的诉求满足禁止判决适用条件,并且审判时机已经成熟时,就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自始禁止行政机关作出特定行政行为或禁止继续作出特定的行为,或者禁止其将来重复作出相同行为。
具体来说,在预防性禁止判决文书中,法院应写明:“判决禁止被告作出(xx行为)”抑或:“判决被告停止(xx行为)”。例如,台湾地区的行政法院判令行政机关不为一定行为的判决内容:“被告不得为原告之企业游走于法律边缘之主张。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或者:“被告在相关捐赠行为完成前,不得进行某市某路某号至某号间人行步道之改建工程。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13]法院在禁止行政机关重作特定行为的判决中应写明:“判决撤销被告所作的特定行为或确认被告的特定行为违法,并禁止被告行政机关无理由地重复作出该行政行为。”
参考文献:
[1]朱健文.论行政诉讼中之预防性权利保护[J].台港澳及海外法学,1997,(1).
[2]胡肖华.论预防性行政诉讼[J].法学评论.1999,(6):3-4.
[3]王建国.能动司法之功能—基于社会转型现实视角的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08,(2):25
[4]王胜俊.把握司法规律、坚持能动司法,努力推动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N].法制日报,2009-05-06(1).
[5][日]大木雅夫.比较法[M].范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2. [6][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88.
[7]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191.
[8][美]杰弗里.C.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M].张茂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63-165.
[9]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10][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M].莫光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94.
[11]吴绮云.德国行政给付诉讼之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12]王彦译.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J].行政法学研究.2005,(1):112-124.
[13]翁岳生.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458.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Prohibits Judgment
LIU Yu-long
(Hainan 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0228)
Administration litigation judgments in the people's court is the judgment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restricting improper expansion of executive power and the final results to solve administrative disputes.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and determines whether the plaintiff's claim can be achieved.China's current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gment is a kind of afterwards relief mechanism.Compared with the full range of law rights relief mechanism provided by foreign countries,right remedy system in our country is not perfect,especially the lack of ban judgment which often makes the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right is unable to get timely relief.For those damages which through afterwards relief is hard to offset,rights relief mechanism in our country can't provide effective relief.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 against judgment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with reference to foreign successful system successful system abroa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ban;ban proceeding;ban decision
D925.3
A
2095-1140(2013)02-0059-06
(责任编辑:王道春)
2013-01-11
刘玉龙(1988-),男,四川宜宾人,海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