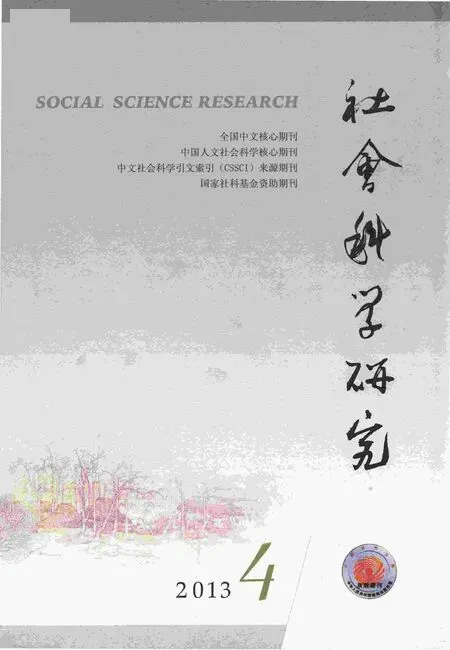宋元时期嘉湖地区的水土环境与桑基农业
王建革
嘉湖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嘉兴和湖州一带,其低地农业的开发主要指于一片浅水沼泽地带中进行围垦,形成圩田河网体系。大约在南宋时期,传统地貌下的圩田与河网已基本形成,明清以后水面破碎化,水网越来越深入到深水区,但总体上只有微地貌的变化。植桑则很早就已经出现,但这一地区的特色——桑基农业,其主体结构和特色景观基本上是宋元时代的产物,明清时期这种小规模的桑基稻田和桑基鱼塘只是单纯地增多。从沼泽围垦到桑基农业,农民通过不断地开河和挖河泥,改变了河流面貌和微地貌形态,正是人与环境的互动形成了闻名于世的桑基生态农业。
本文通过对桑基农业产生过程的历史分析,揭示出一个地区优良生态系统形成所需要的诸自然、社会要素及时间的积累,以期提高国人对中国生态农业的认识,加强保护传统生态系统的历史责任感。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地区桑蚕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补农书》的研究上。陈恒力与王达在对《补农书》的校注与研究中,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与桑基农业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但要在历史中寻求其地貌与环境变化的轨迹,仍然要从宋元时期水土环境的形成开始。
一、山区与平原之间的生境与植桑
早期的嘉湖平原农业开发于山区与平原之间,天目山麓有多溪下流,汇水于浙西沼泽地带,较深水地带易于开发,故出现了以火耕水耨的方式种植水稻,有初步的桑蚕业。六朝宋沈瑀在建德令任上时,曾以官方命令推广种桑,“教人一个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棃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2〕建德如此,邻近太湖的山地也多有蚕桑经营。“周敏,吴兴太守,大开学校,劝人种桑麦,百姓赖之”。〔3〕
山区因为有陂塘水利,开发较早。斯波义信认为苕溪流域早期由于农业技术粗放,“定居地仅限于武康、长兴、乌程西南的山麓台地,这一倾向,到东吴、六朝、隋朝均无变化。”〔4〕唐天授二年 (691年)德清县民上奏请析县,称山区一带“通舟楫,饶鱼稻竹茗桑麻之利”。皮日休对湖州山区也有诗描述,称其桑蚕业发达:“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风根坐钓矶。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莎市卖蓑归。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5〕
山区与平原之间的开发是通过修筑一系列运河或其他开塘工程完成的。
南湖,(余杭)县南二里,苕溪发源天目,乘高而下。县地平衍,首当其冲,淫潦暴涨则泛溢为患。汉熹平二年县令陈浑始筑两湖以潴水,其并溪者曰南下湖,环三十里;并山者曰南上湖,环三十二里。于湖之西北为石门函,以纳溪水,溪水得所潴,而暴流始杀。又于湖东南五亩塍设立滚坝,溪落则湖水仍由石门函,还纳于溪,湖涨则自五亩塍经县东南五里之石棂桥泄入于南渠河。〔6〕
著名的荻塘修成后,附近的沼泽便得到开发利用。(嘉泰) 《吴兴志》卷十九“荻塘”条下有:“荻塘,在湖州府南一里余。据旧图经载云:在州南二里。……晋太守殷康开,旁溉田一千顷。后太守沈嘉重开之,更名吴兴塘、南塘。李安人又开一泾泄于太湖。(唐)开元中,县令严谋道又开之。广德中太守卢幼平又开。”荻塘分天目山下泄之水流,向太湖方向形成溇港,向东形成一般的河道,圩田则存在于河网之间。湖州低地的开发大致如此,先在浅水中开塘,然后在塘的周边开河,河道分割形成圩田四周的河道。以后河道再细化,圩田也随之分割成较小的圩,成为现代桑基农业的基础。太湖东部河网形成以后,太湖湖岸也逐步形成,湖溇区逐步形成稳定的小圩田。
山区与沼泽地之间的圩岸易受水流冲击,植桑固岸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唐末陆龟蒙有诗:“山横路若绝,转楫逢平川。川中水木幽,高下兼良田。沟塍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7〕洞庭山位于太湖中央,植桑也很普遍。《吴郡图经续记》中载苏子美之言:“洞庭民俗真朴,历岁未尝有诉讼至县吏庭下。以桑、栀、甘柚为常产,每秋高霜余,丹苞朱实与长松茂木相差于岩壑间,望之若金翠图绘之可爱云。”〔8〕到了南宋,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桑蚕业与果树业发达,使得这一地区的专业化发展到农民可以脱离粮食生产的程度。“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绍兴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9〕
低地种桑一开始就在圩岸上,也是因为人住在圩岸上,房前屋后便是圩岸,圩岸植桑最方便。六朝时吴均有“陌上桑”一诗: “袅袅陌上桑,荫陌复垂塘。长条映白日,细叶影 (一作‘隐’)鹂黄。蚕饥妾复思,拭泪且提筐。故人去如 (一作‘宁知’)此,离恨煎人肠。”陌,其实是圩岸之意。〔10〕但这时许多沼泽地尚未开发,圩岸上种桑不多,许多仍是在旱地植桑。唐代吴兴县令李清,“大历中为县令,忠肃明亮,以将其身;清简仁惠,以成其政。弦歌二岁,而流佣复者六百余室,废田垦者顷,浮客辐凑迨乎二千;种桑蓄养盈于数万。”〔11〕李清不是以分散的小农经营方式推广植桑的,而是利用了成规模的移民,在某些地段集中经营。“《吴兴记》:‘乌程东南三十里有桑墟。’《梁陈故事》:‘吴兴太守吴敏劝人种桑’。”太守劝农植桑于旱地,一定是不小的规模。到元代已经没有可供劝农的公地种桑,大规模的连片桑地也不过数十亩,“富家有种数十亩者”。富人才可以种数十亩桑。元代的野桑也仍被利用,“檿桑、山桑也,生于野。”〔12〕大多数的野桑分布于山脚地带。
北宋初年曾极力推广平原植桑。政和元年(1111年)五月二十二日有诏曰:“耕桑乃衣食之源,斫伐桑柘未有法禁,宜立约束施行。”〔13〕官方的推动对山区之桑走向平原有着积极的意义。苏东坡在江南时,发现沿山区地带有大量植桑,“浩荡城西南,乱山如玦环。山下野人家,桑柘杂榛菅。岁晏风日暖,人牛相对闲。”〔14〕宋代的桑蚕规模发展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山水暴涨会对这种产业构成冲击。绍兴三十年 (1160年)五月,“湖州安吉于潜山水暴出,坏民田庐桑,人溺死甚众。”〔15〕刘一止提到吴兴一带山水清远,农民经营农桑: “德清盖吴兴支邑,而山水明丽清远,为他邑冠。南朝以来曰沈氏者,世有韪人。或以文雄一时,士虽少,必秀于其额。民贫而安,力于农桑,种艺渔樵之业。”在一则墓志铭中,他言一位太孺人家族是乌程人,“于先生墓之傍,曰玲珑山,薙草植木,畦田圃桑以业其家,以乐其身终焉。”〔16〕“圃桑”,桑植于田块,不像低地那样种于圩岸。南宋时期,官方在制定税则时,将山桑与平地桑划分为园圃类,“缘经界起税,各有等则。以田亩论之,有水田,有平田,有高田;以园地论之,有平桑,有山桑,有陆地,有茶地,有竹脚,有柴样,难以一例。”〔17〕
除了圩岸植桑以外,高地不宜种稻田处也成片种桑。陈旉较早地观察到了这种现象。“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畜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18〕《陈旉农书》所讲的农业习惯主要指江南地区,特别是太湖东部与浙东地区。高地重视陂塘,陂塘与桑基是浙东地区和嘉兴地区常见的地貌单元。尽管陂塘暂时不能大量养鱼,却是后期沼泽地区桑基鱼塘的基本雏形。
南宋以后天目山的植被受到破坏,太湖泥沙含量增加,在此之前却不一样。天目山森林茂盛,山水清远,故无论溇港区还是低地平原,水清稻美。苏轼曰:“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莲蒲之利,寡求而不争。”浅水与清水中丰富的资源带来了丰足的生活。宋代以后,开发日兴,人们多依赖圩田与稻作,丰水环境使得圩田在大水时节受灾严重。“自莘老(孙觉,字莘老,高邮人,时任湖州知府)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19〕尽管如此,水清依然,并兴起一个更为重要的产业,即丝织业。水清纱美,丝绸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但低地的纱一开始并不出名,山乡的纱更有名,嘉泰《吴兴志》中记“梅溪安吉纱有名”,丝也是以“安吉丝尤好”。早期的桑蚕业有很大一部分在山区,也与此有关。直到元朝,仍有部分山区的丝织业不下平原。“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水乡并种苎及黄草,纺绩为布,有精致者,亦足以见女工之不卤莽。”〔20〕山区丝织业的兴盛必然推动养蚕和桑树种植。
在浙西平原与山区交汇处,植桑养蚕在宋代已经成为主要的副业,夏日的桑阴已是田野的主要景观。陆游有诗: “桑柘成阴百草香,缫车声里午风凉。客来莫说人间事,且共山林夏日长。”陆游返浙东家乡时,路过湖州一带,有诗述初夏景观:“桑间葚熟麦齐腰,莺语惺愡野雉骄。日薄人家晒蚕子,雨余山客买鱼苗。丰年随处俱堪乐,行路终然不自聊。独喜此身强健在,又摇团扇着絺蕉。”〔21〕卫泾对浙西围田水利有研究,有“晚晴”一诗讲到桑野景观:“雨断风回忽报晴,山颠初日挂铜钲。云烟藏迹千峰翠,草木增华两眼明。桑野枝空蚕杼歇,溪泉溜急水车鸣。”〔22〕这明显是乡村采桑养蚕完毕后的景观,养蚕之后人们又紧张地进行车水灌溉。山上的桑树高于行人。“绿暗山前路,柔桑宛宛垂。稻秧分陇后,蚕茧下山时。白日缫车急,中宵织妇悲。老年官赋了,不长一絇丝。”〔23〕南宋的楼钥描述了浙东山区的成片桑林,“柔桑弥望两三里,修竹深藏四五家。径处不容行客恋,可怜一步一天涯。”〔24〕
南宋的大开发不单在低地浅水地带进行,也在山区进行。同时发生的水土流失似乎加剧了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湖田区的圩田小规模化,淤积形成稻作土壤。但在此以前的低地土壤,却基本是山水清远环境下的土壤,土壤的质地基本上是湖沼淤积物,且有大量的泥炭。
(湖沼淤积物)主要分布在嘉兴西塘、桐乡乌镇、吴兴菱湖及德清一带,以及其它低洼地区。土壤质地一般都较粘重。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早先湖泊的遗址,滋生过湖沼植物,经过一段沼泽化的过程,因而留下了一定厚度的沼泽腐泥层。这一层含有多量紫黑色粘粒,容重很小。在这层下面,有时还发现泥炭层 (这普查 (1959年)初步查出的泥炭底青紫泥就有两万多亩)。低洼地区的水稻土大多就发育在这一层上面,这也就是当地农民所说的青紫泥。〔25〕
青紫泥土壤是湖沼淤积物,尽管较少,却很肥沃。泥炭大量发生于水稻土形成以前,低地泥炭沉积是世界普遍现象。荷兰沿海低地地区存在大量泥炭层,低地围垦就是围垦泥炭区,开垦的时间也和中国长三角差不多,开挖泥炭的习惯早在12世纪时就广为人们接受。当地的农民从沟中把这些泥炭挖出来并铺洒到土地上,以后还在其中加入沙土。〔26〕太湖流域的泥炭开发基本不用渗砂,因为要种稻。挖河泥实际上是挖掘泥炭与湖沼淤积物,因此形成的稻田土壤有很高的肥力,桑叶产量和水稻产量都很高。赵孟頫的《吴兴赋》有:“其东则涂泥膏腴亩钟之田,宿麦再收,粳稻所便,玉粒长腰,照筥及箱,转输旁郡,常无凶年。”讲到低地地区麦稻的丰产。此外还有丰富的水生动植物: “蒹葭孤卢、鸿头荷华,菱苕凫茨,萑蒲脍余,四望弗极,乌可胜数!其中则有鲂鲤鲦鲿,针头白小,鲈鳜脍余,鼋鼍龟鳖”。在这种初步的围田系统中,桑基农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其平陆则有桑麻如云,郁郁纷纷,嘉蔬含液,不蓄长新。”〔27〕桑麻并种。此时植桑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产丝不像明中后期那样普遍。元代江南的植棉也尚未像后期那样形成专业化的植棉区,丝织品主要用于城市的奢侈品消费,故仍需种麻以供衣物之需。
由于商业经济不发达,官方勒索丝物,农民逃亡,甚至出现陌上桑无人采的现象。
陌上桑,无人采,入夏绿阴深似海。行人来往得清凉,借问蚕姑无个在。蚕姑不在在何处?闻说官司要官布,大家小家都捉去,岂许蚕姑独能住?日间绩麻夜织机,养蚕种田俱失时。田夫奔走受鞭笞,饥苦无以供支持。蚕姑且将官布办,桑老田荒空自叹。明朝相对泪滂沱,米粮丝税将奈何?〔28〕
农民一边织麻布,一边织丝绸。尽管受官府压迫,但由于元代吴兴一带的生境仍处于“山水清远”状态,仍然为丝织品的优质提供着完全的自然条件。苕溪“自有天地有此溪,泓渟百折净无泥。我居溪上尘不到,只疑家在青玻璃。”〔29〕余不溪尤为清澈,“溪流冬夏盈演,玉光澄映,与他水特异,故为名焉。”倪赞有诗:“余不溪水绿生萍,放舟演漾当青春。舟随鹤影忽行远,洞口桃花飞接人。”清水入太湖,分支入湖州。“望中烟草古长洲,不见当时麋鹿游。满目越来溪上水,流将春梦过杭州。”作为画家的倪赞留恋那里的风景,不归梅里而在溪边住了七年。〔30〕清流可以浣纱,山区有各种野生桑树可以发展蚕桑业。
与嘉湖地区发达的植桑传统相比,吴淞江一带的植桑则一直不发达。宋代初年的长洲“地无柔桑,野无宿麦。”〔31〕可能是水质差异所致,吴淞江地区毕竟直承太湖水流,又迎海潮浊流,水质远没有嘉湖一带清澈。后期桑蚕业只发达于吴江湖田区,因那里特别需要植桑固岸,春季农民休闲,也需要副业以补产业之不足。山区由于环境基本得到了保护,仍然有许多人用柘树之叶饲蚕。元代的柘树护理有一整套办法。“柘叶隔年不采,春再生则毒蚕,如要不尽,夏月皆要打落,方可无毒也。”〔32〕此时桑蚕业已转移至平原,山区的植桑必然衰落,柘树与柘蚕所产丝的质量肯定大大低于一般的平原蚕。宋代浙江植桑已经形成桑苗基地,长江以北的战争区要恢复植桑,必须到浙江购桑苗。乾道二年,皇帝命令恢复蚕桑,有关官员上奏道:“州县既知陛下留意,闻皆使人于浙西买桑栽去。”〔33〕
二、低矮桑树的推广环境
早期的蚕桑业主要集中在山区近平原一带,随着低地平原的开发和河岸与圩岸的增多,桑基农业景观大大增多。“吴桑成绿阴,吴蚕盈翠箔。”〔34〕从山区到平原,桑树的单株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山区近平原地区种桑的空间大,可以粗放经营,任桑树无节制地生长,故多形成高大树桑。平原地区的桑树不单受圩岸限制,由于人口密集,需求量大,对桑叶产量也有要求。农民修剪桑树以增加桑叶的产量,而修剪本身会使树形偏矮。宋元时代,平原地区既有高大的树桑,也有低矮的桑树或条桑。
在北方,人们冬天将树身锯断一部分,“离地只留三尺”,春天将一部分新生桑条伐掉,最后形成的树形层层叠叠。〔35〕王祯曾用梅尧臣的诗证吴地的科桑技术。“科桑持野斧,乳湿新磨刃。繁枿一以除,肥条更丰润。鲁叶大如掌,吴蚕食若骏。始时人谓戕,利倍今乃信。”〔36〕梅尧臣的另一首诗则提到北方科桑,“古路草初白,大河冰未成。暖科桑柘美,寒织杼梭鸣。”〔37〕王祯年轻时常在江浙一带走动,《王祯农书》所载伐桑技术实出于江南,特别是嘉湖地区。伐桑用的斫斧很有讲究,“凡斧所剶斫,不烦再刃者为上;至遇枯枝劲节,不能拒遏,又为上;如刚而不缺,利而不乏,尤为上也。然用斧有法,必须转腕回刃向上斫之,枝查既顺,津脉不出,则叶必复茂。故农语云:‘斧头自有一倍叶。’以此知科斫之利胜,惟在夫善用斧之效也。”他对南北方桑树形与采伐习惯的关系有深刻的描述,“然北俗伐桑而少采,南人采桑而少伐。岁岁伐之,则树木易衰,久久采之,则枝条多结,欲南北随宜,采斫互用,则桑斧桑钩各有所施。”〔38〕多采而多结,明显符合嘉湖一带农民对桑叶产量的要求。
梅尧臣提到了江南的鲁桑,实际还有荆桑。一般认为,鲁桑源出山东,其特点是枝干较粗大,叶厚汁多,宜于饲蚕。郑云飞认为古人的荆、鲁桑区别没有现代分类学上的意义,只是外表性状的差异,鲁桑用于采摘,荆桑用做枮木,生物学上其实是同一地区的同一种鲁桑。嘉湖地区的鲁桑也不是从山东传来,而是土生土长的桑。〔39〕《农桑辑要》引《士农必用》言:“桑之种性,惟在辨其刚柔,得树艺之宜,使之各适其用。”〔40〕区别鲁桑与荆桑是为了嫁接之用。《农桑辑要》还提到了官方的区别标准。
桑种甚多,不可遍举。世所名者,“荆”与“鲁”也。荆桑多椹,鲁桑少椹。叶薄而尖,其边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干、条、叶坚劲者,皆荆之类也。叶圆厚而多津者,鲁桑也。凡枝、干、条、叶丰腴者,皆鲁之类也。荆之类,根固而心实,能久远,宜为树。鲁之类,根不固而心不实,不能久远,宜为地桑。然荆桑之条叶,不如鲁桑之盛茂。当以鲁条接之,则能久远而又盛茂也。鲁为地桑,而有“压条”、“换根”之法。传转无穷,是亦可以长久也。荆桑之类,宜饲大蚕;其丝坚纫,中纱罗。《书·禹贡》 “厥篚壓丝”,注曰: “壓、山桑”;此荆之类而尤佳也。鲁桑之类,宜饲小蚕。〔41〕
荆桑相对处于野生状态,鲁桑处于相对的驯化状态。无人工栽培的时候,桑树在野外自由生长,则鲁桑变荆桑。“栽培农业的措施,其实就是抑制桑树的生殖发育而促进其营养器官的生长,否则,桑树就会回到自然的野生状态中去,结果多而产叶减少,大大降低桑的经济价值。”鲁桑低矮,以荆桑为底,荆桑多在附近山区。平原一带的桑属种类是鲁桑 (Morus alba Linn.var.multicaulis(Perrott.)Loud.)和白桑 (Morus alba L.),白桑仅仅是“柱头无柄;果白色,有时淡红色或紫色”。鲁桑和白桑区别甚微,一般情况下,江南农民难以分辨。分类学家又称白桑为荆桑、家桑,鲁桑系白桑的变种,如此越辨越乱,在农民眼中,鲁桑只是桑叶肥厚而已。桑属的山桑 (Morus australis Poir.),又名小叶桑、鸡桑。〔42〕这种桑,古人可以分辨得出,并能区分出野桑及其品种的变异。“野桑若任其长,肥者成‘望海桑’,瘠者成 ‘鸡脚桑’,蚕家贱之。”〔43〕这其实是同一种桑,仍不具备分类学上的意义。发展成望海桑时,桑树植株非常高大,枝叶伸长,形成生长优势,排斥了其他植物。无论是望海桑还是鸡脚桑,桑叶质量都较低,一般只是房前屋后时有种之。“若墙下可以树桑,宜种富阳,望海等种,每株大者可养蚕一筐。”〔44〕农民选择这种野生高大的桑树,实因重视其野生性和抗逆性。
嫁接与修剪最终形成低矮湖桑,浙江地区产量性状好的低桑早在唐代就出现了。《种树书》上讲:“浙间植桑,斩其桑而植栽之,谓之嫁桑。却以螺壳覆其顶,恐梅雨侵损其皮故也,二年即盛。”“二年即盛”,说明低矮之桑可以很快地进入收获期。人们嫁接时注重桑叶的产量与质量。“谷上接桑,其叶肥大”,指谷雨前后嫁接的桑树桑叶产量高。唐代以后江南经济发展,出现了桑叶买卖,桑叶成为商品。“谚曰:雨打石头偏,桑叶三钱片。”这更要求桑叶生产周期短,见效快,故嫁接的低桑得到快速推广,到两宋时期形成大推广。〔45〕元末明初,桑叶买卖大盛,农谚中有更多的对桑叶与雨水的观察,“雨打石头斑,桑叶钱价难。”言旱天的桑叶贵而难买;“雨在石上流,桑叶好喂牛。”雨天损蚕,桑叶多而无用。〔46〕
赵孟頫所讲的植桑基本是一种低矮桑,这种桑种植于宜人的二月份。
仲春冻初解,阳气方满盈。旭日照原野,万物皆欣荣。是时可种桑,插地易抽萌。列树遍阡陌,东西各纵横。岂惟篱落间,采叶惮远行。大哉皇元化,四海无交兵。种桑日已广,弥望绿云平。匪惟锦绮谋,只以厚民生。〔47〕
“插地易抽萌”,指嫁接的插桑。做斫的桑基早在上一年冬天就预备好了,赵孟頫十二月诗中有:“忽忽岁将尽,人事可稍休。寒风吹桑林,日夕声飕飗。墙南地不冻,垦掘为坑沟。斫桑埋其中,明年芽早抽。是月浴蚕种,自古相传流。蚕出易脱壳,丝纩亦倍收。及时不努力,知有来岁否。手冻不足惜,冀免号寒忧。”田野中仍有大桑树,四月时采桑女用梯子采桑。“四月夏气清,蚕大已属眠,高首何昂昂,蛾眉复娟娟。不忧桑叶少,遍野如绿烟。相呼携筐去,迢递立远阡。梯空伐条枚,叶上露未干。蚕饥当早归,秉心静以专,饬躬修妇事,黾勉当盛年。救忙多女伴,笑语方喧然。”〔48〕
修剪拳桑形成于南宋,咸淳《临安志》中提到拳桑,“桑数种,曰:青桑、白桑、拳桑、大小梅、红鸡爪之类。”〔49〕杭嘉湖地区是桑蚕业一体化的地区,嘉湖地区的大多数桑树也种在圩岸上,并修剪成矮桑。李龚《陌上行》一诗对此有描述:
采桑东陌头,日出红光流。采桑南陌头,和风满桑钩。采桑西陌头,日落乌飕飕。采桑北陌头,明月照歌楼。携篮敢惮远,手胝足成趼。蚕饥恐归迟,一日三四返。昨朝蚕三眠,灯前微合眼。梦中见征夫,短衣供筑版。庭树啼霜鸦,梦回自天涯。小姑报蚕起,蓬鬓忙梳爬。相望万余里,那敢兴怨嗟。出门还采叶,细雨湿桐花。〔50〕
李龚老家在山东菏泽,移居吴兴后对当地的蚕桑文化感受很深。他住于“三汇之交”〔51〕,应该是多水流交汇的湖州城附近。陌头是圩岸之地,陌是小路,也是圩岸。
丝织业依靠妇女的劳动,丝织品为官方主要的征收物。
妾本秦罗敷,家住曲江曲。门前杨柳青,春风啼布榖。树头桑初芽,家家蚕始浴。相呼出采桑,采桑如采玉。屈曲廻高枝,攀条剪柔绿。朝晴采桑南,暮雨采桑北。采得桑归迟,小姑怨相促。陌上绮罗人,问妾眉何蹙。妾恨妾自知,问妾何所欲。消磨三十春,渐喜蚕上簇。七日收得茧百斤,十日缫成丝两束。一丝一线工,织成罗与谷。百人共辛勤,一人衣不足。举头忽见桑叶黄,低头垂泪羞布裳。〔52〕
“朝晴采桑南,暮雨采桑北。”可见妇女会根据天气采桑。“屈曲廻高枝,攀条剪柔绿。”圩岸陌头的桑树仍有较高的树形。叶茵晚年居住太湖边的水荡之间。“道南地夷旷,半占龟鱼渊。断岸连疏村,浮云栖平田。”可见水岸边缘也会有种桑的空间,由蚕妇辛苦经营。“浴蚕才罢餧蚕忙,朝暮蓬头去采桑。辛苦得丝了租税,终年只着布衣裳。”又有:“桃花深映水边庄,夫妇相携笑语香。耕耨有粮蚕有种,丁男戽水女条桑。”〔53〕男子戽水是低地圩田常有的农活;条桑,即摘桑,是妇女的工作,稻作与桑蚕业并存。范成大归石湖时看到湖州或吴江一带的景观是:“柳堤随草远,麦陇带桑平。白道吴新郭,苍烟越故城。”〔54〕由于围田开发,浙间已经达到无寸土不耕的程度,稻作的集约化必然推动植桑的集约化,湖桑与湖丝正是在这种集约化基础上兴盛起来的。麦稻二收或稻麦二熟地段,桑树抽绿时,往往正是麦陇发黄时。若有水灾发生,桑会与麦稻田一起受灾,王十朋有诗:“小麦青青大麦熟,秧老欲移蚕欲簇。皇天弥旬作淫雨,害及农桑一何酷。麦枯秧腐蚕不丝,无食无衣岂能育。”〔55〕
嘉湖一带的蚕桑业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黄氏日抄》中咸淳八年春的劝农文中有:
令太守是浙间贫士人,生长田里,亲曾种田,备知艰苦,见抚州农民与浙间多有不同,为之惊怪,真诚痛告,实非文具,愿尔农今年亦莫作文具看也。浙间无寸土不耕,田垄之上又种桑、种菜,今抚州多有荒野不耕,桑麻菜疏之属皆少,不知何故?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56〕
嘉兴地区地势较高,且有大量空闲地。在唐代,“嘉禾之田,际海茫茫,取彼榛荒,画为封疆。”这是开辟屯田时的景观。“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故道既湮,变沟为田。朱公浚之,执用以先,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中亦有船。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57〕尽管水利规划如此之有序,若军队难以组织蚕丝业,市场经济不兴,蚕桑业也不会大盛。宋代以后小农经济兴盛,作为适于小农密集化产业的蚕桑业才随之兴盛。嘉兴界在宋代仍有高大树桑。叶绍翁有诗:“犬驯迎且吠,儿小笑还啼。樱熟施鱼网,桑空卧竹梯。枯枝禽啄折,野草鹿眠低,屋后登山路,牛栏更向西。”摘桑叶仍用竹梯,说明是树桑,屋后有山,说明靠近天目山。还有一处诗提到竹梯:“田因水坏秧回放,家为蚕忙户紧关。黄犊归来莎草阔,绿桑采尽竹梯闲。”〔58〕水坏秧田的形势下农家闭户饲蚕,田野中桑叶采尽,只剩竹梯。
嘉兴平原的特点是有许多高地,这些高地有着适于植桑与种水稻的土壤,而植桑的旱地是长期人力堆叠形成的。
它 (旱地黄斑土)分布在本区东部水网平原的高地,比水田要高出1-4公尺,离河港在3公尺以上,海拔高度约在6公尺以上。大部分都成带状围绕在沿河两岸的高地上。也有一部分是散布在水田中的小桑埂,面积不大,宽度自数公尺于数百公尺 (大多数只有几十公尺宽),或甚至只有数分面积,成为零星块状分布在圩田的土墩上。这些大部分都是人工挖河泥、挑稻秆泥等堆积起来的。〔59〕
江南的水稻土与圩岸土是长期人工耕作与堆叠而成的。较高的土地分类学上称为“平地潮土冲积性水稻土桑基水田”,低水田一般称为“平地潮土潜育性水稻土桑基水田”。〔60〕除了人工耕作与堆叠以外,部分地区的感潮环境也影响了桑基环境与桑树的形态。钱塘江两岸盐化程度高,桑树根系发育有限,难以形成高大树桑。“钱塘江北百里余,涨沙不复生菰蒲。沙田老桑出叶麤,江潮打根根半枯。八月九月秋风恶,风高驾潮晚不落。鼓声冬冬橹咿喔,争凑富春城下泊。”〔61〕杭州一带有培植低桑的优越条件,而嘉湖地区受杭州一带影响,高产的低桑很快得到了大推广。杨万里言:“树树低桑不要梯,溪溪新涨总平堤。杜鹃知我归心急,林外飞来头上啼。”桑树很矮,不用梯即可采桑。〔62〕范成大也有诗歌提到余杭一带的植桑。“落花流水浅深红,尽日帆飞绣浪中。桑眼迷离应欠雨,麦须骚杀已禁风。牛羊路杳千山合,鸡犬村深一径通。五柳能消多许地,客程何苦镇忽忽。”在这里,圩田经营与蚕桑业是最繁重的劳动。〔63〕
另外,水灾频仍也会使圩岸桑形趋于低矮。直到元代,桑树仍常在水灾中枯死。“浙西在水中做世界,官司常常深浚水路,居民常常修筑围塍。自丙子年水政废弛,积水不去,一遇淫雨泛滥,桑柳枯朽,田土荒芜,百姓离散亡。”多年桑可能未长到可大量产叶时,就因遇到水灾而枯死。乡村社会重视桑柳护岸。“乡村钉塞筑坝,河港皆在田围中间。古来各围田甲头,毎亩率米二斤谓之做岸米,七八月间水涸之时,击鼓集众,煮粥接力,各家出力浚河,取泥做岸。岸上种桑柳,多得两济。近因水涝,围岸四五年不修治,状若缀旒,桑柳枯朽。”修圩岸时要取土种树。“更令田主从便栽种榆柳桑柘所宜树木,三五年后盘结根窠,岸塍赖以坚固,此诚良久之计。”〔64〕无论如何,元代苕溪一带近山区地带矮桑得到了推广,矮桑尤其在水灾环境下有推广潜力。吴兴人康棣有诗言:“吴蚕缫出丝如银,头蓬面垢忘苦辛。苕溪矮桑丝更好,岁岁输官供织造。不知何岁转省输,从此居民受烦恼。今年省官贤且明,省中庶务多变更。”〔65〕“苕溪矮桑”,应是苕溪入湖州一带的山区和溇港圩田区的低桑。
南宋时期,蚕桑业收入比重上升,夏季收成以蚕麦并称。乾道元年,湖州一带“二月寒败,首种损蚕麦,六月水坏圩田,饥疫殍徙者不可胜计。二年正月,淫雨至于四月,夏寒损稼,蚕麦不登。”〔66〕在嘉兴,元以后出现干田化趋势,高地引水灌田,河网更形复杂,围田越来越小,桑基越来越细,大桑树益难有生存环境。同时,城市的发展造成对桑叶的大量需求,各行业的人几乎都在闲时养蚕。王炎曾提到铁匠养蚕: “士农工商,虽各有业,然煅铁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使不耕种水田,春月必务蚕桑,必种园圃。今已仲春,拘而用之,使之蚕桑失时,种莳失节,终岁必有困穷冻饿之患。”〔67〕大量养蚕要求更高的桑叶产量,从而推广了矮桑的种植。
三、溇港地区的沃土与植桑
宋代溇港的发展与太湖扩张相关。太湖是因东部排水不畅而成,〔68〕北宋时修建了吴江长桥,下游淤积加甚,太湖遂有所扩张。单谔曾在天旱时看到过太湖露出“昔日邱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数里之间。信知昔为民田,今为太湖也,太湖即震泽也。以是推之,太湖宽广逾于昔时”。〔69〕淤积加甚除了使湖面扩展外,还形成了一部分湖田。
方今淮甸为国藩篱,震泽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无先焉。盖闻毗陵、吴兴之间,沦为沮洳者,皆故墟井聚落也。桑田积多,征赋积减。说者颇咎漕堤,曰禹迹三江仅松江存耳。自堤作而江不足以泻湖,由是岁患涝溢,宜决之便。〔70〕
苕溪水流带来的泥沙使湖田淤积加剧,湖田随之增多。当然,苕溪水流也有一个由清变浊的过程。唐人《白苹亭记旧编》云:“天目山南来之水自临安余杭至郡南门二百六十余里,又地多湫泊,故其势缓而流清;北来之水自安吉至郡西门,百四十里,又岸多山迫,故其势急而流浊。故司漏者权其重轻,独取南来水,但西溪有七十二湾,水势微杀,不为郡城害。”〔71〕多有苕清霅浊的记载。吴兴有王氏园,“王子寿使君家,于月河之间,规模虽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临流有三角亭,苕霅二水之所汇,苕清霅浊,水行其间,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晓者。”〔72〕苕溪总体上的变浊是由山区开发引起的。现代东苕溪侵蚀模数为46.7吨/平方公里,西苕溪侵蚀模数为94.2吨/平方公里。〔73〕湖田与圩岸增多,使低矮的条桑得以推广。
吴江长桥下游淤塞,湖流在湖州溇港处也必流缓停淤,配合各种茭草的随同积淀,土壤的生物过程与地质过程协同发生,溇港区土壤逐步形成。元时的溇港有许多没有置闸。
湖州溇港:按《吴兴志》载六十三处,自大钱港以东二十六处。向年于溇港桥门置立闸版,如遇东北风起,闭闸以防潮浪之暴涨;若值雨涝,开闸泄水入湖;若值亢旱,闭闸积水灌田。于至元甲午年,差官相视,据相视得自纪家桥港、大钱港以西三十七处不曾置锸,除大钱荻浦等五处水势深阔,难以置立外,有三十处今拟一体添置。〔74〕
溇港对水流动态十分敏感,元朝是溇港快速发育并基本定型的时期。受天目山冲积和湖流淤积的影响,加上湖溇区茭草的堆积,圩岸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含氮量都很高。1959年白雀公社太湖沿岸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达3%,氨态氮和硝态氮含量分别达到3级和2级,常年产量400斤/亩左右。溪东大队的迹四圩、迹二圩和东荡圩的土壤耕性“疏松,耕田表土不会大块,烤田后不会形成大裂缝。透气性好,耕层在4-5寸左右,田底很平,有夜潮,施肥见效快。”〔75〕早期的溇港由于天目山尚未大量开发,冲积区内的水流很清,淤积土壤的质地也更好一些。湖流沿太湖岸由西向东流动,最终流向东太湖的吴淞江一带的出水口,湖流减慢,淤积加快,逐渐在东塘运河外围形成七十二溇港。
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言: “今东北之民流徙者众,东南弃田畴者多,平江有湖浸相连,塍岸久废,近或十年,远或二十年,未尝有人疏导者;有地力素薄,废为草莱,潦涨之余,常若沮洳,未尝有人耕垦者,悉号逃田。”〔76〕湖田既称逃田,说明战争时一度放弃,以后在官方的催督下重新开发。湖田区也形成一些封闭的小环境,杨万里发现吴人“河畔多凿小沼,与河相通,架屋其上,藏舩其中。”有诗言: “非港非沟别一涯,茅檐元不是人家。不居黔首居青雀,动地风涛不到他。”在这些地方也有桑畴。“夹岸濒河种稚桑,春风吹出万条长。舩行老眼浑多忘,唤作西湖插拒霜。”〔77〕官方督修这些湖田时,往往就是统一规划河道时,小环境便为河道规划所统一。淳熙十五年,湖州知州赵恩上奏道:
湖州实濒太湖,有隄为之限制,且列二十七浦溇引,导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门,以为蓄泄之所,视旱潦为之启闭。去岁之旱,高下之田,俱失沾溉,委官访求遗迹,开浚浦缕。不数日间,湖水通彻,远近获利。而于斗门,因加整葺,乞诏守臣逐岁差官亲诣湖堤,相视开浚浦溇,补治斗门,庶几永久。〔78〕
溇港之岸易受太湖风浪的冲击,非常不稳定,只有植树才能巩固圩岸,植桑因此大兴。明代江有源认为古人在“诸老岸处栽桑,柘种茭芦护堤固岸,纤悉备具,此所以无水患也,而今皆弛矣。间有知置闸之利者,又置之不得其所,名以节水,而反以壅水,此于兴工之后所当多方讲求,曲为处置,以开吴民百世之利者也。”〔79〕
与湖州相比,吴淞江上游种桑较少。“其土污潴,其俗轻浮,地无柔桑,野无宿麦,餁鱼饭稻,衣葛服卉,人无廉隅,户无储蓄。”吴淞江圩田区长期未能在桑蚕业上有所发展,太湖内的东西洞庭二山却有发达的蚕桑业。郭受的《记》中有:“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舄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苹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故岁一顺成,则粒米狼戾,四方取给,充然有余。出乎胥口,以临震泽,积水无涯,两山对峙,桑田翳日,木奴连云,织纴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陆转,无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壮子,无不贾贩以游者。”〔80〕吴江与吴县一带的太湖溇港围田处当时没有植桑的习惯,工部侍郎李擢也认为“平江水乡,不可植桑柘”。〔81〕
湖州溇港区则早已有桑蚕业。范成大有诗言:“清晨出郭更登台,不见余春只么回。桑叶露枝蚕向老,菜花成荚蝶犹来。”在一年四季中,蚕桑业占了重头。晚春时节农民养蚕繁忙,以致平日很难相见。“邻曲都无步往踪。”农民只在采桑的时候相见。“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地处太湖之滨的人利用杂草堆积成的葑田护岸。“污莱一稜水周围,岁岁蜗庐没半扉。不看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织女们在夏日缫丝织绢,“百沸缫汤雪涌波,缫车嘈囋雨鸣蓑。桑姑盆手交相贺,绵茧无多丝茧多。”又有:“小妇连宵上绢机,大耆催税急于飞。今年幸甚蚕桑熟,留得黄丝织夏衣。”女人纺织的时候正是蚕月以后,这时稻田上男人正忙戽水。“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82〕溇港区的植桑形成麦黄桑绿之景观。范成大有词曰: “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83〕收麦与收茧同时,桑绿与稻青、麦黄同时。王安石的诗应是代表了大多数地区的桑稻景观,“缫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84〕收割小麦以后,水稻和桑树都呈青色。
四、小结
作为江南地区最为发达的生态农业类型,桑基农业很早已经出现,宋元时期才开始大扩展。山区的开发在整个太湖地区的开发序列中是靠前的,六朝时低地尚未大量开发,山区经济就已经很发达,并有发达的桑蚕业。随着农业向平原低地圩田转移,集约化的小农种植业因此形成,在地理和经济相结合的推动下,桑基农业才逐步发展起来。宋元正值江南市镇化发展时期,圩岸植桑的过程也是水网化与市镇化的过程,这种高效率的生态农业类型与河网化、市镇化相同步。到了元代,由于湖溇区在湖流的影响下不断发展,低地地区的桑基农业更形发达,而这一地区也是桑基鱼塘广泛存在的地区。总之,江南的发展是生态、经济与人文互动发展的产物,生态系统的集约化与优美田园推动了江南的发展。
〔1〕〔44〕补农书研究〔C〕.陈恒力编著.王达参校.农业出版社,1958.184,268.
〔2〕梁书:卷五三·沈瑀传〔M〕.中华书局,2011.768.
〔3〕〔同治〕湖州府志:卷六十二·名宦录一〔M〕.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4〕〔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85.
〔5〕〔明〕栗祁.(万历)湖州府志:卷一·郡建;卷二·山川〔M〕.明万历刻本.
〔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4142.
〔7〕〔宋〕郑虎臣.吴都文粹:卷四〔C〕.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宋〕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卷中〔M〕.民国景宋刻本.
〔9〕〔宋〕庄绰.鸡肋编:卷中〔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李昉.文苑英华:卷二百八·乐府十七,吴均:陌上桑〔C〕.明刻本.
〔11〕〔嘉泰〕吴兴志:卷十五·县令题名〔M〕.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6册〔Z〕.杭州出版社,2009.2679.
〔12〕〔20〕〔嘉泰〕吴兴志:卷二十·物产〔M〕.2840,2828-2829.
〔13〕〔33〕〔7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C〕.稿本.
〔14〕〔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十,祈雪雾猪泉出城马上作赠舒尧文〔M〕.明成化本.
〔15〕〔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之十七·杂考四〔M〕.嘉靖三十九年刊本.
〔16〕〔宋〕刘一止.苕溪集:卷二十二·纵云台记;卷五十,墓铭〔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九·论田亩敷和买状〔M〕.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8〕〔宋〕陈旉.陈旉农书:卷上·地势之宜篇第二〔M〕.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19〕〔宋〕苏轼.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三十一,墨妙亭记一首〔M〕.
〔21〕〔宋〕陆游.剑南诗稿校注:卷一·初夏道中;卷三十·示客〔M〕.钱仲联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8,2024.
〔22〕〔宋〕卫泾.后乐集:卷二十·晚晴〔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宋〕刘一止.苕溪集:卷六·绿暗山前路〔M〕.
〔24〕〔宋〕攻媿集:卷七·早行〔M〕.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25〕嘉兴专区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编.土壤志〔M〕.1959.5.
〔26〕〔荷〕G.P.Van de ven主编.人造低地——荷兰治水与围垦史〔C〕.詹灿辉等译.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54.
〔27〕〔元〕赵孟頫.赵孟頫文集:卷一〔M〕.任道斌编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2.
〔28〕〔元〕王冕.竹斋集:卷下·陌上桑〔M〕.寿勤泽点校.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188.
〔29〕〔元〕赵孟頫.赵孟頫文集:卷五、七〔M〕.任道斌编校.103,125.
〔30〕〔元〕倪赞.清閟阁集:卷四·余不溪咏二首并序;卷七·吴中〔M〕.江兴祏点校.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99-100,209.
〔31〕〔宋〕郑虎臣.吴都文粹:卷九〔C〕.
〔32〕〔宋〕温革.分门琐碎录校注〔M〕.化振红校注.四川出版集团,2009.38.
〔34〕〔宋〕沈与求.龟溪集·沈忠敏公:卷二,蚕〔M〕.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
〔35〕〔清〕刘清藜.蚕桑备要:第一篇〔M〕.清光绪刻本.
〔36〕〔元〕王祯.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十七,蚕桑门〔M〕.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396.
〔37〕 〔宋〕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八·送棣州唐虞部〔M〕.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38.
〔38〕〔元〕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农器图谱集之十六,蚕桑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732.
〔39〕郑云飞.“荆桑”和“鲁桑”名称由来小考〔J〕.农业考古,1990,(1):324-327.
〔40〕〔41〕石声汉校注.农桑辑要校注:卷三〔M〕.农业出版社,1982.80.
〔42〕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编著.桑树栽培技术〔M〕.1978.1,25-29.
〔43〕〔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M〕.
〔45〕〔唐〕郭橐驰.种树书:卷中〔M〕.明夷门广牍本.
〔46〕〔明〕娄元礼.田家五行:卷上〔M〕.明张师说校订本.
〔47〕〔48〕〔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二·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奉懿旨撰〔M〕.四部丛刊景元本.
〔49〕〔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风土〔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51〕〔宋〕陈起.江湖后集:卷二十·李龚,采桑行〔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宋〕陈起.江湖小集:卷十七·陈允平,西麓诗稿,采桑行〔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宋〕陈起.江湖小集:卷四十·叶茵,顺适堂吟稿,蚕妇叹;卷四十一·叶茵,顺适堂吟稿,晚年辟地为圃,僭用老坡和靖节归田园居六韵;田父吟〔M〕.
〔54〕〔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二十八·将至石湖,道中书事〔M〕.富寿荪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87.
〔55〕〔宋〕王十朋.梅溪集:卷三·与赵安抚乞疏岳〔M〕.四部丛刊景明正统刻本.
〔56〕〔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七十八·公移,咸淳八年春劝农文〔M〕.元后至元刻本.
〔57〕〔清〕董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李翰一,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M〕.清嘉庆内府刻本.
〔58〕〔宋〕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六十;叶绍翁.靖逸小集·嘉兴界,田舍小憩〔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嘉兴专区土壤普查土地规划工作委员会编.土壤志〔M〕.1959.71.
〔60〕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流域自然资源地图集〔M〕.科学出版社,1991.第20图:太湖流域土地资源.
〔61〕〔宋〕晁补之.鸡肋集:卷九·富春行赠范振〔M〕.四部丛刊景明本.
〔62〕〔宋〕杨万里.杨万里诗文集:卷十三·春尽舍舟余杭,雨后山行〔M〕.王琦珍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224,510.
〔63〕〔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三·余杭道中〔M〕.富寿荪标校.28.
〔64〕〔74〕〔元〕任仁发.水利集:卷三〔M〕.明钞本.
〔65〕〔元〕草堂雅集:卷三·古诗一首上复斋郎中〔M〕.顾瑛辑.杨镰等整理.中华书局,2008.332.
〔66〕 〔民国〕南浔志:卷二十八·灾祥一〔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卷上〔C〕.上海书店,1992.291.
〔67〕〔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十二·上宰执论造甲〔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孙顺才,黄漪平主编.太湖〔M〕.海洋出版社,1993.83.
〔69〕〔宋〕单锷.吴中水利书〔M〕.清嘉庆墨海金壶本.
〔70〕〔宋〕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之四十三·策问十四首〔M〕.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
〔71〕〔嘉泰〕吴兴志:卷五·水〔M〕.2547.
〔72〕〔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吴兴园圃〔M〕.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8.11.
〔73〕潘凤英.太湖东山连岛沙坝形成的探讨〔J〕.南京师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1981,(2):23-30.
〔75〕吴兴县白雀人民公社土壤鉴定报告,1959年5月〔Z〕.湖州档案馆藏.W73-12-17.
〔77〕〔宋〕杨万里.杨万里诗文集:卷二十九·藏舩层,桑畴〔M〕.王琦珍整理.509-510.
〔78〕〔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十七下〔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9〕〔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四章疏·江有源请专官治水疏,万历十五年上〔M〕.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8册〔C〕.482.
〔80〕〔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七·县记〔M〕.陆振岳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542,538.
〔8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四〔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2〕〔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一·初夏二首;卷二十七·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M〕.富寿荪标校.11,373-374.
〔83〕〔宋〕范成大.石湖词·蝶恋花〔M〕.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84〕〔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六〔M〕.清乾隆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