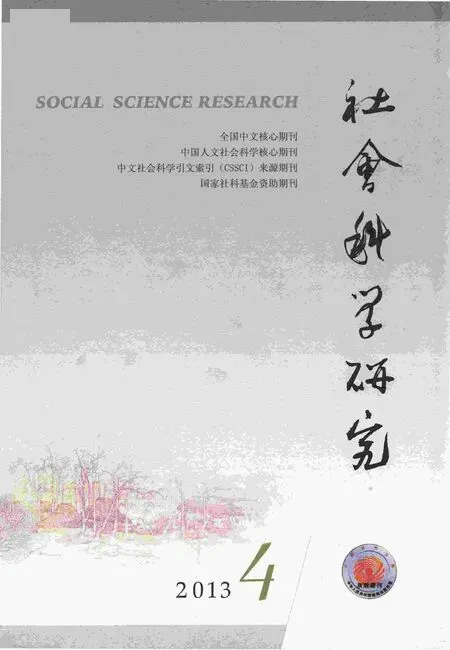新诗“题词”:不容忽视的伴随文本
蒋林欣
翻阅《女神》(郭沫若)、《红烛》(闻一多)、《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李金发)等著名的现代新诗集,异彩纷呈的“题词”①“题词”与“题辞”学界常常混用,如穆旦译拜伦《青铜世纪》将其题下引自维吉尔的诗句“并非阿基里斯的敌手”称为“题词”,参见《穆旦译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18页;裘小龙译艾略特《杰·阿尔弗莱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题下的引文时注有“这段题辞引自但丁的《神曲》”,参见《四个四重奏》,漓江出版社,1985年,3页。本文统一使用“题词”。纷至沓来;再看胡适、冰心、王独清、冯至、戴望舒、艾青、贺敬之等人的不少诗作也附带“题词”,为新诗打上了醒目的标记。在符号学上,题词属于典型的“伴随文本”②伴随文本 (Co-text),由符号学专家赵毅衡新近提出,指“伴随着一个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参见《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41页。,浸透着多种社会文化因素,携带了大量的附加信息,随诗歌文本一同发送给读者,具有一种文学与文化建构的功能。然而,在众多研究者的视域里,题词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仅在品鉴具体诗人诗作或探讨中外文学影响关系时被顺带提及,如一些关于闻一多对古典诗歌的传承、郭沫若与歌德的文学关系、《红烛》赏析、《女神》细读的文章中散见对其题词的简略叙述。当然,也有少量以“题词”或“题辞”为名的文章关注到了文学作品中的题词现象③如闵抗生《尼采与〈野草·题辞〉》,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3期;高杰《〈日出〉题辞考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汤永宽《是瓶子还是笼子?——关于〈荒原〉题辞的释文》,载《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黄仕忠《“玉茗堂四梦”各剧题词的写作时间考》,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等等。,但其问题在于:第一,这些题词的形式混杂,有散文、诗词,有自题、他题和引题,涉及古今中外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散乱零碎;第二,对题词的分析大多附属于文本的思想意义,没把题词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第三,没有着力聚焦以引题为主的新诗题词,没有对其来源、功能、走向等作整体观照,罕见相关研究专章。本文试图对新诗题词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考其源流,举其功能,并以此管窥它与现代新诗、现代文学、现代文化思潮流向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文艺“欧化”潮流里的“舶来品”
新诗题词是一种特殊的“序文”,即位于一本诗集、一首诗、一节诗之前的所引用的诗句或言辞,“引用”是其明显的特征,通常标明了出处,具有“典故”意味。它与法国文艺理论家萨莫瓦约所说的“文首”、“卷首题字”、“卷首语”很接近〔1〕:常在文本开篇,与文本主体分隔,属于一段引言,源自另一个经典文本。新诗题词排除如散文诗《野草》、戏剧《日出》等其他文体文本中的题词,排除如《人力车夫》、《老洛伯》等诗篇所附带的、古典文学中就很常见的散体序文,排除诗集《星空》、《瓶》的“献诗”等诗人自题或读者他题的祝词、献词等属于应用文类的题词,且有别于《红烛》集的《红烛》、《女神》集的《序诗》等属于文本而不是伴随文本的“序诗”。只有诗歌文本前所引用的诗句或言辞才是新诗独有的标记,是在新诗中首次出现的、特有的题词现象。
新诗题词并非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直接继承①在古典文学中能找到的只有文序、“玉茗堂四梦”的作者题词、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后来者题词等。,它究竟来自何处?考察最初的几本新诗集就会发现它是五四时期文艺“欧化”潮流中的“舶来品”。第一本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1920),其中无题词,选入《尝试后集》(1952)的《瓶花》题下录有范成大《瓶花》二首之一,该篇写于1925年;郭沫若《女神》 (1921)中的《无烟煤》题下有:
“轮船要煤烧,
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
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②这是司汤达1834年致狄·费奥尔信中的话。
本诗最早发表于1920年7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俞平伯《冬夜》、康白情《草儿》、汪静之《蕙的风》(均为1922)等集都不见题词;冰心《繁星》(1923)中也没有题词,《春水》(1923)前面有录自《繁星·一二○》的诗句,时为1922年;闻一多《红烛》集(1923)中的《西岸》题下有:
“He has a lusty spring,when fancy clear
Takes in all beauty within an easy span.”
──Keats
该诗写于1920年7月13日,发表于9月24日《清华周刊》。据此可推断,郭沫若当是现代新诗史上使用题词的第一人。而郭沫若所推崇的歌德、席勒等诗人就用过题词,如席勒《大钟歌》题下有:
我呼唤生者,
我悲悼死者,
我击碎雷霆。③这是瑞士夏天豪森市大教堂内大钟的钟铭。
歌德为悼念席勒而作的《席勒〈大钟歌〉跋》又有引自席勒诗《大钟歌》的末句作为题词:
让它发出的第一次声音
标志着本市的欢喜与和平
郭沫若在新诗中使用题词无疑受到了歌德、席勒的影响,因为他早就接近了他们,并在1919-1920年间翻译了歌德《浮士德》中的《夜》、《风光明媚的地方》、《献诗》等〔2〕,1921年又在席勒叙事诗《手套吟》的影响下写成《暴虎辞》,这些都与他写作《无烟煤》、《女神之再生》等诗在同一时期,《女神之再生》引了歌德《浮士德》的诗句作题词。闻一多在清华就接触到济慈、华兹华斯的作品,留美期间更是有拜伦、雪莱、济慈、丁尼生等“在书架上,在桌上,在床上”等着他〔3〕,而这些诗人无一例外地都使用过题词④如拜伦《雅典的少女》《拿破仑颂》《青铜世纪》、雪莱《死亡》《自由颂》《希腊》、济慈《咏声名》《睡与诗》、丁尼生《玛丽安娜》《拂晓》等篇都有题词。,他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西岸》引用济慈的诗作题词,充分说明他使用题词与济慈等人不无关系。可见,新诗题词直接来源于西方文学。
新诗题词是对西方文学样式的模仿,这种模仿不是偶然行为,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在新文学势不可挡的“欧化”潮流中发生的。“欧化”是白话诗诞生时的文学主潮,新文学开启了包括语言、形式、标点等元素在内的全面“欧化”的进程,傅斯年就极力主张“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 (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4〕来创造欧化的国语文学。在新诗中使用题词就是当时文艺“欧化”倾向的一个具体表现,尽管郭沫若、闻一多等人都很少谈到使用题词的缘由,或许这并非刻意的追求与标榜,而是他们在文艺欧化潮流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旧体诗词的“镣铐”被打破,新的诗体规范尚未建立,对于什么是新诗、究竟该如何写新诗等问题莫衷一是,取法西洋文学无疑是一条捷径,模仿也就成了一时的风气。胡适就说创造新文学要以西洋文学名著为模范,因为“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而“西洋文学的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5〕,新诗题词就是“欧化”潮流中的“舶来品”,是取法西洋文学的一个例证。
二、对现代自由诗形的拓展与丰富
作为伴随文本,题词是诗歌文本和外部世界的中间地段与连接点,如同德里达的专门术语Hymen①他用此词说明文字的双重表示功能,既非内亦非外,既在内亦在外,既区分又连接,既不显示也不隐匿。,既在文本内又在文本外,只要它随文本产生就难以离场,在与文本的结合中从诸多层面参与了现代诗学的建构,而这对于探索中的新诗建设特别重要。伴随文本是整个文本的“框架因素”〔6〕,即形式的组成部分,新诗题词的诗学建构功能首先就体现在对现代诗形的拓展与丰富上。
第一,新诗题词打破了中国古典诗歌圆润而封闭的诗形,使现代诗歌文本形式呈现出开放的形态。古典诗歌的形式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常有固定的模式,如五七言绝句、律诗,词、曲等都须符合相关字数、行数、韵律、词牌、曲调等方面的规定,不得随意改变。虽然不少古典诗赋伴随着文序,但其功能重在交代写作缘由或概述所涉事件本末,在形式和意蕴上都与诗歌文本的距离较远。题词使得现代新诗的诗形突破了那些封闭的、单一的、程式化的模式,多向度延展。尽管新诗文本依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并不完全与外界隔绝,题词为它增加了与外界相连的中间地带,或者说开了一扇窗,通过这个窗口,文本可以与它所涉及的文学历史进行对话。如胡适《瓶花》的题词:
满插瓶花罢出游,
莫将攀折为花愁。
不知烛照香薰看,
何似风吹雨打休?
范成大《瓶花》二之一
范成大的《瓶花》由四行二十八字组成,遵循了“七言绝句”这种体裁的规则,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圆满得找不到任何出口,如果要追溯它与其他文本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只能根据文本内部的典故去寻找,或者从范成大的同题诗、其他诗人同题材的诗、同属“七言绝句”体裁的诗等型文本②型文本是显性伴随文本的一种,是由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表明文本所从属的集群,如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作者、同一种题材、同一种体裁等。去探寻。胡适的《瓶花》由于题词的存在而具有开放性,它并不遵循某种固定的体裁模式,其他任何诗作的形式都与之不同,它有两个既区别又联系的系统,无需从文本内部寻觅,透过题词古典《瓶花》这一窗口,我们就会看到一首意境优美、技巧纯熟的现代诗正向“玉人和月摘梅花”的古典意象回流,流向一切关于花月美人的文学历史。
第二,新诗题词的位置并不固定,既可以落在标题内,也可以落在标题外,还可以落在一首分节长诗的中间,它的不断游移更增加了新诗文本形式的活泼多样性,创造出一种舒展的样态和从容的节奏。题词经常出现在一首诗的诗题之后、诗行之前,如李金发《游wannsce》、《絮语》、《远地的歌》等绝大多数诗的题词就位于这一典型位置;有的题词位于一首诗的诗题之前,这在闻一多的诗中最常见,《雨夜》、《青春》、《孤雁》等均如此;有的诗在诗题前、诗题后都有题词,如闻一多《李白之死》诗题之前有李白诗句“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诗题之后又有李白诗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还有的题词位于一首诗的中间,如郭沫若《胜利的死》共有四节,每一节之前都引两句苏格兰诗人康沫尔《哀波兰》里的诗。
题词位置的不确定性使得文本形式舒展自由,节奏从容舒缓,张弛有度。位于文本之前的题词形成一个过渡空间,使读者在尚未阅读文本时先酝酿一种情绪,再缓步进入文本世界,有如曲径通幽之妙,例如李金发《游wannsce》题词:
“看尽鹅黄嫩柳,
都是江南旧识。”③出自姜夔《淡黄柳》,原诗为:“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识”——笔者注。
如同电影的片头、乐曲的前奏,尚未见得文本,题词所弥散着的那股浓稠的乡愁早已渗入人心,这与诗人严重的思乡病相呼应。而像《胜利的死》一诗里位于文本之中的题词则可让读者暂时抽离文本所营造的意境与情绪,到文本之外小憩,犹如古典建筑的回廊与凉亭,于曲折婉转中意味无穷。在诗形上,无论处于哪个位置,题词都标记了文本独一无二的样式,赋予了新诗如同民间手工艺术品般的唯一性特征,不像律诗、绝句那样类似机械复制时代的流水线产品的整齐划一,闻一多、郭沫若、李金发等人带题词的诗作在诗形上就各不相同,而“唯一性”正是“艺术品的光韵”④瓦尔特·本雅明曾说:“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参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87页。之所在。
第三,新诗题词突破了仅从文本内部寻找形式的传统,文本之外的因素首次进入探索者的视线,预示着诗歌形式由内向外延展的趋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在中国文学史上,古典诗歌发生了多次变革,由四言诗到五言诗到七言诗,到律诗到绝句,甚至到词到曲,字数、行数、音韵等方面的规则都随之而变,但那些变革在形式上无一例外地囿于文本内部。现代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入手,要打破旧镣铐,探索新形式,如胡适所说的音节、平仄、句法,钱玄同讨论的长短、音韵,刘半农“破旧韵,造新韵”及增多诗体,陆志韦的长短句、无韵体,闻一多的匀齐、建筑美等,但几乎所有这些形式要素都集中在文本内部,很少涉及题词这样的伴随成分。他们的形式探索在理论主张上并没突破诗歌文本,并没从文本之外的角度寻找新的诗形,但在写作实践中又借鉴、模仿了西方文学的题词,这就在无意识中从新的角度、新的侧面为新诗诗体建设做出了尝试性的努力。
尽管并不是每一首新诗都有题词,题词也不是新诗必要的伴随文本,尽管在后来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的重建现代诗体的探索中,题词又被遗弃,但它拓展与丰富了现代自由诗形,甚至有可能改变仅从文本内部谈形式的传统观念,这无疑参与了新诗文本的诗体建构。再则,现代新诗因题词而具有开放性、灵活性,题词的出现既契合了诗体大解放、寻求新形式的文学潮流,更契合了新文学崇尚自由的精神气质,这又从更深层次参与了现代诗学的建构。
三、对文本意蕴生成的衍射与规约
新诗题词的诗学建构功能不仅体现在文本形式上,而且更深入地渗透到文本意蕴层面,因为它与诗歌文本之间是互文关系,互文手法会使文本产生新的内容,形成由此及彼的衍射效应,流溢出某种特殊的光彩,进而使文学成为“一种延续的和集体的记忆”〔7〕。题词的这种衍射效应主要体现在对诗思的触发、意象的生成、意蕴的扩散等方面,涉及诗人创作和读者接受两个维度。
一是诗思的触发。陆机认为,作文之由不外两途:感于物与本于学,“颐情志于典坟”〔8〕就是说博览先代的优秀作品可以陶钧文思、获得灵感。新诗题词大多数出自历代名家名作,诗人常先有阅读积累和生活体验,创作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其心境可能与题词所在原文本的情绪类似,受原文本的启发,灵感闪现,诗思纷纭,进而挥毫成诗,如闻一多《孤雁》的题词:
“天涯涕泪一身遥”
——杜甫
写此诗时的闻一多正在赴美途中,对渡海生涯大失所望,心情烦闷,“愈加渴念我在清华的朋友。这里竟连一个能与谈话的人都找不着”〔9〕,诗里满是游子思乡的情怀与对祖国母亲的眷恋,反复抒发“失路的游魂”的“零落的悲哀”,泣诉“不幸的失群的孤客”那无边的酸楚。这种人生体验与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流寓成都时,因战火横飞、诸弟远隔天涯,诗人孤身飘零、忧国思亲的心情无比沉痛而作《野望》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的情绪十分相似,而闻一多又是时常“不能忘记杜甫”〔10〕的人,正是杜诗触发了闻一多的情思,促成了《孤雁》,后来编订《红烛》集时又以“孤雁”作为海外系列诗作的“篇”名,说明他在海外孑然漂泊的心情与杜甫当年的心境遥遥相通。又如冯至《北游》的题词:
“……他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
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
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
——望蔼覃:小约翰
这是鲁迅译的“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小约翰》末尾“紧要而有力的一句”〔11〕。此时的冯至独自在哈尔滨谋生,他在冰冷而灰暗的陌生城市里“油一般地在水上浮着,魂一般地在人群里跑着”〔12〕,在雪大风寒的夜里,独立街心,反思自我的前进与沉沦,继而写成长诗《北游》。他远离熟悉的一切,在孤独寂寞中思考理想、价值等严肃的人生问题,这种心境与天赋异禀的小约翰离家畅游世界,追问人生的理想和意义,苦苦寻找那本“解读人生所有疑问的大书”而走过的路是多么类似。那“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的身影既是小约翰也是诗人自己,是他们合二为一的重影,题词所在的原文本《小约翰》无疑触发了冯至写作《北游》的灵感及构思。
二是意象的生成。意象是古典文论和文学中的关键词,但在最初的白话新诗中,意象缺失是突出的症候,被闻一多批为“一种极沈痼的通病”,“很少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13〕。不满于新诗“淡乎寡味”,闻一多十分注重诗歌意象的营造,极力“从古典诗歌中找回传统”〔14〕,题词就对他诗歌意象的生成起到了定调与点睛的作用,如“红烛”、“孤雁”、“红豆”等意象的生成与题词所在原文本的意象紧密相关,原文本的意象甚至成了此文本的核心意象,如《红烛》的题词: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闻一多的核心意象“红烛”直接取自李商隐的“蜡炬”。红烛“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无私奉献精神,及其“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的彻底与决绝,与“蜡炬成灰泪始干”如出一辙。“红烛”意象隐喻诗人那颗火红的心,“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咏红烛就是咏诗人,这是诗人早期满腔热血的誓言,他要像红烛那样“灰心流泪”地“创造光明”,从“红烛”到“心”的隐喻也类似李商隐。李商隐的这首“无题”诗本为寄情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说爱恋至深,只有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刻,相思之泪才会干涸,而此时的闻一多选择了彻底的、无悔的燃烧,要以心火去改变这世界,文本中“红烛”—“心”— “创造”与题词中“蜡炬”— “心”— “牺牲”的模式形成了同构关系,题词就如诗眼,在此,文本的意象“红烛”与题词的意象“蜡炬”相互叠加。
三是意蕴的扩散。新诗题词广阔而神奇的衍射效应还在于对文本意蕴的扩散,使文本意义不断生成,呈现出非自足性和无限衍义的可能。如郭沫若《女神之再生》的题词:

如果没有这段题词,读者就不会如此迅捷地把《女神之再生》与《浮士德》相联系,所能读出的文化因素将在一定时间内停留在“女娲补天”、“共工触山”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层面。但赫然在目的题词首先就宣告了文本的源流,如同路标直接将读者引向《浮士德》,《女神之再生》就不仅仅是中国古典神话的现代演绎,更是异域神话传说与经典文本“横的移植”,象征和谐与创造伟力的“女神”形象也不仅仅是炼石补天、创造人类的女娲,更是西方作为宽恕、恩宠和爱的伟大力量的最纯洁、最完美的体现者圣母玛丽亚在东方的投影,文本意蕴迅速穿越中国本土文化的苑囿,在读者面前展开一条悠远绵长的赫拉克利特河流①赫拉克利特有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波兰著名女诗人辛波斯卡有诗《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透过题词,读者依次看到的是《浮士德》、歌德、德国文学、西方文化……,因为这段题词取自《浮士德》结尾的诗句,它是整篇《浮士德》的提喻,《浮士德》是歌德的提喻,歌德是德国文学的提喻,德国文学又是西方文化的提喻,隐隐约约的“羊皮纸稿本”效应②在中世纪,羊皮纸极其珍贵,僧侣经常把原先写的文字刮掉继续使用,但先前的墨迹还隐约可见。参见《隐迹稿本》,收入《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在此重重交叠,正是题词衍射了这一切,它在瞬间打开读者的视线,发出一声呼唤或唤起一段回忆,使读者简约地回顾与之相关的所有作品,使“全部的文学宝库”与文本“一道在读者的脑中交织”〔15〕,文本意蕴就这样层层扩散开去。
然而,文本意蕴并不会真的无限衍义下去,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庞然大物,任何符号文本既携带了多重含义,也规约了含义的有效性,伴随文本“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16〕,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题词在对文本意蕴进行衍射的同时又对其形成规约,限制读者的阐释,进而限制了文本意蕴多维度衍射的可能,使得文本意蕴只能沿着题词所规定的方向衍射,读者难以偏移这一既定的轨道。例如,面对《女神之再生》,读者首先被题词引导,要理解此文本而不谈歌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浮士德》已在脑海中先入为主,一听到像它这样的经典作品的名字,就“仿佛已经听见它们在下面回响”〔17〕,假如要偏离题词转向儒家思想,就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但事实上本诗与儒家文化并非绝缘。有的研究者已注意到题词的这种规约性,即题词规定了读者的结论,甚至成为一种累赘,“破坏了作品整体的审美价值”〔18〕,这虽有些言过其实,却也不无道理。
题词对诗歌文本意蕴所形成的既不断衍射又无形规约的效应是它参与现代诗学建构的第二个层面,不少新诗的意蕴因题词的存在而更为丰赡,如《红烛》,支撑一个文本的是题词所显示或掩藏的与之相关的整个文学历史,因而具有一种厚重的质感。题词对意蕴的规约又使该文本位于具体的文学、文化语境之中,避免了大而无当的空疏,这种限定性是必需的,萨金特曾说:“乌托邦不存在,通常位于时空中”〔19〕,乌托邦尚且如此,何况文学?
四、对新诗多重文化资源的呈现与记取
新诗题词与诗歌文本之间形成广泛而紧密的互文关系,它“告诉我们一个时代、一群人、一个作者如何记取在他们之前产生或与他们同时存在的作品”〔20〕,因而携带了大量的文学传统与社会文化信息,体现了作者与其所阅读的书籍、所接受的文化影响以及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在与文学历史不停的对话与追忆中呈现出现代新诗的多重文化资源,这是它参与现代诗学建构的第三个层面。
对新诗题词稍作比较分类就会发现它们主要源自两大系统: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例如,郭沫若《女神之再生》引歌德《浮士德》结尾诗句,《无烟煤》引司汤达的话,《胜利的死》引康沫尔的诗,只有《湘累》引了《离骚》,他的题词主要来自西方文学传统。闻一多《红烛》题词引李商隐的诗,《李白之死》引李白的诗,《雨夜》引黄庭坚的诗,《青春》和《秋色——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引陆游的诗,《孤雁》引杜甫的诗,《红豆》引王维的诗,只有《剑匣》引丁尼森的诗,《西岸》引济慈的诗,他的题词主要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传统。
李金发诗歌的题词更为复杂,《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集里的题词十分丰富,数量之多、花样之繁让人叹为观止,在所有的现代诗人中可谓首屈一指,既有陆游、孙道绚、范成大、姜夔等人的古典诗词,又有庄子“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等古代典籍中的话语;既有雨果、魏尔伦、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等人的法文诗,又有莎士比亚、席勒等人的英文诗,还有歌德等人的德文诗;既有西洋诗,还有泰戈尔的东方诗……如《故人》的题词来自陆游的词《沁园春》:“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不相识之神》题下有泰戈尔的诗:
The joy ran from all
the world to build
my body
《Tristesse》题下有魏尔伦的诗:
“Je me souviens des jours anciens et je pleure.”①刘永健译为:“追忆似水的流年,我哭泣。”
《Mal–aimé》题下有席勒的诗:
And forget me,for I can never
Be thine.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见影响李金发诗歌创作的文化资源是多元而繁复的,中西两大文学传统在他的题词里几乎是相互交替出现。
题词所呈现出的这种面貌与新诗的成长环境相一致。一方面,白话文学运动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发生的,新诗也是在对西洋诗的模仿中逐步成长的,西方文化资源无疑渗透到了新诗文本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古典文学传统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性注定了它们与新文学难以割断的血脉联系,本土文化资源必然会渗入新诗的每一滴血液。再加上这一代诗人学贯中西的素养,他们的作品必然融会中西两大传统,郭沫若、闻一多、李金发等人诗作的题词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尽管他们对中西文学传统的取舍各有偏重。
至于诗人们的题词各自偏中偏西或中西交替的原因,主要还是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诗学修养以及个性气质有关。郭沫若虽然也是“受科举时代的余波淘荡过的人”〔21〕,读过《三字经》、《千家诗》等蒙书,做过“赋得体”的试帖诗,但真正引起他文学趣味的还是在留日期间所接近的泰戈尔、海涅、斯宾诺莎、歌德、席勒、惠特曼、华格纳、雪莱、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他既钟情于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又为惠特曼那雄浑豪放的调子所激荡,写出《匪徒颂》、《凤凰涅槃》、《天狗》等“男性的粗暴的诗”〔22〕,摆脱一切旧套,狂飙突进的反传统面目使得他的文化资源选择明显向西方倾斜,他的题词偏向于西方文学传统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闻一多在清华所受的是中西合璧式的教育,但他常对西式的东西感到不满,批评清华“太美国化”,虽然他也接近济慈、拜伦、雪莱,但他更接近杜甫、陆游等,信仰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忠臣”,炽热地爱着祖国的文化,他曾毫不客气地说《女神》过于欧化,缺少“地方色彩”,疑心这是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23〕,他特别倚重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因此他的题词偏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李金发介乎二者之间,他在赴法之前所接触的主要是《左传》、《诗经》、《唐诗》、《古文观止》、《牡丹亭》、《桃花扇》、《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以及《玉梨魂》等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在法国学习雕刻之余苦读法文诗,痴迷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诗,也喜欢雨果、拉马丁的浪漫诗,还读了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小说和泰戈尔诗集法译本,等等,从这一长串书名和人名即可看出李金发所受的文学影响十分庞杂,似乎缺乏主体选择,他因师法象征派而被称为“中国的鲍特莱”〔24〕,但法国意象派、象征派诗人又是从中国传统诗歌、泰戈尔诗歌等东方文学中吸取养料的,这一“出口转内销”的影响关系使得李金发的文化资源选择更加繁复,因而他的题词常常东西穿插,显得游移不定。
此外,新诗题词的来源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传统,那就是现代文化、现代文学自身正在流动中不断生长着的“新传统”,因为有的题词标明了诗歌文本与同时代其他文本的亲密关系。这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引诗人自己的诗,如冰心《春水》集引她《繁星》里的诗句,艾青《向太阳》诗题下以及第四节标题下都引有自己的诗,如《向太阳》的题词为: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引自旧作《太阳》
二是引同时代诗人的诗,如李金发《风》题下有:
欲寻高处倚危栏
闲看垂杨风里老沈尹默
Les vagues blèmes d'Uelin roulent
dans la misère;les vertes collines
sont convertes de jour;les arbres
secouent leurs têtes poussiéreuses
dans la brise,
W.Wordsworth②刘永健译为:“鸟林的白浪在悲惨中流淌,山野遍绿,日光覆盖,树林在微风中点着布满灰尘的头。”
在这里,李金发引了沈尹默的两句旧体诗,这或许是同时代人的诗作首次进入新诗题词的记录。同时,他还引了华兹华斯的法文诗,将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诗句放在同一个文本的边缘,说明沈尹默的诗与华兹华斯的诗一样促发了他的诗思,可作为同样重要的伴随文本。其实,这段题词所呈现的不仅是现代和西方两大文化资源,还有古典文学资源,沈尹默的旧体诗就涵括了古典与现代两个传统,三种话语空间在此并置,既说明了李金发所吸取的文学资源的丰富性,又透露出一个信息:现代新传统很可能与古典传统和西方传统形成三鼎足之势,题词之妙也由此可窥一斑。
三是引民歌,如贺敬之的《拦牛歌》、 《罗峪口夜渡》等,《拦牛歌》题词为:
打牛来呵,打!
快打牛来呵,打!
山上有狼来了呵,
快回去……
——陕北民歌
民歌入题词,显然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歌“大众化”、回归“民族形式”等成了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都涉及利用歌谣、乐府、鼓词、小调、唱本、民谣等民间“旧形式”,写出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新诗歌”来教育大众。贺敬之的民歌题词就是这场摒弃古典传统与西方传统之后的文化“寻根”潮的一个微缩的侧影。
这些来自诗人自己的诗、同代人的诗与地方民歌的题词,既显示了诗人们与当下同步,也说明现代新文学传统正在形成。“传统”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现代文学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场的,但它又在形成自身的传统,清理新文学的传统是近年来学界一大热点,有的研究者就从互文的角度探讨了当代文学文本与现代文学传统中已有文本的关系,如王安忆与张爱玲、当代文学苦难叙事与左翼文学等〔25〕。新诗以现代文学作品为题词比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互文关系来得更早更及时,是现代新传统散落的历史碎片的印证。
题词对新诗多重文化资源的呈现与记取不仅直接参与了现代诗学建构,而且是一种更为深层的文化建构。因为互文性指涉的是文本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更是“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26〕,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西方文学传统与新文学传统就是现代三大文化话语空间,而题词又主要来自这三大传统,它的存在就使得新诗文本参与了当时的文化话语空间,进而实现了自身文化建构的功能。
五、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迅速凋零
对新诗题词作一详细的统计还会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诗作中①李金发《食客与凶年》1927年5月初版,主要收录1923年2月到5月间的诗,编订于1923年5月;《为幸福而歌》1926年11月初版,主要收录1923年到1924年的诗,编订于1925回国前。,从20年代后半期直到40年代末,题词愈来愈贫瘠,虽然冯至、艾青、贺敬之等仍有零星的题词,但总体上很稀疏。郭沫若的题词主要在《女神》、《星空》 (1923),到了《瓶》、《前茅》、《恢复》等几乎销声匿迹,闻一多的《死水》集满是文序,没有一首诗有题词;李金发后来诗作甚少,诗歌生命基本终结,更不用说题词了;冯至《北游》时期有题词,但在他的《十四行集》中并没有题词,可以说,新诗题词在1920-1925年间昙花一现之后就迅速凋零了。
新诗题词为何如此短命?这须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首先,与现代新诗自身的整体走向有关。白话新诗经过打破一切旧镣铐的“破坏”期,逐渐走出盲目模仿西方的混乱无序状态,在1926年转向,进入反思和建设期,穆木天《谭诗》、王独清《再谭诗》、徐志摩《诗刊牟言》、闻一多《诗的格律》等文章的发表是为标志,他们着力寻找新诗的音节、节奏、格律等,要为新诗“创格”,这虽然还是从形式入手,但这些形式都集中在诗歌文本内部,并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向中国传统诗歌吸取养料,而不再是以西洋文学为典范,在“欧化”潮流中催生的新诗题词也就难免被抛弃的命运,闻一多《死水》集中没有题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其次,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文学的走向有关。20年代后期,“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文学的现实功能被强化,艺术审美诉求退居二线,文学包括新诗由多元趋向单一,新文学初期那种自由丰富如春日繁花竞放的景象已不再,题词也就随之萧条,口号宣讲式的文学不需要题词,明快躁进的功利诉求不需要题词充任文本多义性的媒介,在现实需要面前,新诗题词的功能已经丧失。紧随而来的是对五四文学遗产的清理,对“欧化”文艺的批判,对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的倡导,这又使得现代新诗赖以吸取的多重文化资源日益枯竭,枯竭的不是文化资源本身,而是对中西传统的双重拒绝,现代中国新的资源又尚未成气候,题词的疏落就折射出这一时期文学的困境。
最后,与诗人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体选择有关。人是创作的主体,无论是在“欧化”还是在“反欧化”的时代语境下,诗人都可以走不同的路。比如,“优美”的徐志摩就没有使用题词,从他早期的《志摩的诗》到新格律时期的《翡冷翠的一夜》再到后期的《猛虎集》、《云游》②《志摩的诗》(1925),收录1922-1924年间的诗;《翡冷翠的一夜》(1927),收录1925-1927年间的部分诗;《猛虎集》(1931)和《云游》(1932),收录后期的作品。,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没有题词; “痛苦”的穆旦也没有使用题词,他的诗主要写于战火横飞的三四十年代。不使用题词,并不能说他们没有受到西洋文学的影响,不能说他们没有“欧化”的倾向,徐志摩崇敬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还在大学讲授西洋文学课程,穆旦更是热切地读过奥登、艾略特,写过雪莱式的抒情诗,但他们的诗歌探索主要集中在诗的内质上,徐志摩的诗清新优雅,无需题词来增其浓艳,穆旦的诗意蕴暧昧多义,也无需题词来增加内蕴的容量,这些都是诗人们独特的主体追求。并非每首新诗都必需题词,诗人有使用或不使用题词的自由,因此题词衰落的危机从它进入现代新诗那天开始就潜伏着,只是新诗自身发展的历程和整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加快了它的衰落。
新诗题词在新文学“欧化”潮流里诞生与繁盛,“刹那芳华”之后,又在文艺“大众化”、回归“民族形式”、清理“五四”文学遗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迅速凋零,这与现代新诗、新文学的走向基本一致。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而看似微不足道的题词却承载了如此丰富的信息,“一花一世界”,通过它可以管窥到现代文学、文化思潮的流向,而这正是研究题词的重要意义之一。
六、游走在多种伴随文本之间
上文主要论述了新诗题词的源流、诗学建构功能及其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同步关系,但它究竟该归于伴随文本中的哪一类?或许任何分类都无法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标准而没有任何遗憾,现象总比我们能够言说的更为复杂,这是语言的无可奈何之处,“贴标签”似的命名具有先天局限性,虽然“分类命名集观”早就被索绪尔批为“很肤浅”,取消了对语言的“真正性质作任何探讨”〔27〕,但人们的认识逻辑依然是“客观事物”→“概念”→“客观事物”。对于题词也是这样,我们首先据其最显著的特征将它归为“副文本”,但“副文本”并不能涵盖它兼具的如“前文本”、“同时文本”、“链文本”等诸多其他伴随文本的特征。
除副文本之外,题词明显具有“前文本”的特征,即影响此文本生成的先前的文本,狭义上指文本中的各种引文、典故、戏仿、剽窃、暗示等,广义上指文本产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对于一首新诗来说,题词就是一种前文本,它在诗歌文本产生之前就存在,没有此文本,题词所在的文本依然在那里。况且题词是典型的“引文”和“典故”,只是位于文本的边上而不是文本内部,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引文、典故的功能。题词也是“同时文本”,即在此文本产生的同时出现的文本,题词是诗人创作一首诗或编订一本诗集的同时写下来的,是此文本生产时留下的痕迹,它们顺着时间之流在某个相对的时间段内落在了文本上。如果此文本没有产生或者此文本不带题词,那么题词所在的原文本就基本上与此文本无关,只有当两者同时出现,题词对于此文本才具有意义。题词还是一种“链文本”,即读者在接受此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链接到其他文本,如果不是作为此文本的伴随因素,题词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文本,虽然它只是一个独立文本的某一部分,但读者往往会自觉地链接到题词所在的整个文本。例如读者在赏析《红烛》时自然就会链接到“蜡炬成灰泪始干”所在的无题诗,甚至链接到李商隐“锦瑟”“昨夜星辰昨夜风”“来是空言去绝踪”等一系列无题诗。正因为这样,所以本文仅把题词看作伴随文本而不作更加精细的归类。
综上所述,新诗题词从拓展与丰富文本形式、衍射与规约文本意蕴等诸多层面参与了现代诗学的建构,它还在与各种文学作品的对话与记取中呈现出了影响新诗的多重文化资源,透过题词可以管窥到新诗在萌芽、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文学思潮和文化环境,这对于新诗研究很重要。作为伴随符号,它本身有着多副面孔,兼具“副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链文本”等多种伴随文本的特征,具有很大的容量和延展性,在符号学中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对象。如果再将之落实到每一位诗人的创作以及每一个具体的诗歌文本上,将更加复杂和丰富。因此,它是一种不该被忽略的伴随文本。
〔1〕〔7〕〔20〕〔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3-54,81-130,58.
〔2〕上海图书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 (2)〔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2-28.
〔3〕闻一多.致翟毅夫、顾毓琇、吴景超、梁实秋〔M〕.闻一多全集(12)〔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65.
〔4〕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A〕.傅斯年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32.
〔5〕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A〕.胡适文集 (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5-56.
〔6〕〔16〕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2,141.
〔8〕陆机.文赋〔A〕.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 (一卷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6.
〔9〕闻一多.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A〕.闻一多全集 (12)〔M〕.43.
〔10〕闻一多.杜甫〔A〕.闻一多全集 (6)〔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73.
〔11〕鲁迅.《小约翰》·引言〔A〕.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81-285.
〔12〕冯至.北游及其他·序〔A〕.冯至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4.
〔13〕闻一多.《冬夜》评论〔A〕.闻一多全集 (2)〔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69.
〔14〕张新.20世纪中国新诗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02.
〔15〕〔法〕瓦勒里·拉尔堡.承蒙圣·热罗姆之庇佑〔M〕.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46.217.
〔17〕〔法〕米歇尔·施奈德.窃词者:论抄袭,心理分析和思考〔M〕.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85.110.
〔18〕雷成德.“题辞”的内蕴——托尔斯泰艺术研究之三〔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39.
〔19〕〔美〕萨金特.重访乌托邦的三张面孔〔A〕.转引自Tom Moylan.Scraps of the Untainted Sky——Science Fiction,U-topia,Dystopia.Boulder:Westview Press,2000.74.
〔21〕 〔22〕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10,216.
〔23〕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A〕.闻一多全集 (2)〔M〕.118-124.
〔24〕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J〕.美育,1928,(2).
〔25〕温儒敏,陈晓明.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12.
〔26〕〔美〕乔纳森·卡勒.符号的追寻〔M〕.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103-104.
〔27〕〔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