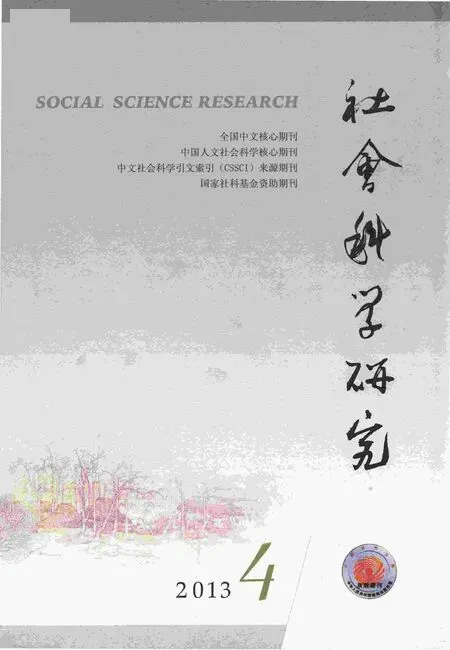禅宗北宗与密教关系研究
徐文明
五祖弘忍之后,禅宗出现南北分化,形成以惠能一系为代表的南宗和以神秀一系为代表的北宗。北宗有广义、狭义两种说法,广义的说法将当时在北方传禅的法如、老安、神秀等派系都归为北宗,狭义的北宗则专指神秀一系。
南北两宗的分化有多种原因和背景,一是地方的南北,二是教义禅风的顿渐,三是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疏密而导致的“官禅”与“民禅”。虽然当时及后世都有着重渲染二宗区别的人,但作为当事人的惠能与神秀都不大愿意承认和强调二宗差别,而更喜欢宣扬二宗本为一家。
据《坛经》南顿北渐第七: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1〕
这表明神秀在玉泉寺时就有南北二宗之说了,而惠能一直强调只有一宗,只是因为人南北利钝之分才有二宗之名。应该说,荆南时期的北宗与南宗差别更小,都与朝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只有在神秀被招入京、成为国师之后,北宗才成为禅宗的主流派系,与朝廷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在禅宗兴盛之时,密教也开始兴起。唐朝初年,便有许多密教经典译成汉语,但密教的正式形成,则是到了八世纪之后,通过善无畏 (637-735)、金刚智 (671-741)、和一行 (683-727)等人的努力才得以完成的。〔2〕由于密教经典的传译和宗派的形成都是在京城进行的,因此入京之后的北宗才与密教开始交涉。
由于神秀在京时间只有五六年,因此他本人与密教的关系不详。从其门人开始,北宗才在京城兴盛起来,影响越来越大,自然与同样开始壮大的密教产生了多方面的联系。
在神秀诸门人中,敬贤 (660-723)被认为是与密宗关系最近的一位,甚至被日本僧人认为是善无畏的门人。
据《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卷一:
一善无畏门人嵩岳敬贤禅师 (付一行禅师事)

已上《传灯录》第四抄之。
私云:嵩岳会善寺敬贤禅师,从无畏三藏受菩萨戒羯磨仪轨,谘问大乘微妙要旨,西明寺惠惊禅师撰集为一卷《禅要》是也。彼敬贤者,恐神秀禅师门资敬禅师事欤,彼《禅要》惠惊禅师所撰,一行禅师加再治欤,以心地秘袂随文可知其旨欤?
嵩山普寂,谥号“大照禅师”也,见《大宋高僧传》。又真言一行从大照禅师受禅法之旨,见小野《纂要集》者。嵩阳寺一行者,无畏门人同体也,且其旨《大宋高僧传》第五一行段所载也。〔3〕
如此认为敬贤为善无畏门人,主要根据是《禅要》。
据《无畏三藏禅要》卷一:
中天竺摩伽陀国王舍城那烂陀竹林寺三藏沙门讳输波迦罗,唐言善无畏,剎利种豪贵族,共嵩岳会善寺大德禅师敬贤和上,对论佛法,略叙大乘旨要,顿开众生心地,令速悟道,及受菩萨戒羯磨仪轨,序之如左。〔4〕
这一序文应当是记录者西明寺慧警禅师所作,然而从中看不到善无畏与敬贤为师徒关系的迹象,与之相反,二人实是“对论佛法”,平等交流,而且“顿开众生心地,令速悟道”,强调顿悟,恰是禅宗宗旨。
言敬贤为善无畏之徒,不是毫无根据。从年龄上看,后者年长二十三岁,足以为之师。另外,据《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卷一:
法侣高标,唯尊奉长老宝思惟,其余皆接以门人之礼。禅师一行者,定惠之余,术穷天地,有所未达,咨而后行。〔5〕
这是强调地位之高,除了尊奉长老宝思维(621-721)外,其他人都视为门人,就连禅师一行也不例外。
据《无畏三藏禅要》卷一:
于是三藏居众会中,不起于坐,寂然不动,如入禅定。可经良久,方从定起,遍观四众。四众合掌扣头,珍重再三而已。〔6〕
这是当时现场的记录,善无畏说法时,在场四众合掌扣头,珍重礼敬,其中似乎也包括敬贤。
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其实当时善无畏与敬贤对座论道,共同探讨,并非只是敬贤前来请益,因此扣头行礼的四众弟子之中应当不包括位居上座的敬贤。
从当时的记录及史料来看,没有任何敬贤拜善无畏为师的明确证据,因此二人应当不存在师承关系。
二人相见是当时作为禅宗代表的敬贤与密教代表善无畏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高峰论坛”,这表明敬贤具有敏锐的目光与预见能力,知道两家日后将会发生许多的联系,故先期联络感情,相互探讨。可惜敬贤所述没有留下记录,保存下来的主要是善无畏的说法。
这次会见应当发生在开元五年 (717)至十一年间。善无畏于开元四年 (716)五月十五日来京 (据李华《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始敕居兴福寺南院,后诏住西明寺。
据《开元释教录》卷九:
以开元四年丙辰,大赍梵本,来达长安。初于兴福寺南院安置,次后有勅令住西明。至五年丁巳,于菩提院译《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沙门悉达译语,沙门无著缀文笔受。其无畏所将梵本,有勅并令进内,缘此未得广译诸经。曩时沙门无行西游天竺,学毕言归,回至北天,不幸而卒,所将梵本,有勅迎归,比在西京华严寺收掌。无畏与沙门一行,于彼简得数本梵经,并总持妙门。〔7〕
这是关于善无畏当时经历的最早记录之一,又出自智升,当然是十分可靠的。据此,约开元四年末,自兴福寺移居西明寺,五年于西明寺菩提院开始译经。
据《无畏三藏禅要》卷一:
行者应知入道方便,深助进修,心如金刚,不迁不易。被大精进甲冑,作猛利之心,誓愿成得为期,终无退转之意。无以杂学惑心,令一生空过。然法无二相,心言两忘,若不方便开示,无由悟入。良以梵汉殊隔,非译难通,聊蒙指陈,随忆钞录,以传未悟。京西明寺慧警禅师,先有撰集,今再详补,颇谓备焉。
南无稽首十方佛,真如海藏甘露门,
三贤十圣应真僧,愿赐威神加念力。
希有总持禅秘要,能发圆明广大心,
我今随分略称扬,回施法界诸含识。〔8〕
此最后一段《附记》,依日本僧人之说,应当是一行所作。一行于开元五年 (717)应诏入京,其于善无畏结识最早始于此年,然最初译经,悉达译语,无着笔受,一行并未参与,他的精力主要用在《大衍历》的编制上。且玄宗下诏将善无畏所将梵本,全部上交,并令进内,因此未得广译诸经。周绍良认为玄宗的真实用意是“由于不喜欢密宗,不希望密宗经典广为人知”〔9〕,此说值得重视。玄宗的态度自然会影响一行,故他与善无畏的真正合作较晚。
假如这一《附记》果为一行所作,那么他当时应当参与了论坛,当然并非主要人物。所谓“梵汉殊隔,非译难通”,表明当时一行不懂梵语,只是按照所忆译者的话进行抄录,并且以此对此前西明寺慧警禅师的记录本进行补充整理,形成《禅要》。
如果此事发生在一行与善无畏交往的初期,则在开元六、七年的可能性较大。
有趣的是,由于北宗在后世知者不多,南宋李石《续博物志》竟然不明白敬贤为何人,道是一行后出家改名“敬贤”,将叔侄当成一人。科技史学者吴慧撰《一行生平再研究》,虽然考证精细,似乎不了解禅宗史,却道“《续博物志》的记载可能确有其事”。
最早撰集《禅要》的西明寺慧警禅师,事迹不详。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传》:
释慧警,姓张氏,祁人也。少而聪悟,襁褓能言,二亲鞠爱,邻党号为奇童。属新译《大云经》,经中有悬记女主之文,天后感斯圣莂,酷重此经。警方三岁,有教其诵通,其含嚼纡欝,调致天然也。遂彻九重,乃诏讽之,帝大悦抚其顶,勅授紫袈裟一副。后因出家,气貌刚介,学处坚固,充本寺上座,拯顿颓纲,人皆畏惮。或于街陌见二众失仪,片招讥丑,必议惩诫,断无宽理。后修禅法,虚室生白。终时已八十余龄矣。九子母院有遗影并赐紫衣存焉。〔10〕
此慧警亦是唐人。武则天于天授元年 (690)以《大云经》颁行天下,当时慧警三岁,则应生于垂拱四年 (688),三岁能诵《大云经》,确实非凡,则天欢喜,赐紫袈裟,后出家,为太原北崇福寺上座。此慧警与西明寺禅师慧警法名一样,时代一致,且北崇福寺慧警亦修禅法。不过僧传未言他是否到过京城,但也很有可能为同一人。假如确为一人,则当时慧警年约三十,有可能从学北宗或为敬贤门人。
《禅要》作者当然是善无畏,记录整理者为慧警或者还有一行。大正藏《禅要》有题名“海仁睿”,吴慧认为就是作者,其实“海、仁、睿”应当是空海 (774-835)、圆仁 (794-864)、宗睿 (809-884)三人的略称,三人都是入唐求法僧,且都将《禅要》带回日本,并不存在“海仁睿”其人。
现存《禅要》虽然主要是善无畏说法的记录,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北宗禅法的影子。如谓“今所发心,复当远离我法二相,显明本觉真如”,又言“如人学射,久习纯熟”,这一修法在《楞伽师资记》所述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说得更加具体。还称“所言三摩地者,更无别法,直是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名为大圆镜智。上自诸佛下至蠢动,悉皆同等,无有增减,但为无明妄想客尘所覆,是故流转生死不得作佛。行者应当安心静住,莫缘一切诸境”,“行者久久作此观,观习成就不须延促,唯见明朗更无一物。亦不见身之与心,万法不可得,犹如虚空。亦莫作空解,以无念等故,说如虚空,非谓空想。久久能熟,行住坐卧,一切时处,作意与不作意,任运相应,无所罣碍。一切妄想,贪瞋痴等一切烦恼,不假断除,自然不起,性常清净”,这与禅宗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
敬贤在当时北宗中地位很高,《楞伽师资记》称“大师付嘱普寂、敬贤、义福、惠福等,照世炬灯,传颇梨大镜。天下坐禅人,叹四个禅师,曰:法山净,法海清,法镜朗,法灯明”〔11〕,誉之为“法海”,仅列普寂之后,位在义福之前,足以表明他的影响。
总之,敬贤与善无畏的对谈拉开了禅密两家合作的序幕,对于唐代佛教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除善无畏外,金刚智也是创立密教的关键人物。金刚智于开元七年 (719)到达广州,八年到达东都。有关金刚智生平的史料有吕向《故金刚智三藏行记》、混伦翁《东京大广福寺金刚三藏塔铭并序》、《开元释教录》卷九小传等。
金刚智同北宗当然也有联系。据《宋高僧传》卷一本传:
开元己未岁达于广府,勅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剎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12〕
言大慧一行、不空为其门人,自有根据,而称大智禅师义福 (658-736)为其弟子,则是新说。此说被作为北宗与密教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证据,广为接受,其实则不能成立。
此说唯见于《宋高僧传》,在唐代史料中则找不到类似的说法。
据《开元释教录》卷九:
开元八年中方届京邑,于是广弘秘教,建曼荼罗,依法作成,皆感灵瑞。沙门一行钦斯秘法,数就咨询,智一一指陈,复为立坛灌顶。一行敬受斯法,请译流通,以十一年癸亥,于资圣寺为译《瑜伽念诵法》及《七俱胝陀罗尼》,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至十八年庚午,于大荐福寺出《曼殊室利五字心》及《观自在瑜伽要》,沙门智藏译语,又于旧《随求》中更续新呪。智执总持契,所至皆验,秘教流传,寔斯人矣。〔13〕
这是关于金刚智来华之后经历的最早记录,其中没有提到义福。《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九载有吕向《行记》大半及混伦翁《塔铭并序》全文,其中也没有提及义福。另外在有关义福的碑文中也没有提到他与金刚智的关系,表明二人确实没有师承关系。
从情理上讲,金刚智来华时,义福已是一代宗师,且年长十三岁,没有理由拜金刚智为师。《宋高僧传》义福传称其“以二十年卒”,金刚智传言其“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灭化,均误,其实义福卒于开元二十四年 (736),金刚智卒于二十九年(741),因此僧传也会有错误,对之不可迷信盲从。
义福本人虽然不是金刚智弟子,但并非与密教毫无关系。据杜昱《有唐薛氏故夫人实信优婆夷未曾有功德塔铭并序》,卢氏名“未曾有”,“自宗师大智禅师,茂修禅法”,又“尝以诸佛秘密,式是摠持,诵《千眼》、《尊胜》等咒,数逾巨亿。则声轮字合,如闻一音,而心闲口敏,更了多字。假使金盘转圆,玉壶倾注,传厥尽美,未云能喻。”如此义福俗家门人未曾有既修禅法,又习密咒,是一个禅修兼修的典型。〔14〕
据李华《故相国兵部尚书梁国公李岘传》:
梁国公讳岘,字某,其先陇西人。曾祖曰吴王,太宗爱子也。父曰信安郡王,玄宗之大臣,肃宗之军佐也。公年二十,学道于大智禅师,志深行苦。禅师谓曰: “汝当为国家陈力,缘不在此也。”
宗室李岘 (712-766)曾任丞相,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于开元十九年 (731)二十岁时曾从义福习禅。据李华《善无畏碑铭》,善无畏去世后赠鸿胪卿,鸿胪丞李岘与释门威仪定宾律师共同监护丧事。虽然出于公事,但也表明他与善无畏可能亦有交往。
北宗各系之中,最有影响的当然是普寂(651-739)一系,而普寂门人中,与密教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是一行禅师。
对于一行在密教及科学方面的贡献,前人论之已详。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大师与全才,一行的贡献与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师承也比较复杂。
一行出家,是从荆州弘景 (634-712)律师,时间在长安三年 (703)二十一岁时。弘景既是律师,为道宣 (596-667)弟子,又是玉泉道素门人,为天台宗玉泉系的一代宗师。弘景与禅宗关系也很密切,北宗普寂、南宗怀让都从其习律。一行师从弘景时,弘景应当住在东都佛授记寺。
过去的史料都给人留下一行出家不久便转到嵩山师从普寂的感觉,吕建福认为“一行先从恒景受戒出家,不久到嵩山拜普寂为师,修习禅门”,“一行在嵩山习禅大约有八、九年时间,至唐睿宗即位后才离开”〔15〕。其实从一行出家到师从普寂,中间有一段时间。
据李邕《大照禅师塔铭》,普寂“长安年(701-704)度编岳寺”,即在长安年间正式得度,成为有度牒的合法僧人,并编入嵩岳寺僧籍,神龙二年 (706)神秀入灭,四众“咸请一开法缘”,普寂依然不听“万人之请”,不愿开法,直到皇帝派武平一前来宣旨,令其领众开法,他才不得已出山传法。因此普寂正式开法不会早于神龙二年(706),一行前来学禅也不可能早于此年。
如此一行在嵩山师从普寂在神龙二年 (706)至先天元年 (712)间。自其出家到神龙二年(706),他可能主要在东都学道,除弘景外,还可能见过大通神秀、老安、玄赜等禅门宗匠。
一行从普寂习禅,具体经历不详。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称其“每研精一行三昧,因以名焉”,成尊《真言付法纂要抄》亦言“契悟无生一行三昧,因以名焉”,因此他主要修习的是一行三昧,也由此得名一行。
一行三昧见于《文殊说般若经》卷下,对于禅宗影响很大。据《楞伽师资记》,道信便引述此经说明一行三昧,后来则天问神秀所传宗旨与依何典诰,神秀称是东山法门,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可见禅宗对一行三昧的重视。经中言得一行三昧,于“诸经法门,一一分别,皆悉了知,决定无碍,昼夜常说,智慧辩才,终不断绝”〔16〕,胜过多闻第一的阿难。一行博学多闻,且记忆力惊人,看来确实得此三昧。
据《旧唐书》本传,“睿宗即位,敕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一行固辞以疾,不应命。后步往荆州当阳山,依沙门悟真以习梵律”。吕建福指出:
按《唐书》中本传,韦安石曾两度任东都留守,一则武则天长安三年,一在睿宗景云二年,故奉敕征召一行在景云二年冬天,一行往荆州当在其冬或第二年,即太极元年(712)。〔17〕
此说有据,一行并非在睿宗即位之年离开,而是直到先天元年 (712)才往荆州。这也解答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一行到当阳,为何不再师从弘景,而是其门人兰若惠真 (673-751),因为弘景于此年九月二十五日入灭了。
虽然吕建福早有此说,后来研究者吴慧先生等似不太清楚,仍然引元代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坚持“710年,一行离开嵩山,遁走荆州”之说,还称“从时间上判断,去到荆州的一行仍能拜谒弘景”,对《旧唐书》一行本传之说置之不理。
一行离开嵩山,不应征召,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有关。睿宗虽为皇帝,却不理政事,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姑侄相残,为争夺权力展开了生死搏斗。一行厌倦世事,自然不愿参与其中。
一行到荆州,主要师从兰若惠真学习律典,但他的身份似乎依然是禅宗僧人,住在神秀的度门寺。吴慧引张说《与度门寺禅众书》及一行答书,说明一行在荆州确实回溯了禅宗师门,另外一行在答书中称“自先师因带不居,遂逾十载。塔树将列,禅庭坐芜,永怀正服,终天何及”,表达了对度门“先师”神秀的深厚感情,表明他有可能见过神秀并始终以北宗为根本。如此一行到荆州,也有可能受命普寂负责管理度门寺。
总之,一行从学普寂至少六载,后来也常向普寂请益,深得一行三昧,是实实在在的北宗僧人。一行后来师从善无畏、金刚智,深明密法,又成为密教大师。他是将禅宗心法与密教教法融会贯通的第一人,也是两宗关系密切的见证。
据《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二:
《释氏系录》一卷
右谥大慧禅师沙门一行,开元中奉勅修撰,已编入史。总有四条:一纲维塔寺,二说法旨归,三坐禅修证,四三法服衣。于中《斋法》附见。〔18〕
这是一行开元中奉敕所撰,其中有“坐禅修证”,肯定是关于禅法的,可惜这一著作今已不存。
在一行现存的《大日经疏》中,也包含着禅宗思想。吕建福先生对《大日经疏》的主要思想进行了细密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禅宗的影响。
一行认为此经宗旨是“顿觉成佛入心实相门”,与禅宗一向强调的顿悟成佛一致。
据《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一〈1入真言门住心品〉:
此品统论经之大意。所谓众生自心,即是一切智智,如实了知,名为一切智者。是故此教诸菩萨,真语为门,自心发菩提,即心具万行,见心正等觉,证心大涅盘,发起心方便,严净心佛国。从因至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故曰入真言门住心品也。
入真言门略有三事,一者身密门,二者语密门,三者心密门。是事下当广说。行者以此三方便,自净三业,即为如来三密之所加持,乃至能于此生,满足地波罗密,不复经历劫数,备修诸对治行。故《大品》云:或有菩萨,初发心时,即上菩萨位,得不退转。或有初发心时,即得无上菩提,便转法轮。龙树以为,如人远行,乘羊去者,久久乃到,马则差速;若乘神通人,于发意顷便至所诣。不得云发意间云何得到,神通相尔不应生疑。则此经深旨也。〔19〕
此一段是对全经大意的总论。禅宗号为心宗,强调以心传心,对心法极为重视。自心具一切智智,即是心本觉义。真言为门,了心为本。发心修行,即知心具万行,心性本觉,心本涅槃,心行方便,心即佛国,总之,心性具足一切功德。以无所住而住其心,是引《金刚经》 “以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惠能即由此一句得悟,一行对此非常清楚,这一段与《坛经》六祖闻五祖为说《金刚经》而大悟一节相当接近。另外,一行据《大日经》言无住住心,惠能据《金刚经》言无住生心,也体现了南北两宗的宗风的趋向有别。
一行又言以三密方便,自净三业,主张自力成佛。同时又引《大品经》,强调今生成佛,初发心便成正等觉,说明禅宗顿悟成佛之义。一行认为心有妄执,便成三劫,若能一生除掉三种妄执,净除三业,就能成佛,无所谓时间长短。
吕建福认为,一行持“一道四乘判教论”,一道即一佛道,四乘即声闻、缘觉、菩萨、秘密乘,从中可以看出《法华经》会三归一与天台教法的影响,也与六祖惠能的“四乘说”有关联。
总之,一行对《大日经》的解释包含着会通禅密的倾向,也可以说,他之所以接受密教,是因为二者有相通之处,他想融合两家,归于一味。
与一行经历类似、学问广博、纵览诸家的僧人不在少数。守直 (真)律师 (700-770)便是其中之一。
据皎然《唐杭州灵隐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铭并序》,守直 (真)先诣苏州支硎寺圆大师受具足戒,后至荆州依真公苦行三年,其后又遍游天下二百余郡,寻礼圣迹,无所不至,“至无畏三藏受菩萨戒香,普寂大师传楞伽心印,讲《起信》宗论三十余遍,《南山律钞》四十遍,平等一雨,大小双机,在我圆音,未尝异也”,后又入五台寻礼,转《华严经》,开元二十六年(738)隶大林寺,大历二年 (767)移住灵隐,五年灭度。守直曾从普寂传楞伽心印,又讲《起信论》三十余遍,合乎北宗“五方便”之意,他的禅律并重也与普寂的宗风一致。〔20〕
守直,字坚道,俗姓范。开元十三年 (725)二十六岁时从苏州支硎寺圆大师受具足戒,圆大师事迹不详,当时另有法兴律师,作《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支硎记》,不知是否为一人。后到荆州依真公,三年苦行,真公即是兰若惠真。寻礼天下二百余郡,从善无畏三藏受菩萨戒香,复从普寂大师传楞伽心印,讲北宗宗论《起信论》三十余遍,《南山律钞》四十遍。又入五台山,转《华严经》三百遍,又转大藏经三遍。
有趣的是,守直虽然与一行没见过面,却是名副其实的师弟,往往步其后尘,一行师从过的惠真、善无畏、普寂也都是守直之师,虽然他学问广博,但在宗系上应当属于北宗,因为他不仅从普寂得楞伽心印,还专门讲《起信论》,多达三十余遍,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起信》当成北宗的宗论,视《楞伽》为宗经,与普寂嫡传门人弘正一致,他重视《华严经》,也与北宗将此列入“五方便”有关。
一行、守直之后,还有不空门人圆敬 (729-792),也是博涉律、密、台、禅的大家。据徐文明《圆敬律师略考》:
圆敬学问广博,得法非一,他与禅宗北宗可能也有关系。他曾讲《楞伽经》,这是当时禅宗的宗经,又讲《起信论》,也是北宗非常重视的经典,被列为“五方便”之一。据《宋高僧传》卷十四《唐杭州天竺山灵隐寺守直传》,守直 (700-770)律师“闻普寂大师传楞伽心印。讲《起信》宗论二十余遍,南山《律钞》四十遍。”〔21〕因此讲《楞伽经》、重《起信论》是当时北宗的标志之一。圆敬之时在东都北宗的势力最大,他在此至少十六年之久,受北宗影响在情理之中。……
圆敬和北宗的关系也有可能更深。为他建塔的弟子为灵湊,与此同时,禅宗北宗也有一位灵湊。据李充《大唐东都敬爱寺故开法临坛大德法玩禅师塔铭并序》,普寂门人法玩 (715-790)有“少林寺弟子上座净业,寺主灵湊”等。这两个灵湊有可能为同一人。法玩既是禅师,又是临坛大德,在律学上亦有成就;圆敬既是天台宗传人,禅诵为本,同样是临坛律师,而且是内道场临坛大德,二人颇为类似,且都在东都弘法,应当有所交流,其门下往还亦非意外。
以圆敬的年龄资历,没有可能直接得法于普寂、义福,他应当从学于他们的弟子辈,当时东京最为著名的禅师为圣善寺弘正,〔22〕其次是同光 (700-770)和法玩,他们都是普寂门下。圆敬与法玩当有师友之谊,故法玩门下的灵湊也是圆敬的弟子。灵湊至少在贞元七年(791)法玩新塔建立时已经是少林寺主,堪称法玩门下的杰出者。可能后来他应召入京,见到曾经从学过的圆敬大师的舍利塔尚未成就,便发大誓愿,率同门兴斯盛事,为先师建成一座庄严的多宝塔,其时已经到了元和二年(807),已是圆敬卒后十五年之事了。〔23〕
虽然两个灵湊是否为一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圆敬既是密教大师,又与禅宗北宗有不解之缘,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与一行、守直相似,圆敬也是会通律、密、台、禅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唐朝第一位僧录,值得重视。
在普寂门人中,最有影响的应当是东都圣善寺弘正,他在代宗朝势力达到顶峰,被公认为北宗代表、禅宗正传。然而他与当时势力最大的密教代表不空似乎没有相互往还的记录,二人分庭抗礼,但不空在朝廷中的地位似乎更高。从现有资料来看,弘正及其门下并未与不空一系密切合作,而是坚持传统的禅法。
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弘正之后北宗本身逐渐走向衰落,禅宗各派中南宗的力量不断增长,牛头宗也走向顶峰,北宗的地位和影响力自然下降。在代宗、德宗时期,牛头宗代表径山道钦(714-792)成为国师,号“国一”大师,其门人崇惠也在与道士史华的比试中胜出,为禅宗赢得了尊重。
据《宋高僧传》卷十七《唐京师章信寺崇惠传》:
释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稚秫之年见乎器局,鸷鸟难笼,出尘心切,往礼径山国一禅师为弟子。虽勤禅观,多以三密教为恒务。初于昌化千顷最峰顶,结茅为庵,专诵《佛顶呪》数稔。又往盐官硖石东山,卓小尖头草屋,多历年月。复誓志于潜落云寺遁迹。俄有神白惠曰:“师持《佛顶》,少结莎诃,令密语不圆。莎诃者,成就义也。今京室佛法为外教凌轹,其危若缀旒,待师解救耳。”惠趋程西上,心亦劳止,择木之故,于章信寺挂锡,则大历初也。
三年戊申岁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宫道士史华上奏,请与释宗当代名流角佛力道法胜负。于时代宗钦尚空门,异道愤其偏重,故有是请也。遂于东明观坛前架刀成梯,史华登蹑,如常磴道焉。时缁伍互相顾望推排,且无敢蹑者。惠闻之,谒开府鱼朝恩。鱼奏请于章信寺庭树梯,横架锋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东明之梯,极为低下。时朝廷公贵,市肆居民,骈足摩肩而观此举。时惠徒跣登级下层,有如坦路,曾无难色。复蹈烈火,手探油汤。仍餐铁叶,号为馎饦。或嚼钉线,声犹脆饴。史华怯惧惭惶,掩袂而退。时众弹指叹嗟,声若雷响。帝遣中官巩庭玉宣慰再三,便赍赐紫方袍一副焉。诏授鸿胪卿,号曰护国三藏,勅移安国寺居之。自尔声彩发越,德望峻高。代宗闻是国一禅师亲门高足,倍加郑重焉。世谓为巾子山降魔禅师是也。
系曰:或谓惠公为幻僧欤?通曰,夫于五尘变现者曰神通,若邪心变五尘事则幻也。惠公持三密瑜伽护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何足惊乎,夫何幻之有哉! 《瑜伽论》有诸三神变矣。〔24〕
此一事实并无异议,崇惠是禅密结合的代表、实有神通也无疑问,问题是他的身份。按照僧传之说,他是国一禅师的门人,勤修禅观,但又以三密教为恒务,专诵《大佛顶首楞严经》神咒数年,故有如是神通。
然而据圆照 (728-809) 《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六《谢赐紫衣并贺表一首》:
沙门崇惠言:昨奉观军容使宣进止,令于章敬寺登剑树、渡火坑,伏奉中使巩庭玉宣进止赐紫僧衣一副者。崇惠闻,有愿不孤,观音之慈速;克念斯应,能仁之力雄,所以入火不焚,以期必効,履刀不割,方表明征。不谓大圣加威,天恩曲被,遂使观身法界,蒙炽焰而无伤;举足道场,凌霜刃而不沮。实冀妖氛永息,业海长清,况道俗同欢,人天毕覩。此则陛下至诚之所感也,岂微僧一志之所为乎!叨沐殊私,无任庆悦,谨奉表陈谢以闻。沙门崇惠诚惶诚悚,谨言。
大历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安国寺沙门崇惠上表。
宝应元圣文武皇帝答曰:
师精勤梵行,夙契真乘,诚之感通,佛所护念。委身烈火之上,投足铦锋之端,坦然经行,如在床席。都城纵观,四部归依。所施非优,烦劳称谢。〔25〕
圆照将此表及答书编入不空表制集,似是暗示崇惠属于不空一系。空海《御请来目录》亦称“崇惠禅师摧邪支倾”,所赖者乃顿中之顿、金刚密藏也,也是强调崇惠为密教中人。二人皆为唐人,且圆照为当时之人,似乎非常可靠。然而空海本身属于密教,圆照虽然为律师,但与不空一系关系密切,二人所述未必完全客观。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不空门人中没有崇惠。在《登刀梯歌序颂谢表等三首》之初中有“大唐大历三年戊申之岁十月二十八日,奉勅于章敬寺建道场,时有江东沙门崇惠”〔26〕之句,表明崇惠确为江东沙门,与僧传之说一致。此外据《宋高僧传》卷九《法钦传》,“代宗睿武皇帝大历三年戊申岁二月下诏”,请法钦入京,“弟子不算多少,听其随侍”〔27〕,如此崇惠随其师于此年进京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在面临道士史华的公开挑战时,最应该出来应战的当然是号称神通法术最高的密教大师,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只是观望推托,无人应战。在这种情势下,崇惠挺身而出,登刀山,下火海,彻底征服了史华及观战的道俗,为佛教挽回了颜面。无论是用武功、幻术还是神通,都需要真功夫,不是随便糊弄的。崇惠现身斗法,不仅为佛教争了光,也为禅宗大长了士气。
崇惠究竟是如何得到这种神通的呢?崇惠强调是由于能仁之力、观音之慈、皇帝至诚之感,不愿归功于自己。不过他强调“观身法界”、“举足道场”,故入火不伤、履刃不沮。观身法界,身即法界,火坑亦是法界,故两不相碍;举足道场,即“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28〕,白刃亦是道场,故不为伤。似乎崇惠强调的还是禅宗的禅观,并非密法。
据僧传,崇惠经常诵《楞严经》咒,此《楞严经》的出现及流传,与大通神秀关系密切。
据子璇《首楞严义疏注经》卷一:
时禅学者,因内道场得本传写,好而秘之,遂流北地。大通在内,亲遇奏经,又写随身,归荆州度门寺。有魏北馆陶沙门慧振,搜访灵迹,常慕此经,于度门寺遂遇此本,初得科判。〔29〕
依子璇之说,此经在广州翻译之后,由房融表奏入内,藏于内道场,大通神秀遇之,写之随身,归于荆州度门寺,后来慧振复于度门寺见之,为之科判。这表明此经出自大通神秀一系,由度门寺流出,详情另撰文述之。总之,此经体现了北宗的思想和禅法,崇惠由此经神咒得到神通,也是间接受到了北宗的影响。
禅宗北宗与密教都在唐朝中期流行于两京中原一带,北宗禅法强调实修,也有不少神异现象,与密教有似。两家之间产生种种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当然也有矛盾与冲突,都是十分正常的。弄清两家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唐代佛教中后期的发展状况十分必要,对两家关系的探讨还需要更多努力。
〔1〕徐文明.六祖坛经注译〔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85.
〔2〕〔15〕〔17〕吕建福.中国密教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01,226,227.
〔3〕〔5〕〔10〕〔12〕〔21〕〔24〕〔27〕大正藏:50册〔Z〕.292上,291中,862-863,711中,797下,816-817,764下.
〔4〕〔6〕〔8〕大正藏:第18册〔Z〕.942中下,944上,946上.
〔7〕〔13〕〔18〕大正藏:第55册〔Z〕.572上,571下,765上.
〔9〕周绍良.唐代密宗〔M〕.钱文忠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30.
〔11〕〔28〕大正藏:第85册〔Z〕.1290下,1287上.
〔14〕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16,117.
〔16〕大正藏:第8册〔Z〕.731中.
〔19〕〔29〕大正藏:第39册〔Z〕.579中下,825下.
〔20〕徐文明.唐代诗僧皎然的宗系和思想〔A〕.王尧主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C〕.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688.
〔22〕徐文明.禅宗北宗第八祖弘正大师考〔A〕.敦煌学辑刊,1999.
〔23〕觉群佛学 (2010)〔M〕.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25〕〔26〕大正藏:第52册〔Z〕.857中,856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