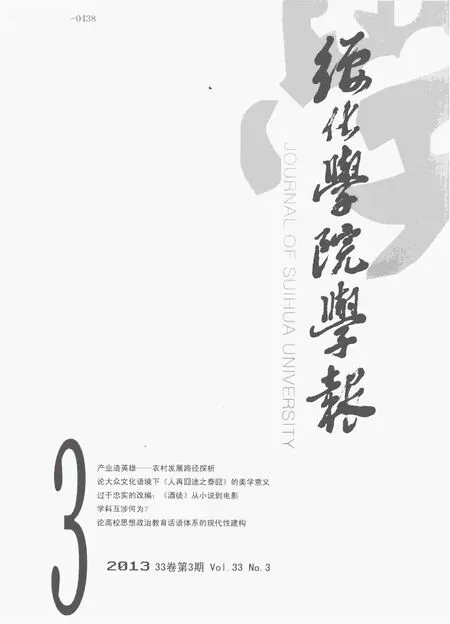学科互涉何为?——《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及其启示
程振翼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48)
在西方,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呼声:“学科互涉的时代到来了”,到今天,学科互涉、学科之间的边界跨越已经成为知识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的态势是,“边界跨越所造成的互动与重组就像边界的形成与维护一样,也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构成的中心”[1](P2),学科互涉与学科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美国学者朱丽·汤普森·克莱恩的《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对于学科互涉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图绘,并且提供了深入的理论挖掘,她对学科互涉所带来的知识生产问题予以重点分析。此书对学科互涉的成因和运作,以及作为国家研究体系的学科互涉等三方面问题做出了独到的理论思考,并且用大量的具体事例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证,这些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虽然此著作成书于上世纪末,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对文化研究这一新兴领域,它仍然有相当可观的参考价值。
一、学科互涉的成因
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认为学科互涉有五大源头:学科自身发展、学生学习研究的需要、职业培训的需求、社会需求、大学功能转变及其内部管理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人归纳出新的动因,由此可见这种现象是复杂且流动的。但是,学科互涉的成因大体说来可以粗线条地分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内部原因是指知识自身发展需要跨越原有边界与边界外的其他知识领域发生关涉。外部原因则主要是指经济、市场、政府、行政管理等权力。
首先分析内部原因。朱丽·汤普森认为学科的边界本身就是具有渗透性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学科之间的绝对对立。就学科本身、专业化(专业的细化)、专业和学科的划分标准这三个方面来讲,学科的边界都是具有渗透性的,学科、专业之间的互涉是必然的。
就学科而言,有学者把诸种学科分为“硬性的”/“软性的”, 或者 “受限制的”/“不受限制的”(潘廷的划分),所谓“受限制的”学科是指那些边界坚固、内部凝聚力和自我封闭性强的学科,如物理学;相反,“不受限制的”学科则是指那些渗透性强、易于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的学科。朱丽·汤普森认为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她认为这种边界的渗透性只存在强弱上的区别,而不会有纯粹无渗透性的学科边界。以地理学为例,它跨越了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界限,它的内部分裂成许多亚学科群,这些子学科之间是互涉的,并且广泛地与其他学科、其他学科的子学科建立联系,只不过这些子学科的互涉性强弱有别,作为大学科的地理学的边界则是在各种子学科的互涉中不断变动。
专业化的过程总是与学科互涉活动联系紧密,学科互涉不仅在专业层面上十分活跃,而且可以说专业化与学科互涉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学科互涉的首要性说法是基于知识不断裂变为更多的专业,而专业化又是日益增加的边界跨越和学科互涉活动的主要原因。”[1](P53)学科互涉是要形成一个多学科及其成员共同构成的“混合领域”,根据多根和帕尔的理论,这个“混合领域”就产生于知识的“专业化—碎片化—混杂化”的过程中。学科互涉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学科互涉的可能性就越大,两者之间是一种正比关系。
另外,学科专业边界的划分标准也是边界渗透发生的所在地。研究主题、对象、理论、方法、概念等等常用来作为划分标准的范畴都不是僵死的界线。知识的对象领域划分不是硬性的,研究主题也不会被块状分割,研究理论、研究方法、概念等则有着很大的普遍适用性,不可能为某一单个学科所独享。学科和专业的划界和命名如同一种贴标签活动,但这种活动不是僵化的、永恒不变的,不能用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来看待它。
另一方面是外部原因,如研究基金的来源、大学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高校为了加强行政管理等等。外部原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工具主义,既学科互涉是为了某种物质的、经验的外在目的而产生的。朱丽·汤普森不无担忧地指出,在目前,外在压力产生的影响要强于内在需求:“日益强大的工具论观点的重压,已经导致学科互涉的扭曲……外生于大学的学科互涉现在比内生于大学的学科互涉具有优先权,因为外生的学科互涉源于社会的‘真实’问题所带来的持久动力和高校履行其全部社会责任的需要。”[1](P15)她认为这种工具主义有“简单化”的风险,一方面把现实生活简单地视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忽略了生活本身的就具有的异质性和合理分类;另一方面它导致了一种粗暴的学科“整体论”,学科之间的差异被取消了,但事实上学科是不在不断地分化的,把它整合为一元的整体是没有意义的。针对这种倾向,朱丽·汤普森强调了学科互涉的“批评功能”,不能把学科知识和学科互涉的主导权交给外在权力,学科互涉不仅仅是“一种做事的方法,还是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学科互涉不仅是一种创造物质价值的工具,更是一种认识论。
二、学科互涉的运作
根据互涉的强与弱,朱丽·汤普森把学科之间的常见的互动关系分为三类,“借鉴中的互补交流”、毗邻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学科之间的互涉。在学科的借鉴关系中,她援引了汤姆·帕克森的互动等级四分法,这种划分依据的标准是学科互动的“力度和亲密度”。1级互动是指一个学科(专业)向另一学科(专业)借入仪器、数据、方法等,借入学科和借出学科并不因此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2级互动比1级互动的程度要高,可能“会形成明确的借鉴团体”,这种借鉴仍然是单向运动,并且不会导致双方向对方发展。3级互动不再是单向度的,两个学科之间会形成对话,并且借入学科和“源学科”在这种互动中会产生变化,“往彼此的方向发展”。4级互动则能够导致一门新的“整合学科”的出现,此时的借鉴和互动不在时外围的、非本质的,它能使参与互动的学科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修辞学的发展是学科借鉴的一个典型例证,经过不同学科之间互补交流,原本属于文学的修辞学成了一个多学科共同占有、互通有无的“贸易区”。
在比邻学科的互动中,存在着三种交叉形式,“第一种是对同一现象互为矛盾的阐释,导致边界争端;第二种是或隐或显得学术分工带来的边界的维持;第三种是对毗邻学科的深切认同,导致边界的模糊。”[1](P89)第三种交叉互动无疑是学科互涉的理想形式,比如历史学由于与其他毗邻学科的互动关系不断增强,直接导致了社会历史学这样新的混合学科的出现。
第三种学科之间的互涉在这里指的是高层次的学科互动,它往往会催生出新的学科互涉领域、新的“混合团体”,但是这并不意味学科互涉领域就是“另一门”学科。以分子生物学的例子而言,这一互涉研究领域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它仍然或者更加需要物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等多学科跨越边界,对其开展进一步合作研究。
总结这三种层次不同的学科互涉形式,朱丽·汤普森“得出一个重要教训:打破和差异在学科互涉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建设性的角色。”学科、专业的边界不是固定永恒的,面对新的问题我们需要打破原有的框架束缚,对于新的学科互涉领域我们也不能将其固化,它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合作,综合各种异质性的内容。她同时反对那种激进的做法,反对把学科互涉视为一种知识的断裂,而认同罗兰·巴特的观点,学科互涉“是本质上的认识论滑动。”[1](P108)对学科互涉更为贴切的比喻是 “噪音”(这一理论源于威廉·保尔松),从其他学科处传来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概念等如噪音一般对原有的知识体系形成了干扰,这种干扰可能是刺耳而无用的,但是假如我们转换知识领域的结构布局,那些噪音可能会变成动听的和声、乐音,并帮助建构起新的知识和意义。
三、作为国家研究体系的学科互涉
在进行个案分析时,朱丽·汤普森把边界研究模式分为三个层次,学科互涉领域、单一学科、国家研究体系。上文所说的互涉成因和运作模式在这三个层级中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最广层面的国家研究体系。
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一书中,托尼·比彻指出在高等教育界已经出现了一种 “三重螺旋”模式,即知识的生产已经不再是局限于象牙塔内部的事务了,工业和政府越来越来多地介入学术领域。“学术—工业—政府”的三重螺旋模式要求形成一种共赢的局面,“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展,大学的研究则把自身作为这个从科学技术知识到产出循环中的一部分。”[2](P8-9)朱丽·汤普森则这种现象称为联盟,建立联盟的根本动机是互利互惠,在这些利益中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她认为虽然这种新的模式虽然发展得生机勃勃,但是面对原来的制度化学科体制结构,学科互涉的作业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限制和障碍主要有:“体制结构、预算范畴和奖励体系”。在新模式兴起的形势下,学科互涉研究大多是在大学的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中进行的,但朱丽·汤普森认为这些“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虚有其表,徒有其名,它们要么以某一学科为核心,要么是对多种学科松散的“杂糅”。相对于大学里传统的学科、科系设置,这些“中心”是一种“隐结构”,虽有“中心”的名号但在大学里往往是非中心的,甚至是边缘化的,被视为一种“外围机构”。虽然研究中心这一“隐结构”被认为很难打破作为“显结构”的高校传统学科制度,但是它也有着活跃性、前沿性等内在优势,它理应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朱丽·汤普森认为“学术—工业—政府”联盟模式的发展必须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保持原有的教育使命感,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原有的职责;其次,研究成果要能自由发表;第三,学术圈内的合作应自由化;第四,限制过多的企业活动;第五,制定好联盟合作的规则,防止利益冲突;第六,完善政策法规保护知识产权。
四、对我国文化研究现状的启示
目前在我国文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时髦的研究领域,不久前文学界对“扩边”问题的广泛争论在当下胜负已分,当初坚定的“守边派”很多也都加入到文化研究的“扩边派”行列中来。从我国的文化研究从发轫到兴起的过程来看,我认为这种“文化转向”在很大因素上是外因促成的,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提出、大量研究经费的倾斜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文化研究的大繁荣。从朱丽·汤普森关于学科互涉的成因分析来看,我们要更加重视在知识领域内部打通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切实让各个学科的研究主题、理论、方法、概念能够更加自由的流通。对于外因,我们则要警惕极端“工具主义”的倾向,始终保持研究的批评性,“关注与批评学科知识的政治”,继承发扬纳尔逊文化研究宣言中倡导的“以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为己任……的传统”[3]。
从学科互涉的运作方式和水平上来看,朱丽·汤普森把学科互涉分为高低强弱的几个层次,互涉的程度越高,能够产出的新知识就越多、越有价值。学科互涉方式可以被分为 “搭建桥梁”、“重新建构”、“超学科整合”几个层级。文化研究需要更多的边界“重新建构”,甚至是“超学科整合”。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应当走出“搭建桥梁”这样的低层次互动,建立积极的双向发展活动,争取在互动的过程中开拓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和视野。另一方面不应该把文化研究制度化、学科化,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名词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标签”,“是一个‘引力领域’,各种传统和力量正在其内部寻求一种‘临时聚会’,它是‘一种磁铁’,将可合并的研究汇聚成一种有疑问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1](P170)它是历史的、建构的,随时准备着扩张和跳跃,“打破和差异”是其活力的源泉。作为一种“噪音”,它要求我们不停地变换、重构我们的知识组织体系,以适应对新问题的研究需要。诚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言:“文化研究是一个过程,是一种生产有用知识的炼金术,如果对它编码,就可能停止其反应。”[4]
对于“学术—工业—政府”的联盟模式,我们则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首先在这个联盟体系中,利益的冲突将会是不可回避的,如何既保持知识生产和学术部落的自身特性而又不至于丧失资金、项目支持等利益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学科互涉研究的话语权的大小取决于布尔迪厄区分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文化资本等四大资本,还取决于包括大量有共同学术志趣的研究个体、充分的基础设施、足够多的研究项目等“临界质量要素”。这要求我们在与外在权力、资本合作时注意多方面的发展,增加各种资本,而不形成偏废的局面。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在经历所谓“中心化”的趋势,这些大学内部的中心不能被有块状分割特征的传统高校学科管理体制束缚住跨越互涉的手脚,而应积极发展为最活跃、最前沿、最有创造力的名副其实的中心,它应该能够自由地与其他关涉学科形成良好的沟通交流。朱丽·汤普森对西方学界的提醒我们同样需要引以为戒。
[1]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M].姜智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托尼·比彻.学术部落及其领地[M].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徐德林.重温“文化研究宣言”[J].外国文学评论,2012(2).
[4]Richard Johnson.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J].Social Text,No.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