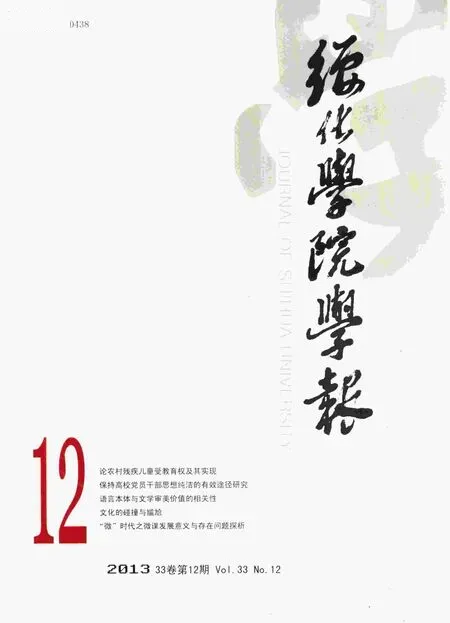理雅各西传“四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树千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苏格兰传教士,英国汉学的开创者,19世纪推动儒学向西方传播的重要人物。其耗时20年心血所编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是中国“四书”古籍向欧洲传播的第一次大规模译介,并且在“四书”的译本也成为理氏身后译者研究文献资料的重要信息资源。而德国传教士安保罗所注的《四书本义官话》、英国汉学家翟林奈所译的《论语》和《孟子》、苏慧廉翻译的《论语》、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译介的《大学》,均坦言参考理氏译本。因此,理氏所译“四书”不仅激发了西方学者对译本本身的研究热情,掀起了欧美“四书”英译的风潮,更引发了辜鸿铭、刘殿爵、林语堂等大师对西人译本的争鸣,进而开启了国人主动向西方译介“四书”的时代。因此,深入探究理氏译本的研究现状,对于传统文化典籍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一
理氏译本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界末期。1872年,《中国评论》在香港创刊,当时理雅各正好完成《中国经典》第一、二卷,儒莲、翟里斯、湛约翰等汉学家就以《中国评论》为阵地,对理氏译本进行了评论。湛约翰认为,理雅各并不是机械地翻译,“特别是在后面几卷,他把一个中文单字,扩展翻译成一个完整的英语句子,这就需要对中国经典的莫测高深进行无懈的思索考证。因此,要是有持怀疑态度的批评者试图探究理雅各博士,他们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时候还得去探究中国那些最优秀经典的诠释者们。因此,我们从这些翻译当中看到了他们的经典对于他们中国人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欧德理对理雅各译本也持肯定态度,他以理氏译本“研究——翻译”的模式为范例,并大量征引其学术绪论、注释的内容,完成了他的典籍译介工作。除《中国评论》外,继理雅各之后,许多译者常在译著的序跋中,都会地对理雅各译文进行评介。但因研究者的视域不同,汉学家翟林奈曾批评理氏:仅在介绍孔子事迹上做得较好,也未总结出儒家道德的突出特色,更没有正确评价孔子本人。而这一切原因则在于理氏的传教士背景严重影响了其公正性。在汉学家们热议理氏译本的同时,中国学者亦注意到了理氏的“四书”的文化影响。他们以强烈的民族意识来捍卫儒家文化。如辜鸿铭在《中国学》中,批评理氏对儒家著作缺乏哲学理解,没有建构和形成对儒家学说的有机整体观念。尽管辜鸿铭是以传统学说的宏观角度去批判理氏的译著,但他仍肯定了理氏在汉学史上的地位,即理雅各作为欧洲传播儒家经典第一人,其著作自有妙处。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理氏的译本早在19世纪末期起就成了汉学界普遍关注的对象。
自改革开放后,对于理氏译本的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研究群体呈现出“墙内墙外,花开两朵”的特点,即海内外学者都介入到了儒家文化与学说著作的研究中。尤其是近年以来,大陆学者对理雅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译本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井喷式的飞速发展。但大陆学者侧重于从语言学角度去评价理氏译本是否为完善。如甑春亮的《谈谈〈论语〉的三种译本》、曹的《〈论语〉英译本初探》、陈浪的《理雅各英译〈论语〉研究》等人的研究成果,就是例证。而港台与海外学者则侧重于从历史与宗教哲学的角度,去评价理氏译本的得失。
二
通过学界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关于对理氏译本的研究,其主要集中在译本语言研究、翻译思想研究和海外传播研究三个方面。具体如下:
(一)译本语言研究
从文献角度看,国内学者主要侧重对理氏译本的语言运用评价。此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单个译本研究,侧重于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译本的对比研究,侧重于理氏文本与其他译者英译文本的比较。正如上文提及的,辜鸿铭是最早对理氏译本的语言提出批评的学者。出于对国学的偏爱,他甚至过激地批评理氏译本为“具有死知识的权威”。但进入新时期后,学界对其的研究成果呈几何倍数增长。如仅在翻译学内,就有学术论文19篇,硕士论文12篇,博士论文4篇。而在专著方面,方汉文的《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方先生肯定了理氏译本的不可替代性,即其译著“为了让说英语的人也能充分地了解东方的哲学思想和灿烂文化”,是一种“学者型”的翻译方式。方先生不仅对理氏译文本身进行较为细致的观照,还直深入地剖析了其文风形成的原因与目的。
(二)译介思想研究
在探究理氏译本的传播思想及其意义方面,海外学者似乎优于国内学者。如香港的费乐仁教授,就从理氏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入理解与传播角度,深入地剖析了理氏解经的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其《服伺圣人还是闷死圣人—理雅各等〈四书〉译者研究》《理雅各著述研究的新视点》《理雅各〈中国经典〉译本研究》等学术论文,就是证明。其他诸如诺曼·吉拉多特的《中国文献的维多利亚式翻译—理雅各东方朝圣之行》、大卫·哈尼的《神坛焚香:汉学家先驱与中国经典文献的发展》、鲍理斋的《圣书主题,英国翻译家与四书》等学术专著,也从不同角度探析了理氏传教生涯对其翻译著作的文化影响。虽然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不如海外研究,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岳峰博士的《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一书,就颇具代表性,该著作结合理雅各的文化背景,比较客观而准确地指出了理雅各在中西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贡献与失误,并且该著作在研究路径的拓展、思路的启发等方面,对学界颇有借鉴意义。
(三)海外传播研究
以传播学的角度研究理雅各对“四书”的译介活动,是近年以来较新的研究拓展领域。在现阶段,鲍宪阔、李艾文的《从〈四书〉的英译看中国经典的对外传译》颇具代表性。文章从儒家经籍内容出发,强调了传统文化对外传译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作者又从“四书”的英译简况,评述了传统文化对外传译的现状。此外,杨平的《〈论语〉的英译研究—总结与评价》,则从传统经籍翻译史的角度,解读了儒家经籍在不同时段的传播状况。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似乎还没有敏感到对理氏译本研究的重要性。即使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学术著作或论文成果,但也属于凤毛麟角。
三
当下随着“中国热”的文化现象在欧美地域的兴起,传统典籍及其文化传播也正在日益升温,笔者以为,对于理氏译本的研究,似应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方能比较深入地探究传统文化著作在海外的影响。
首先,从文本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大多学者大多集中在理氏译本在语言文化层面的缺失。故而,我们可以以史料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各种译本的比较研究,深入探究传统典籍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问题。从1861年至今,理氏译本一直被视为海外四书经典的标准译文,但在此期间,非议之声也屡见不鲜。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歧与论争,其关键就在于学者过分的纠结于译文本身,而忽视了理氏四书译本更重要的组成部分——长篇的序言与详尽的注释。对此,岳峰的《理雅各与中国古经的译介》虽然意识到了该问题的存在,但却未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因此,我们可以试着从史料学的角度出发,考察理雅各在译注四书过程中的底本依据和取材来源,更加细致地爬梳其四书文献编译的过程。
其次,对理氏译本的版本研究可以给予更多的重视。因为理雅各各种版本差异较大,如1861年的首版与189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就有不小的差异。而就文本本身而言,《中国经典》卷一的翻译,因理氏先在翻译中,有从接受朱熹到否定的过程,所以在其不同版本中,皆能体现出他对汉学的肯定。比如在第二版中,他就否定了朱熹的观点。而其他关于语言点的考证和修订更是不胜枚举。因此,关于《中国经典》的版本考证工作对于正确认识理雅各译介四书的思想流变相当重要。
第三,对理氏译本的传播研究亦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由于理氏的译著早于欧美许多翻译者,但至于其具体传播情况,似乎我们却不甚了了。究竟《中国经典》在流传中的情况具体如何,以及欧美大众和中国的接受状况如何,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研究重点。如以中国的理雅各英译四书版本为例,理氏原著经刘重德、罗志野校注,该书定名为《汉英四书》(The Chinese/English Four Books),已于1992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重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此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也于2011年相继出版了理雅各的四书英译本。由此可见,在理氏《中国经典》流传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第四,西方对理氏所译“四书”的接受情况可以给予更多的重视。四书是儒学的基本内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依归,涵摄了天地、社会、历史、人生种种哲思,经由传教士们诠释的四书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典籍传播的一个重要问题。
[1]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段怀清.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J].浙江大学学报,2005(5).
[3]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4]岳峰.关于理雅各英译中国古经的研究综述——兼论跨学科研究翻译的必要性[J].集美大学学报,2004(6).
[5]Th·H·康.西方儒学研究文献的回顾与展望[J].哲学综合,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