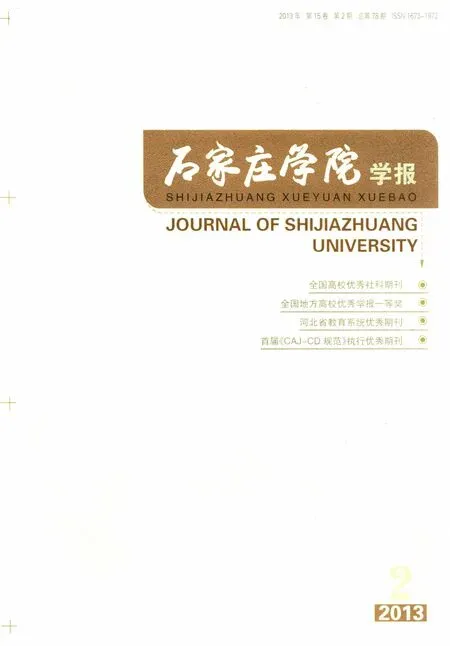回忆:《呐喊》的精神丝缕
王吉鹏,丁春丽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它鲜明地体现了鲁迅回忆的情思。这种情思成了牵着往昔的“精神丝缕”,形成了《呐喊》。从某种意义上说,《呐喊》是鲁迅回忆性创作系列的一部分。其他的回忆性创作还有许多,如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中的《风筝》,收在后期杂文集中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以及关于章太炎的几篇,还有短篇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等。其中,《呐喊》中的《故乡》《社戏》《鸭的喜剧》是突出表现鲁迅回忆丝缕的几篇。
一
鲁迅对于故乡的回忆纠缠在整个 《呐喊》中。《狂人日记》序中写道,“我”是“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孔乙己》《明天》《风波》的故事发生在鲁镇;《药》中所影射的秋瑾被害之地在绍兴城内;《一件小事》开篇就是“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阿Q正传》也是以浙江为背景,可以说,几乎在鲁迅的每一篇小说中都可以寻到其故乡的影子。鲁迅将作品中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自己的故乡,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识的移情,都可以看出“故乡”在其精神世界的独特存在。这种存在在《故乡》中渐渐明朗化,让人们看到了故乡对于鲁迅的意义。“故乡”对于鲁迅来说,不再是空间意义上所代表的生存地域,也不再是时间意义上所代表的过去的欢乐时光,而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精神堡垒”。
《故乡》作于1921年1月,是鲁迅对自己一次真实回乡经历的记述。据鲁迅日记中记载,他确实于1919年12月回绍兴省亲,也正是这一次,他将自己的母亲及朱安接到了北京,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到绍兴。显然,这次的回乡带给鲁迅的记忆并不美好,从小说的开篇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1]501
小说的开篇就借一段景物描写来突显鲁迅对家乡的情感。从心理学角度看,鲁迅这段描述明显符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逃避性心理防御机制理论。所谓逃避性心理防御机制是一种消极性的防卫,以逃避性和消极性的方法去减轻自己在挫折或冲突时感受的痛苦。它包含四个方面,即压抑、否定、退回、潜抑。而鲁迅的这种心理恰恰与其中的压抑和否定相吻合。所谓压抑,是指个体将一些自我不能接受或具有威胁性的、痛苦的经验及冲动,在不知不觉中从个体的意识中抵制、排除到潜意识里去。少年时的鲁迅是带着创伤性的记忆独自走异乡、逃异地的,他将此压抑在他的意识里,逐渐变成潜意识,现在当他真正回到故乡,这种潜意识也就浮现了出来。文章第一句话,他先是用了“严寒”,接着连续用了两个模糊的数词“二千余”“二十余”,这正是鲁迅压抑情感的一种表现。
笔者认为,造成鲁迅的这种表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鲁迅童年的创伤性经历。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如果长期受到忽视、情感虐待,那么会在这个人的心理上形成创伤,而童年的心理创伤对一个人的影响更为强烈,可能会持续一个人的一生。鲁迅的创伤性童年同样改变了他对故乡的认知。他从原本外人奉承、恭维的小少爷突然变成了别人眼中的“乞食者”,需要在别人的侮蔑里接了钱为父亲治病。巨大的心理落差在鲁迅的童年精神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417正因如此,鲁迅才会逃往异地。故乡给鲁迅带来的创伤是幼年的他难以接受的,这处创伤变成一种潜意识影响着他,在他“回乡”事实发生的时候便会触发他的怨怼情感。
二是鲁迅再次回乡所见到的破败、萧索的景象,以及看到记忆中的故乡人的麻木。这样的“故乡”将人变成鬼,怎么能是给予鲁迅心灵慰藉的地方?鲁迅的寄托瞬时轰毁。而一旦失去了这心灵的寄托、精神的堡垒,他“不仅无家可归,甚至变成破碎不全的东西”[2]。所以,鲁迅要逃离这里,去寻找另一处可以收留他的精神天地。这时的逃避隐含着另一种带着希望的寻觅,这种“寻觅”也正是鲁迅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意识。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1]507
闰土先是“站住了”,接着是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鲁迅将“欢喜”和“凄凉”两个完全不一致的词写在一起,让它们同时出现在闰土的脸上却那么协调。从“欢喜”可以看出,闰土是真心的,他依然记得“我”这个幼时的玩伴,为重逢而“欢喜”;而“凄凉”则是感到了这份幼年的友谊变得不一样了,因为闰土长大了,不再是几岁时什么都不懂陪着“我”到处玩的“闰土哥”了。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长大的代价是抛弃心中最真诚的感情,是泯灭人心中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从“老爷”两个字里,鲁迅看明白了这可怕的事实,所以: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1]507
鲁迅对故乡的怨怼情绪,从某一方面看其实是他的一种移情。鲁迅透过闰土的改变看清了这人间最可悲的事实,他需要一个客体来承担发生这改变的责任,由此便产生了对“故乡”的怨。而“故乡”从某一方面来说也确实是造成闰土悲剧的一个原因,所以鲁迅的“怨”也确实是有道理的。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1]510
已经二十几年未见的故乡,当“我”再度离开时,“却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这是因为此次看到的真实的故乡打破了鲁迅心中对“故乡”的美好记忆,给其心理以巨大的震颤,于是他就借着“逃避”以抵制这巨变带给他的创伤。弗洛伊德理论认为,追溯到小孩子时期长期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在以后生活的某一天,当他察觉到在生活的强大力量面前是多么无望和弱小,感到他的情况像他在童年时的情况一样时,便会企图通过重新恢复那种保护了他的婴儿期的力量来掩饰他的希望。鲁迅以“逃异乡”来对待童年的创伤经历,如今回乡后,面对故乡的种种,他既能清楚地感到,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再次以幼年时对待创伤的方式来面对无力的现实,所以他再一次地逃离。
本项目主体结构期间需开展基础沉降监测工作,依据《建筑变形测量规范》确定沉降观测等级为一级标准,具体监测项目包括:(1)主楼及底板沉降监测;(2)后浇带两侧差异沉降监测。本次共设置119个监测点(J1~J119),图2所示为基准点、工作基点规格及埋设示意图。
二
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原理(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分析,鲁迅因为生理的需求独闯异乡,为生计勉强自己,生理需求方面比较不稳定,在安全需求上也很欠缺,所以在情感需求上就相对重一些。这种需求在他生活的周围很难得到满足,于是鲁迅便将这份情感寄托在遥远的故乡上。透过《故乡》我们可以看出,肉体回乡这种真实经历的回忆并不能满足鲁迅情感上的需要,他需要一次精神上的回归,这也是他创作《社戏》的主要动力。
《社戏》是《呐喊》的最后一篇,之后鲁迅便进入了“彷徨”阶段。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篇已经没有了前期“呐喊”的声音,只是单纯地将其记忆中童年的一段记叙下来。全篇气氛温馨,甚至有时会使读者忍不住会心一笑。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鲁迅是借北京两次不愉快的看戏经历引出全文,是“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忽而使我省悟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1]587。鲁迅两次发出“不适于生存”这样的感慨,当然一方面单纯是因为让他不满意的看戏经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与他现实生活的环境相对比,他远离家乡,寓居北京,为生计奔波,甚至参与“讨薪”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五四运动的退潮,支持他“呐喊”的支柱渐渐崩毁;再加上1923年鲁迅正式与周作人决裂,可见作《社戏》之时两人关系必定已是不睦。正是由于面临现实生活与精神上的双重困境,才使鲁迅有“不适于生存”之感。戏台下就仿佛是鲁迅生活的现实环境,锣鼓咚咚地响,人群不断地拥挤,但是在这里他却找不到自己的落脚之所,确实是“不适于生存”。他只有逃出这里,去寻找另一处可以让自己感觉“清爽”之地。他需要一个精神的“堡垒”,将自己隐蔽其中。《社戏》对童年的回忆便起到了这个作用。弗洛伊德认为,“童年记忆是这样出来的,同成年时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完全不同,它们并不固定在被经验的时刻,又在以后得到重复,而是在已逝的岁月,童年已经逝去的时候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改变和被伪造的过程中,它们是要服务于以后的趋势,所以一般来说,它们与幻想并不能被明确地区分开来”[3]58。因此,人们可以透过童年幻想来填补生活故事中的实质。
“但是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1]589,鲁迅不只一次地说道:忘却了书名。在笔者看来,与其说忘却了书名,不如说在鲁迅心里根本没有这样一本书存在,或者说这样一本书是否真的存在其实根本无关紧要。它只不过是一个由头,借此作为对社戏回忆叙写的正当理由。由此可以看出,《社戏》确实是鲁迅对童年经历的回忆,可是这段回忆是经过他有意识地改造过的为他现在服务的,即鲁迅是要透过这样一段被他改造过的回忆来填补现实生活中情感的缺失,而北京看戏的经历正好触发了这段回忆的发生,也就使得《社戏》的创作成为可能。
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1]590
与《故乡》的暗色调不同,《社戏》通篇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当然这与这段记忆发生的时间有关。鲁迅在童年的时候经常与母亲一起回祖母家省亲,小说回忆的背景也正是这时。在鲁迅童年的记忆中,鲁镇的乡亲总是那样热情,鲁镇的孩子们总是那么勇敢、善良、聪明、质朴,是他记忆中最美好的一环。在鲁镇孩子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严格的等级观念,即使打了太公也决没有谁会想出“犯上”两个字;他们有着自由无拘的童年娱乐生活,掘蚯蚓、钓虾、放牛;他们健康聪明,“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1]591。其实这篇小说描绘的也只不过是最平凡的生活、最平常的小事、最正常的人性,但恰恰是这些最平凡、低调的东西却能在鲁迅的生命中发出亮色,一场社戏、一碗豆子成了鲁迅人生中最圆满的回忆。尽管他们有99%都是不识字的,在鲁迅的记忆里却是最“正常”的人,最健康的人。
“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了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看罢,”他于是来回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家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 ”[1]595
在这最简单的对话中,鲁迅将这群孩子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孩子们想吃豆,却没有随便去哪片地里摘,双喜问阿发的意见,让阿发在自己家与老六一家作选择。虽然双喜嘴里说着“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却不会有人将这个“偷”字和丑陋联系在一起,反而可以见出孩子们的可爱与率真。接到问题的阿发也并没有因为自私或利益就让别人摘老六一家的,而是故作老成地来了句“且慢”,引人发笑。阿发上岸摸了一回,就说“偷我们家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因为自己家的豆大,就让伙伴们摘自己家的,这本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道理,也是最应该为人遵守的原则。正是这最基本的东西,鲁迅将之表现在孩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没有被社会的污浊浸蚀的最纯净的灵魂。这显然与鲁迅生活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冲撞。鲁迅看到的社会现实是人们之间的攻讦、诘难,为自身的利益或是自己团体的利益将这人性中最基本的公平原则抛在一边。孩子们身上这种纯真的美,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又在渐渐接触社会中被自己丢弃了,也正因如此,当人们再次从孩子身上看到它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它的弥足珍贵。在他们身上,凝聚了鲁迅对孩子们最美好的期待,也是他心中认为的最美好的人性。所以,同样的罗汉豆,第二天六一公公送给“我”的便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
无论是那夜的“豆”,还是那夜的“戏”,都是鲁迅的回忆,这种回忆侧重的是满足处在回忆过程中的主体的需求,而“豆”与“戏”便是为这种需求开的“药方”。透过那夜的看戏与吃豆子,鲁迅在精神上实现了一次回乡,使他产生了一种满足感。正是这种满足感,让他再也寻不到比之更好的豆子和戏。鲁迅说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135他所谓的“合理的做人”就如《社戏》中的人一样,人性不被扭曲,生活不被逼压。
三
1922年2月底,俄国盲诗人、世界语专家爱罗先珂(B R Epomehk)受邀来北京讲学,蔡元培委托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照顾,并安排他住在周氏兄弟八道湾的寓所。这期间,无论是周作人还是鲁迅都与爱罗先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7月3日,爱罗先珂离开北京赴芬兰参加世界语年会,但于约定之日未归。鲁迅以为爱罗先珂不会返回北京,便作了一篇《鸭的喜剧》来怀念爱罗先珂——“正是他预定的日期已过,大家疑心他不再来了的时候,所以有给他作纪念的意思的。 ”[4]92
爱罗先珂带给鲁迅的影响极大,他们两个是精神上的挚友。鲁迅在早期就已经开始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与爱罗先珂真正意义上的相识是在1922年,这时正是他思想发生变化、转折的重要阶段,前期的“呐喊”精神尚在,也还没有与周作人决裂进入沉寂彷徨时期。可是透过他这时期的杂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鲁迅“呐喊”的声音已经明显减弱。爱罗先珂的到来正是一个契机。这位盲诗人带着特有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勇敢、执著、牺牲自我的精神走进了鲁迅复杂的情感世界。《端午节》正是作于1922年——爱罗先珂在北京的时候,这是鲁迅第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也可以看做是他探寻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开篇之作。由此可以说,这部小说与爱罗先珂有着重要的关系,也体现出爱罗先珂对鲁迅的影响。
爱罗先珂在他的童话作品里完美地呈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在《鱼的悲哀》①此段中未标注的引文均出自爱罗先珂著、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鱼的悲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里写一群生活在冬季冰冷池塘里的鱼期盼着春天的到来,“然而春天什么时候才到呢?”小鲫鱼对此一无所知。春天若是不来呢?母亲只是告诉他:若春天不来,大家的魂灵便要到遥远的国土里去过安乐的生活了。“真有这样的好国土的么?”这样的天真,却以儿童般的口吻表现着自己的固执。他热烈地爱着这池塘里的一切,各种其他的鱼、各种其他的生命。“从这时起,鲫儿便无论怎么冷,无论怎么饿,也再不说一句废话,只是嘻嘻的笑着。等候那春天的来到了。”他勇敢、坚贞、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人类充满好奇。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兄弟姐妹一个个被当做实验对象失去了生命。“鲫儿的悲哀也一样。怀着对于这世间毫无希望的心情”,“请罢,捉了我去,没有捉去别个之前,先捉了我去。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哩”。这是一种强烈的为生命的呼号,突显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无畏和牺牲奉献精神,他们愿意着为自己的信仰奉献一切,也愿意为所有的生命付出一切。
正是因为从爱罗先珂身上及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使得鲁迅不自觉地与中国知识分子相对照,于是开启了他小说的另一个重要题材,即知识分子小说。鲁迅对爱罗先珂的感情很深,《鸭的喜剧》便是这段共同生活记忆的叙写,描绘了爱罗先珂生活中养蝌蚪、鸭子的故事。
鲁迅记忆中爱罗先珂有着文人的敏感,他在刚到北京的时候就对“我”叫道: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1]583
这种敏感与鲁迅压抑的孤独正相呼应,他们是精神上的知音。爱罗先珂有着稚子一样的心灵,他热爱大自然,在他的世界里总是充满了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的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这是大自然的声音。爱罗先珂对人类也充满了爱,他以最真挚美好的心来观照现实世界,以童话的方式让人们从中看到他的热情与理想,又借助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到其中冷酷、残忍的一面。这就是爱罗先珂式的童话。鲁迅认为他的作品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5]214。鲁迅说爱罗先珂“有着一个幼稚的,而且优美的纯洁的心”[5]214。他热爱自然,便买了十几个蝌蚪,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养,虽然他看不到,但是他听得到。后来又买了几只可爱的小鸭子,“小鸭子也诚然是可爱,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跳跃的走,互相打招呼,总是在一处”[1]585,他还要买泥鳅来喂它们。这一切都充满了童趣。只是几只小蝌蚪、小鸭子就可以让爱罗先珂这样满足、开心。后来,池塘里玩耍生活的小鸭子吃掉了原本池塘里的小蝌蚪。
鸭子吃蝌蚪本就是自然界的自然规律,无论是鸭子还是蝌蚪都是最美好的大自然的象征。爱罗先珂以他稚子般的心热爱它们,他希望无论是蝌蚪还是鸭子都可以给这寂寞的北京带来一丝乐趣,但是他却忘记了自然规律,或者说不是忘记,只是有意识地忽略。他只能“唉,唉!”叹息两声。这只是语气词,
[1]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3][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北本不成一句话,鲁迅却用了“他说”,可见爱罗先珂的这两声叹息后面省略的话语,鲁迅“读”懂了,明白了。鲁迅正是借助鸭的喜剧、蝌蚪的悲剧表明,“爱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主义精神。
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了。
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1]586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写出了他对爱罗先珂浓浓的思念。北京还是北京,鸭子也长大了,似乎一切都一样,却惟独少了鲁迅记忆中的挚友。鲁迅在“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这一句话中用了 “还是”“绝无”两个词,可以看出,在爱罗先珂离开北京以后,鲁迅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也一直在等他回来。可是,等了这么久、打听了这么久,却依然“还是”“绝无”消息,可见鲁迅的失望以及在内心深处对他的思念。这篇小说虽然只是写了与爱罗先珂相识后他养蝌蚪和鸭子的一件生活小事,却与《范爱农》《藤野先生》相类,都是鲁迅对记忆中的师友深深的回忆,表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虽然爱罗先珂和鲁迅之间并没有太久的交往,但是爱罗先珂对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鲁迅生命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是鲁迅彷徨开始的重要因素。京:知识出版社,1987﹒
[4]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