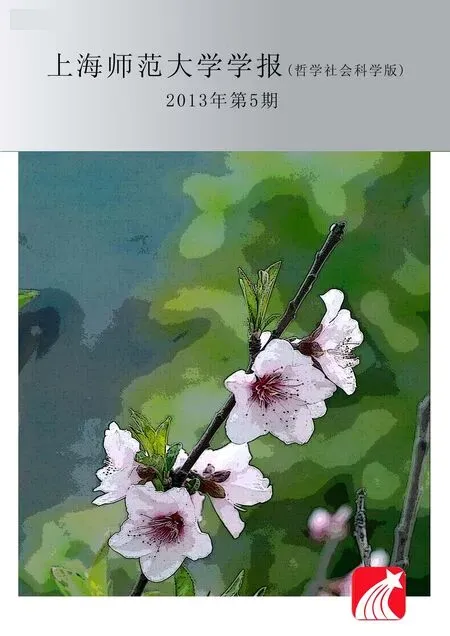从市场的变迁看艺术的命运和使命
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市场的变迁会给艺术带来什么?我们可能会想到,带来的是艺术品的销路问题。市场大了,艺术品的销路会大得多。然而,市场的作用远不只是如此。市场的“后果”,要比我们所设想的要深远得多。可以这么说,市场改变着艺术的生产方式,改变着艺术家,也改变艺术概念本身。
一、产品的美与市场的关系
人们生产出来的物品,叫作产品。将它放到市场上去卖,就叫作商品。于是,同样一件物品,生产者留着自己用,就叫作产品,去销售,就变成了商品。产品做得好与不好,是由所使用的原材料、生产者的技能和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决定的。用料讲究,制作者才能出众;制作时用心用力,做出来的东西就好。
从产品变成商品,是质量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这说不好。并非所有的用于出售的东西,都比生产出来供自己用的东西更好。一种产品变成商品以后,受着一些新的逻辑支配,这些新的逻辑要求产品的生产被改进,但却又对生产被改进的方向作出限定。于是,商品有可能比产品质量更好,也有可能质量下滑。
让我们从这样一个例子说起:什么地方的饭店更好一些?我们大概都有一个经验,火车站附近的饭店,一般说来都是一个城市里最差的饭店。最好的饭店是城里的一些老街区里的老字号饭店。
火车站旁的饭店里,人来人往,来去匆匆。饭店老板或厨师与客人是一种陌生人的关系,在饭店里完成的是一次性的机械性的交易——给钱、充饥、走人。这些客人也许这辈子不再有机会来这家店了。饭店老板也知道这点,所以,快点上菜,让客人吃完就走。
城里的老字号的饭店则是另一种情况:来的客人大都是所谓的“回头客”,即使第一次来,也常常是慕名而来。老板、厨师与客人形成了一种熟人或朋友关系,对来客打招呼,不说“欢迎”,而说“来啦,您哪!”给客人回家吃饭的温馨感觉。饭店讲究名声,饭店老板把烹调和饭店的管理作为一种艺术来完成,不断研究和提高。又由于主人跟客人是一种熟人关系,服务的质量能直接得到反馈,如果客人说了你今天的菜火候欠一点,主人会改进这道菜的做法。就这样,在反馈交流中得到改进,熟人圈子培育出了“老字号”。
传统老街区消失,不仅是一个建筑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问题。房子没了,整个文化也随之消失。老街区消失,相应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消失,传统饭店顾客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也渐渐消失了。
从传统到现代,存在着一种现代商业中的“质量下滑”规律。传统社会是熟人生活在一起,衣食住行都是在熟人间完成。质量形成口碑,古代工商业是靠口碑来维系。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互相不认识时就要相互打交道,并且打完交道后还是不认识,并且也不需要认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如何建立起来呢?怎样来拯救质量下滑呢?人们找到了一个办法:标准化。通过创品牌,做连锁店,于是,有了“麦当劳”、“肯德基”、“吉野家”,有了城隍庙小吃、重庆火锅、天津包子、马兰拉面。
品牌是在现代商业的状态之下出现的。在传统街区消失后,现代商业靠大的品牌和连锁店让客人放心。这些品牌连锁店虽然质量一般,但食品安全较有保障。现代社会的连锁店在竞争中也占据优势,它背后有大资本的支持。随着传统社会变成现代社会,它会不断地击垮一些传统的个人饭店。旧式的老字号不存在了,幸存的老字号也搞起了连锁店。例如“全聚德”,成了一个吸引外地游客的地方。北京人不再对“全聚德”感兴趣,而外地人会觉得到了北京就必须去一次“全聚德”。正是这种心理,把“全聚德”养活了,同时也把“全聚德”给惯坏了。
现代的城市化运动所造成的这一改变,是无所不在的。不光是饭店,其实它与一切产品的生产都有关。
实际上,两种不同的饭店是两种不同交换方式的代表。传统的饭店有精心烹制的美味,有传统商业道德的支持,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活在熟识的人之中,受到赞扬,欣赏自己的手艺,这里面有无穷的魅力,已经不仅仅是挣钱所能包含的了。生活美学,是各种生活乐趣的延伸。在现代工商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个人信任关系不存在了,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任感寄托在品牌上。这一转变在生产者一边,当然并不是不受制约的。品牌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创意、经营理念、资本投入、内部管理、宣传广告效应,再加上可能借用的传统因素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形成的。消费者从对品牌的信任,进而发展为对品牌的炫耀。去哪个饭店,穿哪个牌子的衣服,变成了财富的象征,而财富则变成了美的代名词。现代生活使人们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市场、商品、资本带来了美,也丧失了美。我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后再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制造种种品牌,但却让人失去了一种古代人所特有的享受。
二、当代语境下艺术观念的变化
现代社会带来了美在性质上的根本变化,讨论美学、艺术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看。由此,我们引入到这样一个话题:什么是艺术?
这好像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而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大,大到超出人们的估计之外。很多人就此写过无数的书。李泽厚1980年代初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所写的序言中提到:李泽厚无意之中说过,艺术是可以“写作很多本书的题材”。宗白华对这句话很欣赏。这使李泽厚感到意外,“颇觉费解”。[1](P1)可能更使李泽厚感到意外的,是这个问题此后的发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谈论艺术定义的人越来越多。
先锋艺术出现之后,一些过去人们所假定的艺术的条件都受到了质疑,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例如,过去人们假定,艺术品必然是美的,是个人独创,用康德的话说,与“天才”、“灵感”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持这种观念的人,在碰到先锋艺术时,就会有巨大的困惑。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问两个问题:一些当代艺术品“美”吗?它们成为艺术品是由于它们的“美”吗?
这两个问题,过去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你走进传统的美术馆,例如在巴黎,无论是进卢浮宫还是进奥赛博物馆,这两个问题都不存在。这里所藏的艺术品,都是精美绝伦的作品,是美的最高杰作。过去的理论也肯定这一点:艺术品当然美。人们讨论艺术比生活更美、还是生活比艺术更美的问题,这种讨论绝没有否定艺术之美的意思。人们大都倾向于认为,艺术美是生活美的集中体现。只是有人认为,生活美能不断地给艺术美的创造以启示,是艺术美的来源,并强调,生活中有艺术中所没有的美。人们还可以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美,一个时代的美在一个时代的艺术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因此,艺术的历史可以成为审美观念史的表征、物化和体现。
艺术品美!艺术品之所以是艺术品,是因为它们美!不美的艺术品不配称为艺术品!艺术品的好坏,在于它们的美的程度!这些人们过去熟悉的信条,现在碰到了危机。面对先锋艺术时,它们变得苍白无力。当我们走进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走进北京的“798”、酒厂、宋庄等地时,我们会发现,一些当代艺术品一点也不美,它们或者是很丑、很怪,或者谈不上美与丑。
美不美?这个标准在失效。随着第一个问题无法回答,第二问题也同样被提了出来:一些艺术品即使可能“美”,也不是由于“美”而成为艺术品。例如,一些看上去造型说得过去的物件,如一些现成物或工业制成品,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美”而成为艺术品。有理论家说杜尚的《泉》很漂亮,于是立刻遭到抨击和嘲笑。《泉》成为艺术品,与它的漂亮与否、与它的造型和光泽,没有任何关系。这时,艺术与美分离了。
这的确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许多理论家都觉得难以回答。面对这些问题,有理论滞后的现象。一些我们所熟悉的理论家,都对先锋艺术持回避的态度。例如,在中国影响很大的苏珊·朗格、恩斯特·贡布里希、鲁道夫·阿恩海姆等等,都不直接讨论先锋艺术。在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等人的论述中,涉及到一些艺术中的抽象问题,但对像杜尚、沃霍尔这样一些人的艺术还是缺乏解释力。
对先锋艺术的正面回应,是从分析美学开始的。乔治·迪基用“制度”,阿瑟·丹托用“艺术界”,来探讨艺术的定义问题,说明先锋艺术仍然是艺术的理由。理论拒绝当下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理论被边缘化。正面应对先锋艺术挑战的分析美学赢得了读者,也在艺术家和艺术批评界受到欢迎。正是这个原因,分析美学在西方流行了半个多世纪,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学术界应该怎样对待分析美学?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前几年,在天津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来了几位重要的国外学者,其中有年长的国际美学协会的前会长,也有年轻的在美学界锋头正健的新锐。会后,在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两位从国外来的代表突然叫住我,摆出一付好好谈谈的姿态,质问我为什么让自己的学生研究分析美学?原来,在会议期间,他们与我的几位研究生聊了聊,并对他们的选题不以为然。我说,分析美学在你们那儿过时了,在中国并没有过时。
其实,说“过时”有点夸大,在西方,分析美学还有人坚持,并且不断有新的成果。然而,这里面有一个奇怪的错位。在西方分析美学兴盛时,中国美学界讨论得最多的是美的唯物主义基础、艺术中的形象思维等话题。从20世纪末和21世纪之交开始,分析美学有被主流美学界放弃的趋向。1998年在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召开的第14届世界美学大会,提出了走出分析美学的口号。美学要走出间接性,要引入文化理论的研究成果,要关注社会人生,要重回实用主义对经验的重视,要从非西方的广大“第三世界”的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是新美学的发展潮流。然而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美学界来说,还必须补分析美学课。从莫里斯·维兹到阿瑟·丹托,分析美学家们所提出的重要观点中国人都不熟悉。他们提出的一些有意义的话题,他们对先锋艺术的关注,都值得我们思考。翻译、介绍一些他们的著作,对他们进行研究,对发展中国美学来说很重要。我有几位研究生,分别研究过阿瑟·丹托、门罗·比厄斯利、乔治·迪基、纳尔逊·古德曼等重要美学家。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国内美学的发展有贡献。
分析美学引进后,对“艺术的定义”问题的理解起到了深化的作用。但分析美学只是将研究的触角伸入到当代人们对一些艺术和美学概念的使用而已。只有回到社会本身,才能理解“艺术”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引入的?
我们可能会接触到许多艺术史著作,谈论原始艺术、古代艺术、东方艺术、非洲艺术,以及中世纪艺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等等概念。这些表述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些表述之下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艺术观念。我们所熟悉的艺术观念,是在18世纪至19世纪才逐渐形成。我们是依据那时所形成的艺术观念对古代和东方进行投射,从而将那里所产出的类似物也称为艺术。自20世纪以来,艺术观念又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
在传统社会中,艺术与工艺没有根本的区分。画家、雕塑家与其他手艺人没有什么区别。在欧洲中世纪后期,社会上有三种势力并存:第一是教士,代表着神权;第二是贵族,代表着世俗权力;第三是城市工商业从业者。修道院里的教士掌握着神的权力,人的心灵、教育的权力;封建贵族和君主有土地和军队,是世俗的统治者;而城市工商业者,本来在这三者中是最弱小的一种人,辛勤劳动却备受欺凌,但随着生产的发展、远距离贸易的形成,他们积累着财富,逐渐取得社会地位。
艺术家们本来应属于这第三种人的一部分。艺术是从手工业者中分化出来的。画家、雕塑家,与木匠、石匠、铁匠,本来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说要有区别的话,也许金银首饰匠地位高一些,理由是他们处理更贵重的材料;钟表匠地位更高一些,那是一种更需要复杂技术的工作。
从现代的观点看,手工业代表着一种非常落后的生产效率,与机器大工业无法相比。纺织机出现后,纺车就被淘汰;汽车、火车出现后,长途运输依靠牛车、马车的局面就一去而不复返。效率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与知识就是力量一样,都成为一些现代性的信条。对于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来说,他们有着其他的乐趣,现代性意味着这些乐趣的丧失。
手工业的状态有其稳定性。生活在其中的人,并非处于一种时刻感受到其落后,要对之加以改变的心态之中。手工业者在生产中,会有一种后来只有艺术家才有的感觉。木匠打造床,铁匠打制宝剑,磨片工人磨镜片,建筑师造房子,都有一种对过程本身和对自己作品的欣赏。他们的生产活动,并非只是指向外在的目的,而是指向其本身。这既是生产,也是生活,两者没有分离。这与画家作画、书法家写字、唱歌跳舞的人表演,多少有一些类似。这种对手工业的感受,本身具有审美性。如果说,这种状态作为一种落后的状态要被改变的话,那么它的审美性作为一种社会发展中的刹车闸,成为保留这种状态的力量。
当然,社会的前进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艺术进步的出现,不是由于艺术本身,而是由于生产的进步。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分工。手工业从农业和畜牧业中分工出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手工业者们当然是进一步分工的。中国古代讲“百工”,就是说,有着各种各样的工人在分别做着各种不同的事,每一种工人有着自己专业内的技能技巧,相互不可代替,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各行各业之中,也各有其优良中差,即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行之中,状元是好的,也相应有差的。
到了现代社会,大规模机器工业的出现,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正像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揭示的,工人们对过程的欣赏消失了,人被机器所控制。在这时,完成了设计与生产的分离、生产过程内部各工序的分离、生产与销售的分离。设计者不再生产,他们只是试验,提出思路、画出图纸、生产出样本,再进行产品及其生产工序的定型。这一切完成以后,设计者等待生产者的反馈,再对产品进行修改。生产过程中的各工序,随着自动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位生产者只能像是一盘棋中的某个棋子一样被分配一个角色。
于是,原本按行业进行的分工,被贯彻到了行业内部。我们过去问:你是干什么的?指的是你是干什么行业的。我们可以回答:是打铁的、造房子的、制锁的、造钟表的。随着分工的发展,我们就问:你在哪里工作?在钢铁厂工作的人,不一定在炼钢。在药厂工作的人,不一定是在制药。至于对一位在电脑工厂工作的人,说他是在造电脑,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他所做的是无数的工种中的一种,并且在复杂的工序中承担其中的某一段的工作,如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人,做的是与市场有关的工作,如产品推销、售后服务等等。
分工使得生产者被局限于生产过程的一个很小的片断之中,而不能接触到生产的全过程,他们只是在工作而已,甚至不能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有成就感。原因是,他们看不到在一个庞大的生产过程中,自己所贡献的一部分在起什么作用。当然,他们就更不能与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构成一种直接的人与人的交流关系了。今天,某一位工人所能夸耀的只能是,他在一家大公司工作,这个公司进入了全球五百强,他在这个公司里当了一个部门经理或某项技术的主管,等等。
传统的市场是一种人与人的直接关系。那是个人与个人打交道,熟人之间打交道,依赖的是对个人的信任。同乡、同学、老朋友、老熟人,构成一个商圈,相互之间的商业活动无需合同的制约,而靠传统的道德支持。
在现代社会,这种关系被制度化、非人化了。商业关系不依赖个人诚信和信誉,个人的历练、教养、才华等等变得不再重要。现代商业需要的是法律,是一种契约关系。商人可以尔虞我诈、巧取豪夺,他们与顾客之间靠契约、合同、司法制裁来构成商业关系,而不是个人关系。
合同和契约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一方面具有解放的意义,这种关系消除了人情社会的弊端;另一方面也丧失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种种美好的东西,例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的直接交流、个人的信任、个人魅力的形成并在这种交换中起作用等等。
现代生产的另一种重要的分离,是生产与生活的分离。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出现了一个现象:上班。人们按点上班,按点下班。迟到要被解雇或者扣工资,不许早退或早退也要被扣工资,无故旷工是严重的错误,有事请假要得到批准。或者,反过来说,加班会要求老板发加班工资,节假日要求双倍工资。是否加班被看成是工人的权利,老板要求工人加班须工人自愿,不能强迫。再进一步,我下班以后的时间不属于老板,我下班以后是自由的,做什么老板无权过问。由此还衍生出种种考勤制度,在大企业,上下班要打卡,将这种考勤制度非人化,不是由老板来监督你按时上班,而是由机器监督;也不是由老板来决定是否扣你的工资,而是由机器提供的记录来决定。这一切,都造成一个结果: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分离,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与生活的分离。这样一来,我们的时间被分成两部分:上班是生产,下班是生活。我们还由此产生了一种自由观,上班没自由,下班才自由。自由越多,就是工作时间越少。我在瑞典时,记得有一次上街看“五一”游行,瑞典共产党打出的口号是“六小时工作制”。这就典型地代表了一种观念:更少的工作,更多的自由。
艺术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得以改变。手工业者的小铺子,开着店就是家,不存在工作与业余之分。没有人让他们去打卡,工作是自由的。如果说他们的工作方式的缺陷是效率不高,不一定能挣很多钱的话,这种工作方式有许多值得怀念之处。他们所需要的自由,是自由地工作和自由地销售自己的产品,不被有权有势者征召去做奴隶式的强迫劳动,劳动的成果不被有权有势者巧取豪夺。
现代社会所造成的劳动时不自由、不劳动时才自由,是不是更好?也许不是,但这是无奈的。有一种民间调侃的说法:理想的生活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工作时间越少越好?或者不需要工作就能赚到很多钱,然后想干嘛就干嘛?这些想法好不好?那么,剩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打扑克,或者打麻将吧,更高雅一点,去欣赏艺术吧。审美要无利害,艺术要超功利,正是这么产生的。
艺术是非功利的,是人们在业余时间欣赏的东西。审美要自由,而工作时没有自由。艺术是自由,要让这种自由占据业余的时间。于是,工作与业余的对立、与功利和非功利的对立相匹配。这是大写字母A开头的艺术(Art)的现代艺术观念、是以“美的艺术”(the fine arts)观念为代表的现代艺术体系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三、“终结”观视野下的艺术使命问题
在20世纪接近结束的那几年,也许受基督教与千禧年有关信仰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终结”的说法。民间有,学术圈也有,其中有些还很有名。“终结”的话语成为学术语言,出现在不同的学科之中,激起了阵阵波澜。
怎么看待这些“终结”说?如果你到国外旅行,常会在一些车站和繁华商业区看到有一两个人,身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宣布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有的说是明天到,有的说是明年到。对此,我们早已习惯了,视而不见。是不是这种“终结”话语的发明者,与这些街上挂牌子的人,属于同一种性质?谈论未来,一定要与当下有关。如果没有关系,那就像街上挂这种牌子的人,随他们去吧,他们有表达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我们也有不理会他们的自由。然而,如果这种观点富有哲学的深度,揭示了当代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那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了。
“艺术终结”的说法,是由阿瑟·丹托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我的一位学生张冰博士总结道,艺术在当代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艺术品被接受,不再依靠其提供的美感,而是依靠对它进行哲学的阐释;艺术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将被其他更高的精神形式所取代;艺术在表现手段上的进步可能性被耗尽,不再能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创新;艺术所依赖的宏大叙事不再具有吸引力,从而导致叙事的终结。
这一切的原因,使得黑格尔的预言,即绝对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将从艺术转向宗教和哲学,得到了实现。黑格尔将世界的历史描绘成一个进步的过程。这种进步是由于理念的进步。理念经历了自然界、生物界、人类社会,来到了精神界。绝对精神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过程,从艺术到宗教到哲学。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宗教是理念的超越,而从感性再回到理念自身之时,在绝对精神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就成了哲学。
说到“终结”,大家熟悉的是弗朗西斯·福山,他讲“历史终结”。福山在丹托发文的三年后,发表了他著名的关于“历史终结”的文章。这种“终结”说,同样来源于黑格尔。但是,丹托与福山对“终结”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具体说来,这是两条不同的线索。从黑格尔经科耶夫到福山是一条线索,从黑格尔经马克思到丹托是另一条线索。
福山从一位法国的俄裔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那里受到启发,从自由民主体制的精神以及唯心主义的立场来继承黑格尔主义。科耶夫从黑格尔的词句中捕捉了这样一个观点:历史终结于1806年。他说这一年拿破仑在耶拿-奥尔斯塔特会战中大败俄奥联军,这标志着法国革命的理想得到了实现。一位读着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长大的俄国人,竟然有这样的思想,倒是够叛逆的。他忘记老托尔斯泰曾那么深刻地揭示了天空的伟大和个人的渺小。
福山继承了这种思想,接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向“左”开一炮,说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对的;再向“右”开一炮,认为《华尔街杂志》派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也不对。于是,历史被归结为一种神秘的精神的力量。
阿瑟·丹托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马克思设想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P85)一个人可以从事多种多样的工作,而不是让人局限于某一个方面的专家。社会分工被打破,造成了社会的阶级分化,这是未来的共产主义,这代表历史的终结。
根据这一思路,丹托把艺术的终结说成是这样一种情况:“正如马克思也许会说的那样,你可能早晨是一位抽象主义者,下午是一位照相现实主义者,晚上成了极简的极简主义者。或者你可剪纸人,或者做任何你喜欢透顶的事。多元主义的时代来临了。你无论做什么都已无关紧要,多元主义的意思就是如此。当一个方向与另一个方向一样行得通时,方向的概念就不再适用。”[3](P108)
这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其实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把艺术的未来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将它归结为人的活动方式而不是离开人的活动的某种抽象的观念,回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这三点证明丹托所继承的的确是马克思线索的黑格尔式“终结”观,与科耶夫和福山有着根本的区别。
“艺术终结”观,也许并非是在宣布艺术的死刑。其实,即使宣布了,也无法执行。艺术在黑格尔之后蓬勃发展着。我们所熟悉的大量19世纪、20世纪的艺术精品,都是在黑格尔身后出现的。因此,在黑格尔宣布“艺术终结”以后,艺术恰恰迎来了辉煌的时代。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的某些部门相敌对。这也不意味着艺术就此终结。这种“敌对”会造就特别的艺术需要。在一个生活中没有诗的时代,诗的生产也有可能由于需要而特别兴盛。在一个领域匮乏的,在另一个领域会出现进行补偿的需要。
在说出“艺术终结”之后,丹托多次重提这种说法,并作出种种修正。他说,“终结”不是“死亡”。艺术终结后还会有艺术,正像历史终结后还会有人类社会一样。在这一点上,丹托与福山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一个观点,终结的是“进步”。如果明天与今天一样,后天与明天也一样,或者说,有变化但无发展,历史就终结了,艺术史也就终结了。
我们常常会对艺术的进步感到困惑。真的有某种东西叫做艺术的进步吗?
制作性的艺术品可以在技术的进步意义上讲艺术的进步,能工巧匠的技能和诀窍代代相传,代代有所发展,从而造出精品。从故宫的珍藏到工艺美术展览中看到的工艺精品,我们都能感受到,精湛的传统的工艺能成为一个民族的骄傲,被誉为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们绝非一人之功,也非一代人之功,是经历了许多代人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造型艺术可以在对现实模仿的意义上讲进步。对形的征服,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绘画雕塑要造得像,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这是技能问题。要把握形,又不仅仅是技能问题,要克服许多的观念障碍。例如,当我们说所造的是神像,必须按照某种程式来作时,就阻止了形的改进。一些实用的目的也限制了人们对形似的要求。例如,正如恩斯特·贡布里希所分析的,神像、象棋的棋子、姜饼人、儿童画,以至于一些社会公共场所的符号,都受着其目的的制约,不必过于追求形似。
造型艺术所追求的“视觉的征服”,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造得像不等于照样制作。眼睛看到什么就画什么,那还不简单?艺术史家们告诉我们,这不简单。这里面有视觉的设计,有贡布里希所说的“匹配”,即对仿造物与被仿对象进行对照并对制作流程作出改进的过程,还有对视觉的时代和文化因素的适应,等等。
但是,这一切都有完成或接近完成之时。当这一切被完成或接近完成之时,艺术又会如何进步?没有进步的艺术会走向何方?这时,艺术终结的问题,就再一次严肃地提了出来。艺术终结,不是指艺术死亡,而是艺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失去了再往前改进的方向。艺术下一步怎么办?艺术的前景如何?
所谓艺术的前景,实际上是艺术定位寻找。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现代艺术观念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与市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以对立的形式出现的。工作时没有自由,艺术中有自由。在机器对人压迫、使分工越来越细、使生命机械化之外,艺术提供了人的天才和灵感发挥、人的知解力与想像力协调发展、人的超功利的高雅趣味得以发挥的场所。这对社会也构成了一种补充。
然而,当社会进入到所谓的“后现代”之后,消费社会所推动的美化商品以赢得竞争的观念,对艺术提出了新的挑战。人人都说要重视消费,说我们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其实,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但在过去,都是生产促进消费,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生产过剩了怎么办,是不是就是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了?可以按需分配了?好像又不是。过剩所带来的只是危机。今天,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们都在说,要想经济走出危机,就需要民众有消费信心。人民敢花钱,经济就能发展。
由于生产过剩,就有强烈的竞争。竞争会造成什么?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说:竞争好啊!价格会下降,生产效率会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都会好得多。我们这一代人在生活中吃够了计划经济的苦:产品质量差,服务态度不好,商店里货架空空;去买东西,一问三不知,一问三没有,再加上一问三不理,东西没有买到,带着一肚子气回来了。现在好了,实行市场经济,产品的质量、服务态度全面改善,货架充盈,要什么有什么。
然而,竞争的弊端也会暴露出来。过去,生产是为了满足需要。人们的理想是物资极大的丰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那么,当需要已经满足,不愁吃、不愁穿之时,又怎么办?这时,出现了又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已经满足了?
需要是可以被制造的。生产制造需要,要通过生产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以及相关的消费观念,要通过新产品的生产制造时尚并刺激人们的需求,要通过消费的发展使人们处在一个永不满足的物质追逐之中。这样,经济就发展和繁荣了。
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之中,艺术在哪里?艺术家在哪里?他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如果要谈论“艺术终结”,就必须把这些问题鲜明地提出来。
首先,产品被美化。搞搞设计,使产品的外观、包装都变得漂亮些。也许,那是艺术家的学生们做的事,“真正的”艺术家不愿去做。也许,设计曾经并仍然向艺术学习。但是,设计改变世界,当人们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从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变成生活在人造的环境中时,生活在一种设计出来的世界之中,就既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宿命。
产品竞争的规律,从品质和服务延伸到了审美领域。当产品的生产都已成熟,不再存在着明显的质量问题时,外观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买笔记本电脑,买汽车,买冰箱电视,都要考虑是否好看。美学决定了竞争力。
有人说,由于审美因素,造成了财产观念的弱化。这是不对的。这其实是强化,只是表现形式转化了。财产没有消失,穿着简约有品位的明星比打扮得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的乡下土财主的女儿要更加好看,也更能显示出有钱的样子。
这时,出现了这样的悖论:美学主张审美无功利,商品的美恰恰成了财富的象征。对于艺术家来说,搞设计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重要的还是创作出艺术品。但是,当如果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品都已经美化、艺术化了之时,那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品?艺术家们教出的学生们,学到了一些造型的规律;于是,在商品设计时,他们就“按照美的规律”去制造,让艺术家们自己无事可做了。“劳动创造了美”,但既然美已经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出来,为什么还要艺术家把它们再创造一次呢?
其次,艺术被产业化。艺术本来是个人创作,如果说天才与灵感还没被后来的美学家们强调到那么高的程度的话,最起码,艺术家与接受者有着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关系。妈妈做的饭是个性化的,因此我们就喜欢。街区饭馆的饭,仍有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在,致力于在产品反馈中不断改进,也致力于一种宾至如归的服务。但是,现代连锁店所能提供的,就只是标准化的服务了。这种标准化的服务,是创意的结果:创造出来,经过试验被认为可普遍接受后,就大量复制推广。现代创意产业也与此相类似,艺术家被放到了一个巨大的生产过程中,其中也需要创意,但创意要通过制作、复制、宣传广告、品牌效应等复杂的过程才能实现。
以上两种情况,前一种是工业艺术化,后一种是艺术工业化。这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也许,正是无所不在的美,迫使艺术放弃美。一个处处皆美的世界,是像迪斯尼乐园一样的幻境,也许我们也需要,但这不是人的家园。这是先锋艺术与美脱离的根源。许多学者都提出这样的话题。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在处处都美时,艺术要使人震惊。但是,如果艺术只是要给人以震惊的话,是不是会给各种各样的胡闹开辟方便之门,使艺术界变成疯人院?一些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提出救赎的概念,认为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艺术能够起救赎的作用。
救赎说与前面所提出的补偿说有类似之处。补偿是指社会营养不良,要补充营养,经济发展了,精神有缺失,在艺术中提供补偿。救赎则是指社会有了疾病,艺术是救世的药方。在性质上,两者当然是有区别的。用以补偿的营养品,是美好的,艺术与美结合在一起。用以救世的药品,不一定美,甚至与美无关,正像良药苦口一样,于是,提供的是震惊、恐怖、恶心,其中不具有刺激性的也不过是无色无味而已。这种区别如果被放大的话,那就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分。现代主义仍然追求美,是一种补偿;后现代主义放弃了美,就成了救赎。
无论是补偿还是救赎,都不是生活的常态;正像无论是营养品还是药品,都不是生活必需品一样。所有这些立论,都是以艺术与生活的二分、以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怎样才能回到艺术与生活的合一?怎样才能真正走向物质与精神相连续的一元论?这都是问题,也同时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从这里,我想再次回到一个我曾经多次举过的例子。毕达哥拉斯说过,参加奥运会的有三种人,第一种是运动员,第二种是观众,第三种人是来做生意的。在这三种人中,谁最高贵呢?他给了一个奇怪的回答:观众。这一回答代表了欧洲传统哲学的一个大传统,即对世界和人生的旁观者态度。由于旁观,于是产生主客二分、劳心劳力二分、物质精神二分。这种态度需要“终结”,只有“终结”,我们才能走出“二元”而回归“一元”。
那么,什么叫做“一元”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回到活动而不是静观的立场,回到一种人与人的直接关系之上,回到对参与者的最高的尊重之上。参加奥运会的三种人中,最高贵的应该是运动员,不是观看的贵族,不是来挣钱或提供赞助的生意人。同样,在艺术活动中,回到艺术家的主体地位之上。
让我们再次回到文章开头的例子:车站附近的饭店与城市老街区里的老字号饭店的区别。前者依靠品牌的力量,有了改进。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老字号饭店中的那种个人与个人的关系。
回到人与人直接的关系,是回到一种诗意的过去。古代文人会相互赠诗、赠书画,把自己觉得很得意的作品送给朋友。一位手艺人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用它来挣钱谋生却又不仅仅是谋生。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生活和艺术的态度,对于现代社会还有没有价值?能否作为一种因素留在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之中?它们的价值何在?问题很多,也很有意义,我们需要继续思考下去。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做起,这才是更重要的。从现在做起: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艺术!
[1] 李泽厚.序[A].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Arthur C. Danto.ThePhilosophicalDisenfranchisementofArt[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