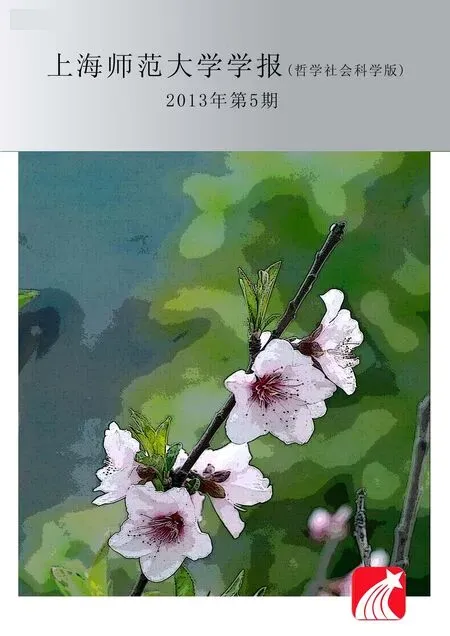环境友好型人格与环境美德面临的挑战①
[美] 桑德拉·简·费尔班克斯
(美国贝瑞大学 神学与哲学系,佛罗里达 33161)
直到最近,西方德性伦理才倡导以自然为关切对象的美德。这不奇怪,因为西方哲学与宗教历来主张人类高于自然、我们与自然之间无须遵循任何道德原则的观念。环保主义者呼吁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否则就不能应对当今环境问题提出的挑战。倡导新的美德以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无论从纠正西方思想的显著缺陷来说,还是就保持地球的宜居环境而言,都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不幸的是,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在诸多方面阻碍了任何新的环境美德教化。因而,环境美德教化不应当是环境教育唯一的中心任务。至少在环境美德观念相容于盛行的好生活观念之前,环境教育应当诉诸人类的自我利益。
一、导言
尽管细节与个例方面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分歧,但我们仍然可以说,西方哲学和宗教整体上助长了对环境的统治与掠夺。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比如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与消费主义的理想生活模式不谋而合,为造成灾难性环境后果的人类态度、价值观念与信念提供了温床。其结果是,我们面对的各种环境问题——全球变暖、自然资源与荒野地区的破坏和消耗,爆炸性的人口增长、有毒的垃圾排放,等等——日益严重,对于子孙后代的生存而言极可能是毁灭性的。包括生物中心主义者、生态中心主义者、以及生态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环境哲学家们呼吁变革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转向强调非人类生命或者自然整体之内在价值的理论。
所有这些环境哲学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否则我们就无法应对当今环境问题提出的挑战。由于这种态度转变意图促成新的、更适当的环境行为方式,因而热心环保的著述者们致力于一项共同的事业,即直接或间接地倡导一种环境美德或一系列新的环境美德。②直到最近,西方德性伦理才认可以自然为关切对象的美德。这不奇怪,因为西方哲学与宗教普遍主张人类高于自然、我们与自然之间无须遵循任何道德原则的观念,除非作为对人类的间接义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康德的论述③)。自然,包括非人类生命、自然对象以及生态整体,具有内价值,从而具有道德地位,这是西方哲学最近才发展起来的理念。
因此,提倡新的美德以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无论从纠正西方思想的显著缺陷来说,还是(几乎确定无疑)为使这样一个星球维持下去成为可能,都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不幸的是,正如我将指出的,美国——因其典型性,我将予以重点探讨——这样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在不同方面阻碍任何新的环境美德深入人心。因而,至少短期来看,环境美德教化不应当是环境教育唯一的、甚至可能也不是其首要的任务。正如我将论证的,重要的是,这种教育应当诉诸人类的自我利益,至少在环境美德观念相容于盛行的好生活观念之前应当如此。
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我对倡导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多位杰出学者所提出的一系列环境美德进行了梳理与归纳,从而简要勾画出一种环境友好型人格。其次,我试图阐述美国文化对于培养这些环境美德所提出的难题。最后,我以可操作性建议作为结论,提出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美国文化,使之走向环境觉醒与关切,推动环境美德的教化。
二、环境友好型人格的应有美德
基于生物中心主义、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等环境哲学的杰出成就,我将描述被这些哲学所赞扬的、环境友好型人格应有的12种美德。在确定这些美德之前,我想就品格特征是什么、何以成为美德的问题作一些说明。罗纳德·桑德勒认为品格特征是“在某些情景中,与行动、情感、欲望相关的、为获得规范性或动机性力量而进行某些考量的意向”(Sandler 2007, 13; 亦可参阅Van Wensveen 2000)。但是,一种品格特征何以成为一种美德?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关于美德的界定,我将简要介绍3种重要的方法。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如果一种品格特征能够推进幸福之目的的实现,亦即增进人类的福祉或人性的兴盛,它就是一种美德 (Aristotle 1999)。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人类本性的特有功能是理性,因而人性兴盛要求发展理性能力。灵魂有两种理性功能: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理性的培养造就诸如智慧、理解、聪慧之类的美德,而实践理性的培养则造就诸如节制、勇敢、正义、慷慨之类的美德。美德是理性使欲望与情感合乎中道的功能展现,是严格训练、习惯成自然的结果。以某种人性繁荣的观念为基础的德性伦理通常被称为幸福论(eudaimonism)。④
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美德概念,其核心是“基于其作为所属自然物种的代表或拥有的物种身份来评价生物个体”(1999, 197)。所以,一物种之优良个体成员所拥有的特征,不单属于该个体,也服务于整个物种的繁荣。一棵植物的组织与机能如果很好地服务于它的个体生存,也有助于物种的繁衍,则它就是优良的(Hursthouse 1999)。她进一步将这种自然主义视角延伸至人类,她认为人类是复杂的社会性动物:
社会性动物个体(作为更复杂物种的一个成员)是优秀的,意味着它在下述方面状态良好、机能健全:(1)它的身体部位;(2)它的功能运行;(3)它的行为活动;以及(4)它的欲望与情感。它是否状态良好、机能健全决定于这四个方面是否能够出色地实现下述目标:(1)它的个体生存;(2)它的物种繁衍;(3)它独有的免于痛苦的自由以及欢愉;以及(4)社会群体机制健全——以该物种特有的方式。(Hursthouse 1999, 202)
她承认关于人类的伦理评价不是依据单纯身体上的反应。评价人类的依据是“我们的偏好、我们的感情和欲求所驱使的行为,以及基于理性的行为”(Hursthouse 1999, 207)。赫斯特豪斯的自然主义可以说是改良了的幸福论,因为它不仅强调个体的兴盛,也强调人类物种的兴盛。
罗纳德·桑德勒提倡以一种多元主义的目的论视角来理解美德。⑤根据桑德勒的看法:
一个人是伦理上优秀的(亦即有美德的),意味着她在以下方面表现良好:(1)情感;(2)欲求;(3)行动(出于理性与偏好)。她是否表现良好取决于这些方面能否有助于推进以下目的:(1)她的个体生存;(2)她所属物种的繁衍;(3)它特有的免于痛苦的自由以及欢愉;(4)社会群体机制健全;(5)她的自主;(6)知识积累;(7)有意义的生活;以及(8)幸福之外的目的(根植于幸福之外的善与价值)的实现——以人类特有的方式(亦即,以一种可以被视为善的方式)。(Sandler 2007, 28)
我更愿意接受桑德勒的美德观,因为它更加全面,结合了幸福论与自然主义的看法。另外,他的多元主义视角尤其适合于环境美德,因为它所包含的理性与动机,超越了个体抑或物种层面的人类兴盛。例如,它能够容纳诸如生物共同体的统一、稳定与美之类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然而,尽管桑德勒的美德理论更为可取,我希望强调的是,我关于美国文化阻碍环境美德培养的主张与上述三种理论都是相容的,并且事实上(我相信)与任何可行的美德理论并行不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美国文化对生态的灭绝性影响使之背离任何合理解释下的环境美德(以及其他美德)。
还应当注意的是,讨论的环境诸美德并不意味着企图提供一种完整的环境美德概念。⑥事实上,本文并不涉及任何一种通常意义上的美德理论;我的策略并不复杂,评述所有完备环境哲学都认可的一些核心美德,并表明美国文化对它们的威胁。
第一个、并且可能最为显见的美德是尊重自然。保罗·泰勒将尊重自然描述为一种理性态度,与康德所说的尊重人相似;它的基础不是爱或喜好,而是对于内在价值的认可。非人类生命、诸如物种、生态系统之类的生态整体、甚至像山川河流那样没有生命的自然对象,都拥有内在价值 (Taylor 2008)。在此意义上,自然不应当被视为工具,不能仅仅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与利益。泰勒与詹姆斯·斯特巴(James Sterba)等生物中心论者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事物如果能受益或被伤害,便拥有“它自身的善”;如果一事物拥有它自身的善,那么,毫无理由地伤害它就是错误的 (Sterba 2008)。根据这样一种态度,自然界具有自身善的任何事物都被赋予道德地位 (Des Jardins 2006)。
大地伦理和深层生态学的倡导者走得更远,不仅承认所有生物体具有内在价值,而且认为整个生命共同体也拥有内在价值。在比尔·德瓦尔(Bill Devall)与乔治·塞申斯(George Sessions)看来,深层生态学的基本直觉之一就是“生态圈中的所有生物体与实体,作为相互联系之整体的部分,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Devall and Sessions 1985, 67)。当阿尔多·利奥波德呼吁人类改变他们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它的普通成员与公民”时,大地伦理同样表达了生命平等的直觉(Leopold 1949, 24)。因此,尊重的美德要求我们承认非人类生命体、自然客体、以及生命共同体的内在价值。
尊重自然要求我们在道德商议过程中运用相关原则;对于每一个原则,都可能存在一种相应的美德。例如,保罗·泰勒论述了尊重自然这一态度所要求的四大原则(Taylor 1986)。不伤害原则要求我们承担的消极责任是,除非出于自我防卫或满足基本需求,我们不应该伤害自然;不干涉原则要求我们承担的消极责任是避免侵害有机体或生态系统的自由;忠诚原则适用于动物,禁止欺骗或失信于动物,比如狩猎、钓鱼、设陷阱之类的活动;补偿原则要求那些伤害自然的人为他们造成的伤害进行补偿(例如,由于一项人类工程而迫不得已毁坏湿地,则应该另辟他处造就湿地)。因此,善待环境的人将拥有不伤害、不干涉、忠诚、补偿正义的美德。⑦
环境良善还要求谦逊的美德,这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谦逊美德意味着接受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将自身视为相互关联的生命共同体的平等成员。根据托马斯·希尔的看法,谦逊是对我们在自然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一种恰当理解,这要求我们获得有关环境的知识,克服自视甚高的观念,并且接受自我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事实(Hill 2005)。
无知可以导致对破坏自然的行为,也可能使人变得不谦逊。希尔争辩说:
[无知的人]似乎并不理解我们是整个宇宙场景中极细微的颗粒、漫长演化进程中极短暂的瞬间;不理解我只不过是地球亿万物种的其中之一,人类历史过程中的匆匆过客。他们当然了解星球、化石、昆虫以及古代遗址,但他们是否真的知晓究竟是什么样的复杂过程使自然世界变成今天的模样?他们是否意识到使他们身体正常运转的内在力量多么地相似于支配所有生物的力量,甚至与没有生命的东西也有着那么多共同点?(Hill 2005, 51)
当然,拥有生态学知识与自然的体验,并不一定意味着谦逊的态度,但它确实唤醒这样一种意识:我们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具有的价值不依赖于它对我们是否有用。与缺乏这种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自视甚高的观念,亦即“参照自己以及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来衡量每一个事物之重要程度的倾向”(Hill 2005, 54)。希尔认为,克服自视甚高的倾向,必须学会基于事物自身的缘故而珍视它们。例如,“阿尔卑斯山脉、海上风暴、科罗拉多大峡谷、高耸的红杉林以及‘头顶的星空’,使很多人把日常俗务、甚至我们这个物种放在了比较不重要的位置”(Hill 2005, 53)。如果我们能够修身养性,抑制面对自然时自视甚高的倾向,则破坏行为会少得多。
最后,希尔认为,缺乏谦逊不仅源于自视甚高,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接纳这样的自我:我作为自然一部分,就像所有其他生物体一样生存、成长、衰老和死亡。我们极力创建人工环境以逃避自然世界,逃避死亡的现实(Hill 2005)。在希尔看来,掩饰我们属于自然的事实很可能表明了自我接纳的缺乏——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不是这样,⑧而缺乏自我接纳能够引发劫掠自然的行为。因此,环境良善要求掌握相关环境知识,贬抑自视甚高,学会自我接纳,成为谦逊的人。
主流环境哲学虽然没有直接探讨谦逊态度,⑨却显而易见地一致谴责面对自然时以人类为中心的傲慢自大。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环境利己主义,因为它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高于”自然,也优越于所有其他的物种;人类的需要、目标和兴趣必然优先于其他物种与生物共同体的需要、目标和兴趣。自然被当作一种供人类使用以实现其目标的资源。大地伦理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摒弃我们作为大地“征服者”的角色,提倡更加谦逊的角色,即生物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公民”。同时,它强调达尔文的演化伦理以及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亲缘关系,倡导我们在本性上属于动物的自我接纳。同样的,深层生态学谴责“在技术统治与工业化社会(technocratic-industrial societies)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人是孤立的、与大自然完全分离的,是优越于并且主宰其他创造物的”(Devall and Sessions 1985, 65)。最后,女性主义采用“傲慢眼神(arrogant eye)”这一概念来表明统治自然的态度。傲慢眼神意味着“一种并吞其他事物以为己所用的、具有侵略性和强迫性的视角”(Warren 2008, 153)。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如此常见地与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谦逊的培养有助于抑制这种态度。
环境哲学无一例外地认可同情、爱与关怀自然或者整个生物共同体的美德。例如,J. 贝尔德·科利考特(J. Baird Callicott)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的基础上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赞成一种扩大的伦理世界,使其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包括“土壤、水、植物与动物,或者从整体谓之为大地”在内的生物共同体(2008, 153)。在他看来,达尔文关于所有生命形式具有亲缘关系的理论与休谟视同情与仁爱作为基础的道德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就是一种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伦理整体主义;这种伦理整体主义“维护生物共同体的统一、稳定与美”(Callicott 2008, 154)。从大地伦理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的德行不仅要求培养同情和关怀的性情,也要求一种关于生物共同体的整体主义观点。获得这些品格对于现代主流哲学来说可能尤其困难,因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子主义与个人主义统治了西方的意识与文化。
深层生态学也倡导培养对于生物圈的同情与关怀。根据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看法,
伴随人类的成熟,人类将因为其他生命形式体验到快乐而感到快乐,因为其他生命形式承受痛苦而感到痛苦。我们不仅因为我们的兄弟或一只狗、一只猫的悲伤而感到悲伤,我们也因为有生命的存在物以及景观遭到毁坏而感到悲痛。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已经拥有无数可以使我们为所欲为的破坏工具,但我们的情感远远谈不上成熟。到目前为止,激发大多数人的情感还局限于非常狭隘的范围。(Devall and Sessions 1985, 75)
深层生态学将我们同情、关怀自然的能力与自我观联系起来,而自我观与自然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对于深层生态学来说,我们鉴别、移情其他物种、自然对象以及整个生物共同体的能力标志着精神境界与道德成长(Devall and Sessions 1985)。深层生态学所理解的自我实现,就是自我与自然世界成为一体,自我被视为更大整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DesJardins 2006)。
最后,生态女性主义者凯琳·沃伦(Karen Warren)提倡我们用一种“爱的眼光”(loving eye)来看待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对于非人类自然世界“充满爱意的认知”,就是尝试理解关切非人类世界——一个被认为对人类而言不相干的、不一样的,甚至无关紧要的世界——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即便人类也是某个生态共同体的成员,他们与岩石仍然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与岩石、或者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对于自我“充满爱意的认知”如果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基础,则这个道德共同体是承认与尊重差异,无论同时存在什么样的“同一性”。(Warren 2008, 40)
沃伦强调关怀、恰当的信任、亲缘、友情在我们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价值。因此,她的环境哲学与上文所述的哲学一样,都从激励环境良善的意义上积极倡导爱、同情、关怀自然的美德。
环境良善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对于简朴生活方式的积极评价。在美国或中国这样崇尚工业和技术的国家,“进步”与否通常以无视生态可持续性的经济扩展来衡量。砍伐森林可以种植农作物以获得食物与生物燃料,可以为家畜开辟牧场,还可以生产木材或其他消费品。海洋渔业由于需要供给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面临枯竭,无数湿地由于新建住宅小区与购物商场而不复存在。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刺激经济增长与盈利;庞大的广告业蓄意创造对于商品、包括那些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商品的欲望。因而并不意外的是,环境良善要求简朴的美德,谴责以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为荣的好生活观念。
在提倡简朴美德方面,深层生态学运动可能是最不遗余力的。深层生态学的纲领包括下述原则:
[深层生态学倡导的]思想观念变迁主要是,注重生活质量(富有内在价值的状态)而不是执迷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将庞大(big)与伟大(great)区别开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觉醒。
为了阐明深层生态学提倡的生活方式,奈斯列举了一些与简朴有关的态度与取向(为了语言表达上的一致性改述如下):
1.以简单的手段……实现目标或目的。
2.反对消费主义,个人财产减少到最低限度。
3.努力使生活变得富有内在价值,行动起来而不是碌碌无为;
4.关心第三、第四世界的处境,尽力避免物质生活水平与贫困者相比反差过大与过高(生活方式的全球一致化);
5.赞赏、并且尽可能地选择有意义的工作,而不仅仅是谋生;
6.赞赏或者参与第一产业——小规模的农业、林业、渔业;
7.努力满足基本需要而不是欲望。抵制“购物”作为消遣或治疗的冲动。减少数目繁多的占有物,偏爱陈旧、磨损、但实质上保存完好的物品。(Naess 1995)
简朴的必要性在于,如果我们只要基本需要的满足,放弃物质层面对于舒适与财富的过度追求,那么,就能够使我们的生活重心回归“自我实现”的现实努力上来,并在整个过程中显著地减少环境破坏(Gambrel and Cafaro 2010)。
最后,环境良善还要求两种认知美德(cognitive virtues):整体性思维(holistic thinking)与非等级化思维(non-hierarchical thinking)。环境哲学的主要流派不仅强调生物中心论的平等,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同时强调谦逊的态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接受我们在相互关联的生物共同体中作为“普通成员与公民”的位置。因此,环境良善要求有美德的人从整体上思考环境。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与女性主义无一例外地将他们的环境伦理建基于生态科学,因为他们强调生物共同体作为整体的内部关系,而不是共同体个体成员的善。科利考特写道:
本体论上的对象第一与关系第二,作为西方古典科学的典型特征,事实上已经在生态学中被反转过来。生态关系决定有机体的本质,而不是相反。(Callicott 2008, 180)
由于这种生态学的取向,环境良善反对个体主义,因为它以诸如感觉、理性、意识、自主或拥有利益之类的心理能力为标准,使道德考量的对象局限于个体。由于诸如濒危物种、生态系统与整个生物圈之类的整体不存在心理体验,因而不能在个体主义视角下被纳入道德考量(Callicott 2008)。在克里考特看来,大地伦理“不断强调的是环境作为整体的统一性、稳定性与美,而不是植物和动物个体对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生物权利”(Callicott 2008, 180)。
第二种认知美德——非等级化思维——要求有美德的人反对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谓的统治逻辑。当然,沃伦也承认等级化思维的某些形式不是道德上应予反对的,因为他们并不导致统治(Warren 2008)。正如沃伦所解释的,统治的逻辑必然是等级化的,呈现出相互对立的价值分离。价值分离的一端被赋予更大的价值,然后这种优越性被用于表明统治劣势者的合理性。例如,心灵与身体构成了对立的两端。男人与心灵联系在一起,女人则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由于心灵被赋予比身体更高的价值,从而男人统治女人就变得理所当然。从历史上看,心灵、理性与男性三者一致被赋予比身体、情感与女性更高的价值。由于自然被明确界定为女性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推断,统治自然与统治妇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Warren 2008)。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基于同样的视角认为,基于阶级、种族、年龄与性别的各种社会等级是自然被破坏的根源(Bookchin 1982, 1990)。因此,有美德的人应当消除等级化思维方式,控制那种统治他人、控制自然的攻击性冲动。环境良善要求一种稳定的自我意识,内心深处崇尚协作、平等与互助。
综上所述,环境良善包括以下美德:
1.尊重自然。
2.不伤害、不干涉、忠诚与补偿的美德。
3.谦逊。
4.关怀、同情与热爱自然的美德。
5.简朴。
6.整体性、非等级化思维的理智美德。
三、环境美德面临的挑战
前文关于诸环境美德的描述表明,这些具有广泛例证的美德将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⑩不过,尽管培养环境美德的努力值得称赞,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面临着严重的障碍。我的评判主要指向美国人:他们约占世界人口的5%,却消耗着全世界约30%的不可再生能源与矿物资源,排放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超过20%(DesJardins 2006)。由于品性的普遍改变面对这些严重障碍,而有效应对环境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因而,直接诉诸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利益以激励负责任的环境行为,至少短期看来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情形。
环境良善的第一个障碍是物质主义的好生活观念。对于任何像美国或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来说,人们普遍向往的幸福景象就是占有和消费商品,从而获得快乐、物质享受与消遣(Leach 1993)。要使这种景象成为现实,需要金钱;金钱因此在任何消费者导向的文化中都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资本主义为了追逐利润,必然通过广告造就和鼓动人们对于商品与服务的欲望。广告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无处不在。广告充斥于电视、广播、广告牌、报纸、邮件、电话、因特网等,将我们淹没。其目标不仅是制造对于这些商品的欲望,而且消解理性对于欲望的节制,鼓励当下的满足。在广告的侵蚀下,行为人对于物质享受的贪欲得不到理性的控制,这对于环境良善、尤其是简朴美德来说是一个巨大障碍。
此外,美国人鼓吹资本主义是唯一能够使我们的物质主义好生活景象持续下去的经济体系。我们当然支持政府对资本主义的冷漠无情有所作为,但我们更是时时担忧任何干预会减缓经济增长,不能满足我们对于消费品的贪欲。莫里斯·伯曼(Morris Berman)将我们的共同文化描述为我们在其中游泳的水: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普遍的消费主义是“水”。它像覆盖所有东西的“皮肤”那样发挥作用,像一件无所不包的披风——造成整个氛围……这是我们的精神风貌,我们的文明精髓。我们视野所及之地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的毒素……(Berman 2000, 52-53)
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为了环境而采取行动,也不愿意支持那些威胁到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政策。深层生态学的倡导者呼吁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回归简朴,重视生活质量而不是执迷于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这与不容质疑的资本主义逻辑恰恰是相反的。美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一家无党派人士组建的独立民调机构——译者注)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18~25岁的美国人中约有80%把获得财富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Irvine 2007)。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人正游弋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水域,他们在经济进步的名义下甚至习惯于允许、容忍或漠视普遍存在的对于个人的伤害——更不用提环境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除非他们相信改变物质主义态度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否则我们不大可能看到他们为环境的缘故而有所改变。
即便德性伦理学家能够说服美国人去相信非人类生命、物种、生态系统与其他自然对象具有内在价值,应当纳入道德考量和受到尊重,这种信念在人类与环境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之时也是经不起考验的。消费主义背后所隐藏的价值序列是经济价值优先于所有其他价值。消费者信心需要以强大的经济为支撑,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则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正是这种利润优先的思维使环境美德所要求的尊重自然变得不可能,更不用说培养人们热爱自然的美德了。
培养环境美德的第二个障碍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拥护个人主义,鼓励理性的利己主义逻辑。有环境美德的人必须摈弃个人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以更加谦逊、更具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然而,个人主义的泛滥已经使所有国民热衷于个人权利而忽略公共利益,进而造就了一个爱打官司的社会。因此,灌输整体主义自然观,即便是使人们相信我们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相互关联与相互平等,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美国人尚且不能保持合理、和谐的人际关系,更不用说与自然保持整体主义的联系了。
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以多种方式造成人际关系的碎片化。例如,取得经济上的成就通常要求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这就会导致破裂的关系。希拉里·利普斯(Hilary Lipps)的描述是很多商界成功女性的真实写照:“为了获得成功,他们放弃了他们的社交生活、兴趣与娱乐,并且很少有时间与家人和朋友相处。”(Lipps 1999, 108)兰诺拉·威兹曼(Lenore Weitzman)预测美国人的结婚率还会有大幅下降。我们的文化“不赞成经营伴侣关系”,因为“经营个人生活与职业在现代社会有更好的回报”(Weitzman 1999, 239)。正是这种工具理性把个人成就与自我表现放在优先位置,把我们所渴求的与他人之关系、与自然之关系都抛于脑后。
进一步说,注重个人成就、并以此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尺,滋养了自视甚高的观念,背离了谦逊的美德。美国文化迷恋名利、崇拜明星,把恶名远扬也当成一种成就。“看我的(look at me)”这种自我中心、迫不及待的心态——展现于电视与通俗小报、运动与娱乐——严重地阻碍了谦逊美德的培养。
环境良善的第三个障碍是许多美国人缺乏对于自然的审美意识。环境良善要求对自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与爱;培养这种欣赏与爱往往需要长时间地置身于美丽的、至少是怡人的自然场景中。这对于热爱与关怀自然的态度来说虽然是必要前提,但显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很容易想到,农民或伐木工人即便大部分时间从事户外工作、置身于美丽的自然环境之中,仍然会把他们的土地视为获取利润的自然资源。但无论如何,置身于自然美景仍然是一个必备条件。托马斯·希尔认为,不能以欣赏的眼光对待无知觉的自然表明了一种审美感的缺乏:
当我们看到露天开矿把山坡变得千疮百孔、花园被铺满沥青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多么丑陋啊!”这样的场景侵袭了我们的审美情感。我相信,任何具有敏锐审美意识的人都会留下一声叹息……更多的时候,美是被丑陋所取代的。(Hill 2005, 56)
希尔的观点是,如果你欣赏自然的美,你就会保护和照料它。以通常的审美体验视角来看,这种观点尤为中肯。根据审美态度理论,美的体验是“无利害的”,因为我们对体验对象的欣赏并不涉及我们个人的实际利益。农民与其他依靠土地谋生的人往往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待土地,显然不可能欣赏它的美(Stecker 2005)。
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成长于或居住在城区或者杂乱延展的城郊,这些地方往往没有什么美感,甚至是相当丑陋的。这不是说,这样的地方没有自然风景区,而是说,这些地方通常很难给人带来审美上的愉悦。例如,佛罗里达州南部密集的房地产开发,造就了看起来千篇一律的房子,也使一览无遗的荒野所剩无几。商业化的林荫大道也基本雷同,两边通常是成排的商场、连锁店和百货商店。这种令人乏味的雷同让人厌倦周围的环境,想要逃避。高速公路与主要街道因为太多的车辆而拥挤不堪,使得人们变得烦躁、易怒和焦虑。美国城市的许多街区与街道到处是垃圾,给人留下衰落与脏乱的印象。整体上说,拥堵与过度开发的体验常常造成压迫感,也会让人有一种患有幽闭恐怖症的感觉。毫无疑问,美国那些杂乱不堪的城郊不是一种能够激发自然审美意识的环境。因此,热爱与同情自然的美德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很难得以培养。
对此的一种反对意见是,包括城区居民在内的许多美国人能够享受各种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休闲活动。骑车、航海、游艇、开雪地车、打猎、钓鱼、滑雪、观鸟、园艺、打高尔夫以及驾驶全地形车等活动,使美国人的无数时光在自然中度过,因而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培养一种关怀自然的态度。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即便这些活动在自然中进行,从而为参与者增强对于自然的审美意识提供了可能,这些活动大多损毁自然,因而是与环境良善背道而驰的。打猎与钓鱼显然违背了泰勒的忠诚原则,因为这是采取欺骗手段杀害动物——因此它们有悖于忠诚的美德。一些垂钓者可能会不同意,因为他们钓到鱼后会将它们放生。但即便如此,鱼无疑是被欺骗而吞食鱼饵的。同时,在这种情形下,鱼被钩住时会承受某种程度的痛苦,放生后也经常会死去。因此,钓鱼活动显然并不表现对鱼的关怀,因而有悖于关怀美德。不可否认,以休闲为目的的垂钓者经常呼吁保护渔场,也倡导鱼的物种多样性,比如保护大西洋大马哈鱼。但是,他们的动机不是源于对于鱼的内在价值的认可,也不是基于对鱼的爱,而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利益——捕捉到鱼时的兴奋感。因此,这是把动物用于实现实用目的,不仅不利于形成对于自然的审美意识,而且损害了谦逊的美德。
另一些活动,比如乘游艇、开雪地车和驾驶全地形车,毫无疑问会产生温室气体,污染环境。这些活动还制造噪音,侵扰和损害动植物的生长。滑雪场地在层峦叠嶂中开路造桥,为了造雪而消耗了水资源。高尔夫球场表明自然环境如何被改造成高度整饬的人工环境:为了保持草地的繁茂与翠绿而无节制地使用水和肥料。当大批的观鸟者追寻罕见鸟类而侵入某个自然区域时,甚至观鸟也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尽管远足、野营、划艇以及园艺这样的活动确实有助于环境良善的培养,但许多流行的休闲活动都是对环境有害的,并且建基于一种自然被用作游乐场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
培养环境良善的第四个障碍是与统治逻辑相关联的社会等级制的盛行。环境良善要求消除等级化思维,因为这种思维与统治自然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如前所述,生态女性主义者宣称,对于妇女——以及对于少数民族与穷人——的统治与歧视直接关联于自然的破坏活动。因而,他们应对环境危机的策略涉及到两性之间公正平等之关系的构建。尊重妇女的态度将会唤起尊重自然的态度。不过,仍然有很多迹象表明美国文化尚未消除妇女的屈从状态。
例如,以下五个迹象表明性别等级制仍然存在于美国。首先,2005年妇女的收入是男性的81%。相比于2001年的76%,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Selvin 2007)。然而,这表明男女之间的工作价值是不一样的。职业中的性别隔离仍然存在,女性从事的职业,例如护理、社会工作、基础教育以及办公室文秘工作,获得的名望与物质回报相对较低(Kaufman 1999)。此外,美国妇女所从事的最主要职业仍然是家庭主妇,因而在经济上依赖男性。第二个迹象是猖獗的色情业(高达几十亿美元的产业)把妇女作为性暴力的对象,从而妇女在性关系中处于屈从的地位。第三,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在我们文化中仍然是明显不平等的。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方式、给他们提供的衣服和玩具,以及与他们一起参与的活动,总是传递着女孩被动依赖、男孩主动独立的信息(Renzetti and Curran 1995)。第四,女性供养的有子女家庭中,44.5%处于贫穷状态。贫困的女性化表明了妇女处于不平等的社会地位(Kourany, Sterba, and Tong 1999)。显然,这一定程度上是因妇女与孩子在离婚后生活水准下降30%,而男性则提高42%(Kourany, Sterba, and Tong 1999)。最后,妇女通常不能在西方宗教中占据重要的领导位置,表明女性被认为在灵性上不如男性。
环境主义者经常指出,我们高于自然、损毁自然的态度很大程度是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例如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因而能够统治地球的观念。即便我们从其积极意义上将统治解释为托管,这种关系仍然包含着凌驾于自然的姿态。如果性别歧视与统治自然之间确实如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的那样存在着关联,那么,并不令人奇怪的是,西方宗教不仅增强了男性优越于女性的态度,也增强了人类凌驾于自然的态度。由于美国文化坚持这些以宗教为基础的对待女性与自然的态度,环境良善就很难茁壮成长起来。
另一些形式的等级化思维,例如种族主义和阶层歧视,与性别歧视一样顽固,并且在我们这种资本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文化中看不到消除的可能。统计数据表明美国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令人震惊。例如,美国CEO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350 到400倍(Rothkopf 2008)。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经济上的分配不均比率最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处于顶端的20%人群的收入是底端20%人群的11倍,而日本是4.3%。此外,这个国家80%的财富掌握在10%的富人手里(Boyer 2003)。这样的趋势不可能在近期被扭转过来,因为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显见冲动就是降低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的成本,从而使公司的利润最大化。
资本主义还以另一种方式鼓励等级化思维。为了产生最大化的利润和实现物质上的成功,我们的文化鼓励进攻、竞争与独立。竞争的本质在于产生赢家和输家——其目标是控制对手,获得相对于他人的竞争性优势。资本主义文化所培养的进攻性与竞争性取向是发展环境良善难以逾越的障碍。
四、结论
总而言之,我们这样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对于培养基本的环境美德构成了严重障碍,对于其他的诸多美德也是严重威胁(Fairbanks 2007)。然而,我们的结论不应该是这些困难无法克服,抑或我们应该放弃倡导环境美德的事业。伴随价值观转型的宏大“世界观变迁”,如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变迁,再如日心说成为普遍共识,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我们没理由断言一种普惠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世界观变迁不可能发生。尽管前面提到的变迁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但我们今天认识到了变迁的紧迫性,也拥有完全即时的通讯技术,因而,一旦必要性充分显现出来,有助于环境美德的态度变化可能很快出现。1998年的欧洲酷热造成几万人死亡,澳大利亚和美洲西南部的持续干旱,诸如此类的环境危机呈现在当代人面前的紧迫感(因为这涉及到生存,而不是兴盛),相比于15世纪的学者重新解释希腊和罗马学说的热望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对于培养环境美德所面对的重重困难,本文虽然不可能提出详尽的解决方案,但指出一些有效、可行的举措还是可能的。
首先,保持环境优良必须成为国家经济与政治议程中更加重要的核心问题。应当尽可能运用每一种手段使公众获悉我们所面对的危险:全球变暖,人口过剩,淡水、石油和煤炭等稀有资源的不断消耗,表层土壤的腐蚀,沙漠化和砍伐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对于唤起必要的紧迫感来说大有裨益。当美国人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汽油、支付更高的电费账单、经历更加频繁、更具破坏性的飓风、承受更多的森林火灾和干旱时,他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关心环境问题了。
其次,为保持和提升美国人培养环境美德的热情,另一种方法是尽可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绿色运动相关的社区活动,例如废物利用,提高家庭、学校、医院和公司利用能源的效率、营建社区花园、观鸟。任何共同践行的活动都会产生亲密感,从而推动人们更加关心实践活动所涉及到的人与非人类存在物。因此,如果摩托车爱好者热爱他们的车子、并且享受骑行俱乐部的活动,关注自然的活动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第三,进一步完善对孩子的环境教育,从家庭开始并延续到公共教育各个层次。无论何种教育都将“可持续”的相关内容列为必修课程,是一个有远见的主张。父母与学校应当帮助孩子参与户外活动,使他们享受自然的美与奇观,例如参观地方公园和国家公园、野营、游泳、冲浪、划船、园艺活动、观鸟。为此目的,社区应当加大投入,保护自然景观、兴建新公园和休闲小道、以及公共风景区。这不仅增加户外活动的机会,而且使更多的公民能够从自然场景中获得审美愉悦,从而增强对于自然的欣赏能力。同时,应当培养孩子对他人、对自然的同情。为此,限制他们观看暴力场景是有帮助的,因为暴力把残忍当成荣耀,使人漠视其他生命遭受的痛苦。此外,养宠物或者去当地动物庇护所做义工,能够培养孩子对动物的尊重与爱。如果这种教育在更早的年龄段开始,环境美德显然可能会得到更好地培养。
最后,我们需要以社会运动抗击消费者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的影响,确立利润和消费之外的意义源泉和生活目标。就此而言,当前经济不景气可能展现了一线希望,因为它使美国人反思他们的消费习惯,考虑一种更加节俭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美国人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已经不得不重新安排优先顺序,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发现把更多时间投入个人关系、教育、社区服务、健康与休闲能够获得更好的回报。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体验将敦促人们认识到有意义的生活是践行美德的生活,而人类社会内部、以及与自然的良好关系则是这种生活的构成要素。
所有上述实际举措将有助于环境美德的培养。当然,由于前文所提到的原因,拯救环境危机迫在眉睫,我们不能坐等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消费者国家发生一场道德革命。现在就需要做的是强化环保活动和政策,以减缓环境破坏。如果像我们上文描述的那样,美国文化确实是环境美德生长的威胁,那么环保主义者需要诉诸人类的自我利益来弥补德性动机的不足。因此,对于环境激进主义者来说,在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的负面影响、忽视环境问题的高昂代价、子孙生活水平的降低等方面隐匿激进主张,也许是更为明智的做法。
(周治华译)
注释:
①本文原名“Environmental Goodnes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Culture”(环境良善与美国文化的挑战);作者同意将本文译为中文。考虑到中文阅读习惯,根据文章的内容,译文题目作了调整。——译者注
②在环境德性伦理学家洛克·凡·温斯维恩(Louke van Wensveen)看来,“所有关注生态的哲学、神学或伦理学著作无不以某种方式包含着德性语言”(2000,5)。
③对康德来说,我们善待动物的义务是对于人的间接义务,因为对待动物的仁慈和关切有可能促成指向人的仁慈和关切,对于动物的残忍有可能助长对人的残忍(Kant 1963)。
④根据斯旺顿(Swanton)的看法,幸福论包括两大论题:“(1)一个人至少拥有或践行核心美德,是其获得繁荣的必要条件;(2)一种特征典型地(部分地)构成(或者有助于)其拥有者的繁荣,是这种特征成为美德的必要条件”(2003,77)。
⑤斯旺顿也提供了一种多元主义的美德理论。她主张的原则是,“一种个性特征之所以被称为一种美德,是因为它作为意向,以卓越(或者足以称之为好的)的方式(通过尊重、欣赏、创造、爱、增进等做法)回应该美德所涉及的对象”(2003,93)。
⑥环境美德方面的专题文献,可参阅Van Wensveen 2000, Sandler 2007, Sandler and Cafaro 2005。
⑦这个论述与桑德勒列举的尊重的环境美德是一致的(Sandler 2007)。
⑧事实上,一些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似乎拥有正常程度的自我接纳。为了解释这些情形,希尔可能需要区分真正的自我接纳与单纯表面上的自我接纳。
⑨有好几位环境哲学家推许面对环境时的谦逊(如White 2008, Dobel 2008, Sandler 2007)。
⑩菲利普·卡法罗从亨利·戴维·梭罗、阿尔多·利奥波德、蕾切尔·卡逊的著作提炼并阐释了环境美德(Sandler and Cafaro 2005)。我关于环境良善的特征描述明显契合于他的阐释。卡法罗列举了环境美德的五个特征:(1)意愿将经济生活置于合宜位置——也就是说,将其视为获得舒适与体面的人类生活的支撑,而不是为了无止尽地寻求占有与消费;(2)信奉科学,同时认识到它的界限;(3)非人类中心主义;(4)欣赏荒野世界,并且支持荒野保护;(5)无论是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生命都是好的基本信念。
[1] Aristotle.NicomacheanEthics[M]. Terence Irwin,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2] Berman, Morris.TheTwilightofAmericanCulture[M]. New York: Norton, 2000.
[3] Bookchin, Murray.TheEcologyofFreedom[M]. Palo Alto, CA.: Cheshire Books, 1982.
[4] Bookchin, Murray.ThePhilosophyofSocialEcology[M].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0.
[5] Boyer, William.MythAmerica:Democracyvs.Capitalism[M]. New York: The Apex Press, 2003.
[6] Cafaro, Philip. Thoreau, Leopold, and Carson: Towards an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A].InEnvironmentalVirtueEthics[C]. Ronald Sandler and Philip Cafaro, eds. (pp. 31-44).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7] Callicott J Baird.TheConceptualFoundationsoftheLandEthic[A].InEnvironmentalEthics:ReadingsinTheoryandApplication(5thed.)[C]. Louis and Paul Pojman, eds. (pp. 173-85).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2008.
[8] Des Jardins, Joseph.EnvironmentalEthics:AnIntroductiontoEnvironmentalPhilosophy[M].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2006.
[9] Devall Bill, George Sessions.DeepEcology:LivingAsIfNatureMattered[M]. Salt Lake City, Utah: Peregrine Smith Books, 1985.
[10] Dobel, Patrick.TheJudeo-ChristianStewardshipAttitudetoNature[C].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5th ed.), Louisand Paul Pojman, eds. (pp. 28-33).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2008.
[11] Fairbanks, Sandra Jane. Can Virtue Flourish in American Culture?[J].ContemporaryPhilosophy, 2007, 27: 21-28.
[12] Gambrel Joshua, Philip Cafaro. The Virtue of Simplicity[J].JournalofAgriculturalandEnvironmentalEthics, 2010, 23: 85-108.
[13] Hill Jr Thomas.IdealsofHumanExcellenceandPreservingNaturalEnvironments[A].InEnvironmentalVirtueEthics[C]. Ronald Sandler and Philip Cafaro,eds. (pp. 50-56).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14] Hursthouse, Rosalind.OnVirtueEth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 Irvine, Martha.WealthisTopGoalforYouths[N]. The Miami Herald, January 23, 2007, Section C.
[16] Kant, Immanuel.LecturesonEthics[M]. trans. Louis Infie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17] Kaufman, Debora Renee.ProfessionalWomen:HowRealAretheRecentGains?[A].InFeministPhilosophies[C]. Janet A. Kourany, James P. Sterba, and Rosemarie Tong, eds. (pp. 189-202).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9.
[18] Kourany, Janet A, James P.SterbaandRosemarieTong.TheDomesticScene[A].InFeministPhilosophies[C]. Janet A. Kourany, James P. Sterba, and Rosemarie Tong, eds. (pp. 217-19).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9.
[19] Leach, William.LandofDesire:Merchants,Power,andtheRiseofaNewAmericanCulture[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20] Leopold, Aldo.ASandCountyAlmanacandSketchesfromHereandTher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21] Lipps, Hilary.WomenandPowerintheWorkplace[A].InGenderBasics[C]. Anne Minas, ed. (pp. 106-14).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22] Naess, Arne.DeepEcologyandLifestyle[A].InDeepEcologyforthe21stCentury[C]. George Sessions, ed. (pp. 259-61). Boston, MA: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95.
[23] Renzetti, Claire and Daniel Curran.GenderSocialization[A].InFeministPhilosophies[C]. Janet A. Kourany, James P. Sterba, and Rosemarie Tong, eds. (pp.4-25).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9.
[24] Rothkopf, David.Superclass:TheGlobalPowerEliteandtheWorldTheyAreMaking[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25] Sandler, Ronald.CharacterandEnvironment[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26] Selvin, Molly.WomenBringHomeMoreDough[N]. The Miami Herald, February 11, 2007, Section E.
[27] Stecker, Robert.AestheticsandthePhilosophyofArt[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28] Sterba, James.EnvironmentalJustice:ReconcilingAnthropocentricandNonanthropocentricEthics[A].InEnvironmentalEthics:ReadingsinTheoryandApplication(5thed.)[C]. Louis and Paul Pojman, eds. (pp. 252-64). Belmont, CA:Thomson Wadsworth, 2008.
[29] Swanton, Christine.VirtueEthics:APluralisticView[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 Taylor, Paul.BiocentricEgalitarianism[A].InEnvironmentalEthics:ReadingsinTheoryandApplication(5thed.)[C]. Louis and Paul Pojman, eds. (pp. 139-54).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31] Taylor, Paul.RespectforNatur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32] van Wensveen, Louke.DirtyVirtues:TheEmergenceofEcologicalVirtueEthics[M]. Amherst,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0.
[33] Warren, Karen J.ThePowerandthePromiseofEcologicalFeminism.InEnvironmentalEthics:ReadingsinTheoryandApplication(5thed.)[M]. Louis and Paul Pojman, eds. (pp. 33-48).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2008.
[34] Weitzman, Lenore J.TheDivorceLawRevolutionandtheTransformationofLegalMarriage[A].InFeministPhilosophies[C]. Janet A. Kourany, James P. Sterba, and Rosemarie Tong, eds. (pp. 230-40).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9.
[35] White, Lynn.TheHistoricalRootsofOurEcologicalCrisis[A].InEnvironmentalEthics:ReadingsinTheoryandApplication(5thed.)[M]. Louis and Paul Pojman, eds. (pp. 14-21).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