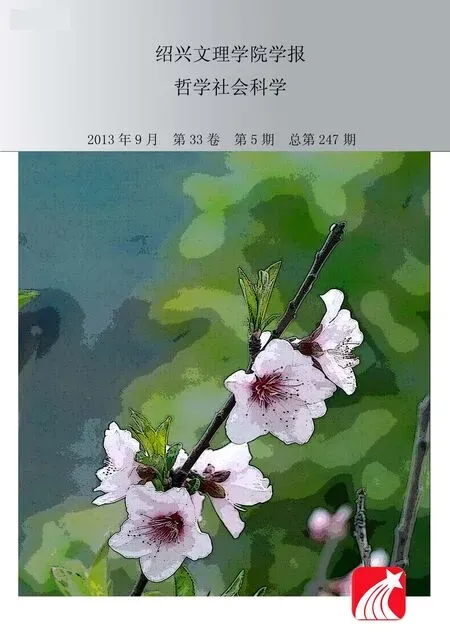地域文化背景与作家的文学个性差异
——吴越文化视域中的鲁迅与茅盾
鲁雪莉 王嘉良
(1.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2.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321004)
地域文化作为作家的生成背景与最初的文化接受源头,对作家文化人格、文化个性的养成产生或深或浅的作用。共同来自于浙江这片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从这里走出的新文学大家鲁迅和茅盾,便同生养他们的文化母体——两浙文化传统有着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于是就使他们在承续传统、领衔建构新文学辉煌“浙军”中有所作为[1]。但如所周知,鲁迅与茅盾的文化个性反差很大,他们的文化选择与文学关注点很不相同,对新文学做出的贡献也各自有异,因而笼统地说他们受两浙文化传统的影响还不能穷尽对作家个体的认知,他们的文化差异性似更值得深究。这当然可以做出多种向度的探究,笔者认为,若是从地域文化背景而造成的文化差异去看,则主要源于两浙文化圈内含吴文化与越文化两个范畴,由此产生不同的文化质地,而鲁迅与茅盾恰是这两个文化圈的典型代表,于是他们的文化个性就会呈现出很不相同的特质。
一
从区域文化视角考察作家个性气质、文化人格的生成,地理环境应是一个可以观照的角度。地理环境(包括山川、气候、物象)对于人格的养成,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近代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2]中曾从山川、地形、风情、民俗、语言等不同文化生态元素阐释南北文学之异同,对体认不同地域作家生就不同气质、禀赋乃至文化个性就颇有启迪。鲁迅亦有论述:“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我还能看出浙西人和浙东人的不同”[3]。鲁迅的这个判断,主要是从地域民性、风情、语言习惯等造就不同文化品性做出的,此说颇能区分“两浙”人的不同文化性格。
史上所说的“两浙”——浙东和浙西,为吴越文化不同的区域,两地地理环境迥异。浙东属越文化区域,域内群山环绕,“土性”特征显著;浙西杭嘉湖地区属吴文化区域,域内水网密布,“水性”特征明显。受此地理环境影响,这两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乃至人的秉性气质都会有很大的差异。一般而言,“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4]。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说到,因地域差异,影响到两地生活习性、民风民俗的不同:“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5]。20世纪初创刊的《浙江潮》刊载论“浙风”的文章也有如此论说:“浙西以文,浙东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泼,浙东之人多厚重”[6]。由是,浙东坚硬劲直之土性与浙西温婉秀美之水性差异鲜明,两相对照。此种不同地域的民风民性,便衍生出相异的文化人格。
浙东“尚古淳风,重节慨”[5],使文人也常带有几分刚硬之气。所谓“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7],以会稽为中心的古越历史上坚实厚重、勇武善战的人物比比皆是,大禹、勾践等是典型例证。鲁迅在其早期著述中曾作过如是描述:“于越古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现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8],从中不掩其对越地民风的激赏之情。
鲁迅的文化个性显出一种坚硬劲直的气质特征,就如其称道柔石具有“台州人的硬气”那样一种“硬气”的特质。由此,可以推衍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经典论断。这种人格力量来源于深厚的“土性”积淀,也来源于越地相沿成习的刚烈民风的承传。固然,“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已积淀在越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使鲁迅颇有“身为越人,未忘斯义”之感兴[9];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更多的是从诸如信念、理想、道德、伦理等思想文化层面接受传统影响,故而,浙东先贤提供的精神范式之于鲁迅显然具有更为直接的借鉴意义。越地历史造就的文化性格,在后来的晚近历史中得到明显的传承。两浙士人中刚勇节烈之士,浙东多于浙西,文化变革思潮的浓烈程度亦然。明清以降尤其是近代以来越中先贤血战前行、无畏叛逆的传统,素来为人所称道。王思任、刘宗周、黄宗羲、朱舜水,直至近代的秋瑾、徐锡麟,无疑是越地一方水土所孕育出的“硬气”人格形象。此种现象也多显现于“文人”知识者中。如鲁迅经常提到且极为尊敬的诸位越中文人,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的徐文长,日记中“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讫相骂”议论臧否、棱角分明的李慈铭等,无一不是刚直不阿之士。由对前贤精神的推崇,可以看出:鲁迅的“硬气”文化人格与“硬骨头”精神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对浙东人文精神和勇于对抗旧传统的叛逆性格的承传。置身于浙东近代以降浓厚而富于变革的人文环境,就思想发生学意义说,鲁迅关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主思想的发端,以及之后成为独标高格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无疑与接受越地人文传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与鲁迅的刚硬文化个性相比较,茅盾的文化性格,受到浙西儒雅风尚的浸淫,明显烙有浙西文人的印记。“浙西以文”的特点,造就此地“慕文儒,不忧冻馁”,“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10]的崇文传统,于是在“儒雅”风尚浸淫下,浙西独多“清流美士”,当然也不乏对我国的文化和文学做出重要建树的饱学之士与诗文大家,例如晚近文学史上名重一时的浙西词派便出于此地。
茅盾置身于崇文的文化氛围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走来,颇为顺畅,由此成就了他地道的“文人”知识者的角色。从现象上看,他当然并非传统浙西文人中的“清流美士”,恰恰相反,其人生经历中曾充满浓厚的革命色彩,政治参与意识也很强烈。但也正因来自于浙西杭嘉湖地区,其文化个性自不可能不受浙西水乡文化的浸淫。也正以此故,其性格上体现出诸多复杂性矛盾性恰恰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茅盾一生充满“矛盾”,其人及其构筑的文本世界“并不像有人说的是简而明的理性图式”,而是“各种矛盾冲突错综地交织在一起”[11]。综观其一生,他是以“文人”的独特方式参与政治,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国家与历史的担当意识,然而文人本色又使他对政治、对革命力不从心,而更多地表现出对文学的牵挂。这是由“革命家”的“沈雁冰”立即转化为“小说家”的“茅盾”的直接动因,由此也造成了他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其自名“茅盾”,实非一时之念,相当程度取决于茅盾的个性、气质与禀赋。“谨慎”是茅盾最鲜明的性格特征,他曾反复申述:他自小“秉承慈训”,以“谨言慎行”为处世准则[12],这集中反映在他于大革命失败后的角色转换上。“从牯岭到东京”、从职业革命家到职业文学家的转变,这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面和理智的估衡。他审度自己的性格、个性,深知自己并非“一个慷慨激昂之士”,“素来不善于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那一套志士气概”[13],适合担当的还是作家“文人”的角色。于是从革命战场上退下来后,他就把自己牢牢固定在文学岗位上,小说创作便成了他沟通文学与政治的有效手段,沉迷于小说虚幻世界的建构,宣泄自我心灵的痛苦和创伤,他获得了前此未曾有过的创作快感,同时也造就了他远比“革命家”更为出色的“文学家”的地位与价值。茅盾的这种谨慎、平和的姿态,并非只表现在革命形势剧变期,而是贯穿其一生行止中。他的“儒雅”风尚和并不激进的文学态度,显现着他为文不忘“救亡”的文人士大夫精神,但也不会扮演一个唱着革命高调的“极左”革命家的形象。左翼文学时期曾对激进的“革命文学家”的创作提出严厉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提倡“中间人物论”而获罪,便都是适例。茅盾为人热情而不激进,积极参与各种论争,但为文并不剑拔弩张,更没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心境平和的他即使面对大波大澜,也并未大喜大悲,只是默默地承受挫折,在“文革”中保持了“十年沉默”[14],并不如有些文化人那样乱了方寸。这一切,都同浙西文人的“儒雅”风尚较为接近,而“儒雅”风尚正构成作家间的谐调关系。茅盾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引领者之一而常赢得人们的敬重,追忆茅盾的《忆茅公》[15]一书,收录了与茅盾同时代的113位著名文化人对“一代文学宗师”表达的“高山仰止”的钦敬之情,留下了文坛的佳话。
二
论及地域文化对作家文学个性生成和文学选择的影响,自觉承传本地域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16]。探究鲁迅与茅盾的文化接受来源,就与本地的“人文因素”所构成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吸纳不同的地域传统内涵就会引向并不相同的文化选择途径。
基于一种自觉的传统接受意识,鲁迅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就表达了他重视承传地域文化的观念。在他笔下能够“匡救”国家的“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固有之血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积淀,也同样包含了两浙文化,尤其是浙东越文化的“血脉”。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越地文人知识精英的推崇上。古越之地,文化积淀深厚,绍兴城几乎是“十步之内,必有先贤遗迹”。这一直触动着鲁迅去发掘这份文化遗产。他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有所谓“十年沉默”时期 (1908—1918)。这一时期,对于鲁迅至关重要。他以自己的坚韧孤独地体验着黑暗,沉浸在抄古碑、辑古书,钻研魏晋玄学,甚至读佛经之中,而首先浮上他心头的是他对故土文化遗产的记忆,着力于对“越中先贤”文化遗产的发掘。在此期间,鲁迅共计收录整理越地古籍22部,包括《会稽记》《会稽典录》《会稽先贤传》《会稽后贤传记》《会稽先贤象赞》《会稽土地记》《会稽地志》等[17],举凡会稽的历史、人文、地理、故实,尽收其中。他对故土文化遗产作如此用力地开掘,并非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于张扬越地“先贤”的文化精神,“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18],即希望越地文化遗产、文学精神有惠于后人,历史积淀的乡贤精神能够世代相传。当然,探究鲁迅文化人格的成因与本地文化传统的关系,其对于越地“近传统”的承传,是尤为重要的。宋明以来越地叛逆封建道统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文化精神,曾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写下过辉煌的篇章,加以时间上的晚近,它对鲁迅更具亲和力和感召力是顺理成章的,由此也赋予鲁迅文化人格更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现代内涵。这可以在鲁迅与浙东“乡先贤”的精神交流中一一找到对应。鲁迅对起于越地的“浙东学派”的诸位先贤,始终敬仰有加,推崇备至,如将客死日本的明末“遗民”朱舜水引作楷模[19],竭力推崇拒不降清、绝食而亡的明末文学家王思任,将其“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之言铭记于心[20]。鲁迅在五四时期便张扬启蒙精神,创作中凸显出鲜明的启蒙主题,无疑同承续“乡先贤”的启蒙文化精神有着直接的关联。
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鲁迅和茅盾尽管都曾受到两浙文化传统的熏陶,但却情状有别。19世纪末期,已经成人的鲁迅对两浙人文传统的探索深至更远历史中“乡先贤”的文化遗产,文化思想中“固有之血脉”印迹更为浓厚;而晚于鲁迅15年出生的茅盾,在其童年与少年时代即受影响于20世纪初的文化大潮。显然,在吸收外来思潮方面,茅盾甚于其前辈作家。他对吴文化传统的承传也有着异于鲁迅的特色。
观照茅盾文化思想的形成,传统文化的承传与接受是一个重要侧面,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自小饱读诗书,对先秦诸子、《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等文史巨著烂熟于胸[12]114,表明其曾接受良好的儒学传统教育。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文化,其核心内容是经世致用,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对茅盾成年以后形成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产生潜在的影响。而就接受地域文化传统言,茅盾步入学校时进的已是“中西学堂”,既读“诗曰子云”,又学“声光化电”,接受的文化已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他本人也没有像鲁迅关注越文化那样对本地的吴文化有很多论述,却在接受本地颇为兴盛的维新文化思潮影响方面见出特色,“维新”文化遂成其文化思想中的第一道底色。茅盾的故乡乌镇地处交通要道,“镇虽一隅,实三郡六邑之屏藩也”,加以文人汇集,文化氛围浓厚,崇尚实业,号召富国强兵的维新运动必然会在这里引起热烈的回响;乌镇就曾聚集过一个青年维新文化群体,他们无心于举业,倾向新学,鼓吹维新,推崇“康梁倡导新政”[21],造成浓烈的维新文化氛围。茅盾于此受教,又有“维新派”父亲的督励,其受教的“第一课”便是维新文化思想教育,对其文化思想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中国20世纪文化同近代文化思潮有着密切联系,茅盾承续本地人文传统从浓烈的维新文化氛围中走出,并以此作为文化思想起点,实有无可漠视的意义。这也正是茅盾青年时期便显示了开放的文化视野,并敢于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上大胆求索的因由所在,并由此成就了茅盾日后成为革命文学家 (其革命色彩的浓重显然甚于鲁迅)。如果说,在新文学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鲁迅等前辈作家大抵有过探索启蒙思潮的浓厚兴趣,那么在“五四”救亡热潮中走向文学的茅盾,显然会选择偏重“救亡”的一面。关注现实、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强化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参与意识,使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学观念总是显示出紧随时代潮流的趋向。就此而言,茅盾此时的文化/文学选择便显现出与时代主潮的契合性,这并非其弱点,恰恰是一种优势,一个亮点。
三
作家的文化个性也与艺术趣味有关,不同的文化个性往往决定了相应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追求,折射出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更为深层的意味。“浙东以武”与“浙西以文”大致勾画出两地人文的不同品性,同时也蕴含着两地文人艺术追求与创作文风的不同。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将明末以降的两浙文风类型概括为“飘逸与深刻”:飘逸“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深刻“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辞的犀利”。虽然周作人并未明确说明其各自的源地,但从两浙作家的创作实践与审美倾向看,可以见出以清丽、幽玄见长的“飘逸”文风多出于浙西,以辛辣、犀利取胜的“深刻”文风多出于浙东,此种情形在现代作家中也有或隐或显的延续。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艺术思维显然刻有更多传统浙东文人的印记:文字犀利如“老吏断狱”,世事洞彻遂有文章的“深刻”。鲁迅的气质颇不同于“才子”型作家,或者说他对“才子”是颇不以为然的,从其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对“才子+流氓”型文人的反感即可看出。鲁迅的艺术思维以厚重与深刻见长,这种刚性的性格质素来自于浙东文化传统。他的文字的犀利 (或者说带有些“尖刻”)甚至甚于他的乡先贤徐文长、李莼客。由此,便形成他独特的审美偏好与艺术趣味。他不喜小巧玲珑,而偏好雄浑阔大,充分凸显在他对浙西风尚的看法中,鲜明显现出浙东人的脾性。譬如他对位处浙西的杭州、西湖并无好感,认为其格局太小,“总显得小家小气,气派不大”;而“西子”的湖光山色之美,“只会消磨人的志气”[22],这显然取决于他浙东人的“土性”思维。在艺术创作上,他亦抱如是观念。他钟情于格调粗犷的浙东绍剧与“目连戏”,对表现厉鬼精魂的剧作《女吊》情有独钟,极为激赏。与之相反的是,他颇为反感体现“吴地”风尚的文艺作品。如“五四”时期,他对鸳鸯蝴蝶派创作的抨击[23];30年代,他对“鸳鸯蝴蝶式文学”及“新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24]。在对“吴人”梅兰芳戏曲艺术的批评上,尽管有着较为复杂的因素,但依然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土性”审美趣味。他对梅兰芳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故作风雅,他反感于“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认为“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25]。鲁迅的审美眼光是独到的,在雅俗、柔刚、女性气质与男性质素之间,他以后者为选择。这种以深厚“土性”为底蕴的审美眼光,与鲁迅刚性质素的创作互为表里,共同造就了鲁迅式的刚烈、深刻文风,遂有其创作 (无论是小说或杂文)对旧世界以犀利的批判和强大的杀伤力。
与浙东文人之“土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浙西人之温婉秀美 (水性)。所谓“吴兴山水发秀,人文自江右而后,清流美士,余风遗韵相续”[26]之说者是。与此相应的是浙西文人“尚儒雅”的独特审美倾向与思维特质。晚近的鸳鸯蝴蝶派产生于吴文化区域 (主要在江苏、上海,也包括浙西的杭嘉湖地区)绝非偶然。由是,浙西文人的文风中显出更多“飘逸”的特质。
有意思的是,在新文学“浙军”这里也部分的印证了吴文化的“余风遗韵”。浙西文人的文风在这个地域的新文学作家那里有程度不同的传承与延伸。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证据是:以“水性”文化为底色的作家的文风大都趋于清秀、飘逸、婉丽,在创作风格上倾向于唯美和浪漫主义。最典型的如徐志摩、郁达夫、施蛰存、戴望舒等作家,以及以“情诗”创作闻名的诸位“湖畔诗人”。这些具有浓烈的“现代”质素的作家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清流美士”,但其人格气质中的飘逸儒雅,审美追求上的诗意灵动,显然都烙印上了浙西传统文化背景中的文人印痕。
与此形成独特个案的是茅盾。茅盾一生致力于“政治与文学”的双重纠葛。其浓烈的革命色彩使他迥异于其他浙西作家。然而,来自杭嘉湖地区的出身使他的创作中浸淫水乡文化的痕迹不可避免,这在他的创作中显而易见。如其在作品中温婉而细腻的文风,时代风云与社会变动大背景下对现实的敏于观察与细腻分析,在人物心理刻画上的细致入微,以及长于分析、思考、批判的创作风格。事实上,正是浙西的水性文化影响了他,使其“社会剖析小说”别具一格。这无疑印证了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之间无法忽视的紧密联系性。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茅盾的创作中关于女性世界的热衷表现以及女性心理的细致描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色,似乎也印证了其受水乡文化浸淫的特质。试看其创造大量的“时代女性”形象便可知端倪,从中显示的不仅是茅盾的细腻委婉品性,甚至还能看出其不乏多情、浪漫的一面。对此,美国学者夏志清曾有一段启示性的论述。夏志清以文学的“地理区分概念”比较了南北两地的代表作家茅盾与老舍的创作风格,“在许多方面,他们两人恰恰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茅盾用的是经过润饰的文学辞藻;老舍擅长纯粹的北京土话。借用历来对南北两地不同感受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老舍代表北方,重个人,直截了当,幽默;茅盾则代表较为女性的南方,浪漫、多情、忧郁。茅盾以其女性画廊而闻名;老舍的主角却几乎全是男子,尽可能避免浪漫的主题。”[27]可以说这段话非常精要地论述了茅盾创作与地域即江南水性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也说明了地域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积淀之于作家文化人格的渗透性与创作品格的影响性。革命作家的身份与具有“水性”文化性格作家的身份和谐地统一在茅盾身上,也许并非特例,却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1]王嘉良.两浙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9(4).
[2]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M]//劳舒,雪克.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62.
[3]鲁迅.致萧军、萧红(1935年3月13日)[M]//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7.
[4]蒋百里.《浙江潮》发刊词[J].浙江潮,1903(1).
[5]王士性.江南诸省·浙江[M]//广志绎: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匪石.浙风发刊词[J].浙江潮,1903(4).
[7]袁康.越绝书(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鲁迅.《越铎》出世辞[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
[9]鲁迅.致黄萍荪(1936年2月10日)[M]//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
[10]朱立乔,吴骞.嘉兴文杰[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
[11]朱德发.茅盾研究的思索[C]//吴福辉,李频.茅盾研究与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2.
[1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序[M]//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
[13]茅盾.从牯岭到东京[M]//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80.
[14]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57.
[15]忆茅公[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
[16]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2.
[17]鲁迅.古籍序跋集[M]//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158.
[18]鲁迅.古籍序跋集·《会稽郡故书襍集》序[M]//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
[19]鲁迅.华盖集·这回是“多数”的把戏[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5.
[20]鲁迅.且介亭杂文末集·女吊[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7.
[21]卢学溥.乌青镇志[M].民国25年(1936)刻本.
[22]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2.
[2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名字[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3.鲁迅.热风·“以震其艰深”[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3:407.
[24]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
[25]鲁迅: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09、610.
[26]浙江通史卷九十九·风俗上·湖州府[M].四库全书(文渊阁版).
[27]西方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场重要论争.尹慧珉,尹宣,译.[C]//李岫.茅盾研究在国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