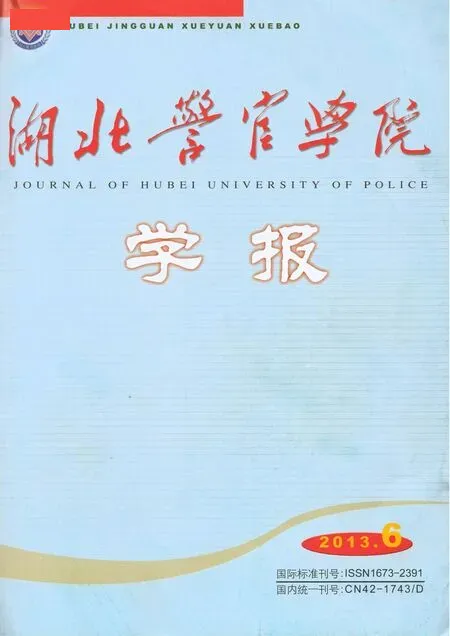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选择问题分析
吴 琼
(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河北 廊坊065000)
模式一词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即用它来说明某种结构系统和制度。立法模式取决于价值选择,有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立法模式。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价值目标在于,既保证行政效率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二者的平衡是影响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发展的两大因素,并制约着这一制度的发展方向。本文在介绍国外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后,对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进行了归纳,并指出选择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主要考量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模式重构,即确立行政本位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并改司法机关的审查模式为诉讼模式。
一、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简介
(一)比较视野下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
由于各国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归属不同,学者们通常将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分为三种模式:1.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2.申请司法机关强制执行。3.折衷模式。[1]笔者认为,上述类型划分现实意义不大,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既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的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的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不同的只是以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为主,还是以申请司法强制执行为主。所以,笔者赞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二分法:美英法模式和德日奥模式。[2]
1.美英法模式——以司法强制执行为原则,行政强制执行为例外
美英法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司法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并对行政权具有约束力。此种模式下,行政机关一般不得自行强制执行,出现行政机关自身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案件或情形,行政机关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通过严格的诉讼规则对其行政决定进行诉讼审查,行政义务就会以法律赋予的司法强制力得以实现。而当行政相对人一方不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行政义务时,行政机关只能提起民事诉讼,作为民事主体请求法院促使相对一方履行,相对一方如若不履行,法院将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金或拘禁;或者依据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对相对人科以刑罚制裁。[3]
作为司法强制执行的例外,即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的情形有以下四种:一是对妨害安全秩序行为的排除;二是对妨害卫生行为的排除;三是对外国人驱逐出境;四是对负有缴纳国税义务财产的查封与扣押。[4]
2.德日奥模式——以行政强制执行为原则,司法强制执行为例外
德日奥模式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德国行政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自力执行,无需由法律作出特别规定。德国1953年出台的《联邦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将此种模式法制化。该法在将大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况,当例外情况出现时,则由行政法院强制执行。如相对一方不履行行政处罚时,负责执行的行政机关有权向行政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审理后,若裁定命令代偿拘留,则由行政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相对人依法执行。再如,对于执行标的为不动产的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也由法院强制执行。[5]
(二)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界定
我国第一部专门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规范,即2011年颁布施行的《行政强制法》。该法是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主要法律依据,其中涉及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主要条款是第13条,第34条,第50条,第53条。根据对法条的理解以及以上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划分,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更倾向于“以行政强制执行为原则,司法强制执行为例外”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点:1.只有在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有强制执行权,否则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一点与德日奥模式不同,因为德日奥模式是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原则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不需要由法律特别规定。2.法律没有授权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非提起诉讼,而且法院的审查只停留在书面审查。这一点又不同于美英法模式下的诉讼程序。
二、选择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主要考量因素
笔者认为,任何法律制度的制定与施行既要立足国情又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选择,首先要考量的是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本身的性质。此外,还要从经济学的成本规律出发,做到保证行政效率与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动态平衡。
以往对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界定,往往把主体因素看作决定因素,进而忽略了该行为自身的特性,如内容、依据、目的等。[6]笔者认为,权利本身的性质不能等同于权利主体的性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应该是行政权。第一,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具有可执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事项,行政强制据以执行的内容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具体行政行为在先,强制执行在后。第二,依据权力分立理论,行政权是一种执行权,司法权是一种裁判权。根据我国《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是有权机关强制不履行行政决定的相对人履行义务的一种执行性行为。第三,从目的来看,贯彻落实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实现行政机关意图是行政强制执行的最终目的,具有行政性。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有效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关键取决于执行成本的大小。如果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的成本低于行政机关,法律就应该以法院执行为原则,反之亦然。纵观现状,我国各种资源相对短缺,尤其是物质资源与人才资源,这就要求在行政领域尽可能避免行政权的外部效应。由于社会新现象的不断衍生,行政领域日益拓宽,行政管理职能逐步扩张,扩大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条件已经形成。对于认为扩大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矛盾的观点,笔者认为,行政机关确实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但并不表示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从行政机关转移到司法机关,问题就解决了,关键是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运行环节进行严格的程序控制和司法监督。[7]
三、重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
通过上文论述,行政强制执行权是一种行政权,由行政机关自力执行的成本小于司法机关,因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应该回归行政本位。同时,可以借鉴美英法模式和德日奥模式的诉讼审查,监督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行为,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确立行政本位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
权力分离是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有效手段,在确立行政本位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时,权力分离理论同样适用。依此理论,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分属不同的行政机构、部门及人员。行政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分属的不同主体,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不能是隶属的关系,以保证权力运行的相对公正性。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时,应做到:1.依法进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2.确立必要性原则,行政机关认为确有必要时方能启动强制执行,而且间接强制执行优先于直接强制执行,同时兼顾比例原则;3.尊重和保障人权,行政强制执行要保证被执行人及其所赡养和抚养家属的最低生活保障;4.建立健全权利救济机制,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时,应赋予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救济措施。[8]
(二)改司法机关的审查模式为诉讼模式
依现行法律规范,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司法机关的审查形式是书面审查,即形式审查。此种审查没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难于发现行政机关的违法情节,审查的标准过于宽泛。审查不予执行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一是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是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是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此种“明显”程度的判断主观性强,起不到预期审查的目的。司法审查的立法意图是以司法权监督行政权,但是宽泛的审查标准加上书面审查形式,使此种审查效果有限,起不到制约和保障的作用。
诉讼是合法性审查,诉讼程序有严格的审查主体、审查对象、法定程序和标准等确定性规则,可以更严格地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避免使法院成为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机关而非审查机关。此处的诉讼审查应以合法性审查为限,排除合理性审查,若以司法思维裁断行政思维,难免导致判断错位,司法不公。根据一般诉讼规则,应赋予行政相对人辩论权,其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决定是否合法进行争论;同时,赋予行政机关上诉权,当行政机关对法院裁定不服时,可以通过上诉途径救济自己的权利。
[1]杨海坤,刘军.论行政强制执行[J].法学论坛,2000(3).
[2]马生安.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及程序设定[J].行政法学研究,1997(3).
[3]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J].中国法学,1998(3).
[4]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8.
[5]周明.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J].法学研究,2010(9).
[6]赵波.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模式选择[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1.
[7]杨海坤.大陆行政强制执行立法思路的优化选择[Z].1999年海峡两岸行政法学学术研讨会年会论文.
[8]石佑启.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及其缺陷[J].河北法学,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