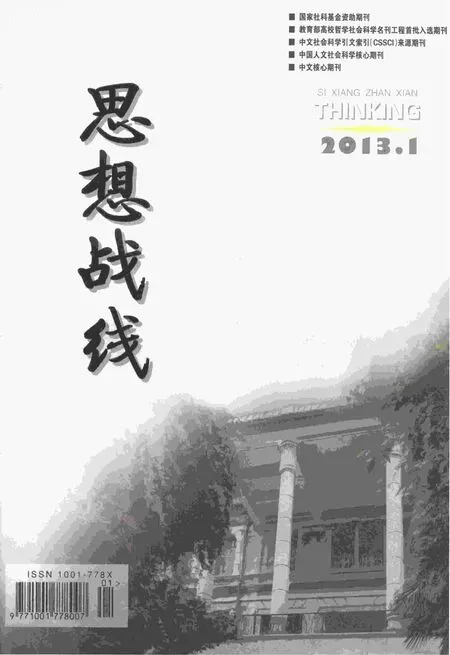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的相容性
张永刚
人们一般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不仅与现代主义形成了差异,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也形成了差异,相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来说,这种差异更为巨大。然而在差异的另一面,一定会具有同一与相容的新空间。同中有异,异中存同,这是事物发展与相互影响交融的基本规律,文化交往也不例外。马克思、恩格斯曾说:“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0页。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有差异的各民族文学必然在相互交流与影响中互补,从而克服了片面和局限,形成差异中具有共同性的世界文学。全球化时代文学、文化的交流互渗,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相异与相容的发生发展方式。因此,在思考后现代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相互关系之时,我们既要看到差异性带来的挤压与挑战,又要看到统一性带来的相容与机遇,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不断发展。
一、多元文化与主体新空间
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与“整体”的解构,个体的文化价值被放大,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也随之得到更多重视。从某一角度可以说,后现代是一个追求并尊重多元多样的时代,“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社会”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
所谓多元文化社会,就是一个社会中存在多种文化。在这里文化是一个关键词语。由于广义的“文化”具有无所不包的意义,因此什么是多样的文化看法颇多。在西方,现代人类学认为文化并无一个实质性的边界,言外之意是并不存在多样文化之说。但也有人认为,文化的边界清楚,它由社会的特定人群构成,他们所处的国家、族别、宗教、居住的区域 (甚至一个有界限的地理位置)等都是界定不同文化的有用因素,甚至就是不同文化的标志。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社会必然包含着多样文化。多元文化既然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客观现象,那么强调多元文化实质上是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应该尊重不同的文化,肯定不同人群、民族各自具有的文化权利。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他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②[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叶兴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用另一个理论家的话来说也就是:“多样化在文化上的表现通常被称为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可以定义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汇集于一个整体,承认这些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形式应该在国家统一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得到保留。”③[美]格雷戈里·克拉埃:《大众文化和世界文化:论“美国化”和文化保护主义政策》,新 蔚译,载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文化认同性的变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页,第53页。强调多元文化,不仅在于表明了一种事实,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一种观念,这是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共识。
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文化相对主义在肯定每一种文化的独立价值的时候,已经把多元文化的观念提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使之获得了更大的理论意义和阐释价值。多元文化观念和文化相对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它在文化意义上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促使多元文化主体意识觉醒,丰富了文化行为的主体世界。在封建帝制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它的意志也成为文化活动的意志,个人只能依附其上,这种文化活动往往成为单一主体的世界,除非出现文化反叛或文化失控,文化本身也将变得十分单一单调。在现代社会,由于现代性的影响,精英意识逐步获得话语霸权,精英主体操控了文化活动,慢慢又形成了另一种单一情形。后现代重视多元多样,打开了一统性的主体空间,使各种理论和观念有了言说可能,思想的活跃程度增强了。在文学创作领域,后现代带来了多样化写作。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界的众声喧哗局面就是一个例子,它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形成的活跃状态不同,20世纪80年代是各种“主义”盛行的时代,多样化文学选择的后面隐藏着现代性的共同理性,忧患意识支配下的宏大叙事作为基调,笼罩着那个时代的写作。因此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复活了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一统天下,“大我”仍然是文学的共同主体。20世纪90年代这个“大我”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小我”。正是这些“小我”丰富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主体世界。
其次,肯定了文化主体行为的个人化或个性化倾向。在宏大叙事背景下,创作主体被纳入时代的整体格局,个人的思想、情感,观察与表达的角度、话语方式,无不烙印上时代的特点,或者必须合于时代的规范才有意义也才会被接纳。这使作品往往会带上史诗般的宏伟内质,崇高、理想、道德等集体之思在作品中回荡,个人的感受不被顾及。即使爱情、生死也会按照时代格式展开,样板化的“革命现代京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它可以作为宏大叙事的极端代表。在主流化的政治意识规范下,文学主体的个性化追求受到严格排斥。当郭路生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写欢送知青远行下乡的诗里,抛弃了“大我”的感情的肯定性书写,而是深入并突出了个人的感受,一个弱小心灵的颤动这种悲情的“小我”情感。虽然使作品真切动人,但却被视为于时代无补而被否定。在这里,后现代这种观念显然已经改变,个人感受被放大,甚至成为支配写作的主要力量。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写道:“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①[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 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页。确实,转化已经发生,就像米歇尔·福柯所做那样,放弃宏大的街头反抗活动,将思考置入日常生活,去探究那些日常生活的种种规则是如何做出来的。“小我”的价值就这样体现出来了。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哪怕是“私人写作”,或者是更多有违公众道德理想的“下半身写作”,其实都显示某种生活化的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们突出了个人的存在。世界毕竟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它应该是多样共容多姿多彩的,统一意志如果过多取消了个体空间,单一的文化状态必然会使人们感到窒息。
置身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空间也更为开阔。无论云南、广西还是贵州的民族文学,在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各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随着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民族身份,民族认同、民族自尊、民族话语、民族特色等成为写作中的重要支持力量,民族写作的多样化方式得到更多理解与宽容对待。民族作家可以通过强化民族身份而受到重视,也可以因为隐去民族身份而得到认可;②如广西仫佬族作家鬼子认为民族身份对于写作并没有重要作用,因此他总是避开民族视觉来表现生活。书写民族历史题材的作品可以出版,表现城市现代生活的作品也有接受市场。少数民族文学真正以多样化写作姿态,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文化。
写作主体空间拓展所形成的积极影响还进入了理论视野,今天“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是民族文学研究的基本视点,③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检索30周年,由汤晓青主编了论文集,该论文集就以此为题,收集了研究不同少数民族文学的论文30篇。参见汤晓青《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是中国现当代的多民族文学这种观念也已经产生;在文学史书写中,也出现了应该补上长久缺席的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呼吁。可以说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多元文化观念,使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创作主体获得了大有作为的新空间。
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好这个空间。如果夸大了这个空间的作用,过分的相对观念必然又将带来新的自我封闭。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常规的意识形态架构,国家至上的现代国民理念,都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中占据着醒目的位置,提示着大家,只有在多元一体民族大家庭中才能拥有的个体存在;而从另一个角度着眼,中华一体生生不息的潜在活力,又是需要由长期共存的多元精神的缤纷呈现来充实和表达的”。①关纪新:《<边地梦寻>序》,载张直心《边地梦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即使在后现代背景下,民族作家所置身的新空间,也是带着这种特质的新空间。这对逐渐走向开放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文化资本与写作新动力
由于文化所存在的差别,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状况,这就是文化资本的基本含义。少数民族文化资本,也就是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为本民族带来相应社会地位的能力。
文化资本的价值根源,建立在不同民族的存在是社会客观事实之上。换句话说,不同的民族文化既然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它同时也就具有了文化的资本基础。民族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相互吸引相互促进发展的潜力,一种民族文化总能在另一种民族文化中获得启迪与进步的力量。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特别是异质文化的交融,往往会造就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奇迹。这证明了文化资本的巨大价值。当然,民族文化资本价值内涵的大小,与一个时代的民族的观念紧紧相连,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人们充分认识到多样共生、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重要性,不同民族文化得到更多重视,民族文化资本也迅速增值。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注意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价值变化的一种情形,这是一种饶有兴趣的变化:
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对汉民族统治传统的强烈自豪感,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民族权利的讨论则存在着一种极具讽刺性的扭曲。在历史上,随着中华帝国的扩大,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以把少数民族和他们的领土合并到中华民族。比如说,有时通过把中国文字引介到以前没有书面文字或者根本没有文字的地方,譬如被中国统治了几乎公元以来的第一个千年的越南就是一个例子。在别的范例中,中国借助文字和语言同时推进。在所有的情形中,他们试图建立帝国的官僚统治机构,汉族文化则被视为少数民族应该向往的典型。数个世纪的汉族人侵、汉文化意识形态的优越感和主要由孙中山在20世纪塑造的民族同种的神话已经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就像现代化那样遍及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只要可能,都企图冒充汉族以谋得优越的地位。但是,最近出现一个出乎预料的逆转:出现了汉人冒充少数民族的趋势。作为对没有分配足够的资源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的指责的积极回应,中国政府已经为那些提出要求的少数民族制定了经济支持和特别优待的政策,引导资金流向这些群体。结果,先前要求成为汉人或以某种方式融入汉文化的那些人,现在正凭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历史传统来重新确认他们自己是文化上的少数民族。②[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叶兴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
沃特森的概括虽然失之简单,但这种变化却一定程度存在,在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重视,经由了政治上的一统和文化上的逐步宽容这样一个过程,逐步实现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③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现在,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地享有某些政治上的礼遇和文化上的优惠。因此确有一些人如沃特森所说,先前已以某种方式融入汉文化,现在又要求重新确认他们自己是文化上的少数民族这种现象。
但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本的意义还更多体现在它的整体魅力上。在西南边疆,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生活情趣融会在他们居住的美丽的大自然中,形成了良好的旅游文化资源和学术研究资源。其中像《云南印象》、《印象·刘三姐》、《多彩贵州风》、《印象·丽江》、《丽水金沙》等,还入选《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名录》,这就是文化资本的一个体现。可以说,民族文化是一个活的资源,可以不断增值的资源,只要你保护得好,运作得好,它就能创造出巨大价值。现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省份都认识到了这一点,甚至把民族文化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这个背景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必然要获得新的写作动力。实际上,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就是得力于民族文化资本的力量。我们以佤族著名作家董秀英为例,可以说董秀英的成功,首先在于她是一个佤族的作家,民族身份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1981年她的第一个短篇《木鼓声声》在《滇池》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鼓励,因为作为佤族第一位书面文学作者,而且还是一位女性作者,她的出现意义丰富。当时著名作家彭荆风称这个短篇作品是“佤族文艺写作上敲响的第一声木鼓”。①彭荆风:《第一声木鼓》,《滇池》1981年第1期。另一位评论家则欣喜地喊出:“佤山,你听见了么,(董秀英)击响的木鼓声已经带着你的呼喊穿过了云海。”②何 真:《木鼓通灵》,《边疆文学》1998年第2期。可见,在作为作家的董秀英身上,显示出来的正是民族文化基本价值。后来有论者说,董秀英在其前期文学创作中之所以令人瞩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佤族女作家的身份而并非其创作实力。③朱 曦,章立明:《文本·文化·美——新时期云南人类学批评》,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6页。其次,董秀英的成功在于她对佤族生活的充分表现,她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生她养她的西盟佤族自治县,她着力表现的是自己的民族——佤族的生活与心灵。可以说,佤族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剽牛、拉木鼓、砍头祭谷的礼仪、司岗里传说、万物有灵的神话宗教习俗以及住竹楼、喝小红米酒、吃烂饭等生活方式,在她生动的书写中带上了更为迷人的边地民族生活色彩,成为人们了解佤族的最为直观而有效地方式。董秀英传达了民族文化的魅力,民族文化的价值也提升了董秀英的文学地位。可以说,董秀英正是以佤族文化吸引读者的优秀作家。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董秀英缺少艺术创意,实际上董秀英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民族艺术风格,其感觉方式、话语表达都极富特色,读来鲜活生猛,活力盎然,极具创意,这是其他作者无法模仿的,也正是董秀英成功的第三个原因。但我相信,即使这个属于作家主体能力范围的原因,在董秀英这里也是浸透了佤族这个民族的活的灵魂的,它仍然与佤族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文学传播与创作新环境
在后现代背景下,文学传播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它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环境,其中包含着诸多积极因素。
文学是依赖语言获得物化形态的艺术,语言需要载体,载体决定着文学的存在方式,也决定着文学的传播方式。在后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电脑、互联网的出现与逐步普及,改变着纸媒时代文学写作的单一方式,也带来了文学传播的变革。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不可拒绝的激动人心的变革。它拓展了作家的行为空间,更扩大了作品的影响范围。当我们抱怨文学的领地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发现作家的声名正在远播他域。正如著名诗人吉狄马加 (彝族)所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信息时代,因为有了电脑,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可以通向四面八方。因为传媒的作用,今天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可以说今天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区域,出现一个重要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当然他的前提必须是真正优秀的作家和真正优秀的作品,我想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世界各地大多数热爱文学的读者所知道。当前世界上的文学呈多元状态,各区域各民族的文学,都以其鲜明特色和文化贡献,被世人所关注”,其结果,“这些区域性文学和民族的文学,无疑是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丰富和加入”。④吉狄马加:《民族文学创作的自信心与使命感》,载杨红昆,欧之德《彝族哈尼族文学评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传播媒介正在以新的方式打开又一扇文学活动之门,把更广阔的世界推到那些敏锐的作家,也包含西南边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面前。
在今天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广播、电视、互联网络作为最主要的传媒方式,迅速覆盖了西南边疆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村落都有了它的踪影,其影响面日渐扩大,越来越深入,在此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民族文化生态和民族文学环境。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于2004年底至2005年初,在广西开展了“大众传媒跨文化传播及其影响调查研究”,对全区60个市县的11个少数民族进行了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广西各少数民族受众中,近40%的少数民族受众认为,近年来本民族在民间文艺,如诗画、建筑和歌舞乐戏等方面有很大或较大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广播电视或杂志关于中外文化艺术传播的影响”;50%的受众认为,近年来本民族受大众传播“时尚文化”的影响,在服饰和生活习俗方面发生很大或较大变化。仅以隆林各族自治县和东兴市统计看,就有94.3%的民族受众平时着装以“现代时尚装”或“汉民族服装”为主。其中41.1%的民族受众认为,这样着装的主要原因是“受传媒都市文化的影响”,认为“与他人或他民族交往具有认同感”,“现代时尚装或汉族服装新潮”等。①李 勤:《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据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课题组调研,目前,互联网与手机已经进入云南少数民族寻常家庭,并且年轻人已成为接触它们最频繁的群体,这样网络传播的信息自然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与交往方式。网络传播就可能给云南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塑造出一种与传统文化氛围不一样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亚文化。毕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一代人,而不是他们的父辈。②庄晓东等:《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6页。由此可见,广播、电视和网络传播,对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正在发生新的分解与重组、嬗变与转化。其复杂的情形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活动在这种新的传媒世界中,既面临着挑战,又充满了机遇。
纸媒传播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历来得到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在许多少数民族省份都有民族出版社,作为文学传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的文学期刊,也历来得到政府的提携。国家有《民族文学》,各少数民族省份都有以发表民族文学为主要侧重的刊物,如云南的《边疆文学》、广西的《广西文学》、贵州的《山花》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症候增强,中国文学中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少数民族文学传播方式和传播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裂变。出版社和刊物都被推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为迎合读者多样化口味,刊物和出版物的民族特色都被削弱了,民族作家的写作似乎失去了天然优势,发表与出版都面临困难。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刊物的变化最为典型的是贵州的《山花》,在改版的过程中,该刊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逐渐淡化乃至淡漠,③陈祖君:《汉语文学期刊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4页。这是十分突出的现象。由《山花》代表的这种状态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文学期刊和汉语文学出版社,包括民族出版社所构建的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空间确实发生了裂变,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明,后现代的传播空间并不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但是这仅只是现象的一面,如果说出版社和期刊走向市场是一种历史必然或时代趋势,那么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被挤压其实是促使其回归文学本体世界有效动力,它意味着民族作家创作主体规约的解缚,创作空间的扩展。新的传播方式把民族作家带到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这个世界所能依靠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主动追求,这并不是坏事,它促使创作主体必须发挥创造能力,去寻找创作的方法与传播的路径,而不是再去等待现成的安排。文学属于心灵,它需要更大的自由言说空间,当自我追求的程度加大,甚至成为现实,我们相信,在后现代冷漠的商业氛围中失去了更多关照与提携的少数民族文学,经过艰难的寻找,获得的将是更大的创造活力与更为宽广的世界。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活动本相,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前景所在。
总而言之,无论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是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后现代毕竟已经到来,后现代文化影响正在发生。在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利弊杂陈的文化景致充满了复杂的意义。单纯的拒斥与接纳、否定和肯定都是片面的。在这里我们需要更多的冷静与思辨,批判与选择,因为在几乎所有领域,后现代都是充满了矛盾的。正如阿兰·罗德威所评价的:“后期现代派是青春的,同时又是颓废的;它才华横溢,同时是邪恶的;它专注于分析,同时又具有浪漫色彩……这就是说,它是自相矛盾的。”④[英]阿兰·罗德威:《展望后期现代主义》,汤永宽译,《外国文艺》1981年第6期。在这样的文化面前,我想再次强调我们的基本态度,就是不要将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思潮,视为与中国较为落后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绝对相左的洪水,也不要视之为拯救的福音,而是要思辨其利弊,汲取其精华,这样才能为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及其理论在后现代潮流中追寻本土化、民族化积累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切实推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使之改变边缘弱势状态,实现合而不同、多元共通的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