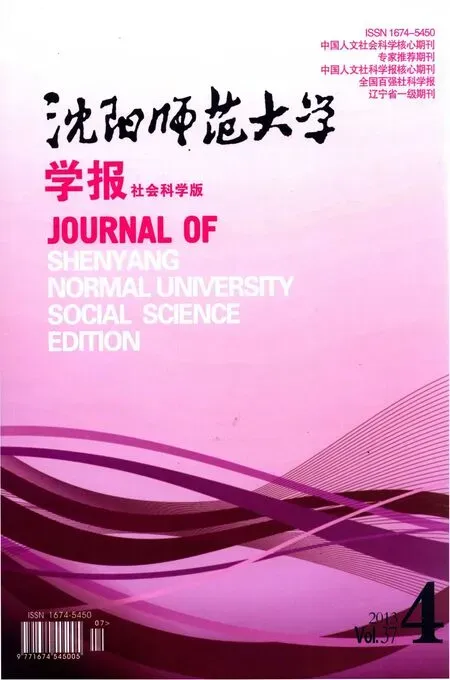《史记》价值评价体系与用人制度的关系
刘丽文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西方历史学家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认为,在历史学中有不可离弃的价值体系,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知识是由价值判断组成的[1]19。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价值体系是历史学家思想知识的凝聚和体现,它不仅直接决定选录人物的原则和评断标准,同时也对人物的塑造发挥一定作用。本文拟对《史记》的人物价值评价体系及其与西汉前期的用人制度关系进行一定探讨。
一、《史记》的价值评价体系及特点
司马迁是将“立德”作为士人最高的价值追求的。他认为儒家先圣孔子的价值原则和道德情操是“德”之至者,将并无什么事功的孔子列为“世家”,崇敬地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2]将孔子看成巍峨的、令人仰视而不可企及的高山,称孔子为“至圣”,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之情。除《孔子世家》外,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孔子,多次引用孔子的言论,认为孔子是值得万世景仰的道德榜样。此外,没有事功而被司马迁作为道德典范歌颂的还有伯夷。在《太史公自序》中歌颂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显然“奔义”“让国”是司马迁倾心的崇高道德之一。
司马迁同样认为“立功”是士人重要的价值选择。《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即他认为,士人应当抓住机遇,及时建功立业。但与他之后的史官文化不同,《史记》的“功”充溢着较为浓重的战国士文化色彩。
(一)“功”的内涵复杂多样,兼有非官方性和非正统性
所谓兼有非官方性和非正统性,就是说在价值取向上不完全以封建帝国的利益和为统治阶级认可的思想行为为标准。
考察司马迁对人物的价值取舍,一个很便当的方法是看他的《太史公自序》。该序阐说了立传的依据,不少议论都表现了他对人物的价值取向。现选录几条如下:
A类: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能信义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B类: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C类:
救人於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不流世俗,不争执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其中A类和B类,分别以正统主流文化认可的人品道德和政治功业为价值取向;而C类,则以与正统主流文化相悖的行为为价值取向。
C类中所说的游侠,是被汉代最高统治者严厉打击的对象,汉武帝曾明令诛杀之。但司马迁认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故而为其作传。商人是被统治者抑制的群体,但司马迁认为,他们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发财致富,是智慧的表现。更何况“商不出则三宝绝”(《史记·货殖列传》),商人的活动客观上流通了物资,应当予以肯定,因此为他们作传。《滑稽列传》的俳优,是正统士人所不齿者。司马迁说“: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得以半更。岂不伟哉!”(《史记·滑稽列传》)要之,也是从“功业”角度的评价,但显然已经突破了等级地位界限。这些都表现了价值取向的非官方性和非正统性。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3](《汉书·司马迁传》)这充分表明了两人所遵循价值标准的不同。班固不能容忍司马迁对专制国家秩序有破坏作用的游侠行为的推崇。他说:贵族游侠战国四公子导致了“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布衣游侠“……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汉书·游侠传》)班固不能容忍司马迁对不入品流的低级士人及操末业的商人的“业绩”的肯定。他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汉书·叙传》)要之,班固是以维护专制帝国秩序所需要的道德为主要标准。他认为“,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而“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汉书·游侠传》)即游侠破坏了固有等级,破坏了社会秩序,蔑视国家法令,擅行生杀之权,触犯了法律,是对大一统国家权威的挑战。商人呢,作为被统治者四民之一,应该安于其位,在物资生活上,遵从他所在等级的规范,因为“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这样,才会“上下序而民志定”(《汉书·货殖传》),封建等级制度才能保持稳定,封建君权才能够稳固。而通过经商致富是一种运用诈力利之举,更何况他们富厚之后,锦衣玉食,与王侯差不多,破坏了固有的等级关系,简直是伤风败俗!
司马迁则兼顾事功和道德两方面,其道德具有朴素的人民性,事功具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司马迁之所以歌颂游侠,是因为“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史记·游侠列传》)即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人们常陷于厄运而投诉无门,指望法律伸张正义吗?法律往往是统治阶级任意杀人的工具,治狱官常是专看皇帝脸色行事。如杜周办案原则是“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指责他为什么不按照法律办事,他理直气壮地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史记·酷吏列传》)哪有什么成法,皇帝认为对就是法律!而游侠急人之难,能在法律之外暗中私行公道,惩恶除奸,“故士穷窘而得委命”(《史记·游侠列传》),受害者告诉无门时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所以“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史记·游侠列传》)至于商人,司马迁肯定他们的治生谋利活动,认为普通老百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善于经营而致富,是一种智慧之举,值得肯定。因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史记·货殖列传》)追求物质利益,追求财富,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人只有吃饱了穿暖了才能去讲究礼节;那些王侯贵族尚且害怕贫困,何况小门小户的普通百姓呢!“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史记·货殖列传》)一些人既无什么高尚奇异的品行,又不去寻求谋生之道,长久地处于贫贱之中,却张口闭口地大谈仁义,是应引为耻辱的!
司马迁在价值评价体系方面与班固的不同表明,班固正统,以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为价值取舍;司马迁的人物评价体系则具有很强的非官方色彩。
总之,司马迁的功名观是没有名位限制和不拘一格的,涵盖的范围极广,可以说,他认为,这样生活都是有价值的:士为知己者死(如刺客);慷慨任侠,扶危济困(如游侠);忍辱复仇,弃小义,雪大耻(如伍子胥));依靠才智,经商致富(如货殖);隐遁避世,谦让奔义(如伯夷);以及“纳忠报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掣旗之功”;“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安书》)[3],等等,难以尽述。
(二)多种价值取向的交叉,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兼顾
在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司马迁往往是以一两种价值取向为主的多种价值取向的交叉,不因为某些人道德上的缺陷否定他功业上的成就。
以《酷吏列传》为例。酷吏执法严苛、残酷,司马迁很不喜欢他们。在《酷吏列传》的一开头,司马迁就说:“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也,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表现了对酷吏严刑苛法的批判。但司马迁同时还认为,酷吏虽酷,在历史上也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酷吏所打击的虽有被逼无路的贫苦人民,但主要还是骄横跋扈的贵族,图谋造反的割据势力,为非作歹的恶霸等。《太史公自序》说“: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由此可见,司马迁是以酷吏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为价值取向而为之立传的。如他说的酷吏宁成就“使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的“宗室豪杰人人惴恐”。酷吏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滑,二千石莫能治,于是景帝乃拜(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史记·酷吏列传》)即司马迁是把酷吏放到历史体系中考察而给予一定程度肯定的。但同时,对他们也作了道德评价,对他们过分杀戮的草菅人命行为十分愤慨。王温舒杀人“至血流十余里”,“会春,温舒顿足而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史记·酷吏列传》)。抨击看皇帝眼色行事的杜周:“善侯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史记·酷吏列传》)他歌颂公正廉明、克己奉公的酷吏郅都“敢直谏”,为人“公廉,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史记·酷吏列传》)也就是说,《酷吏列传》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二:历史作用和政治品格。在对酷吏的残酷嗜杀、执法严酷予以非贬的同时,指出了某些酷吏具有不畏权势、居官廉洁的好品质。
对游侠也是如此,司马迁既有从正统道德层面的衡量,认为游侠某些行为“不轨于正义”(《游侠列传》);也有从普适性道德角度的推崇:“其私义廉退让”,说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自己则“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牛”(《游侠列传》);而最终给予游侠历史地位的,是世俗的道德标准和世俗的事功“: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存亡死生”“,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锄强扶弱“,济王法之穷”和“去人心之憾”(李景星《史记评议》)[2]。
这种对历史人物多角度的评价,在吴起、商鞅、李斯、晁错、叔孙通、公孙弘等人身上也都十分明显。
价值取向的复杂与人物形象复杂的关系是:多种价值取向交叉,不仅使《史记》收录的历史人物不拘一格,没有等级地位的限制;同时也使人物的性格丰满、复杂。因为价值取向的复杂,说明了价值标准的复杂。价值标准的复杂,使作者有可能最大范围地采选所写历史人物性格的最有特色部分,它使人物富有血肉生气。而人的同一行动常常呈现出多种价值形态的交叉,道德系统的“善”与政治系统的“是”未必一致;历史系统的“进步”在道德上未必为人首肯。不同价值判断的矛盾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复杂矛盾,正是人物形象魅力之所在。这一点,前人在总结《史记》为何能把人物写得如此血肉丰满时多所忽略。
二、《史记》价值评价体系与用人制度的关系
人物的价值取向是作者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以往谈《史记》思想的非正统性,多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尤其是李陵之祸相联系。这当然不错。但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史记》价值评价体系与汉初至武帝时期的用人制度密切相关。因为用人制度直接关系到士人的利禄前途,对规范士人乃至全社会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战国时期,士没有固定的仕进程序或说制度。春秋乃世袭社会,春秋后期世袭社会逐渐解体,产生了不以血统而依才具德能论人的新型价值观“三不朽”之说。战国时期,“士”阶层正式诞生。当时七雄并立,天下纷争。结束多元政治,走向统一,几乎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而统一就意味着一国对其他各国的吞灭,因此人才成了面临生存竞争进而统一天下的七雄的要务,“得士者强,失士者亡”,“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4](《战国策·秦策》),“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5](《吕氏春秋·智能》),“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战国策·楚策》),士人地位空前提高。当此之时,士无定主,人格独立,各国君主对士无不尊崇之,或尊为师,或待为友,或委之政,或尊养之。士对君主,尽可批评讽刺,合则留,不合则去,君臣关系不十分固定,士人具有非常自由的选择空间。“士”有的以游说、干谒、推荐等多种方式进入政权机构,施展抱负;有的以轻富贵、傲王侯的高尚节操被舆论赞许;有的以慷慨任侠、舍身报恩、重义轻生的方式博得巨大名声;有的则注重理论探索,“处士横议”,在激烈的辩驳中创建安定天下的方略。当然,更有对富贵利禄的赤裸裸的追求,甚至是不择手段的纵横之士。总之,个性色彩浓重,价值实现方式不一。
从灭秦到汉代的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整个社会都没有一套完整的用人制度体系。曾经为秦王朝统一天下建树巨大功勋的士,进入这个大一统帝国后就与专制制度发生了严重冲突,以至于酿成了焚书坑儒的大案。秦代士人表现出了抗直刚正的气质品格,但也由此遭到了专制皇帝的血腥屠戮。原本在战国时代意气昂扬的士人及其价值观念受到了广泛的钳制,“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2](《史记·高祖本纪》)大批士人远遁避祸:“五经之儒,抱经隐匿;伏生之徒,窜藏山中。”[6](《论衡·佚文》)少数被接纳进政权机构的士人,也要小心翼翼,以避免随时都可能遭到的严刑峻法的裁制。因此,在陈胜揭竿而起时,天下之士云合雾集,纷纷响应。以至于“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3](《汉书·儒林传》)总之,秦文化政策投下的阴影及历史影响,在将秦始皇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同时,也警醒后来的统治者:士对一个政权是十分重要的。
在反秦活动中,一度中断了的战国时期精神自由、士人活跃的情况重又再现,当然此时文韬武略、拔城掣旗之士成为主体,与战国七强势均力敌之时士的活动方式有所变化。相当多的士人如项羽、张良、韩信、萧何、曹参、樊哙、随何、季布等都脱颖而出,借助时代提供的机遇,创立了名标青史的业绩。刘邦更是从一个小小亭长,成就了皇帝的伟业。
汉代从开国直到景帝的几十年,统治者尚未来得及制定一套规范的选士制度,朝廷重要官员一直主要是汉高祖时留下的功臣及其子孙。到汉武帝时“元功宿将略尽”[3](《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虽然其间皇帝曾下过求贤诏书,但毕竟未成制度。如刘邦在去世的前一年,其时海内初平,曾下求贤诏于天下,“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3]。(《汉书·高帝纪》)从诏书内容看,乃是一般的一次性的求贤诏,取士标准也不明确。惠帝、高后时推举孝悌力田,但有研究者认为“其意并不在选拔土人出来担任国家官吏,不过是以免除其徭役负担、给予赏赐的待遇,劝励民众循行、务本罢了”。[7]87文帝时曾下诏求贤,真诚希望才智之士为他拾遗补阙,但并不是常制,并且被征选来的有限的士人,往往只被派做侍卫近臣,并没有在政治上真正重用。如司马相如曾在景帝宫中为郎,后辞官游梁。即“察举制虽然在文帝时已经产生,但作为仕进制度主体的地位并没有确立,而且它本身也还不够完备。这主要反映在此途还不是仕进常制(如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之中,仅仅下过两次察举的诏令),以及所举之人基本未超出现任官吏的范围(如晁错原为秩八百石的太子家令)等方面”。[8]85也就是说,制度化的用人机制,在武帝之前尚未形成。
而西汉前期,诸侯王掌握藩国的政治经济和用人大权,“皆自治民聘贤”[3](《汉书·贾邹枚路传》)“,遍置私人”[3](《汉书·贾谊传》引《治安策》)。秉战国遗风,一些诸侯公卿大量养士。“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之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9](《盐铁论·晁错》)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汉书·梁孝王传》)寻求出路的士便纷纷投向这些王侯贵族。他们游走四方,选择与自己相合者,依附并服务于诸侯,为之奉献才智,诸侯则宠之以禄位,资之以财用。景帝时枚乘、司马相如、邹阳等都曾为梁孝王门客。当时的士,虽不似战国时期雄国并立共争天下时候地位那么“不可一世”,但具有自由的思想与行动空间,士与诸侯王之间是双向选择的,对于选定的诸侯王,士的来去也是自由的。主父偃曾先后游齐、燕、赵、中山等;枚乘、严忌、邹阳等都曾先仕吴王,后去吴至梁;司马相如在汉景帝宫中做郎官,感到诸侯藩国更具有吸引力,遂托病辞职做了梁孝王的门客;吴王刘濞谋反,枚乘上书劝谏,知名于时,景帝拜他为弘农都尉,他“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汉书·枚乘传》)在士与诸侯王的关系上,诸侯王往往都肯于礼贤下士,士成为他们的师友、宾客、臣僚后,则常常感恩知遇,对诸侯王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一秉忠心。如汉景帝之弟梁孝王,因求为太子不果,怒而使人暗杀从中阻挠的大臣,事情败露,邹阳为之奔走天下,寻找谋士,终于使其免遭罪责(《汉书·邹阳传》)。直到武帝时,王侯养士仍然存在,武帝前期时丞相田自行任命大量官员,武帝曾愤愤然地问他:“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总之,汉初至武帝之前没有形成固定的用人机制,整个社会也没有形成一个服务于大一统帝国的、强有力的主流价值评价体系。不能被中央政权有效吸纳的士人必然寻求其他出路,而汉初诸侯和公卿权贵恰好提供了填补的空间,从而形成了在某种程度上与战国“形似”的政治格局。大量寻求出路的士人可以仍然秉持战国遗风,游走各诸侯或公卿权贵之门;而一些诸侯权贵,或出于政治目的,或出于兴趣爱好,也往往能任用士人之所长,给予他们机遇,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诉求。所以,整个说来,西汉前期社会总体价值观念应该说是多元的,是较为个性化的,官方色彩较为淡薄的,即是向战国时期的不拘一格的价值观回归的。
汉武帝时代情况有了变化。随着削藩的成功,武帝将用人大权逐渐收回中央,并在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岁举孝廉一科从此开始成为选官常制。不过,以政治经济实力为准的任子、算赀的选官之法,仍占有相当比重。同时,制度的实行也需要一个过程。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就曾颁诏切责公卿大夫举荐不利,并钦命大臣讨论,最终形成“令二千石举孝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的“法律文件”。(《汉书·武帝纪》)这说明制定了几年的用人制度实行得很不利。而且,雄才大略、生气勃勃的年轻皇帝刘彻,同时还采用了多种方法招揽人才,不少士人是以战国时期一言以动天子的方式进入仕途的。史书对此记述颇多。《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书·东方朔传》说“: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汉书·梅福传》云“: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鬻者不可胜数。”由是,士之不拘一格被荐拔者甚多。主父偃早年游历于诸侯之间,不被所用“,客甚困”,后“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天子对他和同被召见者云“: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俱拜为郎中”(《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东方朔以滑稽多智得亲近;公孙弘以布衣为丞相。总之,如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的诏书所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汉书·武帝纪》)由此可见,武帝本人在常制之外荐拔人才时,也带有很浓的战国式的浪漫作风。
综上所述,汉武帝之前的大汉帝国自身尚且没有形成通过选士方式来引导、建构主流价值体系的自觉意识,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将士人纳入到以大一统封建帝国利益为核心的较为统一的价值标准。武帝即位几年后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统一,确立了儒学为士人晋身的主流思想,有了选官常制,但制度本身的完善及施行都需要一个过程;何况年轻的汉武帝本人也还没有完全摒却战国式的浪漫;更别说思想意识本来就具有惰性,业已形成的价值观是很难一朝消除的。因此汉武帝时期,一些被排除在正统主流文化之外的价值选项,在下层士人、民间甚至社会上层中仍然作为正面道德而受尊崇。如游侠,无论统治者如何打击终究未能消除其巨大的影响力,被汉武帝亲自处死的游侠郭解,生前大将军卫青曾亲自出面替他向汉武帝说情免迁茂陵;他后来举家迁徙时,“诸公”自愿为他出赞助费达“千余万”;“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2](《史记·游侠列传》)
也就是说,由于用人体制上的原因,西汉前期,战国时期蔚为壮观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价值取向不拘一格的士文化,中经秦王朝的短暂消歇,又曾一度重现(虽然它没有达到昔日那样的辉煌),直到汉武帝时代仍然挥洒着强劲的流风余韵。司马迁的价值评价体系,正是这种世风与其个人资质遭际结合的结果。
[1]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张双棣.吕氏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9]桓宽.盐铁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