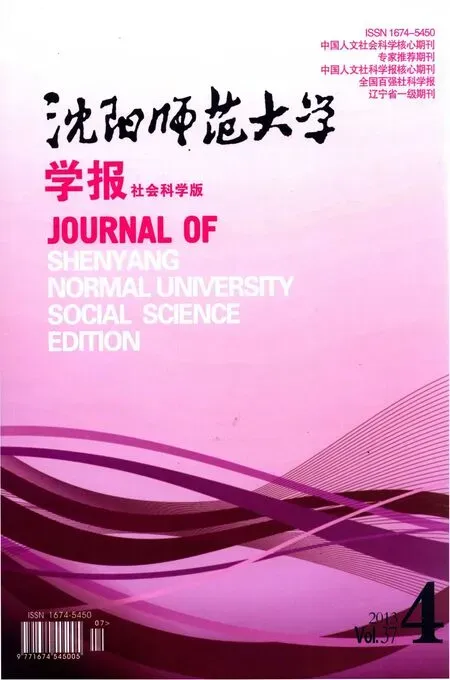人力资本与FDI区位抉择的关系——基于大连市金州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孙宗扬,王庆石
(东北财经大学 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辽宁大连 116023)
FDI的合理引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土的人力资本禀赋,因为本土的人力资本禀赋影响了外资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生产运营的模式、生产成本的控制与经济利润的实现。所以,外资企业的投资决策往往会受到本土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大连市金州新区、原开发区、原金州区2000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发现,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抉择影响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属性决定的。高学历的人力资本会促进高科技含量的FDI引进,而抑制低科技含量的劳动密集型FDI引进。同时,低学历的人力资本会促进劳动密集型FDI的引进而抑制高科技FDI的引进。
一、文献综述
关于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世界银行[1]的定义是:“外商直接投资是投资者为了实现对境外企业的持久管理兴趣而带来的投资净流入。”FDI是与FPI 1相对的概念。FDI一般是对实体资产与资本的投资,而且是长期的具有持续性的投资。FPI一般是对虚拟资产的投资,且是短期投资。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近些年,中国FDI的规模与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也日益提升。所以,针对FDI区位抉择的研究数量也有不少。但是,从人力资本角度研究FDI区位抉择的文献就比较少。
沈亚芳(2007)[2]通过跨期与分区域分析,利用区位选择模型,发现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正作用,并且这个正作用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除了看重中国劳动力的低廉价格,也看中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资本的利用效率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潘渊(2007)[3]以卢卡斯悖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导出了中国卢卡斯悖论的理论模型。他运用人力资本模型分析其与FDI区位分布之间的内在机制,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分析法对人力资本与FDI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
周均旭和江奇(2012)[4]构建了FDI的区位选择模型,对人力资本的质量与异质性进行了全面的考虑。经过对中国各省级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地带进行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的质量与FDI具有正相关性,并且人力资本异质性与FDI负相关。此外,作者发现人力资本异质性对FDI的影响程度甚至高于人力资本的质量。
从上述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人力资本之所以对外商投资有影响是因为不同性质的外商投资对人力资本有不同的需求。研究人力资本对外商投资的区位抉择影响实际上就是研究外商投资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所以,我们接下来将建立实证模型对金州新区的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抉择的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金州新区人力资本与FDI区位抉择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我们的模型变量选取与之前的文献有两点不同。一方面,我们不把外商实际投资额作为因变量。我们的模型因变量是实际外资使用额与GDP的比例(fdishare),它刻画了FDI在金州新区经济中的贡献程度。我们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和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外商投资额的增加是一种必然趋势,它未必能反映出人力资本在这个增长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人力资本对于FDI占GDP百分比的变化的影响意义更为重大。
另一方面,我们不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刻画人力资本的自变量。我们认为,一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根据其资本密集程度、行业属性来分,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是不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需求劳动力群体为中低学历的劳动者,比如中小学生。企业为了控制生产成本,追求最大化利润,不会大量的雇佣高学历的劳动力,因为高学历劳动者的薪水成本更高。在过去的十年中,金州新区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的优势之一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外国投资者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带到金州新区,并结合金州新区本土的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完成了优化的生产资源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量的高学历劳动力并不会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动力。相反地,过高的生产成本有可能成为阻碍外资进入的瓶颈。所以,简单的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刻画人力资本的变量是不合适的。
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使用不同的人力资本变量进行研究。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最大的差异在人员数量和受教育年限上。所以我们使用总受教育年限,即受教育人数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来刻画人力资本的水平。具体的,ES 1是在校小学生总受教育年限,MS 1是在校初中生总受教育年限,HS 1是在校高中生总受教育年限。同时,我们设定小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初中生为9年,高中生为12年。为了方便研究,结合实际经验,我们将中专与职业学校的学生归为高中一类。由于我们无法获得各年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专任教师数量或投资额度,所以,我们无法对各学历的人力资本进行质量差异的修正。但是,我们认为,金州新区总体行政面积不大。对于这样大小的行政区域来说,教育质量的差异不大,这个差异是我们的研究可以接受的。
此外,为了证明平均受教育年限并不能影响地区的实际外资使用额,我们也将其引入了初始模型中进行检验。平均受教育年限aveeduc为各学历在校学生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权重为各学历学生占总学生人数的比重。实证结果表明,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表1给出了上述主要变量的统计概要指标。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州新区各年在校生中占比重最高的还是小学生。尽管在考虑了不同的受教育年限之后,这个差异仍旧非常明显,而高中生的比重最低。

表1 主要变量的统计概要指标
变量的具体定义请参看附录。我们的数据来自于《金州新区统计年鉴》《金州新区发展报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报告》《金州区统计年鉴》。样本结构为面板数据,包括了金州新区、原开发区、原金州区2000年到2011年的观测值。我们选择2000年到2011年的时间区域是因为我们希望利用近十年的数据提取有效的信息,来为金州新区“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发展做出预测和指导。
此外,由于2000年之前的数据已经大量缺失,并且缺乏可信性,所以我们决定使用2000年到2011年的数据。我们使用原开发区与原金州区的数据进行数据加总,作为金州新区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由于原开发区与原金州区在2010年合并之前的统计报告包含的统计项目不一致,所以,数据的缺失与不一致成为本次研究最大的挑战。
我们的数据样本时间长度比较短,包含的时间序列信息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无法利用数据的时间序列信息为研究提供支持。一方面,我们无法对较少的观测值进行时间分段,以查看不同时间段变量关系特征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较少的观测值使得标准回归分析的大样本假设难以成立。在小样本时间的情形中,模型的自变量数目超过了模型的自由度,这使得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的线性模型无法适用。Federico(2000)[5]讨论了混合回归(pool regression)的详细方法。我们认为,使用混合回归分析金州新区实际使用外资额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混合回归利用了不同年限的三个区域(金州新区、原金州区、原开发区)数据进行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它忽略了数据的时间序列特性,但是却能够很好地处理数据的横截面属性。这与我们的目的是吻合的,即通过使用混合回归法,我们增加了回归样本中的观测值,进而更好地研究外资实际使用额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二)实证模型及估计结果分析
a)基准模型只包含我们研究的主要兴趣变量,即fdishare和 es 1、ms 1、hs 1。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我们选择10%的显著性水平作为检验标准。模型中的所有系数均是显著的,并且是联合显著的。此外,我们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服从同方差分布。从表中数据可知,es 1与fdishare存在显著地线性正相关关系,ms 1、经济总产值的分量与贡献;;es:小学生在校人数;ms:初中生在校人数;hs:高中生在校人数,包括职业中专;es 1:小学在校生总教育年限。es 1=es*6;ms 1:初中在校生总教育年限。ms 1=ms*9;hs 1:高中在校生总教育年限。hs 1=hs*12;sfa 1: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值;gdfht 1:高科技产业产值与GDP的比值。

表2 模型回归结果
hs 1与fdishare存在显著地线性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告诉我们当在校小学生的人数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就会显著地提高。而当在校初中生与高中生的人数提高时,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减小。这个结果与我们之前所述的劳动密集型FDI的劳动力需求特点不谋而合。由于金州新区目前的劳动力群体绝大多数为小学文化,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是吸引外商投资的较大优势。如果金州新区的外商吸引模式不变,小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增加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如果更高学历的劳动力增加会提升用工成本,缩小金州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通过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建立了另外两个扩展模型。
b)扩展模型1

在扩展模型1中我们加入了两个控制变量。一个是社会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sfa 1,另一个是高新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gdpht 1。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反映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较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我们期望sfa 1与fdishare有正的线性相关关系。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与生产效率,也能够反映出地区FDI的发展模式。高新技术投资具有风险性,所以,高新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越大,地区经济进行高技术产业投资的信誉越高,不确定性越低,对高科技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越强。我们期望gdpht 1与fdishare有正的线性相关关系。扩展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2。
表2中数据显示,fdishare与es 1仍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而与ms 1和hs 1存在显著的负线性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扩展模型1的回归结果说明我们得到的实际外商投资额对GDP的贡献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是较为稳健的。与基准模型相比,扩展模型1中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系数绝对值都增加了。模型的R2也有显著的提高。此外,sfa 1的系数是不显著的,而gdpht 1的系数显著为正。
c)扩展模型2
在扩展模型2中,我们将对高新技术产业与不同学历的人力资本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所以,我们引入了三个交互变量:

扩展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2。表中数据显示,es 1与fdishare具有显著的正线性相关关系,ms 1、hs 1与fdishare具有显著的负线性相关关系,且主要变量的系数显著性都有提高。模型2的R2值为0.905,处于比较理想的水平。扩展模型2的回归结果说明了我们发现的外商实际投资额所占比例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稳健的。此外,esgdpht的系数显著为负,msgdpht、hsgdpht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具有正作用,且这种推动作用需要较高学历的人力资本支持。
三、政策建议
上述实证结论说明,我们不能草率地得出外商实际投资额的增加会引起某种固定的人力资本需求变化。我们认为,人力资本需求的变化不是简单的由外商实际投资总额决定的,而是更多地受外商投资的属性所影响。事实表明,金州新区近十年来外商投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且主要需求劳动力的特征为低学历的廉价劳动力。如果单纯从吸引外资,增加外商投资额的角度来说,我们只需要保证低学历的劳动力有足够的供给即可。这个结论似乎与我们提倡科教兴国的大战略背道而驰。我们认为,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方面,促进低学历劳动力就业是促进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现阶段我国诸多地区出现“用工荒”的问题以及低学历劳动力招工难的现象。这种招工难并不是由于低学历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的,而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的恶性影响导致了中国出口行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的低学历劳动力使得其工资收入严重低于其边际劳动生产力。低水平的工资收入与物价的不断上涨使得低学历劳动力的供给变得十分不稳定。事实说明,低学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已经妨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低学历劳动力就业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直维持低科技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结构,这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低科技含量的生产结构决定了低学历与低技能的人才需求结构,从而抑制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才素质、民族素质的提高。此外,根据劳动力成本等于边际生产力的均衡法则四,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劳动收入高于低科技产业的劳动收入。中国政府将提升居民收入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居民收入的提高将拉动居民消费的提升,从而实现居民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同时,居民消费的增长又可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与快速发展,形成良性的经济循环。如果中国想要提升居民的收入,从而实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生活水平,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是势在必行的。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加强高学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为其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与保障是中国未来产业结构转变的关键。如前文所述,外商投资是中国产业结构转换的重要助推力。我们应当在未来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大力引进资本密集型外商投资,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通常都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可以提高边际劳动生产效率,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提高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所以,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国未来引进的FDI不仅需要带来资本与资金,更要带来科技与经验,让国外高科技产业的成果传播到中国本土,为国内产业提供先进的国际经验。然而,技术的扩散与传播需要优秀的人才作为媒介。所以,基于未来产业结构的转变,金州新区应当前瞻性地培养优秀的人才,积累坚实的人力资本,为未来引进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产业夯实坚强的人才后盾。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金州新区过去十年以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为主的模式下,低学历的劳动力对吸引外商投资具有重要作用,高学历的劳动力对于吸引外商投资具有反作用。但是,高学历人才对于高科技产业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低学历劳动力对于高科技产业具有阻碍作用。
金州新区在“十二五”期间的重要经济任务之一就是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变。但是,加强资本密集型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建设需要配合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就如我们在本研究中所验证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换策略要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与转换策略同步进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高学历与国际化人才的引进与培养,为高科技行业吸引外商投资夯实坚定的人力支持。
基于数据的局限性,我们无法检测外商投资对GDP的贡献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是否随时间而变化,是否对于金州新区、原开发区、原金州区有所差异。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进行攻克,它们是未来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1]World Bank Staff.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M].New York:World Bank,2013.
[2]Feenstra,R.,Taylor,A.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 New York:The Worth Publisher, 2008: 19-20.
[3]沈亚芳.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7(7):113-118.
[4]潘渊.人力资本与FDI区位分布——中国的卢卡斯之谜[J].湖南大学,2008(6):82-84.
[5]周均旭,江奇.人力资本质量、异质性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J].华东经济管理,2012(8):44-47.
[6]Federico,P. Recent Developments in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The Case of Pooled Time 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 [J].DSSPapers,2000(2):6-41.
-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大学社会教育研究——基于大学服务社会的历史考察
- 生态文明观解析
- 《史记》价值评价体系与用人制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