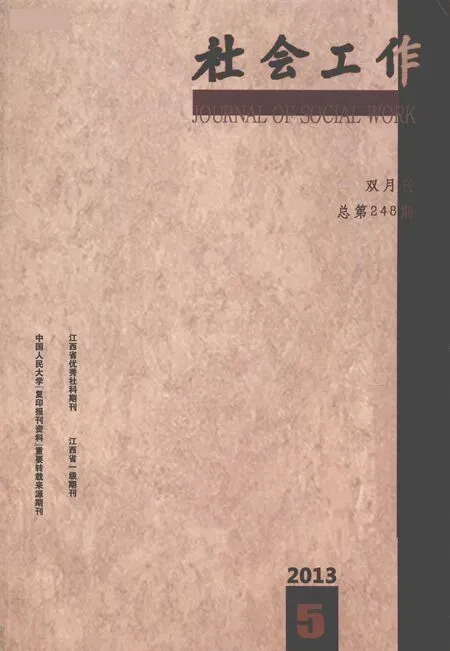社会工作的“时势权力”
何雪松 熊 薇
“势”是中国语境之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它可能提供了一个西方文化中不常见的秩序意义,或是某种中国意义的效力观(余莲,2009)。然而它却是中国人看世界与想问题的基本方式。从个体到政治、从时间到空间都与“势”有着关联。将“势”这个概念引入社会工作是为了厚实宏观议题的把握,以促进宏观层面的改变,因为“势”暗示了“顺势而为”的可能性,这要求社会工作去争取“时势权力”。
“势”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在发展过程之中呈现出丰富的内涵,杨国荣(2012)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非常好的梳理,法国学者余莲则有专著《势:中国的效力观》予以专门探讨。本文在综合各家论述的基础之上认为,势具有政治与伦理的属性、在时空上延展、隐含着结构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第一,“势”具有政治与伦理属性。法家的代表性人物韩非子的治国理念以法、术、势三个字统领。《韩非子·难势》曰:“抱法处势”,这四个词就生动地体现了法与势之间的动态对应关系,法是不变的,而势可变,不变的法要由可变的势予以驾驭,当权者的威力所在就是这样展现“术”。实际上,“势”是与“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传统社会所重视的君臣关系。《管子》有这样的表述:
“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
这个表述之中可以看出,君臣之“位”是在互动之中展现的,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关系,而是基于具体的政治脉络而形成不同的“势”实践之中形成的。这一表述给“臣”的作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当然这样的可能性,是与道统或“术”是结合在一起的。
叶适撰写了专文《治势》,考察“势”与政治兴衰之间的关联。叶适说:“故夫势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则治,离则乱;张则盛,驰则衰;虚则存,绝则亡。臣尝考之于载籍,自有天地以来,其合离张弛绝续之变凡几见矣,知其势而以一身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在他看来,“势”一方面作为必然趋向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夫以封建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县为天下者,秦汉魏晋隋唐也。法度立于其间,所以维持上下之势也。”。但他同时又肯定了人在“势”之下并非毫无作为,“古之人者,尧、舜、禹、汤、文武、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虽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浅深,而要以为天下之势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则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其后,导水土,通山泽,作舟车,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义、礼乐、刑罚、庆赏以纪纲天下之民。”在此,人的顺“势”而为既表现为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变革与发展,“导水土,通山泽,作舟车”,因此“知其势而以一身为之”。也就是说,把握“势”之后进一步借“势”治天下,所谓因“势”而行、顺“势”而为(杨国荣,2012)。
“势”也展现在更广泛意义的社会伦理生活之中。《孟子》记载了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这里所说的是父子关系之中的“势”,也就是父有不能教子的关系动力,因为这个关系里牵涉着情感因素与父亲的权威,“责善则离”,不如易子而教,这样才可保全父子之间的伦理格局。
《淮南子》则记载另一个场景以说明儿子救父亲是势之必然:
“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
即便在父子关系之中也因为特定情景之下必须突破伦理的要求而“骄侮”,因为要“救其死”,也就是不得已之举,因为救命是更大的“法”,这样伦理困境就得以解决。
第二,势体现在时间、空间与关系的延展上。因为“势”既是流动的、异变的,又呈现出特定的空间结构,只有把握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才能真正理解“势”,并从中洞察到“势”的实践意涵。
“势”的时间之维体现为在时间的绵延之中展开,有稍纵即逝的可能,也有不可挡之必然性。王夫之认为“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由此可见,“时”与“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今日所言的“时势”。而中国人是向来重视“时势”的。对此钱穆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中国人常称时代,又称时势。当知此一时,彼一时,彼一时必然会来代替这一时,而那更替接代之转移契机,则有一个势。中国人又常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此两语并没有大分别。凡属英雄,必能造时势,而英雄也必为时势所造成。但若转就时势论,也如此。尽有了时势,没有英雄,仍不成。当流行的时世装变成了俗套,就得要变,但还得期待一真美人出世,而那新美人,又得要有势。一般说来,电影明星易于影响大家闺秀,大家闺秀便不易影响电影明星。而那些空谷佳人,则更难影响人。所以风气转变,又须得风云际会。云从龙,风从虎,风云则凑会到龙与虎的身边。但潜龙仍不能有大作用,必得飞龙在天,那时,满天云气便凑会到他身边。(钱穆,2002)
从空间上讲,“势”就是关系结构,有高下之分,“物类相应于势”。势的空间性常见于“强势”与“弱势”的表述,具有社会结构意味、阶层意味,甚至有阶级意味,表现的是人群之间的关系的空间隐喻。但强与弱之间的关系也是变动的,老子的智慧在于看到对立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最具有启示意义的是老子谈到的“水”的比喻,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强弱是转化的,即便如水般的柔弱,也是有力量的,有胜刚强之“势”,这样势就具有了很强的实践意义。
最后,“势”隐含了结构与能动性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势”具有结构性,它看似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性,即一旦“势”已形成,它就呈现为一种现实的时空状况与关系力量,人必须在行动和实践之中予以正视和面对;另一方面,势又具有转化性,表现为人在“势”面前不是没有作为的可能,人的能动性可以突破时间、空间与关系的局限而采取行动。
结构性与转化性的对立统一就体现在,《孙子》所言的“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也就是说人知势、明势,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有可为。
刘勰曰:“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其中“即体成势”就表明“势”具有建构性。“势”的建构性意味着各种变化的可能性,这为人们追求梦想、改变生活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当“势”作为时间绵延之时,借势而变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只要生命体在时间上绵延,对于中国人而言总是有改变的机会。所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东山再起”,就是等待下一个可能的“时”与“势”。
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先生提到的时势权力这个概念与社会工作有着重要的关联性。所谓时势权力,他是这样解释的,
“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恐、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阻止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费孝通,1998)
社会工作的确只能借助“上善若水”的流变之势去引领或顺应时代的“势”能,从而促进社会的改变,这样的力量就是“时势权力”。“时势权力”来自何处,来自对形势的判断与把握。“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这句话要说的就是只有洞察大势,才有机会。陈亮进一步指出“事之未立,则曰‘乘其机也’,不知动者之有机而不动者之无机矣,纵其有机也,与无奚异!功之未成则曰‘待其时也’,不知为者之有时而不为者之无时矣,纵其有时也,与无奚别!”由此观之,如果社会工作者能够准确把握时势,“乘其机”或“待其时”,掌握设置政策议题的能力,就有可能促成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改变。
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命远远超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视野所及,将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这样的宏观层面的变革联系在一起需要新的理论视野。一般很难从现有的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中获得足够的思想支持,因为社会工作的发展阶段与历史使命均有所不同。西方社会工作虽然也有倡导、赋权、激进社会工作之论述,但总体而言,宏观的把握不够。实际上,全球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动,诸如金融风暴、欧债危机、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都以不同的方式冲击着现有的社会建制,包括主流的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或职业似乎未能起到引领社会的功能,究其原因在于,社会工作尚未充认识到如此全球经济社会变动的深刻后果,也未能及时在理论上有所回应,在实践上当然茫茫然毫无方向。这就要求社会工作直面这样的挑战,寻求知识创新与实践转换。
在这个意义上,将“势”这个概念及其后的思想内涵引入社会工作是有意义的。不过“势”这个概念不太容易进行测量与操作。现阶段,笔者也只能提出两个初步的设想。
其一,社会工作要想把握时势,就需要充分展现社会学想象力,洞察社会的变动脉络。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在面对不同的状况之时,只有当懂得利用其所身处的情景,行动才会带来效果。特别是要关注处于萌芽状态之中的元素,有益者予以鼓励,有害者予以阻止,就如园丁除杂草保护良性植物,这就是为了实现一个趋势所具有的可能性(余莲,2009)。这或许需要具备“一叶知秋”或“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力。所以,社会工作者在关注伦理价值、干预技巧的同时,也需要看到社会学想象力的重要性。否则,只能奔波于一个个的个案,却很难引起社会的关注,更遑论推动社会的改变。因此不能忘记了“社会工作”的限定词“社会”,这个限定词需要做“时势英雄”,这是“工作”的目标之所在,这样才能名副其实。
其二,社会工作要学会顺“势”而为。今天的中国为社会工作发展“时势权力”创造了机会,因为社会的急剧转型、互联网的兴起、个人权利的张扬,为“势”的营造提供了平台。平面化与多中心成为这个新的社会形态的重要特征,这对社会工作者而言是重要的契机,因为社工的力量就在于将不同的人、群体与社群联结起来,今天比以往都有了更好的联结工具与空间。这时候最需要的是社会工作者“顺势”而为,而驾驭“势”的“法”是人的尊严与权利、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样的“法”,即便逆“势”也不能弃守。
[1]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钱穆,2002,《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3]余莲,2009,《势:中国的效力观》,卓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杨国荣,2012,《说“势”》,《文史哲》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