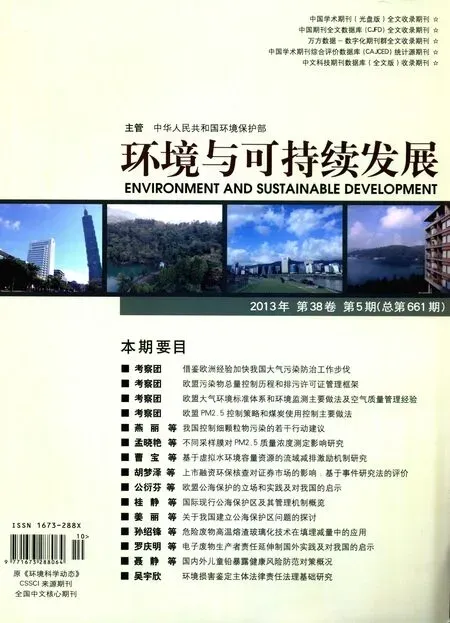关于我国建立公海保护区问题的探讨
姜 丽 范晓婷 罗婷婷 公衍芬 王 群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天津 300171)
公海保护区是一种全新的公海保护方法。尽管目前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公海保护区作为一种全新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形式已被付诸国际实践。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我国历来重视公海事务。在公海保护区问题上,我国既享有潜在的全方位利益,也需要应对建立公海保护区带来的挑战。本文基于公海保护区理论与实践,分析了我国建立公海保护区的潜在利益和挑战以及相应策略。
1 公海保护区的理论与实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86条规定,公海是指“不包括在任何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者内水或者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全部海域”。[1]《公约》第87条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不受任何国家的支配和管辖,即公海自由原则。公海自由原则是海洋法确定的公海制度的基石。20世纪90年代以后,沿海国逐渐完成国家管辖范围以内的海域确权问题。随着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问题的不断出现,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开始从国家管辖以内海域扩展到国家管辖以外的海域制度的修改和调整上。同时,深海捕捞的迅猛发展和捕捞能力的迅速提高导致公海生物多样性风险不断攀升,公海保护问题逐步纳入人们视域,“公海保护区”概念应运而生。
所谓的公海保护区,是指为保护和有效管理海洋资源、环境、生物多样性或历史遗迹等而在公海设立的海洋保护区。21世纪后,随着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愈益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公海保护区日渐成为热点。在2000年的第二届世界保护大会、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2003年的世界保护区大会以及2006年的第八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等大量的国际会议均明确提出“建立公海保护区”的议题[2]。而2003年在“公海保护区专家研讨会”上提议确定的六个公海保护区候选区以及2008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上通过的《建立包括公海和深海生境在内的代表性的海洋保护区网的选址的科学指导意见》,无疑对公海保护区的制度与实践起到积极推进作用和科学指导意义。
虽然公海保护区为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海海洋环境保护提供全新方法,但保护区的设定无疑会限制传统意义上的公海自由,造成国家国内法律制度与公海新环境政策间的矛盾[3]。这种矛盾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建立公海保护区合理性问题的讨论: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积极推进公海保护区建设进程,欧盟甚至提议制定重点规范建立公海保护区的《公约》第三执行协定;而挪威则以建立公海保护区违背公海自由原则为由明确反对建立公海保护区。
尽管关于公海保护区合理性的争论未定,公海保护区的制度框架也尚未统一,但国际社会已将此制度付诸实践。经过国际社会、区域组织及相关国家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在公海建立了三个公海保护区,即1999年法国、意大利与摩洛哥三国建立的地中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4]、2009年11月通过的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5]以及2010年9月通过的大西洋中央海脊海洋保护区。
2 我国关于公海保护事务的态度
尽管公海保护区的发展历史比较短暂,但在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公海环境和资源的大背景下,建立公海保护区业已成为保护国家管辖以外海域海洋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并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对于国际海洋事务的参与是从20世纪70年代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开始的。尽管目前我国尚未开展公海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和实际行动,但我国政府历来积极开展生物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国际合作,并在多个国际会议场合表明和阐述我国关于国家管辖以外海域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立场和态度,虽然并非直指公海保护区,但是这些立场和态度对指导我国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在公海保护区方面的合作无疑起到积极作用。
2.1 密切关注公海保护相关海洋事务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公海保护,积极开展公海保护事务。不仅积极参加保护公海渔业资源协定的制定工作,还批准或参加各个区域的渔业养护与管理公约,并加入有影响的国际或区域性渔业组织。另外,为了履行我国在公海生物资源养护、渔业管理方面的义务,我国还在公海上开展独立巡航执法与联合执法活动。
2.2 主张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兼顾
涉及公海生物多样性问题,我国主张“利用中保护”原则。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在2006年第61届联大审议海洋和海洋法议题时发言指出,我们应着眼于寻求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禁止或限制利用海洋[6]。可见,我国政府主张妥善处理养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主张利用中保护。
2.3 主张以现有法律框架规范公海事务
我国重视现有国际海洋法律框架,认为现有框架是解决海洋领域新问题、处理新挑战的重要依据。我国在2006年第61届联大审议海洋和海洋法议题的发言就指出,养护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和手段,应在《公约》及其他国际公约框架内确定,充分考虑现行公海制度和国际海底制度。可见,我国主张尊重《公约》及现有海洋法律制度,按照《公约》规定处理公海保护事务。
3 我国建立公海保护区的潜在利益
随着世界范围内建立公海保护区趋势的发展,公海保护区这一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和国际海洋实践的新前沿、新热点,不得不引起我国的应有重视。我国不可能置身趋势之外。问题在于我国参与建立公海保护区的实际影响有多大、潜在利益体现在何处。对我国而言,须以发展的眼光,从我国战略利益的高度出发,全方位确定我国在建立公海保护区问题上的战略利益之所在,维护我国分享公海和“区域”资源的战略利益,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在公海应有的海洋权益。
3.1 建立公海保护区的管辖利益
从公海保护区建立的实践来看,不论是依《公约》还是若干国家之间的协议建立的,从客观实践观察,公海保护区的实际管理最终须置于某些具体国家的实际管辖之下。因此,从本质上讲,建立公海保护区并实现对其有效管理能够实现国家管辖权的实际扩张;从实际效果来看,部分沿海国和国际组织推动设立公海保护区,往往以此方式限制了其他国家在该公海海域内开展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等活动的权利,从而保护本国或组织业已获得的利益。可见通过建立公海保护区并实现对其有效管理进而实现国家管辖权的实际扩张已不可避免。通过建设公海保护区,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名的“新海洋圈地运动”正悄然兴起。
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在其1976年颁布《渔业区域法》中对大浅滩位于200海里专属渔区范围之外、占大浅滩总面积10%的两个位于公海的拐角进行长臂管辖。尽管遭到他国的反对,但加拿大在2009年的《加拿大沿岸渔业保护规则》中依然沿袭了1994年《沿岸渔业保护法修正案》的基本规定,继续声称对在200海里专属渔区外的大浅滩处两个拐角从事捕捞活动的船舶具有管辖权。可见,公海保护区的设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沿海国海上管辖权的实际扩张。扩大了其对公海管辖范围,就等于扩大了沿海国的资源储藏量,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面临着资源、环境和发展空间的巨大压力,拓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的发展空间和战略利益,对于我国未来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何在新一轮的海洋圈地运动中占据首发权和主动权,保持我国在公海应有的权益与利益,是我国推进海洋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新课题。适时合理地推进公海保护区建设,能够使我国在新一轮的海洋圈地运动中抢占先机,主动作为、扩展管辖,这是建立公海保护区在扩展国家管辖权方面的利益所在。
3.2 建立公海保护区的资源利益
国家管辖外广阔海域蕴藏着多种战略性资源。这些资源都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公海保护区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有着多重的潜在利益,但毋庸置疑的是,资源利益是其最直接的潜在利益。公海保护区的建立意味着沿海国本国管辖范围和资源储藏量的扩大,这对沿海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公海为全人类所有,保护公海资源不受掠夺,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义务,也是符合各沿海国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对于我国而言,我国面临的资源现状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匮乏。面对21世纪的海洋新世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兴盛越来越依赖海洋。因此,我们要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海洋资源战略思想,研究确定中国21世纪初期海洋资源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战略方针。为拓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海洋资源战略研究设计区域既应包括约300万平方千米的我国主权和管辖海域,更应当涉及到2.5亿平方千米的“区域”与公海。建立公海保护区不仅契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战略利益,更为我国未来的发展预留了可观的战略资源。
3.3 建立公海保护区的科研利益
国家管辖外海域拥有众多的重大基础前沿科学问题。过去十几年深海科技发展实践表明作为高战略技术,发展深海技术和极地技术可带动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而公海保护区本身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过去,只有一些海洋强国有能力进军公海,顺利开展公海海洋科学研究,较早开始对公海各类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并初具规模;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对公海的相关科学研究才刚刚起步。从公海保护区的实际效果来看,部分沿海国和国际组织推动公海保护区的设立,往往以此方式限制了其他国家在该公海海域内开展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等活动的权利,从而保持本国或相关组织对该海域的认知优势,保护本国或组织业已获得的利益。因此打破发达国家的认知垄断,增强自身的公海资源开发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公海保护区的科学认知和法理认知水平较低,而加强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已经开展公海保护区建设的海洋强国合作,提高对包括公海保护区在内的国家管辖外海域的科学认知水平,不仅可以为公海保护区建设提供科研支持,体现我国在公海的实际存在,更有助于提高我国对于公海的实际管理水准,最大限度地拓展和维护本国利益,为我国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4 我国建立公海保护区需应对的挑战
4.1 公海保护区对远洋捕鱼产业的挑战
对远洋捕捞国而言,他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公海捕鱼自由”的规定,而对沿海国而言,则是如何保证其在各自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利益不会受到公海捕捞活动的不利影响[7]。建立公海保护区的题中之义是禁止或限制在保护区内渔产品的捕捞,因此公海保护区对现有公海自由的首要冲击是公海捕捞。
建国初期,我国未能充分行使国际法赋予的公海捕鱼自由的权利,没能有计划地利用公海渔业资源为我国人民谋利益。中国的远洋渔业1985年起步,并开始建立自己的远洋捕鱼船队。目前,我国已拥有1500艘远洋渔船,作业海域遍及三大洋公海和32个国家的管辖海域,成为世界主要远洋渔业国家之一,也是从公海捕捞渔业资源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随着对公海渔业加强管理和限制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限制与挑战。从国际上目前的形势看,对公海渔业的限制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详细。在目前国际渔业法律环境的这一大背景下,公海保护区制度的确立和禁渔措施的实施,无疑会使我国远洋捕捞业首当其冲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与冲击。从农业部渔业局发布的2006年至2010年权威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公海禁渔措施的实施,我国远洋渔业产量也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8]。为了顺应国际社会对公海捕鱼做出限制这一趋势,国内不少专家也从作业方式、作业类型、加强与国际接轨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以逐步符合国际上的要求,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4.2 公海保护区对区域资源开发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各国对“区域”资源调查活动的逐渐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在深海海底进行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铁锰壳开采活动的同时,会对深海平原、热液喷口和海山的海洋生命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所带来的海洋环境问题也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虽然“区域”矿产资源整体受“区域”制度的管辖与支配,但“区域”的上覆水体均属公海,公海保护区的建立势必对勘探开发“区域”矿产资源及开发利用生物资源活动产生限制。国际海底管理局明确表示,愿意成为加强公海海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的适当场所,以避免出现一个与现行“区域”制度相抵触的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
目前,我国政府积极制定开发国际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的战略。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相继开展了大洋海底资源的调查勘探活动,并在中太平洋中部、西南印度洋相关区域获得优先开采权。但与此同时,我国还面临着国际上针对深海底采矿活动而加强环境保护的局面。我国在“区域”开展相关科学调查和研究活动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建立公海保护区会对我参与分享“区域”矿产资源和深海生物资源产生消极影响。为此,我国要树立长远战略眼光,既要积极参与公海与“区域”的调查研究与勘探开发,又要深入研究国际社会及海底管理局对“区域”资源开发环境问题的各种动向,积极调整我国的大洋战略政策。
4.3 公海保护区对国内管理体制的挑战
从制度层面分析,建立公海保护区对一国现有的管理机制及相关安排至少存在两方面影响:第一,虽然在国家管辖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框架已初步形成,但尚未形成建立公海保护区的相对一致的法律框架。且由于公海保护区本身对公海自由原则的限制,决定了公海保护区势必面临与有关国际条约相衔接的问题,需要从现有的法律和机制中寻求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最佳途径。第二,就国内海洋保护区制度与公海保护区制度而言,两者属截然不同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要在公海设立保护区并加以有效的环境保护,不能简单地将海洋保护区制度从国内法领域简单照搬到国际法领域之中,而是需要制度的吸收与创新过程。
尽管公海保护区制度对于主导国家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挑战,主导国家在建设伊始阶段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但国际法对此并非就束手无策,关键在于主权者有关环境的政治意志的转变[9],尤其是可以对国内一些与公海保护不甚相符的体制与安排做出适当的调整和修正。鉴于目前国内体制安排与管理的现状,我国需要有针对性地从以下三方面加强与公海保护区制度的衔接与对轨:首先,我国应加强和建全统筹规划,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国家管辖外海域事务发展的高层次协调体制、机制,为我国国家管辖外海域权益维护和拓展提供保障;其次,我国须加快国内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弥补现有国内关于国家管辖外法律的空白,运用法律这一维护国际海域权益的有效武器,为我国开展公海保护区建设事务提供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我国应当积极加强海洋执法能力建设,以适应和加强目前开展的公海渔业管理执法活动。
5 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海洋环境与海洋资源问题的凸显,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的保护问题被广泛讨论。作为全新的就地保护形式,公海特别保护区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视域。尽管公海保护区发展历程十分短暂,但公海保护区这一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新前沿、新热点与新实践,不得不引起我国的应有重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我国历来重视公海事务。在公海保护区问题上,我国既享有潜在的全方位利益,也需要应对建立公海保护区带来的挑战。
具体地说,对我国而言,在开展公海保护区事务之
前,首先应以发展的眼光,从我国战略利益的高度出发确定我国建立公海保护区可获得的潜在利益,维护我国分享公海和“区域”资源的战略利益。同时,厘清公海保护区制度本身对我国在远洋捕鱼产业、区域资源开发、国内管理体制等问题上的固有影响,总体把握我国建立公海保护区的限制因素之所在。在对建立公海保护区的潜在利益和固有挑战做出通盘考虑后,综合权衡我国建立公海保护区的利弊得失,最大程度地获得公海保护区的战略利益、降低新制度对我国现有产业、体制的消极影响。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我国在公海保护区事务上的应有立场与谈判方向,在多边国际场合中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并进一步结合国内科研调查实际,采取相关行动,既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在公海应有的海洋权益,又能妥善应对设立公海保护区而引发的“新圈地运动”。
[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6.
[2]赵薇娜.公海环境保护与公海海洋保护区之辨[C].高之国,张海文,贾宇.国际海洋法发展趋势研究[A].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
[3]刘惠荣,韩洋.特别保护区: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视域[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5):141-145.
[4]北半球第一个公海自然保护区成立[EB/OL].(1999-11-27).http://www.sina.com.cn.
[5]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在公海上设定第一个海洋保护区[J].国外极地考察信息汇编,2009(16):1.
[6]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在第61届联大审议海洋和海洋法议题上的发言 [EB/OL].(2006-12-07).http://www.fmprc.gov.cn/ce/ceun/chn/zgylhg/flyty/hyfsw/t348882.htm.
[7]慕亚平,江颖.从“公海捕鱼自由”原则的演变看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趋势[J].中国海洋法学评论[C].香港: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出版社,2005.
[8]农业部渔业局.中国海洋渔业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9]王曦.环境与主权[A].邵沙平,余敏友.国际法问题专论[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