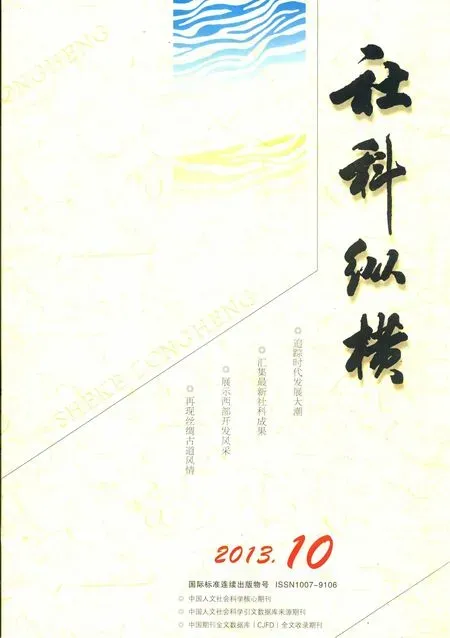传统“苦情戏”情节模式初探
吴小侠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一方面指舞台上的故事来源于鲜活的人生,并如生活一般有声有色、有苦有乐;一方面指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戏剧性、偶然性事件,不是戏却胜似戏。
戏曲舞台上,充满了世俗人生的活泼情趣,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故事既为观众津津乐道,也让剧作家乐此不疲。而在这类描写家庭生活的剧作中,“丈夫远行,妻子在家遭受磨难”为基本情节模式的“苦情戏”,又格外引人注目。
一、几部“苦情戏”的情况
在戏曲家族中,有一部分作品在思想内容、人物关系、情节故事等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有无意之间的巧合因素,也有后来者对前人故事的有意继承与改造。《赵贞女蔡二郎》、《王魁》、《张协状元》、《琵琶记》、《白兔记》、《荆钗记》、《秋胡戏妻》、《武家坡》、《汾河湾》、《铡美案》等皆属于此类戏,它们虽来自不同年代,各部戏在男子远行的原因、时间、离家后各自的表现等方面也有所不同,家中苦苦度日的妻子也各自遭际不同,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还是能发现其所共同具有的本质特征。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谈到词的意义时,曾提出“家族相似理论”一说。他认为,语言的用法虽有多样性,但又有类似性。他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1]如果把苦情戏看作是一个大家族的各个成员,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具有“家族相似性”。
就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南戏也是最早的“苦情戏”是《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徐渭的《南词叙录》记:“南戏始于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又说:“赵贞女蔡二郎,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这两个戏均已佚失,其基本情节只能从有关史料的转引中获得,即蔡二郎、王魁在发迹变泰后,背弃了从前的糟糠之妻,而另娶权门,最后一为暴雷震死,一个被鬼魂活捉。这两个剧中的女主人公则完全是无辜而遭难,对负心男子的惩罚是对女主人公某种程度上的宽慰,更是作者鲜明是非观和善恶意识的体现。
《张协状元》是早期南戏中仅存的一个完整本。通过这个剧本,可以推想出其他两个南戏的情节内容及作者的创作倾向。《张协状元》写张协在困顿时与贫女结为夫妻,进京考中状元后就翻脸不认贫女,且想致贫女于死地。在当朝宰相王德用的帮助下,张协最终又娶回贫女。故事勉强落得一个团圆的结局。可以说,张协是同蔡二郎、王魁一样品德不好的衣冠人物,他们在发迹前后的所作所为及对待患难妻子的前后态度方面,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所不同的是蔡二郎和王魁均遭报应,而张协则得到了作者的原谅,让他与贫女团圆。
此后,又过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间,被称为“南戏之宗”的《琵琶记》诞生了。这里的“宗”显然不是说它是第一部南戏,而是就《琵琶记》的思想意义、情节编织、人物安排等各个方面均可作为中国戏曲的样板作品而言。《琵琶记》对此前同类故事的继承显而易见,对男主人公形象的改造与重塑意图也极为明显。在故事的发生过程中,男子仍是弃亲不养,弃妻不顾,女子仍是受苦受难,但作者高明为男子找到了种种借口,让男子无情无义的举动显得颇为无奈。作者的目的是要塑造一个“全忠全孝蔡伯喈”,但实际看来蔡伯喈既不忠也不孝。由陆游的诗“满村听唱蔡中郎”可知该类故事在民间的流行程度;由朱元璋的“《四书》《五经》为五谷,家家皆有。《琵琶记》如山珍海味,富贵家岂可无耶”的倡导,可以想象这个故事的流布广泛,对此后舞台故事的影响当然也就可以想象。远的且不说,在元末流行的四大南戏中,就有两部明显地带有《琵琶记》的痕迹,即《荆钗记》和《白兔记》,这两部戏中男主人公分别是王十朋和刘知远,他们虽身份不同,一为文臣,一为武将;性情不同,一个痴情,一个善忘,但在他们身上还是能看到蔡伯喈的影子。再到后来的《秋胡戏妻》、《武家坡》、《汾河湾》、《铡美案》等戏,虽从感情色彩上看有喜剧悲剧之分,但其中心情节的构成仍没有脱离“丈夫离家,妻子受难”这一模式。
二、戏剧情节编织技巧
现实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的不竭源泉。漫长的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统治着人们,无论是社会角色还是家庭地位上,男子强大女子柔弱、男子主动女子被动、男子独立女子依附是最寻常的表现,也是为所有人所认可并遵守的规则。男子的主动意识和生活中的强者身份,赋予了他们各种发展变化的可能,可以经商致富,可以边疆立功,也可以读书仕进……虽然大多数男子最终还是默默无闻,但总会有一些人志得意满地衣锦荣归,这些人就是打破平静生活的成功者,是为人称羡的焦点,也是为家庭带来大喜大悲的不安因素。男人的举动首当其冲影响到的是他的父母妻子。当男人外出求发展求变化时,年迈的父母就要靠作妻子的来赡养,因而,男子的离家,实际上给自己的妻子带来了精神上、肉体上的双重压力。众所周知,封建时代的女子因为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因而也没有人格的独立,她们只是丈夫的附庸,她们的阵地永远只在家庭,她们的命运也完全由丈夫决定。由于缺乏主动意识,她们只会被动地等待,在等待中承受生活的磨难,肩负家庭的重担,耗尽青春乃至生命。“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只是对男人们说的,对于作妻子的来说,世界永远就是如家一般大,她们目力所及,永远就是丈夫的所到之处。
舞台上的故事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它比生活更凝练、更集中。极富生活经验和艺术技巧的古代剧作家,本着“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目的,将来自现实或前代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经过一番提炼后搬上了舞台。
在有关夫妻分离的故事中,作者都不忘交代以下几点:
第一,对时间的安排。夫妻相聚的时间,极言其短;分离的时间,极言其长。这样的处理便于以后夫妻相见时形成误会或冲突,富有戏剧性。《红鬃烈马》中,薛平贵和王宝钏新婚不久,就被宝钏的父亲王允用计分开,薛平贵被封为马前先行去攻打西凉,一走就是18年,再回来于武家坡前相见时,王宝钏已认不出他,而他也就有了趁机试探自己妻子的可能。《秋胡戏妻》中,秋胡和妻子罗梅英新婚三天就被迫分离,一走10年,等秋胡功成名就转回家园时,双方都已认不出彼此,因而有了秋胡的戏妻表演。《汾河湾》中薛仁贵也是在新婚后不久就去了边疆立功,等到回来时,儿子都已长大成人。《白兔记》中刘知远,新婚后不久就离开妻子去参军,一走就是16年。16年间,刘知远功成名就,另娶他人,李三娘备受辛苦,身心俱疲。16年后,儿子咬脐郎猎兔时遇见母亲,上演一出悲喜交加的大戏。
第二,对男子离家原因的解释。故事中的男子的行动轨迹就像走了一个圆圈,从家中出发,最终又回到家里。作者要表现的就是他走这一圈的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他变化的原因。故事开始时多为普通人家饱享天伦之乐、生活安宁平静的画面,随之就有外来因素打破了这一宁静:或为家中长辈指望儿子光宗耀祖、改换门庭,逼着儿子去应考,如蔡伯喈;或为男子自己出于对功名的热切追求,如王魁、王十朋、陈世美等人;或为外敌入侵,被朝廷征调去守边卫国,如薛平贵、薛仁贵、秋胡等;或为家中其他人的刁难不容,如刘知远。以上从各个方面为男子的离家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使得后来情节的波澜起伏有了可能。而这些外来因素的加入,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男子的负心、遗忘找到借口和开脱的依据。另外,这样也利于经过一番波澜之后男子与结发妻子的重归于好,有利于剧情往好的一面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平衡了观众曾经失重的心理。
第三,两条线索的平行发展。让曾经的亲人相忘或生恨需要一定的情节设计和铺垫。当夫妻分离后,故事情节就会“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古代剧作者在构思冲突时采用了一种夸张的手法,即让离家的男人取得功名后,便野心膨胀,为了名和利,不惜采取种种手段,甚至抹黑了良心。在外的男子,面对纷繁多变的世界和来自各个方面的诱惑,一个个就像得了健忘症,都忘记了自己曾有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而纷纷过起了“夜夜笙歌,朝朝寒食”的日子,与新娶的娇妻千般恩爱万般缠绵,同时事业上有老泰山撑腰,官越做越大,仕途越来越顺。而在家的妻子们却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丈夫的消息,她们的丈夫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但这不影响她们对丈夫的信赖、思念和忠诚,生活越来越艰难,她们使出浑身解数支撑着本就贫困的家庭,要养育幼儿,侍奉公婆,还会受到乡绅恶霸的欺负。女人的世界永远是家庭,她们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家庭的稳定和家族的延续,她们没有更多的想法,唯一盼望的就是丈夫赶快回来。女人的生活重心就是支撑家庭,这就决定了她们永远只能是等待,被动地等待。
第四,对人物关系的巧妙设置。大量的“苦情戏”中,“苦”的只是女性。男子最终都发达了,或是边疆立功,或是朝中做官。女人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平淡,甚至在丈夫走后还不如以往,她们贤惠、不幸甚至陷入苦难。男人的表现虽不尽相同,但他们是和女主人公构成冲突的对立因素,是形成矛盾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者对男子的处理方式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是属于看事不明。如秋胡,典型的健忘症患者。明知来到了自家桑园前,且看到一女子在采桑,竟没想到是自己的妻子;刘知远,新婚时与李三娘也是千般恩爱,后因李家兄嫂的不容而离家求发展,一走就是16年,且又娶了岳小姐,似乎忘记了在沙坨村还有个结发妻子李三娘。如果不是咬脐郎猎兔偶遇母亲,真不知刘知远何年何月会去主动接回李三娘与他同享富贵;薛仁贵离家18年归来,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他竟然没想到,见到妻子,还会为床底下一双男人穿的鞋而“无理取闹”。
二是属于故意为之。如薛平贵,离家18年后再见到王宝钏,为验证妻子的贞节,便以自己是薛平贵伙伴的身份,编造了种种谎话来吓唬王宝钏。自己在外18年且又娶了代战公主一事似乎丢到了脑后,一回来竟然就试探妻子。虽说试妻一出戏喜剧性很强,但当笑过之后,让人仍不免为男子的强势、霸道和女子的弱势、随顺而感到悲哀。
三是属于有意作恶。如张协、蔡二郎、王魁、陈世美之类,他们的举动本质上与薛平贵、刘知远等没有区别,但由于作者为后者设置了种种借口和转好的可能,因而他们的举动可以得到大家的原谅,而前者由于人性的泯灭和对妻子赶尽杀绝的疯狂举动,无法取得人们的原谅。最终的恶报也是他们罪有应得。
三、“苦情戏”大量出现的原因
首先,舞台上的“苦情戏”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现象的反映,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自母系氏族后,男性作为统治者就创造了男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爱情婚姻中,男性也一直处于支配地位。自周朝,男尊女卑成为一种被社会认可的价值判断。《周易·系辞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礼记·郊特性》也说:“男率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此后,经孔子、孟子及后来各朝各代的儒学大家、理学大家对男尊女卑思想的阐述,女性的思想行为受到进一步束缚。种种规章和规矩成为全社会奉行的经典,不光男人不觉得这样有何不妥,就连女性本身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束缚。女性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属性和主体意识被彻底泯灭了。她们只能适应男性文化的要求,维护男权社会的社会规范,按照男人的意志传宗接代,成为男权的附庸。表现在戏曲故事中,就是当男人提出任何主张或建议,女人不会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她们只是一味顺从,即使内心不情愿,也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出不同意见。
其次,是一种文化现象。“苦情戏”中有相当一部分男主人公是发达了的文人,而文人无良现象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隋炀帝大业年间建立的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大量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仕进的机会,也为无数家庭悲剧的发生埋下了隐患。科举及第者要想求得出路,必须依附达官显宦。而达官显贵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也愿意在新科进士中为自家挑选东床快婿。因此,一些寒门书生一朝发迹变泰,很可能引起婚姻关系的变化。陈寅恪先生谈到唐代富贵易妻的现象时说:“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姻,一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具为社会所不齿。……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2]整个社会都为这样一种风气所熏染,自然那些不管在社会上还是家庭中都没有地位的弱势女子,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和影响。另外,女子遭轻视、被淡化的命运在戏曲形成过程中就已表现出来:从魏晋南北朝时的“踏摇娘”“大面”,到唐朝的参军戏“三教论衡”,所表现的无一不是对女性的轻慢、侮辱,将女子作为取笑对象来对待。
再次,由观众的关注度决定。消费决定生产,消费促进生产。观众对悲欢离合的人生现象所表现出的强烈兴趣,促使了剧作家对这一领域题材作进一步开掘和表现。英国心理学家和文学理论家M·鲍特金说:“有一些题材具有特殊形式和模式,这个形式或模式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一直保持下来,并且这个形式或模式是被这个题材所感动的人的心灵中的那些感情倾向的某一模式或配搭相呼应的。”[3]戏曲追求的是演出效果,是情节的起起落落,是人物命运的升降浮沉。一般人对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生活不会格外关注,而对生活中的偶发事件则会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尤其是生活于封建时代的人们,缺少其他娱乐方式,唯一的娱乐就是看戏,而此时大家更愿意看到的是具有较强刺激性、震撼力的故事。从观众的心理分析,富贵人家的生活,与广大观众相去太远而提不起他们的兴趣,而普通贫贱的生活又因离他们太近而难以产生戏剧感和向往之心。只有那些在他们熟悉的生活的基础上又发生了变化的故事,才会给观众日常过于平淡的生活带来一些亮色和希望,给他们沉寂的内心带来一些起伏和变化。故事起伏的情节能够使他们的心高高悬起,而大快人心的结局又能使他们高悬着的心似一块石头落了地。所以说,这类故事在情节的设计和选择上与观众的心理做到了一致性和契合性。直到现在,电视屏幕上经常出现的“苦情戏”其情节上仍没有脱离古老戏曲情节的影响,也没跳出传统戏的窠臼。因为观众需要这样荡涤心灵的作品,需要这些为生活带来一些亮色和起伏的故事。
[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6:48.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2—113.
[3][英]M·鲍特金.悲剧诗歌中的原型模式[A].见叶舒宽编.神话—原型批评[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