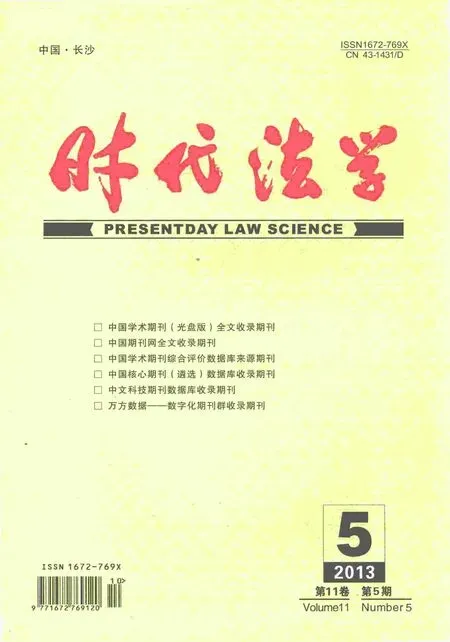杀抑或被杀:胁迫是否是国际刑法的抗辩事由——以著名的 Erdemovic'案为分析视角*〔1〕
姜 敏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一、国际刑法视野下胁迫作为抗辩分析
( 一)Dražen Erdemovic'案件
悲惨的Dražen Erdemovic'案经常被提及。年轻的Croat是无业锁匠,在1994年加入Srpska共和国军队。Srpska共和国起初是Bosnian境内的塞尔维亚实体,随后由领导。1995年7月16日,Erdemovic'和部里其他几个人被下令去Pilica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他被上司告知承载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的车辆将在一天之内到达。这些从Srebrenica来的男子在他们的聚集地陨落后已经向Bosnian Serb警察和军队投降。Dražen Erdemovic'是行刑队的一部分,被下令杀掉这些一字排开、十人一组的穆斯林男子。据Erdemovic'本人估计,他最终射杀了大约70多个人〔1〕判决书,Erdemovic'(IT-96-22-T),审判分庭,1996年11月29 日,§78(以下简称‘判决书,Erdemovic'’)。。
但是——根据他本人被检查机关认可的陈述〔2〕检方似乎并没有为了证实或反驳他陈述的事件而尽力取得Erdemovic'其他战友或上司的证词。Erdemovic'随后在ICTY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对抗被告。——Erdemovic'不愿意遵从这大规模的屠杀任务。他最初拒绝服从上司的命令,但随后被上司告知:“如果你不想这么做,那就站到剩下那一排人里面,把你的枪给别人,让他们开枪打死你。”Erdemovic'十分严肃地对待了这份威胁,他害怕如果自己不执行命令,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将面临危险〔3〕判决书,Erdemovic',前注1,§80.。
经此一役,Erdemovic'将自己的困境告诉了一位记者,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随后将他逮捕,并最终将他带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ICTY)投案。Erdemovic'出庭承认犯有反人道罪的指控。但同时,他告诉法官:
尊敬的法官,我必须这么做。如果我拒绝,当时可能就和那些受害者一同被杀掉了。当我拒绝时,他们告诉我:“如果你为他们感到愧疚,那就站到他们那边,我们也会杀掉你。”我是为我的家庭、妻子和即将满九个月的孩子感到愧疚而不是我自己,我不能拒绝因为他们会杀掉我〔4〕判决书,Erdemovic'(IT-96-22-T),审判分庭,1998年3月5日,§14.。
Erdemovic'根据他的认罪被定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上诉中,他声称自己的认罪无效,因为:他的认罪包含有有罪坦白与能否定有罪的事实陈述,因此其供述是模棱两可的。
程序性问题背后的实质性问题是:一个人如果由于受到生命威胁而犯罪,根据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使用的《国际刑法》,他是否有罪?上诉分庭中五名法官中的大部分人的结论是:如果军人涉及到滥杀无辜的反人道罪以及/或者战争罪,受胁迫不能够成为无责抗辩〔5〕判决,Erdemovic'(IT-96-22-A),上诉分庭,1997年10月7日,§19.。但Antonio Cassese法官与Ninian Stephen法官的结论达成一致——持反对意见〔6〕Cassese法官的独立与不同意见书,Erdemovic'(IT-96-22-A),上诉分庭,1997年10月7日(以下简称“Cassese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这一反对意见,因为Cassese法官非凡的分析能力和国际法的博学知识,使其得到了大量分析过Erdemovic'案件的学者的广泛支持。并且在此案中Cassese强有力地提出的原则,即“受胁迫可以成为无责抗辩,即使是涉及到谋杀的案件”,最终亦被纳入国际刑事法院(ICC)的《罗马规约》〔7〕《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31条(1)(d),ICCSt.请参见脚注17及以下的讨论。。
Cassese法官与大部分法官,尤其是与Gabrielle Kirk McDonald和Chand Vorah法官之间的辩论,关涉到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当仅存在极少数法律文件和判决能处理这个问题,同时各国做法大相径庭的情况下,与受胁迫相关的国际法原则怎样才能建立起来〔8〕McDonald法官与Vohrah法官共同意见的不同意见,判决书,Erdemovic'案(IT-96-22-A),上诉分庭,1997年10月7日,§§43-50(以下简称“McDonald法官与Vohrah法官共同意见,Erdemovic'案”);Cassese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前注6,§§11-46,对二战后法庭判例的详细讨论。?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被会对此进行辩论〔9〕对方法问题更好的解释,请参阅C.Kreß,“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对Erdemovic'紧急胁迫杀人案件的评论”,《刑事诉讼法学杂志》(ZStW)1999年第597卷第111期。。我也不在与受胁迫有关的习惯国际法的现行状况问题上表达任何立场——它从ICTY对Erdemovic'案件做出判决,尤其是判决原则被“国际刑事法院规约”采纳以来,其情况可能已经完全改变。
相反,我想在实质性问题上揭示一些东西,Erdemovic'案件重大的决定已经由判决书清晰地呈现。当一个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杀害了70个无辜的人,他是否应该被裁定犯谋杀罪?我用来描述Erdemovic'案的术语是‘胁迫’,是指一个人以即将来临的死亡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威胁另一个人(行为人)而使行为人犯下违反刑法所禁止的行为的状态〔10〕我将duress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留下了在何种程度下一个人受到胁迫的情况可以作为抗辩这个问题。。
我对问题的措辞表明,相比起用某个既定的法理对现行法中的胁迫进行界定,我对一般性原则更感兴趣,因为这种一般性原则能够解释因胁迫犯罪而侵害被害人的驱动,与对面临着我们永远希望不要但必须做出判决的当事人的同情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国际刑法》中的特殊规则?
Erdemovic'案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这使得难以对其刑事责任进行清晰认定,其中有一项是处理案件的“国际”因素方面。就McDonald法官和Vorah法官的共同意见是:与国内刑法相比较,他们在国际法上主张更严格的责任标准:
我们并不关注国内恐怖分子、帮派领导者和绑架组织的行动。我们必须关注的是:为人类所知的最十恶不赦的相关犯罪中,我们信任的法律原则对持有杀伤性武器的士兵和控制他们于武装冲突中的司令官的其相应的规范性效力……我们尤其关注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及其有效性,以及通过对刑法应有的规范性效力的认知来促进它的宗旨和应用〔11〕McDonald法官与Vohrah法官共同意见的不同点,Erdemovic'案,前注8,§75.。
McDonald法官和Vorah法官明显比较“激进”,将国际刑法作为推动社会政策的一种载体,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战时犯罪行为的应用”。〔12〕McDonald法官与Vohrah法官共同意见的不同点,Erdemovic'案,前注8,§78.因此,法官着手于塑造受胁迫辩护的范围,而且即使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也不会显著地减少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约束。在他们看来,国际刑法的规范性效应,应该是在武装冲突中对侵犯公民利益的行为建立一种强大的抑制作用。Cassese法官断然拒绝这种“激进”方法:
我们的国际法庭是法律的法庭,一切都要受国际法的约束,因此应当避免从元法律来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在刑法领域以政策为导向的做法有悖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13〕请参阅Cassese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前注6,§11(ii)。一些评论家赞同Casses法官的观点,请参阅K.Oellers-Frahm and B.Specht,“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Erdemovic'法律”,《公法与国际法比较杂志》1998年第389卷第58期;E.van Sliedregt,《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刑事责任》(T.M.C阿赛尔出版社,2003年),第290页;A.Fichtelberg,《国际刑法中的自由价值观》,“国际刑事司法(JICJ)”2008年第3卷第6期,第14页。
Cassese法官的说法可能过于宽泛,以政策为导向对法律的解释本身并不违反“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只要法官不超越所适用法规或其他法律文书的条款的公正含义,他/她就可以考虑法律规范背后的政策。但是Cassese对任何以政策为导向的司法“创造”或过度扩张对被告不利的刑事禁令的批判是正确的〔14〕McDonald法官和Vorrah法官最终将绝对道德作为拒绝受威胁辩护的基础而不是受政策引导。请参阅McDonald法官与Vohrah法官共同意见的不同点,Erdemovic'案,前注8,§83.对比R.E.Brools的精确分析,“在黑暗中的法律:暴行&胁迫“,《弗吉尼亚国际法杂志》2003年第861卷第43期,第878-879页。。同样,在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的维护中,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并没有提供对根植于刑法基本原则的有效抗辩的否定的可靠基础。正如Paola Gaeta指出,为什么在国内的刑事司法系统通常被认可的抗辩不能在国际刑法中得到认可,这没有什么理由〔15〕P.Gaeta,“紧急避险可否成为审讯恐怖分子嫌疑人酷刑的辩护?”,(JICJ,2004)第785卷第2期,第790页。。
(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胁迫”
由Erdemovic'案引发的关于受胁迫的争论对负责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最终提交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31条(1)(d)的文本〔16〕第31条ICCSt.阅读:“排除刑事责任的理由。1.除本规约没有规定的刑事责任的其他理由,任何人以下行为都不承担刑事责任:…(d)在法院的司法管辖权范围内构成犯罪,由来源于自己或他人即将来临的死亡、持续的或者即将来临的严重身体伤害的胁迫,行为人必要地、合理地避免以上威胁的行为,考虑不愿造成比尽力避免所造成的伤害更大的伤害。这种威胁也可以是:(i)由他人所造成;或者(ii)该人无法控制的其他情况所构成。”,该条试图在一个规范中涉及不同的实际情况〔17〕关于批评,请参阅A.Eser,“排除刑事责任的理由”[《罗马规约》第31条],注49,主编为O.Triffterer的《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版,哈特出版社,2008年),他认为,第31条(1)(d)缺乏引导并最终尝试失败,其是最不具有信服力的条款,它试着将两个不同的概念结合(证明紧急避险仅仅为受胁迫辩解)。也可参阅K.Ambos,“《罗马规约》中刑法的一般原则”,《刑法论坛》,1999年第1卷第10期,第28页;I.Bantekas,“国际刑法中的辩护”,由D.McGoldrick,P.Rowe and E.Donnelly主编的《常设国际刑事法庭》,哈特出版社,2004年第263卷,第274页.。此外,对辩护的规定不是基于1998年可能存在的任何国际习惯法〔18〕但是参见G.Werle,《法不治罪》(第三版,Mohr Siebeck,2012),于旁注601,声称第31条(1)(d)ICCSt.“毋庸置疑地”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而是基于一种愿望,通过对不同概念的辩护和根植于不同国家传统的辩解的融合,来满足大家的要求〔19〕关于有教育意义的立法程序说明,请参阅M.Scaliott,i“国际刑法法庭前的辩护”,《国际刑法评论(ICLR)》,2011年第111卷第1期,第153-158页。。为了绕过意识形态的冲突,起草者通常使用术语“排除刑事责任的事由”,并避免对辩护的系统定序。这使得在规范合理诠释的系统环境下,对受胁迫或者紧急避险的情形无法得出结论。可以使行为人受胁迫行为正当化的辩护的解释,应当与对行为的违法性没有如何影响而仅仅提供个别的宽恕的辩护的解释区分开来。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31条(1)(d)的要素与之前曾经盛行的受胁迫辩护的特性,至少有三点重要区别。第一,第31条(1)(d)将由非人类来源造成的紧急避险的辩护,与由人类造成威胁的胁迫的辩护融合,虽然许多国家制度曾经将这些辩护区分〔20〕参见以下例子:《法国刑法典》第122条-2,第122条-7;《意大利刑法典》第46条,第54条;§§2.09,3.02,美国法律研究所模范刑法典。。第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这项条文,偏离Erdemovic'案的大部分观点和英美传统之处,在于它不包括在受胁迫的情形下当事人实施杀人的刑事责任〔21〕比照,A.Ashworth,《刑法原则》(第六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第212-215页(英法总结);W.R.LaFave,,《实体法刑法》(第二版,ThomsonWest公司),第74-83页(美国法律的总结)。。第三,第31条(1)(d)从当事人角度的设立了一个柔性的相称性要求〔22〕与通常的紧急避险规定相反(例如,§34,德国刑法典;§3.02(1)(a),美国法律协会制定的《模范刑法典》第31条(1)(d)ICCSt。,这与紧急避险(罪恶之选择)的辩护一致,但不一定与受胁迫的辩护一致〔23〕请参阅第2条(C)所示。。
在这些创新中,由人类原因和非人类原因引起的威胁合并是最没有问题的,因为罪恶的事实来源不具有很大的规范性意义。尽管与Erdemovic'案大部分观点相反,假设在必须满足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包含谋杀在内的案件,受胁迫可以为其开脱责任,这也是被认可的〔24〕请参阅所附脚注64及以下文字。。主观比例要求(要求本人不愿造成更大的伤害)是这种辩护在普通法规的典型特性〔25〕请参阅K.Ambos,《国际刑法》(第三版,C.H.Beck,2011),第202页。关于该特性关键性的评价,请参阅E.Mezzetti,“排除刑事责任的理由”,F.Lattanzi和W.Schabas(主编),《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约的讨论》(第二卷),Il Sirente,2004年第143卷,第166页。。如果行为人对事实认识错误,其可能会导致意外的结果,但不会干扰辩护的逻辑〔26〕例如,一名士兵如果由于一个很容易避免的错误,认为他由于健康遭到威胁而作出的行为只会对财产造成损害,但实际上杀掉了数名平民,而免于谋杀罪的刑事责任,。然而,第31条(1)(d)最有问题的方面是相称性要求(其规定:行为人不能故意造成比其尽力寻求避免的伤害更大的伤害)。这适用于所有国际犯罪,并且因而限制了以一命救一命(或者数命),或者放弃一方面挽救另一方面这些情形的辩护。正如我们所见,这种严格的限制与受胁迫的各种辩解不相称〔27〕关于相同的观点,请参阅R.Merkel,“在国际刑法排除刑事责任的理由”,《ZStW》,2002年第437卷第114期,第254页.。
根据《规约》第31条(2)的含义,重新区分《规约》设立者在第31条(1)(d)中所选择并混合起来的对各种辩护的要求,最终将成为法庭的任务。接下来,对此任务我的目标是致力于为受胁迫辩护的可能要求制作简要的提纲〔28〕第31条(2)ICCSt。规定“法院应当在本规约的前提下,案件排除刑事责任的理由提出之前决定它的适用”。。
二、作为正当化事由的胁迫
胁迫是否能提供正当的辩护事由或者宽恕,其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29〕请参见例子Ambos,“刑法的一般性原则”,前注17,第27-28页;L.Chiesa:“胁迫、英勇主义与相称性”,《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2008年第741卷第41期,第744页。。我的主张是:胁迫是否是正当化的辩护事由或者宽恕取决于当时环境,而且成为正当辩护事由或者宽恕这两种情形有着很大的区别〔30〕有关相似方法,请参阅Van Sliedregt,前注13,第289-290页。。
(一)胁迫与正当化的逻辑
比起这种情形的任何其他结果,如果法律更倾向于犯罪的实施,那么原本为犯罪的行为就是合法的。例如,在正当防卫案件中,比起被袭击的受害者被杀害或者受伤,法律倾向于行凶者被打击。任何正当化的理由都能让当事人有权实施原本为犯罪的行为;同时,其也给正当化行为的受害者赋予了法律上的义务——例如,为自我防卫创造机会的行凶者——会在沉默中败诉。这种期望的合理性可能是受侵害者事先不合法的行为(就如正当防卫或者警察逮捕逃犯的情形),也可能是为同胞提供互帮互助的一般性义务。
团结互助的义务解释了紧急避险行为的正当性。如果我为了灭掉正在我家肆虐的大火而打破了不在家邻居的玻璃,并拿出他的灭火器,我的行为因紧急避险而合理;我的邻居不能阻止我的行为的理由是:法律的预期是他应当放弃自己少量的财产利益以此来避免我财产利益更大损失〔31〕有关紧急避险这一理论的解释(紧急状态),请参阅M.Pawlik,《紧急避险》(Walter De Gruyter,2002),于57及以下;也可参阅R.Merkel,“骑墙派?关于刑事法理学的哲学论证”,刑事科学研究所:“Vom unmo lichen Zustand des Strafrechts”(Peter Lang,1995)第171卷,第178页及以下。。我的邻居的义务的缘由不单是因为这种犯罪行为“两害取一轻”或者这种授权产生了“净利益”(他的窗户碎了,但我的房子还在),而是因为他对这种“净收益”的产生不负责任。只有当同胞生活中的至少应该保持最低程度的团结原则要求这样,法律才可以强制公民放弃其最小的利益。这意味着损失的利益与挽回的利益的差值必须很大才能触发这种义务〔32〕会给予对牺牲义务的社会伦理解释。也许罗尔斯的思想是最为合理的。在文中假设的烧毁房屋的例子中,如果一个理性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房屋面临烧毁,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这个灭火器的所有者或者这个被烧毁房屋的主人,他很可能预先同意放弃灭火器和窗户的完整性,来交换类似的帮助。。
考虑到辩护的一般性理解,受胁迫的情形能否为被他人强迫犯罪的犯罪行为辩护?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假设像Erdemovic'案的情况,在这种案件中当事人没有任何选择来避免冲突。除非当事人按照命令犯罪,否则他肯定会被杀害或者受伤。假设Erdemovic'被告知(可信的)他的妻子和孩子会被杀害,除非他虐待一个穆斯林监狱犯;如果他屈服于这份胁迫并虐待了这个监狱犯,因此挽救了他爱的人的生命,我们能说他的做法合理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很难发生在监狱犯身上,如果这是挽救两个生命的唯一方式,则法律希望他忍受虐待——利益的均衡强烈支持Erdemovic'采取行动,监狱犯健康和尊严的利益必须中断〔33〕同意施刑者行为合理,并不意味着强迫他触犯这个行为的人也不受惩罚。至少在德国,他会因作为间接正犯而因施刑被定罪。请参阅 B.Schünemann,“§25 旁注75”,由 H.W.Laufhütte,K.Tiedemann 和 R.Rissing-van Saan 主编的 Strafgesetzbuch.Leipziger Kommentar(第一章)(第十二版,Walter de Gruyter,2007)。。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犯罪能正当化;但是这种合理性需要实施犯罪所挽回的明显利益,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受害者才能够公平地被期待牺牲自己的利益〔34〕这个要求远高于Cassese制定的比例要求:“所犯的罪行与威胁危害不相称(例如,这发生于为了避免受攻击而杀害)。换句话说,为了使其不会不相称,受胁迫下的犯罪行为必须权衡利弊,在两害之中取其轻。”请参阅Cassese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前注6,§16。。
(二)反对观点
两种观点反对这种结论。在Erdemovic'案的共同意见中〔35〕McDonald法官与Vohrah法官共同意见的不同点,Erdemovic',前注8,§74.,比起James F.Stephen,McDonald法官和 Vorah法官依旧主张〔36〕J.F.Stephen,《英国刑法的历史》(第二卷)(麦克米伦公司,1883),于107-108。:
一个人可能面临两难,这当然是他的不幸[即:因为不遵守命令会被威胁杀害,或者遵守命令但触犯法律],但如果因为不执行命令而受到死亡、暴力相威胁的动因而有罪不罚,这将是整个社会更大的不幸。如果有罪不罚因此而得到保证,这将为串通行为打开一扇大门,并给与作恶的、秘密的和其他方面的团体鼓励。
邪恶的上司对他的下属“给予有罪不罚”——并且想必他们应是这样的结果——通过强迫他们执行非法的命令,这是真实的吗?这可能是James Stephen先生写论文时的情况。但在此期间,间接正犯、帮助犯〔37〕指挥官胁迫士兵杀害平民的行为肯定会被第25条(3)(b)ICCSt中所禁止的“命令”犯罪所包含,并且也可能是在第25条(3)(a)中“通过他人”的形式犯下。,而且——作为最后的手段——指挥官责任的概念已经得到发展,至少上司不能逃避处罚,因为他的刑事责任不取决于下属的刑事责任。就Drazen Erdemovic'案下属处于不利的处境而言,如果他勾结上司,明知不从命令会被杀害的胁迫仅仅是表象,那他毋庸置疑应受惩罚。另一方面,如果对士兵生命的胁迫是真实的,那么指挥者非法的胁迫是造成士兵有罪不罚,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其也是正确的,但这种结果的原因要受胁迫情形辩护的影响。
Luis Chiesa针对受胁迫行为的辩护理由提出了另一个反对意见。他声称,当衡量造成伤害的比例时,“也应当以替代这些胁迫的方式来考虑。当事人实施不合法的、十恶不赦的犯罪来帮助别人”,〔38〕Chiesa,前注 29,于 769。和“除了牺牲和救活的生命数量,必须衡量胁迫情形下不合法行为的协作当事人本身的犯罪意图”。〔39〕同上,于770。但一个女人与用枪指着她头的持枪人“协作”,她遵从持枪人的命令是否“帮助”了他?Chiesa选择用来描述这种状况的术语似乎非常不合适。从纯粹客观主义立场看,可以说受胁迫女人的行为导致了胁迫者希望发生的结果;但“帮助”与“协助”仅仅需要这样?不需要至少与胁迫者计划的认同和串通的意愿的最小值吗?
一些德国学者〔40〕请参见例子 W.Perron,“ §34 旁注 41b”,由 A.Eser主编的:Schāoke/Schroā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第二十八版,C.H.Beck,2010);由 J.Wessels和 W.Beulke主编的《刑法总则》(第41版,HüthigJehleRehm,,2011),旁注443通过对被迫杀人的受害者的处境进行分析,已经从Chiesa的观点得出相似结论。难道受害者不应当保护自己免受被强迫女人的袭击?答案就在受胁迫最低互助原则和随之而来的合理比例的高标准。回到Erdemovic'案,如果他被受虐威胁,初非他击倒一个无辜平民,这个平民可以通过正当防卫合法地抗拒Erdemovic'的伤害,即使Erdemovic'由于被胁迫而造成的伤害比Erdemovic'可能造成的伤害更严重。但是如果根据上面的例子,如果Erdemovic'没有服从非法的命令,他的家人都一定会死,而受害者没有权力为他自己辩护〔41〕但是,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在这种情况下Erdemovic'——缺乏自主决定权——可被比喻为是受害者健康风险的自然原因。当他必须保护自己健康的,可以依赖于紧急避险的辩护。。
(三)杀害能正当化吗?
这些因素在受害者生命危在旦夕时会改变吗?受胁迫可以为杀害辩护吗?有几个因素抨击一个确定的答案。其中最无信服力的是“生命的神圣性”,其被英国法庭引用,当被控谋杀时,完全禁止把受胁迫辩护事由〔42〕在他们的共同意见中,McDonald法官和Vohrah法官提及一长串英国案例,当局引用“生命的神圣性”和“法律赋予对人生命保护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作为将受胁迫作为指控谋杀的辩护的主要论据。特别见于R v.Howe and others[1987]AC 417,1 AII ER 771,785(1987)。请参阅“McDonald法官与Vohrah法官共同意见的不同点”,Erdemovic',§71。。在Dudley和Stephens案〔43〕R.v.Dudley与Stephens案件[1881-5]14 QBD 273 DC,AII ER。在Dudley与Stephens案件中,受害者的杀害是由自然因素引起(通过紧急避险与一般法下受胁迫的传统区分,使得这成为紧急避险案件)。但问题可能会与此相似,假如,如果一位在救生船的乘客将Dudley与Stephens威胁于枪口之下并胁迫他们杀害Parker,即船舱男孩。的典型紧急避险案件中,如果可以通过杀掉一个人来挽救三条生命,那“生命的神圣性”就不是刑事上禁止杀害从而挽救三条生命的合理依据。在一个世俗国家,也不是人类不能通过扮演上帝的方式决定谁生谁死的宗教规则,就可以为为谋杀定罪的可靠基础;其特殊地适用于当事人牺牲一个人挽救多条生命的情形。
但是任何以受胁迫作为抗辩的上诉必须以团结原则的限制为终点。我们可能都愿意提供我们的财产,甚至忍受暂时的疼痛,来挽救生命;但大多数人会——在无知之幕的背后——拒绝为他人着想而放弃生命,即使其对社会有极大好处〔44〕有人可能会争辩,战场上的士兵——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志愿服务于武装斗争——确实作出了这个决定:为了他人的好处而牺牲自己。但是保护国家的集体努力,可以很好地与一个人为了他人和士兵而牺牲某人的生命的情形区分,即使他们明确并且认可对他们生命的威胁,一般也会有从战场上返回的合理期待。。法律也没有规定或者期待他人牺牲生命的正当理由,即使其他人会因此获救。因此,杀害一个人不可能合理,即使行为人被威胁于枪口之下,如果不执行射击他人的命令会被杀害。即使是本身的功利计算也不能胜过每个人的生命权。如果我们假设,一组十个士兵被告知他们会被处决,除非他们杀害一个无辜的监狱犯,那他们击倒监狱犯是不合法的。因为法律不能规定受害者为了士兵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生命〔45〕对比 K.Bernmann,《EntschuldigungdurchNotstand》(C.Heyman,1989),第341-345 页;Pawlik,前注31,第258-260 页。。
但是在Erdemovic'案的情形,近一步复杂的情形使我们踌躇。这些穆斯林犯人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站成一排等待被击毙,而且给予这一大批塞族士兵处决这些犯人的欲望与现状,他们的生命注定无法逃脱。即使Erdemovic'成为了一个英雄,加入了犯人的行列,他当时也会被其他士兵杀害,最多晚几分钟。由于这种事态,Cassese和Stephen法官认为相称性要求得到满足,于是Cassese法官善辩的指出:
因此,判例法看起来是这些诉讼的例外——在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不确定一个人在受胁迫的情形下拒绝实施犯罪,那在任何情况下犯罪都只能由除被告以外的人实施。这种案件最简单的例子是,尽管是在死亡的威胁下,受害者已经由集结的执行队杀害,并且被告在执行队中以某种形式参与,既可以是积极分子也可以是组织者。在这个案件中,如果执行队的一个人最先拒绝服从命令,然后遵守被胁迫的后果,他可能会被处决:的确,不论他是被杀还是参与执行,这些平民、战争中的犯人等,都始终会被击毙。如果他遵守法律责任不去杀害这些无辜的人,他会失去他的生命,除了树立人类的英雄典范(法律不允许要求他树立),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好处:他生命的牺牲也无济于事。这个案件中罪恶威胁(对生命的威胁和随之而来的死亡)将大大超过救济(他防止了犯罪,没有参与执行)〔46〕Cassese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前注6,§44.Stephen法官得出相同的结论:如果……证据与上诉人多次陈述一致,那么他的选择不是受害者的死亡或者自己的死亡,更确切的说,他们的死亡或者他自身和他们的死亡,整个比例问题是毫无意义的;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与其他人的生命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如果这可以被比作一个选择,则是许多生命或者许多生命加他自己的生命。请参阅Stephen法官的独立与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IT-96-22-A),上诉分庭,1997年10月7日,§19(以下简称“Stephen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也可参阅Brooks,前注14,第875页:“Erdemovic'是谨慎的、深思熟虑的;他正确的衡量了各种行动的利与弊。事实上,在严格的功利主义下,通过确保自己不成为受害者,他参与到大屠杀使得死亡的人数降到最低。”。
但将Erdemovic'案的事实行为(射杀70名无辜的穆斯林人),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Erdemovic'拒绝射杀犯人,接着与犯人一同被射杀)相比较,接着根据这种对事件假设的过程使其免罪,这样做合适吗?这不会打开相似的争论“如果我不做其他人也会做,所以我是无辜的”的诉讼闸门?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如我们上面所做——则不会有受害者根据法律的要求为了救Erdemovic'而献出生命,这难道没有为解释Erdemovic'的事实行为设立一道绝对的屏障,无视他拒绝射杀后的情形吗?假设Erdemovic'是少数有必要技术、能够躲在地下洞穴射杀70个无辜的人之一;如果Erdemovic'的生命被威胁,拒绝提供这项技术,则指挥官需要两个时间去寻找另一个专家。我们还会认为Erdemovic'的抗辩“受害者始终会死,所以我杀掉他们救活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我们至少还存有疑惑,而这些疑惑可能会延长受害者的生命。
因此Erdemovic'处境的关键性因素,可能不是Erdemovic'是执行队的成员,因此其可能被代替的事实,而是即使没有Erdemovic'决定去执行的情况下,受害者也可能只有几分钟的存活时间的事实。他们的剩余生命时间太短以至于根本不能进入相称性计算?是不是这意味着Erdemovic'的生命几乎为零?也许换句话说,法律要求一个人放弃最后一样东西——非常不情愿的——他三分钟的生命时间,来挽回一个在他面前有着明亮的很长未来的男人的生命,如果他被允许射杀这些受害人?
在德国,一项法规允许空军击毁任何被恐怖分子绑架并假设在飞行的飞机,就像911事件一样要撞入一栋建筑物或者其他地方,从而杀死地面上的很多的受害者。此项法规和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被广泛讨论〔47〕§14,德国航空安全法((Luftsicherheitsgesetz),授权德国国防部部长对飞机采取任何行动以避免灾难。§14(2)阐述,只有当飞机是被用于对抗危害人类并且使用武装力量是唯一能够避免当前危险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下,可以立即使用武装力量。。这条法律会给予国家代理人员杀掉被劫持飞机上无辜乘客的许可,Erdemovic'案件的难题,基于同样的理由:乘客无论如何都被注定了,在被劫持的飞机坠毁前几分钟的生命是没有存续的价值的。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否定了这种观点,并认为法条的有关规定违反了宪法应保障生命权和〔48〕第2条(2),德国基本法,规定“任何人有身体完整和生命的权利。”人类尊严的规定。法院明确拒绝由于乘客没有被希期望继续活下去而贬低其生命的价值的观点〔49〕请参阅联邦宪法法院2006年1月15日的判决,1 BvR 357/05,《联邦宪法法院判决》2006年第158卷第115期,第158页:“人的生命和尊严受到宪法平等保护,无论这个人的实体存在期间。任何人对此否定或者怀疑,否定了被劫飞机上身处危机且无路可逃的受害者因为人格尊严而收到的尊重。”。如果遵循这样的思路〔50〕对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明确留下的在刑法下9·11难题的适用解释,德国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请参阅同上,旁注130。请参阅例子M.Pawlik,“§14条第三款的航空安全法——打破了规定?”Juristenzeitung,2004年第1050卷;V.Erb,“§34旁注122-128”,由B.Con Heintschel-Heinegg主编:《慕尼黑刑法典评论》(第二版,C.H.Beck,2011年)1.,则Erdemovic'案的情形不具有正当性,因为即使犯人的生命与其他人的相比算起来已经没有几分钟,他们也不能被视为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尽管这种绝对的情形对于消除任何根据剩余生命的时间而化的线有很大的优势,但这将理论置于现实之上。如果有人可以问其中一个犯人,是愿意立刻就被Erdemovic'击杀,还是愿意两分钟过后由另一名士兵击杀,而他的牺牲可以挽救Erdemovic'的姓名,大部分人可能乐于放弃剩下两分钟的痛苦,即使他们并没有太关心Erdemovic'的个人命运〔51〕关于类似的被劫持飞机难题,请参阅Merkel,前注27,第452-453页。。
因此,根据当事人具体的、不同寻常的约定,我倾向于认定Erdemovic'的行为是正当的。但要我定义一种一般规则,即:当一个人的生命所剩无几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时,一个人通过杀害另一个人来挽回自己的生命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会使我为难〔52〕如果认可我的观点,大部分受害者不会有不同。因为每个人被期望放弃现存很短的生命时间来挽救Erdemovic',适用于不论100个受害者还是1个受害者。。当然,正当性也不能延伸到那种,当事人通过保持被动来给予受害者一天或者几个小时的生命的情形。让人深思的可能是:一个理性的受害者是否会倾向于坚持要维持那种很短时间的生命存续?
三、胁迫作为宽恕事由
受胁迫杀人无罪的理论可能表现得过度,并且根据我以上所指出,我不会在超越了不寻常事实的Erdemovic'案件上坚持它。那么,因为被迫犯罪宽恕他们是否合理?
在此,我们开始考虑在刑法中的宽恕的一般概念。就像防卫过当〔53〕请参阅《德国刑法典》§33:“犯罪者因为极度混乱、惊吓或者恐惧而超越了正当防御的范围,不应该受到惩罚。”或者对上司非法命令的错误信赖〔54〕请参阅第33条ICCSt。那样,宽恕与它们有相同之处,即当事人没有正当性地犯罪但过失责任可以大大减少的特殊情形。法律反对当事人的所作所为,并且被害人因此有自我防御的权利;但因为环境对当事人的巨大心理压力,他可能被宽恕于他的所作所为。防御过当就是一个例子,一个为生命安全担忧的人突然受到攻击,她使用少量暴力手段足以抵挡侵略,并且不应当杀掉攻击者。但因为突然的非法攻击造成的额外心理压力,这个人的罪责大大降低,法律因此宽恕她超越正当防卫和杀掉攻击者的界限。如果法庭在此案中判被告人无罪,并不意味着社会认可她的行为,而只是一定程度的同情。鉴于这种情形,许多人和被告一样比需要回击得更重〔55〕请参阅Chiesa,前注29,第752-753页。。
重要的是注意在得到宽恕的情形下当事人刻意地自愿地行动〔56〕比照S.Hanssen,“国际刑法中精神状态辩护事由”,《ICLR》2004年第83卷第4期,第95页,声称可以得到宽恕的情形——包括受胁迫——可以被描述为“非自愿”。根据G.A.Knoops,《现代国际刑法的辩护》(2008年第二版,Brill),第47页,受胁迫的事实根据源于当事人控制自己行为和自由意志能力的减损。也可参阅G.A.Knoops,“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对刑事抗辩的分歧”,由J.Doria,H.-p.Gasser和C.Bassiouni主编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制度:纪念Igor Blishchenko论文集》(Brill,2009年)第779卷,第783页,声称对于像受胁迫的情形而宽恕,“压倒性的外部环境造成如此的心理压力以至于没有理性的人能够承受它”。如果确实在这样的情况,受胁迫可以成为类似精神失常辩白的理由,而不是单纯的宽恕。。例如,对防御过当的宽恕适用于当事人知道她会杀掉攻击者并且自愿决定这样做的情形〔57〕与§33,德国刑法典有关,大多数学者认为即使当事人知道自己将会超越正当防卫的界限,即: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法,也可适用宽恕制度。请参阅F.Zieschang,“§33旁注49-52”,由H.W.Laufhütte,K.Tiedemann和R.Rissing-van saan主编的《莱比锡刑法典评论》(第二章),(第十二版,2006 年,De Gruyter)。。当事人根据环境的压力也有一种道义上的选择,她可以决定是否保持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这种(受限制的)自由使得受宽恕与辩护的情形相区分,例如精神失常或者法律上不可避免的错误。在后一种情形,当事人是不可能遵照法律的要求的,因为她可能无法了解到与之相关的法律,或者她的精神疾病妨碍她遵照法律的要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辩解是强制性的——惩罚她是极其不公平的,因为她无法遵照法律。相比之下,在受宽恕的情形下,如果当事人使用了特殊的自我控制或者约束,他原本是可以避免违反法律的。但是因为刑法只需要在有人没有达到社会行为的最低标准时作出回应,如果当事人没有辜负最高的道德期望,他可能会被原谅(被宽恕)。因为这些情形很少发生,如果法庭施行象征性的反对而不是判被告人无罪,一般震慑是不会被严重影响的〔58〕比照S.Yee,“Erdemovic'案判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质疑中的里程碑”,《格鲁吉亚国际法与比较法杂志》,1997年第263卷第26期,第297页(功利主义或者主张惩罚主义理论都不能否定将受胁迫作为谋杀的抗辩)。也可参阅Merkel,前注27,第454页。。
其显而易见,受宽恕理由的性质和结果与认定正当化事由的理由区别很大,其更加接近于仅仅减轻处罚的一种情节。法律制度是给予完全的宽恕还是仅仅降低在紧急应变情况下犯罪人的罪行,这实际上是个政策问题。前南国际法庭上诉分庭的法官之间的交流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宽恕和减刑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Erdemovic'案中,McDonald法官和Vohrah法官认为:“当一个被指控的人在受胁迫的情形下实施了禁止行为,他不应该被谴责,不应当承担完全责任,这是文明国家所认可的一般法律原则”,并把特殊困难情况下受胁作为降低处罚的情节予以充分认可〔59〕McDonald 法官与 Vohrah 法官共同意见,Erdemovic'案,前注8,§ §66,85。。相反,Cassese法官指出:“不论法庭允许减少多少控告,基本事实仍然是,如果要裁定他的行为性质,其行为仍然是犯罪,并认为他本应该有不同的表现”。〔60〕Cassese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前注6,§48.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两方都是正确的。通过给予被告人宽恕,法院认定他本应该有不同的行为,但他的错误是次要的,所以不需要受到惩罚。通过给予宽恕,法律显示出了表现道德的灵活性的方法。Cassese法官简要描述为:“法律基于社会对其成员合理的期待,它不应当设置硬性的要求人类实施殉难行为的行为标准,或者标立像犯罪那样任何低于这些标准的行为”。〔61〕Cassese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前注6,§47.
四、以“胁迫”为由宽恕一个人的条件
一个处于生命或者健康受到威胁情形的人,当处于一种不同寻常压力的环境,那么受到胁迫能得到宽恕吗?如果他决定为了他自己(或者他爱的人)的切身利益而不是做出正确的决定,放弃被要求实施的犯罪行为,我们会倾向于原谅他。这种原谅的倾向甚至适用于超越Erdemovic'案这种极端案件的情形,例如,一个人在受胁迫的情形下有一定的考虑时间,他按照要求杀掉了受害者,以此来保护他的身体完整而不是他的生命。宽恕的范围甚至应当在这种情形之上,即(不准确地)被描述为给予当事人别无“道德抉择”而只有犯罪〔62〕请参阅例子,Stephen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前注6,§54;Eser,前注17,旁注49。。在大多数受胁迫的案件中,当事人仍然有选择的余地。甚至是Erdemovic',即使危急对他是最严重的,也可以拒绝服从命令,使司令官继续对他威胁并射杀他,或者可以决定成为一名英雄,牺牲自己的生命〔63〕C.Fourne,t“当孩子超过他的父亲——国际刑法中允许的辩护”,《ICLR》2008年第509卷第8期,第529页。。在这种情形下,受胁迫的人总有一种道德上的抉择。尽管如此法律也会给予宽恕,这样做不是过度慷慨的行为,而是合理的决定:如果一个人因为选择不为陌生人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实施刑事处罚,这会设下一种不合理的高标准〔64〕关于这种观点的激烈争议,请参阅Brooks,前注14,第873-874页。。
然而,法律的制定者可以自由的调解拟制宽恕的政策。因为一个人在受胁迫下的情形所为,不会对无条件免责有道德要求,法律应当建立一些宽恕当事人的情节(而不仅仅是减轻处罚)。
这种情节可以考虑当事人面对的压力的及时性和强度。只有当威胁是针对当事人的生命,或者包含当事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威胁情形,甚至是涉及到对当事人自由或者行动的威胁,立法机关才可以决定给与宽恕〔65〕§35,《德国刑法典》给予一下情况宽恕:如果当事人为了避免对自己“自由”的风险而实施犯罪,但共识是:短期的自由剥夺是不能构成宽恕的充要条件;请参阅Perron,前注40,第35页,旁注8.。通常情况下,对当事人家人的威胁被同等视为对其本人的威胁,但并没有对其所爱的人的范围的明确规定〔66〕奇怪的是,第31条(1)(d)ICCSt并没有把对人的威胁的辩护限制在与行为人接近的范围内,而仅仅要求有“对本人或者他人即将到来的死亡,持续或者即将到来的严重身体伤害的威胁”。。在各种法律制度的不同立法中适用的一般标准是:承受惩罚的人是一个正常的、理性的、可能会诱发(严重)犯罪的人〔67〕Chiesa,前注29,第762及以下。创立了一种包含若干政策决策的“可以理解的选择”标准;也可参阅Eser,前注17,旁注56;Ambos,前注25,第203页。。
受胁迫而进行的宽恕与正当化事由的区别在于:它不限制于当事人的罪行要与威胁的伤害相称的情形。因此Erdemovic'如果因为被上司以受折磨威胁,除非执行命令而杀掉犯人,他应该被宽恕〔68〕第31条(1)(e)ICCSt.通过要求相称性而模糊了合法与宽恕的标准;请参阅Chiesa所做的批判,前注29,第750页。。但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和他被胁迫的伤害的总的不平衡可能成为否定宽恕的理由〔69〕在德国法之下,许多作家在总体不相称的案件中,偏向于(不成文的)法定标准的限制(§35,德国刑法典);请参阅Zieschang,前注57,§35,旁注62-63,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借鉴;也可参阅Chiesa,前注29,第757,767页。。因此,宽恕可能被保留——如果一个军人在以受折磨为威胁的情形下杀了几百个无辜的犯人。并且,这为立法机关(或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法院)根据或多或少或宽松或严格的流行于社会之中的标准来定义一个限度。
对于受胁迫宽恕的进一步例外情况可以适用于(经常被适用于)〔70〕请参阅《德国刑法典》§35(1)(2);《模范刑法典》§2.09(2)。:当事人对于自身造成的困境而难逃其责的情形〔71〕这种例外也被Cassese法官他的不同意见书涉及,Erdemovic'案,前注6,§17,第31条(1)(d)(ii)ICCSt中提及。通过要求紧急避险必须“由一个人无法控制的情形构成”而提及这种例外。尽管这种限制从字面上不适用于受胁迫的情形,如果当事人本可以通过对同伴更加谨慎的选择而避免受到胁迫的情形,法官可能仍然会否定宽恕。请参阅Kreß,前注9,第623页。也可参阅Fichtelberg,前注前注13,第15页,认为当事人由于缔约过失责任的原因,在这种情形应当受到责罚。。比如,一个人明知自己加入一个狂暴激进的人领导下的一伙恐怖分子,如果某个时候他不执行由恐怖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会被领导人以杀害相威胁,这是不会得到宽恕的。并且,这种例外的限制是灵活的。如果当事人应当预见他的处境,因此否定他的宽恕理由充足吗?或者他应当被宽恕,除非他明知(或者罔顾后果地)承担了风险?对于其他例外情况,问题应当由法律制定者来决定。
最后,如果当事人自动承受胁迫以此来保护的利益,是其在受胁迫情况下正将要计划毁坏的利益,这种胁迫不能被认为应当宽恕。某些专业人员,比如警察或者消防人员,当他们面临着专业人员应当防止风险时,可以期待他们不会放弃他人。比如,一个被教育过如何处理暴力犯罪情形的警察,被期待专业地处理这些情形。如果他屈服于一个武装强盗的威胁,杀死或者致伤了一名无辜的受害者,而不抵制犯罪,则他的宽恕请求不会被听取。但是,只有当某些专业人员面临危险,能够承受此危险并且被训练过如何处理时,这种公认的受胁迫宽恕的例外情形才能剥夺他们的宽恕。考虑这种情形:一个罪犯用枪指着一个消防员的头,命令他将一根燃着的火柴扔进干草堆,造成了灾难性的火灾。由于被抢指头的威胁不是一个消防员认可承担的风险,也没有被训练过如何面对这种情形,当这个消防员被指控纵火时,他可以要求(至少)宽恕,因为受到胁迫。
根据对Erdemovic'案件的分析,许多学者认为基于受胁迫的宽恕是不成立的,因为Erdemovic'作为一名军人,有着保护生命的特殊义务,包括那些无辜平民的生命〔72〕McDonald 法官和 Vohrah 法官的共同意见书,Erdemovic'案,前注8,§84;Yee,前注58,第298 页;Oellers-Farhm and Specht,前注 13,第408 页;Chiesa,前注29,第29 页;Eser,前注17,旁注57.。根据前几段的区分,我认为这种观点缺乏信服力。士兵有责任对抗摧毁敌军;当战争法禁止他们攻击平民,他们——不像军人——没有保护,服务公民的特殊义务。此外,一个军人负责勇敢面对敌人的攻击,并且他被训练以应对这种攻击;但是他的训练并不能让他准备抵制自己上司或者其他敌军成员的非法威胁〔73〕H.van der Wilt:“国际刑法中的辩护与宽恕:对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判例的评价”,由B.Swart,A.Zahar和G.Sluiter主编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遗产》,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5卷,第293页。。因此,Erdemovic'案情中的士兵,不能以其专业责任为借口从而排除其以胁迫请求宽恕的权利。
五、结论
这种分析会给Erdemovic'案带来什么影响?他的行为可能是合理的,但这取决于案件确切的事实。同样,Erdemovic'可能有请求宽恕的权利,但他可能没有绝对的根据。尽管他发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因此进入受胁迫宽恕的法律条款规定的处境,但有两个事实与他背道而行。他自愿与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签署协议,本可能(或者应当)知道他这样做加入了经常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军队;并且Erdemovic'为了保护自己生命而杀害的人的数量很大(但他们的剩余生命时间很短)。在Cassese法官看来,他明确指出这两个因素需要在Erdemovic'案判决之前得到进一步阐明〔74〕Cassese法官的不同意见书,Erdemovic'案,前注6,§50。。
如果Erdemovic'被突然发生在他身上的超越他控制的事件影响,他可能得到宽恕。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在他决定加入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哪一天,他的悲剧已经不可避免。正如Rosa E.Brooks曾经对这个问题精辟的总结:
至Antonio Cassese:Erdemovic'的故事是必然的,是道德运气最差的。Erdemovic'被困于超越自己控制的事件,他就像棋盘上的一颗棋子那样没有更多的自由:他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某一天单单地发现自己处于无法维持的局面……大多数人将Erdemovic'当做一个失败在很早之前就开始的,但只在Srebrenica中得以圆满的道德代理人。根据这种观点,Erdemovic'的犯罪可以追溯到几年前;他的犯罪是坚持的立场以及对某种组织和个人忠诚的重复失败〔75〕Brooks,前注14,第881页。Brooks也指出无罪开释Erdemovic'有着很大的政治压力,因为“惩罚Erdemovic'是纪念Srebrenica受害者悲痛的唯一机制……总有人必须受到惩罚,而他就是那只待宰羔羊”。同上,第885页。。
最终,胁迫不过是一个词,有一个柔软的核心和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即使法官努力用概念使判决达到公平公正,事实仍然是刑法不擅长于处理冲突的情况,刑法典不是面临艰难抉择的人的最佳道德指南。Dražen Erdemovic'案件足以证明这个发人深省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