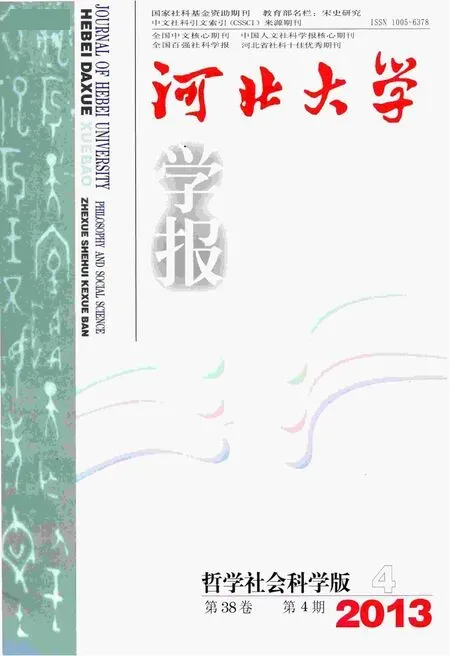宋代地方豪民与政府的关系
贾芳芳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中唐以来,伴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不少人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土地和财产的主人。到了两宋,由于“不抑兼并”国策的推行,民户贫富分化也呈加速之势。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豪民以其不同于普通百姓的财、权、势优势①综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对豪民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胡昭曦、王曾瑜、朱瑞熙、林文勋、张邦炜、邓小南、梁庚尧、黄宽重、王善军、张文、刁培俊、贾芳芳等人。他们对豪民的研究(限于篇幅,诸位先生的论著篇目不再一一列举),就其观点来看,主要大致分两大类:一类是强调豪民作为乡村社会精英,在国家赋税、灾荒救济中的积极作用;另一类是突出豪民作为违法犯忌者,在地方武断乡曲、为非作歹的消极作用。但对宋代豪民的主流身份特征,目前学界尚无专文。,逐渐成为影响基层社会的特殊群体。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诸多事务,都在其参与下定格或发生变化。当然,无论豪民的财、权、势如何与众不同,从根本上决定其影响力与性质的,则是其与政府或合作或斗争的关系。
一、地方豪民的特征及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
宋代地方豪民的主体是形势户,即品官之家的官户和富裕的吏户。但其整体背景相当复杂,有的不属形势户,也算豪民。宋代地方豪民主要包括,地主、地主兼商人、官宦、胥吏、讼师、一些经黥配之后的恶吏等。在宋代的文献中有称豪右、豪强、豪民、大姓和豪家的。豪民与普通百姓的区别,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豪民有政治背景,常以此在基层社会作威作福;二是豪民有经济实力,可以借此在基层社会施加影响;三是豪民有武力做威慑,他们豢养爪牙,用武力欺压良善。
(一)豪民的政治特征
宋代的地方豪民,相当一部分是官户或者富有的吏户,即使其本身并不为官,也常与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与皇族和后族有联系,故其在政治上有依靠。豪民的政治背景,是他们区别于普通百姓,并可以在基层社会实施影响力的有力凭借。
1.本身的政治影响力。豪民以钱捐买官位,步入政治舞台。景德年间,陈留县大豪卢澄,“常[尝]入粟得曹州助教,殖货射利,侵牟细民,颇结贵要,以是益横”[1]6657。南宋顺昌豪民官氏次子,用掠夺来的财富,“纳粟得官”“任鄱阳西尉”[2]409。捐买官位,不仅提高了豪民的社会地位,也为豪民带来了经济财富。
还有一些豪民的政治影响力,来自于家族,如品官之家的官户或富裕的吏户。他们因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而豪横无忌。北宋时,浦城县“多世族,以请托胁持为常,令不能制”[3]10419。陈尧咨知长安府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二千石鲜能治之者”[4]134。睦州遂安县“有恃荫暴横闾巷间”者[5]202。对于有着超过自身政治权力的豪民,地方官对其只能姑息纵容。
豪民中的另一部分人是寄居地方的官员,他们凭借上下联通的政治影响,暴横于基层社会。治平年间,寄居郓州的王逵“干挠州县,本路之人比之盗贼。但干有利,无不为者”[1]3860。不仅如此,王逵居乡还“持吏短长,求请贿谢如所欲”[3]10622。寄居者的政治影响力,令地方官对其“为害乡曲”[1]4045、持吏短长姑息迁就。政和年间,提举洪州玉隆万寿宫曾孝蕴居池州,“干扰州县,侵夺民田”[1]3927。开禧年间,宫观官项安世“阴险凶残”,居家“武断一乡”[1]4063。
2.与各级地方官员的关系网。不少豪民通过其家族和乡里官员,同地方官员建立联系。政治关系即政治背景。南宋时,新贑县豪民曾千龄,先利用知县韩元卿的贪欲,与之结识。后又“以孤遗侄女与元卿之子结婚”。自此通家出入,请求关节,武断乡曲,“官府不问,法令不加”[6]606-607。盘综错节的关系网,使豪民往往能得到地方官的庇护,“其上世有恩于我,我今居官,终不成以法相绳,遂宽释讼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无所告诉”[7]2736。
凭借政治关系网,豪民的气焰更加嚣张。南宋中后期,有豪民“把持士人数辈,控胁本州官吏,形势之家侵害闾里”[6]603。东阳豪民蒋元广“在州则交结黥吏俞鉴等,以通腹心之谋,县吏望风惮之,罔不惟命。一方善良,吞声饮气,谁敢与之抗衡”[2]424。新贑县豪民曾千龄豪横乡里,“两乡几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财货”“必多牵引”“拥高赀,据大第,歌童舞女,美衣鲜食,以匹夫而享公侯之奉”[6]606-607。
3.中央大员的靠山。还有一些豪民与中央官员有联系。与中央大员的交情,成为其肆虐基层的政治凭借。雍熙年间,秦州豪民李益“厚赂朝中权贵为庇护,故累年不败”。及秦州推官冯伉“屡表其事,又为邸吏所匿不得达”。后来因为其它的事,皇帝亲自下诏捕之,但“诏书未至,京师权贵已报益”[3]8949。真宗时曹州豪民赵谏,“多与士大夫郊游”[3]9871。在被捕系狱后,“搜其家,得朝士内职中贵所与书尺甚众,计赃巨万”[1]6584。豪民与官员的勾结,于辇毂之下完成。
对于此类豪民,地方官员往往不敢招惹。大中祥符年间,权知开封府刘综就说,“贵要交结富民,为之请求,或托为亲属,奏授试秩,缘此谒见官司,颇紊公政”[3]9433。通天的政治背景,对于地方小官来说,是惧怕的。更有不少地方官直接攀附豪民门下。神宗时,郑膺寄居秀州华亭县,因其为吕惠卿的舅舅之故,一路监司“如王庭老之辈皆卑下之,而招弄权势,不复可数,至夺盐亭户百姓之地以为田”[8]6586。
(二)豪民的经济特征
除了在政治上有依靠,豪民在经济上也有实力,是大地主、大地主兼商人,是非贫弱者。强大财力,成为豪民豪横乡里的凭借。真宗时,抚州豪民李甲、饶英,“恃财武断乡曲,县莫能制”[3]10076。王益为临江军判官,“军多诸豪大姓之家,以财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挟为不法”[9]599。南宋东阳豪民蒋元广,“骤致富强,称雄一方”[2]423。雄厚的经济实力,令地方官不敢小觑。就连地方政权也因此为“豪户控持”[6]636。
具体来讲,豪民因经济实力而在基层社会实施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客观原因:
严重的财政压力,令地方官对经济实力雄厚的豪民,有着不得已的需求与依赖。绍兴二十三年(1153),温州布衣万春上书言:“乞将民间有利债欠,还息与未还息,及本与未及本者并除放,庶少抑豪右兼并之权,伸贫民不平之气。”高宗因顾虑“若止偿本,则上户不肯放债,反为细民害”,只是部分采纳了万春的建言[10]260。宋高宗的顾虑更是地方官员的顾虑。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0《新淦申临江军及诸司乞申朝廷给下卖过职田钱就人户取回》中提到的新淦县的例子,更为典型:
照得江西诸县惟新淦最为难治,二十年间为知县者十政而九败,为人吏者朝补而夕配。推原其端,皆缘财赋窘乏,入少出多。通一年计之,常欠二万余缗。官吏无以为策,只有恳求上户预借官物,县道之柄从此倒持,豪强之家得以控扼。请求关节,残害细民。苟有不从,便生论诉。[6]633
有宋一代的财政紧张,导致地方财用不足。面对着政府运转的经济需求,地方官员对豪家大姓的经济支持是真心需要的。灾荒年间豪民对救济的参与,就是重要一例。经济实力是豪民赈济灾民、帮地方政府渡过难关的必要条件。
优厚的经济利诱,令地方官难抵诱惑。豪民的财富,往往来路不正。贿赂官吏,他们常舍得投资。天禧二年(1018),河北都转运使李士衡知青州,临淄麻氏“具粟千斛以献”[8]2103。在豪民直接的经济利诱下,除了少数修身自爱的廉洁之士,大多数官吏都会受此污染。哲宗时,梅州“土豪缘进纳以入仕者,因持厚赀入京师,以求见(章)惇,犀珠磊落,贿及仆隶”[11]793。更有贪图钱财的官吏,因豪民的财货贿赂而与之勾结。豪民为非作歹,“而官司施行,每不能伤其毫毛,无他,豪断取财,不义致富,不吝钱、会,以结有求之吏,不惮殷勤,以结无识之士,不惜宝货,以结无耻之官”[2]392-393。
此外,豪民利用财力上下交结的“能量”,也令地方小官畏惧。豪民“财力足以搬使鬼神,毁谤足以欺惑王公,是以世之贤士大夫,亦有畏之者”[2]392-393。在此情况下,地方官被动地对其迁就。
(三)豪民的武力威慑
豪民的武力威慑,是其区别于普通百姓,武断乡曲第三个特征。豪民武力威慑的来源之一,是蓄养的恶势力。徽宗时,青龙大姓陈晊,“凭所持畜凶悍辈为厮仆”[5]203。豪民蓄养干仆为之爪牙,“日夜渔猎人家物产”,豪强资干仆之力,干仆凭豪强之势[6]606。南宋时,豪民陈瑛“交结配隶,而济其恶,主把公事,拿攫民财”[2]400-401。豪民武力威慑的来源之二,是结成利益集团的宗族等同党。豪民“交结同党为羽翼,蓄养无赖为爪牙”[2]406,以武力威慑一方。嘉定时,溧阳县“大姓夤缘相庄以自结,势尤横,颐指气使,官吏莫能违”[12]772。武力威慑是豪民暴横于乡间的重要凭借。
(四)豪民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
地方豪民凭借上述不同于普通百姓的财、权、势优势,在基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发展为影响宋代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群体。概况来讲,豪民在宋代基层社会的影响,可分两大方面:
一是轻财重义、乐善好施的“长者”。一些豪民借“高资巨产雄视一乡”[13]卷一五《余彦诚墓志铭》的经济优势,“发廪、捐金、疗疾、赈贫、造桥、砌路,遗迹不湮”[14]750,惠及一方的善举赢得了乡里“长者”的美誉。
南宋前期,汉州长者李发轻财重义,“遇岁不登,辄为食以食饿者”。在乾道年间汉州灾荒时,民“就食李家者,日至三四万人”。为表彰李家在地方的贡献,“州郡及诸使者始上其事,孝宗皇帝嘉之,授初品官,其后孙寅仲登第,唱名第三世”[15]卷下《救荒报应》。在此美誉的基础上,豪民频繁参与基层事务的决策。衡州花药山崇胜寺法堂修建时,大家意见不一,“于是召州之大姓、长者相与谋”[16]卷七《花药山法堂碑》。凭借着道德宽厚公正等影响力,豪民也积极参与乡里关系的调停。南宋豪民刘允恭“赋性方直,气象深厚,后生辈为不义事,必诘之,厉然见于颜面。以是乡之士大夫推为长者”“有争讼者或诣君求决,君则为之陈道理曲直、法令可不可,往往羞缩逊谢以去”[17]卷二○《刘令君墓志铭》。“轻财重义”,乡闾“仁厚长者”[18]卷三六《王延嗣传》,是此类豪民的身份特征。
二是仗势欺人、武断乡曲的“豪横”。与“长者”形象不同,还有一些豪民凭借财、权、势的优势,在乡间欺凌弱小,打骂地方官吏,甚者因小过杀人害命,对抗地方官府。而就其违法犯禁的主要特点来看,地方豪民就是武断乡曲的宋代黑社会势力。
雍熙年间,秦州州民李益为长道县酒务官,“家饶于财,僮奴数千指,恣横持郡吏短长,长吏而下皆畏之”,因推官冯伉不屈从于他的淫威,李益便遣奴数辈,趁冯伉在市中按行公务之际,“拽之下马,因毁辱之”[3]8949。由于地方官吏都不敢正视,豪民残虐细民就更无所顾忌了。宣和年间,朝奉大夫方邵夺同郡王之才“舍屋,怒其不从,又弯弓射其门”[1]3933。隆兴年间,潭州一张姓豪民“凶恶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杀不问。门前有一木桥,商贩者自桥上过,若以柱杖拄其桥,必捉来吊缚”[7]2657。势力膨胀的地方豪民,在基层社会以“豪横”的身份存在。
豪民是宋代基层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或以乡里兴建私塾、救济穷苦的“长者”形象,或以武断乡曲、左右地方政治的“豪横”形象,存在于基层社会。那么,豪民作为特殊的“民”,其身份性质究竟以哪种为主?除了豪民自身的素质决定外,影响这个群体身份主流特征的,还有那些?
二、地方豪民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是不能容忍出现与中央对抗的地方势力的,朝廷对之往往采取限制和镇压的方针。
(一)最高统治者的态度
宋太宗曾说,“朕今收拾天下遗利,以赡军国,以济穷困,若豪户猾民,望吾毫髪之惠,不可得也”[8]814。他曾将江南“有大姓为民患者”“尽令部送魁首及妻子赴阙,以三班职名羁縻之”[3]9416。并对惩治豪民的地方官进行褒奖。吉州有豪猾萧甲危害乡里,久为民患。知州梁鼎“暴其凶状,杖脊剠面徙远郡”后,得到太宗的赞赏,获“赐绯鱼”,并“记其名于御屏”[3]10057。宋太宗的态度,代表了北宋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宣和七年(1125),尚书省条下条:“诸非见任官,有贪恣害民,干扰州县,而迹状显著者,监司按劾以闻。”这是专门针对官户中的豪横者,徽宗予以批准[1]6542。
南宋时,抑制豪民的政策继续延续。绍兴十年(1140),高宗说:“朕观自昔,守令能抑强振弱者,始号循良。今豪右稍不快意,必中伤之。自今州县吏有能称职而或诬以非辜者,须朝廷主张,庶使 吏 得 自 效,而 民 被 其 惠 矣。”[19]725淳 熙 四 年(1177),寄居严州分水县的豪民王中实,率众闯入县衙,“围守三日”,欲殴击知县王斌。事后知县王斌遭论罢。孝宗得知后说,“如此则守臣亦可肆其无礼矣”“恐相仿效,不可不治”[1]3465。有宋一代,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决定了中央对地方豪民的政策。
(二)中央限制豪民势力的禁约
为限制豪民势力的膨胀,中央制定了许多抑制措施。首先看政治方面的禁约:
限制富民为官。咸平四年(1001)五月,真宗诏“自今三班使臣知县,不得以诸州衙吏及富民受职者充”[1]3468。天圣六年(1028)十月丁丑,仁宗诏“武臣毋得补富民为教练使”[8]2483。中央意图以此限制财雄闾里的富民,在经济上有实力后,又在政治上雄踞一方。
禁止官员与富民往来。为防止钱权交易,中央禁止官员与富民往来。大中祥符六年(1013)三月,真宗诏:“富民得试衔官者,不得与州县官属使臣接见。”[8]1820官员如敢为豪民请托,更为中央所不容。绍熙年间,明州富民厉雄欺凌乡民被查。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史弥正等人为厉雄求情于守臣高夔,被高夔弹劾于朝。光宗诏罢史弥正宫观之职[1]4023。中央也很明白,富民与政治人物的交结,是富民在拥有财富后,探求政治依靠的重要途径。
禁止官员卸任后,在曾任职地寄居。为防止地方官在曾经的任职地,利用政治影响扩大势力,中央制定了这样的禁约:淳化二年(991)十二月,太宗诏:“岭南诸州幕职州县官等并许携妻孥之任,秩满不得寄寓于部内,违者罪之。”[1]6497-6498《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外任官罢任未及三年而于本处(谓州官于本州,县官于本县)寄居者,徒一年。”[20]111这对于限制官户在地方势力的发展,显然有益。
严行约束官员子弟。对于豪民中官员子弟的恶行,中央也深恶痛绝。宋太宗曾下诏:“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检,甚为乡党所知,虽加戒朂曾不悛改者,并许本家尊长具名闻,州县遣吏锢送阙下,当配隶诸处。敢有藏匿不以名闻者,异时丑状彰露,期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3]13547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诏:“诸路州军县镇应文武官见居远任,家属寓止者,如其子孙弟侄无赖不干家业,即言行约束,苟不悛革,则并其交游之辈,劾罪以闻。”[1]6500中央希望通过来自政治上层的力量,来压制为非作歹的“官二代”。
除了政治上的禁约,针对豪民的经济禁约更加细致:如限制豪民侵吞、垄断公共财物。太宗时,允许“客旅”向开封官仓出售粮食,但“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及与人请求折纳”[1]5950。北宋后期的青苗钱借贷,规定“形势之家不当给”[1]4869。绍兴八年(1138),规定:“诸坊场以违碍人承买者,杖一百,诈隐者加一等。”这里的“违碍人”包括“见充吏人”[1]5248。
对于地方豪民仗势不纳租税的情况,中央也想了许多办法。如严惩不纳租税的豪民。太祖时,各县每年要造“形势门内户”的夏税账目[1]6371。形势户输租违期,则“别立版簿”,派专人依限督责[8]258。若还有不纳者,则重加处罚。“诸输税租违欠者,笞四十,递年违欠及形势户杖六十(州县职级、押录并户案吏人、乡书手加三等),品官之家杖一百。诸上三等户及形势之家,应输税租而出违省限,输纳不足者,转运司具姓名及所欠数目申尚书省取旨”[20]626-627。减免租税时,对以形势户为主体的豪民从窄。南宋中期的《庆元条法事类》卷47《赋役门一·违欠税租》记载:诸上三等户及形势之家,“其未纳之数,虽遇赦降,不在除放之限”[20]627。
对于豪民欺凌小民,中央也有许多约束政令。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诏:“江湖间贫民捕鱼,豪户不得封占。”[8]1708淳熙十六年(1189),户部郎中丰谊言,“沿江并海深水取鱼之处,乞许令众户舟楫往来,从便渔业,勿有所问,不得容令巨室妄作指占,仍旧勒取租钱”“豪强尚敢违戾”“择其首倡,重作惩戒。”得到孝宗批准[1]6557。此外,关于“形势之家”不得“辄置狱具”,也有明文的禁约[20]805。
在高度重视中央集权的宋代,为限制豪民势力过度膨胀,中央制定了许多禁约,并对一些为非作歹的豪民进行镇压。这对打压地方豪民的非法行径,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显然有益。但具体对豪民的或扬或抑,临民最近的地方政府的态度,则更为重要。
三、地方豪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与中央政府对豪民的态度不同,地方政府与豪民的关系复杂,有勾结,有摩擦,也有镇压。
(一)勾结
防范、限制和打击豪民势力过度膨胀,保护民众免遭其害,本属地方官府应尽之责,“受公朝委寄,观风问俗,锄奸卫良,乃其职守”[2]392。但在豪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诱惑和威势威慑之下,地方官府却与其勾结起来。对豪民的违法犯禁,地方官府岂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公然支持和庇护。
与地方官府的勾结,为豪民聚敛财富提供了便利。绍兴三十年(1160),臣僚言,临安府“钱塘南山士庶坟墓极多,往往与形势之家及诸军寨相邻,横遭包占、平夷,其子孙贫弱,不能认为己有”。豪民的兼并多由地方官吏“容情,擅行给佃”所致[1]6573。在地方官府的支持庇护下,大量的官田、私田被豪民所侵占。豪民拥有了土地,也拥有了土地带来的财富,经济实力更为膨胀。
与地方官府的勾结,为豪民霸占水利提供了便利。仁宗时,越州馀姚县“陂湖三十一所”“虽累有诏敕及敕令”“官司因循请托,或致受纳赂遗,令形势豪强人户请射作田”,致有“遂废水利去处”[1]4911-4912。治平三年(1066),都水监言,“诸处陂泽本是停蓄水潦”之所,“豪势人户耕犁高阜处,土木侵叠陂泽之地,为田于其间,官司并不检察”“致每年大雨时行之际,陂泽填塞,无以容蓄,遂至泛滥”[1]4914。对豪民的霸占水利,地方官府或不闻不问,或公然支持帮助。
与地方官府的勾结,为豪民逃避赋役提供了便利。宋高宗时,荆湖南路一带实行科配,“其间形势官户、人吏,率皆不纳,承行人吏又于合纳人户,公然取受,更不催纳。其催纳者尽贫下户,因缘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21]746-747。孝宗时,唐仲友上奏说:“催科既急,勾稽不明,形势鲜或谁何,下户重并追扰。”[22]3547赋税征收中贫富不均的状况,因豪民与地方官府的通同作弊,而更加严重。
与地方官府的勾结,为豪民左右司法提供了便利。大中祥符七年(1214),洋州豪民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诬其子为他姓而专其赀,嫂屡诉官,甲辄赂吏掠服之,积十余年,诉不已”[8]1685。英宗时,长安大姓范伟“积产数巨万”“出入公卿间,持府县短长,数犯法,至徒流,辄以赎去。长安人皆知伟罔冒,畏伟不敢言。吏受赇者,辄为伟蔽匿”[23]卷三五《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在与地方官府的勾结下,豪民的势力更加膨胀。
(二)摩擦和镇压
豪民违法吞并、恃势强占,甚至欺凌官吏、杀人害命的情况,在宋代的史料中多有记载。因此造成的赋税失陷,官弱民强,以及对基层社会安定的破坏,给地方的统治带来危害。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代表,从维护统治集团和自身利益的角度,对势力膨胀的豪民进行压制打击。
对不纳租税的豪民的打击。真宗时,浮梁县“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出租,畜犬数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此前的县令“不肯禁”,常是里正代其输租。胡顺之到任后,几番催督,但豪户仍拒不纳税。胡顺之“乃令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门而焚之”,情急之下豪户全家急忙逃逸。胡顺之“悉令掩捕,驱至县,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尽痛杖之”,说:“胡顺之无道,既焚尔宅,又杖尔父子兄弟,尔可速诣府自讼矣。”但豪户并无一人敢诉,“自是臧氏租常为一县先”[4]109-110。
对蔑视地方官员的豪民的打压。豪民势力强大后,对地方官员的凌辱蔑视,引起了官员的反感。真宗时,鲜于侁摄治婺源,“奸民汪氏富而狠,横里中,因事抵法”。群吏罗拜说:“汪族败前令不少,今不舍,后当诒患。”鲜于侁怒,立杖汪氏,恶类从此屏迹[3]10936。绍兴年间,静江府古县豪民秦琥武断乡曲,持吏短长,“邑大夫以下为其所屈”。高登知县后,“面数琥,声气俱厉,叱下,白郡及诸司置之法”。一贯为所欲为的秦琥“忿而死”[3]12130。
为了维护基层社会的安定,清正的官员对违法杀人害命的豪民,进行了坚决镇压。理宗时,高斯得为湖南提点刑狱,攸县富民陈衡老“以家丁、粮食资强贼,劫杀平民”“愬其事者,首吏受赇而左右之”。高斯得发其奸,“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毁衡老官资,簿录其家”[3]12325。一些正直官员出于扶弱抑强的公正理念,对豪民势力的抑制镇压,有利于其嚣张气焰的收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伸小民不平之气。
面对地方官员的打击与镇压,不甘示弱的豪民也会极力反抗,不少地方官甚至因此丢官罢职。仁宗初年,“中人用事者罗崇勋之徒,交通县豪,借之意气,以渔夺细民,吏不敢何”。陈留知县王冲,“以法绳之”。大姓田滋等因此制造流言飞语,污蔑王冲。王冲被“坐除名,徙雷州”[24]782。宁宗时,瑞州大姓幸氏“贪徐氏田不可得,强取其禾,终不与,诬以杀婢,置徐狱”。徐氏诉其冤情,提点江西刑狱赵汝谠“以反坐法”,黥窜幸氏,籍没其家。幸氏逃走,并“告急于中宫”,赵汝谠被调湖南[3]12397。在利益的作用下,豪民与地方官府的摩擦也多有出现。
(三)以勾结为主的关系,决定了其“豪横”的特征
但在宋代黑暗腐败的地方官场中,事事处处以私利为先的地方官,根本不可能把抑强扶弱作为主要政务。在利益的需要下,与豪民的勾结,成为地方官场公开的惯例,也成为了其彼此关系的主流。
太宗时记载,“剑南诸州民,为州县长吏建生祠堂者”“官吏有善政,部内豪民必相率建祠宇,刻碑颂,以是为名,因而掊敛,小民患之”[1]6498。豪民通过巴结地方官吏,来达到武断乡曲的目的;而地方官则通过联络豪民,来达到利用其财、权、势为自己服务的目的。不少官员上任之后,都是先要去拜访当地的豪民。“县官甫下车,则先诏问权要声援,往往循习谄媚,互相交结”[1]6691。而在相互利益需要下,豪民与地方官府以勾结为主的关系,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以“豪横”为主的身份特征。
结 语
豪民是宋代基层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以不同于普通百姓的财、权、势优势,成为影响基层社会的主导阶层。不仅普通百姓,甚而政府官员,都对他们俯首帖耳。那么,宋代地方豪民究竟是基层社会兴建私塾、救济穷苦的“长者”?还是武断乡曲、左右地方官府政治的“豪横”?除了豪民自身的素质外,其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决定性因素。当政府对其势力的发展合理引导,有效治理的时候,地方豪民的积极作用成为主流。当政府因私利受制于豪民,软弱无力不足以临民御民的时候,豪民的消极作用就成为主流。在宋代,由于地方政治的腐败,豪民与地方政府的勾结,成为彼此关系主流的态势,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以“豪横”为主的身份特征。
[1]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27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6]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7]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朱熹.朱子全书·三朝名臣言行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2]刘宰.漫塘刘先生文前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7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13]郑刚中.北山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方大琮.宋忠惠铁庵方公文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9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15]董煟.救荒活民书[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沈辽.云巢编[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7]韩元吉.南涧甲乙稿[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8]范祖禹.范太史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9]熊克.中兴小纪[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20]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M]//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21]李纲.李纲全集[M].王瑞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4.
[22]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3]刘攽.彭城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4]刘敞.公是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