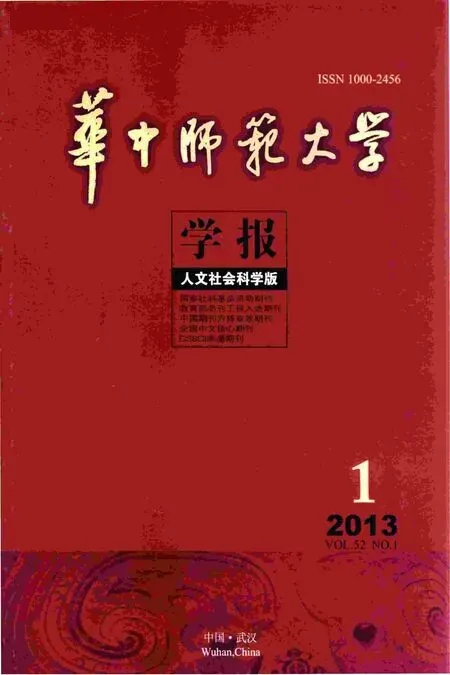“史统散而小说兴”与“史诗衰而小说兴”——冯梦龙与巴赫金小说起源思想比较研究
张开焱
(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石435002)
作为形式构成之一的叙事文类与文体是否积淀着特定的历史信息与文化精神?众所周知,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文论家都是否定的,但弗·杰姆逊这样的学者在《政治无意识》中却明确断言一切叙事文类与文体都携带着其起源时的“历史信息”,也就是说,历史、史诗、小说这些叙事文类与文体表面看是纯形式构成,但特定历史信息与文化精神悄然积淀其内。我们发现,冯梦龙与巴赫金关于小说起源的有关见解给杰姆逊的观点提供了支持。这两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国度和文化历史环境中的文化人,在关于小说的起源问题上,竟有某些惊人的相似见解,这些见解对我们思考小说的精神特征和起源、思考叙事文类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极具启发性。
一
首先,他们都认定小说产生在各自民族或文化史上古代文化的奠基时代。在小说起源问题上,冯梦龙有一段名言众所周知——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①
明清文化人在讨论小说的起源时多有类似表述:
古史亡而后小说兴,“齐谐”见述于漆园,梦卜多载于盲史,即宋玉之赋行雨,子长之传琴心,厥体滥觞,实托之始。②
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从事于六德六行六艺,国无异政,家无异学,何其盛欤!周衰而后,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推所长,……③
这些表述与冯梦龙的见解基本相似,这些言论都确认,中国小说的源头在春秋战国时代(“周季”),像韩非、列御寇、庄子、左丘明、宋玉等人的作品中,都有小说的因素或片段存在。将小说起源追溯到上古时代其实并不是冯梦龙的创见,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十五家小说,多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而且在班固的“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的断言中,我们甚至可以把小说的起源追溯到更早设置稗官的西周。不过,冯梦龙认定小说起源于“周季”,也即周之末世,就是春秋战国。这个时间的认定具有特殊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宋代曾巩在给自己重新辑录校正的汉代刘向的杂书(也可以说是准小说)《新序》做的序言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个时间点认定的意义: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尝不相为始终,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之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余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能有出其间者也。及周之未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余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盖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意,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所短,务其所得而讳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复知其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汉兴,六艺皆得于散绝残脱之余,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一切不异于周之末世,其蔽至于今尚在也。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也,扬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为众说之蔽,而不知有所折衷也。④
这个长篇序言也是分析中国古代包括小说在内的百家“众说”何以出现和何时出现的,曾巩的时间认定和冯梦龙一样:“周之末世”。而且曾巩分析了所以如此的原因。这篇序言对于我们理解上引冯梦龙那段言论的思想内涵十分重要,后者可以看成是对前者的归纳,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将一再回到这个展开性表述中,以此作为探讨冯梦龙表述中理论内涵的佐证。冯梦龙像中国古代许多文化人一样,许多很重要的见解是以精练的命题或简要的语言表述的,其丰富的理论内涵需要结合其他文化人相关的见解来阐释。
冯梦龙将小说起源的时间确认为“周季”的春秋战国时代,而这个时代正是西方历史学家所命称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即几个主要的人类文化圈奠定自己基本文化模式的时代。在华夏文化的奠基时代,小说出现了,尽管它刚出生时还很幼稚嫩弱,但日后的参天大树就是从这株嫩弱的幼苗开始其生长过程的。
巴赫金也将西方小说的滥觞期追溯到古代希腊时期。一般说来,西方权威的观点认为小说的起源是与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联系在一起的,小说是一种近代兴起的、与资本主义历史相伴随的文化形式。不仅西方的文体学家们这样认定,就是卢卡奇、戈尔德曼、杰姆逊等具有更广阔社会和思想视野的人也这样认定,他们都认为小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与之相比,巴赫金的小说起源观真是独树一帜。他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专列《希腊小说》一节,认定西方小说起源于古代希腊,并具体讨论了古代希腊三种重要的小说类型和三种重要的时空体,即“传奇教喻小说”、“传奇世俗小说”、“传记小说”;而且,不仅是这些类型构成了西方小说最早的源头,古希腊、罗马大量的“庄谐体”作品如民间笑谐性作品、民间歌舞剧、整个田园诗、寓言、早期回忆录文学、“卢奇安对话”与“苏格拉底对话”、梅尼普讽刺体等,都是西方小说的重要来源,“‘庄谐体’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所有这些体裁,才是小说的真正前身”⑤。正是它们,开启了西方小说的源头。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他追溯复调小说的源头时,也再一次将古希腊各种庄谐体、苏格拉底对话体等作为复调小说的来源。
于是,我们发现,两个不同国度和时代的文化人,当他们面对小说这种文化样式时,都不约而同地将它的起源期追溯到各自文化的奠基时代,即中西文化的轴心时代。
二
与他们对小说起源时间确认相关的是,他们都认定,小说的兴起都与一种具有绝对权威性的历史叙事形式和传统的衰落有内在的对应关系。这种历史叙事形式与传统在冯梦龙这里是“史统”,在巴赫金那里是史诗,它们的衰落正是在各自文化的奠基时期。
冯梦龙在追溯小说起源时断言“史统散而小说兴”,也就是说,小说的兴起只能在历史叙事传统(“史统”)的权威性丧失之后。前引清人“桃源居士”在《宋人小说序》中谓“古史亡而后小说兴”,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曾巩的《〈新序〉序》也隐含了相近的看法。结合古代文化人的相关言论,在此归纳“史统”基本内涵是:
1.“史统”在冯梦龙这里指的是上古三代关于历史叙事的神圣原则与传统,它被认为是最神圣、最崇高、在上古甚至是唯一的文化形式。上引曾巩的序言中对此有明确表述:“古之治天下者,……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在中国古代文化人的描述中,文字的发明者仓颉同时也是最早的历史写作者,他和华夏人文始祖黄帝一起出现:“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⑥文字的发明者又是历史叙事的肇始者,暗示历史与文字有本原性联系。在历史话语就是“文”全部构成或核心构成的时代,包括小说在内的其它关于人类生活的叙事方式和话语自然没有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2.“史统”在春秋战国时代被孔子所继承,并体现在其撰写的历史著作《春秋》之中。但这个“史统”在春秋之前和之后的处境大不一样。在春秋之前的上古时代,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神圣性和唯一性,而在春秋之后,其神圣性、唯一性和权威性丧失了。多种关于人类生活的观念与叙述开始出现,所谓“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指的就是这种状态。
3.历史叙述的是已经过去时代的生活,是以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为中心的伟大人物们的功业和生活过程,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谓历史著作“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业,并天地而久大。”就是“史统”在历史叙事对象和功能方面的不变认定。而在春秋以前的历史叙事传统中,最神圣的对象就是“二帝三王”们的功业与言行,他们是华夏民族传说中奠基时代的伟大人物;历史叙述对象的过去性,决定了这种叙事类型与当下正在进行和发展着的社会生活、与芸芸众生生活的隔绝状态,用冯梦龙的话讲,就是不“通俗”(冯梦龙“通俗”概念内含涉及小说的多个方面,表现对象的大众性、当代性是其主要方面之一)。
4.由于历史叙事对象的伟大崇高特性,决定了历史叙事的语言和风格具有庄重严肃的特点,历史叙事文体是一种庄严雅正崇高的文体。
5.历史叙事须体现官方指认的历史伦理意识,即所谓的“道”,它是理解和评价历史的价值尺度。
这个“史统”在冯梦龙看来,到春秋战国时代丧失了权威性,其标志之一就是曾巩所说的诸子百家“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所短,务其所得而讳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复知其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就是在这种精神背景中产生的。冯梦龙“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确认的是,小说在起源上就和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绝对权威性的历史叙事规则之间有内在的对立性和不相容性,在历史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或最权威的叙事方式的时代,小说不可能产生。小说的产生,只有在这种史统丧失了权威性和唯一性的时候才有可能。
中国历史叙事中所谓“三皇五帝”、“二帝三王”以及他们的时代,其实都并不是信史,而只是神话传说历史化或者历史神话传说化的结果,因此,它们既含有某些史实的可能因素,更有大量集体虚构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上古历史叙事作品和西方上古史诗几乎具有同样的特征。
很有意思的是,巴赫金在研究西方小说的起源问题时,也确认小说和史诗具有一种内在的对立性和不相容性。他专门写过一篇《史诗与小说》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结论,我们可以比照冯梦龙“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归纳为“史诗衰而小说兴”。冯梦龙确认史统权威的丧失才是小说兴起的前提,巴赫金也确认史诗的衰落是西方小说兴起的条件。
巴赫金指出,史诗这种文化形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长篇史诗描写的对象,是一个民族庄严的过去,用歌德与席勒的话说,是‘绝对的过去’;(2)长篇史诗渊源于民间传说(而不是个人的经历和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自由的虚构);(3)史诗的世界远离当代,即远离歌手(作者和听众)的时代,其间横亘着绝对的史诗距离。”⑦由于史诗表现的是伟大祖先的世界,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颠峰”时代,因此,它所叙述的这个世界具有伟大、崇高、绝对、不可质疑的特征。“关于过去时代的传统,是神圣而不可篡改的”⑧,这个世界是定型、完美的,也是封闭的、完成了的,它与我们——作者和听众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这使得史诗这种体裁在“我们见到它时,它已经是完全现成的体裁,甚至已经僵化、接近死亡的体裁”⑨。而小说在巴赫金看来有着与史诗完全不同的特征:史诗是面向过去历史的,而小说是面向现实和未来生活的;史诗是靠记忆的,小说是靠认识的;史诗是靠传说的,小说是靠实践的;史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的,小说的对象是正在展开和进行的,未完成的;史诗是绝对的,小说是相对的;史诗是封闭的,小说是开放的;史诗是崇高的,小说是低俗的;史诗话语是纯粹的,小说话语是驳杂的,等等,这决定了小说与史诗内在精神上的对立性。
巴赫金并不仅仅只在一般文体学意义上理解史诗和小说的体裁特性,而是将史诗与小说的文体特性与特定社会政治力量、社会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来谈论。在巴赫金看来,史诗这种崇高的体裁总是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趣味相关联。像史诗这种“崇高体裁里对过去的理想化,具有官方的性质,统治的力量和统治的道理(即所有完成了的东西),将其一切外在的表现,都形诸于过去这个价值等级的范畴中,形诸于保持距离的遥远的形象之中(从手势、服装直到风格,即权力的一切象征)。而小说则同永远新鲜的非官方语言和非官方思想(节日的形式、亲昵的话语、猥亵行为)联系在一起。”⑩史诗与小说需要完全不同的基础,过去、记忆、绝对,那是史诗产生的基础,而“经验、认识和实践(未来)——这三者才决定着小说”。小说这种体裁因此在特定时代是与新兴的社会力量、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趣味、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官方的思想与非官方的思想,这正是史诗与小说在精神内涵上的根本差别,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不相容性。综观巴赫金一系列论文论著,不难看出,他认为西方小说的产生,是在史诗、悲剧这些崇高的文学形式衰落之后,这个时代就是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化时代。小说这种体裁与苏格拉底对话体、梅尼普讽喻体、各种亲昵、笑谑、具有狂欢化特征的低俗文体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是在它们基础之上产生的。
三
与此相关,冯梦龙和巴赫金都确认小说起源上的民间性或泛民间性。
在冯梦龙那里,小说从起源角度讲,就是一种和民间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精神形式,小说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文必通俗”、能“谐于里耳”。冯梦龙的“通俗”基本的意思是小说体现着民间的生活、眼光、趣味、立场,这是在确认小说的民间根性。从汉代班固谓小说乃起于稗官,是民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刍尧狂夫之议也”开始,中国历代文化人都在确认小说的民间根性,正统文化人确认小说的民间根性是为了证明小说的文化地位和品格的低下。而冯梦龙恰恰认为通俗是小说最有力、也最有价值的文化属性,他指出,小说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必须符合民间众生的趣味,小说如果像六经国史“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饰,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他将自己搜集、整理、编撰和创作的小说集分别命之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即著名的“三言”,他谈这样命名的原因在于:“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也。”
结合冯梦龙有关言论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般含义,“通俗”、“适俗”中的“俗”应该包含这样一些基本意涵:一是和高贵的统治阶级相对立的芸芸众生,民间大众;二是和官方的或主流文化认定的高雅趣味相对立的民间大众的低级趣味;三是指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区别于统治阶级的高贵生活;四是与这些意涵相关联的当代大众的现实生活,以区别于过去的、已经死亡了的伟大人物们的历史生活。小说通俗的特性意味着小说必须在这些方面全面接近民间、接近时代、接近现实、接近下层。对于小说通俗性的这些内涵,清代罗浮居士有很明确的解释: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辩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
冯梦龙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表现出这种认识,他的小说也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意识。
在小说起源问题上,巴赫金也十分强调小说与民间、现实、时代生活的联系。上引巴赫金关于史诗与小说差异性论述的有关见解已经很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点。在《长篇小说的话语》这篇重要论文中,他也特别强调小说语言与诗歌语言的根本差异之一是前者的杂语性、多语性、开放性、未完成性和对话性,而这些特征首先存在于民间现实生活话语中,因此,小说是反映现实民间话语存在状态的最合适形式。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这篇长文中,他辟有专节着重论述民间文化的时空体对小说时空体的巨大意义,论述民间文化中的骗子、傻瓜、小丑三大角色对小说形象类型的重要影响。在论述有关拉伯雷小说的文化和文学特征的著名论著中,他甚至主要从欧洲古代到中世纪的狂欢节和狂欢节文化的角度来论述拉伯雷小说的精神内涵和文学特征。在多篇论文中,他都强调古代希腊、罗马民间众多的文体对小说的重要意义。所以,巴赫金传记的作者迈克尔和克拉克·霍奎斯特在评价巴赫金小说理论的特点时才有这样的判断:“巴赫金将三个范畴——小说、民间性、杂语——看成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在人的意识中发动着一场永恒的革命。”
巴赫金对小说面向当下社会现实的特性也十分重视和强调,他指出由于小说面向当下正在发展的现实,面向人们正在进行着的社会实践,因此,它永远是新鲜的、“低级”的、短暂的、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和未完成的。“当代现实、转瞬即逝的东西,‘低级’的东西,现时——这种‘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生活,只有在低级的体裁里,才能成为描绘的对象,但它首先是在民间笑谐作品的极为广阔丰富的领域中,成了基本的描绘对象。……正应是在这里(民间笑谐)寻找小说的真正的民间文学的渊源。”“把未完结的现时,作为一个出发点和思想艺术关注的中心,这在人们的创作意识中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奠定了长篇小说体裁的基础。”巴赫金进而指出,正是小说面向当下“低级”的、正在发展的永不完结的现实生活的特性,决定了小说一系列与其它面向过去的文体大不一样的文体特征,如对时间的全新感受和处理、对个人体验和自由创作的特别重视、由于内容的开放性和未完结性而导致的对形式上完整性的特别要求,等等。这些内容和形式上的特征,恰恰与史诗的特征是对立的。
四
最后,冯梦龙和巴赫金的小说起源观中,都确认了小说的思想性特征。
冯梦龙“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还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小说从起源上讲就和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见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他在本文开始的引文中,将战国时代的两个有名思想家韩非子和列御寇作为“小说之祖”是意味深长的。包括冯梦龙在内的宋以后许多文化人将都庄子、韩非、列御寇等寓言家尊为小说之祖,他们这样说,大约是在突出寓言与小说在虚构想象特征方面的脉承关系。但寓言不仅是一种具有虚构想象特征的文体,还是一种有极强思想性的文体,思想正是这种文体的内核。这个内核在“寓言”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就携带着。“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的《天下》篇和《寓言》篇,是庄子的后学所作,他们指出《庄子》一书表现方式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至于这寓言、重言、卮言“三言”的准确所指为何,古今讨论者众,主要的分歧在对“重言”与“卮言”的理解上,以及它们与“寓言”的关系问题上,而对于“寓言”本身的理解,则分歧很小,大都认为“寓言”是指的“有寄托之言”、“有寓意之言”,这个理解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寓言这种文体,从文体史角度讲,是从上古神话发展而来的,是神话进入理性时代后的哲理化形态,形象其外,哲理其内,这是寓言的根本特征,先秦那些寓言家首先都是思想家。因此,不管冯梦龙在内的明清文化人是否是有意识地从确认小说思想性角度来谈论的,他们将庄、列、韩等寓言家奉为小说之祖,应该无意识地内含了思想是小说根本构成因子的认识。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内面,还隐含着“道统散而小说兴”的潜命题。大约因为这个潜命题冯梦龙之前的文化人(如曾巩的《〈新序〉序》中)已经有过相当明确的论述,所以,冯梦龙才省略了相关的论述。因此,我们可借助冯梦龙之前文化人的相关表述揭示他“史统散而小说兴”中“道统散而小说兴”潜命题的存在。
《文心雕龙·史传》中,刘勰强调历史叙事要“依经树则”、“附圣宗经”,并在评价司马迁、班固等历史学家将吕后的传记列入帝王的“本纪”时,指责他们“违经失实”:
“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者?疱羲以来,未闻女帝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立为纪,谬亦甚矣。”
吕后是汉高祖之后十多年汉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和班固才将她的传记列入“本纪”,这种处理遵循的是事实真实的原则,但刘勰却认为这“失实”了,因为他指出妇人参政违背周武王这样的圣贤立下的政治生活规则(“妇无与国”),而且“三皇五帝”、“二帝三王”以来的历史圣典如《尚书》和《春秋》,也没有记载妇人担任最高政治领袖的例子。违背了圣贤立下的政治生活禁令和历史圣典的惯例,自然就是“违经”,而“违经”的历史必是“失实”的历史。因为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则“经”即是“道”的最高体现和表述,“宗经”就是“宗道”,“违经”因此就是“违道”;这明确地确认了“道”是历史叙事的内核和判断标准,它也正是所谓“史统”的本有内涵。所以,“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内面,隐含的是“道统散而小说兴”的逻辑结论。
上引曾巩《〈新序〉序》更是将“道统散而小说兴”这个潜命题揭示得十分清楚,从小说起源的角度看曾巩这段话,可以认为它是冯梦龙“史统散而小说兴”命题的展开形式。对此笔者在有关论文中有深入讨论,有意者可参看。为了避免重复,此处只给出基本结论,1.“史统”的内核是“道统”,“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隐含着“道统散而小说兴”的结论;2.建立在“一道”基础上的古史和古史传统在远古社会曾经有不可质疑的崇高性、唯一性、权威性,它实际上是统治者历史观念、立场和意志的体现。只有“一道”、“一说”的时代小说是不可能产生的;3.小说只可能产生在多道并存、众说纷纭的社会,冯梦龙将小说的起源追溯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正内含着这样的认识;4.小说是最需要思想(“道”)的文体,“道”是小说的精神内核;5.小说所需要的不是一种思想,而是多种思想(“多道”、“众说”)同存并在。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巴赫金也十分重视从起源角度论述小说与思想多样性的内在关系,他在研究古希腊、罗马小说的兴起时指出,它们都与一种稳定的世界观、思想体系的衰落有内在的联系:“在希腊化时代的歧语和杂语世界中,在罗马帝国中,在中世纪的教堂语言思想集中化发生解体和衰落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小说的长篇萌芽。在近代亦复如是,小说的繁荣总是同下述事实联系着:语言和思想的稳定体系出现解体。”正是因为小说与思想、尤其是与多种思想的内在关联,所以,巴赫金将苏格拉底对话形式当作是西方小说的来源之一,甚至明确称之为“当时的小说”。在巴赫金看来,小说与诗歌最大的不同之一,就在于后者是单纯的感受、感情和体验的产物,而前者则需要远为复杂而深刻的思想构成,小说是思想性的文体,小说中的形象是思想性的形象,或者说是渗透了丰富思想的形象,思想对小说具有生命悠关的意义。小说还不仅需要一种思想,而是需要多种思想,需要多种思想之间的交流、对话和碰撞。小说内在的思想性、对话性决定了小说只能在一个具有多种意识形态、多元世界观的社会和时代才有获得大发展的可能。正是这个认识,使巴赫金将小说看成是思想对话的场所,确认小说与思想的本源性关联。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对思想与小说关系的强调众所周知,他说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思想的人物,思想是这些形象的内核;他说对话性是复调小说的根本特征,而对话的核心内容,就是具有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人物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冲突、争辩、对抗与对话,这些对话正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对话在小说中的显现形式。巴赫金对现代复调小说的思想性认定,与他对小说起源阶段小说思想性的认定,具有内在脉承关系。
五
为什么在小说起源、文化精神和文体特征等问题上,冯梦龙和巴赫金这两个时代和国度毫不相干的文化人会有如此相近的见解?笔者想原因有四:
一是中西小说起源方面某些相似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小说起源的春秋战国,是思想大解放和文体大解放的时代,上古“一道”、“一说”的局面不复存在,与此相关的上古历史叙事的权威性、崇高性和绝对性受到挑战,“多说”、“多道”、多种叙事形式和其它文体形式出现了,并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而西方小说的最早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那是一个和中国春秋战国一样具有文化奠基意义的时代,到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化时代,远古史诗崇高的文化地位受到挑战,史诗文化已经衰落,多种学说、多种思想、多种叙事形式出现并获得了大发展。这种文化背景为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条件。
二是小说内在特征的某些相似性。中西小说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但另一方面,中西小说也有一些内在的共同性和相似性特征,这些特征会使学者们对它们作出相近或相同的认定。
三是小说在他们的时代已经开始大发展或者已经获得了大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其内在的精神特征和文体特征已经开始形成,这为学者们对它们进行合适研究和概括提供了客观条件。
四是他们都对小说有超常兴趣并对小说文化价值有超常认定,这个主观基础在他们对小说起源见解的共同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UEF组采用外固定支架固定,按常规方式进行治疗,对合并皮肤撕脱的患者同样采取打薄戳孔原位回植,创面以VSD材料封闭,给予-0.04~-0.06 MPa的持续负压吸引,同样于术后3~5 d左右拆除VSD,根据情况行换药、植皮或Ⅱ期皮瓣修复。
正是上述原因,使两位生活在不同国度和时代的文化人有十分相近的认识,在今天看来还有特殊价值。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冯梦龙和巴赫金将小说的起源与各自民族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叙事文类历史和史诗完全对立起来,是否遮蔽了后者对前者的积极影响?答案是肯定的。
关于历史叙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积极影响,研究成果众多,在此不展开介绍,笔者只提及杨义先生《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的一个重要见解,他说神话、子书和史书是最重要的“小说三祖”:“‘小说文体三祖’的关系好有一比,神话和子书是小说得以发生的车之两轮,史书则是驾驭着这部车子奔跑的骏马。”在他看来,中国小说借鉴了“史籍诗心”,在语言、文笔、叙事、虚构、题材、手法等方面,全面受着史籍的长期影响和灌溉;同时,小说中的“拟史批评”也以史籍作为最高规范。因此,历史叙事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毋庸置疑。中国古人对此有众多言论,笔者在拙文《中国古人眼中的小说:驳杂的世界》中对这些言论有专门的梳理和论析,有意者可参看。但正是在这个常识性背景下,冯梦龙的小说思想就更显示出其过人洞见了。他所处的时代,小说已经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创作实践中小说的文体独立和自觉,迫切需要文化人在理论上从传统的史学视野中走出来,确认小说不同于历史叙事的精神和文体特征所在,冯梦龙上述思想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在理论上走向自觉状态的标志。他是通过无视传统文化人强调小说与历史关联性的权威观点,获得对小说精神特征和文体特征洞见的。
这种情形在巴赫金那里也一样发生。一般西方学者都从文体发展史角度,将史诗看成是西方小说的最早源头,黑格尔甚至断言近代小说是“市民社会的史诗”,以强调小说与史诗的内在脉承关系。但巴赫金却表达了与大多数西方学者完全不同的见解,恰恰将史诗看成是与小说完全对立的文学类型,他以对西方诗学史关于小说与史诗内在同一性关系常识的有意盲视,换来了对两者关系的深刻洞见,这是巴赫金的过人之处。
注释
②桃源居士:《宋人小说序》,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790页。
③马纬云:《唐代丛书序》,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797页。
④曾巩:《新序目录序》,陈杏珍,晁继周:《曾巩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