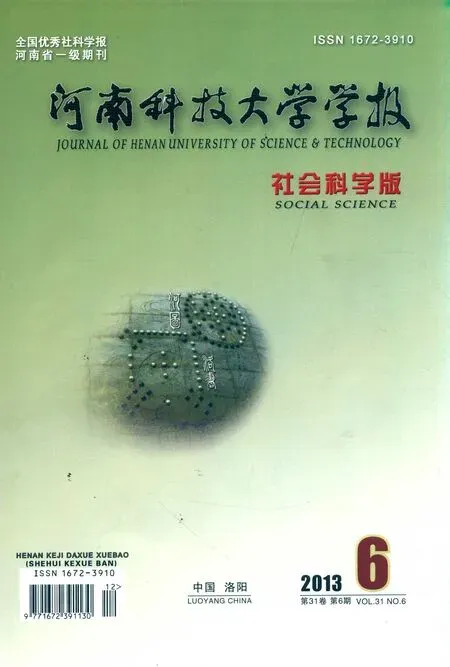郭沫若绿色文论的生态诗学
伊彩霞,黄大军
(1.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系,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2.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艺文寻珠】
郭沫若绿色文论的生态诗学
伊彩霞1,黄大军2
(1.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系,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2.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论生态美学谱系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早期郭沫若形成了以启蒙为底色的生态自然观,强调大自然是个体观、文化观、社会观的终极根源。本着这样的文化理念与诗学理念,郭沫若确立了以“自然流露”为主导的文艺诗学观,以“文化—审美”为双重视域的生态批评观,这种自然、文化与审美的多向交织,大大扩展了他的批评视野与批评境界。凭借充满启蒙意向与生态意蕴的早期文论,郭沫若卓然跻身于当时一线批评家之列,并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郭沫若;自然观;生态诗学
从“五四”登上文坛到1924年翻译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发生思想转变,再到1926年彻底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郭沫若为他的早期文论划上了略显突兀的句号。然而,这短短数载的早期文论在其整个批评历程中的分量与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它构成了郭沫若文论的绿色阶段,同时宣告了作者作为20世纪一位优秀文艺批评家的诞生。凭借《三叶集》、《文艺论集》以及《文艺论集续集》(部分篇章)等早期文论,郭沫若以火热的启蒙意向与充沛的生态内蕴,卓然跻身于当时一线批评家之列。根据自幼塑就的自然情结与文学天性,“五四”留日期间,他广泛接触了众多具有生态意蕴与“自然书写”性质的中外文艺作品,并在西方近现代文明与“五四”时代精神的双重濡染下,形成了以启蒙为底色的生态自然观,这赋予了其文艺审美观与文艺批评观特殊的宇宙论色彩与文化开放性。
一、启蒙映射的生态自然观
(一)生态自然观
郭沫若自然观的价值主体是它的生态性。在郭沫若的自然体验中,自然界不是外在对象与“他性”存在,而是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沟通二者的是大自然无限的生育力、生命力以及无所不在的神性。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指出:“从更深的层面看,人类生态学的前提是人们对自然和命运的信仰,即宗教信仰。”[1]207郭沫若融汇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斯宾诺莎与歌德的泛神论等思想,形成了自己对泛神论的独特信仰:“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2]正是在泛神论的宇宙秩序中,形塑了郭沫若感受大自然的文化范式。在他眼中,生生不息与漫无目的是大自然的永恒形态,也是大自然保持至高目的与谨严律令的不竭动力,人类只有纯任自然才能净化灵魂,积极创造才能克服人性异化与文明危机。通过泛神论的哲学洗礼,郭沫若消除了自然与自由、理念与感性、优美与崇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关系,实现了自然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生命吻合,自然演变为充满激情、乐观、乌托邦幻想和艺术憧憬的精神主体,而人则从向自然的投入中获得了生成转化的无限可能性,这种心物一元的文化活力论构成了郭沫若自然观的生态基础,并成为他评价人类文化的基本尺度,如其所言:“二十世纪是文艺再生的时代;是文艺再解放的时代;是文艺从自然解放的时代;是艺术家赋予自然以生命,使自然再生的时代;是森林中的牧羊神再生的时代;是神话的世界再生的时代;是童话的世界再生的时代。”[3]215所以在他看来,“欲消除人类的苦厄则在效法自然,于自然的沉默之中听出雷鸣般的说教”。[4]150
(二)启蒙自然观
郭沫若自然观的时代表征是它的启蒙性。这种启蒙意向首先表露在他的“泛神论”思想中。历史上的泛神论是一种将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借以凸现自然界价值的哲学观点。郭沫若的泛神论论证了神、自然与自我的同一性,强调了自我至高无上的哲学价值,这种泛神论与其说是自然本位的,不如说是人本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它确立了主体的绝对权威与首要价值。虽然这一泛神论思想凸现了人在宇宙(世界)中的核心位置,但它并不否认自然价值及其与人的共在关系,正如郭沫若所感悟的,泛神论是一种融理智与感情于一体的宇宙观,哲学家、艺术家要想摈弃死的宇宙观,创造有生机、有活力的精神文化,就自然要趋向泛神论,这样才能感发宇宙全体的无穷活力与创造内蕴。而泛神论的日常启蒙意义则在于,它使个人不再臣服于自然与神灵,也不再依附君、道、父母等旧伦理主体,而是实现了个体文化实践的自觉性与自律性。无疑,经郭沫若改造过的泛神论,已与它的精神本源颇有暌违,咸立强就表示:“此泛神论非彼泛神论,在郭沫若那里,泛神论与物活论、生命哲学、唯自我论等思想纠缠在一起,终究只是‘这位诗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意体现’罢了。”[5]郭沫若泛神论的思想价值就在于这种本土化与接受变形,以及“五四”式的对自我价值与自然活力的兴奋体验上。
郭沫若自然观的启蒙性还表现在,他提出的文化现代化思路——“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吸收古人的遗产,以期继往而开来”,[6]就矗立在这种对大自然动态精神的哲学领悟上。在文化范型上,郭沫若发现“动”与“活”是古今中外一切进步文化的个性,“静”与“死”是一切消极、受动文化的本质。他称印度与希伯来文明属“出世—静观”型,中国与希腊文明为“入世—动态”型,于是他将中国文化的再生寄托在“动的文化精神”[4]155的恢复上。这一方面促使他由肯定希腊文明走向对近代科学精神的推崇,另一面又促使他积极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合理性。他认为希腊文明是近代科学文明的母体,科学精神在于追求普遍妥当的真理,伟大的科学家对真理的探索是一种英雄之举,他们的成果施诸实用可以增进人类幸福。自然与文化的活力论还影响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评判。他认为未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周秦之际,在儒道两家那里保存着中国最真切、最纯粹的古代精神——注重现实、注重实践。因此,通过横向比较,郭沫若从中西文化内在共通的“动的文化精神”出发,提出了个人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文化设计。
二、“自然流露”的文艺诗学观
(一)从自然到主体
“五四”之际是郭沫若文学创造的浪漫主义时期,他醉心于大自然生生不息、永恒发展的创造潜能,视大自然为个体观、文化观、社会观的终极根源,培育了主体对自然与文艺的半宗教性的献身与追求。凯特·里格比指出:“浪漫主义思想无疑超越了笛卡尔哲学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它将人的意识和创造性看作是自然所固有的潜力的显现。”[7]郭沫若的哲学自然观亦与之同出一辙。对郭沫若来说,自然之于自我是本源与母体,而自我之于自然则是象征与活力,自然与自我相互塑造的最大成果就是“生态自我”的生成,“生态自我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将宇宙精神贯彻到自己的人生中,与宇宙中至高的生命节律合拍,自我实现的同时兼顾他人和他物的利益,这时‘我’便冲破了与他人和他物的界限而与世界融为一个整体,完成了在更高层次上向母体回归”。[8]郭沫若正是以“生态自我”为原点,发展了一种宇宙自然、人性自然与诗性自然三元辩证的人文生态学,这种文化观主张宇宙人生只有按照生态美的理念才能完成创造自身的任务,才能谋求自然与人类的生命交感,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创造性与超越性。可以说,郭沫若关于“自然与诗人一体”,[9]135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10]等诗学观中的“自然”,就是生态美的内化与转化形式。这种对自然的审美化解读,不仅有利于抵制一切有限需要与工具理性,更有利于保持对象的自由和无限。
从文艺与自然的生成关系出发,郭沫若确立了以“自然生成”为本位的文艺诗学观。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诗模仿自然”作了如下解读:“我看他这句话,不仅是写实家所谓忠于描写的意思,他是说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诗的生成,如象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9]47他之所以认同亚里士多德,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大特点是经常从有生命的自然界出发,而不像德谟克利特那样从无机自然界出发”,[11]85从创造与生成的角度,他很欣赏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家不只去模仿现实存在的事物。他们还能模仿应然之物”[11]97的观点。郭沫若用“自然物的生存”比附文艺生产,内里渗透着华兹华斯、雪莱、柯尔律治等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家的深刻影响,浪漫文艺观认定艺术创作活动与自然造物遵循着同样的法则。然而,郭沫若对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重构,并不能根除二人文艺观的根本分歧。3年后,他不仅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而且对19世纪“受动的文艺”、“只在做个自然的肖子”的文艺表示了严厉拒斥,[3]214声称“近代的文艺在自然的桎梏中已经窒死了”,“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3]215以致给人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印象,但正如柯尔律治所指出的:“‘模拟自然的精神’(Naturgeist)等同于一个人外化他自己的‘活生生的、产生生命力的思想’”,[12]因而郭沫若舍弃无机自然与静态自然,高扬动态自然与创造自由,最终实现了对文艺模仿说的螺旋式超越。
(二)从主体到文本
从宇宙自然过渡到“人性自然”,郭沫若从自主自律的生命与主体中找到了诗学灵魂,其中,泛神论对自我的推崇与生命哲学对自我的肯定,都使他把艺术家置于文艺活动、文艺批评的首要环节,这形成其以“艺术家—作品”为轴心的艺术“表现说”。柏格森说过:“我们最有把握确定、也了解得最清楚的存在,无疑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关于其他各种对象的观念也许全都是外在的,肤浅的,而我们对自己的知觉则是内在的,深刻的。”[13]早在《三叶集》时期,郭沫若就已极为关注文艺家人格问题,他曾慨叹:“人之不成,诗于何有?”[9]50“诗的创造是要创造‘人’。”[9]49在构建艺术家的完美人格方面,郭沫若有两点深刻体悟:一是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宜,艺术需要创造性直觉;另一点是提倡以“美化感情”为中心,涵盖自然、社会、美感、哲理等多个人文领域的艺术训练方法。因此郭沫若的艺术论实则一维的人格决定论,即只要艺术家是完满的、艺术的,其创作就是有价值的,换言之,个性发展是郭沫若艺术论的核心,他坚信艺术乃人格创造与人格冲动的表现,唯有个性圆满、人性健全的诗人才能写出普遍的文艺、满足读者要求的文艺。
郭沫若这种对艺术家本质的强调,决定了他对文学本质与文学创造的个人解读。通过考察原始民族的口头文学与幼儿的自由诗歌,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14]节奏即情绪的自然消涨,亦即诗歌与生俱来的本性。他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9]14“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9]13为此,他为诗歌开列了一个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9]16上述诗歌四要素中他最重视的因素是情调(即节奏),在《论节奏》、《文学的本质》、《论诗三札》等文章中,他反复重申节奏(即内在律或无形律)之于诗歌的重要性。他发现艺术创造与自然现象在发生学上具有同构性,诗歌的节奏根自宇宙律动,正是充满韵律与活力的宇宙律动赋予了诗歌以生命力与感染力,这种“节奏论”使他倾向于素朴的诗学观,使他崇奉纯任自然以及诗人体现自然的作诗原则。如其所言,内在律是诗歌的生命,外在律只是陪衬,较之旧体诗,他认为自由诗别具一种特殊的裸体之美。上述“自然流露”的诗学观,不仅是郭沫若解放诗体、解放人性的文化利器,也是他五四诗歌永葆青春灵性的创造奥秘。
三、“文化—审美”的生态批评观
(一)立足审美批评
作为“五四”之际一位异常活跃的现代批评家,郭沫若建基于文艺观之上的批评观同样饱含生态性。正是前者效法自然、自然生成的精神个性,决定了后者崇奉审美自律、尊重文艺本性的内容及实践。此即郭沫若早期文论倾向唯美主义的生态根源。郭沫若称文艺是艺术家内心智慧的表现,艺术品是艺术家情感自然流露的产物,无功利与无目的乃是艺术本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称唯有无目的性才使艺术合乎时空与生命节奏,趋近文明与人类演进的自然本性,因而又断言“艺术对于人类的贡献是很伟大的”。[15]201这表现在:首先,他以唯美主义立场评价艺术在“统一人类的感情和提高个人的精神,使生活美化”方面具有“不朽的价值”。[15]204其次,体现在他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社会呼吁,他希望艺术能美化日常生活、扩大艺术家生活,让艺术家深入社会真实,发生救国救民的自觉。一言以蔽之,郭沫若主张艺术与人生一体两面,文艺内容若植根生活,不论它采取何种形式,都是血与泪的文艺,都是震撼读者魂魄的文艺,“艺术本身是具有功利性的,是真正的艺术必然发挥艺术的功能”,[16]226“和人生无关系的艺术不是艺术,和艺术无关系的人生是徒然的人生”。[16]227所以,郭沫若从审美救赎角度将艺术重塑为历史进化的原动力,声称艺术的大用说不尽。
如果说在郭沫若那里世界/作家/文本三者之间形成了创作层面的文化生态建构,那么批评家(读者)/文本/作家三者之间则构成了艺术接受层面的精神生态链条。早期郭沫若对批评任务、批评家素质、批评标准等问题的阐发,以体验、关联、生命、创造等活性原则为主导,极具审美张力与生态品性。郭沫若认为批评是崇高严肃的事业,唯有理想的批评家才能胜任愉快,既不负作者又不欺读者。他称这种批评家是不世出的,称批评也是天才的创作。他认为批评家想要超越作家去阐释、评价作品,“就非有更深厚的同情,更锐敏的感受性,更丰富的智识不行”。[17]他又指出批评家若没有披沙拣金的勇气与毅力,就无法在漫无标准的文艺界与漫无限制的文艺家中发现艺术天才,并且批评不应一味寻美而不去求疵。最后,他还告诫读者读一切深邃的书都应该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去批评,唯有立足审美判断力,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才可能获得创见。显然,上述观点不仅有利于科学定位文艺批评的地位与功能,更有利于形塑文艺批评的生命个性与生态品格。
(二)通向文化批评
郭沫若早期文论的另一特征是它的历史文化视野,这使其批评能够突破审美自律论而融入广阔的文化网络。如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一个人文主义时代,五四新文化则是中国的一个“人与文化”的新生时期,它张扬人的价值与世俗生存权利,提供了多种构建自然、文化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现代方案。其中,从生态世界观角度揭橥启蒙大纛的郭沫若代表了这股文化新潮中最具激情与热力的生命维度。这在其文论方面,主要表现在他不局限于就文艺谈文艺,而是在一个容纳天空、大地、诸神和人的文艺空间中,在与民族、历史、文化、时代、风格、美学、阶层、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的阐释中,显示出批评尊严与文化活力,且他的《文艺论集》初版本中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王阳明礼赞》、《论中德文化书》等文就不折不扣地属于文化评论。因而,郭沫若的文论也是文化论。同时,早期郭沫若将审美作为文化尺度的思想倾向,使审美精神融入他的文化批评,又导致他的文化论形同审美论。他曾称瓦特·裴德“不是狭义的文艺批评家,他是广义的文化批评家”,[18]其实他本人也可作如是观。所以,郭沫若早期文论是一种“文化—审美”批评,它扎根于“自然与文化互相补偿”[19]的价值论模式,在身心之间、我与他者之间、多元文化之间建构了文艺批评的深层语义,表达了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首先,郭沫若早期文论从文化的高度倡导灵肉一致的人格与文学。早期郭沫若评价孔子与歌德是球形天才,其文化尺度就是二人在灵肉二维的完满发展。在《〈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中,郭沫若肯定“《西厢记》是超越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20]322并以国人对缠足的崇拜为例证,指出“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性欲者一个庞大的病院!”[20]322-323这不仅点明了《西厢记》反礼教的文化内涵,更从文化高度诠释了现代人道主义取代封建礼教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其次,该时期的郭沫若还在文论中表达了我与他者的和谐人际内涵与世界主义思想。在《论中德文化书》中,老子与尼采在反抗有神论、反抗既成道德,张扬个人本位方面凸现的思想锋芒得到郭沫若的高度肯定,而二人“是为己多而为人少”[4]157的偏见则招致了他的严厉批评。可见,郭沫若“五四”时期在观照自我与他者关系时所持的权准就是一种平等互惠的生态伦理观。在《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中,这种思想更被泛化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该文号召复活传统中国的世界主义精神,“使我们中国得早一日成为世界主义的新国”。[21]再次,郭沫若对文化的多向探讨增进了早期文论的文化活力与文化个性。郭沫若的很多文论都涉及重大的文化母题,比如在《论中德文化书》、《整理国故的评价》、《论诗三札》等文章中,他就对人类几千年文明的起源与目标,各种文化模式的特质与现代化命运,中西文化的优势互补与文化差异,新文学发展与世界文艺的关联等命题作出了深刻的文化检讨……这种文化研究大大拓展了他的批评视野,体现了论者无限的精神活力与创造个性。
[1][美]林恩·怀特.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M]//[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7.
[2]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11.
[3]郭沫若.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4]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致宗白华兄[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5]咸立强.寻找归宿的流浪者——创造社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136.
[6]郭沫若.一个宣言——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作[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22.
[7][美]凯特·里格比.生态批评[M]//[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7-218.
[8]王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40.
[9]郭沫若.三叶集[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0]郭沫若.文艺的生产过程[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17.
[11]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2]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7.
[13][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7.
[14]郭沫若.文学的本质[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52.
[15]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在上海大学讲[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6]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7]郭沫若.批评与梦[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40.
[18]郭沫若.瓦特·裴德的批评论[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54.
[19]马永波.现代性与生态危机[J].文艺评论,2010,(5):24.
[20]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1]郭沫若.国家与超国家的[M]//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85.
On Eco-poetry of Green Literary Review of Guo Moruo
YI Cai-xia1,HUANG Da-jun2
(Depart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Heilongjia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Mudanjiang 157011,China;Department of Literature,Mudanjiang Normal College,Mudanjiang 157012,China)
Guo Moruo is an important founder and pioneer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pedigree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y.Based on enlightenment,he formed an early ecological view of the nature,which laid more emphasis on the ultimate sources of individual view,cultural view and social view.In line with the cultural and poetic ideas,he established the literary poetic view with the dominance of“natural language”and the ecocriticism view with dual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and aesthetics,which greatly widened the vision and realm of criticism.With the view full of enlightenment and ecological connotation,Guo Moruo should be taken as a first-class critics at that time,and his theory also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later literary criticism.
Guo Moruo;View on Nature;Eco-poetry
I206.6
:A
:1672-3910(2013)06-0058-05
2013-06-27
黑龙江省教育厅201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532385)
伊彩霞(1979-),女,满族,黑龙江牡丹江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黄大军(1977-),男,吉林伊通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