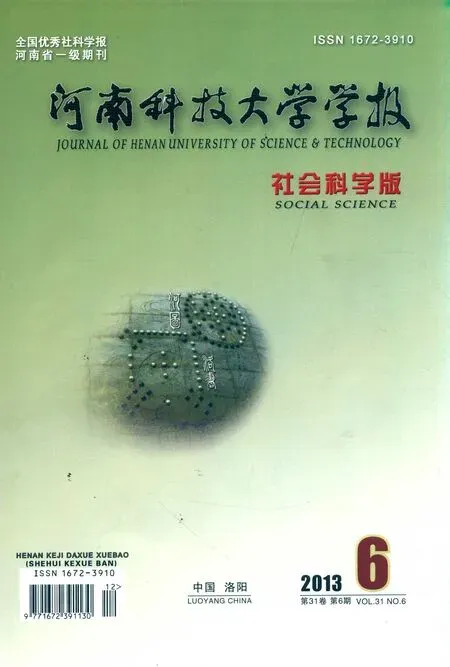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高智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口 570228)
【艺文寻珠】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高智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口 570228)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陶渊明;隐逸诗人;隐逸诗;田园诗
研究六朝隐逸诗,陶渊明是绕不开的话题。因为钟嵘《诗品》把陶渊明称作“隐逸诗人之宗”,所以陶渊明几乎成了隐逸诗人的象征。在隐逸文学发展史上,陶渊明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古代至他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隐逸文学。在隐逸诗歌史上,他就像一座横亘的高峰,使人无法超越。
虽然陶渊明研究成果斐然,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例如,钟嵘品陶“隐逸诗人之宗”在六朝是否被公认?“只为田家语”是不是时人对他的普遍看法?《文选》与《艺文类聚》辟“隐逸诗”而未录陶诗,所录陶诗,多入“田”部、“园”部,原因何在?陶渊明隐逸诗歌中,为什么鲜见“隐”踪?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的地位,何时得以确立?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探索。
一、陶渊明隐逸思想的特殊形态
陶渊明的隐逸是一种特殊的形态,有别于六朝一般的隐士。六朝隐士炼丹求仙,佛道杂糅,几成时尚。如果用隐士的诸多标准衡量,陶渊明似乎都是徒有虚名。他实在是一个独特的隐士。六朝隐逸现象纷纭复杂,无论是愤世嫉俗存身成仁的忤世之隐,还是蔑视富贵立德体道的避世之隐,抑或以退为进待价而沽的待时之隐,都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如隐士是礼义秩序的突围者,他们对传统的礼义制度持保留并改造的态度,既遵循礼义制度的基本伦理,如孝悌、仁德等,又对国家政治权力领域表示抗拒,对现有秩序表示批评或不满,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与神仙道化系统关系密切等。与此相比,陶渊明在现世秩序中的“撤退”,主要目的是保全个性独立与精神自由,是醉心田园回归自然的真隐,与以隐逸博取浮名彰显德行的隐逸要区别开来。
(一)辞官目的
陶渊明辞官主要目的是“归田之隐”,而非一般岩穴之隐,“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年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他喜欢农耕生活,这有别于一般隐士。“不为五斗米折腰”,虽有出于人性独立的要求,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缘于“性本爱丘山”,对“躬耕田园”、“开荒南野际”的喜欢。这与脱离农业生产的隐士大为不同。
陶渊明主张“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年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回归田园,崇尚力耕,自耕自食成为他理想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他受到舜耕历山、思慕父母影响,反映出自给自足的思想;另一方面,这亦是其家风濡染的结果。曾祖父陶侃,虽至显宦,但出生低微,居于槃瓠蛮杂居的“五溪”,被嘲为“溪狗”,发迹前属于“寒门”。《晋书·列女传》载范逵访陶侃,侃母湛氏“截发卖与邻人,供肴馔”,家贫若此,大概属于地位低贱的阶层,经常从事农业生产。后陶侃任荆州刺史,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陶侃对于劝课农耕,务勤稼穑很有一套方法,这对陶渊明喜欢“开荒南野际”的农事劳动有直接影响。他很可能从小就参加农业生产。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游西走。”“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陶渊明因家贫,一家老小常事耕作。颜延之评陶渊明“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由此可知他参与农业劳动之外,还卖过菜,打过草鞋,织过席子,与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无异。自29岁出任州祭酒,他就一直怀有回家躬耕之意,“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移居》其一)。41岁做了彭泽令,他不愿奉迎督邮成为导火索,于是乃解印绶回归故里。他热爱农耕,萧统对此褒扬不已,以为史无前例:“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大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集序》)
陶渊明从事农耕,也和家庭环境大有关系。萧统《陶渊明传》载其妻翟氏“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南史》亦曰:“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终其一生,夫妻同心,汲汲于农事。所以陶渊明《自祭文》有“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等语。总括一生,勤劳耘耔,悠然于田园之乐,这就是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
(二)拒入庐山莲社
陶渊明隐逸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不合时宜”,与隐逸潮流保持距离。他婉拒庐山莲社,与炽风正盛的隐士集团划清界限。《莲社高贤传》云:“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莲社是当时名噪一时的隐逸集团。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七月,在慧远主持下,刘遗民等130人,同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斋会,发誓往生西方,由刘遗民撰写发愿文。刘遗民等人多隐居山林,与慧远交往颇深。此外,参与者还有当时著名隐士雷次宗、周续之、毕颖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十八高贤传》中,除上述诸人外,还有慧永、道生、慧持、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等人。另不入社诸贤传,列有陶渊明、谢灵运、范宁三人。陶渊明《和刘柴桑》诗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正是他婉言谢绝刘遗民的援引而作,称“未忍言索居”,是他不想脱离现实生活去隐居,主要是眷念田园与亲人。“茅茨已就治,新田复应畬……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实际上他已和割舍妻儿入山林而不返的隐士划清了界线。就此而论,大约可以推出,陶渊明是心隐甚于身隐的。
(三)少在征辟之列
晋宋之际,隐士常被征辟,而陶渊明不应征辟,也少在朝廷征召之列,似乎也可看出他与其他隐士的区别。刘宋新朝,为粉饰太平,朝廷搜寻隐逸,求贤诏书频发,“孝顺忠义,隐滞遗逸,必令闻达”(宋武帝刘裕《矫晋安帝诏》,见《全宋文·卷一》)。武帝即位,即征戴颙:“前太尉参军戴颙、辟士韦玄,秉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进退。并可散骑侍郎,在通直。”(《宋书·隐逸传·戴颙传》)尔后他又重点招揽庐山隐士集团,下书辟宗炳、周续之等:
“吾添大宠,思延贤彦,而兔罝潜处,考槃未臻,侧席丘园,良增虚伫。南阳宗炳、雁门周续之,并植操幽栖,无闷巾褐,可下辟召,以礼屈之。”(《宋书·宗炳传》)
文帝于元嘉二年,又诏征戴颙、宗炳:
“新除通直散骑侍郎戴颙、太子舍人宗炳,并志托丘园,自求衡荜,恬静之操,久而不渝。颙可国学博士,炳可通直散骑侍郎。”
刘宋大肆搜寻隐逸,庐山莲社诸人,多见于列,今所见材料,鲜见征召陶渊明。《宋书·隐逸传》将刘遗民、周续之与陶渊明并举,其实不能简单等同一类,刘与周都辞家别亲,隐于庐山,且朝廷屡加征召。后者则居于乡里,亲朋在旁,置身家中,从事农耕,“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与传统的隐逸模式是相悖的。在农耕社会里,辞官归田也算常态,加之“不为五斗米折腰”,因此陶渊明不在征辟之列亦在情理之中了。
(四)与佛、道关系疏离
从东汉到三国,随着佛教开始输入中国,人们开始接受佛老性命学内容并以本土黄老之学来比较理解佛教教义。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佛经的翻译,人们对佛教教义有了更加深入系统的了解,出现了一批既精通佛学,又通晓儒、道的大师,佛家的性命学进入繁盛时期。于是小乘佛教的禅定也开始被人们所认识,运用意识进行呼吸修炼,坐禅静修的方式,使“虚静”不仅成为隐士的“养生术”,而且成为士人的一种潮流。魏晋以降,佛教传播日盛,“四方学士,竞往师之”,佛教和隐逸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佛教主张以“大寂”“执寂”来达到“禅观”,和隐士崇尚的“虚静”一样,成为修炼“心性”的重要方式之一。
夫执寂以御有,策本以动末,有何难也。(《祐录》卷六:《安般注序》)
以大寂以至乐,五音不能聋其耳矣;以无为为滋味,五味不能爽其口矣。(《祐录》卷六:《阴持入经序》)
东晋偏安江左之后,隐士多沾染儒道。隐士学佛结社,成为潮流,著名的有前述庐山隐士集团等。个人修行则更普遍,《南齐书·高逸传》中的刘虬,罢官还家,隐居不仕,潜心学佛,注《法华经》。《梁书·处士传》载范元琰事,称其“博通经史,兼精佛义”,朝廷屡加征辟,皆隐居不赴。《魏书·隐逸传》中的冯亮,笃爱佛理,世宗召为羽林监,固辞不受,还山与僧徒礼颂为业。隐逸与道结合,更广泛一些,如葛洪归隐罗浮山,炼丹修道。陶弘景隐居之后,搜罗道教古本真经,著《真诰》、《真灵位业图》等道家经典。当时的隐士,多有隐士和道士双重身份。
整个六朝,隐士非佛即道,鲜有例外。在时代潮流中,陶渊明却很“另类”。他怀疑佛教的“轮回”,“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感士不遇赋》)。他写作《形影神》三首,反对唯心论,质疑佛教神不灭论,“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影答形》)。逯钦立就此论曰:“此诗乃反对慧远的报应说和形尽神不灭说。”[1]陶渊明诗作中偶有“冥报”、“幻化”,“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也仅是感叹“世事难料”、“死没无常”而已。朱光潜论及陶渊明与佛教关系,说“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底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诗里不但提到‘冥报’而且谈到‘空无’,我并不敢因此就断定渊明有意地援引佛说,我只是说他的意识或者下意识中可能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2]他还认为道教的炼丹服饵、神仙之学不可信,“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神释》),求仙行不通,批评修炼成仙荒谬,认为神不灭论不可信。表达自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提出生死在天的宿命观,与祈求成佛成仙的隐士有着不小的距离。整个六朝时期,隐风大炽佛道兴盛,陶渊明浸染其中,鲜受影响,究其原因,梁启超认为陶渊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处用力处都在儒学”,强调陶渊明是“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3]
(五)与陶弘景等六朝隐士的比较
六朝时期隐逸类型发生了变化,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真假隐士,鱼龙混杂。东晋士人既沿袭先秦以来传统的儒学影响,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又受传统道德影响,不事二君,高尚其事;既受佛教思想影响,心神空灵超脱人生,又受道家思想影响,崇尚无为,崇尚养生。而陶渊明等则受自然田园的影响,性情恬静,清心寡欲,寄情农耕,变为新的隐逸类型。
《晋书·儒林传》与《晋书·隐逸传》录陶潜、汜毓、董京、硃冲、伍朝、鲁褒、谯秀、辛谧、张忠诸人为隐士,除了硃冲“以耕艺为事”与陶渊明相近外,其余诸人,汜毓“不蓄门人”,董京“被发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谯秀“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张忠“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或行为乖张,个性张狂,或饵石服药,寻道觅仙,与陶反差较大。
比陶渊明晚出的陶弘景,是六朝隐士的典范,与陶渊明颇为不同。两人的自称差异很大。陶渊明作品中,自谓“余”“我”“先生”等,不见“隐”踪。陶弘景则自谓“隐居先生”、“隐居”、“华阳隐居”、“陶隐居”等:
隐居先生在于茅山岩岭之上,以吐纳馀暇,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本草序》)
太岁庚辰,隐居曰:余宅身幽岭,迄将十载,虽每植德施工,多止一时这设,可以传芳远裔者,莫过于撰述。(《肘后百一方》)
华阳隐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词:窃寻下民之命,粒食为本。农工所资,在于润泽。(《请雨词》
山民陶隐居仰咨:《论》云:前佛后佛,其道不异。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随方受职,西国密迩,厥路非远。(《难〈镇军沈约均圣论〉》)
从两人与隐逸有关的作品看,他们对隐逸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陶渊明诗作中谈及“隐”的仅有两处:《命子》其一“凤隐于林,幽人在丘”。《与殷晋安别一首》“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陶弘景作品中,几乎处处可见隐逸,专篇论述隐逸的文章即有《华阳颂》、《发真隐诀》序、《寻山志》、《云上仙风赋》等。
二、陶渊明隐逸诗歌的特殊形态
(一)作品中反映的对隐逸的态度
陶渊明诗歌,反映了隐逸与田园的结合,保持对岩穴、山林之隐的疏离。陶渊明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隐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九日闲居》),“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归园田居》其四是陶渊明对隐逸态度的集中体现: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陶渊明“携子侄辈”,去看望隐居“荒墟丘垅间”的朋友,不见隐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问采薪者隐者行踪,得知隐士“死没无复馀”,引发感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篇首“久去山泽游”,寓示了他对“山泽”为代表意象的“隐逸”文化是保持距离的。“山泽”和“田园”是陶渊明思想中的分水岭,隐居山泽做隐士,不如隐于田园从事农耕,“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咏贫士》),“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对田园的热爱和高洁的操守也可合二为一。
陶渊明轻视沽名钓誉的隐逸,拒入庐山莲社,似乎不太喜欢隐士枯淡无味的生活。他主张日常生活艺术化,评论隐逸现象时,着重强调“自然”和“归耕”两点,“密网裁而鱼赅,宏罗至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他在《咏贫士》、《咏二疏》、《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评论隐士,主要是表达“固穷守节”之意。
陶渊明的很多作品不是“避世”,而是积极“入世”,关心民瘼:“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饮酒》);“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拟古》);“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杂诗》);“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这些作品皆有悯时伤世,浓郁豪放的一面。金元好问评“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清沈德潜也赞曰“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说诗晬语》)。
(二)隐逸与田园结合的完成
隐逸诗到东晋,表现为隐逸与玄言的结合、隐逸与山水的结合、隐逸与佛教的结合,而隐逸与田园的结合,则由陶渊明完成。陶渊明诗歌分类,田园诗占主导,多作“农家语”。从题材内容来看,廖仲安把陶诗分为田园和咏怀两类,[4]锺优民则将其分为田园、哲理、抒情三类。[5]袁行霈、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2卷,又把陶诗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有所增益,较为完备,强调了田园诗的重要地位,认为“他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题材”,代表作多为集中写田园生活的作品。认为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劳动中蕴藏的美,把平凡无奇的农村生活写得诗情画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6]
通观陶诗,多是农事诗,描写农耕生活为主,“居备勤俭,躬兼贫病”(颜延之《陶征士诔》),是小农社会里最寻常的农事活动,是士大夫与农业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把普通的农事活动上升为艺术化的审美体验。
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受东汉以来田园赋体的影响很深,陶渊明之前描写田园生活的赋体已经很普遍了,源头可以上溯到东汉中期张衡的《归田赋》。李善《文选》注曰:“归田赋者,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汉末仲长统有《乐志论》,“使居有良田广宅,北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描摹了一幅充满自然气息的田园生活画卷。魏晋开始盛行《藉田赋》、《归田赋》。曹植《藉田赋》写王公贵族参与农业劳动,“千乘之体于陇亩之中”“玉手劳于耕耘”。稍后的缪袭《藉田赋》祭祀土地,颂扬“田祖”。潘岳《藉田赋》篇幅宏大,为这类作品的杰构,“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设坛拜祭,“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劝穑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农业为立国之本,物产之饶以供日常之需,可以致孝。张华《归田赋》“归郏鄏之旧里,托言静以闲居”,声言归于旧里,参加农业劳作。这些赋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对陶渊明影响很大,他的田园诗赋,如《归去来兮辞》等,都可以看出上述作品的影响。
陶渊明有一些论及隐逸的诗歌,以隐居自况,表明自己田园生活的情趣,借“衡门”之闲,抒“灌园”之乐,如《答庞参军并序》其一: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命子》诗10首(《册府元龟》作《训子》),前6首述陶氏先世功德,“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朝代隆替,世事纷乱,陶氏人才像凤凰隐蔽在山林一样,隐居山丘而不仕,后4章表达对儿子的希望,“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山河,启土开封”,诫勉儿子勤奋不懈,积极入世。
三、陶渊明身份定位推论
钟嵘《诗品》评陶渊明“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这是给陶渊明准确的定位,此后遂为定论。但反推论之,钟嵘云“岂直为田家语邪?”是否可以推出自东晋至梁,陶渊明的定位都是“隐士”或“田园诗人”呢?
沈约撰《宋书》,列陶渊明入“隐逸传”,对其作品只字未提,大约是默认陶渊明隐士身份的。而《文选》与《艺文类聚》未录陶诗,似乎可以说明,整个六朝时期,陶渊明隐逸诗人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强化和确认。
(一)《文选》与《艺文类聚》辟“隐逸诗”未录陶诗
萧统是第一个真正认识陶渊明价值的人,他为《陶渊明集》作序,并撰《陶渊明传》,言“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陶渊明集序》),六朝以华丽秀美文风为尚,萧氏独具慧眼,以为陶渊明“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夸赞其作品“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萧统对其躬耕田园、不慕名利的品性很是欣赏,“加以贞节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文选》录诗23类,首列隐逸诗,分为“招隐诗”与“反招隐诗”,其中“招隐诗”录3首,左思二首陆机一首;“反招隐”诗录王康琚1首。《文选》所录陶渊明诗共7首,分别是《挽歌》、《饮酒》2首、《咏贫士诗》、《读山海经》入“杂诗”类,《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入“行旅”类。但整个“隐逸类”诗未录陶渊明一首作品。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六,“人部”二十一辟“隐逸类”,收录唐前隐逸资料,录隐逸诗37首,其中晋代11首,张协1首,张华2首,张载1首,左思2首,陆机2首,闾丘冲1首,王康琚1首,辛况1首。《艺文类聚》录陶诗10首,却未有一首诗入“人部”隐逸类。各诗分布情况如下:《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入“人部”行旅类,《读山海经》其一入“杂文部”,《贫士诗》“万族皆有托”(《咏贫士》其一)与《咏贫士》其四“安贫守贱者”二首入“人部”贫类;《饮酒》十三“有客常同止”入“食物部”酒类;入“产业部”田类的有《杂诗》“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其一“开荒南野际”、《饮酒》其五及其七,即“结庐在人境”与“有客常同止”并为《杂诗》一首,两首诗并入“产业部”园类;“杂文部”史传类录《咏荆轲诗》。
《文选》与《艺文类聚》辟“隐逸类”,而未收录一首陶诗,把陶诗归入他类,绝非偶然。从两部书的分类看,陶诗多入“产业田园”类与“行旅杂诗”类,正说明他的诗歌已经完成从隐逸到田园的结合,同时也说明,从东晋至初唐,陶渊明隐逸诗人的称号,还未被广泛接受。
(二)陶渊明入“隐逸传”探究
房玄龄等著《晋书》,仍列陶渊明为隐逸传。把陶渊明列入隐逸,和史书的编撰体例是有关系的。二十四史中几乎皆在隐逸记载,其中十四史特辟隐逸专传,有关六朝史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皆有隐逸,只是名称各异,《晋书》《宋书》《南史》《北史》作隐逸传,《梁书》作处士传,《魏书》有《逸士传》,隐逸史料的兴盛,说明了这一时期隐逸思潮的泛滥。
正史中特辟《隐逸传》,无非是要树立道德上洁身自好的圣人,提倡士人淡泊功名,不过分汲汲于仕途,这也正是《隐逸传》中常说的“激贪止竞”的目的。[7]陶渊明之前西晋的朱充,以耕艺为业,好学而贫,征书到来,便遁入山林隐居。(见房玄龄等《晋书·隐逸传》)。陶渊明眷念田园,钟爱自然,虽没有征书频下,隐居山林,但因其曾祖陶侃的影响力,加之自己弃官躬耕的行为艺术,在六朝隐风盛行的潮流中,入隐逸传,导致其诗歌成就被忽视,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决定的,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陶渊明隐逸诗人身份确定
陶渊明同时或稍后,绝少论及他的隐逸诗作。六朝文风以华美为尚,对其评价多集中于道德品性,对其文学成就评价不高。颜延之在陶渊明去世后,为他写下《陶征士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钟嵘《诗品》虽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但仅列陶渊明为“中品”,对其评价不高,对其诗避而不谈。
唐立国后,陶渊明的影响渐大,诗作的田园风光与闲适的口味深得唐人喜爱。王绩《醉后》诗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孟浩然云:“赏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他们对陶渊明十分崇拜。李白仰慕其人品,引陶渊明为知己,“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白居易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访陶公旧宅》)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以“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表达自己的羡慕之情。唐以后,苏轼与辛弃疾等的推崇,陶渊明隐逸诗人的地位才在文学史上确定下来。
四、结语
陶渊明自诩“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他隐于田园,旨在农耕,“躬耕自资”,摒弃山居岩栖枯淡冷寂的隐居生活;他不应征辟也少在朝廷征召之列,他不满意当时隐士的生活方式,自觉与隐士保持距离;他不溺于佛道,不以隐逸为名,不自谓隐士。种种异于隐士的表现,恰好说明陶渊明懂得隐逸的真谛。他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用他的诗歌创作,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使之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这是他对中国隐逸诗学的重大贡献。
[1]逯钦立.《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M]//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218.
[2]朱光潜.诗论:第13章[M]//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254.
[3]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7.
[4]廖仲安.陶渊明[M].北京:中华书局,1963:67.
[5]锺优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82-194.
[6]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5.
[7]戴显群,王营绪.正史《隐逸传》反映的隐士隐逸原因及编撰意图[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6-80,90.
An Argument on Tao Yuanming as“Father of Recluse Poets”
GAO Zh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Hainan University,Haikou 471023,China)
Tao Yuanming was regarded as“Father of recluse poets”by Zhong Rong(钟嵘:AD468-518)in his Poetry Gradings,which did not get confirmed in the Six Dynasties(AD220-589).As a hermit and a pastoral poet,Tao Yuanming showed great differences from other hermits and pursued a perfect recluse life by dropping out of official life and taking up a cultivated life.He combined poem writing with pastoral life and opened up a path for artistry of easy and comfortable recluse life.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ao Yuanming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cluse poetry in terms of reform in recluse poetic form with rich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unique recluse spiritual space.
Tao Yuanming;recluse poet;recluse poetry;pastoral poetry
I206.2
:A
:1672-3910(2013)06-0041-006
2013-07-04
高智(1974-),男,重庆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