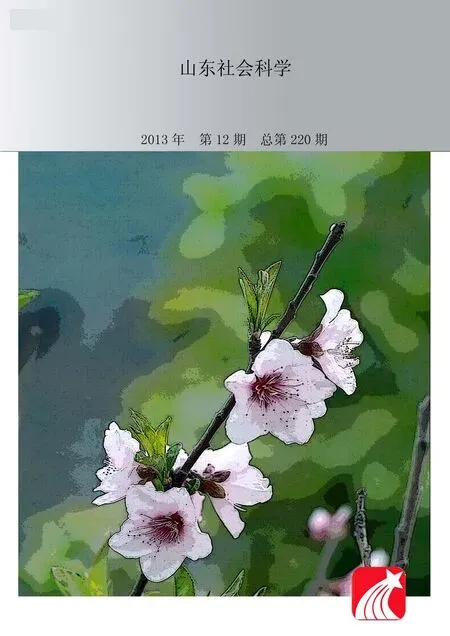《神谕女士》的母亲形象及文化隐喻探析
张传霞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神谕女士》(LadyOracle,1976)是“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国内外研究者对作品的叙事技巧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极大兴趣,提出互文性、身体叙事、现代寓言等等观点。然而,阿特伍德是一位有着理论自觉的作家,艺术技巧只是其表达主题的工具,我们应透过叙事的表层来考察背后的深刻寓意。女性生存是阿特伍德作品的三大主题之一,她塑造了众多陷于生存困境的女性形象,但母亲形象却并不多见。鉴于此,《神谕女士》中的母亲在阿特伍德的女性谱系上就显得特异,不得不引起关注。在作品中,阿特伍德不仅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了母亲对女主人公琼童年的影响,还采用梦幻、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让母亲的幽灵多次出现在琼成年后的生活中。母亲是琼挥之不去的影子,因此是探解作品女性主义主题的一把钥匙。
在父权文化中,做母亲是“女性唯一有价值的命运”①Luce Irigaray.Thinking the Difference Trans.Karin Monti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4. p.99.。从某种极端的意义上讲,做女人就意味着做母亲。女性身份与同母亲身份紧密相连,“理解母亲就是理解女性”②刘岩:《母亲身份研究读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因此要建构独立的女性主体,必须从研究母亲的身份开始。而要理解《神谕女士》中的母亲,就不得不借助“元文本”——丁尼生的长诗《夏洛特姑娘》(TheLadyofShalott,有人译作《夏洛特夫人》)。“夏洛特姑娘”是中世纪骑士传奇《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因其神秘凄美的气质成为西方艺术常见表现题材。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据此写成的叙事诗《夏洛特姑娘》,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神谕女士》中引用的就是该诗作。故事的大意是:夏洛特姑娘被诅咒囚禁在夏洛特岛上,她只能通过镜子看世界,并且要把镜子反映的景象编进织物,决不能停下来看窗外,否则诅咒就会降临。一天,骑士兰斯洛特从夏洛特窗前经过,他的影子出现在镜子里。夏洛特被兰斯洛特吸引,离开织机跑到窗边。这时镜子碎裂,诅咒降临了。可是,夏洛特为了寻找爱人,还是溜出了塔楼,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阿特伍德在作品中并没有正面描写《夏洛特姑娘》,而是在行文中或隐或显地加以暗示。阿特伍德把《夏洛特姑娘》有机地镶嵌在作品中,与母亲的故事形成一种跨时空隐喻,其效果就像夏洛特织布那样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女性真实生存的图景。
一、作为“高贵女主人”的母亲——自我囚禁的“夏洛特”
“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③[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位置在家庭,而在家庭中的位置是由她作为母亲的角色决定的。“这是父权文化中所有女性的位置。……在家庭中,女性被安排得如此合理,以至于家庭就自然地成为她所属的地方”。[注]Juliet Mitche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A Radical Reassessment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London: Penguin Books.1974. pp.405-406.女性被父权文化被动地安排进家庭,并被赋予“高贵女主人”等神圣的名称,让女性甘心情愿承担被分配的社会角色。所谓“高贵女主人”中的“主人”,不是出入自由的“特赦令”,而是打造精美的“黄金甲”。要成为“高贵女主人”要具备很多条件,如相貌娇美、品味高雅,更重要的是把家庭当作事业去经营。由此可见,“高贵女主人”实质是男权文化给女性施放的迷惑性咒语,目的是把女性囚禁于家庭。
琼的母亲就是一个中了男权文化魔咒的女性。她把当“高贵女主人”作为理想去追求。“她为我们奉献了一生,她遵守本分,将家庭当做毕生的事业。”[注][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神谕女士》,甘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下文所引原文皆据此,不一一注释,只随正文夹注页码。母亲为扶持丈夫的事业举行家庭聚会,为了女儿的未来千方百计让她减肥,为了让起居室和别人家一样而研究家装。母亲也曾尝试家庭以外的工作,但很快就回归家庭,“她觉得无法发挥自己”(第73页)。母亲已经把男权社会的咒语内化为自我的行为标准,不愿走出家庭。在这个意义上说,母亲是自我囚禁的“夏洛特”。家庭是她的塔楼,丈夫、女儿、家务是她的织机。
在家庭这个“所属的地方”,母亲真的是“主人”吗?她真正的境况是什么?在家庭中,母亲没有名字只有职能,她是母亲和妻子。然而,无论在女儿眼中还是丈夫眼中,她都是一个异化的形象。在琼看来,母亲是长着三个脑袋的怪物。除了叫她“母亲”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称呼,更没有稚嫩的爱称。亲密的母女关系异化为冷漠的职业关系:“我们关系早就被职业化了:她的角色是经理人、发明人、代理人,而我是她的产品。”(第72页)母亲失掉了生理学意义上的“母性”,只剩下社会伦理意义上的“母职”。她充当男权社会的“教习嬷嬷”,按照男性审美标准塑造女儿。在父亲看来,母亲是一个牢骚满腹的怨妇。他们分房而睡,父亲大部分时间以工作繁忙为由不在家。父亲不和母亲谈心,即使发生争执,父亲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寥寥数语打断母亲(如闭嘴、我告诉过你别提这事)。可见,在这个“所属的地方”,她空有“主人”的名衔,没有自我也没有实际主导权,“人的个性和尊严被剥夺”[注]张中锋:《论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与文化救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无人倾听也无人关心她的痛苦,她被流放到荒芜的精神世界。因此本质上她是这个家庭的“他者”,是被女儿和丈夫的精神世界排除在外、“包裹在寂静中”[注]刘岩:《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的夏洛特姑娘。
与夏洛特姑娘一样,母亲也以死亡终结。不同的是夏洛特姑娘死在了寻爱途中,而母亲死在了“塔楼”里。关于母亲的死亡,琼感到迷惑。意外?自杀?还是他杀?琼通过翻看家庭相册,获悉了母亲死亡的原因。早期相册中,有很多母亲与年轻男子的合照,那时母亲没有结婚,年轻貌美,很受追捧。照片中的她朝着镜头快乐地笑着。后来是母亲与父亲的结婚照,再后来只有母亲自己,接下来全是琼的照片。当琼六岁以后,“照片突然没有了。一定是母亲在那个时候已经放弃了我……也许她不再希望保存我的成长记录,她已经认定我没救了”(第43页)。家庭相册是记录母亲生命的另一种密码,通过解读我们发现,母亲在踏入婚姻时生命之花就已经开始枯萎,家庭的高墙阻断了其他的生活可能。而“塔楼”内,“父亲和我完全没有按照她所希冀的那样,让她的人生充满意义”(第200页)。据此,母亲死于绝望,而婚姻家庭是罪魁祸首。
“在漫长无爱的婚姻中,女性原本鲜活的生命被一点一点榨干,强大的父权制如铜钉般将她们牢牢钉住,使之动弹不得。”[注]高娟:《“可怕的母亲”与“巫母群像”——论莫里亚克与张爱玲对传统母亲形象的颠覆性书写》,《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通过母亲和父亲争吵的只言片语我们可以推断出,母亲未婚先孕,为防止名声受损,不得已嫁给了父亲。从此断送了母亲追求自我生活的可能性,于是她把重心放在支持丈夫事业、培养女儿成为淑女上。母亲希望通过支配丈夫和女儿以实现自我。正像波伏娃分析的母亲对儿子和女儿的复杂关系那样,母亲渴望分享儿子征服世界带来的不朽英名(《神谕女士》中父亲承担了儿子的功能),所以督促父亲学习麻醉技术并张罗家庭聚会以期帮助父亲发展事业;母亲把琼当作自己的一个分身,“把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之处投射到女儿身上”[注][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试图通过女儿达成她的心愿。但是结果并不如她的意,父亲不愿回家,女儿以更加肥胖抗拒减肥。两个分身对她的背叛,使她本来就空荡的自我更加无所依托。因此,可以说夏洛特死于对诅咒的抗拒,而母亲则死于对父权制咒语的依从。
二、 作为“神谕女士”的母亲——逃出塔楼的“夏洛特”
鲁迅先生在1923年12月26日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做过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指出女性独立面临重重阻碍,并从事理上推想,“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注]鲁迅:《坟:鲁迅杂文精读》,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72页。。那么不妨仿照鲁迅先生也来作一番假设,夏洛特姑娘不死会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逃出家庭的琼在社会上的一系列遭遇中寻得。琼的经历表明在男权社会中咒语无处不在,要实现自我的真正自主绝非易事。
首先女性面临的是自我束缚。女性已经把男权意识内化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自觉践行男性对女性的各种期待。所以,琼只有在主动减肥变成美人后才敢逃离家庭,且改名换姓隐瞒肥胖的过去。即使依靠写作获得了经济独立,在男性爱人面前还是要收敛锋芒,扮演安静纯洁的天使。需要注意的是,琼的哥特小说创作给她带来了财富,却没有带来心灵的满足。原因在于,她的哥特小说完全是男性阅读期待下的产物,书中充斥的是英雄拯救美女的套路,就像她实际中经历的那样。琼的哥特小说是男性思维的写作,因此不能构成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克苏(Héèlne Cixous)所说的“女性书写”。
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书写”从琼尝试自动写作开始。当琼的感情生活陷入困境之时,写作也面临瓶颈。为让写作有新意,琼尝试自动书写。她买了一面和母亲的一样的三面镜,点燃蜡烛放在镜子前。她凝视镜中的烛火,进入催眠状态。她潜入了无意识,发现在地底下有一个不快乐的女神。每次清醒琼都会在纸上写下一些词汇,她把词汇联缀充实就形成了同名散文诗《神谕女士》。起初琼并不知道那个深藏地下的女人是谁,后来琼体验了男性社会对她的一系列“暴力”之后,才明白那个不快乐的女人是她的母亲,那些词汇是母亲发给她的神谕,母亲就是神谕女士。
这就涉及女性建构自我身份的第二层阻力:语言。男性话语建构着女性形象,并阻碍女性的自我表达,因此只有发明一种有别于男性话语的言说方式,女性才能建构起自我主体身份。母亲的幽灵以及通过自动书写展开的潜意识对话,都是女性言说、女性书写的尝试方式。母亲是被男权文化建构出来的,她使用的是男性话语。这种男性话语主要有两个弊端:首先它传递的是男性价值观念。在这种价值体系中女性处于客体的位置,最终会沦为男性的消费品。母亲以男性的审美观改造琼的体型,并“威胁“女儿减肥否则嫁不出去。本质上母亲在替男性“教育”女儿,她是男性社会价值观的发言人和代言人,“母亲角色承载的是父权意志”[注]石万鹏:《论“五四”以来女性文学中母女关系的写作》,《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因此母女之间根本没有交流,只有灌输和被灌输,琼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变体。其次,男性话语属性为男,不能表达女性的欲望和需要。“如果不发明一种语言,如果不找到自己身体的语言,那我们的故事就不会有太多办法再现。”[注]Luce Irigaray.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Trans. 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214.在男权社会里,母亲已经丧失了自我表达的能力。阿特伍德在文中关于母亲嘴唇的描写意味深长地表现了这一点:“她的嘴唇很薄,却用口红在唇边画出了一个更大的嘴,像贝蒂·戴维斯的嘴,那让她长出了一张奇怪的双层嘴,真嘴嵌套在假唇里,如影子般显现”(第73页)。因此,在现实生活层面母亲与女儿无法也不能交流,她必须发明自己的语言表达自我,母亲的幽灵就是她表达自我欲望和痛苦的另一种“语言”。
母亲使用的这种“语言”对于习惯了用男性语言言说和理解的琼来说无异于“神谕”,对母亲发出的“神谕”的参详经过了复杂的过程。母亲的幽灵在其生前死后五次出现在琼面前,琼的态度也经历了厌恶、恐惧、漠视、好奇到最后同情理解的变化。母亲的幽灵每次都出现在琼的生命转折点上:即将成人之时、陷入爱情之时、举行婚礼之时、婚姻出现危机之时、逃避无望之时。这些都说明母亲一直在给琼发出“神谕”,从来没有放弃过琼,只是琼已经习惯了用男性话语思考,所以对母亲发出的“神谕”并不理解。当她逃出家庭,以一个女人的身份进入真正的男性社会,体验到曾经加诸在母亲身上的一切的时候,她才听懂了母亲发出的“神谕”。
从一定意义上说,逃出身体禁锢的母亲用别样的话语方式诉说了女性的痛苦,建构了自我主体性,同时也帮助琼一步步地建构起主体性。琼作为又一个逃出塔楼的“夏洛特”,并没有找到理想中的“骑士”。她遇到的三个男人无一不是想控制她、改造她的“父亲”。为迎合她的“骑士”,她隐瞒肥胖的过去、压制写作的才华。琼放弃自我去寻求爱,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男人的一面镜子。正是在这样的体验基础上,琼才认清了母亲的“夏洛特”处境,“她就是那个在死亡之舟上的女人,那个被困在塔中、披着光滑秀发、眼神哀伤的女人”(第378页),才听懂了母亲发出的“神谕”: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反射物而存在,女性都是被男权文化施放了咒语的“夏洛特”。
丁尼生笔下的夏洛特虽然身体逃出了塔楼,但她还没见到爱人就已经死去。在她一生中没有任何人听到过她讲话,她是一个被彻底消音的形象。因其美丽圣洁,她成为男权社会的理想女性形象,被用来规范女性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丁尼生的夏洛特对女性解放来说是首先要破除的一个咒语。阿特伍德笔下的母亲虽然身体始终没有离开家庭的塔楼,但是她采用各种方式去言说自己的痛苦,这种逃离比夏洛特的逃离更有意义。“作为意义承载者的女性身体始终都处于被压抑与奴役中,一如米歇尔·福柯所谓话语是社会性权力的体现,只代表权力,而不代表真理。”[注]季红真:《永不陨落的文学星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母亲不仅用“神谕”这种有别于男性话语的方式诉说了男权社会对她的“迫害”,而且帮助女儿认清了自己的“夏洛特”命运,为下一代的女性解除父权魔咒奠定基础。
三、母亲的文化隐喻
母亲是西方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常常代表丰饶、生产、起源、死亡、危险等意义。但这些文化象征是男权社会赋予的,是被建构起来的。在西方文明起源问题上,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里加蕾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整个西方文化基于杀母。”[注]Irigaray, Luce. “Women - Mothers, the Silent Substratum of the Social Order.”The Irigaray Reader.Ed. Margaret Whitford. Trans. David Macey. Cambridge, Mass.: Wiley-Blackwell Publishers.1992.p.47.伊里加蕾所说的“杀母”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谋杀,而是指把母亲从男性权力中心驱逐,剥夺母亲的话语权,使母亲只存在于支撑男性社会秩序和欲望秩序层面上。母亲是女儿的养育者,母亲主体性的缺失会造成女儿主体性的缺失。因此要建构独立的主体身份,必须打破母亲的沉默状态,让母亲发出自己的声音,恢复被男性历史割断的女性谱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神谕女士》中的母亲不仅是一个物质实体,还是一个文化隐喻。她代表了整个被男权话语建构起来的女性神话,这个女性神话就像施放在“夏洛特”身上的咒语,在一代代的女性身上重演。母亲通过“神谕”的方式言说自我的痛苦,揭开了男权话语建构女性传统的神秘面纱。琼通过读解母亲,洞悉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实施的咒语,也找到解除咒语的方式。最后,琼和母亲建立了相互倾听、平等交流的“女性与女性”的互惠关系,“我们俩将相互陪伴沿着走廊,走进黑暗”(第378页)。母女携手走进黑暗隐喻从西方文明源头便被割断的母女关系纽带的恢复,表明琼汇入了被男性文化遮蔽的女性谱系,从而建构起女性的主体身份。只有女性不再局限于母亲、女儿的社会角色,建立一种女性与女性之间平等关爱关系的时候,女性才能真正建构自我主体身份。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而通过塑造母亲的形象思考女性自我救赎方式,在她的文学地图上无疑是特异而深刻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