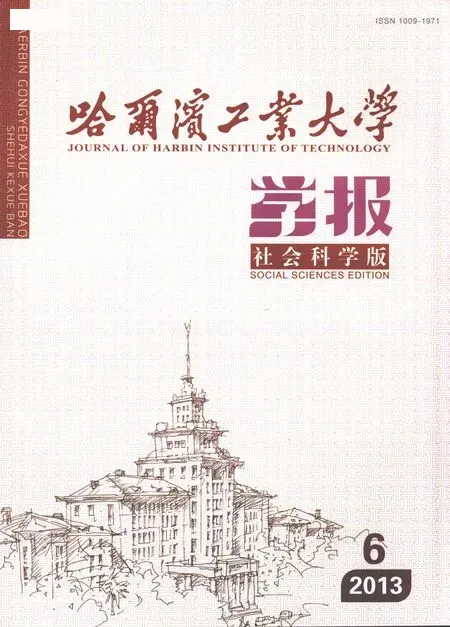作为逻辑的文字:从文字观到文学观
王妍
(哈尔滨工业大学媒体与设计艺术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01)
逻辑一词,乃清末严复对希腊语λóγοç(逻各斯)的英文logic的音译。何为逻辑?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这一概念时,意谓一种隐秘的智慧,一种世间万物变化的微妙尺度和准则,它内在地规定着事物的本质与命运。逻辑外显为语言。而对于语言来说,没有文字,语言将无所附丽,文字是语言的“外在的逻辑”。形(字)、音二位一体的文字,是语言呈现的方式。现象学家胡塞尔指出:为观念服务的介质——文字是“构成性的语言”,是“精神性的身体”,作为这样一种“身体”,文字便不单纯是一种“肉体”或事物,不是石头上的刻写或书页上的字符,它逃离所有的事实性和物质性,而被还原为自我表达的意向,一种“书写(或阅读)的意向”[1]。事实上,不是“中西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文字体系的不同”[2],而是中西文字的差异及其表意体系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图式,而思维又反过来规定了语言(道说)的方式,即一种先验的意向结构。本文力图通过思考文字的问题回答中西审美差异的基本问题,通过文字与存在、文字与思维的关系,考察中西审美范式差异的源始根基。
一、中西文字逻辑及其意向结构的差异
(一)以“字”建序与依“言”立法——字逻辑与语法逻辑
1.赋形、正名、名象——以“字”建序的汉字逻辑
在中国古人看来,书写—文字达到了经纬天下的建序作用,其妙有三:
其一,显迹赋形。天地、鸟兽、地宜、身与物都是文字的法象取类的依据,而这些事物也成为所造书契显迹赋形、分理相别的对象。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唐张彥远说:指示造形的文字是“古先圣王,受命应菉……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3]此言虽对“文字”的产生有神秘主义的圣化色彩,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文字是“指事造形,非其常也”(王弼《老子》第一章注)的创举,因为文字的确起到了洪蒙初醒、天人相分的创世作用。
其二,正名百物。天地宇宙被苞括于文字笔画,“世界”在“字”中显迹赋形,各具其名。“字”既具“文”形,又兼“音”声。字之“声”为“鸣”,“鸣”与“名”通。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释曰:“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名,是也以声赋义的命名。“字”以其形其声,将昏暗不明的存在开启到可见的“明”中。文、字即为万物之“名”,也使万物分“明”,文字使世界明晰起来,世界在“字”中赋义、命名、分明、生成。《礼记·祭法》云:“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正名百物,是先圣治理天下的前提,文字是整饬世界的利器。
其三,分职明象。《隋书·经籍志三》中说:“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僣滥者也。”[4]字不仅是“物事”之名,也是“人事”之名。“名”并不仅仅可以“命形”,还可以命“象”。《荀子·正论篇》言:“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可见,许多抽象的理念,甚至“王制”,都是依名所“象”的,“字”还是人伦世界秩序的建构者。后世学者把文字视为“经艺本,王政之治”。“经”是“常则”,由文字书写的“经”,是经纬人伦世界、实现清明王政之治的重要方式。
从“形”到“象”,从物事到人事,汉字逻辑建立起整饬有序的世界。在中国,甚至形成了“相信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名教”。①原载1928年7月《新月》1卷5号,北京大学档案馆收集整理。把字学看作“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章太炎)。那么,汉字经纬天地的建序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呢?
美国文艺理论家欧内斯特·F·费诺罗萨认为:汉文化“可以其独特的材料,利用古代种族所使用的同一程序,从视见之物过渡到了未见之物”。在费氏看来,这“独特的材料”是纯图画般的汉文字,“同一程序”则是汉字的独特形态形成的一种“隐喻”机制。费氏研究发现,汉字具有形象性、动态感、隐喻性和字与字之间关联烘托的性质,进而以之建立了隐喻的框架。他说,就汉语而言,隐喻是直接存在于这些客观事物的“速记图画”(按:指汉字)之中的,是从“视见之物”向“未见之物”的过渡[5]75-78。庞德认为,费氏触及到了东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运用的歧异点的根柢。但是,以费氏的西文化背景看来,汉字是“视见之物”,而“未见之物”——“他物”是借由汉字图画呈现出来的。在西方学者的眼中,隐喻和逻辑是分不开的:隐喻可以在一种逻辑基础上大量他造出来。所谓“隐喻”,是指此物特点被带到或转移到他物之上,以至他物被说得是此物的语言过程[5]77。这种转移与携带的是人为操作,隐喻的喻体和本体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内在的关联。我们以为,汉字并非“速记图画”,汉字思维也并非“隐喻”所能涵盖。汉字能够达成从“视见之物”过渡到“未见之物”的隐喻机制的是汉字的“字象”,“字象”才是汉语言独特的“材料”,叶维廉早就指出:汉字“以象构思,顾及事物的具体的显现,捕捉事物并发的空间多重关系的玩味,用复合意象提供全面环境的方式来呈示抽象意念”[6],“代表了另一种异于抽象字母的思维系统”;这种思维系统被石虎名之为“字思维”,字思维以每个独立完足的汉字字象为基础,不因其在句子的位置、语法关系、词语结合的方式、词性、成分、或倒置或穿插而影响它的“所指”,它直接呈现意义的视觉印象总使人不至于误解;“字思维”才是汉语言的“同一程序”,汉字构建了中国人的思维及阅读习惯,读者和创作者一样,“有着同样建构的大脑,有把握这种质料与成果的天然能力”[7]。“字”象是汉字的内在逻辑,它兆始于巫风时代,成熟于甲骨文对“神意”的刻画之“文”,甲骨文“字象”自明地彰显着微妙的神喻,在汉文化人文理性形成的过程中,汉字字象从神意之象转换为“圣人”表征“道”的“象”,“字”成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字象”所澄明之“道”确立了“字”的至高无上的本体地位,“字象”成为中国文化建构世界的“常则”——这就是字逻辑。
2.道说、标记、法则——西语言依“法”立言的语法逻辑
西方文化中,“音”是万物创生的第一推动,神“一言而万物资始”。西方人坚信,“语词(言)实际上成为一种首要的力,全部‘存在’与‘作为’皆源于此”[8]。因此,“字音”是认识世界的“逻辑”。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梭直到索绪尔,西方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语言观传统,那就是推崇口说的言语,贬低书面文字,“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9],是描写性的、堕落的、第二性的、中介的中介。而“声音在理想化过程中、在概念的生产和主体的自我呈现中”“具有奇怪的特权”[10]67。然而语音毕竟是时间线性的,如何把无形的思想与“道说”变成可以表达,能够把握的理性,将上帝从不着边际的“无限精神”变成可由概念、逻辑、理性所能把所握的logos——“神的理性”。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语词系统与思维系统是相一致的。要表达一个清晰合理的思维就不能离开一个清晰合理的词形与语法”[11]。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对言说遵循的法则和技巧进行研究,并开创了“语法学”。
声音的时间性线性决定了字母文字的线性排序,语法可以称为关于排列词语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将语言划分为字母、音节、连接成分、指示成分、名词、动词、曲折变化和语段等八部分”,文字按照正确的顺序符合逻辑的“定式安排”,才由此具有了意义[12]。文字意义的实现依靠环环相扣的词与词之间紧密的结构关系,由线性的句子以及上下文顺序的环顾来实现。阅读是在逐字逐句的过程中线性展开的一种理性过程,“像在代数中一样,具体事物是通过按照规则运行的符号或数码体现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具体事物根本没有形象可睹。”[13]105世界的存在也是一种理性可以认知把握的逻辑,世界的秩序就在这种理性的语言中所把握、描述和建构。
除了正确的顺序之外,语法还依赖一系列繁复的标记规则。标记本身虽不具有意义,但它具有指示某个对象的功能。性、数、格、时、体、态的标记性存在、识别、解码,成为语法逻辑的重要元素。西语言按照语言自身的逻辑规律又逐步推演出一系列的语法范畴,建立了西方系统的语法体系。逻辑化语言铸造了逻辑化思维,规定了西方文化逻辑化建构世界的思维方式。
西语言的“音”与汉语言的“字”,是中西文化建构世界所选择的不同的语言逻辑路向。而这也正是汉文化与西文化传统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对于本文来说,这正是中西审美范式差异的潜在内禀性。
(二)“字”以“比类”与“概念”“指代”——象逻辑与概念逻辑
1.“字”以“比类”的象逻辑
中国文化中,“字”乃为“生”,万物化生即为“字”,世界在“字”中万象纷呈,草长鸢飞。那么,汉字如何孳乳为一个涵容万象的文字系统?考察汉字衍生的六书之法可见,“比类”为原则的“象逻辑”使汉字成为一个蓬蓬勃勃的字象系统,至今彰显着其生动的活力。
以“比类”为原则孳乳汉字的方法有三:
其一,依类赋形。古人仰天俯地,依类赋形,用绘画的方法画出物体,笔画“随体诘诎”,同自然物体的态势相一致,采用与自然物事相类的原则造字。在此基础上,按照事物的属性和声音,依照义符与声符相类的原则组成新的文字,这些文字的出现使汉字的意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知此明彼。取这种比类取譬的方法,使汉字思维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迈出了一大步,成为汉语言抽象思维逻辑的发端,使汉字脱离了图画象形的婴儿期,走向成熟的文字体系。
其二,比类会意。面对幻化万千的世界,依类赋形的方式显然无法全面描述人世间和自然界的种种行为和现象,会意的汉字应运而生。许慎云:“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类”指事类,“谊”同义,“撝”同挥,指犹言导向。会意字由符合事理义类的字素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组合而成,观者可以根据这些字素的“比类导向”理解字义。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看,会意字的意义,不仅仅是各字素之和,而是超越了部分之和,达成一个意义的“完形”。“会意”字的意义,就是人心营构之“字象”。会意字并非完全是人的行为方式或客观现象的直接写照,字形所体现的也不是只是事物之间的外在关系,人们必须通过“字面”去“会”其所表现的抽象之“意”——某种“形而上”的意义。这也证明,汉字不是“象形字”,汉字是一个基于“字象”的表义系统。因为它的结体方式在影响着意义的构成。汉代的《说文解字》中收会意字1167个,组合的方式多种多样,交叉错综,说明会意的“字象”在汉代以前早已经成为汉语言思维的一种方式。汉字以会意的方式巧妙地营造出字象表征的世界,也酝酿出建立在具象之上的抽象的汉字思维——“象逻辑”。
其三,比连类推。许慎《说文解字》突出的创举,就是将汉字以“部首”的原则进行排列分检。依意味将汉字加以分类。他在总结汉字的构形规律时,把一部分汉字归为“转注”字,这类汉字的特点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建类”是区分事物类别的意思,“类”即事类;“一首”即是确立代表事物类别意义范畴的“字”(形),即立一字为根,以该字形作为其构成基础,创造出新字,为“类属字”。“凡某之属则从某”,类属字对根字的形、音、义有承袭从属的关系,人们只要识读根字,自然会识读理解新造的“类属字”,这便是“同意相受”。此外,汉字还可以通过以音的“类”达成字义的类推,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会通某字的字义,这就是“假借”字。古汉字的音训之法可以说是这种音转的应用。假音转义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汉字的表达。
汉字通过类比、会意、类推的方式表述天机、物理以及人事“存在”之象的方式,形成了汉字形象生动、气韵迭生的字象逻辑,其举一反三、简明易懂、超越性的“象逻辑”力量,为汉字的继承提供了内在的活力。即便你不识某字,也可以通过该字的字根推知和领会该字的字音和字义,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表象、概念、结构、符号、象征、图像,都做不到的。比类原则使汉字从象形的“像”升华为汉文化思维的“逻辑的象”。
2.概念指代的概念逻辑
神用言语命令造成的东西便造成了,进而创造了万有。这句话表达了一种源远流长的西方语言观:语言为事物命名。命名被当作对于某个或某些实际存在事物指称的名称。文字则是命名的书写形式,是不可靠的。柏拉图曾在《斐多》篇中说:“如果我用眼睛去看世间万物,用感官去捉摸事物的真相,恐怕我的灵魂也会瞎的。所以我想,我得依靠概念,从概念里追究事物的真相。”[14]“理式”虽然是无法看见或用感官感知的,但是可以为概念名称所表达,为人的“理性”所认识。某一概念不仅指称某一对象(本身)的属性,还可能指称某类事物的属性(共性)。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理性思维。概念是命名的内容,字词是命名的物质形式,概念依存于字词,字词是概念的形式。文字所指代的概念才是用理性思考而真相、把握真相的媒介。从“命名”,到“概念”,再到“指代”,西方语言观规定了语音与字词的性质。字词的“概念”“指代”逻辑成为西方语言观的主流思想。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尽管有分歧,但是无论是讨论文字符号与观念之间的任意性、标记某个观念对于思维的表达作用和遮蔽、扭曲作用,还是提出一种人工语言或理想语言如莱布尼兹,他们都一致认为,文字只要基本记号含义精确、结构简单、能够表达命题的逻辑形式,就可以准确表达概念、指代理念。就算出现理解上的分歧,人们也可以根据明确的语法规则来推演出正确的解答。这种概念思维是一种对象化思维方式,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规定性思维,人通过概念对世界加以规定,并通过概念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本质。文字本身并没有意义,人们只有将文字所指称的概念内容(即真值)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世界的认知。世界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把握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才是通往世界的逻辑路向。
(三)“字”属“阴阳”与“声”以“区分”——和逻辑与分析逻辑
1.“声分平仄、字别阴阳”——汉字阴阳相生的和逻辑
阴阳相摩、和合相生是中国古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它成为汉文化哲理的基调。对于汉字来说,不论是声音还是字形,都体现了这种观念。
首先,汉字声分平仄、阴阳相和。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在《四声切韵》中总结了汉字古音平、上、去、入四声的读法,沈约撰写了《四声谱》,说明中古时期,中国人对汉字的读音规律及汉字韵律之美已经有了清楚的认知与把握。他们对音韵的讨论最终形成了汉字字音的“平仄”理论,以声调是否有升降为标准,将汉字读音分为平、仄。汉字声分平仄,字别阴阳的特点,使汉语具备“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汉文化诗讲格律、文求骈俪,汉语(字)文学的审美特征皆因此而出。这种声律上的抑扬顿挫、平仄轮回、奇偶对称、气韵律动,更利于主体对自身情感的发抒与表达,追求一种阴阳和谐的节奏与韵律。程纪贤研究了汉字音韵一个汉字为一个音节的特点,发现在句中停顿的两侧,偶数音节与奇数音节两相对照,偶数音节与奇数音节在句内轮替充作重音,形成如海浪一样的律动,造成了一种音乐性……这一基于阴阳法则(偶数为阴,奇数为阳)而又互成对照的韵律,阴阳互换,符合宇宙间基本的律动[13]105。汉字读音序列与意义结构吻合宇宙秩序与人的心理“秩序”。
其次,造化赋形,体植必双。汉字在构形上讲求阴阳调合。这种特性缘自法象自然的造字理念。蔡邕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自然即有“阴阳”之“形势”,“肇于自然”的汉字是也必当如此: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转笔,宜左右回顾……。藏锋,点画出人之迹,欲左先右。(汉·蔡邕《九势》)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汉字构形阴阳相合的和合关系。称汉字“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唐人欧阳询《八诀》)。笔画在穿插、向背、相让、黏合、救应之间,发迹多端,触变成态,或分锋各让,或合势交侵,亦犹五常之于五行,虽相克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唐·张怀瓘《书断》)的构形态势。
左提右挚,上下感激、对交制衡的各种结构单元组合而成的汉字,呈现出生动的阴阳交合之“形势”,具有高度的构字智慧,使汉字的识读不是编码解码的翻译,也不仅仅是将部件进行组合的读图思维。心理学研究表明:汉字“部件知觉与其说是依赖于字形的结构方式因素,倒不如说是依赖于字形的空间部位,更确切地说,是依赖于部位与字形整体知觉的紧密程度”[15]。汉字这种构形特征影响了汉文化艺术讲求“体植必双,辞动有配”,达到“精味兼载”(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汉字部件之间正反、尊卑、轻重、抑扬、长短、开阖、明暗、浓淡、高低等不同质的对立都化做阴阳调和的生化过程——它们不是二分的,而是互动的感兴与会意。阴阳互动的观字方式和思维始终支配着中国人的审美思维和审美趋向。
2.“声”以区分——西字区别明析的分析逻辑
然而西文字却不同。西文字以“声”为义,字母的发音送气、不送气,阻塞、不阻塞、清与浊、元音与辅音都有区别性质、表明意义的重要作用,字母间的形态差异更接近于语音学上的“区别性特征”[16],文字成为对象化的物理形式,字母表将字母、音节等分类,用 in、dis、al、s、ed、ing 等字母声音以前缀或后缀的形式同该类事物的本性相对应,按照性、数、格、体、态、数做标记,形成区别与分析的思维逻辑。这种分析性思维“将对象按照规定分为确定的组成要素并作概念的分析,逐步认识每个要素和要素间的关系,最后达成对对象的整体性认识”[10]280。这种由要素到关系再到整体认知的思维逻辑,在西方诗学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概念的明晰伴随着分析的精确,一直是西方诗学的传统[17]。“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各种形式材料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美丰富者化为规定性与个体性。”[18]西方诗学擅长在分析的基础上建构庞大系统的体系化诗学。西方美学把与逻辑语言相关的“明晰”看成一切言语的美,并且认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与明确’”[19]。从分析的语言到分析的美学,在西方占据主流位置的美学体系始终是建立在逻辑语言观基础上的,直到20世纪后半叶以后的分析美学学派,仍然秉持分析的原则,可以说把分析性思维发展到了极致。
(四)“字”以“名”重与“词”“物”对应——悟逻辑与再现逻辑
汉森指出,“物质名词”构成古汉语最鲜明独特的风格。“物质名词的突出预示了一个与西方主导思想迥异的语义理论”[20]。这一点可谓别有洞见。古代汉字不仅是以物质名词居多,就是其他词性的汉字,也都可以变通为“名词”来使用。中国第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把实字分为五类: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其中静字相当于今天的形容词,状字相当于今天的副词。把虚字分为四类:介字、连字、助字、叹字;但是,他也指出,汉字到具体的句子当中,用途不同,词义也有别,所以又提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在古代汉语中,形容词、动词、数量词可以活用为名词,代词如“斯”、“是”也常常因其名词性回指的作用而代替前文出现过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21],既便是助词“等”,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因其名词词汇义逐渐磨损,由名词“等”虚化而来的,变成只表列举的助词[22]。可见,汉字用法以“名”为重。“名”本身并不仅是对物的指称,“名”还是象征系统,是对人间物事的“命名”或“况谓”,“名”对个人来说是存在的表征,对人伦来说是一种教化的工具或“象征”的系统。每一个“名”都是一个有着“召唤结构”的“格式塔”,即在汉字笔画的裂隙间,观者通过视觉组织汉字各个组成部分,调动全部感官具身体验各个组成部分、各个不同深度层面的映照关系,建构不同的空间和体量、出入虚与实、真与幻的意象世界,在汉字“象象并置”的构形中领悟意义。如张怀瓘所言:“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自非冥心玄照,闭目深视,则识不尽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23]这种由“观”而起的心物互动意向结构,形成了汉语言背景下的“悟逻辑”。
西文字的命运始终纠结于“词与物”的关系,从古代至近代语言哲学,直至20世纪初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画论”,都围绕词与物、名与实的对应关系展开。西方传统语言观认为,某词必对应某物,如果词与物之间不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一种自然联系,一种至少部分的同一性的话,那么,一个词语就不可能“意谓”一个物。不管是“自然论”还是“约定论”的对应论,都坚持语词与事物、言语与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相似性,并且认为事物、思想、声音、字词是存在着逻辑等级秩序的。音必指代实在的存在,词的描述必须与物具有逻辑一致性与形象一致性,音只能凭借其本身对应、象征获得意义,凭借其本身的事物的模仿与再现来得到显现能力。词物对应论规定了西语言的再现逻辑路向。
二、从文字观到文学观:基于文字意向结构的中西审美差异
文字决定语言、语言模仿文字,两者的反向力量即文字的结构原则或意指方式在语言结构中的投射。中西文字的差异潜在地规定了中西审美品质的差异,形成了中国意象美学与西方仿像美学的差异。
(一)意象美学与仿像美学
汉字以字象为义摄,推而广之,“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24]立象以尽意,这是汉字的道说方式,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道说方式,也是中国意象美学的道说方式。“立象以尽意”一语概括了意象美学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对中国传统美学思维有一种统领性的开启意义。中国文化经典,主要是诉诸字象思维而创造的,中国文论也不例外。对于“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机《文赋》)的遗憾、“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的无奈,中国文论选择用绝妙精微的文字作为美学范畴,将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文道”留给读者自己去探幽揽胜,品悟于心,形成了中国古代标举“意象”的具身性、情感性取向的中国意象诗学。
而西方语言观相信,“这些指称对象的共同本质属性的音节和字母,根据事物的本性仿造构词,用以摹仿事物的本质”[25]。“对语词的逻辑使用可以再现‘纯粹的事实’,因为语词的逻辑结构与纯粹的事实结构之间有一一对应的符合关系,这种对应性即‘正确性’和‘明晰性’。”[26]因此,一方面认为语言文字是模仿现实的仿像,一方面要求这种模仿达到无限逼真地再现“事实”。莱布尼茨甚至发明了理想化的“人工语言”,试图使文字可以通过编码解码的客观化逻辑推衍,达到摒弃人的情感因素,最“客观”地“再现”现实的效果。这种科学理性的思维逻辑“把文学艺术也纳入到知识和真理的系统,体现出一种以“真理”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的理性诗学精神”[13]97-98。西方自古代以来一直盛行到18世纪的艺术摹仿说,以及反对再现理论的表现主义,甚至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建立在“再现论”之上的。由于西文字观的二元对立,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艺术作为观念的语言,一定处于二难境遇:西方文论总是在现实与反映、真与伪、实在与艺术等的二难对立中做出选择。
(二)情感美学与理性美学
正因为意象思维让每一个个体成为探幽览胜,品悟于心的主体,所以意象美学是实践美学也是情感美学。以中国第一部文字书写的经典《诗》为例,编诗、教诗、赋诗,都是建立在意象思维基础上的情感实践和情感交流。这种交流能够实现的机制,就在于汉字“名词没有性、数、格的屈折变化,动词也没有数和时态的屈折变化……。这些特点,再加上细部结构所必备的连接成分的省略,创造了一种仅仅依赖词序和语境的孤立句法,一种使意象无所依傍的性质得以强化的句法”。①余宝琳《非连续诗学:抒情诗中东方和西方应和现象》,载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1979)这种非连续、并置,诉诸感觉、想象,陈述语气,绝对时空,非个人性的意象语言[13]111(高友工、梅祖麟分析中国近体诗语言时提出意象语言与命题语言的概念,但用其定性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也十分贴切),无论省略人称代词、省略介词、还是省略比喻词,无论语序如何“省略”与“颠倒”,主体都可以“毫无限制”地以参与者的体验逻辑去体悟,都有从字象转化为意象的能力,使潜在的实体可能充当主语。因为创造者和接受者一样,主体间心领神会,体验身在其中的一种理解和感受。意象语言削弱了认识论的概念意义,强化了情感逻辑。《孔子诗论》言:“诗无离志,乐无离情,言无离文”(——文(字、名)与情、志——是并列的本体,一语道破了“文(字)”的情感逻辑本质。诗可以“群”,可以“怨”,“诗言志”,“诗缘情”,这些中国传统诗论的纲领性观念,为中国传统美学涂抺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而中国的美学也正是通过情感逻辑完成了美学体系的建构。
西语言“逻各斯”(希腊语本义是“言说”)是以规则程序来表达的话语系统,渗透着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只有理性把握的东西才是最“真”的,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美”的。因此,无论是黑格尔的《美学》还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无论是悲剧、喜剧的本质还是崇高、优美的定义,都显露出历史主义、心理主义、科学主义等科学理性的基底。他们擅长于将某种品质规定为具体的量化指标,以此来衡量其是否符合美的标准。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了关于一篇“好文章”必须遵循的五条原则:第一,恰当地使用相关的词汇并给予正确的组合;第二,用专门的固定称呼指称某物,而不要泛泛地讲;第三,避免含混不清的用语;第四,遵守普罗泰戈拉将名词分为阳性、阴性、中性的划分法;第五,用正确的词尾表述单数和复数[27]。这也形成了基于理性的仿像美学重在明晰的审美特征,与基于情感的中国意象美学贵在含蓄的审美品质形成了巨大差异。
(三)生成美学与静观美学
正是因为汉字逻辑创造了一种可逆转的语言,其中主客、内外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映衬,汉字逻辑使词具有向一般性转化的的能力,使中国诗论有倾向“意象描述”的特点,形成了整个中国诗论“弥漫着‘梦一般的抽象’和‘无所不在的朦胧’”(温姆塞特语)[13]110-112。使中国诗论的意指范畴在确定性之外,还具有开放性,多样性的解读,主体的心流被带入不间断的发展变化状态中,“在事实与寓意之间,辩证的往返片刻不曾停歇[28]。中国美学范畴呈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绵延,例如,围绕“兴”、“气”、“象”等元范畴,派生出一系列重要的诗论范畴,以“象”为例,生发出物象、观象、取象、类象、兴象、拟象、言象、意象、境象、气象、形象、审象、味象、象外、忘象等等范畴体系。由于汉字的透明性组织①汉字构型于二维空间,由字根以模块组合的方式在一个正方块内而组成。这些模块之间,并非只按照一个固定视点去表现,模块间形体相交、重叠,体现出多维参照系的空间关系,因此,汉字具有“空间层化结构”的透明性。容忍甚至鼓励多层次、多元化的解读,也提倡个性化的解释,它激活思考,包容差异,形成了中国诗论意象纷呈,绵延不休的横向拓展的特点。
如果说中国诗论具有生成性,那么西文论则是具有静观性。西语言观认为,“说出来的言即是语言。”话一旦说出来,就成了一种现成的东西,可以像其它东西那样拆碎成的言、词、物。文字是对某事物的指示。“指示”一词是逻辑用语,一个符号“指示”或“代表”了一件事物,二者之间是静态的逻辑关系[29]58。文字作为“意义指示”,文本的书写非直接的声音或动作语言,书写使瞬间消逝的说话“事件”固定下来[29]205。这种置换中话语丧失了活生生的场景,而文字写就的本文则有了相对独立性[29]208。西方文论擅长把审美对象当代客体,对之进行审美静观,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完备的美学体系。因此,西方美学的历史表现为一个纵向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打破传统美学范式、建立新的美学范式的过程,“理念”、“上帝”、“理性”、“真”等相继成为本体,西方美学先后围绕着艺术如何模仿这些本体进行了深入的探析。而尼采“上帝(终极价值)死了”、福柯“人(理性)死了”、波德里亚“真(真实)死了”的论断,也正是这种静观美学的范式革命。只有在西方语言观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论断,才能真正意义上理解他们对西方传统文化颠覆性的、震聋发瞆的瓦解力度,才能理解西方古典美学、现代美学、后现代美学的革命式进程。从另一个角度说,文本的固化、话语的语境被破除了,文字的离身性与主体的不在场性,“作者欲望是一回事,文本意谓的是另一回事,它比作者写作时意谓的意义要复杂得多”[29]205。文字的出现使人与人面对面的对话关系(话语)转变为更复杂的读写关系,从而开启了西方解释学美学的路向。
(四)体验美学与诠释美学
汉字一方面显迹赋形,一方面联接着人的身体与行为,成为人与自然沟通的媒介。一切物事人情都可以作为中国意象美学的范畴,甚至动词、形容词都可以作为具有普适性特征的意象论诗。中国诗论中,玉、石、水、气、香草美人都是诗学意象,作为表达诗论的话语,名词如“风骨”,如“气韵”;动词如“兴”,如“悟”;形容词如“高古”、如“雄浑”、如“中和”,都是意象美学的重要范畴。这些之所以可以用来论诗,是因为意象思维使中国人习惯于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利用这些字象来获取抽象的意蕴,运用感官体验的方式理解抽象的观念。“字象”造就了中国“比兴”美学的基础,而“比兴”美学则形成了中国诗学的基调,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形成成熟的美学特征和审美方式。章学诚云:“战国之文,深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30],可谓深得其旨。
取象比类的前提是“观物”,“观”在中国意象美学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观”,不仅仅是眼“观”,而且是五感并用,直至是心“观”、气观——“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懂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庄子·人世间》)此“心”乃意绪疑虑,此“气”乃生命本真。在诗学的领域里,从感知字形,到感悟字象,主体经历了感官感知物象的“原象”,通过联想和想象,生发为无形无质的“类象”,进而抽象模拟或建构“拟象”系统,体悟宇宙之“大象”的过程。在物与象之间,在物理事实与人为阐释之间,每个人可以通过全身心的多感知体验,超越“外部的旁观者”式静观,亲身参与到心与物的互动,凭借意象成为创造性过程的一部分。个人解读占据主位,意义就会存在于主体具身体验的过程中,隐含的、内在的和暗示的意义通过参与者对对象的反复的认同而构建。在直观、直感、直觉的体验之中获得“韵外之致”和“言外之意”。
对于西文字来说,“终极本体”(如理念、物自体)是没有语言能完全企及它、把它表达出来的。词语是逻辑的使用,而不是感知的使用,它是诠释的而非具身体验的。西方文论的总体基调是“命题语言”,“命题语言”的特点是“连续、句法统一,诉诸智力、理解,其他语气,相对时空,诗人作为主体的语言”[13]111。语言依附于人的理性与意识,它受到逻各斯或神言的控制,担负了传达永在不变之真理的崇高使命。因此,语言总是以确定、明晰、直接、有序、的“逻辑”和“语法”解释本质的“诠释学美学”。西方文论以一系列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建构而成,颇像可以随意拆解的机器,而这与中国诗学范畴讲求浑融整一的大美灵韵大异其趣。
三、结语:具身体验的中国意象美学与再现诠释的西方仿像美学
文字不单纯是石头上的刻写或书页上的字符,而且是一种先验的意向结构。文字系统对整个语言系统所发生的影响,在于语言的结构原则或意指方式。如果说“字音”形成了西方人认识世界的“理则”,那么“字象”则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常则”。作为逻辑的文字,其意向结构的差异奠定了中西审美差异的基调,这种基调“具有赋灵作用”[29]142。如果说汉字具有图形特征,西字具有符号特征,中国是汉字思维,西方是语音思维,那么,当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具身的天性更适合处理图形相关的认知过程,语言的天性更适合处理语言相关的认知过程[31]。汉字是有形的,实证的,它不是意识形态,不必想,不必听,只需“具身”地去“观”。汉字作为汉语的质料,它自己在说话。而西字却只能依靠一系列的语法规则来推其理义。也许正是因此,海德格尔才大声呼吁:西语言要“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29]151。让语言自己说话,德里达才表达出“放弃一切深度,外表就是一切”[29]228的变革态度。
汉字以“字”建序、“字”以比类、“字”属“阴阳”、“字”以“名”重,衍生出字逻辑、象逻辑、和逻辑和悟逻辑,形成了汉语言情感理性的具身性意向结构;西字依“言”立法、“指代”命名、“声”必“区分”、“词”“物”对应,衍生出语法逻辑、概念逻辑、分析逻辑和再现逻辑,形成了西语言科学理性的对象化诠释意向结构;作为逻辑的文字决定了中西语言符号体系、赋义方式、思维路径、体验模式的差异,从文字观到文学观,从逻各斯到诗论,彰显着中西美学理论范畴及理论体系差异的文字规定性。从文字意向结构的角度来看,西方是理性逻辑,中国是情感逻辑;西方诗学臻于真,中国诗学深于情;西方诗学辨于物,中国诗学观于心。也许,正是中西文字意向结构的差异,建构出中西不同“意向性形态”的审美世界及其意义。
[1]DERRIDA J.E.Husserl'origin of geometry:an introduction[M].trans.by John Leavey,Jr.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97.
[2]李秀琴.从中西文字体系看汉字文化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J].中国哲学史,1998,(4).
[3][唐]张彥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南京:凤凰出版社传媒集团,江办美术出版社,2000:1.
[4]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04.
[5]傅璇琮,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6]叶维廉.东西比较文学模子的应用[M].台北:饮之太和,1980:267 -268.
[7]葛兆光.汉字的魔方[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61.
[8]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甘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70.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M].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5.
[10]赵奎英.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1][美]德曼.解构之图[M].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4-55.
[12][加拿大]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305.
[13]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14]柏拉图.斐多[M].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72.
[15]喻柏林,曹河圻,等.汉字形码和音码的整体性对部件识别的影响[J].心理学报,1999,(3).
[16]JAKOBOSON.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M].The M.I.T.Press,1952:1 -3.
[17]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9-40.
[1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61.
[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65 -266.
[20]汉森.古代中国的语言与逻辑[G]//[美]郝大伟,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23.
[21]朱淑华.上古指示代词“斯”、“是”名词性回指比较[J].社科纵横,2011,(4).
[22]张瑜.古汉语“等”的词性演变[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5).
[23]张怀瓘.载文字论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45-146.
[24]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8:213.
[25]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546.
[26]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89.
[27]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1.
[28][美]柯林·罗,斯拉茨基.透明性[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74.
[29]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96.
[30]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5.
[31]LOUWERSE M M,JEUNIAUX P.The Linguistic and Embodied Nature of Conceptual Processing[J].Cognition,2010,114(1):96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