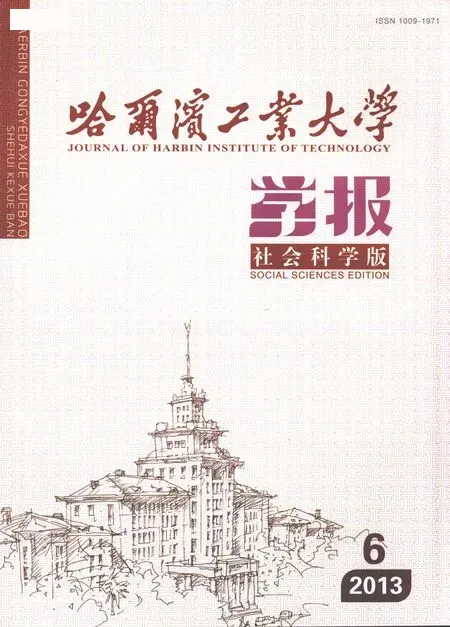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外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问题
王福友
(哈尔滨商业大学 法学院,哈尔滨150028)
一、案例
甲公司于1999年从A省B市人民政府手中得到坐落于C区某地的三块国有土地。2003年7月3日B市人民政府发布《整治通告》,启动××路整治建设工程,对该三宗土地使用权予以提前收回。甲公司与D新区××路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于2003年9月8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对坐落于三宗土地上的建筑物按照每平方米1300元予以补偿,涉及有房产证书的房屋建筑面积12145.82平方米,已竣工尚未使用的房屋28000平方米;围墙共计1454米,按照每延长米120元予以补偿;各种树木按每株20元予以补偿,共计6520株。上述三项合计补偿款52,494,446.00元。该协议书同时规定,对甲公司土地使用权范围内的其他附属物及设施,不再予以补偿。
三宗土地的权属状况是:(1)1号地面积11375.3平方米,1999年11月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地上有违章在建工程面积16474.06平方米。(2)2号地面积69880平方米,甲公司于2003年4月4日在未交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违规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3)3号地无国有土地使用证,无地上物。2003年9月12日,甲公司向指挥部做出书面承诺:“关于63700平方米土地的土地证,我公司承诺于2003年10月1日之前办完”。9月15日,甲公司向B市国土资源局补交了3号地的土地出让金。
补偿协议达成后,截至2003年12月10日,指挥部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房屋拆迁补偿款。甲公司亦依约交回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等。指挥部顺利实现了对××路的整治,其中2号地于2006年4月由市国土局挂牌出让给乙房地产开发公司,用以房地产开发,且于2009年完成开发。
2007年8月24日起,C区政府才向市政府有关部门启动收回涉及甲公司的上述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程序;2008年12月17日,B市国土局做出收回甲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甲公司不服该决定,于2009年3月11日向A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6月8日申请人对行政复议申请予以撤回,省政府做出“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2009年7月6日,申请人以被申请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本身未予补偿为由向省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9月4日,省政府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B市人民政府对三宗土地地上建筑物占用土地以外的土地给予补偿。
二、拆迁补偿协议被行政复议的效力
在不动产征收过程中,政府部门身兼行政权力拥有者与国有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其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抑或民事行为,应予明辨。行政复议仅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之情形,①《行政复议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如房屋征收决定、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1年)第14条规定: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不予补偿决定等;若政府部门以民事主体身份从事民事行为,则依法不能被行政复议。具体到补偿领域,征收补偿协议与补偿决定因性质不同而异其适用。征收补偿协议系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共同协商而达成,政府以土地所有人身份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无行政复议适用之空间。征收决定由政府以行政权力拥有者的身份单方作出,系具体行政行为,应适用行政复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6条第1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做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做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第3款规定:“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第16条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第1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对于拆迁管理部门作出的补偿安置裁决没有明确规定可以适用行政复议。在具体法律关系中,若双方平等协商达成“权利—义务”关系,应认定为民事关系;反之,若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由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相对方只能予以接受,形成“权力—义务”关系,则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行政复议制度旨在通过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对侵害相对人合法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矫正,故其针对的是“权力—义务”的行政法律关系。本案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由甲公司与指挥部在协商基础上达成,并非指挥部单方强制做出,性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无行政复议适用之余地,故省政府无权对争议的拆迁补偿协议内容予以行政复议。该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具有民事效力,值得探究。甲公司与指挥部达成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乃双方平等协商的民事合同,但经省政府受理且做出对甲公司有利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应理解为是对原补偿协议的变更?省政府乃指挥部的上级部门,虽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具有支配下属的权力,但在民事领域二者为两个不同的主体,不能以二者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而使其主体身份混同,故省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不对指挥部产生民事效力。《行政复议法》并未规定违法行政复议的效力及救济问题,故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矫正机制对其加以解决。明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属于民事合同的属性,就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基于此,B市政府有权拒绝履行省政府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之法律解释
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届满被提前收回时,其本身是否作为被补偿的项目,我国立法在不同时段上有不同规定,经历了由“相应补偿”向“不予补偿”立法模式的转变。“相应补偿”立法模式以《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第42条、④该条例第42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提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国家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已使用的年限和开发、利用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第19条、①该法第19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土地法》(1998年)第58条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58条的规定,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等为代表,均规定应根据土地使用者已使用的年限和开发、利用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不予补偿”的立法模式以《物权法》(2007年)为标志,其第148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其立法理由是“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取得的是对土地使用的权利,国家收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建设用地,不适用有关征收的规定。但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由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是按照建设用地的使用期限缴纳出让金的,因此,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人还应当向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退还相应的出让金”[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亦采此立法模式,其第13条第3款规定:“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两种立法模式实际上是以2004年宪法修正为分界点,《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确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提前收回时,涉及公民的私有财产应依法征收并给予补偿的原则,从而改变了粗暴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过程中对私有财产的侵犯。两种立法模式虽然都涉及“补偿”,但在不同的语境下“补偿”的内涵却有所不同,突出体现在处理房屋与土地的关系上。“相应补偿”立法模式的实质是以“土地涵盖了房屋”,土地上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未被纳入征收的范围依法得到补偿,故该语境下,字面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相应补偿”不仅指土地使用权本身,而且主要包含地上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补偿问题。立法中界定的“相应”主要是考虑: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土地使用的实际年限涉及土地出让金问题,土地使用权人一次性按照约定使用年限支付土地出让金,但却被土地所有者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故不退还相应的土地出让金实属不当;土地使用者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则主要针对土地上的投入开发、利用成本,体现为地上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价值,并主要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之规定。该如何处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若将二者平行适用,就会导致“房屋要补,土地使用权也要补偿”的结论,而违反法律解释的基本原理。事实上,二者乃不同位阶的法律,立法法确立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原则,《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必须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确立的原则下加以适用,故将“相应补偿”理解为是对国有土地使用权自身的“相应补偿”违反了立法意旨。“不予补偿”模式是在明确地上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依法征收补偿的前提下,对提前收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仅退还相应的补偿金,《物权法》第42条③《 物权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第3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与第148条成为该模式的规范基础。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的规定值得深入检讨。该法第6条规定了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应获得征收补偿,④《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第6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第20条却规定仍然要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给予“相应的补偿”,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第20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适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其实质是在“相应补偿”模式与“不予补偿模式”间采取了“折中的模式”。第20条与《物权法》第148条规定相抵触,且背离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提前收回的法律性质,依据新法优于旧法之法律适用原则,该第20条应不予适用。“相应补偿”模式表面上是针对土地使用权,但主要是考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补偿,涉及土地使用权自身的仅应考虑土地出让金与实际使用年限的匹配问题,其与“不予补偿”立法模式实质上并无二致。“不予补偿”的立法模式深刻反映了征收补偿的内在意义,征收本质上相当于买卖行为,乃私人或集体所有权被国家强制买受,征收补偿系因为所有物出卖而产生的对价。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提前收回,不存在所有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变动,若对其予以征收补偿,则意味着将原本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又卖给国家,并从中获得巨额补偿。
本案争议双方达成房屋补偿协议的时间是2003年9月8日,而甲公司于2009年7月6日主张应对其国有土地使用权作出补偿,该时间段跨越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的两种立法模式,故应该如何适用法律至关重要。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6条规定的精神,应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①《 民通意见》第196条规定:1987年1月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1987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民法通则处理。本案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是否予以补偿的问题,应适用2003年9月的法律规定,即采用“适当补偿”模式,具体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并结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之规定。省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应属法律适用错误。依此立法模式,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享有相应补偿权,但必须深刻把握“相应补偿”的法律意旨,其实质是对地上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补偿,既不能理解为是对土地使用权的单独补偿,也不能理解为是对土地及其地上房屋等的分别补偿。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之法律适用
(一)“相应补偿”模式的适用要件
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第19条之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得相应补偿的前提应是“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若土地使用者尚未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人应依法主张对违法使用土地行为的排除,补偿问题无从谈起。本案共涉及三宗土地,其中1号地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号地于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达成前在未交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违规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3号地始终无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取得存在两个法定要素:一是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是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者究竟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发生怎样的效力值得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1998年)第55条第1款规定:“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第11条第3款规定:“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第13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可见,当事人是否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标志应是登记并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对当事人未支付土地出让金的法律效力做了规定。其第15条规定:“土地使用者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当事人是否缴纳土地出让金仅发生债法效力,并不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标志,即便在当事人未交付土地出让金,但经过登记并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则意味着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物权法》的规定体现了这一原则,②《物权法》第139条规定: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机构应当向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发放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物权法》第141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支付出让金等费用。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16条)。本案甲公司于2003年4月4日在未交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办理了2号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应认为其依法获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对于3号地,2003年9月8日指挥部与甲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9月12日,甲公司向指挥部做出书面承诺“关于63 700平方木土地的土地证,我公司承诺于2003年10月1日之前办完”;9月15日,甲公司向B市国土资源局补交了3号地(63 700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但一直未能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故不应认为其依法取得了3号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二)甲公司无权主张国有土地使用权之补偿
甲公司依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第19条,依法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相应”补偿请求权。但其通过与指挥部达成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已经行使了该权利,且因为政府征收行为的结束该权利也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法律基础。“相应补偿”模式下,土地使用权补偿主要考虑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两个方面。(1)关于实际使用年限问题。甲公司对1号地和2号地享有补偿权,1号地于1999年获得土地使用权,使用年限为40年,而实际使用仅为4年,应对剩余36年的土地出让金予以退回;2号地虽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未缴纳土地出让金,故无土地出让金退回问题。甲公司虽补交了3号地的土地出让金,但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故应依法主张对缴纳的土地出让金予以返回,而与本案所议补偿问题无关。对政府而言,乃不当得利应予返还。(2)关于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甲公司在1、2号土地上共有照房屋评估价格22 356 776.00元,无建审手续在建工程评估价格23 582 091.42元。按拆迁补偿政策,无照房屋按照房屋重置价格的70%给予补偿,甲公司无照房屋应获补偿款16 507 463.70元。全部房屋应获补偿合计38 864 239.70元,而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数额为52 494 446.00元,比有照与无照房屋补偿总额多了13 630 206.30元。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2条之规定,其中的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均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仅应给予适当补偿。“房屋补偿协议书”中对全部建筑均予以了超标准的补偿,显然对甲公司有利。考虑到1号地应退还36年土地出让金的因素,双方达成的补偿协议不但是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而且亦符合公平之要求。
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物权请求权还是债权请求权,不无疑问。该请求权若基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而产生应属物权请求权;若基于土地出让金合同而产生,则其应属债权请求权。《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第19条规定观察,国家在国有土地使用年限届满前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单方决定提前收回,其构成了土地出让合同的法定解除。《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法律规定情形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是否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予以“相应的补偿”,不是所有权人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定条件,而只是土地出让合同解除的法定结果,故土地使用权“相应补偿”请求权应属于债权请求权,并与《物权法》第148条规定的退还相应的出让金请求权作同一解释。这一点与房屋等的征收补偿请求权具有性质上的差异,根据《物权法》第42条之规定,在征收补偿的情况下,是否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予以补偿构成征收的前提条件。权利人获得补偿时并未丧失所有权,若不给予补偿而强行征收,构成对所有权之侵害,应依《物权法》规定行使物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各国立法差异较大,例如德国民法承认物权请求权因时效消灭;日本民法规定继承恢复请求权罹于消灭时效。学界以不适用消灭时效为主流观点[2]。《物权法》对该问题未予明确规定,学者认为,物上请求权很难适用诉讼时效[3]183。在本案件中,甲公司享有的土地使用权补偿请求权乃债权请求权,应依法适用诉讼时效。甲公司自2003年开始,即知道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的事实,且得到许多事实的证明。本案涉及的三宗地已被政府收回,且已经修路或者另行出让给他人进行开发,甲公司对这一事实并无疑问,其于2006年6月27日致函C区政府,表示“甲公司在江北的土地是案件再审期间被政府依法征用的,并给予补偿。自被征用,土地的使用权就发生了转移,不存在该土地再被政府或是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收购”。其于2008年12月17日主动撤回对B市国土局作出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的行政复议申请亦为明证。而甲公司仅于2009年7月6日才通过行政复议途径主张权利,故已过诉讼时效。甲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补偿请求权无论从实体上还是时效上均已消灭。
系争案件中,甲公司基于其与指挥部达成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已经实质性地行使了土地使用权“相应的补偿”请求权,其权利行使的方式是,以在房屋及树木补偿上获得多的利益,而放弃了对土地使用权相应补偿的享有。故甲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相应的补偿”请求权已经实体性消灭。从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中未直接明确土地使用权补偿项目这一事实观察,即便双方对该请求权的实体消灭存有争议,但作为债权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当无异议。
五、建筑物占用的土地范围之厘定
行政复议书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申请人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两宗土地范围内建筑物占用土地以外的旅游用地依法予以补偿。”其涉及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地随房走”原则下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范围究竟如何判断。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即最狭义的理解,单纯从字面意义上考察,“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是指房屋墙体与地面衔接所组成的土地面积。第二种理解,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是指整个地基的面积,其显然比字面意义要宽泛。但这些理解均存在法律上的错误。法律层面上,这样的文义解释违反了土地作为物权客体的独立性。土地乃民法上特殊之物,连绵不断,该如何确定其法律上的独立性是问题之关键。《土地管理法》(1998年)第11条第3款规定:“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土地之独立性以登记确认为标准,我国台湾地区即按宗登记以确定其独立性,“绵延无垠之土地在形式上或物理上本非独立之物,但依社会经济观念,仍可依人为方式予以划分,而在土地登记簿按宗登记,赋予地号,则各该地号之土地自得分别成立物权。此际,一地号所表示之土地即为一独立物,在法律上得为一所有权客体。”[4]我国法律虽未明确对土地在法律上的独立性作出规定,但学者亦采取上述认识,“一幅土地的某一部分,在物理上与其他部分难以分开,但在交易时,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部分作为交易对象,且在交易前可以通过登记而确定其‘四至’范围和坐落的地点,这样分割为各部分的土地也可以成为独立物。”[3]36本案若坚持对“占用范围内”的文义解释,就导致了房屋及其直接对应地基四至的部分土地因给予被征收人补偿而由B市政府收回了土地使用权,其他部分的土地仍由甲公司继续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局面,而B市人民政府在该土地上进行的路桥建设行为已构成对被征收人用益物权的侵犯。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有关规定所涉及的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应理解为是以保持土地独立性为前提,以登记机关确定的一宗土地为其范围。这也与使用权人获得土地的整体用地保持一致。《土地管理法》(1998年)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使用人获得土地的目的不在于使土地闲置,而必须用于建设。《物权法》明确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就土地与地上建筑物的关系而言,运用国有土地是根本。“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于利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因而土地使用权的设立与存在,并不以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附着物的存在为必要。”[5]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亦采此立法例,“地上权系为使用他人土地之权,而非于他人土地上有附着物所有权之权。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的所有权属于地上权人。地上权既为使用他人土地之权,故地上物(工作物或竹木)之有无,与地上权存续无关。”[6]建设用地使用权存在的这一目的,决定了国家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意义,其根本在于消灭国家所有土地上存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公共利益需要,对地上建筑物予以征收仅仅是实现或者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系争案件中被征收人的主张以及省政府行政复议的结论,都是对这一目标的背离,而导致B市人民政府征收的结果仅仅是花巨资买回些房子,而该房屋占用范围之外的土地使用权仍归甲公司。本案A省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书所提的“占用范围内”土地问题是否适用“地随房走”原则仍需检讨。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物权法》等规定所涉及的“地随房走”原则适用的领域较为特定,主要包括转让、抵押、互换、出资、赠与等情形。①《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8年)第31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担保法》第36条第1款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第3款规定: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物权法》第147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系争案件乃土地所有权人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而消灭用益物权的行为,并不属于上述情形。就立法目的探究,之所以在转让或者抵押等情形下适用“地随房走”之原则,“从性质上来讲,建筑物不能离开土地的使用权而独立存在。因此,在对建筑物进行交易时,要同时考虑土地的使用权,同时,在对建有建筑物的土地进行交易时,应该认为,这是受到建筑物使用权限制的土地的交易。”[7]故“地随房走”原则的适用旨在实现房产交易的可能并维护交易秩序,房地权属一致性在房屋原所有人处得到了维护,在房屋交易过程中为确保这种一致性,必须适用法定的“地随房走”原则,通过限制主体的意思自治而确保不动产交易秩序与安全。建设用地使用权提前收回的情形下,因地上建筑物等的所有权归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所有,而土地原本就归国家所有,房屋所有权人仅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我国房地权属一致原则体现为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一致,而不是房屋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的一致。在建设用地使用权提前收回的场合下,土地使用权是否收回的权力掌握在国家手中,并通过单方意思表示来实现,无需通过完成对房屋的征收而基于法律规定加以实现;同时,是因为要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才对其地上建筑物予以征收补偿,而不是为了征收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而附带性地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故在消灭用益物权的意义上,适用“地随房走”原则是对该原则的滥用,也是对用益物权消灭制度的误解,在这一领域无该原则适用之可能。
结 论
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乃民事合同,征收人之上级主管部门对此必须明察,不能因被征收人的恣意主张而对其性质产生错判。对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进行行政复议造成对民事权利的不当干涉,且易引起城市化进程中征收的非法治化困境。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提前收回与征收集体土地所有权、私人房屋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即便是针对《物权法》发生效力之前的案件,亦应按照法律的体系性解释等原则,与《物权法》作同一解释。否则,会导致土地使用权人以较低成本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在土地升值的背景下,再按照补偿原则高价卖给国家的局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系当事人对征收补偿作出的一揽子处分,若在此之外再行谋取其他所谓补偿,尤其是主张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本身的补偿于法无据,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1]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31.
[2][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Ⅱ:物权法[M].王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
[3]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4]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5.
[5]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63.
[6]王泽鉴.民法物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2-283.
[7][日]我妻荣.新订担保物权法[M].申政武,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