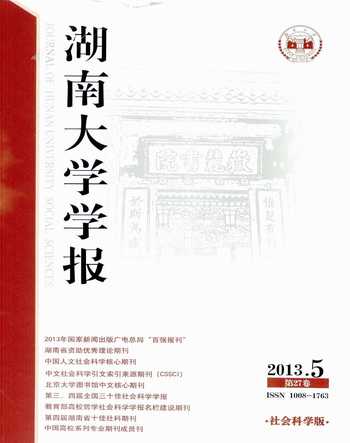论孔子音乐思想的伦理启示*
张碧霞
(1.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2.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乐通伦理”作为我国古籍中首现“伦理”二字的书面记载是当今学者论证音乐与伦理相生关系的凿证。当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直截了当的指出孔子的挺立中国传统道德主体、开辟价值之源的“仁”观既是其伦理道德的核心亦是音乐之为音乐的“超越性原则”。[1]据此,音乐与道德的辩证发展成为学界热论的议题之一,以音乐与道德命名的文章不胜枚举,并催生了诸如《音乐伦理学》此类的探索性著作。当笔者对繁芜丛杂的论说进行学理上的考证与梳理时,不禁为高尚的道德情操滋养了美妙的音乐、“美善统一”[2]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成为理论基调而雀跃,但亦为如此多的论证多为资料堆砌或事实叙述而扼腕,对音乐与伦理的理论解释工作相当匮乏,与音乐伦理相关的确定的理论基础与解析方法还没有形成。近年来,随着逻辑解析的发展,“哲学解析”的风气在学界十分盛行,解析法适用与研究一部著作和个人理论,据此,笔者拟选定孔子的“善”、“仁”、“和”三个观念,先研究三个观念所包含的确切音乐思想,再就其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分别整理出上述三个观念关于伦理价值的论证,通过对论证本身的结构以及论证彼此间的逻辑关系的分析,为“以乐储善”、“仁乐合一”和“乐以教和”的结论更加精确而客观做方法论上的尝试。
第一 “以乐储善”:孔子“礼乐”观的应然之解
“以乐储善”之如此述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追慕李泽厚先生的汇集《伦理学纲要》中“以美储善”理论范畴。李先生通过解构“人性能力”包括“理性内构”、“理性凝聚”、“理性融化”三方面,对“以美储善”做了如下既体系化又注重真切感受的论述:
审美能力由于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不同,不是前者排斥、控制后者而是参与、交融,使之不同于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而更为复杂多样,在审美这里,“能力”与“情感”经常混而为一。而自我克制自我牺牲等意志能力习而久之,进入某种特定情感状态即美学—宗教的“圣贤”境地,就是美德,也就是“以美储善”。[3]
从历史本体论的理论立场出发,以现实人的生存特征为依托基础,自然就把“美学”放到了第一哲学的高度,与“乐与政通”一起作为对中国传统泛情感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仁”在以亲子家庭关系为主轴的传统宗法社会以“重生”、“重情”等情感同时赋予给整个宇宙自然天地万物)的理论承续。在这里,人性情感与人性能力在道德层面汇通、融合和同一化,即自由意志与自然情欲理性化发展的渗透与干预,凝聚为“以美储善”,以审美之能力蕴储自我牺牲、意志等伦理之善。至于“以乐储善”,借助人性情感与人性能力的辩证关系来钩稽并重建理论基础,固然可以避免“过分体系化”的某些缺陷,单也能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将次序井然、因果明确、排列整齐、体系严密的理论逻辑,拆解成过分注重自身感受的纯客观描述。警与此,笔者拟从有趣的事项背后,挖掘潜藏着的理论意识:包括从原典“礼乐论”儒学探寻以乐储善何以可能、地域音乐文化“以乐储善”的现代转型等。
“礼乐论”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集中表述,是统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论和认识论。先秦时期,以亲子为核心的血缘宗法社会是小生产的农耕经济时代的产物,源于上古氏族群体的巫术风俗因中国人操之在我、重视生命问题、先明明德的思维习惯,经周公制度化而化为“礼”,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准则、生活规范,也即是彭林先生所说“因俗制礼”[4].这种源于上古巫术祭神之俗的“礼”外化为伴随各种仪式的“礼仪三百,威仪三百”的经验知识,烦琐细碎到连孔子都要“入太庙每事问”,诚然如朱夫子所说孔圣人这样问可能是为了表示谦虚,但如若不是有如此等级森严而又杂多的名物度数,孔夫子亦不会就此特去不耻下问吧?为了让“礼”更加的含情脉脉,周公就用更加艺术化、规范化的“乐”去规定礼“敬文”、“节文”的基本特征。因此,“礼乐”在当时常常是不可分的,孔子则把礼乐并重,以规范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作为“礼”和“乐”的共同特征,并把“乐”置放于“礼”之上,所以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之说,“乐”在孔子这里有了最高的艺术价值。
“音乐”在古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乐记》从功能性和影响力方面,把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德音之谓乐[5]
“以乐储善”浸润在字里行间,有德才有乐,德是乐的先验,是普遍性原则。而以“善”为最高目的的德无可避免的成为乐的至上规定,以上见诸于孔子对韶乐“尽善”的评价。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礼乐论”在郁郁乎文哉的礼治主义统摄下,诉诸于“以乐储善”是其应然之则。从审美之维,李泽厚先生得出“以美储善”,从“礼乐论”实际操作层面则能推导出“以乐储善”,此“乐”是经验层面的存在,是繁琐晦涩仪礼的艺术化表现、亦或是教化手段,存在于伦理学实践领域。在此,“善”作为终极目标,是合目的性的存在,与康德伦理学相同,“善”是作为摒除道德只能作为先验原理而同一、自我一致、普遍、空无内容的尴尬而赋予的具体的道德律令。作为道德律令的“善”是超感性的、纯粹形式内容,只要放置于实践层面,涉及到现实行为,就有了“善”的具体之分,是其实践对象的理性凝结,对于“作乐”来讲,“善”赋予了“乐”最高层面的内容,“乐”作为为了满足了人的某种需要的工具,为人作为感性现实的存在和发展而服务。“以乐储善”作为“礼乐论”的应然之解,是“礼乐论”的基础,是目的和内容的统一,自律和他律的消融,二者相互联系、制约、渗透而又相对独立地和自主地发展变化。
第二 “仁乐合一”:孔子乐论的超然之境
其实,“善”的实然亦或应然,在于其所相对应的是认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而绝不关系于文化背景的古今与中外。在把“善”最为最高道德律令的认识层面上,先秦儒学大师与康德莫逆于心,认为“善”是实践理性对感性经验的先验凝结。但与康德所不同的是,孔子对“善”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尽”,即“善”作为最高道德律令,是经验到先验的跨越,但具体到“乐”的层面上,还有一个“超然”的存在,这个“超然”在康德那里是上帝、是灵魂、是善良意志,而孔子把其视为“仁”,孔子的所谓“尽善”,实指“仁”的精神而言。据此,徐复观提出了“仁美合一”是孔子的要求:
我的想法,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通过各种乐器、通过各种形式,而表达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只存乎一个作曲家演奏者的德性,亦即他的艺术精神所能上透到的层次……提升到孔子所要求的音乐境界,既是仁美合一的境界[6]
如上所述,“为人生而艺术”是孔子“人之为人 ”的一生实践所循,为“人生而艺术”的音乐即肯定作为音乐本体的自律美,又规定了音乐他律的内容“善”,要求美与善统一。黑格尔批判康德缺乏具体内容的道德律令时嘲讽的指出,“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地方,也就不会有矛盾”。[7]同样,“善”与“美”这两个普遍性概念很易理解,但却很难具体运用,即很难下个判断,即“善”“美”统一有什么样的具体规定?本人妄加揣测推断,美与善的统一是以时间、历史为维度的实践过程的反映,二者应有一个价值层面的共同诉求,“仁”与“乐”的相得益彰是“美”与“善”自然统一的最高境界,是儒家乐论的超然之境。儒家乐论本着为人生而艺术,以“乐”为人生修养之资,为人格完成的境界;不仅就音乐而言音乐,也就音乐的自身提出要求,体认音乐最高意境“仁”,“仁乐合一”是儒家乐论最高层次的自觉。
“仁”是性与天道融合的真实内容[8],孔子的学说中“仁”与“礼”联系甚密,“克己复礼为仁”,即循理而行之实践活动,孔子是由“仁”到“礼”论其实践程序,而“礼乐”之不分的理论实际,使“仁”与“乐”和在了一起,成为儒家乐论追求的最高境界。劳思光先生论证“仁”作为孔子所指叙之自我境界亦可作为上述观点之佐证。[9]通过对《论语》的解读,劳先生将“仁”归摄于自我境界之以价值自觉为内容的德性我,而以生命力和生命感为内容的情义我和以知觉理解即推理活动为内容的人之我都依附于德性我,是德性我之附属。德性我之如此范定在音乐艺术活动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孔子对六乐的评价,实则是对制乐者德性的评价,“韶”之所以尽善又尽美,主要是帝舜的功德之高,周武王制作的“武”因其德性逊于舜而只能尽美;“郑声”因其不符合道德标准,而受到孔子的德性制裁,冠以“淫”这一道德意义的判断继而决定废除这种音乐,并把废存这种不合道德标准的音乐作为政府之责;这种德性我对音乐艺术的规范和要求不但体现在《论语》中,也充斥于孔子对《诗经》的搜集中,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曾经给《诗经》都配了音乐,其配乐的标准既是合于《韶》《武》《雅》《颂》,现今音乐已难觅,但从如今还保持对《诗经》的风、雅、颂的制目方式可见一斑。德性我的最高要求即是“仁”,见于孔子“仁者人也”,孔子把人的最高美德汇与仁,并且与乐相得益彰,对后世儒者的音乐理论产生重大影响,使儒家乐论既有应然之则又有了超然之境,是中国乐论自觉时期之开始。
第三 “乐以教和”:孔子乐教的伦理旨归
“无声之乐,是和之至”是徐复观站在极究之地对儒家“乐教”之所从出的思考和所立之言。[10]早在先秦,乐教因其“成教化、助人伦”的德育功能就被列入“六艺”之列作为必修科目,“和”作为音乐思想见诸于《国语·郑语》,史伯把包括音乐在内的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提炼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音乐与自然万物是相辅相生,是去同求和的“声一无听”。[11]《左转·昭公二十年》中晏婴就“和”与音乐的关系从主客体人与自然的相反相济的关系中,即肯定客体所达到的平和状态,也论及主体“心平德和”。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12]
在此,晏婴提出了“声亦如味”的重要理论,为“艺味说”在中国文艺发展史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奠定基础。“和”是此论述的主旨,不同的形式相成、相济以成乐。音乐之“和”包括“气、体、类、物、声、律、音、风、歌”等不同事物的和谐共处,和“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相对立概念的矛盾统一。音乐之“和”的最终目的则是“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由此可见,“德和”是古人对音乐美的最高要求,音乐的教化之意溢于言表,具有伦理属性的“和”是此教化的主旨,“乐以教和”的涵义透显与此。音乐之“和”在伶州鸠处则表现为“乐从和,和从平”,伶州鸠赋予“和”以“平”的审美准则,和平之声所追求的“德”音让民众听之则能生蕃殖之财,得中德之道继而宁神、合人,《国语·卷三·周语下》:
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13]
“民是以听”的音乐即是审美对象,亦是驯化民众的手段,所谓“德音不愆”,以“德”为旨的音乐能使人平和、消弭暴佞,使人与自我、他我和谐相处。“平”丰富了音乐之“和”,即无过无不及、任何一方都不过分突出自己是“和实生物”的另一重要原则。为此,作为教育实践层面的音乐既有主次之分,又有纵向过与不及的限制,二者的平衡统一促进了音乐的创新与变革。孔子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音乐的教育功用,提出“兴观群怨”等一套完整的乐教理论。兴、观、群、怨的提出基于孔子重音乐的教化作用、社会功能轻音乐的娱乐、美感作用的乐教思想。其中,具有引譬连类之职的“兴”通过对个别音乐事项的譬喻挈领普遍德性,作为乐教资源、道德规范;“观”作为诗、乐的主要作用有“观风俗之盛衰”、“观道德之状态”、“观政教之得失”之意,在孔子的乐教理论中,“观”是乐教的社会功能,音乐教育的功能即是通过观察社会的道德状态,调整用乐的规范;至于“群”,孔子把“仁”作为乐教的内容,只有宣传仁德与仁政的音乐才能交流感情,协调关系,乐之所以“可以群”,在孔子看来还表现在乐教能宣扬礼仪,使人知礼,有“礼”有“仁”的音乐能使人“和而不流”。“怨”在学界引发了诸多的争议,李泽厚先生认为“可以怨”就是肯定了艺术可以表现各种不满意、发牢骚(以符合仁为原则)的情感;[14]而蔡仲德则驳斥李的观点,认为孔子不仅并未肯定艺术表现各种不满意、发牢骚的感情,而且是恰恰是反对表现这一类感情的,痛斥“郑声淫”,主张并实践“放郑声”。[15]为何有如此截然相反之观点,很值得以后再著文研究。笔者认为,“兴观群怨”是乐教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为了教化“和”而制定的内容、规范、方法、原则等,“和”是诸多乐教思想的一个普遍性目标原则。
“以乐德教国子”的乐教思想是孔子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的“修己”之法。孔子乐教思想有其“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根据,在孔子看来,人在其本性上是相差无几的,之所以有道德品质上的差异,源于后天习俗的不同,因此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是必要之举[16]。道德教化是一个系统而繁杂的过程,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据此就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说,孔子由此把乐教作为有所成之学,置于教育之首,推动了后世乐教的发展,亦成为“乐以教和”之现代乐教观的理论渊源[17]。“乐教”理论和“和”的思想均溯源于孔子处,并继续作为现代音乐教育的核心理念并围绕着自我与他我和谐共存的主旨开展论证,因此,乐以教和将继续作为乐教的伦理旨归而迸发艺术的生命活力[18]。
以上论述,只是“文明的碎片”、“冰山的一角”,孔子的音乐思想博大精深,笔者在此仅选择与“礼”“仁”“和”相关的若干音乐论述,竭力避免以偏概全、人云亦云,若如此蜻蜓点水般的梳理和考证能为孔子音乐伦理思想的研究吸引大学界更多眼光来批评指正,则于愿足矣。
[1]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2] 王小琴.音乐伦理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3] 李泽厚.伦理学纲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4]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刷馆,2010.
[7] 黑格尔.康德哲学论述[M].商务印书馆,1962.
[8] 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9]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刷馆,2010.
[1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12](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3]尚学锋、夏德靠: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5]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16]李金善,受志敏.儒家诗教生成的礼乐政治背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36-40.
[17]李建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主体困境[J].湖南社会科学,2011,(2):1-3.
[18]唐凯麟,贺才乐.儒家诚信传统与诚信道德建设[J].湖湘论坛,2011,(3):41-44.
——长春市第一中学学校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