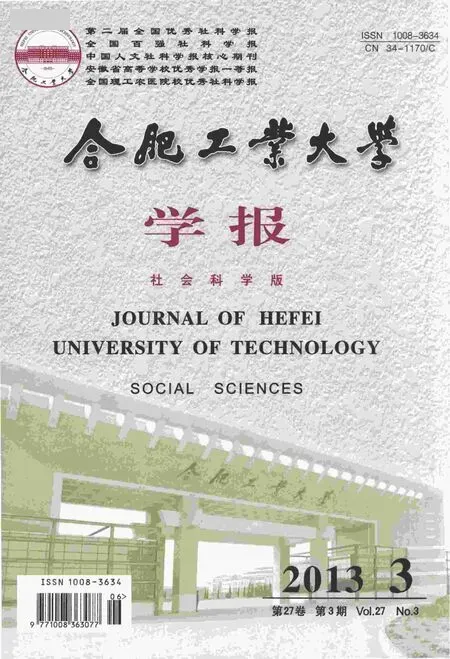论《死水微澜》的野史神韵
王 超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所谓“野史”是相对正史而言的。正史作为一种官修和集体著述,表达的是主流、正统的意识形态,所追求的是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梳理。有别于此,野史则为个人言说,或表现亲身经历或讲述道听途说之事,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野史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是对正统话语的疏离,当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对正史起着补充完善之作用。中国古典小说自产生之初便与“野史”传统密不可分。《汉书·艺文志》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小说之本源与野史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晚清以降,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获得长足发展,并孕育出相当丰硕的艺术成果。所谓小说乃“引车卖浆者之流”,竟从最边缘的民间土壤上蓬勃生长,而最终为精英文化所吸纳,顺利实现了雅俗共赏与上下合流,不可不让人喟叹历史的吊诡和神秘。现代的小说大家如鲁迅、老舍、沈从文、张恨水等,都注意汲取野史传统和民间文化中的养分;而李劼人也如这些大家一样,注重提炼小说的野史神韵。《死水微澜》虽是“大河小说”中篇幅最小、最不像历史小说的作品,却具有最高的艺术成就和最广的文学影响。它有意偏离重大社会政治事件,而以私人视角传递和表达个人经验。李劼人曾如此介绍小说内容:“背景为成都,时代为光绪庚子年之前后,内容系描写当时之社会生活,洋货势力逐渐浸入,教会之侵掠人民。对西人之盲目,官绅之昏庸腐败,礼教之无耻,哥老之横行,官与民之隔膜,以及民国伟人之出身。”[1]乍一看,时代背景、社会全貌都被他囊括笔下,但小说之妙在于“咸以侧笔出之,绝不讥讽,亦绝不将现代思想强古人有之”。有别于传统正史,有别于宏大叙事,《死水微澜》关注的是凡夫俗妇的生存境遇和心灵激荡,小说以私人化的视角传递和表达着作家的历史观。
一、乡下女人的情爱秘史
《死水微澜》以村妇匹夫、妓女嫖客、黑帮强盗之间的恩怨纠纷与情感纠葛为叙事线索。相较于波澜壮阔的社会风云来说,这些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作品正透过这“冰山一角”,巧妙地折射出所谓的“痼弊时代”。而那个“死水”中泛有“微澜”的天回镇可以说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一个剪影。邓幺姑显然是小说的叙述焦点,历史风云和社会变迁不过是她的生存背景。不同于才子佳人中的模范佳人,不同于传统旧式的祥林嫂,不同于出走的娜拉,邓幺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小说通过对她的一幕幕寻情记的全景述说来展示“乡下女人的情爱秘史”。
邓幺姑本是务农人家的女儿,却是丫头身子小姐命。她“自幼爱好,粗活路不做,细活路却是很行的”①文中引用小说内容部分出自华厦出版社2009年版《死水微澜》,以下同。。而父母更是对其爱护有加,从来不让她喂猪、织布。邓幺姑第一次对情爱的追求表现于婚姻的自主意识。邻居韩二奶奶对成都的夸大美化,引起了邓幺姑对繁华都市的向往,于是成都便成了幺姑认为的她的最好的归宿地。即使后来韩二奶奶早亡,她也没有放弃嫁去城市的决心。邓幺姑终于成了兴顺号的掌柜娘,虽然这与想象仍有差距,但也是她迈向黄金梦想的第一步。日子久了,邓幺姑渐渐不满与蔡傻子过着无话可说、平庸无趣的生活。她无不羡慕地对刘三金说:“你们总走了些地方,见了些世面,虽说是人不合意,总算快活过来,总也得过别一些人的爱!”她更坦言,在嫁给蔡傻子之时,就爱上了见多识广的罗歪嘴。而后邓幺姑和罗歪嘴能走到一起自然有刘三金“拉皮条”之功,但实际上邓幺姑的主动仍是主导原因。她既能在男人摆龙门阵时大骂洋人,颇具见识和气概;又在生活细节上对罗歪嘴给予关心体贴,有着女性的细致温柔。这就无怪乎向来视女人为玩物的罗歪嘴都要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这场发生在弟妹和大伯之间的男欢女爱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对此,作品并没有以道德偏见来口诛笔伐,也没有流于世俗色情的书写,反而以热情饱满的笔触抒写着男女之间的纯粹情爱。
经过李劼人的艺术提纯,邓幺姑表现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女人。她顺从内心的声音——人为情死,追求最本真的生命体验,以爱的真诚对抗世俗的虚伪。李劼人对邓幺姑的塑造建立在“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他曾说过,这类女性“我看的很多;很亲切。她们的生活、思想、内心、境遇我都熟悉”。而法国的留学经历给予李劼人跳出传统观念的契机和参照,那种“尊重真实的爱情,并反对世俗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反对结婚后两方爱情已变,然犹为法律及风俗所拘非不可的苦恼”的主张深深影响了他。故而,邓幺姑追情逐爱的过程都变得可以理解,她既不愿被世俗偏见所束缚,也不会为无爱婚姻献祭,更难得的是她不愿装模作样,而敢于当众表达对罗歪嘴的爱。邓幺姑对情爱痛快淋漓的追求,带着现代性的要求回到“人”本身的诗意召唤。这个“人”显然不是大写的、理性的人,而是个体的、感性的人。于是,作家在对这几位“自然人”的艺术表现中暂时忘记了他的士大夫地位,忘记了他以小说批判社会的壮志情怀,当然也暂时松懈了他的道德理念与矜持,完全沉浸到充分自由与自然的艺术境地之中。”[2]李劼人塑造了邓幺姑,而邓幺姑可以说成就了《死水微澜》,诠释出艺术的、人性的“永恒价值”。
当然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面对一系列的变故,祥林嫂是无法选择命运而只能走向死亡,娜拉则可能重新投入到男性的怀抱。在风云际会的时代,中国女性的出路却在邓幺姑这里有了另一种回答,她再次做出选择——嫁给土粮户顾天成。她想通过这场改嫁来彻底改变命运,以个人感情换取各种现实的利益。从少女时期的物质憧憬,到成为蔡大嫂后婚姻的破灭和内心的躁动,再到成为罗歪嘴心灵相契的伴侣,最后在外力的冲击下成为大粮户家的顾三奶奶,邓幺姑这一生展现了女性爱欲追逐的旅程。作者给予邓幺姑充分的自由精神和大胆强悍的性格,并在整部作品中透露出强烈的世俗享乐色彩。在和罗歪嘴的交往中,她能表现出最彻底最热烈的感情。在罗歪嘴逃亡之后,她重情重义却不为其所困,其叛逆和改嫁的行为越发彰显其独立个性。从这个层面来看,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女人自主意识的成长史。
二、日常生活中的心灵史
对于日常生活,赫勒将其定义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3]。如此概念化的界定着实玄奥,令人费解,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常识对之做一通俗解释:日常生活无非就是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烟火人气之类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李劼人很擅长讲故事,他将各色人物置入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既有对作为大背景的城镇、时代特征的纪实,又有对推向前台实景的日常生活的虚构,读来让人甚为亲切。郭沫若就曾这样说过:“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4]衣食住行等琐碎的日常生活形象建构了小说独特的审美空间,同时也暗示着个人在历史洪流面前的心灵激荡和变化。
《死水微澜》对邓幺姑的日常生活着墨最多。邓幺姑七岁就开始缠脚,到十二岁完成,期间常常痛得半夜都不能睡着,连她母亲都于心不忍,她却宣誓般地说:“为啥乡下人的脚,就不该缠小?我偏要缠,偏要缠!”“三寸金莲”之说已然遭到现代社会的摒弃,但邓幺姑却仍对此奉若圭泉。与之相呼应的另一个细节是,邓幺姑有心“闹嫁”,最大的梦想就是嫁去成都大户人家,即便做小老婆也可以。但是这个梦想以父母的不同意而告终。而此时邓幺姑的反应只是心急,她伤心、哭泣,却从不敢让其他人知晓。等到她偷听到要嫁与蔡顺兴做掌柜娘,心中十分满意。邓幺姑这些反应都是“照规矩”行事,“乡间诚然不比城市拘泥,务农人家诚然不比仕宦人家讲礼,但是在说亲之际,要姑娘本身出来有所主张,这似乎也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读到此处不禁让人顿生疑窦:如此个性大胆的邓幺姑为何纠缠在这些“传统规矩”上呢?只有重新回到晚清那个痼闭时代,回到内陆四川,才能对此一问题心领神会。
晚晴以降,中国社会逐渐打开了对外看世界的眼光,但是,这个时代还远远未达到像五四时期那样对现代、理性的自觉追求,可以说处在“前现代”的状态。而在偏僻的西南内陆,其自给自足农业文明的性质仍未曾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也未得以从根本上的动摇。与之相伴而生的就是愚昧落后的文化思想观念。这正是小说的题眼之一——死水。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上节提出的疑问。邓幺姑虽然身上具有强悍的原始生命力,但是作为一个在传统封建社会、在封闭的盆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并不具备自觉反抗旧社会旧传统的意识,反而承袭了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的一面。作家所谓的“礼教之无聊”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而小说中对顾三奶奶(顾大成的前妻)的日常情状之刻画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她是“如此的一个合规的乡妇”,“除了对自己极其刻苦,害了病,连药都舍不得吃的而外,还有一桩好处,就是‘无违夫子’四字。”她鼓励丈夫纳小老婆,自愿成为出气筒,如此“尽职、省俭”的女人最后因为一只母鸡的意气之争而丧命,真是可怜可悲。病危之中,她还心心念念要夺回老母鸡,不是为了给自己蒸药鸡,而完全是为了节省持家。这一幕与葛朗台临死前之举同具讽刺意味,但不屑的哂笑并不足以概括阅读者的感受。在此,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礼教压抑下的血泪史,更看到了个人在历史洪流面前沉寂的精神状态,犹如一潭难以流变的死水。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等各方面都受到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直接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微澜”是“死水”般的近代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前奏。彼一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就在“微澜”中展开。郝公馆是一户半官半绅的人家,“生活方式虽然率由旧章,而到底在物质上,都掺进了不少新奇的东西”。当大保险洋灯、照相机、留声机器等西洋物品进入郝家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逐渐打开了对外看世界的眼光,觉得“洋人到底也有可令人佩服的地方”。这些都是“暴风雨前”的郝公馆和当时几个所谓志士思想发生巨变的基础。当然,邓幺姑显然是这个思想转折期的最典型的形象。在这个“前现代”的特殊社会时期,邓幺姑对情爱的追逐显然带有物质功利的生活逻辑和务实色彩,且这一变化在其成为顾三奶奶之后更为显著。后期邓幺姑的打扮更为新潮,那些俏丽的挽发、风致的衣裳都是从“洋婆子”那里学来的,其日常生活细节蕴含着中国新旧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全部生动内涵。殖民者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不断影响着老中国儿女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他们的思想上激起了复杂的“微澜”。也就是说,西方近现代文明正在冲击封建蒙昧主义的“死水”,它使一部分人的心灵起了新变。《死水微澜》生动记录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从而反映了“前现代”社会里中国普通百姓的心灵、精神的变化。
三、地方话语里的风俗史
地域特色是《死水微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郭沫若曾感慨道:“例如青羊宫看花会,草堂寺喂鱼,劝业场吃茶,望江楼饮酒,铁路公司听演说流泪,后院讲堂骂土端公……这些几乎没入了忘却的深渊里的过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复活了转来。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的。”[4]从饮食服饰到瓦屋建筑,从社会组织到民间话语,从民俗信仰到风俗活动,李劼人将所有的人和事都放置、都被浸润在川西的色彩之中。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对川西的地方特色实现了全景式的描绘,俨然是小说版的近代《华阳国志》。
小说一开始就详细介绍了天回镇。天回镇不只是个地域名词,还具有浓重的川西特色。等到赶集的日子,它的地方特色就更加突出。“赶场是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所能听到的全是人声”。与这沸反盈天、轰轰烈烈的人声形成对比的是,人们却用手语打哑谜似地讨价还价,这是四川人尤其是川西坝人特有的交流方式。再譬如“赶青羊宫”,作者先对青羊宫做了细致、精准的刻画,其地理方位、建筑年代、结构造型等都一一评述。另外还特别用心地介绍了摸羊子的神话,在提供地方风物的历史掌故的同时,为古迹涂上一层浓重的地方色彩。而“赶青羊宫”的习俗,竟阶层有别。附近的乡民大抵来此烧香、抽签;而城内的大户人家则要推算好“子丑寅卯”才热闹出行郊游。像郭沫若这些“局内人”于此便能感受一番故乡之情,而局外人亦能由此领略四川独特的乡土风情。
论及小说中最具川西风味的地方,便在人们的你来我往、一言一语之中。四川人特别喜爱讲故事、扯闲话,这种交流方式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摆龙门阵。“龙门阵艺术的显著特征就是以故事讲述为主……同时又包含了若干自由穿插的叙述手段,将故事向着前后左右的方向扩宽开来,以丰富我们的见闻,它以‘说书’的表述方式颇为相似,却又不局限于‘说书’的独白模式。”[5]李劼人熟谙其道,对此方式的运用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给天回镇的人打上了川西的地方烙印。邓幺姑的一生和龙门阵有着莫大关系,她因为听韩二奶奶的摆龙门阵而向往繁华都市、因为喜欢罗歪嘴的龙门阵而爱上其人、因为与刘三金摆龙门阵而彻底激发了自由强悍的天性。另外,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说袍哥活动、洋教盛行、义和团、百日维新、红灯教、光绪帝出逃等等,差不多都被各色人物用摆龙门阵的方式说出来。通过这种散漫的聊天方式,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似乎消散了原有的严肃感和沉重感,竟然演变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可有可无的谈资。此外,小说还特别善用四川方言叙述,让人在阅读中享受川音川语的劲道和风味,大量方言俗语用之于人物,既能看出教民、官绅、兵痞、妓女等说话者的各色身份,又能劲道地传达出巴蜀文化风气。在这个还处在“前现代”时期的天回镇,白话文、普通话还远未普及,加之主角人物的身份要求,李劼人采用民间话语叙述可以说“地方色彩极浓,而又不违时代性”。
《死水微澜》是作者宏大写作计划中的一个小“序曲”,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大幕尚未拉开,故而李劼人才能沉浸在一种彻底放松的状态,生动地传达出极具个人色彩的认识。在历史的表述上,作品没有刻意追求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记录,而以不同于正史的视角来描述历史的一角、触摸被忽略的人和事。
[1]李劼人.《死水微澜》前记[C]//李劼人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2]沈庆利.问解李劼人难题[J].当代文坛,2011,(1):23-28.
[3]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3.
[4]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C]//李劼人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5]李 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18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