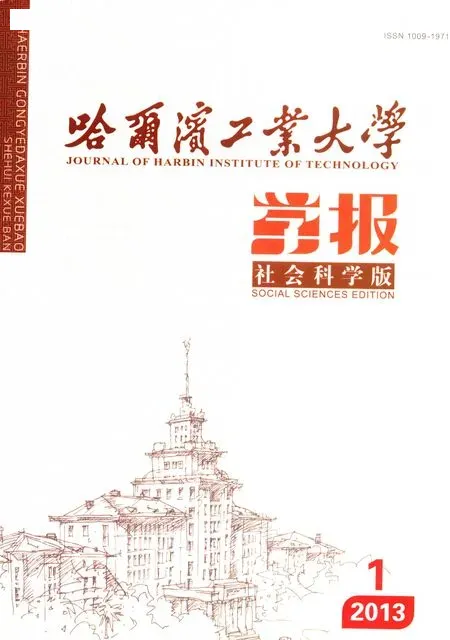俄罗斯文化对新时期东北文学的影响
金 钢
(1.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哈尔滨150025;2.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哈尔滨150018)
20世纪以来,在中国新文学萌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俄苏文学艺术和苏联政治理念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北新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俄苏文学的接受过程大体与新文学主流保持一致,所不同的在于东北地区由于地缘上的特殊性而受到了俄罗斯文化的广泛影响,这使得东北新文学在接受俄苏文学影响的过程中具有了自身的独特性:俄罗斯文化因素(而不仅仅是俄苏文学和苏联政治理念)深入而连贯地蕴涵于东北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而这种影响的连贯性在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新时期东北文学的走向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中、苏两国执政党交恶,中国开展“反修”运动,苏联文学也被视为“修正主义”文学而受到错误的批判,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中成为禁书。但是,在这一时期苏俄文学作品并没有在民间消失,不少青年在“文革”中的地下读书活动中接触到的主要文学作品仍然是来自苏俄的。张抗抗曾说:“我本人就是读着苏俄文学长大的。在我整个少年青年的成长时期,几乎读遍了俄罗斯和前苏联最有影响的小说、戏剧与散文。我们熟知前苏联以及俄国最优秀的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家与作品,滋养了整整两代中国人。从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里、契诃夫一直到肖洛霍夫,他们所提供的思想与艺术养料,曾经那样强烈地唤起过我的激情与良知。”[1]可以说,在“文革”的文化沙漠中,苏俄文学作品较之中国的红色经典更加受青年们所喜爱,苏俄文学深沉而又感伤的氛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那一代人。所以,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上的“伤痕”、“反思”、“寻根”等思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与苏联“解冻”后文学的相似之处。不过,中国文坛的环境由过度压抑到宽松的逆反,使得西方文艺思潮大规模涌入,文坛上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创新探索层出不穷,“现代派”、“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冒出一些标新立异的艺术旗号,形成了“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局面。
在新时期的东北文坛,文学的发展既受到主流文学思潮的冲击,又具有自身的特色;既有金河、邓刚、白天光、谢有鄞为代表的乡土寻根文学,张抗抗、梁晓声为代表的知青文学,马原、洪峰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又有阿成、迟子建等独具个性的创作,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创作格局。新时期东北文学可说是继现代的东北作家群之后又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探讨俄罗斯文化和文学对其的影响,首先需要理清其发展的脉络和走向。新时期东北文坛的大多数作家都是以东北地区历史文化的变迁和人民的生存境遇为创作源泉的,并且在理论上提出了“东北文学”的概念。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谈道:“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2]2随即一些作家也纷纷撰文予以响应,一时间在文学界出现了“寻根”的热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东北作家金河在《鸭绿江》上相继刊发了关于“东北文学”的几则断想,提出了“东北文学”的口号,倡导建构“有特色的东北文学”①1985—1986年间,金河在《鸭绿江》先后发表了四篇关于“东北文学”的断想,分别为:《东北的“文化土层”——“东北文学”断想之一》(《鸭绿江》1985年第10期)、《假如来个外星人——“东北文学”断想之二》(《鸭绿江》1985年第11期)、《掬一捧长江水——“东北文学”断想之三》(《鸭绿江》1985年第12期)、《要识庐山多看山——“东北文学”断想之四》(《鸭绿江》1986年第4期)。。这引起了东北作家和学者的热烈讨论,《鸭绿江》连续几期刊发了相关评论文章,大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赞成者认为:“历史上的东北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其中南北朝时的鲜卑、唐代的高丽、唐末和宋代的契丹、宋末的女真、明末和清代的满族等等,都曾经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些民族大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理想、典章制度……即大都具有独特的文化。正是这些民族的文化同汉文化的融合构成了东北文化的特殊类型。”这种“特殊类型”就是东北历史上形成的“尚武、尚力的文化精神”,在“东北作家群”笔下表现为“对力的讴歌和礼赞,是对力的追求和向往,是对力的抒发和伸张”。并谈到“这种特异的文化精神”对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而“导致的中华民族性格的软化”的现象能“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这即是“当年‘东北作家群’崛起文坛的意义,也是我们今天创议东北文学的意义”[3]。相似的观点还认为,“‘东北文学’口号的提出,还有助于我们正视历史和现实,提高独特的审视生活、理解生活的自觉性,创作出真正独具特色的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文学作品来”[4]。与上述不同的观点则认为,“有没有实际形成‘东北文学’的可能”,“值得研究”。“代表作家作品”和“共同的文学观念”是一种标志,“没有这种标志,人们很难具体把握你所提倡的是什么东西”。并认为“东北作家间缺少一种特有的共同的文学观念、理论主张和美学追求,这也是‘东北文学’难以成立的事实之一”[5]。
今天再看当年“东北文学”口号的提出,单方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有失偏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口号的提出并非狭隘的地方观念所致,而是在世界文化浪潮的影响下民族文化自省意识的表现,正如韩少功《文学的“根”》文中所言:“这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2]3可以说,“东北文学”口号的提出,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地域文化文学意识的觉醒,使许多作家由原来不自觉地表现地域文化的特征到自觉地开掘地域文化的富矿,进而将东北地域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无疑对新时期东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提供的实绩来看,新时期东北文学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乡土文学,存在地域观察视点差异的知青文学,包含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因素的新潮文学,独具特色的不可归为任何流派的作家的个体文学。而这四方面的文学创作所围绕的核心和源泉就是东北地域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其发展的焦点是将这片地域历史积淀的多元文化,有意识地与现代文明和最新的文化意识交融起来,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存状况给予悉心关注和深入思考,以现代审美观点去发掘和熔铸民族世代相袭生生不已的伟大生命力和民族精魂,在吸纳了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的同时,保持了对本土文化之根的坚守,从而具备了深厚的思想内涵,揭示出新时期东北文学粗犷、浑厚而又浪漫、瑰丽的地域特色。
二、俄罗斯文学与新时期东北文学的思想内涵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各种文化思潮蜂拥而入,意识流、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批评、现象学、阐释学等多种文艺思潮纷纷闪亮登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各种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时期东北文学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这些文艺思潮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文本形式和叙事技巧上。在思想内涵方面,新时期东北文学并没有脱离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也与苏联“解冻”思潮后的文学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关注
“解冻”思潮中,苏联作家们批判了40年代末以来四处泛滥的“无冲突论”,恢复了俄苏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涌现出一批敢于揭露矛盾、反映现实的好作品。特别是农村题材的作品,一扫过去的“粉饰”习气,大胆揭露矛盾,针砭时弊,积极干预生活进程,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力量。很快,这种以暴露和批判社会消极现象为主的创作趋势扩展到苏联文学之中,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6]。而新时期的东北作家们也对他们亲历的岁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无论是乡土文学、知青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对之前和当下东北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探讨。万捷的长篇小说《叩拜黑土地》在浓郁的地域风情的描绘中对东北乡村生活状况给予了深刻的揭示。这部长篇聚焦三中全会前后的东北农村生存现实,对一个伟大时代转折之际农村各色人等的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对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的农村生存状态和人们的行为模式、精神世界作了多侧面的叙写,表现了历史的转折带给农村的巨变。“大锅饭”时期,农村中好吃懒做之徒横行,他们看乡、村领导的眼色行事,“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实行土地承包后,农民们拥有了自己的承包土地,农民的生活与脚下的黑土地紧密结合起来,农民的主体意识显现出来,个性获得前所未有的张扬。
知青生活的浪漫与激情、挫折与磨难使得知青一代人更为喜爱、更能理解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使得知青文学的内涵更为贴近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新时期东北的知青文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代人心中难以抚平的创伤,可以看到一代人为青春、理想献身的悲壮和与命运抗衡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也可以看到对社会、人性中假丑恶的揭露和直面现实的忧患情怀。早在80年代中期,梁晓声就推出了中篇小说《溃疡》,以犀利的文笔和形象的刻画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的滋生给予了激烈的抨击。之后相继推出的《冰坝》、《军鸽》、《预阵》、《喋血》等中篇小说,对时代大潮下各阶层人的生活状态作了真实的富于生活质感的描述。《冰坝》记述了一个“丧失了普遍的群体意识和责任感的村庄”在自然灾难降临时付出的沉重代价。在翟老松的大火与翟茂生的炮声中,冰坝消融了,村民得救了。然而凝结在人们心头的冰坝是否也释然了呢?可悲的是翟老松、翟茂生和芋子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并未从根本上达到警示人们的作用。村民们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将救灾款包括为三位死者立碑的四千元钱一分而光后作鸟兽散。翟村的“钟”的确早已失去了警示的权威性,作家却在字里行间,以力透纸背的深沉忧患敲响了世纪末的警示之钟。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不但对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物质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对精神世界也产生了激烈的撞击。东北历史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东北人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呈现出复杂的变化状态,关仁山、孙春平等作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探索和透视。由于诸多地理历史的因素,铸就了东北人与其广袤、雄奇的自然地理特征颇为吻合的粗犷豪爽热情的性格特征和诚实守信、团结互助的世风民习。千百年来,这些均被视为传统美德为世人所称道。如今这一切都在受到不断的撞击与叩问。孙春平的中篇小说《轱辘吱嘎》中年轻美丽的豆腐坊女老板谷佩玉为其善良热情、诚实守信吃尽了苦头,她纯朴的美德不断成为他人设置陷阱的契机。“使坏”频频得手的王吉琴也并未因遭致村民的白眼与谴责而善罢甘休,而是随着她境遇的改变而愈加变得无耻与疯狂。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既属于文化又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迫切问题,即面对刚刚转型的还没有完全进入有序状态的市场经济,仅仅靠传统的道德良知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了。
(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大自然历来是俄罗斯文学关注的焦点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可以体察到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面前应当承担的责任,成为人们认真思考的主题。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等作品都谴责了摧残大自然的暴行,赞美了生命与自然的永恒交融。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新时期东北文学之中,东北的大荒原、大林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的大潮之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只注重经济收益,而没有看到环境破坏问题的严重性,对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前“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富饶情景早已变成了遥远的传说。迟子建曾这样写道:“俄罗斯的文学,根植于广袤的森林和草原,被细雨和飞雪萦绕,朴素、深沉、静美。……俄罗斯的作家,无不热爱着这片温热而寒冷的土地,他们以深切的人道关怀和批判精神,把所经历的时代的种种苦难和不平、把人性中的肮脏和残忍深刻地揭示出来。同时,他们还以忧愁的情怀,抒发了对祖国的爱,对人性之美的追求和向往。这些质量,正是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的作家身上所欠缺的。”[7]而在迟子建的创作路程中,以忧伤的情怀去抒写人性之美与自然伟力正是她一直以来的文学追求。在她的作品里,自然是人和谐而富有诗意的家园,它和人构成了一个神圣的整体,乡民们也因为和自然的契合而有了惊人的凝聚力和敏锐的生命感觉。
吉林作家杨廷玉的两部长篇小说《危城》、《不废江河》,也都表现了绿色环保的主题,将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场景和生活画面中,在纵横交错的关系、矛盾、情感纠葛中刻画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叙写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引发的种种矛盾冲突,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环境污染的渊源是人文环境的污染,急切地呼吁人们要“克制与生俱来的贪欲,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敬重人类的母亲大自然,为人类的繁衍生息,留下绿地,留下蓝天,留下恬静优美的家园”[8]269。表现出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危城》题记所写的:“重叠的时空背景下凸现生存的窘迫,于那灵魂的挣扎中发出焦灼的呐喊。”[8]1人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如何在大自然中诗意地栖居这一主题,在俄罗斯与东北这样大自然的伟力表现得比较充分的地域更易于为文学所关注。怎样的生存方式才是正当的,如何处理经济、科技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命题。
(三)对生与死、罪与罚的宗教性道德追问
宗教主题的宏大深邃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所有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俄罗斯作家,为穿过肉体显示灵魂,除了灵魂还是灵魂。”“俄罗斯人就是这样,他们总是要把生命的意义追问到死,拷问出自己灵魂的洁白来,而这一切都脱离不开宗教的理念”[9]。而在新时期东北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优秀的作家如洪峰、迟子建等人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一种对生与死、罪与罚的宗教性道德追问,一种对尘世生活的眷恋与拒斥、对善的圆满追求的渴望和无法真正实现的绝望所产生的痛苦和矛盾。
洪峰创作的一个特异之处就在于他对儒家文化中所缺少的罪与罚主题的思考和探索。关于原罪,在我们这个以儒家文化为特征的国家里,是一个比较陌生和隔膜的概念。社会的人伦关系成为人基本的行为准则,这时,我们是不承认罪的,忽略和遗忘掉人的原罪。我们会承认恶,而恶则是隶属于阶级的集团的,它不需要个人担待,而罪则需要个人的承担。中国人很容易地接受了善与恶的概念,而回避掉罪与罚的意识。中国人承认自己是社会的政治的人,而很少注重自己又是自然的个性化的人,于是,他们对自我历来是采取遗忘和悬置的态度。天理是永远高于人欲之上的。而在洪峰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罪与罚”的追问,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现代社会中魔界与深渊的横陈,现代人情感的放逐与漂泊,以及那在劫难逃的宿命般的上帝与魔鬼的同时召唤等等,都重重地敲击着读者的灵魂。他在中篇小说《第六天的下午或晚上》里探问道:“人应该按什么原则活着?”可同时“我知道,我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别人或许能够中道而返,但我不能。我预感到生命早就安排好了我的一切”。因为“我不可能没罪”,上帝曾经指明了人的必然处境:“你们若瞎了眼,便没有罪了。”“我知道我的世界永远一片黑暗充斥着罪恶。我还深信我不能不沿着黑暗罪恶的歧路继续前行”[10]。“我”与珠蓝,与M女士,与Z姑娘,男人和女人都在试探着,在黑暗的歧路上用肉体作为前进的导向,在这里凸现出来的是人的原欲。不过仅用原欲并不能完全揭示罪的内涵。在《离乡》中,洪峰进一步诠释了罪与罚。这篇小说一改往日的潇洒自若而显出忧郁和顿挫,“你将化成尘埃的一分子永远漂浮空中失去家园”。“我努力让自己安静。我要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忏悔的故事。“我”曾打了一个热爱“我”而“我”并不热爱的姑娘。这是一种罪:破坏和亵渎一个人美好的感情,把一个人推向深渊。而内省与忏悔即是罚,是追求自我的超越与完善的第一步。有时我们的罪并不是生命的张狂、恣意妄为和野性,而是在传统的正常的社会秩序面前的萎缩。
综上可以看出,在新时期东北文学的思想内涵中,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和关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和对生与死、罪与罚的宗教性道德追问,其关注的对象与思考的理路与俄罗斯文学有诸多相通之处。在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新时期东北文学这种发展状况可以说有俄罗斯文学在东北新文学的进程中影响的惯性发展的因素,不过,更说明了东北文学由于地域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与俄罗斯文学的天然亲近感。
三、蕴涵俄罗斯文化因素的地域文化的重新展示
近代以来的东北地域文化,是本土原始文化与中原文化互动融合,加之俄日外来文化影响所形成的,是一种以汉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中的俄罗斯文化因素,在现代东北文学中一直有所显现。不过,新时期以前的东北文学由于启蒙救亡等政治性目的,对这种异域文化风情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展现,而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文学中,则出现了对其有意识的表现和对这种历史文化因素的深入开掘。
在东北地区,俄罗斯文化风味最浓的城市当属哈尔滨。而对这座城市的俄罗斯文化风味表现最为用力的作家就是阿成。阿成的创作非常关注本土的风俗文化,他在小说《胡天胡地风骚》中写道:“特快列车迅速而有力地在北满大地上行进。火车轮下的铁路,已有近百年的寿命了。它是由清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俄人在莫斯科签订建筑的(说是李鸿章受了俄人三百万卢布的贿赂),它与旧俄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连在一起,成为贯通欧亚大陆的桥梁。肃慎子孙的某些俄人之风,也包括这一城市的某些欧式建筑,都是与这铁路有关的。火车上,常见乘务员推着食品车,卖俄式的列巴、里道斯和比瓦(面包、灌肠和啤酒)。在全国,可以相信只有哈尔滨的灌肠,才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风味。”[11]阿成在这不长的一段叙写中,就将一座城市的历史和风情简约地勾勒出来。而在他的小说《间谍》中,则介绍了哈尔滨的侨民情况。[12]从阿成的创作中,可以真切地看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俄罗斯文化风味,而这种异国风味的描写也给阿成的作品增添了岁月流淌的历史苍凉感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在中俄边境地带,民间的俄罗斯文化风味更浓。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我”——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之口讲述了活动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部落的兴衰故事。河的左岸就是俄国,鄂温克人和俄国人有着频繁的接触。他们和俄国安达(商人)交易生活用品等。伊万的老婆娜杰什卡就是他用兽皮从俄国安达那里换回来的。不过,日寇入侵时,娜杰什卡带着他们的孩子吉兰特和娜拉又逃回了左岸。而“在我眼里,河流就是河流,不分什么左岸右岸的。你就看河岸上的篝火吧,它虽然燃烧在右岸,但它把左岸的雪野也映红了”[13]。鄂温克人与俄国人既有战争,又有贸易、交流,边境地带的文化和人民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并不严格地分“左岸右岸”。
杨利民、王立纯合著的《北方故事》是一部纯朴、浑厚、具有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东北多元文化的特质在小说中得到了多侧面的展示,草原文化、俄罗斯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人物命运的变化中渗透交融。小说中描写了一个颇具魅力的俄罗斯姑娘叶莲娜,她给放马营带来了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她到金铁匠家不久,就撺掇金铁匠“在铁匠炉旁修了一个烤炉用来烤面包”,引得村里人都来看稀奇。没过几天,她“又张罗改房子,在墙外罩上木板,房顶做成俄式尖顶,房上还装一只神气活现的风信鸡”[14]。她苦难的身世与遭遇,她的美丽、善良、勤劳,无不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她充满了同情和喜爱。她与金铁匠、二江的婚姻爱情交织着浪漫与凄美的情愫。他们“拉帮套”的生存状态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东北地区缺少中原几千年一脉相承的伦理文化传统,人们对“拉帮套”的生存方式比较宽容,而且俄罗斯姑娘叶莲娜受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很少,她对金铁匠是感激,和二江才是真心的相爱。事实证明,她和二江的婚姻虽然不合理法,却是洪家三兄弟中最为和谐美满的一对。这不能说不是对封建礼教的讽刺和批判。可悲的是,她和她深爱的二江都没能逃过日寇的屠杀,她带着她唯一的奶牛在草地上采花的时候,被日寇罪恶的子弹击中,永久地融入了这块土地。作家倾注笔力将这位异国姑娘刻画得异常美丽生动。
综上,新时期东北文学更加注重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思考和开掘。半个世纪以来,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共同的社会发展格局和文明进程似乎使东北的多元文化的个性特征逐渐弱化,但仔细观察,仍可感受到漫长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并见诸人们的生活与行为方式之中。新时期东北作家对具有俄罗斯文化因素的地域风情的描写:一方面,表明了东北地域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能够吸纳俄罗斯文化中的智慧和美德,为东北文化增添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也是对东北地域历史的追溯和关注,而关注历史的目的正在于把握现在。
总之,俄罗斯文化对东北新文学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一以贯之的动态过程,虽然受历史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影响,东北新文学对俄罗斯文化的接受角度和接受范围有所不同,但这种影响一直都没有间断。新时期以来,在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文学创作异彩纷呈的情况下,东北文学发展的路向更为贴近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出现了对本土地域文化中俄罗斯文化因素的有意识的描绘,对其生成原因也进行了自主的探索,这应该是新时期东北文学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学的一个独特之处。吸收了俄罗斯文化新鲜血液的东北文学以其异质文化特色和个性丰富了新时期的中国文坛。
[1]张抗抗.东北文化中的俄罗斯情结[J].作家,2003,(10):20.
[2]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3]李兴武.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创议“东北文学”之我见[J].鸭绿江,1986,(5):71-72.
[4]荒原.“东北文学”可行说略[J].鸭绿江,1986,(6):73.
[5]尹权宇.也谈“东北文学”[J].鸭绿江,1986,(5):74.
[6]李毓榛.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5.
[7]迟子建.那些不死的魂灵啊[N].中华读书报,2006-08-23.
[8]杨廷玉.危城[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9]金亚娜,等.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1.
[10]洪峰.重返家园[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430
[11]阿成.欧阳江水绿[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35.
[12]阿成.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290.
[1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12.
[14]杨利民,王立纯.北方故事[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118.